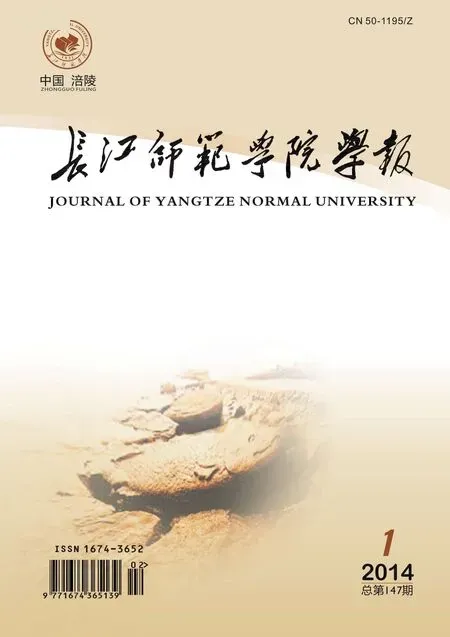論陳學昭早期文學創作中的女性意識
王俊虎,鄭瑩瑩
(延安大學 文學院,陜西 延安 716000)
論陳學昭早期文學創作中的女性意識
王俊虎,鄭瑩瑩
(延安大學 文學院,陜西 延安 716000)
陳學昭作為中國女性解放的先驅,她初登文壇就表現出了對女性命運的極大關注。她早期的文學創作可以看做是 “五四”時期覺醒女性的悲鳴,她以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和生活經歷為素材,塑造了眾多在 “五四”時代精神的感召下追求獨立自由,但最終卻陷入苦悶、彷徨,甚至無路可走的具有鮮明個性特征的女性形象群體,以此來批判和嘲諷腐朽墮落的男權社會,解構男權婚戀神話,揭露黑暗的社會對女性的禁錮和戕害,將鮮明的女性獨立意識融入到自己早期的文學創作,為在男權、族權、夫權、父權、神權等壓迫蹂躪下的眾多女性喊出了獲取解放、獨立、自由的心聲。
陳學昭;文學創作;女性意識;男權;時代女性
千百年來,在封建宗法制度相當完備的舊中國,女性一直被視為男性的附屬品而并非獨立的個體存在,她們是被忽視、壓迫、奴役的弱勢群體。對于這樣的境況與待遇,她們自身似乎已經習慣或者認命,“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傳統倫理道德讓她們一生都致力于做一個 “賢妻良母”,將嫁人、生育作為自己最大的人生理想,作為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唯一途徑。縱覽中國古代文學史,不難發現,女性寫作多是自我的傾訴和吟唱,抒發內心的閑愁哀怨。而 “五四”思想的啟蒙,使女性從沒有自我意識到發現自我,她們渴望擺脫舊禮教、舊道德強加在她們身上的桎梏,渴望表現自我、實現自我。在這樣的時代驅使下,一批受過正規教育的知識女性 “浮出了歷史地表”,開始書寫婦女在家庭、社會中所遭受的 “非人”待遇,以表達對黑暗社會的不滿和憎惡,對男權中心主義的蔑視和抨擊,對舊禮教、舊道德的抗爭和反叛。
陳學昭就是其中的一位,雖沒有同時期的冰心、廬隱名氣大,但在她的作品中所蘊含的女性意識卻是大膽的、超前的,即使在21世紀的今天也依然具有現實意義。陳學昭,原名淑英、淑章,1906年出生于浙江海寧的一個小知識分子家庭。因家中藏書較多,她自小就閱讀了 《史記》、《資治通鑒》、《綱鑒易知錄》,并在母親的幫助下,偷偷閱讀了 《紅樓夢》、《水滸傳》、《西廂記》等古典文學著作。也是因為喜歡學習 《昭明文選》,便有了后來的筆名 “學昭”。父親在她七歲時便離世,哥哥們對她要求極嚴,動輒責罰打罵,母親作為傳統的家庭婦女生性懦弱,面對哥哥對她的欺辱與打罵,母親只能偷偷地流淚。這樣的生活環境塑造了陳學昭孤傲、倔強、清高的個性氣質,而這樣的性格對她后來的生活和文學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22年,年僅17歲的她孤身一人來到上海,開始了長達大半個世紀的孤旅漂泊生活。1923年冬,陳學昭以一篇名為《我所希望的新婦女》的文章受到時任 《時報》主筆的戈公振的青睞,并特地寫信鼓勵她多多地寫作,至此陳學昭開始了她的寫作生涯。
縱觀陳學昭的文學創作生涯,其按照作品創作風格以陳學昭抵達延安為界分為前后兩期,這里側重從陳學昭到延安前的文學創作入手,探討其中蘊含的女性意識。縱覽她早期的文學創作,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從初涉文壇就表現出了對女性生存現狀及前途命運的極大關注,她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了對個性解放、獨立自主的不懈追求,對封建男權、族權、夫權、父權、神權給予了辛辣的諷刺,并以獨特的女性視覺與生命體驗進行文學創作,表現出那個時代女性內心的苦悶、猶豫和彷徨。
一、現代新女性所應有的新品質
《我所希望的新婦女》是1924年元旦陳學昭發表在 《時報》增刊上的一篇散文,也是她的處女作。面對千百年來女性所處的受壓迫、受奴役、被蹂躪的處境,陳學昭站在女性的立場,從個人修養和社會事業兩個方面以闡述她對 “新婦女”的認識和思考。她認為新婦女應該在人格上 “了解這個變化不已的世界”[1]1,要有正確的人生觀,不依附于男子,擁有自己獨立的思想、情感和意識,要有自己獨特的見解,要 “拿道德的、公平的、明察的態度來對待外界。不為盲目者所稱贊,但求同道者的同情,更具有不屈不撓的犧牲的博愛的精神”[1]1。中國封建社會,秉承 “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評判標準,女子從小只能在家專注女紅 (工),嫁人后相夫教子,沒有接受教育與參與社交、工作的權利。在這篇文章中,陳學昭認為女子應該具有和男人相同的受教育和工作的權利,她認為女子只有經濟上獨立才能在人格上獨立。她在文章中要求女子 “要對于自己下一番苦功夫,得到深切的學問與經驗”, “不以皮相、半解的知識來自欺欺人”[1]1。在她看來,很多女子之所以求學只在于想以此 “求得較高的配偶”[1]2,求得物質的報酬。在 《給女學校教師的公開信》中,她明確指出了女子自古以來在教育上被忽視的問題,并且嚴厲批評了有些女教師沒有真才實學、思想渺茫、頭腦空洞,她們只把教育工作看做獲得勞動報酬的一種手段,對教育工作不熱衷,得過且過;對學生不聞不問,漠不關心。這些觀點都是陳學昭作為女性解放的先驅,站在現代女性的立場和角度,看到女性在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女性在生活中所處的弱者地位的原因,具有鮮明的現代女性意識。
在中國舊禮教、舊道德的束縛下,中國的女子缺少作為獨立個體的主體性,在封建神權、族權、父權、夫權的四重壓力下逐漸具有了奴性的特征。她們習慣于固守家庭、相夫教子,做一個賢妻良母。在傳統倫理道德中,“賢妻良母”是對一個女性最高的評價,而中國的婦女也在這樣的評判標準下嚴格要求自己。在陳學昭看來,正是因為那些賦予女性的諸如無私奉獻、相夫教子、賢妻良母等 “傳統美德”的枷鎖才致使中國的女性一直處于 “非人”的地位。在傳統社會,女子將美滿婚姻當做自己畢生不斷努力的事業,渴望通過嫁個好人家來使自己獲得優厚的物質報酬,依靠自己的天然性別來獲取生活的物資。甚至可以說,她們把婚姻當做事業,把嫁人和生育當做自己的 “天職”,而一個女人如果沒有嫁人,沒有生育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價值,會被人看不起,甚至遭到家人的唾棄。所以很多女性窮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做一個男權社會中有 “價值”的人。在 《我所希望的新婦女》中,作者認為女子的價值并不僅在于為人妻、為人母,還在于等同于男性的社會價值。她鼓勵女性走出家庭,去實現自己母性以外的價值。她認為女性要實現人格獨立,最重要的就是自立,而自立就是要在經濟上獨立,要在經濟上獨立就必須要有自己的事業而不應固守于家庭,“一個獨身的女子,對于社會上,一定會比家庭里的賢妻良母發展的多。”[1]2在 《給女學校教師的公開信》中,她也表現出了對女教師的希冀,希望她們能夠認真對待教育事業,真正在教育上有一番作為,從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不難看出,陳學昭對于女子的教育、職業、婚姻等問題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她眼中的新婦女就是應該在人格上獨立、個性上解放、有學識、有自己的事業的新女性。她鼓勵女子走出家庭的樊籬,打破傳統倫理道德的神話,去從事適合自己的職業,不依附于男子,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新女性。
二、抒寫時代女性內心的苦悶
幼時坎坷的經歷,形成了陳學昭敏感、多疑、倔強和反叛的性格,對家庭的失望和對自由、獨立的追求,使她渴望去外面尋找自己的天地。她說:“我是一個流浪者,孤零漂泊的流浪者!天涯的游子,只有天涯的浪花是一生的快伴!”[2]50
作為被 “五四”文化激蕩出歷史地表的新女性,陳學昭敏感地感受到了來自家庭、社會、文化、倫理道德等帶給女性的擠壓、束縛和屈辱,她把自己的滿腔悲憤都化作鮮活的文字,以此表達出時代女性覺醒后無路可走的內心苦悶和迷惘,同時也對黑暗的社會和傳統倫理道德以及男權中心主義給予了嚴厲的批判和質疑。她以同情和悲憫、厭惡和諷刺的雙重情感向讀者形象、真實地描繪了 “五四”落潮期女性的生存現狀和內心的焦灼、苦悶,讓我們看到了時代女性的悲涼生存境況。
《倦旅》是陳學昭的第一部散文集,在這部作品里,她化名 “逸樵”,將自己去安徽四師任教時的所見所聞所感用細膩的筆觸向我們娓娓道來,繾綣纏綿,清新婉麗,近似于作者年輕心靈的內心獨白,真摯、細膩,帶有年輕女性對人生對命運的迷茫和感傷。正如她自己在 《關于 〈倦旅〉的寫作》中所說,《倦旅》“記下了自己前一段的流浪生活,反映了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有時充滿了悲哀凄愴,有時充滿了憤怒激昂。”[8]298文中主人公面對美好的自然風光卻無心欣賞,而是陷入了自己的思索當中,她認為人生就像 “浮萍浪花一樣的漂泊著……”[3]14無處安身,只能隨波逐流,充滿著對前途命運的彷徨迷惘之感。“我顧視來路,又若是的隱約;我瞻望前途,又若是的渺茫。唉!我的心啊,將如何安放,在這樣的旅途之上!”[3]14作者借主人公表達了自己的孤蓬漂泊的感傷和哀怨。在 《我的母親》中,作者這樣寫道,“在這廣大、空漠、擾雜的道路上,我躑躅著,我徘徊著,到處都是這不可撲滅的灰塵,到處都是難以選擇的歧路。我空寂的心,我飄渺的魂,我失去了努力的目標,我憎恨著一切……”[4]51,從這些字里行間,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在面對現實人生的前途命運和種種艱難險阻時內心痛苦的無奈和絕望,這也是處于那個時代的新女性內心的真實寫照。“我看破了!這夢幻的人生!這厭倦的生活!”[4]52我們看到了夢醒后無路可走的女性內心的痛苦和焦灼,對生活的厭倦和對人生的絕望,這是那個時代追求自由進步的現代女性內心的共鳴。側重抒寫自然景物的散文集 《煙霞伴侶》表現出與作者平時創作不同的藝術風格,她自己在 《天涯歸客》中說:“我并不很喜歡,這里面的好些散文是吟風弄月的”[6],但其實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在描繪大自然的湖光山色的同時,也流露出作為女性所特有的情愫。雖在描繪風光萬物,但郁積于心頭的依然是一個新女性無盡的哀傷和糾結于內心深處的悲涼與迷茫。“等是有家歸不得,杜鵑休想耳邊啼”的有家難歸的無奈和感傷。在《如夢》中綠漪想 “求一個真理”[5],可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她無能為力,她猶疑、徘徊、失望。她認識到了這個社會的畸形,她渴望逃離,可走來走去還是走不出這個讓她窒息的圍城,最后她不禁感嘆,這一切都如夢一般的飄渺!
在這些作品中,字里行間都彌漫著一種淡淡的感傷情懷,寓于作者內心深處的是屬于那個時代所特有的感傷和苦悶。在這些散文里,人物有著趨同的共性,她們追求獨立、自主,在 “五四”精神的感召下,她們打破了傳統倫理道德強加在她們身上的桎梏,走向社會追求自己的理想,但黑暗的社會現實卻阻礙了她們追求進步的步伐,她們變得焦灼不安、痛苦、迷茫甚至絕望。作者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來建構文章,用自己手中之筆書寫著時代女性的生存現狀,表達了作者對覺醒了的新女性的生存現狀的同情和憐憫以及對她們前途命運的擔憂和對黑暗社會現實的無情鞭撻,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意義。陳學昭把追求進步自由的時代女性寫進了中國文學史,是覺醒了的時代女性的代言人。
三、解構男權社會的婚戀神話
陳學昭是我國20世紀最早具有獨立女性意識的時代女性之一,但她本人在經歷一次次的突圍、反叛和抗爭后,最終還是陷入了無愛婚姻的泥淖中,她錯失了兩個摯愛她的男子,卻和兩個她不愛也不愛她的男子建立了戀愛、婚姻關系。陳學昭自身的婚戀悲劇就昭示了在這個受封建倫理道德影響頗深、男尊女卑觀念根深蒂固的中國,女性解放之路是何其艱難、曲折和漫長。
獨立自主、個性解放的 “五四”時代精神在中國女性解放運動中表現出來的典型就是女性擺脫傳統的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婚姻的枷鎖,追求婚姻、戀愛自由。一批自由意識覺醒、思想解放的新女性率先勇敢地向封建包辦婚姻發起了挑戰。正如陳學昭在 《南風的夢》中所說:“戀愛是不能奉命的,任憑是誰人的命都是不能奉行的。”[7]167在舊中國,女性一直過著 “順從”的生活,依靠男性而活,她們把自己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男性身上,從父親到丈夫再到兒子,而正是這種近似于奴性的依賴,使男性更加鄙視女性,使她們的地位變得越來越低下。她們把婚姻看做自己謀生和獲取生活之資的最有效途徑,把嫁人、生育當做自己的 “天職”,而忽視了自己作為 “人”的價值。陳學昭在1927年1月的 《給男性》一文中,站在女性的角度,以女性的視角真實地發出了女性自己的呼聲,揭示了女性在愛情、婚姻和家庭所處的弱者地位,并對男權中心主義給予了辛辣的諷刺和嚴厲的批判。在 《他給她》中,作者以一個男性的口吻告訴戀愛的女友“戀愛并不是我們整個人生”[10],女性除戀愛外還應該有自己的思想、意識和情感,有自己的事業。這也可以看出作者在這里是站在一個男性的角度上來鼓勵和勸告女性不要使自己陷入男權的婚戀神話。
《南風的夢》是作者的一部自傳體小說,小說以作者自己和季志仁、蔡伯齡、孫福熙的友情和愛戀為素材,向我們講述了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女性克明的愛情悲劇,揭露了男性的暴虐、無恥和狹隘、貪婪、自私,顛覆了男權的婚戀神話。毛一波在《〈評南風的夢〉》中認為,“從 《南風的夢》我們看得見男性的偏狹、疑忌和殘酷的劣根性來。”[8]323克明是具有現代意識的新女性,在遭受來自各個方面的重重擠壓之后,她依然保持著自己高潔、自尊、自主的品格,她寧可做一個跌倒在十字路口的餓殍,即便受到人們的譏笑和踐踏,也不愿匍匐在男權的威勢與玩弄下吃一口安穩飯。這些言論是作者借克明之口喊出的時代女性的最強音,表明了她們內心對獨立自主的渴望和對男權的蔑視和諷刺。文中的人物是一群受 “五四”精神影響的青年男女,他們在面對感情時內心情緒的變化,反映出了在黑暗的社會現實和傳統的倫理道德禁錮和束縛下內心的矛盾和苦悶的情感。有論者認為:“《南風的夢》是一個失戀者的呼聲,女性的靈魂的呻吟”[8]323。陳學昭是把自己寫進了故事,用自己痛苦的生活經歷和獨特的生命體驗來書寫時代女性對理想、自由的追求。在文中,克明具有開放和超前的性愛觀與藐視傳統倫理道德的貞操觀,她認為,男人多是用下半身思考男女關系的可憐生物,因為他們以為 “占有了一個女人的身體,便可以占有她們的靈魂”[7]第一卷,61。這些觀點都源于她獨特的女性視角和女性立場,這些大膽的言論,是對封建舊禮教、舊道德的反叛,具有鮮明的性別意識。
在 《幸福》中,作者塑造了一個 “子君”式的人物 “郁芬”,她不顧父母反對勇敢和自己所愛的人結合在一起,她沒有像子君那樣婚后只把目光投注于個人生活的小天地,而是做一個獨立的女性,堅持自己的工作。然而,在當時的黑暗的社會現實下,并沒有一個寬松的可以任女性自由發揮自己才能的工作氛圍,面對工作的不順和家庭中丈夫的不理解,她痛苦和迷茫。魯迅說,出走的 “娜拉”,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而郁芬最終還是陷落在了婚姻的 “圍城”中。我們看到,在男權社會中,女性個人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她們覺醒了,甚至有很大一部分人奮力地突出了封建的重圍,大膽地反叛封建倫理道德,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在面對來自家庭、社會、傳統文化的壓力時,她們反抗、掙扎、左沖右突,渴望實現自己的價值。但面對強大的外部壓力,她們還是陷落了。“郁芬”式的女性在當時不是個例,作者用自己敏銳的觀察、獨特的視角,通過郁芬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了黑暗的社會和傳統的倫理道德對于女性的擠壓和殘害,表達出對女性的同情和對男權婚戀神話的質疑和反叛。
四、結語
陳學昭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代女作家,她是在 “五四”時代精神的感召下走上女性解放之路的先驅。初涉文壇,就表現出了對女性命運的極大關注和思考。她早期的文本主要以散文為主,表達個人的情感,在感傷迷惘中帶有不斷向上的自強不息的力量。表現女性知識分子在當時對自由的渴望以及理想與現實社會之間發生矛盾時內心的無可奈何與彷徨迷茫之感。站在女性的視角,用自己細膩的筆觸描摹她們的靈魂,抒寫她們的情感。作品中飽含著抗爭反叛、苦悶迷茫的情緒,向讀者真實地刻畫出了試圖突出重圍的時代女性不斷的追求與抗爭的心靈軌跡。
[1]陳學昭.我所希望的新婦女[A].陳學昭.海天寸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2]陳學昭.寸草心[A].陳學昭.海天寸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3]陳學昭.倦旅[A].陳學昭.海天寸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4]陳學昭.我的母親[A].陳學昭.海天寸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5]陳學昭.如夢[A].陳學昭.海天寸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58.
[6]陳學昭.天涯歸客[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26.
[7]陳學昭.陳學昭文集(第1卷)[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
[8]丁茂遠.陳學昭研究專集[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
[9]單 元,萬國慶.突圍與陷落——陳學昭傳論[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8.
[10]馮小青.陳學昭文學創作中性別意識的覺醒[J].學術探索(理論研究),2011(2):91.
[責任編輯:田 野]
I206.6
A
1674-3652(2014)01-0080-04
2013-11-28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陜西文學對延安文學的承傳與發展研究”(12XZW020);延安市社會科學專項資金規劃項目“左翼知識分子與延安文學體制建構研究”(13BWXC30)。
王俊虎,男,陜西大荔人,博士,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