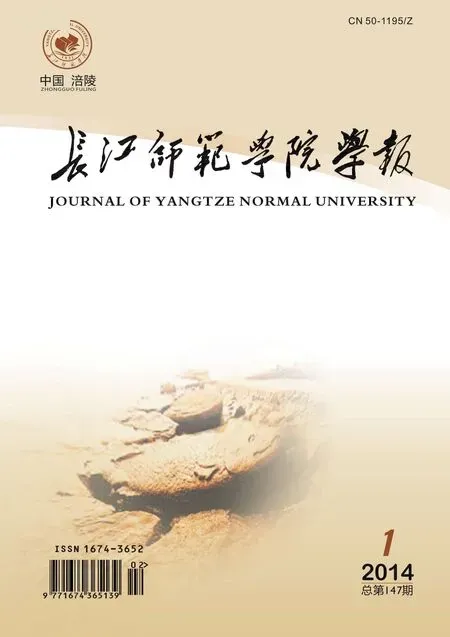“路”上的人生
——論 《吶喊》《彷徨》中 “路”的敘事意義
余新明
(廣東第二師范學院 中文系,廣東 廣州 510303)
“路”上的人生
——論 《吶喊》《彷徨》中 “路”的敘事意義
余新明
(廣東第二師范學院 中文系,廣東 廣州 510303)
“道路”作為一種時空體,在小說情節的建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 《吶喊》《彷徨》中,魯迅寫到了眾多的 “路”,這些 “路”既制造了熟人的相遇,也制造了陌生人的偶遇,有的還以其隱喻意義有深化情節的內涵,推動情節向前發展。這些 “路”上的人生,體現出的是小說人物痛苦、愚昧、麻木、冷漠的生存狀態,具有深遠的啟蒙意義。
《吶喊》 《彷徨》;路;相遇;偶遇;隱喻
一、“路”作為一種時空體
衣、食、住、行是我們人類的基本需要和最常見的生存狀態,是我們人類生存的四大要素。前三者不言而喻,至于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人如要活動 (為了生存不能不活動,活動是生存的必要條件之一)就必須要 “行”,而要 “行”就離不開 “路”,在路上行走 (后來發展到坐船、乘車、坐飛機等多樣化、現代化的交通行為)是我們人類非常普遍的一種行為。因此,作為對我們人類生活的反映的文學,在敘事寫人時就少不了“路”,“道路”是文學中的一個非常常見的空間意象。巴赫金在分析西方小說中的 “時空體”時曾指出西方文學中大量存在一種 “道路”時空體。我們先來看看他是怎么論述的:
……小說中的相會,往往發生在“道路”上。 “道路”主要是偶然邂逅的場所。在道路 (“大道”)中的一個時間和空間點上,有許多各色人物的空間路途和時間進程交錯相遇;這里有一切階層、身份、信仰、民族、年齡的代表。在這里,通常被社會等級和遙遠空間分隔的人,可能偶然相遇到一起;在這里,人們命運和生活的空間系列和時間系列,帶著復雜而具體的,不同一般地結合起來;社會性隔閡在這里得到克服。這里是事件起始之點和事件結束之處。這里時間仿佛注入了空間,并在空間上流動 (形成道路),由此道路也才出現如此豐富的比喻意義:“生活道路”,“走上新路”,“歷史道路”等等。道路的隱喻用法多樣,運用的方面很廣,但其基本的核心是時間的流動。[1]
在這段引文中,巴赫金對 “道路”時空體在小說中的作用,尤其是對建構小說情節的作用作了非常清楚而有意味的說明,盡管他認為 “時空體在作品中總是包含著價值的因素”,但與其他時空體不同的是,他認為 “道路”時空體 “范圍雖廣大,感情和價值色彩卻較弱”[2]。顯然,他對 “道路”時空體更注重的是它們在建構小說敘事上的重要作用(他稱之為 “情節作用”),如制造人物的邂逅、相遇,成為事件的起始之點和事件結束之處等等。這就充分說明,我們在研究小說的敘事時,就絕不能忽略 “道路”這一空間意象的敘事作用。
道路的主要功能是人們用它來進行交通行為,它主要起著溝通和連接作用。當路的兩邊有了各種人文建筑,如住宅、店鋪、樓房時,它就是街道(有時也稱為街、街上、街頭);當人們乘船來進行交通行為時,所利用的江河湖海被稱為 “水路”(“水道”),在水路上行進的船可視為另一種形式的“路”,這些都可看做是 “道路”的不同形式。魯迅是一個非常關注 “路”的小說家,在 《吶喊》《彷徨》中他多次寫到了路,道路的這些不同形式在《吶喊》《彷徨》中都有存在,我統一稱它們為“道路”式空間意象,它們積極地參與了小說的敘事建構。
誠如巴赫金所言,“路”主要是一個 “偶然邂逅的場所”,“在這里,通常被社會等級和遙遠空間分隔的人,可能偶然相遇到一起”。不同的人相遇到一起,就有了可以言說的故事,有時也因人們的相遇而推動故事向前發展。巴赫金在講到 “道路”時空體在西方小說里的表現時,提到了西方的騎士小說和流浪漢小說,他們都從一地轉移到另一地,是一種大范圍的空間轉移,因而他們在路上相遇的一般是陌生人。而魯迅筆下的中國社會,是一個鄉土觀念根深蒂固的文化區域,人們不是迫不得已一般不會離開自己的家鄉,他們一般生活在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 “熟人社會”[3]里,因而在中國的小城鎮里,在廣大的村莊里,在路上相遇的多為熟人。這是與西方小說里的相遇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是與現代都市 (那是一個 “陌生人”社會)小說大不相同的地方。但魯迅在 《吶喊》《彷徨》中除了有大量的鄉土社會 (小城鎮和鄉村)的各種道路外,也寫到了具有現代氣息的北京社區的街頭 (如 《一件小事》《示眾》等),所以在 《吶喊》《彷徨》里的道路相遇,就既有 “熟人”的相遇,也有 “陌生人”的偶遇。
二、熟人在 “路”上相遇
熟人在路上相遇,一般會發生什么?由于他們彼此有一定的認識和了解,也就是說,在相遇之前他們之間就有一段 “歷史”存在,所以在路上相遇了,總會多多少少發生一點事情,普通的如熟人見面打個招呼。但在小說里,由于我們人類總想在審美對象中尋找意義 (作家這樣寫,讀者也會這么看),所以人們的相遇就沒有這么簡單,它總有值得玩味的東西。
最值得玩味的就是他們間的 “說”。由于相互有一點的了解,所以他們相互間就有對話、言說的可能,而這些 “說”則成為形成故事情節、透視人物靈魂的重要手段。在 《祝福》中,“我”在河邊遇到了祥林嫂,就形成了一段關于 “靈魂有無”的精彩對話。作為魯四老爺的侄兒,“我”在魯鎮生活過多年,對祥林嫂應該是非常了解的,而作為魯四老爺家的女傭,祥林嫂也應該是知道 “我”的基本情況的,所以他們的相遇就有了對話的可能性。因為 “我”是 “出門人,見識得多”,所以祥林嫂一開口就向 “我”問靈魂的有無問題——這個問題她是不會去問其他的魯鎮人的,因為魯鎮人都信其有,而祥林嫂在到魯鎮前是不太信的,因為當柳媽說她死后會被閻羅大王鋸成兩半時有這么一句:“她臉上就顯出恐怖的神色來,這是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所以她想找人確證一下。而祥林嫂的這種想法的深層動機是她預感到自己就要死了,她既想因為人有靈魂而見到兒子阿毛,也想沒有靈魂而免去被閻王鋸成兩半的痛苦,這就足以見出封建思想對她的精神戕害之深。如果祥林嫂不開口說話,那又有誰能知道臨死前她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呢?而這一點,對于 《祝福》能夠達致的啟蒙深度,具有決定性意義。在敘事上,是河邊 “我”與祥林嫂的相遇使祥林嫂有了開口的機會,沒有這次相遇,就沒有這么一個精彩的對話和深刻展示祥林嫂靈魂深處的故事情節。在結構上,這段對話也為下文祥林嫂的死以及 “我”對祥林嫂半生事跡的片段的回憶埋下了伏筆,并最終與這些材料形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另一個值得玩味的是他們間的 “做”。熟人見面,有時相互間還會采取一些行動,這些行動也構成了故事情節。單四嫂子在街上遇到了藍皮阿五,藍皮阿五就借幫她抱孩子而乘機揩她的油,這一相遇的情節就充分地折射出單四嫂子所處的險惡社會環境。當阿Q在路上遇到王胡時,他就和他比捉虱子,因為他一向看不起王胡,他要在捉虱子上超過王胡。當他失敗時,就出現了先是與王胡吵接著被王胡打的場景。阿Q看不起王胡,而王胡也深知阿Q的底細,所以他們的相遇就有了這樣的故事。這是展現阿Q性格的一個典型場景,阿Q的自大自賤表現得很形象。不僅如此,《阿Q正傳》還充分利用道路這一公共空間,不同的人都可以在這里行進而讓阿Q遇上不同的人,如他在這里遇到未莊的閑人,遇到假洋鬼子,遇到小尼姑,遇到小D,這就形成了不同的故事情節。這些不同的情節也有類似的地方,就是 “打”,或者是欺負。阿Q被閑人打,被王胡打,被假洋鬼子打,和小D“龍虎斗”,唯一他欺負別人的一次是調戲小尼姑,因為小尼姑是比他更弱小的人物。這些打與欺負,就鮮明地體現出未莊的等級性質,也生動地寫出了阿Q的精神面貌。而對小尼姑的調戲,還推動了故事的發展——阿Q想女人而產生了 “戀愛的悲劇”。阿Q住在土谷祠里,一般的情況下未莊人是不會到他那里去的,所以魯迅就讓他在未莊的街上走,讓他遇見不同的人,以構成小說的基本故事情節。
還有一點是他們間的 “看”。盡管熟人見面一般會以 “說”和 “做”為主,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他們之間的行為卻以 “看”來進行,即不用語言而是用視線來傳遞情感和信息。在 《狂人日記》中,當 “狂人”由于受到某種啟示而發生了啟蒙覺醒的時候,他在他周圍的所謂的正常人眼中就是 “瘋子”,是 “狂人”,他擁有的啟蒙思想使他與周圍的人格格不入,這樣他就與那些他曾經很熟悉的人失去了對話和交流的可能。在語言交流不能進行的情況下,他與周圍的人就用相互間的 “看”來互相觀察。小城鎮居民的日常生活是程式化的、單調的,現在出了這么一個 “瘋子”,無疑是在他們單調乏味的生活中注入了一些刺激性的東西,因此狂人到哪兒都有很多人來圍觀,充當一向為魯迅深惡痛疾的 “看客”。魯迅先生曾說過:“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4]看客的目光在覺醒的狂人看來,卻含有一種 “吃人”的心理在里面。這些人本是狂人素來熟悉的,但在狂人 “發瘋”之后,他們就不再 “熟悉”了,狂人在他們眼里是陌生的,他們在狂人眼里也是陌生的,狂人發現他們似乎想“吃人”,這是狂人在沒有 “發瘋”時根本就發現不了的。街頭與看客的相遇恰恰是狂人思想發展 (對中國社會和歷史的思考和認識步步深入)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①王富仁先生認為狂人覺醒有三個思想層次:“(一)首先一般地認識到社會吃人,周圍的人吃人;(二)繼之認識到他的親人吃人,他的大哥吃人:‘吃人的是我的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三)最后認識到自己也曾吃過人。這三個思想層次是‘狂人’對封建思想、封建倫理道德由淺入深、由形到質、由表到里不斷深化的認識過程。”(參見《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 〈彷徨〉綜論》,第161、162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而第一層次實際上是通過在街頭狂人與他人相遇來完成的,并且成為后兩個層次的基礎,因此可以說這是這篇小說敘事的一個起點。,狂人的活動空間由家外慢慢縮小到屋內也與這種相遇有密切的關系。也就是說,狂人在街上與周圍的人形成的 “互看”在思想上包蘊了非常豐厚的內容,在敘事上也推動了故事的發展,可以說是巴赫金所說的 “事件起始之點”。
在 《祝福》中,當喪子之后的祥林嫂再次來到魯鎮做工時,在街頭她與魯鎮人的相遇就成了她向他們訴說痛苦的地方,訴說她的凄慘遭遇,她想以此來博得魯鎮人的同情,好讓魯鎮接納她 (關于這一點前面已有論證分析)。但魯鎮人只是 “從祥林嫂的痛苦中感到了一種滿足”,而且 “不是倫理的,而是審美的滿足和快感”[5],魯鎮人并不真的同情祥林嫂,所以在希望得到同情和并不同情之間,也就失去了真正溝通和交流的可能性,魯鎮人和祥林嫂之間表面上是祥林嫂在說而魯鎮人在聽,而實際上是 “看”與 “被看”的關系。在魯鎮人看來,祥林嫂的痛苦訴說是讓他們感到滿足和快樂的一種“表演”,因為 “‘看客’現象的實質正是把實際生活過程藝術化,把理應引起正常倫理情感的自然反應扭曲為一種審美的反應”[5]。這反映了魯鎮對祥林嫂的拒斥,是祥林嫂走向死亡道路上的重要一環,也是整個小說敘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情節。
三、陌生人的 “路”上偶遇
與熟人相遇主要是 “說”和 “做”不同,陌生人因為在相遇前他們彼此并不認識、了解,所以他們相遇在一起時多為 “看”。若對方很平常,是他們習見的,他們則看一眼后就匆匆走過;但如果對方的穿著、神情或其它方面顯得有點怪異的話,那么他們就會停下來仔細地 “看”,以給他們的生活增添一些談資或調料。
中國廣大的鄉村與小城鎮是 “熟人社會”,而具有現代氣息的都市則是 “陌生人社會”,所以陌生人的偶遇一般都發生在都市里。在 《示眾》里,當刑警牽著一個 “示眾”的犯人出現后,盛夏的京城的馬路上,馬上就聚集起一圈看客。因為犯人和圍觀者的彼此陌生,所以圍觀者想了解犯人的各種情況,這是他們 “看”的直接原因,而深層原因則是同上文所說的那樣,他們想尋找一點 “審美的滿足和快感”,好來調節一下他們單調、無聊的生活②這篇小說開頭、在示眾的犯人出現之前,就花了五個自然段的篇幅來渲染夏日京城街道上人們生活的單調和無聊,給人一種懨懨入睡的感覺;在后文,則以一個抱小孩的老媽子說的“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揭示了他們“看”的根本動機是“好看”。。犯人看到這么多人看他,在無事可做、有刑警看著也不敢說話的情況下,犯人也看起周圍的看客來了,這也許是他打發這段無聊的示眾時間的最好辦法。所以在犯人和圍觀者之間就形成了一種 “互看”的關系;而圍觀者則不僅看犯人,他們彼此間也因為偶然相遇或爭搶看犯人的“地盤”而彼此“互看”。所以,“看”在這里就成為所有在場者最重要的行為方式,甚至可以說是除了爭 “地盤”和極少的言語外的唯一行為方式。他們一方面看別人,另一方面則被別人看,幾乎每一個人都被卷入“看/被看”的視覺糾纏中。每一個人都想看出點“端倪”來,但魯迅直到小說結束也不把這 “端倪”端出來,“《示眾》的最大特點在于,魯迅造成了懸念,維持著懸念,轉移著懸念,但最終也沒有消除這些懸念”[6],他只是單純地讓小說里的人們“看”,也讓我們讀者 “看”。“看”是這篇小說的唯一 “焦點”和最大 “看點”,而沒有馬路上陌生人的相遇,這樣的 “看”是無法出現的,這正是這篇小說敘事得以完成的全部秘密所在。
在 《阿Q正傳》中,當阿Q被捉到城里去時,他與居住在城里的居民的偶然相遇也可以說是 “陌生人”的相遇。其一是因為城的范圍遠較未莊這樣的小村鎮大,居民人數眾多,他未必每一個人都認識,即使如遠近聞名的舉人老爺,如果阿Q沒有到過他家做工,他也未必能認識他,只是聽說有這么一個人而已;其二是我們所說的中國近現代小城鎮也是一個 “熟人社會”,那基本上是針對小城鎮的居民而言的,對于縣城來說,阿Q不過是一個居在鄉下的農民,盡管他上過幾次城,但城里的絕大多數居民于他來說,仍然是 “陌生”的。所以,當阿Q在縣城的街頭游街示眾時,他與圍觀的人群之間,也是一種 “陌生人”的相遇。在偶遇時,在阿Q押赴刑場時,他們無法用語言進行溝通,他們彼此只是用眼睛來觀察對方 (的陌生、新奇處)。與 《示眾》一樣,在阿Q與看客之間,,也形成了一種 “互看”的關系,而麻木、冷漠、殘忍的看客心理則通過阿Q對看客目光的心理感受而深刻地揭示出來: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們。
這剎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風似的在腦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腳下遇見一只餓狼,永是不近不遠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時嚇得幾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這壯了膽,支持到未莊;可是永遠記得那狼眼睛,又兇又怯,閃閃的像兩顆鬼火,似乎遠遠的來穿透了他的皮肉。而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并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是不近不遠的跟他走。
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里咬他的靈魂。
“救命,……”
阿Q的這種感覺非常類似于狂人對周圍人的目光的感覺,狂人也老是覺得周圍的圍觀者的目光里有一種吃人的力量。當圍觀者人數眾多時,被圍觀者會不自覺地感到一種心理壓迫,即我們常說的“眾目睽睽”,而當眾目睽睽的目光的出發點是事不關己、看熱鬧乃至冷漠、殘忍的 “審美”時,它就會因數量的眾多而進一步由心理壓迫演化成如阿Q所體味到的可怕的 “吃人”力量。這是看客和看客之外的他人難以體會的,只有被圍觀者才能真正地感受到。魯迅曾說:“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7]這里的圍觀者,也用眾多的目光,對即將行刑的阿Q進行 “精神虐殺”。這是一個典型的 “看客”場景,其深刻的思想意義卻通過被看者——阿Q揭示出來。“陌生人”的路上相遇、他們互看的視線碰撞則是建構這一切的全部基礎。
四、“路”——人生的隱喻
巴赫金在談到 “道路”時空體時曾提到了它的隱喻意義,比如生活道路、心靈道路等等。就 “道路”這個詞語本身來說,它具有很強的隱喻性,這在東西方文學中都很常見。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比較著名的有屈原在 《離騷》中吟唱的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詩句 (這兩句被魯迅寫到了《彷徨》的扉頁上),還有李白 《行路難》中的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等等,屈原和李白都借實體的路的難走 (“修遠”、“多歧路)而表達一種對人生之路永不屈服、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在西方,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的 《未選擇的路》則是寫 “路”的名詩,這首詩借樹林里因道路分岔而不得不進行選擇的實際情況,反映了對人生之路進行選擇的艱難以及不能每條人生之路都進行嘗試的惆悵,讀來頗多哲理意味。作為洞徹人生的思想大師,魯迅在 《吶喊》《彷徨》中不僅寫了許多本體意義上的路,還借此發揮,寫到了許多具有隱喻意義的 “路”。
最有名的是 《故鄉》結尾的一段話:
我想: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在這里,“路”成了希望的象征,魯迅借此表達一種不管人生之路如何難走都要對未來充滿希望、都要堅定地走下去的人生信念。巴赫金說在《帕爾齊法爾》這類小說中認為隱喻意義上的道路義 “取決于主人公的錯誤和墮落,取決于在他的現實道路上遇到的事情”[8]。這告訴我們魯迅小說中隱喻意義上的 “路”也必須與小說里人物遇到的事情結合起來分析。在 《故鄉》中,“我”回到了故鄉,卻發現故鄉與自己是如此隔膜,連少年時的好友也與自己無話可說了。小說寫道:“我躺著,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這里的路既是實指,也是人生之路的隱喻。“我”有 “我”的 “路”(“辛苦展轉”),閏土有閏土的 “路”(“辛苦麻木”),楊二嫂一類人也有他們的 “路”(“辛苦恣睢”),而這些都不是 “我”所希望的人生之路,所以 “我”希望找到一條新的人生道路,就像在沒有路的地面上,很多人去走,就可以踩出一條路來。因此,結尾的隱喻意義上的 “路”,就成了對美好希望、美好未來的象征,而希望大家都去走,則是鼓勵中國人都去為這美好的未來而奮斗。在這段話之前,小說的故事基本上都結束了,但這兒的“路”的隱喻卻使故事極大地拓展了意義空間,并且具有了一種形而上的哲學意蘊。
在 《傷逝》中,也出現了許多隱喻意義上的“路”,這些 “路”,無一不是隱喻意義上的 “路”:人生之路,或曰生活之路。依據巴赫金的觀點,“路”的隱喻意義與人物在現實道路上遇到的事情有關,而小說里涓生、子君遇到的是各種人生困境:因為他們的同居與當時的封建禮教不合,所以子君與家里斷絕了關系;涓生被單位給解聘了,他們失去了生活下去的經濟支柱;因為貧窮,他們遭遇房主的冷眼;因為經濟問題,他們漸生齟齬,最后分開,最終是子君回到家里去并在冷眼中死亡,涓生則在痛苦中依然為生活奔波……在這些人生困境中,他們總想找到出路 (“新的生路”),但由于大的社會環境的重壓,他們因為強烈的愛而對社會的反抗,卻都歸于失敗。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小說里涓生、子君的人生軌跡基本上可歸結為 “尋找新路”,這也是小說里絕大部分故事情節的內核,也是推動故事向前發展的根本力量。他們始終找不到新路,則充分說明魯迅對 “五四”時期青年男女追求婚姻愛情自由所作出的冷靜而成熟的判斷與思考。涓生、子君尋求新路的失敗,正說明 “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的真理。因此,這篇小說里眾多隱喻意義上的 “路”,既在敘事上把各個情節串起來并成為關鍵性發展動力,也在思想主旨上成為總的歸結點,可以說是敘事結構和思想內容上的“雙重焦點”。
總之,《吶喊》《彷徨》中的這些 “路”,不僅制造了小說中的相遇情節,更以其豐富的意蘊反映出小說中人物的命運和思想,寫出了近現代中國人一種普遍的生存狀態——“路”上的人生,這是一種痛苦、愚昧、麻木、冷漠的人生,因而具有深遠的啟蒙意義。
[1][2][8][俄]巴赫金.小說理論[M].白春仁、曉 河,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44、444、445.
[3]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8—11.
[4][7]魯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70、129.
[5]高遠東.《祝福》:儒道釋吃人的寓言[A].汪 暉、錢理群,等.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論魯迅(二)[C].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40.
[6]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280.
[責任編輯:黃志紅]
I206.6
A
1674-3652(2014)01-0084-05
2013-12-09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空間理論視域下的魯迅小說研究”(11YJC751109)。
余新明,男,湖北孝感人,博士,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