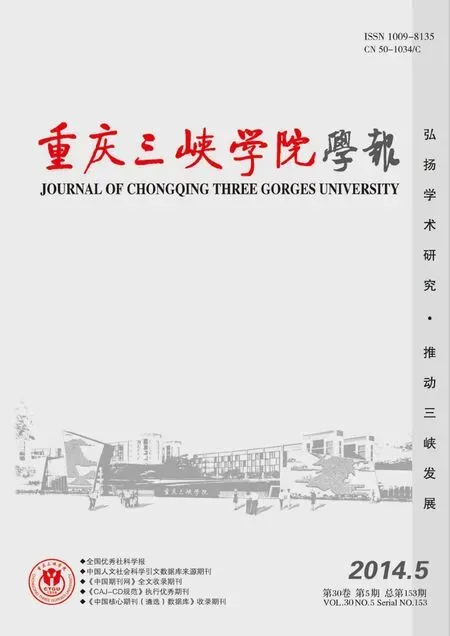析沈周文人山水畫與汪野亭山水瓷板畫異同
張麗娜
?
汪野亭研究 主持人:黃念然
主持人語:汪野亭作為近現代瓷繪藝術發展進程中革故鼎新的大師級人物,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他對前輩大師創作理念及其審美精神的不懈學習與汲取。魏晉六朝之氣韻生動,宋元山水畫之俊逸,明代沈周之豪放,董其昌之以書入畫,清代王石谷之清麗厚實,石濤之蕭散狂放等等,均能入其彀中而賞其風格,悟其意境,師其技法,從而在博采眾長之中自出機杼。本期開始將主要研討汪氏創作理念及其技法對前輩大師的繼承與創新,力圖由此厘定汪氏瓷板畫創作師古而自新的藝術歷程。
析沈周文人山水畫與汪野亭山水瓷板畫異同
張麗娜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 430079)
結合汪野亭與沈周的個人經歷和心理歷程,從創作風格、創作題材兩方面比較沈周文人山水畫和汪野亭山水瓷板畫之間的異同,探尋沈周的創作對汪野亭的影響,以及汪野亭自身作品獨有的特色,以期進一步認識汪野亭的瓷板畫創作。
沈周;汪野亭;師古與求己;創作風格;創作題材
當代美術評論家陳傳席曾精煉地概括了每一位藝術大師一生的經歷,先“神于好”,再“精于勤”,最后“成于悟”。每個藝術家的創作之路都從仰慕前輩的優秀作品開始,但只停留在神往階段而不付諸行動的話一輩子都只是一個空想家;心中有了目標就朝它前進,以勤補拙,慢慢完善自己向先賢靠近;當技藝積累到一定程度時,能否化蛹成蝶就在于最后一步——悟,這需要藝術家本身的天資稟賦和人生機緣。用馬克思辯證主義哲學來闡釋這段“成藝”的歷程實際上就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神于好”和“精于勤”是量的積累,它們如木之本、水之源;“悟”是由量變向質變飛躍的臨界點,越過了它才能真正擁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中國傳統文化璀璨輝煌,繪畫藝術在其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每個時代繪畫領域都不乏能人異士引領潮流,身為“珠山八友”之一的民國畫家汪野亭就是這樣的英才,他變革了墨彩山水,在陶瓷繪畫中完美再現了中國畫青綠山水的用筆設色,將中國繪畫風骨與陶瓷工藝融為一體,開創出“汪派山水瓷畫”的新格局。他的成就是師古與求己共同作用的結果,而明代畫家沈周在其整個藝術創作的師古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沈周(1427—1509年),字啟南,號石田,晚號白石翁,長洲(今江蘇蘇州)人,世代隱居吳門。明代畫壇人才輩出,“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卻始終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沈周正是“明四家”的靈魂領袖。沈周開創了吳門畫派,將宋院體與明浙派的硬度和力感融入元人的含蓄筆意,兼以吳鎮墨色形成了磅礴而蒼潤、質樸而宏闊、平淡而悠遠的“粗沈”風貌。他的學生文征明稱贊他的作品為“風流文物,照映一時。百年來東南文物之盛,蓋莫有過之者。”[1]24本文將結合二人的個人經歷和心理歷程比較沈周文人山水畫和汪野亭山水瓷板畫之間的異同。
一、取“粗沈”之貌畫汪派山水
沈周的繪畫經歷了由“細沈”向“粗沈”蛻變的過程。畫作由布局繁復曲折、結構嚴謹有序、筆法銳利細密、風格縝密細膩的細筆勾染逐漸脫胎為布局簡疏明了、用筆雄渾蒼勁、墨氣淋漓老成、格調雄健宏闊的粗筆點簇。汪野亭早年即仰慕“粗沈”之豪健,汲取“粗沈”之豪逸天真創造了屬于自己的汪派山水。
(一)布局用色
汪野亭的瓷板畫和以往瓷板畫之間在色彩的選擇上有很大的不同。傳統粉彩于康熙晚期創燒,雍正時期發展成熟并達到高峰,粉彩山水瓷畫亦隨之出現。隨著時間的推移,粉彩山水瓷畫逐漸由硬朗勁健、揮灑自如轉為刻意雕琢、柔婉細膩。乾隆后至清末陷入程式化且缺少活力,用色俗艷秾麗,逐漸為大眾所不喜。清末民初,一批文人畫家迫于生計的壓力加入陶瓷繪畫創作,開始嘗試以陶瓷作為載體表現傳統國畫的神韻,使瓷板畫獲得了新生,這種瓷畫風格后人謂之“淺絳畫派”。但因文人缺乏陶瓷工匠的技藝,這些制成品出現了“色階少,光澤度差,顏色容易剝落等不足,還有待完善。”[2]汪野亭敏銳地感受到了傳統粉彩山水瓷畫和淺絳山水瓷畫的優點和缺陷,決定將二者融為一體加以革新,創造有傳統文人風韻的瓷板畫作品,融合的關鍵就在于“粗沈”之豪健。
“粗沈”的風貌在其晚期畫作《京江送別圖》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畫中主人乘舟遠去,江面平遠淡抹而出,幾乎不著顏色,留出大片空白盡顯水之浩淼悠遠;群山以粗筆披麻皴法出之,墨色溫厚圓潤,更顯山之蒼茫高遠,并以淡墨于群山間隙輕抹遠山輪廓,遠山更兼云霧掩映,墨色濃淡結合盡顯山之蒼秀飄渺。主體輪廓純用墨色繪制,具體人、景、物的點染則采用各種顏色,以灰藍、淺灰藍、桔色制衣,以土黃色填山,以墨綠色點葉。沈周還嫻熟地運用了中國傳統繪畫“計白當黑”的手法,在畫作上留下了二分之一左右的空白表示山之態、水之勢。沈周晚期的畫作墨與色、虛與實的交融互滲已至神境,畫作整體清新淡雅而又不至于寡淡無味。汪野亭早年學習時就已醉心于“粗沈”之用筆老辣干練,著墨之氤氳淋漓,設色之清淡雅麗,決意將其運用于自己瓷板畫創作中。
汪野亭的瓷板畫《空山雨后》明顯可見沈周畫作中豪逸之氣。這幅畫作近景兩岸的巖石以珠明料粗勾輪廓,燒成后成色為干灰色,類似于沈周畫近山時的干筆皴擦,又在珠明料上覆蓋藍料凸顯巖石的厚重冷硬;兩岸間一泓清流延伸至遠方,流水以一木橋相連,一村夫體態微蜷從橋上走過,步履輕松適意,與沈周《京江送別圖》中那個持竿過橋的漁夫極為神似。中景采取“計白當黑”的手法設大片空白用以表現流水,在空白上覆蓋厚薄程度不一的雪白料,表現出水流的流勢和波瀾,“產生了從平面走向空間的視覺效果。”[3]遠景僅以寥寥數筆畫出遠山輪廓,留下大片空白覆以厚薄程度不一的雪白料,營造出山上云霧掩繞的空濛潤澤之境,潺潺的流水和山中的云霧似乎自然連成一體,形成了水天一色的神妙韻致。據統計,汪野亭瓷板畫中多有留白,一般留白占畫作的三分之一,有的甚至占了畫作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再覆以厚薄程度不一的雪白料妙顯遠山之輕煙淡巒、近山之蒼勁有力、山間云霧之飛騰飄渺、山下流水之浩淼綿長。這種顯山繪水之法與沈周晚年豪逸之風頗為神似,整幅畫作空靈流動而又飽滿充實。
(二)詩書畫互溶
蘇軾曾說“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詩書畫三者本同根同源,詩的意境連綴起來就是一幅畫,書畫二者皆由毛筆所作,運筆時揮腕的力道、下筆時筆鋒的選擇、停頓時筆勢的扭轉等技巧本就相通,中國畫是詩書畫三者溶于一體的產物。汪野亭早年就已醉心于沈周放縱恣肆的書法,力仿沈字之灑脫奔放。汪野亭的字由此也逐漸發生了蛻變,由早期的清秀虛軟走向古樸恣意,這個變化在他“汪”字的落款中清晰可見,開始“汪”的第二畫和第三畫一般是連在一起的,后來第三筆和第四筆連得很近,甚至有些直接就連在一起了,用筆愈發老辣瀟灑,字體愈發自然隨性。
書之隨性恣肆與畫之飄逸疏野間,氣的連貫性或許讓汪野亭進一步領會到了書畫同源同體的真諦。原先瓷板畫的書畫是截然分開的,一般是一面作畫,一面題詩,觀者在欣賞時難免有斷層之感。汪野亭大膽突破前人窠臼,率先運用“通景山水”章法裝飾瓶類制品,繪畫采用散點透視法,在圓柱式的器皿上展開一幅完整的畫面構圖,使連綿的群山、幻邈的煙云、蒼潤的巖石、緩靜的流水、蔥郁的樹木連成一體,形成360度貫通不絕的完整構圖,無一絲勉強刻意銜接的痕跡,欣賞者在任何角度都可以充分體味山之姿、水之味,“山水源頭無覓處,游子信步山水中”的意境油然而生。同時,在畫作中直接題詩、寫字、落款、下印,真正將詩書畫印融為一體,是文人畫與瓷板畫的完美融合。這種裝飾風格開20世紀初景德鎮粉彩山水裝飾章法的新風,后人多沿襲此章法繼續進行創作。
二、盡前人題材兼己意
“自古善畫者,莫非衣冠貴胄、高士逸人。”[4]75沈汪二人雖非衣冠貴胄,但皆可稱得上是高士逸人。繪畫題材上,沈周和汪野亭也多有相似之處,但汪野亭又有自己的特殊題材。中國的山水畫并非對山水的純粹客觀描繪,而是要“胸中有丘壑”,將人事融貫于山水之中,于山水中展現某種精神,“山水以形媚道”、“圣人含道映物”,[5]22形成“有我之境”。因此,中國山水畫中大多并不只有高山、流水、草木這種純自然界的萬物,一般還會點綴以茅屋、亭臺、樓閣、行船、游人等,這些看似不起眼的點綴之物使原本沉寂的山水變得饒有生趣,形成情景交融之境,“情景者,境界也”。[6]113這些小的點綴物最能看出創作者的意趣,探尋創作者的心靈最宜從這些小處著手,以小觀大。
(一)人跡點點品旨歸
沈汪二人的相似之處在畫中人物的刻畫上可見一斑,畫作中的人物一般體現了作畫者的社會交往范圍、日常生活活動、心中信仰偏好等。因此,人物的選擇和表現中往往能窺探出創作者的人性之美、心靈之美,正如西晉顧愷之曾有言:“人最難,需形神俱得,次山水,次狗馬,難成而易好,不待猜想妙得也。”每一個畫家都會跟隨著心靈的腳步在作品中表現不同類型的人物。沈周的畫作中有雅會切磋的儒士,見《魏園雅集圖》;有杖策尋隱的高士,見《山空無人圖》;有依依話別的友人,見《京江送別圖》;有徜徉山水的閑人,見《高木西風圖》;有信步由韁的旅人,見《灞上風雪圖》;有坐于堂屋的雅人,見《東莊圖》;有辛勤勞作的農士,見《虎丘餞別圖》。從這些人物中可以看出沈周平時的生活軌跡,他是一個傳統的中國文士,既秉持著儒家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準則,喜好與文人雅士結交,于綠水青山中談詩論藝、共話世事;又向往著道家“無為而治”、“抱守虛靜”的澄懷觀道,孑然一身訪名山,杖策披棘待古松,體味隱逸孤野之樂。汪野亭筆下也有這樣的一群人,他們或是論詩訪友的文人雅士,見《修竹茅亭圖》、《石嵐飛瀑圖》、《空山秋色圖》、《攜琴訪友圖》等;或是粗麻短褐的平民百姓,見《空山雨后圖》、《溪山煙雨圖》、《湖濱垂釣圖》等;或是走山覓水的隱者高士,見《松林杖策圖》、《山水圖》、《長橋波影圖》等。這些人物的刻畫體現出沈汪二人作畫旨趣的一致,這種一致性是他們為人處世態度的折射,他們都深受儒家“入世”之法影響,喜好廣結各階層好友,且堅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文人風骨;又沉醉于道家“出世”之清靜無為,喜歡游歷山水,春慕“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夏賞“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秋感“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冬守“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這種題材的相似性源自于他們經歷的一致性。
首先,沈汪二人皆社會交往廣泛,他們結交的對象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這些形形色色人物就是他們繪畫的素材。沈周社會接觸面之廣在歷代隱逸畫人中是十分罕見的,使者、大夫、縉紳、好學者每天都到他家拜訪,可以說是絡繹不絕。從其墓志銘中可見沈周廣泛地與自己同道中人交往,這些人物大抵具有文人的身分,有一定的文化素養,能夠在雅集文會中舞文弄墨、共同參與文藝活動。除了與和自己有共同愛好的人交往之外,沈周還慷慨親和地對待無甚學識的白丁,“販夫牧豎”持紙來索畫,亦“不見難色”,[1]18“下至輿皂賤夫有求輒應。”[1]24汪野亭亦好廣泛交游,“月圓會”內八友自不必說,與瓷藝圈中的吳靄生、汪大滄、陳香生、余灶昌等也多有往來,還常與上層社會中愛好藝術的文人雅士賞瓷論畫。這些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時,或圍爐論經,或眠琴綠蔭,或當窗吟詩,或品茗作畫,極盡風雅淡泊之能勢。對待貧苦百姓,汪野亭也十分仗義。賣菜為生的樂平同鄉王榮初被指為地下黨遭當局逮捕,他以身家性命將他保釋;街坊或親朋間發生糾紛,他必不偏不倚,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解決糾紛,并自費赴茶館調解的茶資;因此,他受到眾人的敬仰,1942年辭世時,500多位各方人士護送其靈柩上船回樂平安葬。
其次,沈汪二人皆具文人風骨,雖與權貴交往,但并不屈膝阿附權貴為自己謀取利益。沈周15歲時就代父任糧長,赴南京接洽公事,那時的戶部侍郎崔恭是名愛好文學的雅官,沈周作了一首百韻詩上拜,崔恭見了大為驚異并有些懷疑這是否出自15歲少年之手,因而面試一首鳳凰臺歌,沈周援筆成詩,作得十分精美工整,崔恭大喜贊其為王子安(唐代王勃,字子安,六歲能詩文,少年作《滕王閣序》名震寰宇,初唐四杰之一)復生;沈周后來因畫藝卓絕、文采斐然、風骨高潔受到許多朝中重臣的青眼相待,如李相國、屠太宰、吳侍郎等皆傾心與之相交,聲名不可謂不煊赫。但有一次他被誤以為是卑賤的的畫工而被派去繪察院的壁畫,也是欣然前往。汪野亭也是這樣的一個人,雖不排斥與權貴交往,但并不刻意討好巴結,他1915年所作的墨彩瓷板《江山勝景圖》就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質獎,當時已成為全國最著名的瓷畫大師,作品供不應求。民國大總統曹錕曾派專人蒞鎮收購他的瓷板畫,平日也會與杜重遠之類的上層雅士坦誠相交。但對于他不愿結交的虛偽權貴,汪野亭不愿虛以委蛇,某專員五次求畫未果,其警衛拔槍相逼,專員按住手槍并訓斥手下休對先生無禮,汪野亭識破此雙簧戲法,促其開槍,專員掃興而去。
最后,沈汪二人皆好暢情于山水之中,或拄杖扣柴扉,或空山悟萬籟,或溪畔聆群響,這些體驗運用到山水畫中不僅有利于描山繪水,盡顯山姿水態,還有利于陶冶性情,更好地把握和表現人物的風韻。沈周一生極愛出游,有大量紀游感懷的詩作與畫作為證。有人將沈周旅游的地點,分類整理為:僧寺游、南京游、杭州游、天臺游、宜興游、虞山游以及吳中游。倘若瀏覽《沈周年譜》,可以發現沈周于成化乙酉(1465年)游南京之后,幾乎年年出游;直到正德己巳(1509年)逝世當年,83歲高齡的他,尚有宜興善權洞之游。汪野亭亦是如此,他自謂“一生好入名山游”,一為體驗,二為寫生,常道“山川脫胎于予也,予脫胎于山川也”,足跡遍布景德鎮及其鄰近的祁門、婺源、黃山、樂平的名山古剎。
然而,與沈周不同的是,汪野亭畫作中還有一類重要的人物——僧侶,《明月松間照》即是典范之作。畫作采用平遠式構圖法,構圖嚴謹有度,近景最顯眼的位置佇立著三棵古松,運筆勁健有力,松樹自古就與堅貞、隱忍、高潔等品質聯系在一起,劉禎《贈從弟》一詩有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凄,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畫者以樹皮上密集額橫點和突起的樹瘤來表現樹的風霜,最前面的古松態勢尤為驚人,幾乎與地面平行生長,但仍然生意盎然;這棵古松后站著一名僧侶,身著紅色袈裟,腳踏純黑僧鞋,雙手藏于寬袖之中,身體微微向前傾倚靠在面前古松上,頭部以45度角向上仰望,神情悠遠平和,仿佛已與天地融為一體;畫作中雖然并未繪出明月,但僧侶的意態、畫上的題款及整幅畫作籠罩的若有似無的清輝都間接表現出了明朗的月華,整個畫作虛實相生完美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幅松下望月圖,給人以靜謐、安詳、淡遠之感。
那么汪野亭為何對僧侶這類人物如此偏愛呢?這和他醉心于佛教有莫大的關系。佛家宣揚萬物皆空,以苦——人生皆苦、集——苦的原因、滅——超越苦難、道——脫苦之法為佛家“四諦”,即四大真理。汪野亭一生坎坷,佛家理念對其人生態度的構建、審美趣味的選擇、擺脫塵世的紛擾有重要的意義。汪野亭晚年社會動蕩,戰亂頻繁,瓷板畫生意每況愈下,長子和幼子還險被抓去充軍,這些都促使他多有出世之心,參憚悟道、誠心禮佛。這種禪意融貫于其山水瓷畫中形成了孤遠清寂、超凡脫俗的境界。同是“珠山八友”之一的王大凡為其作詩一首云:“煙水蒼茫疊疊山,孤云未許俗人攀;閑中每喜尋僧語,靜里常思學駐顏。”可以說是對其禮佛生活最好的刻畫。
(二)船行悠悠有真意
除了人物,行船也是沈周和汪野亭山水畫作中經常出現的意象。舟船雖是人造之物,但和自然界有著莫大的關系:首先,制作舟船的材料是取自自然界的林木;其次,舟船的制作是古人受自然的啟發而得。《世本》中記載古人“觀落葉因以為舟”,《淮南子·說山訓》中也說“見簌木浮而知為舟”,最早的“船”是用許多根木椽或竹桿扎成的木筏或竹筏,繼而是獨木舟,“挎木為舟,刻木為楫。”因此,舟船可以說是陸地和流水的交融,是天人合一的產物,是自然的饋贈和人類智慧的結晶,沈汪二人的山水畫作中多次出現的舟船正體現出他們已將己身融于萬籟之中,達到了物我合一之境。但是仔細觀察他們的畫作,我們可以發現二人畫的舟船有明顯區別。沈周的畫作中舟船一般為獨木舟或烏篷船,以烏篷船居多,見《京江送別圖》、《東莊圖》、《獨游孤山圖》等。汪野亭的60幅畫作中,舟船出現了26次,偶見獨木舟(見《客路青山圖》),但多是烏篷船和帆船同時出現在一幅畫作中,且帆船占據著主要地位,見《長橋波影圖》、《秋江帆影圖》、《破浪乘風圖》、《山川秀色圖》、《桃園問津圖》、《古剎鐘聲圖》等。舟楫雖小,卻可以反映出許多信息,從中可窺見沈汪二人人生軌跡的異同。
沈周出生于書香門第,家學底蘊淵博,從小接受的是正規的教育;15歲時接受父親糧長一職開始受俗務纏身,但也并未遇過什么坎坷辛酸;45歲時即將家中事務交付長子,過上屬于自己的閑云野鶴的生活,可以說沈周的一生是比較平順適意的,尤其是晚年他已完全步入了“詩意的棲居”。因此,他畫作中的舟船多是簡單的一葉扁舟,或者帶頂的烏篷船,這兩種船都比較適合獨自一人或邀朋攜友來一場短途的旅行,乘船者既可獨立于舟頭極目眺望,感清風入懷,聞百鳥啼鳴;又可與幾名友人藏于篷下,或躺或臥,品茗論詩,追古懷今。可見,沈周對現世生活基本是滿意的,他從未想過要前往某個遙遠的彼岸。
汪野亭則不同,他的求學和成藝之路一步步走下來充滿了汗水和辛酸。汪野亭家庭貧困,父親只是一個木匠,他自己開始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私塾先生。因醉心于繪畫,他決定放棄教書這份穩定的工作去學習美術,好在他父親和祖父都十分支持他的決定,他才得以考入江西省陶業學堂接受正規的教學、系統的培訓,為以后創作打下堅實的專業基礎。晚年經歷日寇入侵、山河破碎、風雨飄搖之難,更加看淡世事。同時篤信佛教,佛家宣揚的來世、輪回、彼岸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渴望前往一個安靜祥和沒有紛爭的彼岸。敦煌壁畫、帛畫、紙畫中的“觀音經變”里出現的舟船大多都是帆船,有個詞叫“揚帆遠航”,帆船似乎冥冥之中就給人一種可以將人帶往遙遠的極樂之土的感覺。除此之外,白色風帆在水中漂蕩搖曳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水上飄浮的白蓮,佛教在很多地方都以蓮為代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蓮即是佛,佛即是蓮。汪野亭在1942年創作的《古剎鐘聲圖》上題詩曰:“古寺晨鐘響入云,客帆風正洗潮平,林泉到處皆名勝,山水之間有妙人。”將帆船和古寺連在了一起,那客帆的歸處正是古寺。帆船正是他用以表明自己身處此世,心向彼世的意象。
三、小 結
沈周和汪野亭都是各自時代中聲名煊赫的杰出人物,汪野亭融“粗沈”之貌于己變革的“粉彩山水瓷畫”,一掃前人瓷作之弊端,首創詩書畫印于一體的“通景構圖法”,成為瓷繪界競相借鑒和模仿的典范,一直傳承沿用至今。他們的創作題材也多有重合之處,但汪野亭在沈周的基礎上又有自己的特色[7]。兩代大師隔著數百年遙遙相望,他們之間必然存在著還未被發現的相同和不同之處值得我們進一步探尋。
[1][元]馬祖常.石田先生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6.
[2]汪雪媛,江葆華.汪派山水瓷畫藝術[J].景德鎮陶瓷,2008(3):15-16.
[3]劉靜.從“雪白”的使用看汪野亭瓷畫之藝術風格[J].藝術市場,2008(2):72-73.
[4]張建軍.中國畫論史[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
[5]潘運告.漢魏六朝書畫論[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7.
[6]楊大年.中國歷代書畫采英[M].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87.
[7]王小梅.論汪野亭瓷板畫之淵源[J].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3(6):63-65.
(責任編輯:鄭宗榮)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Shen’s Literati Landscape Painting and Wang ’s Porcelain Plate Painting of Landscapes
ZHANG L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Shen Zhou influences Wang Yet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tter’s works by means of comparing the drawing style and subject matter in Shen’s Literati landscape painting and Wang’s porcelain plate painting of landscap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e their mental course, so that Wang Yeting’s porcelain plate painting can be known by more people.
Shenzhou; Wang Yeting; learning from the past and creation; style; theme
J211
A
1009-8135(2014)05-0064-05
2014-05-10
張麗娜(1991-),女,江西南昌人,華中師范大學2013級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文藝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