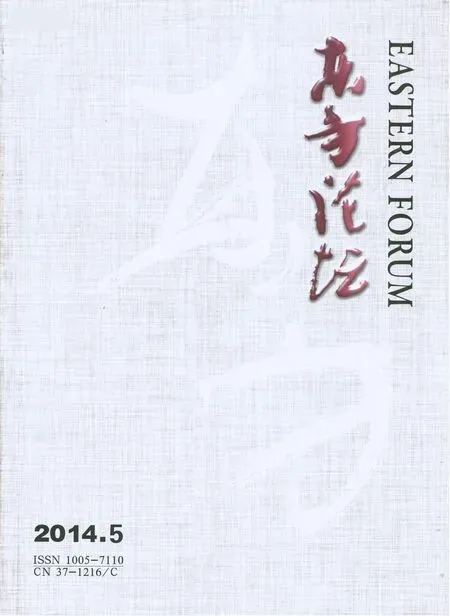“微物”的“神”性——論阿蘭達蒂·羅伊視野中的賤民形象
黃怡婷
(中國社會科學院 外國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印度女作家阿蘭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是一位很特別的作家。她蜚聲國際文壇,但她至今只創作了一部小說——《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1997)。她的出版物很多,除了《微物之神》這部獲得1997年英國布克文學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的小說之外,她的大部分文字是與印度時政緊密相連的中短篇評論文章。她不是一個單純的作家,人們在提及她時,往往會同時突出她的另一個重要身份:積極介入時政評議、維護底層平民利益的社會活動家。其實,《微物之神》這部小說也與印度的時政密切相關。本文試圖借由闡述《微物之神》小說中維魯沙、瑞海爾和維里亞巴本這三個人物身負的個人力量,分析小說的題眼“神”字,從而試評作者羅伊對印度底層民眾作為個體如何成長并獲取力量的思索,及其對推動印度社會發展的價值。
一、卑微者的力量
羅伊在談及自己的寫作時說,“我沒覺得《微物之神》和我的非小說作品之間有巨大的差別”[1](P36),而且“我寫的許多作品的主題,小說也好,非小說也罷,都是權力(power)與無權(powerlessness)的關系和它們之間無盡的循環斗爭。……我的寫作無關國家和歷史,而是關乎權力。關乎權力的偏執和冷酷。關乎權力的本質特性。”[2](P14-15)羅伊聚焦權力問題源自她對印度社會現狀的判斷。她曾說,印度“這個分層級且水平分離的社會……沒有通婚,沒有社會融合,也沒有人際——人道——互動以團結各階層。所以,當社會的那底層半部分被切斷并消失時,它發生得悄無聲息”[3](P6);而在另一方面,“掌權者了解真相”[4](P76),但他們并不在乎,且仍會以傷害底層民眾的方式固化社會形態,維護自己的特權。因此,在印度“種姓、階級和權力大體一致的傳統模式目前仍未從根本上發生變化。”[5](P141)印度著名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也認為:“不作為仍是當前印度經濟的一個中心問題——表現出常見的營養不良、普遍的文盲、高發病率和死亡率等形式。這是對人類應重視的基本自由的否定,而且這些不足在人們參與經濟擴展和社會變動的實踐中將嚴重限制人們的機會。”[6](P30)在印度這樣一個獨特的種姓社會中,處于底層的賤民群體和落后種姓顯然便是承受這上述印度“中心問題”折磨的主體,是印度社會中“無權”的那一方代表。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羅伊曾明確表示自己只為“無權”的底層民眾寫作,并隨之確立了自己的寫作目的,即引導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只有發出了聲音,才有被關注的可能,才有擺脫受壓迫社會地位的希望。而要發出聲音,就要有能力講述自己的故事——不僅僅是事實,更重要的是如何講述它。為此羅伊曾經這樣表述她的寫作策略:“事實并不是唯一的真相。你講故事的方式,展開敘述的形式,也是一種真相。……要以一種普通人能夠理解的方式講故事,從那些專家、學者、經濟學家和確實在進行誘騙的人們那里奪回我們的未來。”[4](P77)
在《微物之神》這部小說中,羅伊透過一對七歲雙生子瑞海爾和艾斯沙未受種種社會規范禁錮的純凈眼睛來觀察阿耶門連這個位于印度克拉拉邦的小村落,以兩位主人公——出身信仰敘利亞正教望族家庭的離婚女子阿慕和青年木匠賤民維魯沙——與周圍人的關系糾葛和矛盾沖突,來詮釋上世紀六十年代印度鄉村傳統社會中不同階層、種姓和性別的人群之間的權力關系和斗爭,展現了“權力的偏執和冷酷”和它所造成的印度社會畸象。不過,正如物理學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總是共生共存,權勢重壓之處也必有反對強權的力量萌發,這正呼應了羅伊所強調的“power”一詞的另一層意思,即力量①根據《朗文當代英語辭典》,“power”一詞作為名詞,主要包含兩方面意思:一為控制或影響人或事的能力,可譯為“權力”;二為從事某項事情的能力,可譯為“力量”。(參見《朗文當代英語辭典(第三版增補本)》,英國培生教育出版有限公司編,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1102 頁。)。
羅伊曾在其多部作品和采訪中反復強調,不論面對的是裹挾著強大資本而來的帝國主義侵略,還是在印度古老土地上植根數千年的傳統陋習傷害,亦或是隨著時代變化而新產生的民眾權力喪失等等,印度的普通民眾要發掘自身力量,要“把我們的耳朵貼到地上,并尋找理解這個世界的其它方式”[7](P46)。為此,普通民眾要做的是“磨礪自己的記憶,……從自己的歷史中學習”[8](P76),最終用“我們講述自己故事的能力來斷絕它的氧氣,羞辱它,嘲笑它”[8](P77)。比如,《更大的共同利益》(The Greater Common Good,1999)一書分析了高種姓群體對低種姓群體的專制和壓榨,著力于為后者拓展更廣闊的社會生存空間;而《普通人的帝國指南》(An Ordinary Person’s Guide to Empire,2004)則揭示了在全球化、現代化過程中,政府和外國資本如何聯手剝奪賤民和原住民(adivasi)的利益,使他們失去生活的依靠;在《傾聽蚱蜢》(Listening to Grasshopper,2009)中,她則聚焦當代印度的民主進程,致力于創造聯系,以期消除因宗教信仰和種姓階層不同而生的對立和仇視給人們帶來的種種災難和傷害。而在比羅伊的大多數政論作品更早問世的《微物之神》中,她的這一理念已經有了較全面的表現。男主人公維魯沙這一形象就是羅伊理想中印度普通民眾力量在小說中的化身。他不但在追求政治地位、情感交流和社會交往等方面都體現出與他的父輩截然不同的態度和做法,對社會權力不平等狀況全面反叛,而且他出眾的個人能力使他成為追求羅伊在小說中探索瓦解印度社會傳統權力體系,達成底層民眾能夠“講述自己的故事”這一目標的關鍵所在。
維魯沙的力量首先表現在他勇于參與政治斗爭活動來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而且他的勇氣不僅體現在他為此采取了行動,更在于他在政治立場上有著其他人所不具有的純粹、堅定的態度。工會運動的發起人和印共果塔延地區的負責人皮萊把組織工會和抗議游行當成他撈取政治資本、改善個人生活的工具;工廠主恰克則把成立腌果廠工會當成他實現個人政治理想的試驗田;而其他普通工人雖然多少也參與工會活動,但卻沒有一個真把它放在心上的。只有維魯沙是正式黨員和工會會員,而且參加了標志性的科欽游行。這展現出他鮮明的、毫不遲疑也毫無心機的向往,向往能夠經由為政治理想奮斗帶來社會地位的提升,從而享有展現才華、改善生活的機會。當其他所有卑微的工人、仆人尚滿足于眼前為人仆、為人奴的生活時,他作為一個最卑微者,對自己的未來卻懷抱著如此光明的暢想。這表明維魯沙確實如羅伊所愿的那般,是努力“尋找理解這個世界的其它方式”的一員,而不再是其他那些被動接受現狀,毫不重視自身力量的一般民眾了。
在愛情中,維魯沙同樣具有強大的力量,這體現在他能夠對青梅竹馬阿慕奉獻出最真摯且不由自主的愛情。綜觀整部小說,愛情是罕見的:帕帕奇與瑪瑪奇之間毫無夫妻之情可言,有的只是暴力控制和被動馴服;皮萊夫婦的互動中體現更多的是搭伙過日子的現實;恰克與瑪格麗特的婚姻則擺脫不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召喚和追隨關系的濃重意味;至于工廠中的普通工人和賤民維里亞巴本夫妻,則壓根兒就沒什么感情生活可言。反觀維魯沙與阿慕之間的互動:阿慕的美麗、直率和對不幸婚姻的抗爭,深深地吸引了維魯沙;而維魯沙英俊的面孔、健美的身材、總是展現在臉上的“微笑”[9](P163),尤其是他在機械上的天分,對阿慕也有著一股不言而喻的吸引力。他們倆的互相靠近,主要是基于對對方內在和外在美的戀慕。這表示維魯沙對自己生而為人擁有平等愛人和被愛權利具有深切認識,并且能夠以純然的、不帶任何功利的眼光欣賞人類情感的美好。他對待愛情的這一態度首先是對種姓制度的蔑視。按照《摩奴法論》的規定,高種姓男子勉強可以娶低種姓女子,卻從沒有低種姓男子與高種姓女子這樣的婚配[10](P42)。而在父親帕蓬這位順從的老“帕拉凡”①小說原文為paravan,賤民的一種。(見Arundhati Roy,The God of Small Thing .London:Fourth Estate,2009,p.76.)眼中,他更是具有“帕拉凡”所不該具有的“不正當的確信”[9](P68),面對愛情,想愛就愛了。其次,這也是對傳統男權統治的棄絕。他并不追求像阿慕的前夫、兄長等人那樣對阿慕的命運擁有統治力,而是期待與心上人平等相戀,這更體現了他對自身情感力量的肯定。
此外,維魯沙在爭取社會政治地位和個人幸福中體現出的勇氣顯然源自他所擁有的最優秀的職業技能。筆者認為,作者羅伊也正是借由賦予維魯沙以認識機械構造和操縱接卸產品的極高天分,道出自己對印度底層人民如何才能“有能力講述自己故事”的思考。維魯沙的天資和勤勞,使之深得主人家的賞識。瑪瑪奇出資送他去讀書,并稱贊他如果“不是一個帕拉凡,那么他可能成為一個工程師”[9](P67)。恰克認為“他的價值是無法估計的,實際上,經營工廠的人是他”[9](P258)。可以說,維魯沙以一己之力撐起了腌果廠的技術重擔;沒有他,腌果廠是不可能正常運轉的。
聯想到羅伊在她的新作《傾聽蚱蜢》中所指出的,當今的印度政黨都是在有利自己的輿論宣傳之下,極力控制學校、醫療機構和災備管理機構。“他們理解無權。他們也理解人民,特別是無權的人民,不單有實際的、單調的日常需求和渴望,還有情感的、精神的、娛樂的需要。……‘奪取權力’這一傳統主流左翼理想……已不能順應時代了。”[11](P39-40)羅伊對印度政黨運作模式的這一解析表明,在保證政黨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為大眾或至少一部分民眾,提供平民教育和人身安全保障是一個政黨獲取支持的關鍵。羅伊的這部書出版于2009年,這可說明當今的印度普通民眾已普遍意識到教育權和生存權的重要性,尤其獲取教育機會是提升個人發展空間的根本所在。再看小說,我們可以認為羅伊讓生活在上世紀60年代的維魯沙接受高于當時絕大部分賤民所獲得的教育,輔以他本身的天分,使他擁有超出大多數人的專業技能,正是她心中對底層民眾如何獲得發展的思考在小說中的體現。
維魯沙稱得上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賤民形象,但羅伊并沒有把維魯沙的命運也同樣地理想化。他的死與他所處的社會群體在社會生活和政治斗爭中的弱小有密切關系。站在維魯沙的角度來看,與阿慕的相戀是他追求自我發展的必然結果,父親和伊培家族的激烈反應是他無法避開甚至應在預料之內的社會現實,唯有皮萊這位發動他抗爭的引路人最終的背棄是他沒有想到的。皮萊作為印共果塔延地區領導人和工會的發起者,只關注于追逐自身政治利益而非真把賤民種姓或工人階級的權益放在心上,使得維魯沙失去了社會能為他提供的唯一一重保護,被徹底地拋入了絕望之中。“革命”“黨的利益”等等成了“另一種和自己敵對的宗教,另一個由人類心智所建造,卻被人性所摧毀的建筑物”[9](P264-265)。回顧印度獨立之后各種姓群體在政治活動中的相互博弈,可以看到:總體來講,占據印度人口16.2%的賤民群體[12]得到了歷屆政府的扶持和幫助,生存條件和社會地位有所改善,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仍處于社會的最底層,社會的主要資源還是把持在高種姓人群手中[13](P320-328)。同時,由于印度的全民普選制,任何黨派要獲取政治權力,都必須得到足夠多選民的支持。于是,人口眾多的落后種姓和賤民群體手中的選票成了各政黨都需要極力爭取的目標。這樣,就出現了美國學者布拉斯(P.Brass)所謂的“極端聯合”(coalitions of extremes)[14](P68),即把持權柄的高種姓政客與低種姓民眾聯合以獲取選舉勝利,而在實際操作中則往往是“高種姓領導人利用了達利特②英文為Dalit,是印度取消賤民制后對原來賤民的稱呼。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Dalit[OL]。……工人們”[14](P69)。前者得到預期中的政治資源后,是否還與他的底層支持者們站在一起,常常要打一個問號;而處于弱勢地位的底層民眾面對這樣的局面,往往是無力還手,只能忍氣吞聲。事實上,羅伊本人對這部小說名字的解釋也呼應了上述現實狀況,即它要表達的是“世界是如何侵入小事件和小人物的。而且正是緣于此,源于人們絲毫不受保護,……這個世界和社會機器就侵入到他們最微小又最深處的核心,并改變了他們的生活”[15](P305)。由此可見,在印度這樣一個獨特的民主社會中,出身低賤的卑微者們若光是挖掘自身的“力量”,仍難以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社會境遇,他們還需要占據社會大部分優勢資源的高種姓群體中有識之士的大力援助。
二、卑微者的解放
從印度近現代史來看,這個國家的“政治始終由傳統精英群體掌握”[14](P67)。換言之,印度社會的任何變革都離不開上層高種姓精英群體的推動或配合。在種姓問題上,也不例外。長期主導印度政壇的國大黨歷代領袖便為消除種姓歧視,推動社會融合而不遺余力,其影響力并不亞于往往單槍匹馬的賤民領袖。屬于婆羅門種姓的開國總理賈·尼赫魯(J.Nehru)曾表示:“大家知道,我將根絕種姓制度擺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這是導致我們國家虛弱的最主要因素。”[13](P321)在他任內,廢除賤民制度,保護賤民權益的條文寫進了印度憲法。另外,他的女兒英·甘地(I.Gandhi)能得國大黨元老們推舉為總理,理由之一也與她對待種姓問題的態度有關:“(她)在自由運動的大人物中成長起來,具有理性和現代思維,完全沒有任何派別主義——邦、種姓或宗教。”[16](P140)這兩位執政時間最長的印度總理對消除種姓制度影響的堅持奠定了印度政界精英群體對待種姓問題的基調。
在小說《微物之神》中,另一位主人公、阿慕的女兒瑞海爾的所作所為正體現了這一群體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作為伊培家族的一員,瑞海爾的出身帶著與生俱來的神圣①瑞海爾的曾外祖父曾接受過敘利亞基督教正教總主教的祝福,后成為當地最受教徒愛戴的神父。(見《微物之神》第20-21 頁。),但她并沒有像家族的領導者外祖母、姑婆等人那樣成為這種家族神性的捍衛者,更沒有把這種宗教上的優越感帶入到與低種姓的交流中②按照小說中廚傭克朱瑪利亞的說法,只有非賤民才可以信仰敘利亞基督教正教。(見《微物之神》第158 頁。)。童年時代,她把維魯沙視為“最親愛的朋友”[9](P63)。在隨后的成長過程中,她也一直保持著對卑微者或卑微事物的親近之意。在修道院寄宿學校讀書期間,她曾給牛糞裝飾上鮮花,于是被罰當眾朗讀牛津字典中“墮落”一詞的定義。評論家福克斯認為,她的這個舉動不單是對傳統規范的一種反抗甚至挑釁,也表明“她有興趣并有能力發現卑微事物的美”[17](P40)。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她對卑微事物的欣賞,暗示了她對處于社會主流之外的社會底層民眾價值觀的認同和力量的肯定。而且,瑞海爾不僅具有精神獨立性和平等意識,她還能把自己的力量傳遞給胞兄艾斯沙,助他抵御人生巨變的打擊,走出上一代人悲劇命運的心理陰影。艾斯沙的身份和經歷很特殊。他原本應該是伊培家族的繼承人之一,但母親阿慕與維魯沙的私情曝光,加上倫敦來的表姐蘇菲意外溺亡,一夕之間改變了他的命運。有學者因此認為,艾斯沙成年后的沉默是“對卑微者的一種極端回應”[17](P39)。一方面,他受家人操縱,違心指控維魯沙以維護家族名譽,又無辜背負了為表姐蘇菲之死負責的罪名,終被逐出家門,成了各方勢力維護自身利益的犧牲品;另一方面,客觀上他是導致維魯沙慘死的推手之一,并為此感到愧疚悲傷,可是從來沒有人留意過他的這一番心緒。家族和社會中各路人馬斗爭的結果使他從一個富家小少爺無可抵御地淪入社會的邊緣人群,深切體會了身為卑微者的悲哀,沉默成了他唯一能選擇的抗爭方式。由此,若對比艾斯沙與維魯沙的命運,我們可以發現他們之間的相似之處:前者生就高貴血統,成年后卻落魄低賤;后者天生聰慧勇敢,卻以慘死獄中了局。他們一個主動選擇了沉默,一個被迫永遠沉默,都是被社會遺忘的人。這樣,瑞海爾對艾斯沙的主動靠近和安撫就具有了雙重的救贖意味。作者寫道:
“她移動她的嘴。
他們美麗母親的嘴。
挺直坐著,仿佛等著被逮捕的艾斯沙將手指伸向那張嘴,觸摸它說出來的話,握著它的呢喃。他的手指循著它的形狀移動,然后觸摸牙齒,然后,他的手被握住了,被親吻了。”[9](P302)
瑞海爾和阿慕在形象上的重疊,使得兩代人的情感遭遇也得以重疊。瑞海爾對艾斯沙的撫慰,同時也是給予維魯沙的。從這個角度來說,瑞海爾的舉動已經超越了個體情感交流的范疇,具有了不同社會階層、不同種姓的人們尋求互相理解、交流和支持的象征意義。同時,親吻、撫觸這樣極親昵的肢體動作又透露出兄妹間濃厚的溫情,傳遞出作者所關注的人性關懷。簡言之,從瑞海爾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所期待的不是社會優勢群體挾種姓或宗教優越感,行慈善之事,而是不同社會群體間基于人人平等原則而進行的對等的交流,并最終達成情感上的接納甚至融合。
三、卑微者的“神”性
在印度這樣一個舉世無雙的宗教國家,自古以來萬物都有其“神”性①根據2001年印度人口普查報告顯示,99.93%的印度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剩下的0.07%印度人,他們的宗教信仰未得到統計。(參見”Census of India,2001”,http://www.tn.gov.in/deptst/areaandpopulation.pdf [OL])。。及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為順應世界資本主義大發展的潮流,印度掀起了種姓改革運動和賤民解放運動,連原本不潔的賤民都逐漸開始擁有自己的宗教神性。當時,幾乎所有的民族主義社會改革家都態度堅決地聲討賤民制度[13](P321),而“大雄”甘地(M.K.Gandhi)和賤民領袖安培德卡爾(B.R.Ambedkar)是其中兩面最具號召力的大旗。甘地曾經在上世紀30年代為改良印度教種姓制度,廢除“不可接觸制”,發起為賤民爭取種姓平等地位的“哈利真運動”(harijan movement)。“哈利真”一詞由名詞“hari”和動詞詞尾“jan”構成,“hari”是印度教大神毗濕奴的稱號,“jan”在印地語中則意為“出生”,因此這個詞意即“大神之子”。甘地用它來代替“不可接觸者”,指稱被排除在傳統種姓體系之外的賤民群體[18]。這個名稱表明甘地首先把賤民納入到原本只接納種姓教徒的印度教體系內,其次他還給予賤民與種姓教徒平等的教內地位。在印度這樣一個以印度教為主流的宗教國家內,甘地的這一立場給建立在舉世無雙又“無懈可擊的神學和哲學基礎之上”[5](P65)的種姓制度帶來的是一場強震,為賤民謀求平等、自由的發展機會開辟了一條道路。另一位改革家安培德卡爾本身即為賤民出身。切身的社會歧視體驗令他在為賤民謀求在印度教體系內的“平等、民主和博愛”[19](P87)時,比甘地更為迫切。當他發現在印度教內不能獲得滿意的斗爭成果后,不惜號召自己的數十萬追隨者皈依宣揚“眾生平等”的佛教,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新佛教運動”(Neo-Buddhism),并對佛教經典按照有利于賤民解放運動的原則進行了重新詮釋。從這兩位印度近現代賤民解放事業領袖的主張來看,他們都是借由肯定賤民在宗教體系內與種姓教徒的無差別的信徒地位,賦予其宗教“神性”,從而達到解放賤民群體,改良甚至瓦解種姓制度,促進印度社會向現代轉型的目的。
然而,并非每一個“微物”都會覺悟到自身所具有的“神”性。相對于歸屬種姓體系內的普通民眾,賤民群體無疑在政治、經濟、宗教及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的地位都處于人群的最底層。他們首先是卑微者——辛勤勞動卻只能維持最低生活保障,無力更無意識對自己的命運作任何改變。小說中維魯沙的父親維里亞巴本就是這一人群的典型代表。作者寫道,他是一個“舊世界的帕拉凡,曾經歷過‘倒著爬’的日子”[9](P67)。他被花崗巖碎片弄瞎了一只眼睛,而瑪瑪奇出錢為他安裝了一顆他無論如何無法自己負擔的玻璃義眼。此后,“沒有人”,包括瑪瑪奇,“期望維里亞巴本還清”這個債務;而后者則從此對瑪瑪奇及其一家人“懷著一種如泛濫河水般深而廣的感激之情”[9](P67)。在這件事情中,雙方的態度正體現了印度村落中居于掌權地位的高種姓富有家族與處于依附地位的賤民群體之間的傳統關系:在“超經濟”的賈吉曼尼制度下,“低種姓依附于高種姓,前者世代為后者提供各種服務,并接受一定的實物作為報酬”;在這種“固定的主子——奴仆關系”中,高種姓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面都擁有低種姓的絕對忠誠[5](P249-256)。維里亞巴本的“忠誠”[9](P238)顯然是毋庸置疑的。他以主動告發兒子維魯沙與阿慕的戀情來表達他效忠主人甚至“愿意徒手殺死他的兒子,愿意摧毀他的創造物”[9](P69)的心意。從這一角度來說,他的所作所為體現出來更多的是種姓制度所施加在他身上的奴化意識,而非他自然流露的個人情感。
不過,即使是這樣一個謹守賤民言行準則的面具式人物,卻也有感情外露的時候。小說中寫道,他選擇在一個預示神祇發怒的暴雨天,用酒麻痹了自己,又向瑪瑪奇歷數了伊培家族歷代對自己家族的恩惠以說服自己,最后涕淚交流地向瑪瑪奇坦白了那對青年人的一切。可見,他雖然在理性上堅定選擇了“忠誠”,內心卻因對兒子的“愛”[9](P238)而飽受煎熬,而他做出告發舉動那一刻的大雨滂沱與老淚縱橫則是他的“忠誠”與“愛”最凸顯也是矛盾最趨激烈的時候,道盡了這位老人的悲哀與傷心。由此可知,作者對這一人物是“哀其不幸”的。
此外,對于維里亞巴本從無改善自身生活境遇的抗爭意識,作者羅伊也并未顯露出任何“怒”氣,正如她自己所說:“一個人既不可能足夠強大,亦不會太過弱小,以致可置身事外。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是完全被卷入到這個世界運轉的方式中去了。”[4](P49)同樣地,維里亞巴本既是一個從“舊世界”過來的老“帕拉凡”,他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便也只能是老式的了。只是他這番義無反顧地告發,雖然成全了自己“忠誠”的好名聲,代價卻是他珍如生命的兒子付出了一條性命——尤其他是明知其結果而為之,便讓人在痛心于他的順從之外,更感到一股使人不寒而栗的絕望。這在事實上是一種泯滅人性的做法,是間接的自我毀滅,也是對自我力量的徹底否定。因此,作者雖不是“怒其不爭”,但始終是“嘆”其不爭的。而維里亞巴本堅持賤民的“忠誠”卻換來凄慘晚景,這也從側面暗示了作者對維魯沙尋求發展自身力量的肯定。
維魯沙本應是一個和他的父親一樣身份、地位的最卑微者,但他卻成長為羅伊筆下的“微物之神”①小說中作者兩次以阿慕的角度描寫維魯沙,并稱其為“微物之神”(參見《微物之神》第208、304 頁)。,具有了“神”的光彩。維魯沙作為渺小“微物”的一員,卻在政治、經濟、社會地位乃至個人情感追求等方面都向強大的社會傳統發起挑戰,他的力量所迸發出的光芒令人炫目。他在思想上的大膽突破和在職業地位上的超然獨立,無疑正符合羅伊對印度普通民眾,尤其是賤民的殷殷期望。從這一角度來說,維魯沙是當之無愧的“微物之神”。他的“神性”是他作為一個純粹的人主動沖破一切社會束縛,努力挖掘自身各種力量而獲得的,早已超出了印度傳統宗教和種姓制度框架內某一類人所應具備或只能具有的能力。
顯然,羅伊在小說中沿用了甘地、安培德卡爾等先驅者為卑微者披上的“神性”光環,不過她筆下的這一卑微者的“神性”已大大突破了宗教的禁錮。這從作者所設置的故事背景中也可看出一二。首先,小說的整個故事發生在印度南部克拉拉邦的敘利亞基督教正教信徒社區,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最強調種姓制度的主流印度教文化氛圍。其次,在小說的第十二章,作者對當地的卡利卡沙舞有一段專門描述:舞者們在舞臺上演出的母親貢蒂、婚生子般度五子及其私生子迦爾納之間的故事與大史詩《摩訶婆羅多》中描寫的主要情節并無二致,但演出這部戲的舞者們卻早已遠離了那個信仰純真的年代。正如作者所言:“他(指卡利卡沙舞者)訴說諸神的故事,但是他的故事出自不敬神的人心。”[9](P217)由此可見,宗教神權的大大削弱,使得原本披著神性外衣的種姓制度在某種程度上開始慢慢轉變成一種可被改造的社會規范,不再是神圣不可褻瀆的宗教制度的一部分。這樣,小說中各種人物本身的思想和性格特質就得以凸顯,從而使這“神性”轉而主要表現為底層民眾,尤其是賤民,依靠自身的努力和人格魅力發展自己,顯現力量,并最終在維魯沙身上得到集中體現。由此,羅伊大大擴展了卑微者“神性”光環的輻射范疇,強調了印度底層民眾尋求發展、自由和平等地位的主動性和必然性,并得以從人道關懷的高度來照拂她對整個印度社會發展的期待。
從維魯沙與阿慕的故事開始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到雙生子返回故鄉的九十年代,小說的時間跨度達三十年之久。這三十年是印度獲得國家和民族獨立后重要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轉型期。在這個時期內,伴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民主政治進程的推進,印度政府持續加大對賤民群體在教育、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賤民已經崛起為印度政治舞臺上的一支新興力量,“種姓政治”成了形容印度政壇的關鍵詞,其“影響幾乎無處不在,不僅僅局限于政治領域,而且進入教育與官僚機構”[13](P334)。這樣的變化在造就賤民精英群體的同時,也在事實上強化了“賤民”這一身份標簽,使得“消滅賤民制”[13](P328)這一印度歷屆政府的目標化為烏有。更甚者,以“利益”[13](P339)為核心的現代種姓政治活動甚至還加劇了賤民群體內部精英分子與普通民眾之間的距離[13](P335),加上不同種姓之間原有的森嚴壁壘,使得絕大多數仍生活在貧困和文盲狀態中的賤民群體難以獲得改善生存條件的機會[13](P326)。
對照現實,小說中羅伊筆下的這兩代人承受著和印度社會中千千萬萬普通民眾一樣的重壓,但他們身上人性的光輝與個人情感的流露給這殘酷的生活蒙上了一層面紗,使之不再顯得赤裸裸以利益為先。小說結尾一章,阿慕與維魯沙在河岸邊身與心的融合美得有如童話般不真實,但這何嘗不是羅伊面對印度這樣一個“分層級且水平分離的社會”的殷切期待呢?正如她自己所言,“我持續進行寫作、思考。我是在尋求一種理解。不是為我的讀者,而是為了我自己。這是一個探索的過程。……也是一個推動我自己更長遠和深入地看待我所生活著的這個社會的方式。”[4](P74)而她對這個社會的不斷“探索”顯然已向世界各地的讀者們展示了“理解這個世界的其它方式”,并極大地觸動了他們對自己現實生活的看法②羅伊在接受采訪時曾非常欣喜地談到人們讀了她的小說之后給她的各種反饋。這些反饋主要涉及讀者對家族關系的看法、對社會關系的思索、對婚姻的體會、對童心和鄉土描寫的欣賞、對恐懼的克服等幾方面問題。讀者們或表示有所共鳴,或表示激發了新的感悟。參見Shoma Chaudhury,“Ten Years On …”,The Shape of the Beast:Conversations with Arundhati Roy [C].London:Hamish Hamilton,2010.p.236.,使人們不因“無力看到這個世界既定模式之外的樣子”[2](P17)而困于絕望之中,失去力量。這就是羅伊這位曾經如瑞海爾般遭受傷害、卻頑強實現自我成長的女作家,為現實社會中千千萬萬個“維魯沙”和“阿慕”所做出的實實在在的努力。從這一角度來說,羅伊本人可稱得上是另一番意義上的“微物之神”。她作為第一位獲得重大國際英語文學獎項的印度本土作家,其里程碑意義或許在這一點上可以得到更好的體現。
[1] David Barsamian.“The Colonization of Knowledge”[A].The Shape of the Beast:Conversations with Arundhati Roy[C].London:Hamish Hamilton,2010.
[2] Arundhati Roy.“Come September”[A].The Ordinary Person’s Guide to Empire[M].London:Harper Perennial,2004.
[3] N.Ram.“Scimitars in the Sun” [A].The Shape of the Beast:Conversations with Arundhati Roy[C].London:Hamish Hamilton,2010.
[4] David Barsamian.“Development Nationalism” [A].The Shape of the Beast:Conversations with Arundhati Roy[C].London:Hamish Hamilton,2010.
[5] 尚會鵬.種姓與印度教社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6] 阿瑪蒂亞·森,讓·德雷茲.印度:經濟發展與社會機會[M].黃飛君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7] Arundhati Roy.“The Loneliness of Noam Chomsky”[A].The Ordinary Person’s Guide to Empire[M].London:Harper Perennial,2004.
[8] Arundhati Roy.“Confronting Empire”[A].The Ordinary Person’s Guide to Empire[M].London:Harper Perennial,2004.
[9] 阿蘭達蒂·羅伊.微物之神[M].吳美珍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10] 摩奴法論[M].蔣忠新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11] Arundhati Roy.“‘And His Life Should Become Extinct’:The Very Strange Story of the Attack on the Indian Parliament”[A].Listening to Grasshoppers[M].London:Penguin Books,2009.
[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lit [OL].
[13] 王紅生.論印度的民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14] Christophe Jaffrelot,“Caste and the Rise of Marginalized Groups” [A].Sumit Ganguly,Larry Diamond and Marc F.Plattner,ed.,The State of India’s Democracy[C].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7.
[15] E.Nageswara Rao.“South Asian Writers in English:Arundhati Roy” [A].Fakrul Alam,ed.,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Vol.323)[Z].GALE,2002.
[16] 王紅生,B.辛格.尼赫魯家族與印度政治[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17] Chris L.Fox,“A Martyrology of the Abject:Witnessing and Trauma in Arundhati Roy’s The God of Small Things”,ARIEL [J],33.3-4(2002).
[18]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ijan [OL].
[19] Owen M.Lynch.The Politics of Untouchability: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a City of India[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