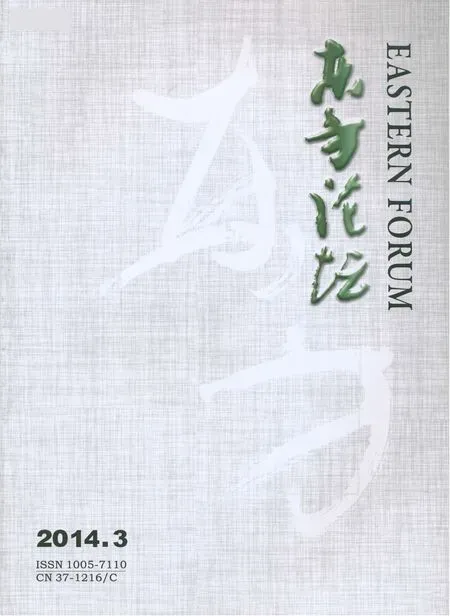論行賄罪受賄罪互動規(guī)制之完善
——基于囚徒困境理論的思考
董 桂 武
論行賄罪受賄罪互動規(guī)制之完善
——基于囚徒困境理論的思考
董 桂 武
(青島大學 法學院,山東 青島 266071)
刑法第390條第2款規(guī)定的行賄罪特別自首制度的設立目的主要在于通過對行賄人行賄行為的輕打擊以換取行賄人揭發(fā)受賄人的受賄行為。我國司法實踐存在輕打擊行賄罪重打擊受賄罪的現(xiàn)象,同時存在著不合法的對行賄罪潛規(guī)則不起訴。囚徒困境原理揭示在行賄罪被免予起訴的情況下,行賄人較優(yōu)的選擇是揭發(fā)受賄行為。行賄罪與受賄罪互動規(guī)制中,應引入辯訴交易,且行賄罪特別自首制度應改為行賄罪特別自首、坦白制度。
行賄罪;受賄罪;規(guī)制;囚徒困境;辯訴交易
行賄罪、受賄罪作為對合犯罪,常常發(fā)生在“一對一”的情況之下,一方面行賄人與受賄人的犯罪證據(jù)難以取得,另一方面行賄人與受賄人又是具有同盟關系的犯罪共同體。這導致諸多賄賂犯罪難以偵辦,數(shù)量眾多的行賄人和受賄人逍遙法外,受不到應有的懲處,產(chǎn)生了大量賄賂犯罪黑數(shù)。因此,我國刑法規(guī)定了行賄罪特別自首制度以換取行賄人如實招供其行賄行為,從而打擊受賄行為。我司法實踐卻常常進一步以放棄打擊行賄人以換取行賄人供述受賄人的受賄證據(jù),從而打擊受賄行為。但是,從今年起,我國檢察機關改變了過去司法實踐中的輕行賄重受賄的刑事政策,加大了懲治行賄犯罪力度,寄希望通過懲治行賄行為預防受賄行為。問題是,輕行賄重受賄的互動刑事政策①在規(guī)制賄賂犯罪中是否具有合理性?在何種程度上具有合理性?是否需要改進或設計相關制度以促進對賄賂犯罪的規(guī)制?新調(diào)整的行賄罪和受賄罪同等打擊的刑事政策能否實現(xiàn)我們遏制腐敗的預期目標?
在行賄罪和受賄罪是否同罰的爭議上,我國學者一直存在著不同的主張:第一種觀點主張行賄罪和受賄罪的社會危害性并不等同、我國行賄罪受賄罪刑罰結(jié)構偏重,因此,行賄罪和受賄罪不應該同罰,[1]有學者進一步認為應該將刑法第390條第2款規(guī)定的特別自首制度從“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改為“不以犯罪論處”或“不追究刑事責任”,以實現(xiàn)公職人員不敢受賄的局面;[2]第二種觀點主張應該加大對行賄罪的打擊,以杜絕行賄遏制受賄;[3]第三種觀點則從行賄的風險較小,收益卻相對較大,重受賄、輕行賄存在不合理性,實踐中以輕打擊行賄獲取重打擊受賄的辯訴交易作為反腐敗的措施不僅無效, 反而具有極大的危害性,因此,主張實施重行賄、輕受賄的戰(zhàn)略和制度以有效遏制腐敗。[4]
一、輕行賄重受賄的規(guī)制現(xiàn)狀
無論是從刑法規(guī)定,還是從司法實踐來看,我國對于賄賂犯罪的規(guī)制都存在著輕行賄重受賄的現(xiàn)象。
(一)規(guī)范:行賄特別自首
我國刑法第390條第2款規(guī)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該款規(guī)定了行賄罪的特別自首制度①行賄罪特別自首制度要求行賄人不但要如實交代自己的行賄行為,而且要如實交代自己的行賄對象——受賄人。且行賄人自首僅交代自己的行賄行為而不交代受賄人能否作為自首則存在疑問。刑法第67條第1款規(guī)定的一般自首與該條第2款規(guī)定特別自首的主要區(qū)別在于行為人人身自由是否被限制,刑法第390條第2款規(guī)定的特別自首與刑法第67條第2款規(guī)定特別自首制度的區(qū)別則在于量刑時所給予的從寬優(yōu)惠的差別。,其設立目的主要在于通過對行賄人行賄行為的輕打擊以換取行賄人揭發(fā)受賄人的受賄行為。根據(jù)在于:其一,我國刑法第67條的自首制度,作為量刑情節(jié),其法律后果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對于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從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與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的兩相比較中可以看出,行賄罪特別自首制度較普通自首具有更高的優(yōu)惠,這種優(yōu)惠的意義只能存在于行賄人對受賄人的揭發(fā)。其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2〕22號)第七條規(guī)定因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而破獲相關受賄案件的,對行賄人不適用關于立功的規(guī)定,依照我國刑法第390條第2款的規(guī)定,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而第八條規(guī)定行賄人被追訴后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依照關于坦白的規(guī)定,可以從輕處罰,因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fā)生的,可以減輕處罰。該規(guī)定進一步說明了特別自首制度的重點在于通過減輕對行賄行為的處罰以換取行賄行為人對受賄行為的揭發(fā),從而打擊受賄行為。
我國刑法規(guī)定的行賄罪和受賄罪法定刑結(jié)構存在著較大的區(qū)別。我國刑法第390條第1款對行賄罪設置了3檔法定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而我國刑法第386條規(guī)定受賄罪的處罰依照貪污罪的規(guī)定處罰,受賄罪的法定刑存在多個檔次,涵蓋了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至死刑等多個量刑幅度。顯然,行賄罪的法定刑結(jié)構輕于受賄罪的法定刑結(jié)構。
值得注意的是,美利堅合眾國法典第18編第201條規(guī)定的重型賄賂罪和輕型賄賂罪的法定刑均為相當于賄賂價值3倍的罰金或15年以下的拘禁刑或兩者并罰,而輕型行賄罪和輕型受賄罪的法定刑相當于賄賂價值3倍的罰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拘禁或兩者并罰。行賄罪受賄罪在法定刑上一樣處罰,是聯(lián)邦賄賂法的特色之一。[5](P9)
行賄罪和受賄罪是否應該對應相同的法定刑呢?筆者認為,行賄罪和受賄罪法定刑不做區(qū)分,不具有合理性。原因在于:其一,行賄罪和受賄罪的社會危害性不同,刑罰配置也應該存在差異。貝卡里亞認為,犯罪行為的階梯應該和刑罰的階梯相符合,[6](P18)相同階梯的行為配置相同階梯的刑罰,行賄罪和受賄罪顯然不是在同一階梯的行為,因此也不應該被配置相同的刑罰。其二,白建軍教授編制的《中國刑法罪刑等級關系表》顯示,我國刑法規(guī)定的受賄罪的罪量(犯罪嚴重性程度)與刑量(法定刑嚴厲程度)一致的,而行賄罪的刑量相對于其罪量是偏重的[7](P278、292)。這在一定程度說明,行賄罪和受賄罪不應該配置相同的法定刑。②筆者對白建軍教授的罪量和刑量關系的量定方法存在疑問,但其研究結(jié)果仍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因此,我國刑法對行賄罪、受賄罪配置不同的法定刑具合理性,其不同本身不具有輕行賄罪重受賄罪的功能。
(二)司法:放行賄擊受賄
通常情況下,一個受賄人可能對應著多個行賄人,即在查處一個受賄案件,與之相應,應該查處與之對應的多個行賄案件。但是, 2003年1月至10月廣東省廣州市兩級法院審理案共受理賄賂案件136件,其中行賄案件僅28件;2006年上海市檢察機關立案查處貪污賄賂案件446件,行賄案僅47件;2000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查辦賄賂案件9872件,其中行賄案件僅為1367件,占賄賂案件總數(shù)的13.8%[8],2006年至2013年,濰坊市奎文區(qū)檢察院共查辦賄賂犯罪案件53件53人,其中,受賄案件立案47件47人,行賄案件立案9件9人,行賄案件僅占賄賂案件的總數(shù)的17%,行賄案件年均立案1件1人[9],我國處罰的行賄人遠遠少于受賄人。因此,常有受賄人在法庭上發(fā)問“行賄人到哪里去了”[10]。筆者無法獲取上述所有行賄人消失的具體原因,但從相關報道可以推測出,如此數(shù)量巨大的行賄人之所以消失,其大部分可能在于這些行賄人檢舉了受賄人,作為相應的獎勵,檢察官讓該部分行賄人從審判中消失。雖然這主要是基于筆者的揣測,但這應該是符合事實的。因為,檢察機關查明受賄人的受賄行為,其前提是已經(jīng)查明了行賄人,否則在受賄人否認受賄的行為的情況下,該行為不能作為受賄認定。①正是基于此,才有巨額財產(chǎn)來源不明罪的適用可能。
消失的行賄人沒有進入審判程序,在偵查或?qū)彶槠鹪V階段被作為無罪處理,但行賄罪特別自首制度的設定是行賄人須被帶入審判程序,接受審判,其特別自首僅是量刑情節(jié)而已。司法實踐中行賄人的消失,說明行賄罪特別自首制度作為量刑情節(jié),在引導行賄人揭發(fā)受賄行為的作用并不很大,否則,不會存在如此之多的行賄人在審判階段消失的現(xiàn)象。
感同身受的現(xiàn)實告訴我們,身邊的賄賂犯罪并沒有因為輕行賄重受賄的刑事政策而減少,這常常被認為放棄追究行賄人以換取懲治受賄人的刑事政策并沒有實現(xiàn)預防賄賂犯罪的目標。因此,有論者主張受賄的根源在于行賄者的行賄行為,應對行賄罪與受賄罪實行同罰,從根源上消除受賄現(xiàn)象[11]。筆者認為,行賄罪和受賄罪是否實行同罰,是由司法實踐具體情況所決定的:首先,如果司法實踐中檢察官有足夠的證據(jù)能夠證明行賄人和受賄人存在行賄受賄行為,檢察官一定會對行賄行為和受賄行為同罰,不會存在消失的行賄人;其次,司法實踐常常發(fā)生雖然有證據(jù)證明受賄人受賄,但是相關證據(jù)的證明力并不強,此種情況起訴存在敗訴的風險,或者明知受賄人收受了行賄人的賄賂但是沒有證據(jù)能夠證明行賄受賄行為存在等情況。在這兩種情況下,偵查行為或公訴行為就依賴于行賄人的配合,行賄人的配合就會減少敗訴的風險,或者實現(xiàn)追訴的目的。因此,司法實踐中,行賄罪、受賄罪的不同處理方式,受制于行賄受賄行為證據(jù)的收集,正是所收集的行受賄罪證據(jù)的證明力常常達不到可以同時處罰行受賄罪的程度,只能采取通過減輕對行賄人的處罰以換取受賄人收取行賄人賄賂的可靠證據(jù),這實屬一種無奈的選擇;再次,懲罰犯罪能否預防犯罪一直存疑,因此,輕行賄重受賄的刑事政策所指向的應該是能否有效的打擊受賄犯罪,而非能否有效預防賄賂犯罪。
二、囚徒困境理論揭示的規(guī)制路徑
鑒于行賄罪和受賄罪屬于密室犯罪,犯罪證據(jù)極難收集,因此,如果對行賄罪和受賄罪同罰打擊,可能的結(jié)果是不但所能打擊的行賄罪數(shù)量減少,所能打擊的受賄罪數(shù)量也會相應減少。如果像目前輕打擊行賄重打擊受賄的打擊方式,必然放縱對行賄罪的打擊,導致行賄人肆無忌憚。鑒于規(guī)制行賄受賄行為與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具有極強的相似性,研究囚徒困境理論對于如何規(guī)制行賄受賄行為就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囚徒困境理論
所謂囚徒困境,是非合作博弈論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其反映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矛盾,主要是指下述案例所發(fā)生的情況:[12](P30-32)(P8-10)
張三、李四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捕,偵查人員懷疑其有故意殺人行為,但現(xiàn)有證據(jù)對于他們的故意殺人罪的證明力明顯不足,如果一個人供認或者兩個人都供認則可認定。當然,如果兩個人都拒供,則仍可判他們較輕的故意傷害罪。
兩人被分開拘留后,偵查人員向其交代以下政策:如果兩個人都供認,每個人都將因故意殺人罪被判5年有期徒刑;如果兩個人都拒供,則兩個人都將因故意傷害罪被判處1年有期徒刑;如果一個人供認而另一個拒供,則供認者因為具有坦白表現(xiàn)判處緩刑,拒供者將因故意殺人罪而被重判10年有期徒刑。
被告張三、李四根據(jù)自己的供認、拒供不同情況,其刑罰量就會產(chǎn)生四種不同的結(jié)果:(1)被告張三、李四均拒供,張三、李四均因故意傷害罪被判處1年有期徒刑;(2)被告張三拒供,被告李四供認,被告張三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10年監(jiān)禁,被告李四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緩刑;(3)被告張三供認,被告李四拒供,被告張三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緩刑,被告李四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4)被告張三、李四均供認,張三、李四均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
針對上述四種情況,對于被告張三、李四來說,其可能的選擇為:(1)如果對方拒供,則自己供認便可立即被判處緩刑,而自己拒供則會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因此,供認是比較好的選擇;(2)如果對方供認,則自己供認將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而自己拒絕供認則會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因此供認是比較好的選擇。因此,無論對方拒供或供認,自己選擇供認始終是更好的選擇。
被告張三、李四均選擇供認的結(jié)果是兩人均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而如果該兩人均選擇拒供的結(jié)果則該兩人被判處1年有期徒刑。從結(jié)果來看,兩人選擇拒供要比選擇供認所獲收益要高。但是,被告張三、李四均選擇拒供不符合各自的個人理性需求,不是納什均衡,其每個人選擇供認是其較優(yōu)的選擇,否則拒供者就可能被利用,不但沒有實現(xiàn)較優(yōu)的利益,反而遭受了較重的損失。進一步,即使被告張三、李四事前訂立了攻守同盟,該攻守同盟不是納什均衡,也沒有人有積極性遵守該約定,該約定必將形同虛設。
(二)行賄受賄困境
為了簡約適用囚徒困境理論,我們對偵查或?qū)彶槠鹪V行賄行為、受賄行為過程中的行賄罪受賄罪做以下限定:首先,假設行賄行為、受賄行為均能構成行賄罪、受賄罪,但是偵查或?qū)彶槠鹪V的證據(jù)證明力較弱,如無行賄人的配合,受賄人的受賄行為將不被處罰;其次,雖然受賄所得財物不能查證屬實,可以巨額財產(chǎn)來源不明罪處罰,但是在本部分暫按無罪處理;再次,我們假設行為人實施了行賄行為之后,在偵查機關或?qū)彶槠鹪V機關詢問其行賄行為的時候,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的行賄行為,其被偵查機關或?qū)彶槠鹪V機關以不起訴處理,也即行賄人供認自己行賄行為將被釋放。
在上述限定之后,如一個對合的行賄行為和受賄行為案件發(fā)生,偵查機關收集的證據(jù)不能同時打擊行賄人和受賄人時,行賄人、受賄人的拒供、供認選擇就會出現(xiàn)以下組合:(1)行賄人拒供、受賄人拒供,行賄人和受賄人均被釋放①這是司法實踐中行賄者和受賄者常常拒絕供述行受賄行為的原因,即檢察官具有較弱的證據(jù)證明行受賄存在,或者無證據(jù)證明行受賄行為存在,行受賄行為就無法被定罪。;(2)行賄人供認、受賄人拒供,行賄人被釋放,受賄人被定為受賄罪;(3)行賄人拒供、受賄人供認,行賄人被定為行賄罪、受賄人被定為受賄罪;(4)行賄人、受賄人均供認自己的行為,行賄人被釋放、受賄人被定為受賄罪。此四種組合與典型的囚徒困境的選擇存在著兩個明顯差別:(1)行賄人、受賄人均拒供的情況,行賄人和受賄人均被釋放,而在典型的囚徒困境中,即使兩個行為人均拒供,仍然會被處以一定的刑罰;(2)行賄人、受賄人均供認自己的賄賂行為的情況下,行賄人仍然會被釋放,而在典型的囚徒困境中,行為人會被處以比拒供稍高、比一方拒供一方供認稍低的刑罰。
根據(jù)上述組合,行賄人具有以下可能選擇:(1)受賄人拒供,行賄人無論是拒供還是供認都會被釋放,在此種情況下,行賄人拒供和供認沒有優(yōu)劣之分,如果考慮到行賄人所受到偵查機關的各種壓力,行賄人較優(yōu)的選擇是供認;(2)受賄人供認,行賄人拒供則行賄人就會被處以行賄罪,行賄人供認就會被釋放,因此,此種情況下,行賄人選擇供認是一個較優(yōu)的選擇。(3)在不能確認受賄人是否能夠拒供的情況下,行賄人的較優(yōu)選擇為供認,因為供認對于行賄行為來說,無論對方選擇什么,自己都可以被釋放。因此,當行賄人交代行賄行為可以免責的情況下,加上司法實踐中行賄人拒供其行賄行為仍可能導致被定罪處罰②司法實踐中,較弱的證據(jù)并不必然導致認定行賄罪受賄罪的失敗。,行賄人交代行賄行為是一個較優(yōu)的選擇,這也是司法實踐中少用行賄特別自首制度,而多見行賄人消失的原因——行賄人更愿意在被不追訴的情形下揭發(fā)受賄行為,而非出現(xiàn)在不確定的審判中。
需要指出的是,囚徒困境中的行為人被假定為僅僅是理性思考的動物,并沒有考慮到行賄人的感情等其他情況。有時可能獲得行賄人的證詞比受賄人的口供更困難,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相互之間有親戚、朋友、上下級等關系,即使開始不存在某種特定的關系的到后來也因行賄而變得關系密切,所以相互之間成為義氣哥們,互相隱瞞,導致對行賄者取證往往像擠牙膏似的,增加了取證的難度,此時,事前約定可能就會構成納什均衡,就可能實現(xiàn)集體理性。[13]因此,即使給予行賄人交代行賄行為可以免責的優(yōu)惠,如要實現(xiàn)囚徒困境理論所示的結(jié)果,仍需匹配多種司法措施。
三、規(guī)制賄賂犯罪路徑的實現(xiàn)
我國規(guī)制賄賂犯罪的司法實踐,主要采用在偵查或?qū)彶槠鹪V階段給予行賄人免予起訴的承諾,以換取其交代受賄人的受賄行為。此規(guī)制賄賂犯罪的措施符合囚徒困境理論所揭示的路徑,但問題是,這種措施符合我國相關法律規(guī)定嗎?如果不符合,我們應該如何完善呢?
(一)不起訴之難
行賄受賄規(guī)制的囚徒困境表明,行賄人如實交代行賄行為如被免予追訴,當其行賄行為和與之相對的受賄行為面臨追訴,其較優(yōu)的選擇是交代行賄行為。司法實踐也多存在對行賄人不被起訴的情況。但問題是,我國刑法第390條第2款設定的行賄罪特別自首制度能否成為檢察官做作出不起訴決定的依據(jù)呢?首先,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73條第2款規(guī)定對于犯罪情節(jié)輕微,依照刑法規(guī)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該款的適用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犯罪情節(jié)輕微,二是存在法定免除刑罰的情節(jié),兩者必須同時具備,才能被適用。行賄罪的特別自首情節(jié)屬于法定免除刑罰情節(jié),因此,行賄罪的特別自首情節(jié)行為是否能被作出不起訴決定,關鍵看是否行賄行為屬于犯罪情節(jié)輕微,如果屬于犯罪情節(jié)輕微,就可以被作出不起訴決定,如果不屬于犯罪情節(jié)輕微,就不能被作出不起訴決定。實踐中多數(shù)行賄行為基本上不屬于犯罪情節(jié)輕微的行為,《刑事訴訟法》第173條第2款適用的余地不大。其次,非犯罪情節(jié)輕微的行賄行為,行賄罪的特別自首制度作為量刑情節(jié),只能由法官在審判時適用,也即非犯罪情節(jié)輕微的行賄行為必須進入審判階段,非犯罪情節(jié)輕微的行賄行為僅出現(xiàn)在非審判階段顯系違法。
正是基于此,非犯罪輕微的行賄行為不被起訴,就會惹來極大的爭議。較早對行賄行為不予起訴的重慶綦江虹橋垮塌案中,被告人林世元因收受賄賂11萬余元而被定受賄罪被判處死刑,但是向被告人林世元行賄11萬余元的行賄人費上利卻僅因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對其行賄行為根本未予定罪處罰,引致了于法無據(jù)、違背法律要求的強烈批評[14]。該批評可以同樣擴展至所有的被不起訴的非犯罪輕微的行賄人——非犯罪輕微的行賄人被作出不起訴的決定或者不被追訴均是于法無據(jù)、違背法律規(guī)定的。
(二)可能之選擇
在偵查或?qū)彶槠鹪V階段,為了獲得受賄人的受賄行為證據(jù),給予與之相對的非犯罪輕微的行賄人免予起訴優(yōu)惠顯系違法,因此,要實現(xiàn)囚徒困境理論所揭示的規(guī)制賄賂犯罪的路徑,我們不得不討論立法完善等其他可能實現(xiàn)的途徑。
1.不追究刑事責任
張明楷教授認為,將我國刑法第390條第2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修改為“不以犯罪論處”或“不追究刑事責任”就可以使行賄者、受賄者處于不信任狀態(tài),置行賄人、受賄人于囚徒困境,進而國家工作人員不敢受賄或不像現(xiàn)在一樣受賄。[2]筆者認為該措施并不能實現(xiàn)其所要實現(xiàn)的目的。首先,對行賄特別自首行為如“不追究刑事責任”,必然需要同時適用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73條第2款,檢察官要作出不起訴決定,須行賄行為犯罪輕微。如此,不追究刑事責任必然和免予處罰取得一樣的效果,多數(shù)只能適用于審判過程中,其效果明顯不佳。其次,對行賄罪特別自首行為如“不以犯罪論處”,將導致本來構成犯罪的行賄行為無罪,明顯與法感情不和。①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行賄人如實交代行賄行為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可能帶來的一個可怕的后果——“行賄人”栽贓陷害“受賄人”,也即根本不存在受賄行為,但是,由于各種原因,行賄人“交代”了行賄行為。再次,給予行賄罪特別自首如此之優(yōu)惠,能否足以破壞行賄人和受賄人之間的信任存在疑問,目前的行受賄行為,多發(fā)生在信任人之間,現(xiàn)在多數(shù)情況是非熟人的財物或利益已經(jīng)無人敢要,正如前所述,此種情況可能已經(jīng)構成納什均衡。因此,行賄人揭發(fā)受賄行為而破壞行賄受賄人之間的信任關系,實難與現(xiàn)實的行賄受賄人的利益同盟關系相抗衡。
2.引入辯訴交易
我國司法實踐針對行賄行為所作出的不起訴主要存在兩種情況:一是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第173條第2款的規(guī)定作出合法的酌定不起訴,如行賄行為已經(jīng)構成犯罪,但情節(jié)輕微,是否起訴主要看行賄罪犯罪嫌疑人是否配合偵檢機關追究犯罪件;二是潛規(guī)則不起訴,此不起訴是非法不起訴,行賄罪行為人犯罪情節(jié)并非輕微,依法應當起訴,但為了更大的司法利益而被放棄起訴,如以不起訴換取非犯罪輕微行賄人揭發(fā)受賄人,這是我國潛規(guī)則不起訴的典型。[15]正如前所指出的一樣,這種潛規(guī)則不起訴于法無據(jù),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常常被嚴厲質(zhì)疑。
與潛規(guī)則不起訴相伴生的是行賄罪特別自首制度效用較低而導致其被適用頻次的降低。因此,如果僅從囚徒困境理論所揭示的規(guī)制賄賂犯罪的路徑來看,檢察官能夠給予行賄人不起訴決定是較優(yōu)的選擇。這一方面要求檢察官具有對非犯罪輕微行賄人具有作出不起訴決定的權力,另一方面也要求檢察官能利用行賄罪法定刑對行賄人進行威懾,從而確定自己和行賄人討價還價的能力。檢察官與行賄罪犯罪嫌疑人的議價能力必須以能夠做出不起訴決定為基礎,與此同時也具有使行賄罪犯罪嫌疑人面臨刑罰處罰的可能,兩者必須能夠相輔相成,才能取得實效,因此,如將我國刑法第390條第2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修改為“不以犯罪論處”或“不追究刑事責任”,則會讓檢察官喪失與行賄人的議價能力,實不可取。檢察官具備了與行賄罪犯罪嫌疑人的議價能力,也就具備了與行賄人進行辯訴交易的權力。
在目前行賄罪特別自首制度對打擊受賄罪不力、潛規(guī)則不起訴存在違法的背景下,筆者認為應該:其一,在行賄罪受賄罪的互動規(guī)制中引入辯訴交易,給予檢察官與行賄罪犯罪嫌疑人的議價權力;其二,行賄罪特別自首制度應轉(zhuǎn)化為行賄罪特別自首、坦白制度,行賄人在被移送起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以與辯訴交易制度相配合。
四、申論
到底是行賄行為誘發(fā)受賄行為,還是受賄行為誘致行賄行為,基本上就是一個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問題,我們無法將此問題界定清楚。但是,根據(jù)賄賂犯罪的自身特點以及我國目前腐敗犯罪的防治措施體系,我國長期采取了重點打擊受賄罪的刑事政策:(1)刑法規(guī)范確定行賄罪特別自首制度,以給予量刑優(yōu)惠獲取行賄人揭發(fā)受賄人的受賄行為;(2)刑事司法實踐以不起訴行賄人換取行賄人揭發(fā)受賄人的受賄事實。但是,這種輕行賄重受賄的刑事政策逐漸被行賄罪受賄罪同罰所取代。
筆者采用囚徒困境理論思考行賄罪受賄罪規(guī)制困境,發(fā)現(xiàn)行賄人如可被不起訴,其較優(yōu)的選擇是向偵查或檢察機關交代其行賄行為,也即如行賄人可被不起訴,偵查機關或檢察機關能夠更容易從行賄人處獲得受賄人的受賄犯罪證據(jù),從而實現(xiàn)打擊受賄犯罪目的。顯然,行賄罪受賄罪同罰的刑事政策與囚徒困境理論所揭示的規(guī)制路徑不符,而我國司法實踐中的對非犯罪情節(jié)輕微行賄人不起訴卻符合該規(guī)制路徑,但是,對非犯罪情節(jié)輕微行賄人不起訴卻違背我國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
根據(jù)囚徒困境理論所揭示的規(guī)制賄賂犯罪的路徑、以及我國長期以來的賄賂犯罪查處司法實踐,筆者提出引入辯訴交易、重新界定我國刑法第390條第2款內(nèi)涵的建議。
第一,行賄罪附條件不起訴的完善。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73條規(guī)定了法定不起訴和酌定不起訴制度,行賄罪的不起訴只能存在于酌定不起訴,適用酌定不起訴必須具備犯罪情節(jié)輕微且可免除處罰等兩個條件,行賄人如實交代行賄行為,其已具備可免除處罰條件,但是,通常行賄罪不會是犯罪情節(jié)輕微。因此,為檢察官能夠具備行賄罪辯訴交易權力,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73條建議增加第三款:行賄人在被移送審查起訴之前如實交代行賄行為的,適用前款的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決定對行賄罪犯罪嫌疑人附條件不起訴的,應當根據(jù)行賄罪犯罪嫌疑人的具體情況確定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的考驗期限。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內(nèi)發(fā)現(xiàn)漏罪或犯新罪的,行賄數(shù)額累加計算。
第二,重新界定我國刑法第390條第2款內(nèi)涵。我國刑法第390條第2款一般被認為是行賄罪的自首制度,其須符合自首主動投案和如實交代罪行的要件。為鼓勵行賄人積極交代受賄人的受賄行為,并實現(xiàn)檢察人員的行賄罪辯訴交易權力,不僅對行賄人的自首行為給予量刑優(yōu)惠,行賄人的坦白行為也應該給予量刑優(yōu)惠。因此,我國刑法第390條第二款建議改為:行賄人在被移送起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1] 盧勤忠.行賄能否與受賄同罰[J].人民檢察,2008,(14).
[2] 張明楷.置賄賂者于囚徒困境[J].書摘,2004,(8).
[3] 陳國權.嚴懲行賄∶ 凈化政治空間——論行賄罪的危害與懲治[J].政治與法律,1999,(3);大野.論對行賄者的嚴懲[J].河北法學,2000,(3),等等.
[4] 劉大生.試論加大對行賄犯罪打擊力度的反腐戰(zhàn)略[J].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2,(1).
[5] 王云海.美國的賄賂罪——實體法和程序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
[6] 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M].黃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7] 白建軍.罪刑均衡實證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8] 李亮.“行賄狀元”案久拖不決行賄非罪化、量刑畸輕化傾向嚴重[EB/OL].http∶//www.legaldaily.com.cn/bm/ content/2008-01/27/content_788591.htm,最后訪問時間2014年4月30日.
[9] 朱新偉.行賄行為的懲治困境與對策研究[C].山東省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2013年學術年會論文集,未刊稿.
[10] 李娜.缺少必要偵查手段致行賄案不易發(fā)現(xiàn)[N].法制日報,2011-05-27.
[11] 李松.寬縱行賄行為禍患大[J].決策探索,2009,(21).
[12] 囚徒困境案例及理論均見∶董志強.身邊的博弈[M].北京∶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07;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jīng)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3] 江鵲,馮帝焱.突破行賄人拒證的“利器”——偵查中角色的轉(zhuǎn)換.[J].中國檢察官,2006,(6).
[14] 趙秉志.關于重慶綦江虹橋垮塌案的幾點法律思考[EB/ OL].http∶//www.criminallawbnu.cn/criminal/Info/showpage. asp?pkID=9816,最后訪問時間2014年4月30日.
[15] 龍宗智.正義是有代價的——論我國刑事司法中的辯訴交易兼論一種新的訴訟觀[J].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2,(6).
責任編輯:侯德彤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gal Regulation ov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ffering and Accepting Bribes-in Light of Prisoner's Dilemma Theory
DONG Gui-wu
(Law School,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266071,China)
According to Section 2 of Article 390, the Criminal Law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pecial Voluntary Surrender System on Offering Bribes infl icts light punishment on bribers and mainly aims to make them expose bribees. In the juridical practice of our country, there are phenomena that light punishment is inflicted on bribers and severe punishment is infl icted on bribees while not indicting bribers as an illegal, latent rule. In light of prisoner's dilemma theory, the fi rst choice of bribers is to expose bribees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former will not be prosecuted. Plea bargaining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legal regulation ov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ffering and accepting bribes and the Special Voluntary Surrender System should be changed into Special Voluntary Surrender Confess System.
crime of offering bribes; crime of taking bribes; regulation; prisoner dilemma; plea bargaining
D914.392
A
1005-7110(2014)03-0115-07
①筆者認為賄賂犯罪乃至腐敗犯罪較有效的防治策略在于官員財產(chǎn)公開、合理的媒體監(jiān)督等相關非刑罰措施的實施,因此,本文是基于我國目前的腐敗防止體系,所討論的主要問題限定在賄賂犯罪發(fā)生之后,如何有效懲治賄賂犯罪。
2014-04-30
董桂武(1978-),男,山東膠南人,法學博士,青島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