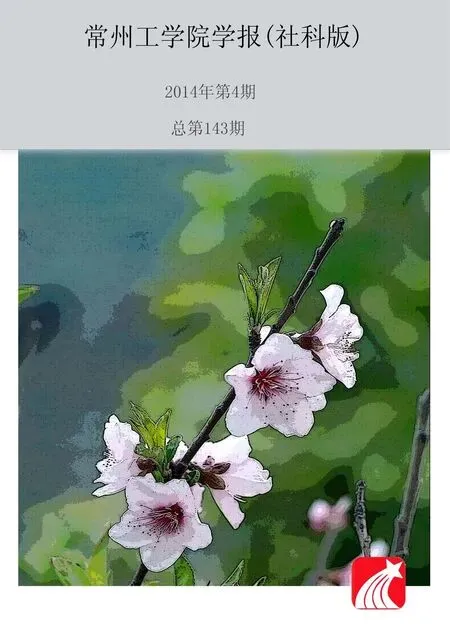從《名士與狐仙》看汪曾祺的士大夫情懷
陳英
從《名士與狐仙》看汪曾祺的士大夫情懷
陳英
(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常州衛生分院,江蘇常州213002)
汪曾祺是士大夫文化熏陶出來的最后一位作家。其“士大夫文化”主要來自于家庭,來自于他的祖父和父親。他的小說創作與自己的生活貼得近,虛構的成分較一般小說家少,作品人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家自己的生活理想。最典型地寫出了士大夫神韻,寫出了汪先生的士大夫情結的是寫于1996年的《名士與狐仙》,作品主人公楊漁隱就是晚年汪曾祺心靈的投影,精神的慰藉。
汪曾祺;名士與狐仙;士大夫情懷
汪曾祺被稱為“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此說廣為流傳。這個說法是1987年《北京文學》編輯部舉辦的一次汪曾祺作品研討會上“北大的幾位年青學者”提出來的。其實,說他是“士大夫文化熏陶出來的最后一位作家”,更恰當些。
士大夫,在中國舊指那些以做官為目的的知識分子,或已是官員,或將來有可能為官員,是官僚與知識分子的混合體。1905年9月,清廷發布諭旨,宣布廢科舉,士大夫階層就消亡了,只是一些讀書人的“士大夫情結”還在。
說汪曾祺是“士大夫文化熏陶出來的”,所以有著“士大夫情結”,倒可以成立。
一
汪先生1920年出生在高郵,“我的曾祖父中過舉,我的祖父中過拔貢”[1]。他的父親汪菊生沒趕上科舉,在南京讀過舊制中學,“我見過他在學堂時用過的教科書,英文是納氏文法,代數幾何是線裝的有光紙印的”[2]。其實,不要說他的父親,他祖父都已沒有機會繼續沿科舉的路走下去了。他回憶說:“祖父中過拔貢,是前清末科,從那以后就廢科舉改學堂了。他沒有能考取更高的功名,大概是終身遺憾的。拔貢是要文章寫得好的,聽我父親說,祖父的那份墨卷是出名的。那種章法叫做‘夾鳳股’。”[3]22
汪先生的祖父雖然沒能取得更高的功名,拔貢也不能直接做官。但他很是能干,“聽我父親說,我們后來的家業是祖父幾乎是赤手空拳地創出來的”。因為他的曾祖父做“鹽票”虧了本,“甚至把家產都賠盡了”[3]23。
如果說汪先生是“士大夫文化熏陶出來的”,那么,這“士大夫文化”主要來自于家庭,主要來自于他的祖父、父親。
汪先生祖父是創業的能手,“置田地,開店鋪”,田有兩千多畝,店有兩家藥店,“一家是萬全堂,在北市口,一家是保全堂,在東大街”,“中年以后,家道漸豐。但祖父生活儉樸,自奉甚薄。……喝了酒,常在房里大聲背唐詩:‘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汪銘甫的儉省,在我們縣是有名的。但是他曾有一個時期舍得花錢買古董字畫。他有一套商代的彝鼎,是祭器。不大,但都有銘文,難得的是五件能配成一套。……他還有一個奇怪的古董:渾天儀。……他有幾張好畫。有四幅馬遠的小屏條。……他還有很多字帖,是一次從夏家買下來的。……我小時候寫的《圭峰碑》《閑邪公家傳》,以及后來獎勵給我的虞世南的《夫子廟堂碑》……都是初拓本,原是夏家的東西。祖父有兩件寶。一是一塊蕉葉白大端硯,……一是《云麾將軍碑》,據說是個很早的拓本,海內無二,這兩樣東西祖父視為性命……他是幼讀孔孟之書的,思想的基礎當然是儒家。……他屋里的桌上放的兩部書,一部是顧炎武的《日知錄》,另一部是《紅樓夢》!……我的祖父本來是有點浪漫主義氣質,詩人氣質的……有一天,他喝了酒,忽然說起年輕時的一段風流韻事,說得老淚縱橫……”
汪曾祺父親“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是畫家,會刻圖章,畫寫意花卉。圖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漢印。他會擺弄各種樂器,彈琵琶,拉胡琴,笙管簫笛,無一不通。……他養蟋蟀,養金鈴子。他養過花,他養的一盆素心蘭在我母親病故那年死了,從此他就不再養花”[4]197。
不厭其煩地抄了那么多汪先生對祖父、父親的回憶,就是為了說明,他從小生活在什么樣的家庭里,受著什么樣的“士大夫文化的熏陶”。汪先生上小學后,這種“熏陶”的效果就表現出來了。“我小時了了,國文成績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時得佳評。”[4]198“我在五小頗有才名,是因為我的畫畫得不錯。”[5]
不僅在學業上,汪先生從小讀書偏于文史藝術,數學一直不好,而且在個人氣質上也深受傳統士大夫文化影響。西南聯大畢業的歷史學家何兆武先生回憶說:“我們宿舍里有位同學,是后來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級,年紀差不多,都十八九歲,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時候他頭發留得很長,穿一件破的藍布長衫,扣子只扣兩個,趿拉著一雙布鞋不提后跟,經常說笑話,還抽煙,很頹廢的那種樣子,完全是中國舊知識分子的派頭。”[6]看來在汪先生的氣質中,“名士”成分還是較明顯的。這也難怪,他聽聞一多先生的課,印象最深的是:“聞先生打開筆記,開講:‘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
二
汪先生曾說:“小說就是回憶。”他的小說創作與自己的生活特別貼近,虛構的成分比一般小說家少。但看他的小說,人物大量是底層的市民,士大夫形象并不多。一位是談甓漁(《徙》),“是個詩人,也是個怪人。他功名不高,只中過舉人,名氣卻很大。……他教出來的學生,有不少中了進士,談先生于是身價百倍,高門大族,爭相延致。……他家里什么都有,可是他愿意到處閑逛,到茶館里喝茶,到酒館里喝酒,煙館里抽煙。……他常常傍花隨柳,信步所之,喝得半醉,找不到自己的家。……他一邊吃蟹,一邊喝酒,一邊看書……”這位談甓漁是有原型的:“我的祖母是談人格的女兒。談人格是同光間本縣最有名的詩人,一縣人都叫他‘談四太爺’。我的小說《徙》里所寫的談甓漁就是參照一些關于他的傳說寫的。”[3]28
另一位是俠義仁厚的王淡人(《故鄉人·釣魚的醫生》),這是一位不為良相則為良醫式的人物。他為人治病,收費“各憑良心”,“王淡人看看病人身上蓋著的破被,鼻子一酸,就不但診費免收,連藥錢也白送了”,“王淡人是有點傻。去年、今年,就辦了兩件傻事”。一件是鬧大水,“泰山廟北邊有一個被大水圍著的孤村子,一村人都病倒了”,他冒著生命危險去救治,“看著的人的眼睛里都蒙了一層眼淚”。另一件是給一位“把家業敗得精光”的“小時候一塊掏蛐蛐、放風箏的朋友”治病,留他在家里“白吃,白喝,白治病”。汪先生在散文《我的父親》里寫道:“我的小說《釣魚的醫生》里寫王淡人有一次乘了船……到一個被大水圍困的孤村去為人治病。這寫的實際是我父親的事。”他的父親叫汪菊生,字淡如。
還有一位是季匋民,曾在《歲寒三友》《鑒賞家》中出現。“季匋民是一縣人引為驕傲的大人物。他是個名聞全國的大畫家,同時又是大收藏家、大財主,家里有好田好地,宋元名跡。”這個季匋民古道熱腸,熱心扶持后進。主動幫助家鄉畫師靳彝甫去上海辦畫展,勸他“行萬里路”,很喜歡靳的幾塊好田黃,但并不強求:“既然如此,匋民絕不奪人之所愛。不過,如果你有一天想出手,得先盡我。”[7]《鑒賞家》中寫季匋民與賣水果的葉三之間平等真誠的交往,把他的真性情寫得入木三分。“季匋民從不當眾作畫,他畫畫有時是把書房門鎖起來的,對葉三可例外,他很愿意有這樣一個人在旁邊看看,他認為葉三真懂,葉三的鑒賞是出于肺腑,不是假充內行,也不是諂媚。”[8]9-10
“季匋民有一個脾氣,一邊畫畫,一邊喝酒。喝酒不就菜,就水果。畫兩筆,湊著壺喝一大口酒,左手拈一片水果,右手執筆接著畫。畫一張畫要喝兩斤花雕,吃斤半水果。”[8]9汪先生很喜歡季匋民,也許是這個人身上的氣質與作者相吻合吧!就以作畫為例,徐城北的《汪曾祺印象》這樣寫道:“他(汪曾祺)作畫的姿勢十分瀟灑,右手執筆,左手插褲兜中,或者拈著一支香煙若有所思,任憑人圍觀。畫累了,他會要人備酒,白酒,一次喝半斤,或者還多。喝了酒就長精神,能一口氣做許多幅畫,寫許多幅字。”
以上人物都是80年代初寫的,而最典型地寫出士大夫神韻的,是1996年寫的《名士與狐仙》。此時離他猝然辭世已不滿一年了。
三
《名士與狐仙》以作者故鄉高郵為背景,寫一位隱逸名士楊漁隱的晚年生活。楊漁隱住在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一個小小的紅漆獨扇板門,不像是大戶人家的住處”,過著一種恬淡自然的生活。他“不愛應酬,不愛理人”,“很少出來,有時到南紙店去買一點紙墨筆硯,順便去街上閑走一會兒”。“除了幾個做詩的朋友,偶然應漁隱折簡相邀到他的書齋里吟哦唱和半天,是沒有人敲那扇紅漆板扉的。”“日長無事,楊漁隱就教小蓮子寫字,小字寫《洛神賦》,教她讀唐詩,還教她做詩。”(這是多么美好的人間樂事、雅事!在汪先生生命的最后幾年,也曾認真地教過家中的小保姆認字、寫字。三年里,她“學完了好幾冊小學語文課本,在一摞一摞的紙上,規規矩矩地寫滿了生字”[9]。)
小蓮子是伺候楊夫人病的年輕女傭人,小楊漁隱幾十歲。后來楊漁隱在夫人去世后娶了小蓮子,“不是扶正,更不是納妾,是明媒正娶的續弦”,并特別跟他的詩友們交待,“小蓮子的品格很高,不可褻玩!”這事在親戚本家、街坊鄰居間掀起了軒然大波。楊漁隱對這些議論紛紛、沸沸揚揚全不理睬。楊漁隱很愛小蓮子,毫不避諱。他時常挽著小蓮子的手,到文游臺憑欄遠眺……若遇到天氣晴和,就到西湖泛舟。有人說:“這哪里是楊漁隱,這是《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
楊漁隱是得了急病,猝然離世的。小蓮子“痛不欲生,但是方寸不亂”,處理后事,有條不紊;整理遺物,整整齊齊。有一天,“小蓮子不見了!……老花匠也不見了。……楊家來人到處看了看,什么東西都井井有條,一樣不缺”。
小說借“走南闖北,無所不知”的張漢軒之口,說小蓮子他們“是狐仙。——誰也不知道他們是從哪里來的,又向何處去了。飄然而來,飄然而去,不是狐仙是什么?”。
這是一篇很值得回味的作品,楊漁隱、小蓮子,是很值得研究的人物,如果把楊漁隱與作者的晚年生活聯系起來思考,更有意味。
林語堂先生在《中國人》一書中寫道:“中國人明確地認為:人生的真諦在于享受淳樸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歡樂和社會關系的和睦。兒童入學伊始,第一首詩便是:云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在中國人看來,這不僅代表片刻的詩意般的快樂心境,并且是追求人生幸福的目標。中國人就是陶醉在這樣一種人生理想之中,它既不曖昧,又不玄虛,而是十分實在。”[10]
林語堂先生所說的傳統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在中國隱逸詩人陶淵明用以自況的《五柳先生傳》中,有著最典型的描寫:“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
再看汪曾祺先生的晚年生活。1990年,汪先生在自己七十歲生日時寫了一首詩《七十書懷出律不改》:
悠悠七十猶耽酒,惟覺登山步履遲。
書畫蕭蕭余宿墨,文章淡淡憶兒時。
也寫書評也作序,不開風氣不為師。
假我十年閑粥飯,未知留得幾囊詩。
在1992年初寫的《自得其樂》一文中,他把自己寫作之外的業余生活主要概括為:“寫寫字,畫畫畫,做做菜。”在寫自己書畫有童子功,做菜有怎樣的心得之后,在文章結尾,作者突然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很欣賞《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說得何等瀟灑。不知道為什么,漢宣帝竟因此把他腰斬了,我一直想不透。這樣的話,也不許說么?”大概作者太喜歡這段話了,在這年年底寫的小說《鮑團長》的結尾,寫鮑團長辭去保安團長的“信送出后,他叫老伴攤幾張煎餅,卷了大蔥面醬,就著一碟醬狗肉,一包花生米,喝了一斤高粱。既醉既飽,鋪開一張六尺宣紙,寫了一個大橫幅,融《石門銘》入行草,一筆到底,不少踟躕,書體略似王蔭之:‘田彼南山……’”。
為什么汪先生這么喜歡這段典型的隱逸之士的文字呢?固然與其氣質有關,他曾在《無事此靜坐》一文中說:“我小小年紀,就已經有一點隱逸之氣了。”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社會和閱歷的原因。典型的表述要數1991年初寫的《隨遇而安》,也是在結尾處:“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經死掉的,大多數都還在努力地工作。他們工作的動力,一是要證實自己的價值,人活著,總得要做點事。二是對生我養我的故國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復對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輕信,恢復年輕時的天真的熱情,恐怕是很難了。他們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這段話是沉痛的,在汪先生文章中是不多見的。但如果擱在十多年前的70年代,甚至80年代初,他敢寫么?
其實,在“寫寫字,畫畫畫,做做菜”之外,汪先生晚年生活中還要添三個字:“喝喝酒”。他自己說是“悠悠七十猶耽酒”。劉心武回憶說:“汪老嗜酒。”1993年底才認識汪先生,并逐漸與之多有交往的程紹國寫道:“平常時候,特別是沒喝酒時,汪老像一片打蔫的秋葉,兩眼昏花,跟大家在一起,心不在焉,你向他喊話,或是答非所問,或是置若罔聞。可是,只要喝完一場好酒,他就把一腔精神提了起來,思路清晰,反應敏捷,寥寥數語,即可滿席生風,其知識之淵博之偏門之瑣細,其話語之機智之放誕之怪趣,真令人絕倒!”(《文壇雙璧》)真是酒前酒后,判若兩人。
鄧友梅對此也有回憶,說汪先生因身體原因被家人限制喝酒,所以他早上出門買菜后就到酒店打二兩酒,站在一邊喝完再回家……嗜酒竟至如此!
汪曾祺到晚年,藝術感覺竟能如此敏銳細膩,文學史上少有。這與他特別愛生活、愛美有關。他在62歲那年曾寫過一句詩:
我于是告天下人:
與其拜佛,
不如膜拜少女!
他認為“少女無邪”。他75歲在甌海,“本地有一位十八九歲的少女,五官和身材都極漂亮,攙著汪先生走路,無微不至。汪先生顯出興奮的樣子,聽憑指引……汪曾祺回到北京,寫了一篇散文《月亮》,……就是寫這一位女孩的。這位女孩給他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夫人對汪曾祺是了解的。在甌海,那位十八九歲的女孩攙著他走路的時候,夫人在后頭對我說:‘老汪這個人啊,就是喜歡女孩子。你看你看……’后來夫人腦血栓,‘松卿倒在床上,還疑心曾祺和保姆有關系’。”(《文壇雙璧》)
汪曾祺對于美的事物,美的人,是不容易忘懷的。他年輕時在昆明見過一位美人,1947年寫的《綠貓》一文首有記述。到1996年,汪先生作了一幅畫,叫《昆明貓》,題了長長一段款識:“昆明貓不吃魚,只吃豬肝。曾在一家見一小白貓蜷臥墨綠軟緞墊上,嬌小可愛。女主人體頎長,斜臥睡榻上,甚美。今猶不忘,距今四十三年矣。
四十三歲一夢中,美人黃土已成空。
龍鐘一叟真癡絕,猶吊遺蹤向晚風。
“1997年3月,汪先生去世前兩個月,他寫了散文《貓》:‘……這位母親已經過了三十歲了,身體高高的,腿很長。她看人眼睛瞇瞇的,有一種恍恍惚惚的成熟的美。她斜靠在長沙發的靠枕上,神態有點慵懶……好看的女人、小白貓、蘭花的香味,這一切是一個夢境。’”
汪曾祺對美,是執著的。
還是回到《名士與狐仙》,回到楊漁隱。楊漁隱之隱,是功成身退,還是仕途厭倦?是避禍辭官還是拒絕入仕或不仕新朝?也許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仗著祖蔭平平淡淡瀟瀟灑灑過了一生?不知道。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楊漁隱的生活,汪先生是欣賞的,是向往的。或者甚至可以說,楊漁隱就是晚年汪曾祺心靈的投影,精神的慰藉。
中國的隱逸文化長久而深厚,對于隱逸之士,有人斥之為逃避責任,有人譽之為高風亮節。對此筆者沒有能力以簡單的好與不好為之貼標簽。但至少,它是歷史上文人失意后的歸宿,年老后的寄托,甚至包括許多政治人物。汪曾祺在《嚴子陵釣臺》中寫道:
“范仲淹有兩篇有名的‘記’,一篇是《岳陽樓記》,一篇便是《嚴先生祠堂記》。此記最后的四句歌尤為千載傳誦:‘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范仲淹是政治家,功業甚著,他主張‘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很入世的,為什么又這樣稱頌嚴子陵這樣的出世隱士呢?想了一下,覺得這是范仲淹衡量讀書人的兩種尺度。立功與隱逸,常常同時存在于一個人身上,或者各偏于一面,也無不可。范仲淹認為嚴子陵的風格可以使‘貪夫廉,懦夫立,大有功于名教’。我想即使到今天,這對人的精神還是有用的。”
名士楊漁隱在汪曾祺小說人物中,應是有較高地位的。雖然,現在認識到的人還不多。
[1]汪曾祺.我的家[M]//我的高郵.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9.
[2]汪曾祺.我的父親[M]//我的高郵.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31.
[3]汪曾祺.我的祖父祖母[M]//我的高郵.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
[4]汪曾祺.多年父子成兄弟[M]//我的高郵.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
[5]汪曾祺.我的小學[M]//我的高郵.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56.
[6]何兆武.上學記[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127.
[7]汪曾祺.歲寒三友[M]//汪曾祺全集:一(小說卷).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357.
[8]汪曾祺.鑒賞家[M]//汪曾祺全集:二(小說卷).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9]程紹國.文壇雙璧[J].當代作家評論,2005(1):14-22.
[10]林語堂.中國人[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110.
責任編輯:莊亞華
I206.7
A
1673-0887(2014)04-0022-05
10. 3969 /j. issn. 1673 - 0887. 2014. 04. 006
2014-03-31
陳英(1968—),女,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