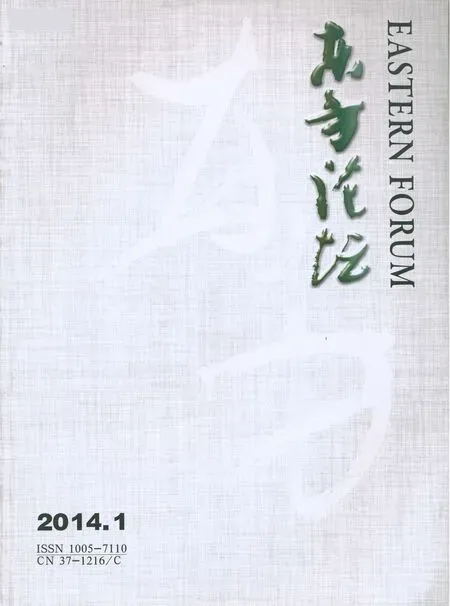文學中的法律史學研究及其限度
許 慧 芳
(中國政法大學 外國語學院,北京 102249)
文學中的法律史學研究及其限度
許 慧 芳
(中國政法大學 外國語學院,北京 102249)
文學中的法律史學研究是“文學中的法律”中較早出現的一個學術研究領域。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法學學者們通過對不同時期的文學作品中的法律意象的解讀,不僅為法律史學研究提供了更加豐富的素材,而且也提出了文學作品對于法律史學研究的價值的探討。對文學中的法律史學研究的學術史的分析將有助于反思文學,尤其是歷史文學作品對于法律史研究的意義。
文學中的法律;法律史;文學;限度
文學中的法律史研究,作為“文學中的法律”(Law in Literature)的重要研究主題之一,早在19世紀末就已經受到了法學學者的關注。1883年,歐文·布朗(Irving Browne)以《文學中的法律和律師》(Law and Lawyers in Literature)為題,對從古希臘至19世紀末期的文學作品中的法律和律師的描寫進行了梳理,從而為法律史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布朗之后,1928年威廉·霍爾茲沃斯(William Holdsworth)所發表的《作為法律史學家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As A Legal Historian),則是對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經典作品《荒涼山莊》(Bleak House)﹑《匹克威克外傳》(Pickwick Papers)以及《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等小說中的法律人﹑法庭﹑法官以及司法程序和審判活動進行的法律史學分析。在這一時期,法律史學的研究不再僅僅是對素材的簡單梳理,而是進入了更深層次的觀察和研究中。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以艾·沃德(Ian Ward)為代表的學者,通過對莎士比亞戲劇《理查德三世》 (Richard Ⅲ)﹑《國王約翰》 (King John) 以及《理查德二世》(Richard Ⅱ)等作品中王位繼承﹑君主與臣民之間的關系等憲政主題的探討對英國伊麗莎白時期的憲政制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1](P59-89)。和霍爾茲沃斯的研究相比,文學作品已經不是僅僅用于法律史學研究的參考資料,而是成為法學的專門的研究對象。
一、問題的提出
無論是對于文藝理論學者還是法學學者而言,文學中的法律史研究都是一個相對而言爭議較少的研究領域。包括對“文學中的法律”中的各個方面均持批判態度的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 Posner),也承認冰島傳奇和荷馬史詩等文學作品是了解古代北歐和古希臘復仇社會運作方式的重要文學來源[2](P71)。然而,正如沃德教授所指出的,在眾多“文學中的法律”文獻中,較早出現的文學中的法律史研究,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卻漸漸不再是“文學中的法律”中研究的主要問題,文學作品更多的是作為法理學中倫理學問題研究的重要素材而出現在學者們的論著中。沃德教授對此的解釋是“或許這主要是因為它(文學中的法律史研究)的相對無爭議性,以及這一論題的非哲學性視角”[1](P59),而波斯納的解釋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學作品都像荷馬史詩或古斯堪的納維亞語的傳奇,是我們了解他們社會制度的主要知識來源,當代的法律史研究所依賴的是“更加完整﹑更加冷靜的數據來源”,而不是像狄更斯的小說這樣包含著虛構,甚至錯誤的法律描述的文學作品[2](P189)。
我們不能要求文學家在創作的時候,能夠準確甚至是精確的描述法律現實,同樣文學中存在的錯誤的,甚至是虛構的法律現象也不應當被用于法律史法學研究的素材。湯尼·莎普(Tony Sharp)在《文學中的法律》(Law in Literature)一文中,指出“文學在討論法律問題的時候,傾向于通過法律問題的描述來表達作者所要傳達的思想,即反映和揭露現實中的問題,而它在進行這種描述的過程中,對法律適用的前提,法律的實施以及法律適用的結果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歪曲”[3](P91),對文學作品的解讀應當限于作品本身,而不應當進行不恰當的延伸。
然而無論是霍爾茲沃斯還是沃德都沒有將研究的重點放在對于文學作品中的法律現象的真實性的考證。前者所關注的是文學家通過敏銳的觀察和細致的描述對于歷史法律情境的還原,而這只是作為法律史學研究的參考[4](導讀,P15),而后者關注的是通過對人物成長的描述以及人物關系的解析來剖析法律制度變遷中的問題及困境[1](P59-89)。相反,學者們認為文學對于法學的價值不在于它所記述的事實的真實性,而是其所表達的主題的真實性。文學本質上仍然是人類生活的再現,它無法脫離生活而創作。而經典和暢銷的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并始終是支持者和批評者們所關注的重點,正是因為它們呼應了人們對于生活的內在體驗和感悟。
本人擬從文學作品對于法學史研究的價值入手,對文學中的法律史學研究的思路進行逐一剖析,分析該研究的理論前提﹑理論基礎以及對于法學理論和法律實踐的價值,從而對文學,尤其是歷史文學作品對于法律史研究的意義進行重新反思。
二、文學作品對于法律史學研究的價值分析
文學對于歷史學研究的價值是毋庸置疑的。在史前文獻檔案出土并被成功破譯之前,作為世界文學史上最早的文學作品之一的神話是歷史學家賴以了解早期人類社會的“孤證”[5](P3)。希臘史學家科諾普·提爾瓦爾(Connop Thirlwall)曾指出,“我們所了解的有關希臘最早居民的情況來自希臘人自己的陳述”[5](P3)。在沒有其他考古資料支撐的情況下,我們對于遠古人類法律文明的猜想也只能依據來自于古代先民們口耳相傳的傳說記載。
隨著考古研究的發展,包括文字記載等大量實物的出土,法律史學的研究更為客觀,更接近于歷史真實。這些“更加完整﹑更加冷靜的數據來源”成為法律史學研究的主要依據。然而包括法律史學家在內的歷史學研究者們提出的又一個問題是,這些殘存的歷史遺跡,以及關于法律制度的學者記載給我們留下的僅僅是概括性﹑斷言性的描述,而對于實踐性的法律研究而言,學者們更加期待的是對于史料中的法律制度的運行﹑以及法律適用者的體驗等等法律生活的考察。文學,為法學研究者們提供了這樣的研究窗口,“因小說家敘述時事,必須牽涉其背景。此種鋪敘,多近于事實,而非預為吾人制造結論”[6](P5-6)。也正是如此,霍爾茲沃斯在英國法律史研究中發現,狄更斯在其小說中對19世紀前英國法律生活的細致入微的描寫所展現的法律生活,對于這一時代英國法律史研究的貢獻可以和同時期法律史研究者的論著相提并論。法律史的一個研究目的是盡可能的還原所研究年代的歷史事實和細節,而包括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司湯達(Stendhal)﹑狄更斯﹑奧諾雷·巴爾扎克(Honoré Balzac)等作家的文學作品,以其對生活的深刻體察和細致入微的描述再次獲得了法律史學家的關注。
不僅如此,文學也成為法學學者探尋法學的政治歷史傳統,發現為宏大封閉的歷史話語體系所遮蔽的法律生活的細節的重要的史料來源。盡管法律史學家們都在盡力的還原所研究年代的法律生活原貌,但即使是法學史學家本人也無法否認,無論是歷史學家的著作,還是他們本人的論著,所記述的歷史并非有聞必錄,雜亂無章,歷史研究是在提煉和取舍﹑去粗取精的過程中逐步清晰,而研究者所秉承的指導性的觀念將負責歷史資料的遴選﹑鑒別﹑評價,提供指定的歷史闡釋,并毫不留情的撲滅另一些不同的觀點[7](P238)。然而這種“鑒定”卻并非真的可以改寫歷史,當我們在考察一種法律制度及其思想淵源的時候,我們卻不得不回復到對其的歷史溯源中,而包含著多元文化話語,以自己的方式記錄了全景化歷史的文學為法律史學家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質料來源,也因此莎士比亞的戲劇曾一度成為法律史學研究者的重要文學經典,《亨利五世》被用于研究中世紀的歐洲國際法,《理查德三世》﹑《國王約翰》以及《理查德二世》被用于研究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早期憲政思想的重要補充資料。
三、法學學者對于文學作品的史學思考
和其他“文學中的法律”相比,對文學作品進行法律史學研究擁有更為廣泛的研究者群體,來自法律史學﹑法理學等多個研究領域的學者們都對此有著濃厚的興趣。文學不僅為法律史學研究者們展示了栩栩如生的法律人﹑訴訟庭審等法律場景,也為法理學研究者們提供了法律思想發展﹑演變的宏大法律生活畫卷。
從現有的文獻研究來看,文學在不同的問題研究領域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在對古希臘﹑北歐早期等先民社會的法律制度的探討和研究中,由于缺乏相應的考古資料和文字記載,以神話﹑史詩和傳奇等為主體的文學作品成為相應時代﹑地區的主要研究素材。而在對具有豐富法律史料記載及考古資料支撐的古代及其之后社會的法律制度的探討和研究中,現實主義風格的戲劇﹑小說等文學作品以其對于所屬時代的政治生活風貌的真實而又細致的刻畫,成為法學研究者們推究作品主題所表現的同時代政治法律思想及其制度文化的補充性研究素材。
1.文學中初民社會的法律生活
斯堪的納維亞的冰島傳奇,古希臘英雄傳說以及荷馬史詩等文學作品常常被包括法學﹑歷史學等學者們用于探求初民社會法律生活的重要的研究素材。
威廉姆·米勒(William Miller),通過對流行于冰島的北歐傳奇故事的研究,系統的分析了先民時代冰島賴以維系其公共秩序的復仇為主要內容的法律體系的轉變過程[2](P71-78)。在此基礎上,波斯納根據冰島社會轉變過程中政治司法權力運行機制,運用經濟學成本收益原理,對作為冰島法律體系的主要內容的復仇的成本,懲罰的執行成本,贖金制度等內容進行深入的剖析[2](P71-78),對法律替代血親復仇進行了合理性的論證。
作為兼具法律經濟學和深厚文學素養的法學研究者,波斯納同樣樂于通過荷馬史詩來闡釋先民社會中國家的起源,以及保險﹑財產法﹑家庭法﹑合同﹑侵權的嚴格責任制度﹑刑罰等一系列法律制度的發生和變遷。《伊利亞特》(Iliad)和《奧德賽》(Odyssey)中所描述的政治法律生活,成為波斯納反思和批評當代對于國家等政治法律現象起源和發展研究的重要素材。在國家問題上,雖然“從霍布斯到諾齊克,一些政治哲學家都在尋求為國家正當化,認為國家是解決內部安全問題的一個方案”[8](P147),波斯納通過荷馬史詩中故事細節的分析,指出“習慣﹑禮物交換﹑榮耀﹑親屬關系以及其他見于荷馬史詩中的前政治制度機構,就為國家提供了一個替代性的秩序體系”[8](P147),國家并非是保持社會內部秩序的唯一可能的解決辦法,“荷馬史詩并沒有顯示,大規模的公共項目就要求有政府的監督,但它們確實展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如何組織起來,對一個有城墻防御庇護的不公者實施報復”[8](P147),以及“如果一個社會中,財富分配不平等,富裕的個體就會有動力雇傭家臣,國家也許最終就從這樣的武裝起來的隊伍中浮現出來了”[8](P147)。
其實,從文學中探求初民時代的法律政治生活并非是法學學者開創的研究論域,文學研究中對此有著更為豐富詳實的考證。以古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為例,尼爾森﹑詹寧斯﹑維里科夫斯基﹑佩洛普等學者先后通過對古希臘﹑古埃及等故事發生同時期的歷史進行考據,認為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可能是對科林斯戰爭中王朝之間軍事沖突和外交妥協的隱喻,或者是對古埃及王埃赫那吞(Akhenaten)一生的故事再現,或是對古希臘王位繼承制﹑陶片流放法﹑僭主政治等的文學體現和反映[5](P193-238)。
如果將法學學者的研究和文學學者的研究加以比較,雖然二者都是基于神話﹑傳奇和史詩所進行的包含著想象和推理的研究,但是前者更多的強調的是邏輯的理性分析和合理性論證,而后者則更多的立足于歷史學的研究。
2.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的法律描寫
現實主義[9](P181)風格的戲劇﹑小說等文學作品,由于其對于作品主題所屬時代社會風貌,甚至是對瑣碎性﹑物質性的細節的近乎忠實的記錄和描述,備受法律史學研究者的關注。在目前的研究中,莎士比亞的歷史劇,司湯達﹑狄更斯﹑巴爾扎克等學者的歷史小說成為法學學者常常用于法律史學研究的對象。
法律史學家霍爾茲沃斯對于狄更斯小說的法律史研究,是對現實主義小說進行法律史學分析的經典。作為16卷本《英國法律史》的編撰者,霍爾茲沃斯認為狄更斯對于19世紀英國法律運行機制﹑執法者及其工作狀況,以及法律對于人們的影響的記述是近乎精確客觀的,“沒有作家能夠如此深刻地理解這些藝術素材的規模與復雜,破落與繁華”[4](P11)。作為法律史學教學的講義,霍爾茲沃斯以法院與法律人的居所,法律人﹑法律助理與法律文員,大法官法院程序以及普通法程序等為基本線索,對狄更斯的《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遠大前程》﹑《荒涼山莊》﹑以及《匹克威克外傳》等小說中的法律人﹑法律場景以及法律程序等法律現象的描寫進行了系統的梳理,以文史互證的方式向我們展現了19世紀英國法律生活的完整圖景。
法哲學學者沃德則從莎士比亞《理查德三世》﹑《國王約翰》以及《理查德二世》等三部歷史劇入手,對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早期英國都鐸王朝時期的憲政思想進行了系統的考察。作為對英國憲政思想發展的歷史性研究,沃德首先對莎士比亞三部歷史劇創作的時代,16世紀90年代至17世紀早期的都鐸王朝所面臨的政治困境,即王朝的政治危機以及關于君主制﹑混合君主制的抉擇難題等進行了描述;其次,沃德對于莎士比亞歷史劇的政治內涵研究的兩種主要觀點,新歷史主義和唯文化論主義的研究進行了歸納和分析。在完成對作品創作的歷史背景,以及對于作品的不同的解讀方式的分析之后,沃德對莎士比亞所塑造的理查德三世﹑約翰以及理查德二世等人物形象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闡釋了人物身上所升發的憲政主題的探討。
顯然,和早期的法律史學學者強調對法律真實的客觀再現相比,當代的法學研究者更加強調的是歷史文學中的人物所體現的政治法律內涵,文學中的法律史研究不再僅僅是故事與歷史客觀的簡單對照,更加強調的是語境中的法律思想的體現和闡釋。
事實上,無論是先民社會的游吟詩人,19世紀崇尚現實主義﹑自然主義風格的擅長描繪社會風俗史的歷史文學作家,還是當代的文學紀實者,甚至是被冠以“后現代文學”的小說家們,都始終沒有放棄對于人類歷史的觀察和探求。當我們將他們的作品放在歷史的維度下進行考察的時候,作者向我們展示的不僅僅是歷史事件的發生和變遷,還有他們對于如何看待歷史的多元思考。如果說荷馬史詩﹑狄更斯小說﹑莎士比亞的劇作等等作品的作者眼中的歷史真實是唯一的﹑客觀的,作品是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進行虛構和再造,那么被稱之為“后現代”的文學作者們所看到的歷史則是多元的,“歷史不再是一種具有唯一性的客觀解釋,而是一種只有在多個文本的共同作用下才會顯現的一個動態平衡體”[7](P238),在后者的作品中,我們看到的不再是宏大的敘事結構,而是通過故事中不同人物角色的敘述,故事中所討論的包括媒體﹑官方聲明在內等不同文件的記述呈現的歷史真實。在當代文學研究中,通過這種方式所創作的歷史小說,雖然其主人公及其生活經歷是完全虛構的,但是以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為代表的文藝理論家們則認為這種作者基于大量的史料整理﹑收集﹑加工和分析基礎上所構建的文學作品,雖然可能并不是具體歷史事件的真實,但卻是符合歷史邏輯﹑情感邏輯﹑人倫邏輯的真實,甚至提出了“歷史的虛構與小說的真實”的觀點[7](P238-273)。當然,從目前的文學中的法律史研究來看,尚沒有關于這類文學作品中的法律史的研究與探討。
四、文學作為法律史料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和文學中法律研究的其他論域相比,文學中的法律史學研究吸引了更為廣泛的研究者,無論是法學學者,還是文學理論研究者﹑文學作者都對文學中關于歷史主題的闡釋進行了豐富而深入的探討。盡管如此,文學中的法律史學研究并不是毫無邊界的。來自對這一領域研究的最主要的批評就是文學作者對法律現象的描述是不準確的,不僅僅存在著虛構,對法律認識的錯誤,甚至還包括來自作者主觀判斷的歪曲。如何分析文學作品中的虛構與真實,如何看待文學中的歷史故事,對這兩個問題的界定直接決定了研究者對于文學中法律史學研究的研究路徑,以及他通過文學作品進行法律史學分析所獲得的結論。
即使是文學中法律史學研究的支持者,也并不否認文學家對于法律現象的描述并不是非常準確,甚至在對一些重要的法律實踐的認識上存在著嚴重的錯誤,狄更斯就曾經在《荒涼山莊》中將本應當由遺囑檢驗法院審理的賈迪思訴賈迪思案,安排給大法官法院來審理[2](P141)。雖然事實上,這種法律上的嚴重錯誤并未影響狄更斯的這部小說為同時代,及其之后,甚至當代的學者作為研究19世紀英國法的補充性材料的地位,但顯然,小說關于法律實踐的錯誤描述不能作為法律史學研究的基本法律事實之列。
對文學中的法律史研究的真正具有影響的批評來自另一個問題,即文學創作中的虛構對于文學中法律史學研究的影響。我們可以欣賞虛構的文學作品,甚至是以歷史為基礎虛構的歷史文學,但是我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都無法接受一個虛構的歷史,歷史應當是曾經發生過的事實。然而在這里我們討論的前提是“虛構”是我們認為從沒有發生過的事情。那么對于無法被證實的,但通過其他已經被證實的事實可以推理出的“事實”,并且這種推理是符合我們所公認的歷史邏輯﹑情感邏輯以及人倫邏輯,甚至是理性經濟分析邏輯,對于這樣的“事實”,我們又該如何認定呢?這樣的“事實”無疑是虛構的,雖然符合邏輯,但是我們找不到可以證實其存在的證據,但是它們無疑也是重要的,因為文學作者,尤其是歷史文學作者們正是通過這些“虛構”的“事實”將歷史的碎片連接起來,為我們再現了豐盈的故事場景。
歷史無疑有著它自己“必然”的發展軌跡,但是我們同樣無法否認歷史中也同樣充滿了偶然性,一個小小的蜘蛛也可能改變一位將軍的一生,“蝴蝶效應”的例子俯首皆是,我們無法預知未來,同樣在很多時候我們無法確切的知道過去發生了什么,事實上,即使是歷史學家也會告訴我們,我們不必為了探求過去而去進行考證和考據的研究。我們研究過去是為了理解現在,把握未來[10](P23)。當波斯納在對文學作品中的虛構對于法律史學研究的意義提出批評的時候,他也在通過古希臘悲劇﹑荷馬史詩研究初民社會的國家形態以及法律生活,而不是投身于考古,專注于古墓銘文的研究[11](P1995)。而當唐·德里羅(Don DeLillo)明確指出奧斯瓦爾德(Oswald)是他純粹虛構出來的一個人物的時候,我們卻無法否認《天秤星座》(Balance)創作中所采用的關于肯尼迪遇刺時的新聞資料﹑官方文件等等大量的歷史材料,雖然沒有進入歷史學家的記述,但確實是當時真實存在的記述[7](P269-273)。而又有誰能夠據此否認德里羅據此而創作的虛構人物所經歷的一切是完全虛構的呢?這部小說曾引起的巨大轟動不正是說明了這個虛構人物所體現的這段歷史讓作者同時代的人們確實看到了他們生活中的一個側影呢?如果是“虛構”,那么它不足以構成對文學中的法律史研究的批評,除非我們真的能夠證明“虛構”的聯系是錯誤的,歪曲的。符合“邏輯”的“虛構”事實上在某種意義上延伸了人類對于自己的思考,幫助我們反思歷史,從而更好的面向未來。
[1] Ian Ward.Law and Literature:Possibilities and Perspective[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2] [美]理查德·波斯納.法律與文學[M].李國慶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3] Tony Sharp ,Versions of Law in Literature[C].Law and Literature(current legal issues).Vol.2,1999.
[4] [英]威廉·霍爾茲沃斯.作為法律史學家的狄更斯[M].何帆譯,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2009.
[5] 王以欣.神話與歷史——古希臘英雄故事的歷史和文化內涵[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6] 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7] 王建平.美國后現代小說與歷史話語[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8] [美]理查德·波斯納.正義/司法的經濟學[M].蘇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9] 張德明.世界文學史[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10] [英]愛德華·卡爾.歷史是什么[M].吳存柱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81.
[11] Richard Posner .Overcoming Law[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1996.
責任編輯:侯德彤
Legal Histo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its Limitations
XU Hui-fang
(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2249, China )
Study of legal history in literature is one of the earliest fields of research under the "law in literature". From late 19th century to early 20th century, by means of interpreting legal images in literary works of different times, legal scholars provided legal history studies with abundant materials and brought about the discussion concerning the value of literary works to legal history as well. Academic researches on legal history in literary works will benefi t the retrospection of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signifi cance of historical works to legal history.
law in literature; legal history; literature
D90-05
A
1005-7110(2014)01-0022-05
2013-11-29
許慧芳(1979-),女,內蒙古包頭市人,中國政法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法理學,法律語言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