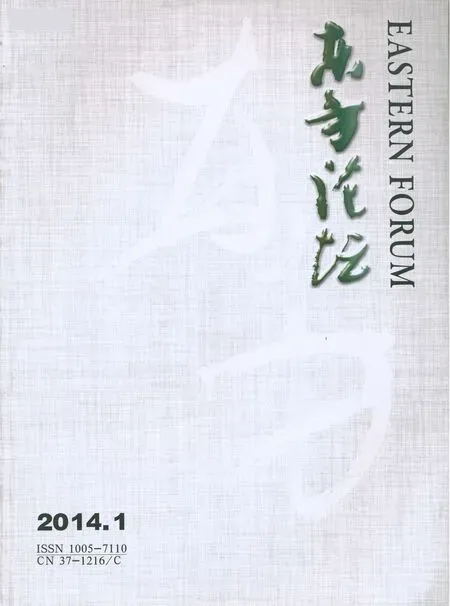革命時代的生活與文學之美
——《這邊風景》簡論
(青島大學 文學院,山東 青島 266071)
革命時代的生活與文學之美
——《這邊風景》簡論
王金勝 段曉琳
(青島大學 文學院,山東 青島 266071)
對于王蒙個體和當代文學史來說,《這邊風景》都是別具典型意義的作品。小說深入、直觀地展現了作家16年新疆生涯,飽含著當年的王蒙與今日的王蒙對青春歲月的極大熱忱與真誠。它以豐富的經典細節,表現了革命年代邊疆百姓的切膚生活和情感,而“意識流”和“小說人語”手法的運用,擴展了作品的藝術表現力,構成了作家穿越文化時空的靈魂對話。
《這邊風景》;細節;意識流;“小說人語”;當代文學史
什么是好的小說,有沒有衡量一部好的作品的通行的標準,恐怕是一個見仁見智的難題。但有一點不應該被忽略,那就是:無論在什么年代哪個民族,那些秉承著真誠﹑善良和正直之心,及純正而嚴肅﹑虔敬而樸實的態度,通過鮮活創新的藝術形式和獨具魅力的質感語言,傳達了深厚的個體思想與深刻的個性情感體驗,給予讀者以穿透時空的精神感染力的作品,才是好的作品。而王蒙的這部塵封四十年的《這邊風景》正是這樣的作品。
小說以四月三十號夜間發生的兩噸多小麥被盜案件為始,推開了這蕩氣回腸的人民公社時期的新疆伊犁畫卷,并以小麥被盜案為主線,在1962“伊犁-塔城邊民外逃事件”,“四清”運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接連不斷的階級斗爭背景下,將邊城伊犁的秀美,生產生活的壯闊,風土人情的真實,用帶著蘋果香,馕餅香,與奶茶香的筆墨敘寫出來,讓讀者看到了王蒙那真實而激動人心的青年﹑壯年,看到了中國真實而鮮活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這便是王蒙雖九死而未悔的當年好夢,這便是王蒙那“黑洞當中亮起”的“光影錯落的奇燈”[1]。
一、生活·愛情·信念:那不可摧毀的美與真
新疆是王蒙人生中最重要的坐標之一,與伊犁的邂逅是王蒙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從1963年,29歲“流放新疆”,直到1979年,45歲的王蒙才回到北京,其間整整16年,人生最重要的時期就在邊疆度過。在新疆題材作品集《你好,新疆》中,王蒙以小說﹑散文﹑詩歌等體裁回顧了自己在新疆的生活經歷,而這部70萬字的大長篇《這邊風景》則是對王蒙16年新疆生涯的更深入更直觀的展現,這當中飽含著當時的王蒙與今日的王蒙對“這不過是人生”的青春歲月的極大熱忱與真誠。
王蒙在談到創作過程時自述:“在整理這部書稿當中我得到的一個結論,就是生活是不可能被摧毀的,愛情更是不可能被摧毀的,文學不能被摧毀,世界不能被摧毀。所以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在有霧霾的情況下,在我自己也感到非常無奈的情況下,我仍然歌頌我們的新疆,仍然歌頌我們的各族人民,仍然歌頌愛情,仍然歌頌生活,仍然歌頌青春……”[2]翻開《這邊風景》,我們會發現,在眾多的斗爭嘶喊下,“本質上仍然是那親切得令人落淚的生活”,是青春時代的黃金年華,是“瑣細得切膚的百姓的日子”,是“活潑的熱騰騰的男女”[1]。這不可摧毀的生活,是飄著果香與奶茶香的異域邊疆生活。
一部成功的作品中,往往離不開豐富的經典細節。這些不可復制也不可缺失的細節,在作品中是一種結構性的存在,它們與小說的情節事象融為有機的整體,貼膚地呈現著百姓的日子,彰顯著那份被政治話語所遮蔽的令人沉醉的生活,是一份有著作家真切心靈感受的真實,也是一份讓讀者產生親歷目見的真實感的證詞。王蒙在談到現實主義小說時,對于經典現實主義作家的細節捕捉和表現能力贊不絕口:“對細節的描寫生動﹑詳盡﹑準確。……現實主義寫對話如聞其聲,寫肖像﹑場景如月光﹑晨霧﹑樹林﹑暴風雪﹑海﹑船使人如臨其境,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現實主義在描寫上取得的成就是無法逾越的。你現在想在人物肖像﹑城市氛圍或天氣變化的描寫上超過托爾斯泰,超過巴爾扎克簡直是無望。”[3](P26-27)
這伊犁的異域生活,首先是吃喝拉撒,婚喪嫁娶的俗世日常生活。從馕餅茶炊到土爐壁毯,從割麥刈草到刷墻抖氈,從婚喪公事到牧耕生產,從小姑娘的友誼到婦女團體的茶談,無不細碎而真實,無不生動而鮮活。其中第17章的麥收與第49章的打馕寫得尤為精彩。在伊犁,麥收并不像內地那樣具有龍口奪糧,十萬火急的性質,而是一場規模宏大,持續時間長的大作戰,凡是喘氣的都要投入到這浩浩蕩蕩的麥收中去。在麥收之前要進行一場動員全社員的大聚餐,宰牛打馕,灌肺燒湯,賣貨存倉的緊張節奏,以一種濃烈的節日氛圍召喚著即將到來的神圣勞動。從這動員大餐到正式開鐮,再到打場收倉,王蒙的麥收寫出了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氣勢,這份宏偉的翻滾著濃烈麥香的激情,即便在今天看來也是令人心潮澎湃的。
在新疆,馕的重要性無與倫比,打馕是一件大事,在這件大事里是伊犁人最日常的生活與最日常的勤勞智慧。如果說麥收是一種集體的宏闊的真實生活,那么打馕則是一種個體的家庭的,最普通也最重要的日常生活。從馕餅的分類到土爐的構造,再到打馕的各個具體流程,王蒙以一種熱誠的尊重與真摯的欣賞來書寫“馕”這種最具新疆特色的維吾爾主食。“米琪兒婉走上臺去,跪在爐口邊,左手端起淡鹽水,右手蘸著向發白的爐壁上一甩,嗞啦,水珠一碰爐壁就化成了水汽。這個動作的目的是防止馕熟后粘到爐壁上揭不下來,同時通過觀察這種現象和聽這種響聲判斷爐壁的熱度。如果水珠一甩上嗞地化成了白煙,聲音尖厲短促,說明爐壁太熱,發黑。如果‘嗞——啦’一聲,慢慢地化成水汽,聲音低鈍,說明爐壁溫度不夠,根據不同的爐壁溫度掌握烤馕的時間長短。打馕前這水珠兒的一甩﹑一看﹑一聽,是打馕全部技術中最高級微妙的一招……”[4](P610)此外,《這邊風景》中還有諸多王蒙式的獨特發現,而這些獨特發現都來自于生活中那可觸可感的細節。“誰注意過小姑娘們的友誼?她們形影不離,梳一樣的頭發,戴一樣的頭飾,穿一樣的靴鞋。甚至她們當中如果有一個人有某種習慣動作——譬如擠一擠左眼吧,不久,朋友們就都會擠起左眼來。她們在一起眉飛色舞地說啊,說啊,沒完沒了地說啊,她們的談話對于最親愛的生身母親也是保密的。”[4](P49)這一段生動細膩的友誼敘寫,即便是王蒙在重讀《這邊風景》時也感嘆仿若是“天假王手”,“像個女孩兒寫的”。
更重要的是,王蒙對于不可摧毀的異域生活的敘寫決不局限于吃喝拉撒熱氣騰騰的生活日常,而是在真正參與到生活中去后,深入關注到少數民族日常生活下的宗教﹑哲學﹑美學﹑文化心理層面。《這邊風景》中的民族民俗生活,常常是以對比的方式展現——南疆與北疆的對比,塔塔爾族和維吾爾族的對比等等,但更多也更直觀的是漢維兩族間的對比。比如“維吾爾人形容大小長短與漢族最大的不同在于,漢族人形容大小長短,是用虛的那一部分,如用拇指與食指的距離,或左右兩手的距離表示大小長短,而維吾爾人是用實體,如形容大與長,他可以以左手掌切向右肘窩,表示像整個小胳膊一樣大,而用拇指捏住小指肚,則表示像半個小指肚一樣小。”[4](P594—595)但是,王蒙在這些生活習慣下發現了更重要的差異“生活習慣的差異畢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們十分可愛的隨性﹑熱情﹑樂觀﹑幽默和對美的追求。”[4](548)即便是上文所提到的最普通最日常的打馕,王蒙也發現了這最日常的做飯中的“維吾爾人生活哲學的某些特點”,“第一是重農主義,他們認為馕的地位十分崇高,有人甚至說在家里馕的地位高于一切。第二是唯美主義,他們差不多像追求一切實用價值一樣追求各種事物的審美價值……很少有別的民族像維吾爾人這樣在自己的最一般的干糧上刻花紋的。”[4](P609)更為重要的是,王蒙在漢維兩族之間的差異下,又發現了更為可貴的共同性,更為重要得多的共同點,從語詞語匯到風俗習慣,兩族人民都有著不可分割的血肉相連的共同性。
真誠摯熱的愛情,永遠都是王蒙作品中最溫暖動人的部分。在這不可摧毀的生活中,也包含著鮮活得令人落淚卻不可摧毀的愛情。《這邊風景》中細致深入地描寫了三對男女令人動容的愛情故事。第一對是熱情潑辣的狄麗娜爾與浪漫溫柔的廖尼卡,他們的愛情在手風琴的歌聲與玫瑰花的芬芳中成長綻放。小說如此描寫狄麗娜爾與廖尼卡愛情的開始:“我騎著自行車在公路上飛馳,突然,背后一顫,一個姑娘跳到我的自行車的貨架子上,事先連個招呼都沒有打。那就是她,她時而用一只手扶一下我的后背,一會兒撒開手,讓我老是擔心她會掉下來。于是,我心花怒放,車蹬得飛快,我記得車一直緊跟著一輛解放牌大汽車飛跑。到了伊寧市,背后突然又是一震,等我回過頭來,她已經消失在西沙河子的白楊林里。”[4](P56)愛情如此美好,純真,熾熱。任是誰讀到這樣的文字都會為之感動。第二對是沉靜溫順的雪林姑麗與正直善良的艾拜杜拉。王蒙對雪林姑麗是偏愛的,作者專門拿出一章,以“你”第二人稱敘述為這丁香花一樣的姑娘作了“小傳”,并在這一章最后跳出小說敘述,專門引用寫丁香的古詩詞來表達對雪林姑麗的喜愛與贊美。雪林姑麗對艾拜杜拉的仰慕與暗戀,雪林姑麗輾轉反側不能成眠,雪林姑麗新婚后無處言說卻又實實在在的幸福,在王蒙的筆下都是這樣的細膩流轉,生動可感。比如在對艾拜杜拉鐘愛而又心疼的無限柔情里,雪林姑麗無法入眠而在靜夜中獨坐,在無邊的夏夜的靜謐里,細細聆聽玉米拔節的聲音,田野上彌漫的香氣,“有青草的嫩香,有苜蓿的甜香,有樹葉的酒香,有玉米的生香,有小麥的熱香,還有小雨以后的土香”[4](P205),涼風將陣陣香氣吹到雪林姑麗的鼻孔里,令她如癡如醉。這便是愛情初始時候的苦澀﹑甜蜜﹑親切﹑質樸。到新婚旖旎時,王蒙特意為雪林姑麗和艾拜杜拉寫了兩個生活細節來突顯愛情與婚姻的幸福,一是“脫靴”,二是“情話”。“脫靴”是新婚夫婦間的小別扭,雪林姑麗因為新婚之夜艾拜杜拉不讓她給自己脫靴而心里有點小別扭,其實這只是個美麗的誤會,那只是艾拜杜拉對她的愛與尊重。“情話”是雪林姑麗夫婦間最核心私密的暗語,“大寨……我想大寨……”,“快點過來吧,我要給你說大寨……”[4](P382)這是夫妻間親密相合的私人情話,這暗示著婚姻的甜蜜與幸福。第三對是堅強獨立的愛彌拉克孜與勇敢多情的泰外庫,這一對的愛情相較于前兩對而言,更加的艱難,更加的苦澀也更加的深刻熱烈。愛彌拉克孜是個美麗堅強,自尊自立的獨手女醫生,而泰外庫則是有過一次失敗婚姻的苦車夫。泰外庫因為愛彌拉克孜的堅強獨立而愛上她,而愛彌拉克孜也為泰外庫笨拙的質樸,癡情的赤誠與猛烈的真摯所深深感動。“泰外庫夜奔”在我看來是《這邊風景》中最為動人的愛情情節,愛彌拉克孜與泰外庫因為誤會與奸人的蒙蔽而鬧翻了,愛彌拉克孜拂袖離去,泰外庫在絕望的痛苦與無處言說的濃情下,沒有穿棉衣就在這寒冬的夜里,向著愛彌拉克孜離去的方向奔跑,在月光下看著她的身影,她的臉,她的腳步,就這樣只注視著她跟著她奔跑了一路,最后又遠遠地默默地看著愛彌拉克孜在醫療室的電燈下伏案哭泣,泰外庫的心都碎了,他悲痛欲絕,用巨大的愧悔責備著自己。這便是愛情的苦澀與艱難,這便是愛情的真與美,這便是生活的真與美,在任何時代,在任何時候,都沒有人可以摧毀,可以拒絕這樣的真和美。
生活之所以不可摧毀,因為它內含著王蒙一以貫之的青春信念與生命熱忱。“生命是生動的,標簽指向正確與擁戴的時候,它是生動的,指向有錯與否定的時候,生命的溫暖與力量絲毫沒有減少,更沒有不存在。世界與你自己本來就是擁有生命的可愛可親可留戀的投射與記憶。”[4](P703)《這邊風景》真實地表達了王蒙個人處在逆境﹑國家處在亂局時的現實。即使身處這逆境與亂局,王蒙依然真誠地熱愛著這片土地,熱愛著這些少數民族。對日常生活的熱忱,令王蒙的精神世界充滿陽光。《這邊風景》延續了《青春萬歲》﹑《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等王蒙早期作品中的理想主義色彩,總是以一種堅定熱情的信念,相信過并依然相信著。當時的王蒙并無意挑戰極左的政治形態,而是盡量靠近那些斗爭的“口號”,但是,在這些政治“口號”的鐐銬下,王蒙依然去書寫吃喝拉撒,柴米油鹽,寫漢族﹑維吾爾族﹑塔塔爾族的百姓生活,這戴著鐐銬的舞蹈,畢竟仍舊是舞蹈,依舊美麗動人。不可摧毀的生活,不可摧毀的青春,王蒙以其鮮活的個體生命體驗,將生命的真,生活的真,生存的真,人性的真,以穿透時空的情感和精神感染力傳達給讀者,將塵封洗去,在流金歲月中流淌出雖九死而猶未悔的當年好夢。
二、“意識流”與“小說人語”:穿越時空的對話
《這邊風景》是王蒙四十年后的驀然回身,是一道幽暗時光隧道中的電閃雷鳴,是從往事中翻身走出來的記憶,是從遺體走向新生的青春。在《這邊風景》中我們可以看到那段過往的歲月,那個過往的王蒙,真實的青年﹑壯年時期的王蒙。這個王蒙看似是過時的,被遺忘的當年的王蒙,卻依舊是與那1950年代青春吶喊﹑1980年代華麗歸來的王蒙血脈相連,從未離去的真實王蒙。
《這邊風景》的創作時間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時的王蒙主要的閱讀經驗是現實主義的作品,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巴爾扎克這樣的現實主義大家影響了王蒙的創作實踐。注重細節﹑注重人物形象的描繪與刻畫成為那個時候王蒙文學創作的一大特點。直到1970年代末以后,王蒙的創作才真正變得自由﹑大膽﹑先鋒﹑實驗。如王蒙所言:“我在1974年前后那個時代寫小說,遠遠不像后來膽子那么大,我應該說是相當謹慎的,我是用最傳統的方法來寫小說的。比如要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故事,這個故事要有很多的情節,并且情節的發展是合乎邏輯的,故事還要有懸念,懸念要能夠抓住讀者的心,讓讀者不能忘懷。我覺得,在這種比較傳統的創作方式里面,仍然也有它另一種的樂趣,而且容易被讀者所接受,現在我再看這兩卷書,不但對讀者是新鮮的,對我自己也是新鮮的。”[2]事實上,1978年“歸來”后寫的《向春暉》《最寶貴的》《悠悠寸草心》等小說仍然保持著王蒙的現實主義風格,變化是自1979年的《春之聲》《夜的眼》《布禮》《蝴蝶》和《風箏飄帶》等小說開始,突破了沿襲已久的現實主義敘述方式,將意識流等現代主義小說因子融入創作。雖然王蒙以及其他批評家曾多次提到寫于1970年代的《這邊風景》是老實的,保守的,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但在《這邊風景》卻早已散發著明顯的現代意識流氣息。這種王蒙式的意識流敘事在泰外庫這個人物身上,運用得十分明顯﹑到位。
第三十九章寫的是,泰外庫迷戀上了美麗堅強的愛彌拉克孜,初嘗相思暗戀的好漢子泰外庫,為著不知所措間所萌生的不可阻擋的愛情而苦惱,而沉醉。在這一章中王蒙運用意識流的小說手法,中斷了傳統的線性敘事模式,運用大量的筆墨來敘寫泰外庫的心理真實,令讀者為這個少言寡語的,善良多情的,熾熱真誠的苦車夫的愛情所深深打動。“朦朦朧朧,他似乎看見了戴著土黃色的大方頭巾﹑穿著紫紅色的連衣裙和深灰色線呢外衣的愛彌拉克孜仍然蹲在火灶前。這難道是真的嗎?這難道是假的嗎?從一大早,到現在,他的房子里充滿了的是蹲著的愛彌拉克孜。愛彌拉克孜的挺拔的身軀與修長的獨手臂是多么健壯與堅強……”[4](P496)“從來到走,不過是幾分鐘的時間,然而,這間房子永遠地留下了愛彌拉克孜的印記,空間里仍然彌漫著愛彌拉克孜的音聲,空氣里仍然彌漫著愛彌拉克孜的氣息。每一件冰涼的﹑呆板的東西都變活了,會說話了,暖和了。不漂亮的﹑不可愛的﹑對于泰外庫來說不過是冷淡的暫住一下的房間變得親切了,牽腸掛肚了。條案上立放著的手電筒挺身作證:‘我是愛彌拉克孜親手用過,又親手拿回的。’灶里的閃爍著微光的余火悠悠絮語:‘我的溫熱是愛彌拉克孜姑娘留下的。’上了年紀的﹑歪斜了的門充滿喜悅地歪著頭,它在敘述愛彌拉克孜醫生怎樣把它拉開,又關上。墻壁上的裂紋,也像因為歡喜美麗的愛彌拉克孜的到來而笑開了花。”[4](P497)在這里,王蒙中斷了小說的情節鏈條,放棄了小說人物的外部刻畫,而是通過人物心理的閃回﹑停頓﹑放大﹑延長﹑重復﹑獨白﹑對話,將寫作的焦點對準人物的內心世界,將泰外庫的內心﹑人格真實而生動地刻畫出來。在這里,泰外庫的強壯的拳頭與沉默寡言的性子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也有著溫熱可愛的豐富的情感,他可以愛人也可以被人愛。由此可見《這邊風景》的“最傳統的方法”其實并不保守,1970年代的王蒙不僅有著1950年代的現實主義風格與對“十七年”的精神追求,也暗流著1980年代后王蒙創作探索的可能與小說創新的潛質。
對于《這邊風景》每一章后面的“小說人語”,王蒙如是說:“這本書出來,對于讀者來說是新作,對我來說卻是舊作,我不想對這部舊作做過多的改動,第一我沒有這個能力,第二就會使那個時代的很多時代特色都消失了。但是另一方面,作為新作,2012年我對它重新作了整理歸納和某些小改動,我需要有一個21世紀的態度和立場,需要給讀者一個交代,所以出版社的廣告詞就是:‘79歲的王蒙對39歲王蒙的點評。’一般情況下,小說不這樣寫,但中國有這傳統。《史記》有‘太史公曰’,《聊齋志異》有‘異史氏’,所以我覺 得中國人能接受這種形式。也可以不寫‘小說人語’,最后寫一篇很長的概述,我覺得那不是好的辦法,好像自己給自己做結論似的,更倒胃口。‘小說人語’比較靈動,借這機會說說其他的也可以。比如打馕那章,我借機寫了我當時的房東大姐,既是親切的,又是自由的。它是可即﹑可離﹑可放﹑可收的。”[5]《這邊風景》的文本,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1970年代的小說文本,二是新世紀當下寫作的“小說人語”,一個是當年王蒙的波瀾壯闊,一個是當下王蒙的寧靜坦然,小說人說小說,既是文體上的一種創新,又在兩個文本的對照互文中勾勒出一個鮮活的完整的王蒙。
這些“小說人語”,多為精短的隨感,大致可以分為幾類:一是對舊作文本的自我點評,比如第5章的小說人語“誰注意過小姑娘們——西北地區更喜歡用的詞是丫頭——的友誼?她們形影不離,梳一樣的頭發,戴一樣的頭飾,穿一樣的靴鞋……嗚呼,心細如發,發現了新大陸上的一株小草……天假王手,怎么像個女孩兒寫的!”[4](P52)二是對小說文本中的人名﹑地域﹑政治背景﹑民俗文化進行注釋注解,如第4章的小說人語“中國這邊稱之為塔塔爾,俄羅斯那邊的俄語表述則被中國人譯為韃靼,首府是喀山,它與莫斯科﹑彼得堡并列為俄羅斯三座文化歷史名城。”[4](P41)三是對當時與當下態度與立場的再說明,如第43章的小說人語“這篇小說很注意它的時間與空間坐標下的‘政治正確’性……但寫來寫去它批判的是極左……形‘左’是真相,畢竟有這么一次批‘左’了……恰恰是從‘社教:二十三條’中,提出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命題。正是‘社教’運動,還沒有來得及收尾,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進入了更加強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4](P543)四是因重讀舊作而喚起的對于舊事故人的懷念,如第14章小說人語“在伊犁,小說人有一個還不算深交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約爾達西’……然后他趕了幾十年的馬車……他已經不在了,愿他的在天之靈安息”[4](P163)。五是對文本作小說學的說明,如第32章小說人語中對于反面人物的小說學解釋,第40章小說人語中對“小小章洋”——“小說學要求攪屎棍的出現”做出評點,第41章小說人語中對“章洋的執拗與自我毀滅是重要的小說-戲劇元素”作出簡議說明等。六是散論隨感的精美小品,如第18章小說人語對于“善”的精妙短議,以及第42章小說人語對悲哀,對愛情的精美隨感。
與小說正文相比,“小說人語”少了當年那風起云涌的狂熱與濃烈,多了歲月沉淀后的自然靜美,但是“小說人語”仍然有著與小說正文一樣的真摯與赤誠,那游走鮮活的情感底色仍舊是生活世界中永不消逝的光明和對美好的永不放棄的肯定。特別值得一說的是第六類“小說人語”——散論隨感的精美小品,這一類小說人語由小說文本所觸及而生,而又不局限于小說文本,而是以字字珠璣的語言和深刻睿智的視角,書寫出更為廣闊的價值觀與更為動人的生活哲理。“重壓下的﹑深度凍結的悲哀,反而是恍若沒有的,可以被忽略的,可以是‘卻道天涼好個秋’的。只有當重壓開始減弱﹑當冰凍遭遇暖流﹑當你獲得了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希望的消息以后,那時的眼淚才會釋放出你刻骨的悲哀來。我們畢竟有理由相信愛。有理由歌唱愛情。有理由擺脫那些骯臟的﹑變異的﹑虛假的﹑裝腔作勢的命名,回到愛情的最本真最純潔的層面。”[4](P531)此類“小說人語”精美而自然,樸實而優雅,流露著難能可貴的平靜與克制。四十年前的青年王蒙在人生低谷,夢想被放逐的境遇里,以其不可磨滅的熱忱和信仰將西域伊犁的生活以及真實的心靈感受,用文字真誠地記錄下來,四十年后,那早已歷經沉浮,踏遍坎坷,靜水流深的老年王蒙重拾舊稿,重拾那真實存在過的人生年華,以“小說人語”的方式,進行跨越時空的自我靈魂對語,最是那熱淚盈眶的,仍舊是不可磨滅的青春與不可摧毀的生活。
三、空白處依然活著的文學:王蒙的脈絡與文學史的脈絡
王蒙在文學史上的痕跡,或者說王蒙的創作痕跡,我們所熟知的大概是兩個時期:一個是“十七年”初登文壇的王蒙,這個時期的王蒙貢獻了《青春萬歲》《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等青春熱情的現實主義作品;二是“新時期”的王蒙,1978年王蒙以《向春暉》《最寶貴的》等現實主義風格作品回歸文壇,并在1979年以《春之聲》 《布禮》《蝴蝶》《風箏飄帶》等現代實驗性作品在1980年代初的文壇引起震動,1986年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的發表標志著王蒙小說創作的真正轉變與創作達到的更深廣的高峰,進入1990年代后王蒙以“季節”系列小說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進行探索。那么20世紀60至70年代這20年間的王蒙則是一個“空白”,用王蒙的話來說,就好像是吃魚時魚頭魚尾都已經做出來了,卻沒有了“中段”,而《這邊風景》正是王蒙對于自己最豐腴的“三十歲﹑三十五歲﹑四十歲”那段黃金年華的重拾,是對自己20年創作空白期“中段”式的填補。因此《這邊風景》的再出版,再發現對于認識一個“完整”的王蒙有著不可磨滅的重要意義。
王蒙如此評價作為自己創作“中段”的《這邊風景》:“我覺得我在40歲前后寫的這本書,比起我的《活動變人形》來說它更富有生活的豐富性和更多的細節,有更多的描寫和更多的具體形象,與我寫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相比,這本書是完全新鮮的生活經驗,比如邊疆生活﹑少數民族的生活等。”[5]應該說,這是符合實際的。
單從小說語言的角度看,《這邊風景》對邊疆少數民族生活和風景的表現就具有濃郁的民族與地域特色。小說表現的邊疆伊犁的風景,是維吾爾族﹑漢族﹑塔塔爾族﹑回族﹑俄羅斯族等多民族雜居的風景,因此相較于《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青春萬歲》而言,小說中有大量的詞匯直接來自于少數民族語言,王蒙也為此做足了注釋,不僅為“泡克”“卡孜”“克孜”“汗”“阿洪”“酷”“貝薇”“匹什卡克”“卡什圖什”“哎鳩雞哞鳩雞”等詞匯作了注釋,而且為與這詞匯語匯相關的民俗,宗教背景,政治背景等都做了大量具體的說明。此外,為了讓讀者更多地了解維吾爾族人的語言邏輯﹑文化心理和情感表達方式,王蒙《這邊風景》中的許多對話都取自維吾爾語的直譯,比如“再見,泰外庫哥,謝謝您借給我的電筒。再見,伊力哈穆哥,時間到來的時候,請您到我們那兒去玩。”[4](P487)要說起這地道的民族語言特色,第45章再娜甫為安慰雪林姑麗痛罵庫瓦汗部分可謂是個典型,“庫瓦汗!你這個卑鄙的說謊者!下流的誣陷旁人的人!你怎么敢欺侮雪林姑麗,欺侮這個最老實最善良的人。你的舌頭好像蝎子的尾巴,你的牙齒好像魔鬼的鋸子。我,再娜甫今天來找你,就是要割掉你那毒汁四濺的舌頭,拔掉你那鋸人身腰的三十三顆牙齒!”[4](P564)原汁原味的語言,像是用少數民族語言寫成的異域生活畫卷,濃郁的民族地域特色,為讀者吹來一股強勁的奶茶味兒,西域風。
但是《這邊風景》與1950年代的王蒙仍是血脈相連的,這部作品實際上更接近于“十七年”的王蒙,在審美上與《青春萬歲》《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很靠近,熱愛人民,熱愛勞動,滿懷激情與信念,在敘述過程中總少不了發自肺腑的抒情。同時《這邊風景》與1980年代的王蒙同樣是骨肉相連的,這部作品是王蒙16年新疆生涯的真誠紀錄,而16年的新疆生活正是王蒙1980年代創作的重要精神源頭。這一段沉入最底層的生活經歷既是苦難的又是幸運的,正是對大地和人民的最親密接觸孕育了王蒙的的平民思想與歷史意識,孕育了王蒙對苦難的寬宥與擔當,孕育了王蒙的自我反思與批判意識,使新疆伊犁成為王蒙不斷重返的精神故鄉。因此《這邊風景》已經不僅僅是塵封的青春與塵封的當年王蒙,更重要的是《這邊風景》是王蒙思想史,創作史上的重要階段,是不可或缺的人生“中段”。可以說在那被遺忘的20世紀60﹑70年代,空白處,青春真實存在,文學依然活著。
這種創作流脈上的連續性,同樣可以獲得一個語言視角上的闡釋。王蒙是20世紀80年代最重要的幽默作家之一,他的幽默可以戲謔,可以機智,可以娛樂,也可以自嘲,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幽默是一種深厚的智慧。這種幽默因子在《這邊風景》的早已萌生,甚至成為了一種“王蒙式幽默”風格——幽默﹑精準。如小說中關于尼牙孜庫瓦汗夫婦的描寫。
其一:“對于庫瓦汗這樣的女人,一遇到吵架她就興奮,進入類似發情與競技的狀態,她的口才和體力都活躍起來了,到了這種境界以后,爭吵什么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爭吵本身,一定要吵下去,要去獲得一種‘為藝術而藝術’的滿足。”[4](P201)
其二:“他那樣努力地﹑堅持無懈地笑著,他的笑容遍布了他的五官和全身,即使動物會笑,那么,貓兒見到了老鼠或者雄雞見了母雞也不會笑得這樣好﹑這樣感人。這是一種發射性的和富有黏附力的笑,他的頭臉微微前探,似乎要把笑容發射出去,用笑容去擁抱對方,用笑容把自己黏附在對方身上。”[4](P503-504)
這兩段描寫有兩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精準,以及由這精準所帶來的令人忍俊的幽默效果。此類睿智的幽默在這部寫于1970年代的小說中俯拾皆是,而此類幽默之所以酣暢淋漓,恰恰是由于他語言運用的精準,每一個詞,每一個比喻,每一種敘述,每一種描寫都以最簡潔明了的方式處在最恰當的位置,讓語言的力道剛剛好,而且更為可貴的是這樣的精準幽默的語言并不來自于苦心經營的精雕刻畫,而是一如既往的質感,自然。幽默精準的語言依舊是來自于生活,來自于對生活的切身參與以及對這切身參與的生活的切身洞察。
從文學史的角度看,《這邊風景》的啟示性意義有兩點。第一,是對“四清”運動文學題材空白的填補。在當代文學題材中,反映文革的作品從來都不缺少,不管是敘寫文革時代中人性的幻滅與生存的荒謬,還是暢言知青時代血色浪漫的無悔青春,不管是反思文革中中國幾千年的陋病積習,還是懷念狂熱時代那狂飆突進式的革命熱忱,文革題材是一個作品輩出也是佳作輩出的重要文學題材,但是文革前夕的政治運動,像“四清”運動或者說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樣的題材卻鮮有作家作品去表現,而實際上文革前夕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政治運動階級斗爭卻是實實在在存在過的,那日日斗,月月斗,“民族問題說到底是階級斗爭問題”的時代從來都不是歷史的空白,而且如果沒有文革前夕一浪高過一浪的階級斗爭做準備,更加徹底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會突然到來。因此對文革前夕“四清”運動題材的文學敘寫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對于歷史的文學性記憶填補,也為同時期的文革文學提供一個對照文本,更為后來的文革題材寫作提供一個相為呼應的歷史語境。《這邊風景》為20世紀60﹑70年代打開了一扇窗,從這扇窗里,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20世紀60﹑70年代鮮活的生活,也看到了那時期的文學創作和文學創作語境,可以說,在那“空白”的20世紀60﹑70年代,文學依然活著。
第二,《這邊風景》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重要發現。基于前兩點,可以說《這邊風景》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重要發現,發現了文學史中不可遺漏的當年王蒙,也發現了中國歷史中不可遺漏的20世紀60﹑70年代,更發現了文革文學中不可遺漏的另類寫作風景。《這邊風景》可以算作是文革期間“潛在寫作”的另一種形式,是特殊的歷史時期所誕生的一部重要的具有文學意義和文學史意義的優秀作品。什么樣的作品應當寫入文學史?大約有兩種,第一種,高含金量的作品,這樣的作品往往以深刻的思想和豐沛的個人體驗,新穎的藝術形式探索與對現代漢語的高超駕馭力而具有穿透時空的精神感染力。第二種,坐標式的作品,一個時代﹑一個領域﹑一個題材﹑一個作家的坐標式作品。而《這邊風景》正是二者兼有的作品,《這邊風景》“雖然不無從眾的嘶喊”,但作品的內核仍然是不可摧毀的生活與青春,不可磨滅的人性的真與美,仍然有著跨越時空的情感﹑精神穿透力,而且《這邊風景》是王蒙的重要坐標,是認識新疆與了解民族民俗文化的范本,是對“文革文學”的豐富和生動,也是文革寫作中不可或缺的優秀代表。
[1] 王蒙.前言·這邊風景[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3.
[2] 王蒙.在那些空白處文學依然活著[N](記者劉穎訪談).天津日報,2013-07-05.
[3] 王蒙.小說的世界[A].王蒙說[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4] 王蒙.這邊風景[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3.
[5] 王蒙.《這邊風景》就是我的“中段”[N](記者劉颋﹑行超訪談).文藝報,2013-05-17.
責任編輯:馮濟平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Landscape Here by Wang Meng
WANG Jin-sheng DUAN Xiao-lin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China )
The Landscape Here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both for Wang Meng and for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Depicting his 16 years' career in Xinjiang, it is full of the author's enthusiasm and sincerity in the prime of his life. With rich classical details, the novel shows us the borderland people's life and emo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 Application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words of the novelist extends the artistic expressive force, forming a soul dialogue which can transcend space and time.
The Landscape Here; detail;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words of the novelist;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207
A
1005-7110(2014)01-0100-07
2013-05-15
王金勝(1972-),男,山東臨朐人,青島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段曉琳(1989-),女,山東萊蕪人,青島大學文學院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