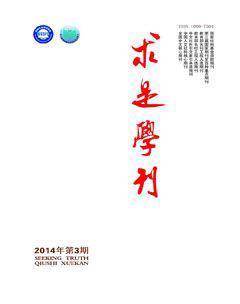俄羅斯公民請愿制度述評
哈書菊++李洪波
摘 要:請愿權是現代法治國家的人們對于國家政治設施或其本身權益,向民意機關或行政機關陳述其愿望或者意見,請求國家機關作為或不作為之權利。請愿制度是當今很多國家施行的權利保障制度,是各國制定訴訟程序性規則的基礎性制度。俄羅斯的請愿(обращение)制度立足于俄羅斯聯邦憲法,具有憲法性基本權利的請愿權是俄羅斯訴權的基礎,包括建議權、聲明權和申訴權。俄羅斯的權利多元救濟制度中的請愿權制度,與世界各國權利救濟發展趨勢大體一致,可以說基本是成功的。這對處于改革階段的中國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俄羅斯;基本權利;請愿制度;請愿權
作者簡介:哈書菊,女,法學博士,黑龍江大學法學院教授,黑龍江大學法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從事憲法學與行政法學、訴訟法學研究;李洪波,男,黑龍江大學社會科學處副研究員,從事民法學研究。
基金項目: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人本視域中的民事訴權保障研究”,項目編號:10C036;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發回重審制度調研報告”,項目編號:12B076;黑龍江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項目“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交叉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2522210
中圖分類號:D9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4)02-0001-06
請愿制度是現代法治國家普遍采用的保障權利的制度。2006年俄羅斯聯邦頒布的《俄羅斯審理公民請愿的規則》中詳細地規定了俄羅斯公民的請愿權制度。該規則為俄羅斯公民有效地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提供了制度性基礎。
一、俄羅斯請愿制度的歷史溯源
溯其本源,請愿制度源于1215年英國《自由大憲章》有關請愿權1的規定。所謂請愿權,是指“人們對于國家政治設施或其本身權益,向民意機關或行政機關陳述其愿望或者意見,希求國家機關作為或不作為之權利”[1](P266)。請愿權的權利主體一般為非特定性主體,可能是與請愿事項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利益人”,也可能是與請愿事項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非利益人”;請愿涉及的事項非常廣泛,大到國家政策、法律法規、人權問題、公共福利,小到與請愿人自身利益相關的事項;請愿的主管機關可以是立法機關、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或者其他特設機關。因此,可以說,具有憲法性基本權利的請愿權是俄羅斯公民訴權的基礎,是為實現“第一權利”的一種程序性權利。
二戰后,許多國家的憲法都對“請愿權”作了明確的規定。據統計,到1976年,在有效的142部憲法中有69部規定了請愿權。[2](P51)20世紀80年代以來,又有許多國家的憲法中確定了公民的請愿權,如1987年韓國憲法第26條、1991年羅馬尼亞憲法第47條、1991年德國憲法修正案等。請愿權除了被載入各國的憲法,還得到許多國際人權公約的確認。如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1965年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和1966年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任擇議定書》。另外,1950年的《歐洲人權公約》、1969年的《美洲人權公約》和1981年的《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等區域性國際公約中也對請愿制度進行了明確規定。
俄羅斯公民的請愿權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解體前的蘇聯時期。1968年蘇維埃聯邦共和國頒布了《審理公民建議、聲明和申訴的規則》1。盡管《審理公民建議、聲明和申訴的規則》中沒有直接使用 “請愿權”一詞,但該規則中的“建議權”、“聲明權”、“申訴權”等內容的實質可以說就是請愿權。該規則先后經過1980年和1988年兩次修改、補充,但這兩次修改和補充都只是在具體操作內容上進行改動,實質內容并沒有被觸及。蘇聯時期三個版本的《審理公民建議、聲明和申訴的規則》都規定:“公民向國家和社會機關提出建議、聲明和申訴,是實現和保護個人權利、鞏固國家機關和居民聯系的重要方式,是解決當前和將來國家的、經濟的和社會文化建設問題的最重要的信息源泉。公民請愿有助于鞏固對國家活動和社會組織的監督檢查,是勞動者同懶散的、官僚主義的和其他工作中的不足作斗爭而參加管理的形式之一。”2這就意味著,俄羅斯公民的請愿制度,實質是指俄羅斯公民心中有所期望,而向有可能實現這一期望的國家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和公職人員提出請求和表達意愿的制度。不難看出,此時俄羅斯的請愿制度以“權力救濟”為其基本功能,強調的是對于“權力”的維護,忽視對“權利”的救濟。
“俄羅斯聯邦憲法在俄羅斯全境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直接作用并適用。俄羅斯聯邦所通過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不得同俄羅斯聯邦憲法相抵觸。”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以憲法規范的形式確定了“國家保護人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每個人都有權以法律未予禁止的一切方式維護其權利和自由”。其中,包括公民的請愿權。“俄羅斯公民有權親自請愿,以及向國家機關、地方自治機關提交個人的和集體的請求。”可以說,俄羅斯公民的請愿權是一項公民基本權利,俄羅斯是在憲法規范的層面對請愿權予以確認的。俄羅斯公民的請愿權也是一項程序性基本權利,即當俄羅斯公民的其他法定權利受到侵害時,俄羅斯公民有權要求國家有關機關給予救濟,以使其他法定權利能夠得以實現,獲得確實保障的權利。俄羅斯“保障對每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提供司法保護”;俄羅斯公民“對國家權力機關、地方自治機關、社會團體和公職人員的決定和行為(或不作為),可以向法院提出訴訟”;“每個人都有權根據俄羅斯聯邦的國際條約訴諸維護人權與自由的國際組織,如果現有受法律保護的所有國內手段都已用盡的話”3。盡管在1993年,俄羅斯“人權”憲政原則就已經確立,但直到2006年《俄羅斯審理公民請愿的規則》的出臺,才在法律層面宣布1968年、1980年、1988年的《審理公民建議、聲明和申訴的規則》作廢,將立法宗旨明確為:“是調整有關俄羅斯公民為實現俄羅斯憲法所保障的對國家機關、地方自治機關的請愿權相關的法律關系,并且規定了審理公民對國家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和公職人員的請求的程序規則。”這標志著請愿制度從“權力救濟”模式向“權利救濟”模式的轉換。
二、俄羅斯公民請愿權實現的基本方式
俄羅斯公民的請愿權主要是通過行使建議權、聲明權和申訴權等方式來實現的。一般認為,請愿權主要是公民向國家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和公職人員提出書面的建議、聲明或者申訴的權利,同時,也包括公民以口頭的方式向國家機關、地方自治機關提出請求的權利。俄羅斯公民請愿權實現的基本方式是建議、聲明和申訴等。其中,“建議”是指為了完善法律和其他規范性文件、規制國家機關和地方自治機關的活動、發展社會關系、改善社會經濟和其他范疇的國家和社會活動而由公民提出的意見;“聲明”是指俄羅斯公民為了實現憲法性權利與自由以及為了保障他人的憲法性權利與自由而提出的請求,或者報告有關行為違反法律和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國家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和公職人員在工作中的不足,或者是對上述機關和公職人員提出批評;“申訴”是指公民為恢復或者保護受侵犯的權利、自由與法定利益,或者是其他人的合法權利、自由與法定利益而提出的請求。
按照俄羅斯的立法解釋,俄羅斯公民的建議權與中國公民的建議權的權利內容基本一致,都是指為了更好地改善社會關系,完善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作而提出的建設性意見的權利。俄羅斯公民的申訴權與中國公民的申訴權的權利內容也是基本一致的,都是指公民的合法權益受到國家機關或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非法或者不當行為侵害時而向有關機關提出請求救濟的權利。相比之下,俄羅斯公民的聲明權是一項具有廣泛內容的權利,涵蓋了中國憲法中所規定的公民的批評權、控告權和檢舉權。1《俄羅斯審理公民請愿的規則》用三個詞界定了俄羅斯公民的聲明權:請求(просьба)、報告(сообщение)和批評(критика)。從前面的說明不難看出,這三個詞所表達的語義與中國公民所享有的批評權、控告權、檢舉權的內容基本是相通的。
從權利保障的視角看,俄羅斯公民的請愿權具有雙重性質:監督公權力和保障私權利。其中,建議權主要是監督公權力性質的權利,不屬于直接的權利救濟方式,但對形成抽象立法行為,促成事前救濟有積極意義。聲明權也基本屬于監督公權力性質的權利,沒有直接權利救濟的性質,但它可以促成事前救濟,并在涉及個人權利損害的條件下可以轉化為事后救濟的權利。申訴權是與公民權利損害聯系在一起的,所以是權利獲得直接救濟的一項權利,是權利保障不可或缺的憲法性基本權利。因此,俄羅斯公民請愿權的行使,既是對國家權力行使進行的監督,也是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尤其是對受到損害的權利的補救。
根據請愿內容是否帶有爭議性質,是否有損害的存在,俄羅斯公民的請愿權主要是通過非司法性和司法性兩種程序實現的。公民提出的不具有爭議性質的請愿是通過非司法性程序實現的,主要是指公民就有關國家和社會發展問題向有關國家機關(主要是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提出的書面建議或者聲明,因不具有權利爭議性質,適用一般意義的非司法性程序。公民提出的具有爭議性質的請愿,一般需要通過司法性程序解決。這里的司法性程序又可以分為準司法性程序和司法性程序。前者諸如俄羅斯行政重新審查制度,類似于中國的行政復議制度,是指俄羅斯公民有權對公權力機關,主要是行政機關實施了侵犯公民的權利與自由的行為(決定)的時候,按照權力隸屬關系向實施了侵權行為的機關的上級機關提出申訴;后者如俄羅斯行政訴訟制度,是俄羅斯公民在國家機關、地方自治機關、企業和社會團體、公職人員等實施了侵犯公民的權利與自由的行為(決定)的時候,有權向法院提起控告的制度。上述請愿行為既可以是集體性行為,也可以是個體性行為。
俄羅斯公民的請愿權,除了適用上述非司法性和司法性程序外,還可以通過一個特殊的主體,即人權全權代表來實現。人權全權代表制度在俄羅斯的確立主要是為了落實俄羅斯憲法中作出的國家有義務維護人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的承諾。俄羅斯人權代表制度是憲法或法律預先規定的,由專門的公共服務人員獨立負責,主要是受理有關俄羅斯公民對國家機關實施的侵害其憲法性權利與自由的控訴。俄羅斯人權全權代表在被授權后,有權進行調查,提出建議更正行為或提供建議報告。[3]盡管俄羅斯《憲法》第103條只是很籠統地規定國家杜馬有設立人權全權代表的權力,但畢竟是在憲法規范的層面確立了俄羅斯人權全權代表的合憲地位。1997年2月的《俄羅斯聯邦人權全權代表法》將憲法中的抽象性規范予以具體化。根據《俄羅斯聯邦人權全權代表法》的規定,在申訴人窮盡了司法救濟和行政救濟以后,仍認為沒有得到救濟的前提下,人權問題全權代表有權受理公民對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的決定或行為提出的申訴。
俄羅斯憲法賦予公民的請愿權,既包括實體權利內容,也包括程序權利內容。救濟程序的啟動必須借助于公民程序性請愿權的行使。同時,公民實體性請求權需要在救濟程序中實現。
為貫徹憲法“人權”保障原則,《俄羅斯審理公民請愿的規則》專門對公民提出請求的安全保障作了規定:當俄羅斯公民為批評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的違法或者不當的職權行為時,或者為了保護自己與他人的合法權利與自由時而向國家機關、地方自治機關以及公職人員提出請求時,禁止對他們進行打擊報復。沒有本人的同意,審理請求時不允許泄露請求的內容信息以及涉及公民私人生活的信息。這些有關實現請求權的安全性保障規范,是俄羅斯國家為實現人權保障而設置的眾多安全閥中的一個。另外,俄羅斯《行政違法法典》在第30章中有關于審理行政違法案件的具體程序規則,既包括有關行政重新審查制度,也包括行政訴訟制度,還包括檢察監督制度。上述兩部法典不但規范了俄羅斯公民實現請愿權的程序規則,除訴訟途徑外,還規定多種救濟途徑。
與該法相銜接,能夠整合為請愿制度的法律還有《俄羅斯聯邦仲裁程序法典》和《俄羅斯聯邦民事訴訟法》等。《俄羅斯聯邦仲裁程序法典》專辟一編規定了“行政法律關系和其他公法法律關系在第一審仲裁法院的訴訟程序”,主要針對“要求撤銷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案件的審理”、“對國家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其他機關、公職人員的非規范性法律文件、決定、行為(不行為)提出爭議的案件的審理”以及“行政違法案件的審理”作了較為具體的規定。《俄羅斯聯邦民事訴訟法典》的第三部分專門就“公法關系案件的審理程序”作了特別的規定,指出俄羅斯普通法院有權審理下列公法關系案件:審理有關公民、組織和檢察官對規范性法律的全部或者部分內容的異議的申請,并且聯邦法律沒有將這些申請列入其他法院的審理范圍;審理對國家權力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公務人員、國家和自治市的職員作出的決定以及作為(不作為)行為的異議的申請;審理保障選舉權和俄羅斯聯邦公民參加全民投票權案件的申請;審理其他依法應由法院審理的公法關系案件。1
比較而言,俄羅斯《對侵犯公民權利與自由的行為和決定向法院提出控告法》主要是從憲法性規范的角度規定了俄羅斯公民有向法院提出控告的權利。《俄羅斯審理公民請愿的規則》和《行政違法法典》還或多或少地有關于行政訴訟制度的規范。尤其是《行政違法法典》明確指出:公民對于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的行為提起的申訴,必要時法院可以按照民事訴訟規則進行審理。到目前為止,俄羅斯還沒有獨立的行政訴訟制度,其行政訴訟主要體現在民事訴訟制度中。俄羅斯《行政違法法典》的規定契合了俄羅斯一些民事訴訟法學專家的想法。俄羅斯民事訴訟法學專家在分析民事訴訟程序和行政訴訟程序的基本制度以及兩個程序原則的相同點時,普遍不贊成對行政司法程序進行專門的立法。有些學者還進一步提議,制定統一模式的民事訴訟法典,按照他們的設想,民事訴訟法典中不僅要包括調整公法關系案件的規范,也要包括調整與企業家活動相關聯的民事或者行政案件的特別程序的規范。[4]當然,與行政訴訟法學家呼吁建立獨立的行政司法程序力量相比,民事訴訟法學家的主張并不是占主流的觀點。更何況,兩種救濟無論是合并也好,分開也好,并不影響俄羅斯公民訴權的正當行使。
三、俄羅斯請愿制度中的法治精神對中國的啟示
俄羅斯請愿制度的設立是對“人、人的權利與自由是最高價值”的憲政精神的具體落實。人權保障理念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首先體現在資產階級國家憲法之中的。如今人權保障理念在世界各國普遍被提升為憲法原則。人權保障理念在俄羅斯憲法中得以確立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勞動者權利(права трудящихся)—‘公民權利(права граждан)—‘人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 (права и свободы человека и гражданина)。”[5](P22)1991年11月22日俄羅斯通過了《人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宣言》,宣布接受國際法上公認的人權原則和準則。1993年俄羅斯以全民公決的形式通過的現行憲法明確規定“人、人的權利與自由是最高價值”,以處于國家最高法律位階的憲法規范的形式將人、人的權利與自由放在了所有權利體系的“最高價值”地位,確立了憲法的人權原則。俄羅斯的人權保障制度發生了歷史性的根本轉變。為落實憲法中的人權保障原則,俄羅斯還陸續制定了一系列具體法律法規,如《俄羅斯聯邦全民公決法》、《最低勞動工資法》、《俄羅斯聯邦社會服務基礎法》、《職業聯合會及其權利與生活保障法》、《俄羅斯聯邦立法規則》、《勞動保護法》、《公民健康保護法》、《對侵犯公民的權利與自由的行為和決定向法院提起控告法》以及其他有關俄羅斯公民行使請愿權的規則。這些具體法律法規從不同方面把憲法中的人權保障原則轉化為具體的法律權利。與此同時,俄羅斯還與他國簽訂了一系列有關人權保障的國際條約。可以說,俄羅斯在反思和總結歷部憲法有關人權保障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更加突出和強調人權原則的憲法意義,為俄羅斯指明了法治建設的前進方向。人權保障也是中國未來法治建設的價值和目標,它將指引著中國法治建設的發展,同時,法治建設又將為人權保障創造條件并提供保證。
俄羅斯請愿制度是實現俄羅斯國家在憲法中所作的“承認、遵循和捍衛人與公民的權利和自由是國家的義務”的承諾的有效制度。首先,在現代法治社會國家,國家權力的行使者有義務向公眾社會不斷提供合理的、有效的公共政策及必要的公共服務,不斷促進社會公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類社會文明的可持續發展。賦予公民請愿權可以使國家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及時了解民眾意見,吸收民眾的智慧,有助于國家公共政策的理性化。其次,權力不被限制即容易被濫用,為了克服公共權力的濫用,就有必要從法律制度層面為社會民眾提供能直接參與國家與社會的管理的保障。請愿正是縮短公共權力與民意的距離,是社會民眾直接參與國家與社會的管理,與公共權力進行直接溝通與對話的一種重要方式。請愿制度的設立可以有效地防止權力的濫用。限制濫用權力,保障正當權利的需求正是當今世界各國憲政精神的要旨所在。另外,請愿制度的設立可以擴大民主參與程度,培養公民的公共意識和民主習慣。賦予公民請愿權能夠喚起人們對于國家事務、社會事務的關注,從而激發其民主參政的熱情,推動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有助于推動民主法治國家建設的發展步伐。例如,2003年“孫志剛收容致死案”引發的“三博士”與“五學者”的建議就是中國典型的請愿案。1顯然,設立請愿制度有助于社會民眾及時將不滿情緒宣泄出來,避免社會矛盾的聚集激化,進而可以起到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利益主體出現了多元化格局,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利益不均衡,導致新型社會矛盾不斷出現。當國家沒有能力及時解決這些社會矛盾的時候,就應當有義務為社會民眾通過制度層面宣泄其不滿情緒提供暢通的渠道。“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顯示,社會穩定來源于人們對統治權威的服從和尊敬,而這種服從和尊敬的前提則是社會合意與社會共識的達成。作為民眾表達意見、直陳愿望的一種重要方式,請愿能夠在社會大眾與政治當局之間架設起交流與協商的平臺”,“從這個意義上說,請愿權無疑起到了“減震閥”、“過濾器”的作用”。[6]
目前,我國由于沒有在憲法規范的層面明確規定請愿制度,缺乏具體法律的規范,請愿制度存在著許多沒能理順的法律問題,如在機構設置方面,存在受理請愿的各機構職責不分、政出多門,受理請愿的機構往往意識不足、功能錯位等問題。綜上,在現代法治社會國家,請愿權具有極為重要的憲政價值,已經被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所認可,并通過憲法規范和國際法規范的形式予以確立。特別是二戰結束后,各國權利救濟制度的發展趨勢,明顯地表現出救濟方式趨向多元化、救濟范圍趨向擴大化、救濟程序趨向法典化、救濟規則和方式趨向國際化的特點。俄羅斯建構的請愿權制度,是與各國權利救濟發展趨勢大體一致的,可以說基本是成功的。這對于同樣處于改革階段的中國來說,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俄羅斯所建構的權利多元救濟制度中,憲法司法審查制度、人權全權代表制度、檢察官參與訴訟制度和國際司法救濟制度,也頗有借鑒意義。
參 考 文 獻
[1] 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論》,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04.
[2] 亨利·范·馬爾賽文,格爾·范·德·唐:《成文憲法的比較研究》,陳云生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3] 孫海濤:《俄羅斯公民權憲法保障制度研究》,黑龍江大學法學院2004屆研究生學位論文,中國優秀碩博論文網.
[4] Б·Н·Лапин,Н·А·Ченина:?О проблемах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суд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странах СНГ?,Москва,Праводение,2002,ст4.
[5] 哈書菊:《人權視域中的俄羅斯行政救濟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6] 楊海坤,章志遠:《公民請愿權基本問題研究》,載《現代法學》2004年第4期.
[責任編輯 李宏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