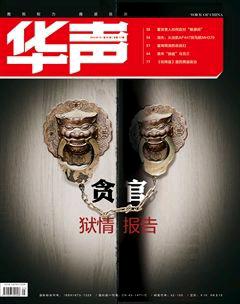龍泉寺方丈與官員在一起時聊什么
孔令鈺

2006年杭州舉辦“首屆世界佛教論壇”,學(xué)誠作為中國佛教協(xié)會副會長,司職機場內(nèi)的迎賓接待,因為時間沖突,他沒能及時接到韓國智冠長老以及香港鳳凰衛(wèi)視董事局主席劉長樂。學(xué)誠特意緊追二人,追到出關(guān)的地方,一定要送上問候。同去的弟子,一邊擺弄著偶爾不好使的相機,一邊拍下這些瞬間。
他非常了解世俗的形制規(guī)格。中國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zhàn)2009年訪問法門寺時,學(xué)誠以法門寺方丈身份接待。當(dāng)天,他剛剛從外地趕回西安,收到寺里的短信:連戰(zhàn)先生下午15:00到,停留20~30分鐘,請問師傅,按什么標(biāo)準(zhǔn)接待?送什么禮物?
學(xué)誠回復(fù):可與市里領(lǐng)導(dǎo)商量。建議按上次接待泰國總理標(biāo)準(zhǔn)。
他每天會收發(fā)許多短信,所以特意挑了一款內(nèi)存大、可將短信導(dǎo)入電腦的手機。不到三個月,短信存了兩千多條。
“學(xué)誠法師啊,你的事情可是驚動了黨中央啊!”
在龍泉寺,有時候凌晨三點多,弟子都會聽到短信提示音,那一定是學(xué)誠發(fā)來的短信。光掃一眼屏幕右邊的滾動條,弟子都能估計出信息有幾百字的篇幅。內(nèi)容自然與學(xué)佛體會有關(guān)。
凌晨三點,學(xué)誠已經(jīng)起床,做過早課,用過早齋后,他會在六點半之前乘車離開鳳凰嶺,進(jìn)城到廣濟寺“上班”——中國佛教協(xié)會在那里辦公,傍晚再乘車返回。算起來,一天有三個小時在路上。
這種鐘擺式的“工作”節(jié)奏,將學(xué)誠的清修與世俗世界定期連接起來。平日,如果接送學(xué)誠“上下班”的汽車臨時出了岔子,他就坐公交車。一次在頤和園附近的公交車站等車時,一輛黃色QQ小車開過身去又倒了回來,司機問去哪兒,學(xué)誠說龍泉寺。就這樣司機將他免費送了回來。后來偶爾早上沒車接送,學(xué)誠會給這個QQ小車司機打電話請他來接,司機照樣會準(zhǔn)時到達(dá)。司機說,其實也不記得學(xué)誠在路上跟他聊過什么。
但趕到龍泉寺來與學(xué)誠聊天的人,就從來沒少過。官員們習(xí)慣夏天來寺里坐坐,學(xué)誠的博客記載得非常清晰:2012年6月~8月間,僅副部長以上官員就至少來過五位,大部分并不是來自宗教口。
前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說,學(xué)誠忙到兩個重要活動撞期的時候,不得不向中央請假。
2007年年底,十一世班禪在福建參觀學(xué)習(xí),安排了一場在廣化寺的活動,當(dāng)?shù)仡I(lǐng)導(dǎo)希望學(xué)誠回廣化寺迎接,不巧當(dāng)天他的日程早就定下:赴臺參加在中臺山禪寺舉辦的“海峽兩岸和平祈福法會”。法會是由葉小文以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xié)會會長的名義發(fā)起和參與的,為此葉小文專門為學(xué)誠向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請假。在香港機場轉(zhuǎn)機時,兩人見上了面,葉小文打趣說:“學(xué)誠法師啊,你的事情可是驚動了黨中央啊!”
“佛教里有尊菩薩叫不休息菩薩,×市長是不休息菩薩!”
弟子們很佩服學(xué)誠與官員打交道的能力。2009年冬天,學(xué)誠在故鄉(xiāng)福建參加完武夷山禪茶文化節(jié),離開主辦地南平時,時任市長專程到機場送行。
趁著候機時間,市長給學(xué)誠輪換泡了不少好茶,最后還拿出了自己珍藏的五十年金駿眉。到了登機過安檢,市長把學(xué)誠送上飛機時,一路小跑。
“功不可沒”,“了不起”,“不簡單”,“干勁十足”,“你在創(chuàng)造奇跡,精神感人”,在與官員聊天時,學(xué)誠不吝嗇用這些褒揚之詞,說到最后都是禪機。有個市長天天進(jìn)工地催進(jìn)度,一邊嚴(yán)厲督促下屬“趕緊把圖紙拿出來啊!”一邊對站在跟前的學(xué)誠圓場說:“學(xué)誠法師講究慈善,做善業(yè)的。我是做惡業(yè)的。”學(xué)誠接一句:廟里有很多佛像,既要慈眉善目,也要金剛怒目。“佛教里有尊菩薩叫不休息菩薩,×市長是不休息菩薩!”
2011年2月3日農(nóng)歷大年初一,游人在北京龍泉寺燃燈祈福,祝愿新年平安吉祥。
在另一個場合,學(xué)誠與在軍事院校教過八年哲學(xué)的將軍聊天。將軍告訴學(xué)誠“我覺得佛教也是無神論”,學(xué)誠答,“佛教不承認(rèn)有一個救世主,佛教講緣起法,不認(rèn)為有第一因。”談話間,將軍稱贊學(xué)誠比起前些年來,在待人接物各方面都有很大變化,過去太謹(jǐn)慎。學(xué)誠說,還做得不好。
現(xiàn)實生活中,學(xué)誠是一個很善于和陌生人找話題的人。和經(jīng)濟學(xué)家聊GDP,和詩人聊文學(xué),和媒體人聊麥克盧漢。一次在醫(yī)院住院,有位醫(yī)生常過來找學(xué)誠聊天,醫(yī)生是球迷,談話難免說到足球“竟然也和他談?wù)撈鹆俗闱颍桓焙茉谛械臉幼印!钡茏訂枌W(xué)誠怎么會了解足球,學(xué)誠半開玩笑,“就會這么幾句,接下來就要談佛法了。”
“都是佛菩薩給我們開光,我們怎么給佛菩薩開光?”
官員們喜歡學(xué)誠出現(xiàn)在自己管轄的地域。有的地方政府官員在網(wǎng)上看到學(xué)誠的信息,派人將其從北京請來,帶著他去看當(dāng)?shù)卣谂d辦的石窟工程,說他們那有寺廟、有佛像但是沒有主人、沒有方丈。旁人幫腔,“有寺沒僧就沒有靈魂啊!”
相似的話講了幾遍。學(xué)誠只是稱贊。
他也有不太樂意做的事,比如題詞。按照戒律,出家人不應(yīng)該花太多時間“學(xué)字求工”,但走出去,總有人想求他一幅題字。
2008年,在小浪底航空度假村,某科研院校院長想請學(xué)誠題詞,學(xué)誠推辭。院長助手已經(jīng)在身邊鋪開宣紙,學(xué)誠繼續(xù)推辭。學(xué)誠的朋友圓場說,法師需要構(gòu)思一下。
就這樣,等人都走了,學(xué)誠才問了一下身邊的弟子,寫什么好?然后繼續(xù)問:“我是否也要練一練字?”因為“常常被人逼著寫”。
弟子覺得師傅練字很有必要,而且建議寺里的同學(xué)們也練練,畢竟以后走出去也可能遇到這種情況。學(xué)誠未置可否,只是說:“同學(xué)們大多二乘習(xí)氣,見到這些人就發(fā)懵。”
學(xué)誠另一件不熱衷的事,正是一些寺廟相當(dāng)熱衷的事:開光。
他偶爾會參加一些開光儀式,但龍泉寺作為海淀區(qū)唯一一所政府批準(zhǔn)對外開放的佛教寺院,自2005年復(fù)建以來,除了在當(dāng)年舉辦了一場恢復(fù)宗教活動場所的頒證儀式,就從來沒有辦過一場跟開光有關(guān)的法會。
有人問為什么不辦一場,學(xué)誠說,都是佛菩薩給我們開光,我們怎么給佛菩薩開光?
對于知識分子,學(xué)誠的心思很復(fù)雜
如果以龍泉寺的日程安排稠密程度來看,學(xué)誠真正的興致所在還是講學(xué)。
2007年,北大國學(xué)社成員到龍泉寺拜訪學(xué)誠,想要聘請其為名譽顧問。學(xué)誠非常高興,談到和社員交流時,他說:“包括要請什么老師,在什么時間段講,我們廟里都可以配合。”緊接著他也謹(jǐn)慎地補充:“要有一個觀念,不一定讓所有人都信佛教。”
學(xué)誠曾在北大、人大、清華、中傳等學(xué)校開辦佛學(xué)講座,2010年應(yīng)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邀請,為其暑期課程班做講座,這是該院歷史上第一次邀請僧人走進(jìn)課堂。
每年,一撥撥的高校學(xué)生,甚至外國留學(xué)生組團前來參訪。
龍泉寺還與北京師范大學(xué)合作,建立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龍泉基地。在揭牌儀式上,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將目標(biāo)明確定為“三高”:培養(yǎng)高端國際型人才;進(jìn)行高端國際交流;組織開展高端研究及其成果的出版。
他也請各界人士到寺里來講學(xué)。北大教授樓宇烈在這里講《中國佛教史》,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說《世界宗教與文明》,國務(wù)院發(fā)展中心研究員胡振華談《中國與中亞國家交流歷史與現(xiàn)狀》,當(dāng)時81歲的法國天主教神父,也前來開了一場講座,名為《法國神父眼中的中國漢傳佛教》。
不過,對于知識分子,學(xué)誠的心思很復(fù)雜。原香港理工大學(xué)校長潘宗光教授來講完課后,學(xué)誠請他吃了碗面條,但又擔(dān)心他沒吃飽:“不如帶幾個餅在路上吃。”潘宗光推說不用。行將離開,一位弟子拿出了紅包送給潘宗光,學(xué)誠說,“路上買點茶!買點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