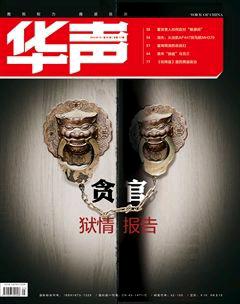綁架道義的“忠臣”

Q 夏老師您好!我們單位最近正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一些同志借機(jī)猛向領(lǐng)導(dǎo)“開炮”,貌似很令人快意。但事后我卻發(fā)現(xiàn),這些人提的意見,都含了個人目的。這個問題您如何看,意見又該如何提呢?(遵義:張一德)
A 小時候去看草臺班子唱戲,每每看到紅臉出場,用手將垂胸的長須一甩,虎眼一盯,鏗鏗鏘鏘唱到“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此時便全身熱血沸騰起來。待到紅臉在皇帝面前據(jù)理力爭,氣暈皇帝奪回正義時,心里爽得大聲叫好。隨著年齡增長,又多看了幾本閑書,我對一直屹立在心目中的紅臉,竟有些懷疑起來。
大家都知道魏征是位敢于“直諫”的大臣,李世民是位好領(lǐng)導(dǎo),對于魏征的冒犯頂撞并不計較,反而拿魏征當(dāng)銅鏡用,常常對著這面鏡子,像當(dāng)下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要求的一樣,“照鏡子,整衣冠”,效果還“征(真)不一樣”。李世民對魏征喜愛有加,魏征理所當(dāng)然地官越做越大。
在魏征與李世民之間,似乎魏征占據(jù)著更多的選擇權(quán)與主動權(quán)。魏征為何能這樣牛?細(xì)細(xì)想來,只因他占據(jù)了道義的制高點。
事實上,歷史上那些忠臣直士,包括魏征這樣的“良臣”,他們之所以敢于直諫甚至死諫,除了骨子里有股“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氣概外,他們內(nèi)心或多或少還有一種道德優(yōu)越感,甚至他們的忠直還常常綁架了道義。因為只要皇帝不聽他們直諫或是因此降罪他們,皇上就成了萬夫所指的昏君,而直諫之人卻因勇猛剛烈撈足名望。有了這樣的名望,在生前是一筆豐厚的政治資本,可憑此叱咤政壇;于死后則是一筆傳世千古的道德資本,倘若幸遇明君,還可憑此蔭澤子孫。因此,無論最終成為良臣還是忠臣,敢于犯上直諫者都會成為“贏家”。
也許正是這個原因,一些臣子甚至頂著“直諫”的高帽,常常有事無事尋些雞毛蒜皮的事來找皇帝的岔子。三國時魏人楊阜,因打馬超有功,被封為關(guān)內(nèi)候。到魏明帝時,他又升了。楊阜是那種敢“抗疏”之人,他常常上書,對魏明帝的政令提出不同意見。上面收到這些意見后,大多看完就扔到一邊了。楊阜為此很生氣,提出辭官,但沒被批準(zhǔn)。楊阜越發(fā)覺得自己還是有分量的,便進(jìn)一步雞蛋里挑骨頭。有次魏明帝穿著隨便了點,楊阜就不客氣地當(dāng)面指責(zé)他不成體統(tǒng),魏明帝非常郁悶地回去將衣服換了。過了不久,魏明帝最疼愛的女兒死了,他心痛萬分,提出要為女兒送葬。楊阜又跳起來反對,說先王和太后去世時您都沒去送葬,女兒死了反而去送葬,這哪里合禮數(shù)?楊阜說的雖然有道理,但他這種不體會對方心情的直諫,讓魏明帝很是感冒。魏明帝沒有聽楊阜的,將他涼在一邊,照樣去給女兒送葬了。楊阜被弄得灰頭土臉的,自此消沉了許久。
憑心而論,皇帝也是人,他們有著普通人一樣的七情六欲,同樣也需要普通人一樣的尊嚴(yán)。那些所謂的忠臣直士倘若真心提意見,犯得著非要當(dāng)面頂撞,讓皇帝下不了臺嗎?與楊阜同為曹魏時期的名臣陳群,他給主子提意見時就非常注意策略方法。《三國志· 魏書二十二· 陳群傳》記載說:“司空陳群則不然,其談?wù)摻K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shù)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群于是乎長者矣。”同樣是提意見,陳群悄悄地進(jìn)行,上疏數(shù)十道卻不讓任何人知道,這樣的人,自然更令人敬重。
逆拂龍鱗,舍命直諫,精神自然可貴,勇氣更是可嘉。撇開這些直士的個性與直諫策略暫且不論,倘若他們是挾裹道義而為,而在綁架的道義里又隱匿著私欲,這樣的忠臣,不要也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