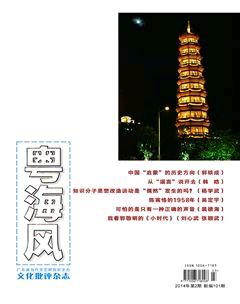中國左翼文學的復雜涵義
聶國心
一、問題的提出
新世紀以來,不少學者開始關注“中國左翼文學”的具體涵義。有的學者如程凱直接提出要尋找左翼文學的“歷史規定性”[1],劉海波對“左”、“左翼”、“左傾”等詞語作了詳細的“語詞梳理”[2];有的學者如王富仁、周景雷則間接觸及這個問題,他們認為中國左翼文學早就“被民族主義文學所消解”[3],“延安文學并非左翼文學”[4],這些命題的背后都涉及如何理解“中國左翼文學”的問題。
回顧“中國左翼文學”的研究,人們對這個概念的理解確實很不一致。
就這個概念的內涵來說,有兩種代表性的情況:一種是不少學者對“中國左翼文學”的概念未作認真的梳理,把一些不屬于或不完全屬于“左翼文學”的“現象”不加區別地當作“左翼文學”來研究。一種是許多學者看到了魯迅、茅盾與創造社、太陽社、周揚等人的矛盾,卻沒有人認真梳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和“左聯”的內在矛盾及其不同的文化訴求。他們更喜歡把“中國左翼文學”當作一個整體來研究。這樣做的好處是能夠“刪繁就簡”,突出“中國左翼文學”的歷史地位和影響。缺點是忽視甚至遮蔽了其內部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造成對它的“統一戰線”性質認識不足,進而影響到對它評價的真實性和科學性。
就這個概念的外延來說,也有兩種代表性的意見。概括說來,即是所謂廣狹二義。廣義的理解是把從1928年“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開始的“中國左翼文學”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的“新時期”。比如胡喬木1980年在《攜起手來,放聲歌唱,鼓舞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在紀念“左聯”成立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5]中就明確地說:“我們現在的文藝和文化仍然是左翼文藝和左翼文化”,“仍然是30年代的文藝和文化運動的繼續。”一些流行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著作,雖然在論述不同年代的文學時使用了諸如“工農兵文學”、“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新時期文學”等不同的詞語,也從“發展”的角度看到了它們之間的某些不同點,但在論述它們之間的聯系時,與胡喬木的觀點是基本一致的。
進入1990年代后,盡管有學者注意到了不同年代的“中國左翼文學”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仍有不少學者強調它們之間的聯系。比如程光煒就認為“中國的左翼文學運動”,是“在‘五四文學革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卻在許多重要方面改變了‘五四新文學的價值目標和思想選擇,而轉向中國革命具體實踐。我們現在稱之為50—70年代文學的‘當代文學,實際是此前左翼文學思潮在新的、特殊歷史語境中的一個發展。”[6]林偉民的《中國左翼文學思潮》,全面論述了“中國左翼文學思潮”的發生、發展、巔峰及衰落,其時間段是從1928年到1976年。他在后記中“感慨萬千”地說:他“無法直面左翼文學思潮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歷程”,“一場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學壯潮猶如‘飛流直瀉三千尺之氣勢涌進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峽谷,掀起震撼中華大地的千層浪,導演出中國二十世紀文學最悲壯、最慘淡的最后一幕。”[7]顯然,林偉民是把“無產階級文學壯潮”和“左翼文學思潮”看作是可以互換的概念在使用的。
狹義的理解則是把“中國左翼文學”限定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第二個十年內,或者限定在“中國現代文學”的范圍內。所謂“左翼十年”、“紅色的三十年代”等等說法,都是在表明“中國左翼文學”的特殊時段。雖然持“狹義的中國左翼文學”觀的學人有許多并不否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和“左聯”對后來的文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甚至也承認它的某些準則還左右了后來文學的走向,但很顯然,他們更多地看到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和“左聯”的獨特性,更多地看到了它與后代相類似的文學的不同之處。比如,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就把“中國左翼文學”限定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1937)”。艾曉明的《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其論述的時段是從1928年到1949年。按學界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時段的一般界定,艾曉明論述屬于“現代”時段內的“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應該在書名中加上“現代”的限定詞。她之所以沒有這樣做,可能一方面是她的專著重心在“探源”,自然更多地考察“源頭”的“左翼文學思潮”;另一方面則顯然隱含了她對“中國左翼文學思潮”特定內涵的獨特思考。她在書的“引言”中,簡要辨析了“馬克思主義文學”、“無產階級文學”、“左翼文學”等“在這一論題中要經常接觸到”的“幾個相互聯系的概念”。雖然她明確表示,她“所討論的左翼文學思潮”,“其時間的下限并不限于‘左聯的解散”,但卻嚴格限定在“中國現代文學這個歷史階段”內。只有在講“無產階級文學”時,她說到了“當代文學”中的“文革文學”。她說:“無產階級文學這個概念,指的既是在20世紀20、30年代這一特定歷史階段盛行的一種文學運動,更是一股具有20世紀時代特征的思想潮流。”它“時隱時現,起伏不斷,并不限于20世紀20、30年代。”但她也同樣明確地認定,“20世紀20、30年代的革命文學與60、70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然有著質的區別”[8]。
與艾曉明這種“猶疑”相類似,洪子誠一方面運用了籠統的左翼文學“一體化”的概念,另一方面又謹慎地指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學與1940年代的工農兵文藝和1949年后的社會主義文學有著不同的內涵。他不斷地對自己使用的“一體化”概念進行解釋。他說:“在談到50到70年代文學的時候,我和另一些人經常使用‘一體化的說法。這個說法不是意味著這個時期的文化、文學的單一性,事實上仍存在復雜的,多種文化成分、力量互相滲透、摩擦、調整、轉換、沖突的情況。”[9]直率地說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學已被后來的文學“改造”甚至“消解”的是王富仁、王得后等先生。王富仁說:“我們總是認為在十七年的時候取得勝利的是左翼文學的文學觀,從而認為左翼文學到最后成了一種主流文學。實際上不是。左翼文學很早就被解構了。”“到了40年代在解放區文藝里左翼文學就受到了一種壓制,除了少數人成了毛澤東思想的闡釋者。像蕭軍、丁玲、王實味,這些左翼文學的人物,直接受到了整改,不是說消滅,是改造,改造成適合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這就是說不是左翼文學改造了其他的文學,而是左翼文學被另種文學所改造,這是一種消解形式。在40年代的抗日戰爭當中,左翼文學被民族主義文學所消解。抗日了,一些左翼文學家已經不再堅持原來的左翼立場。”[10]王得后在“粗略地考察了魯迅文學和左翼文學的異同”后也得出結論:“左翼文學已經終結”[11]。
長期以來,“中國左翼文學”的涵義好像是不證自明的,即使學術著作也不做必要的界定。人們習慣于用極端化的政治思維來思考文學,也就容易簡單化地使用政治思想的理論框架來度量文學,以黨派或其他政治勢力的性質來確定其所倡導或贊賞的文學的性質。這樣做很容易出現“文不對題”的錯位,常常會誤把一些不屬于或不完全屬于“左翼文學”的“現象”當作“左翼文學”來研究,而把一些典型的“左翼文學”排除出自己的研究視野。比如,左翼政黨在其與執政的右翼政黨抗爭的時候倡導的文學,顯然具有“左翼文學”的性質。但對于一些并未與左翼政黨結成反抗的聯盟,甚至對左翼政黨的政綱進行過激烈批判的政治勢力創造的具有抗擊“右翼文學”作用的文學,是否應歸入“左翼文學”的研究范疇?在左翼政黨奪取了部分地區或全國的政權后,它所倡導的文學是否還一定具有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左翼”的性質?當“左翼文學”成為共和國唯一的文學時,是否還能稱作“左翼文學”?它與“國家文學”有著怎樣的關系?與新生的具有“批判性”和“反叛性”的“異端”文學又有著怎樣的關系?“左翼文學”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是單一的“批判性”,“革命性”,“歌頌性”,“激進性”,還是具有多方面的特征?“左翼文學”為何還要反“左”?“左翼文學”內部的“左”、“右”又是如何劃分的?如何看待“左翼文學”內部不同的文化追求?
諸如此類的問題,都說明探討“中國左翼文學”的涵義,不僅需要,而且是必須。但要做好這項工作很不容易。本文想簡略地做一點梳理。
二、“左翼”的涵義
在漢語中,“左”、“右”最初都是指人的身體的一部分,即左、右手。《說文解字》[12]釋“左”字為“手相左,助也”。釋“右”字為“手口相助也”。可見,同樣是“輔佐”、“輔助”之意,“左”、“右”手的功能地位并不等同。“右手”的作用更直接更重要。后來,由左、右手引申出指稱方位的意義。“左”指人“面向南時靠東的一邊”[13],“右”則正好相反。
“翼”的本義是“鳥類和昆蟲的翅膀”,“左翼”指左邊的翅膀。它后來的引申義用于軍事領域。中國古代有所謂“三軍”即中軍、左軍、右軍之說。“左翼”即指軍陣中的左邊一陣。這仍只是在確定方位的意義上使用,并沒有現代政治學意義上的涵義。但因為鳥類和昆蟲的翅膀天生兩邊各一,有“左翼”必有“右翼”,而且左右中間還有“主軀干”,這樣的“本義”倒與現代政治學意義上的左、右翼的寓意有著天然的疊合。
自然,這畢竟只是一種“聯想”,并沒有確鑿的歷史依據。因為從現有的資料來看,現代政治學意義上的“左”、“右”翼的概念完全是西方議會制度的產物。《辭海》對它的起源是這樣描述的:“法國大革命初期,1789年5月,國王召開三級會議,貴族與僧侶坐在右邊,第三等級坐在左邊。其后,國民會議召開時,主張民主、自由的激進派坐在左邊,保皇派、保守派坐在右邊,無形中形成左右兩派。19世紀,歐洲國家的議會也以議長座椅為界,分左右兩派就坐。后左派、右派即分別成為政黨派別政治上激進或保守的代名詞。”[14]
可見,在現代政治學的意義上,“左翼”是相對于“右翼”而言的。“左翼”應該是與追求民主自由的“在野派”聯系在一起,“右翼”應該是與強調穩定和秩序的“執政派”聯系在一起。西方議會制度是現代國家的產物。只有在承認和尊重個人及社會各階層的基本權益,允許他們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并運用約法的方式來調節他們之間的矛盾的現代國家,才會有所謂“左翼”、“右翼”之稱。中國古代是專制社會。專制皇權最忌諱臣民結成“朋黨”,更沒有“約法”的形式來保障個人及社會各階層公開表達自己思想的合理權益。它只需要“左”、“右”手的“相助”,而不會允許有“對稱抗衡性”的“左翼”的公開存在。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左翼”一詞至少具有四個基本涵義:一是“抗衡性”。也即是說,“左翼”的存在,是以社會政治生活中“多翼”的存在為前提的。只有“一翼”的社會,就無所謂“左翼”。二是“批判性”。“左翼”的“抗衡性”作用,只有通過“批判性”對抗才能實現。放棄了“批判性”,也就放棄了其自身存在的意義。三是“民眾性”。“左翼”應該是關注底層民眾的生活,代表著底層民眾的權益的。四是“先進性”。西方議會制度誕生之初,專制皇權思想仍比較濃厚。“左翼”的“先進性”,是在激烈地反對皇權、追求民主自由這個特定意義上獲得的。如果離開這個特定的涵義去談“左翼”的“先進性”,則無論穿著什么漂亮的外衣,至少都是一種明顯的誤讀。
值得注意的是,“左翼”的這四個基本涵義是“一個問題”的四個側面,它們是相互聯系、不可分離的。換句話說,只有同時具備這四個特點才算得上是“左翼”。
當然,“左翼”一詞的實際使用情況相當復雜。其中最突出的是“左翼”內部還有“左”、“右”翼之分。而且,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史實來看,“左翼”內部的“左”、“右”翼之爭,其“激烈”與“殘酷”的程度,絲毫不亞于“外部”的“左”、“右”翼之間的對立,有時候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與其“外部”斗爭只反“右”不同,“左翼”對自己內部的“左”、“右”翼兩個極端都反對,有時候還突出反“左”。列寧甚至于1918—1920年連續寫了《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嚴重的教訓與嚴重的責任》、《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一系列文章,明確地把“左翼”內部的“左派”錯誤表現說成是“幼稚”,把它的實質歸結為“自由散漫”、崇尚“革命空談”的“小資產階級性”[15],揭示其產生的根源是“離開無產階級進行堅韌的階級斗爭的條件和要求”,“不能表現出堅韌性、組織性、紀律性和堅定性”,并把這種“動搖不定,華而不實”的“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看作是“工人運動內部布爾什維主義的另一個敵人”[16]。列寧第一次把“左翼”內部的“左”的錯誤歷史化、系統化、理論化,為日后世界范圍內“左翼”內部的“反左”運動提供了理論依據。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兩次“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時間前后相隔三十六年,但重心均在反“左”。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做出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主要批判了中共早期歷史上三次“左傾”錯誤,即1927年底形成的“左傾盲動主義”、1929年下半年形成的“立三路線”和1931年1月—1935年1月長達四年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確認了建國后中共所犯的歷次錯誤,都屬于“左”的性質。指出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是“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17]。
有意思的是,盡管“左翼”對自己內部的“左”進行如此的“清算”,但“左”的泛濫卻仍是“左翼”內部難以革除的痼疾。
三、“中國左翼文學”的涵義
“中國左翼文學”是在特殊的國際國內背景中產生的。從外在表象上看,它與當時國際左翼文學主流“同步”;細察其內在特征,則發現“它與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也“具有非共時性的非同步發展的性質”[18]。如果從“左翼”一詞的基本涵義出發,著眼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和“左聯”內部的矛盾,那么,它至少具有五層涵義:
一是急功近利的政治實用性。
“文學”屬于人的思想、情感等“精神層面”的內容,更多地蘊含著文化層面的涵義。雖然議會政治中的“左翼”不僅具有政治實踐層面的涵義,也具有政治文化層面的涵義,但相對于豐富復雜的文學而言,其文化層面的涵義不同,覆蓋面也不一樣。
“左翼”與“文學”的聯姻,使得它既具有鮮明的政治文化色彩,又具有與生俱來的“文學”特性。這個道理本來是清清楚楚,無須多說的。但在“中國左翼文學”的演變過程中,來自“左翼政治家”與“左翼文學創作者”中的大多數人,卻在“不同的運行方向”上不約而同地忽視了本來應該作為“左翼文學”主體特征的文學性。
“左翼政治家”是立足于政治思想斗爭的需要而向文學伸手,努力把文學改造成為本階級政治思想斗爭的工具,成為“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19];“左翼文學創作者”則是從改造社會與人生的理想出發,主動承載政治思想斗爭的內容,以至于在這種“積極接納”的過程中甘愿做政治革命的“留聲機”而忘記了自身立足的本性。這種狀況,即使在魯迅、茅盾等一直強調“文學性”的作家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魯迅、茅盾等作家在加入“左聯”后創作上的變化,就不能說與這種“追求”的“時代潮流”毫無聯系。“中國左翼文學”創作中普遍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也與這種特點密切相關。
二是你死我活的黨派斗爭性。
在“中國左翼文學”興起的時候,中國非但沒有類似西方的議會政治制度,而且是在“中國式的議會政治”也已經“潰敗”,國民黨武力奪取全國政權后又進行大規模的“清黨”行動時開始的。當時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黨派斗爭,尤其是處于執政地位的國民黨與處于被圍剿地位的共產黨之間的斗爭,不是通過合法的和平手段進行,而是以“你死我活”的“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充滿了血腥的武裝殺戮。國民黨就多次動用政權的力量查封書刊書店,逮捕殺害左翼作家。這就從政治層面決定了“中國左翼文學”不僅具有與生俱來的濃厚的黨派政治性,而且具有特別徹底的否定性和異常激烈的對抗性。所謂甘愿做政治思想斗爭的“留聲機”,熱衷于描寫行刺暗殺等個人恐怖行動,甚至公開表達自己的“辱罵和恐嚇”,都從一個側面表達出這種斗爭的“你死我活”性質。
這種斗爭性質決定了中國的“左”、“右”翼文藝集團理論主張上存在的一些差異和不同的側重點,不可能通過理性的學理探討和理論論爭予以解決。他們都希望依靠政黨的力量去爭奪“唯我獨尊”的話語控制權。“右翼文藝”借助政權的力量,要求取消“多型的文藝意識”,企圖以“民族主義文藝”的“中心意識”來統領文藝界[20]。“左翼文藝”所要求的也“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21]“左翼文藝”的這種思維,在與“新月派”等自由主義文藝的論戰中,表現得也非常突出。
如果說,“否定性”和“對抗性”的特點,與“左翼”的基本涵義還是吻合的話,那么,這種“你死我活”的斗爭性質,則明顯與民主政治的基本涵義相左。
三是困難重重的啟蒙批判性。
左翼文學的理論背景,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斗爭。按照羅伯特·文森特·丹尼爾斯在《革命的良心》一書中的說法,歐洲大陸普遍采用“左”、“右”來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在19世紀70年代。當時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早已形成,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日益暴露并趨尖銳化。作為左翼文學最重要理論根據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在深入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無法調和的內在矛盾的基礎上創建的。左翼文學的核心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從理論上說,左翼文學首先應該出現在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中。
但是,世界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發源地,是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后的蘇聯。這個既有著西方血脈,又有著東方傳統的國度,雖然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有很大的差距,其本身存在著專制思想的濃厚印跡,但也早在18世紀后期就開始了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的啟蒙。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反專制斗爭過程中,俄國的資本主義得到較大發展,資產階級逐漸壯大。這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以及左翼文學的出現,提供了一個相對成熟的基礎。
比較而言,“中國左翼文學”產生的基礎又要薄弱得多。“中國左翼文學”興起的時候,被認為是中國資產階級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才剛剛過去不到十年,其演化的趨勢還是逐漸走向衰落。雖然中國社會由“五四”開始加快了由傳統的專制向現代資本主義的過渡,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沒有也不可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形成規模,更不用說中國資產階級的成熟及其弊端的暴露。中國社會專制思想仍然相當濃厚,專制制度仍然相當普遍。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在與頑固的專制思想和制度的激烈斗爭中,屢屢顯得力不從心。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反專制的歷史任務遠沒有完成。這就給“中國左翼文學”提出了一個雙重性的歷史責任:按其本身的理論,必須努力創造“無產階級文化”來反抗“理論上”處于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文化”;但其現實的歷史任務,卻又必須聯合“資產階級”去共同反抗“實際上”占據著統治地位的“專制文化”。遺憾的是,雖然“中國左翼文學”提出的口號是“反帝反封建”,但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把自己批判的重點放在了資產階級。不但大資產階級要批,連小資產階級也要批。而對于“反封建”的理解,側重點也不在清除專制思想。有時候甚至還反過來運用“專制”思想來批判“資產階級”。也許這并不是它的“本意”,但由此造成的思想混亂卻是我們認識“中國左翼文學”時不能不特別注意到的。
當然,“中國左翼文學”中也有以魯迅為代表的一小部分人堅持反專制的啟蒙批判性立場,但因為“主戰場”在批判資產階級,他們不但遭遇到專制勢力的頑強抵抗,而且時時受到“左翼”內部的嚴厲批評。他們的聲音顯得微弱,行動更是困難重重。
四是理論資源的混雜性。
“中國左翼文學”的理論資源和創作方法都是從國外移植過來的。除了瞿秋白等少數懂俄文、了解俄國的知識分子直接從蘇俄翻譯介紹了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無產階級文學理論和作品外,絕大多數是由魯迅、沈端先、馮乃超等曾經留學日本的知識分子從日文、英文、德文等“第三國”文字轉譯的。而且,從當時翻譯工作總的演變趨勢來看,開始主要是翻譯介紹蘇聯、日本等國的作家理論家闡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著作,后來才將翻譯介紹的重點轉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魯迅特別看重瞿秋白的翻譯,既因為瞿秋白是從俄文直接翻譯,也因為瞿秋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比較系統地翻譯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拉法格、普列漢諾夫等人的論著的第一人。
魯迅對當時“中國左翼文學”理論上的混亂非常不滿,曾寄希望于懂俄文的人能從原蘇聯直接翻譯一些著作。但懂俄文的蔣光慈既看不起翻譯,也看不起理論。以他為代表的太陽社中的大多數人也是如此。
其實,即使直接從俄文翻譯,蘇聯的無產階級文藝理論也是存在著巨大差異的。1923年在蘇俄發生的一場激烈而又影響巨大的文藝論戰,托洛茨基、沃隆斯基與“崗位派”的觀點就勢不兩立。如果再進一步追問,情況亦復如此,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創始人的主張就存在差異,在后來的傳播、接受、實踐過程中,因民族、國家、政治文化等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闡釋,出現不同的派別、路線,并引發激烈的沖突。”[22]
蔣光慈的創作更多地受到原蘇聯文學的影響,后來也是最早被“清算”的作家之一。
五是理論辨別和消化能力的薄弱性。
“中國左翼文學”所借鑒的外國文藝理論如此斑駁陸離,而大多數倡導者又缺乏理論辨別和消化能力,往往只能夠跟隨別人亦步亦趨。太陽社大多數人看不起理論,其理論家錢杏邨又被胡秋原批評為“充滿理論混亂”[23],被馮雪峰批評為“不理解文學和批評的階級的任務”,“常常表現的階級的妥協與投降”[24]。即使注重“理論斗爭”的創造社“新銳”如李初梨、馮乃超等人,專注于理論指導工作的周揚等人,也對流行的無產階級文學理論缺乏辨別和消化的能力,在他們倡導無產階級文學的過程中,機械搬運的印痕也非常明顯。
“中國左翼文學”理論家的這種狀況,一方面使得他們的批評常常難中腠理,往往需要運用唱“空城計”的方法來虛張聲勢。魯迅對此極為反感,曾希望能“有一個能操馬克斯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25]他,但結果卻令他非常失望。另一方面的表現是思維的混亂。比如,在對“左翼”、“右翼”的理解上,左翼作家普遍把“左”僅僅看作是“提出一種目前還不能實行的方針,超過了現實的革命階段”[26],而沒有認識到有許多“左”的東西其實是與人類的普世價值背道而馳的,是永遠不能實行的。于是,不少人毫不顧及這些詞語的基本涵義,往往是把他們自己認為好的東西就往“左翼”中塞,認為不好的東西就往“右翼”里套。明明胡適、梁實秋是“自由主義者”,但因為他們曾批評過左翼文學,就把他們斥之為“右翼文人”。明明在“左聯”解散問題上周揚等人持的是“右”的觀點,卻仍批判成“左”的錯誤。有時面對同一個歷史事實,同樣的評論人在不同的時期也可有截然不同的評價。比如,針對馮雪峰在與“自由人”、“第三種人”論爭中寫的文章,夏衍等人在1950年代末可指責其為“右傾機會主義”,在改革開放后又可說成是“左傾機會主義”。這種思維的混亂也給后人認識“中國左翼文學”帶來了許多迷障。
總之,“中國左翼文學”的涵義具有多方面矛盾糾結著的特征,它是一個充滿著矛盾的聚合體。
(作者單位:廣州大學)
本文為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項目(GD11CZW13)
[1]程凱:《尋找“革命文學”、“左翼文學”的歷史規定性》,《鄭州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年第1期。
[2]劉海波:《二十世紀中國左翼文論研究》,上海:復旦大學2003年博士論文。
[3][10]王富仁:《關于左翼文學的幾個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1期。
[4]周景雷:《延安文學并非左翼文學》,《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
[5]《人民日報》1980年4月8日。
[6]程光煒:《左翼文學思潮與現代性》,《海南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2002年第5期。
[7]林偉民:《中國左翼文學思潮》第350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8]艾曉明:《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第3—6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9]趙園、錢理群、洪子誠等:《20世紀40至70年代文學研究:問題與方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2期。
[11]王得后:《魯迅文學與左翼文學異同論》,王得后:《魯迅教我》第252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2]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影印版。
[13]《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第168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修訂第3版。
[14]《辭海》(第6版縮印本)第2573頁,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
[15]列寧:《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列寧選集》第3卷第530、53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
[16]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4卷第188、18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
[17]《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第3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8]王富仁、楊占升:《馮雪峰與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馮雪峰與中國現代文學》第2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
[19]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20]《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北京大學等校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3冊第79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21]魯迅:《“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魯迅全集》第4卷第20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22]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第10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23]胡秋原:《錢杏邨理論之清算——馬克斯主義文藝理論之擁護》,蘇汶編:《文藝自由論辯集》第54頁,上海:上海書店1982年根據現代書局1933年版影印。
[24]馮雪峰:《“阿狗文藝”論者的丑臉譜》,《雪峰文集》第2卷第35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25]魯迅:《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魯迅全集》第4卷第236頁。
[26]趙浩生:《周揚笑談歷史功過》,《新文學史料》1979年2月第2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