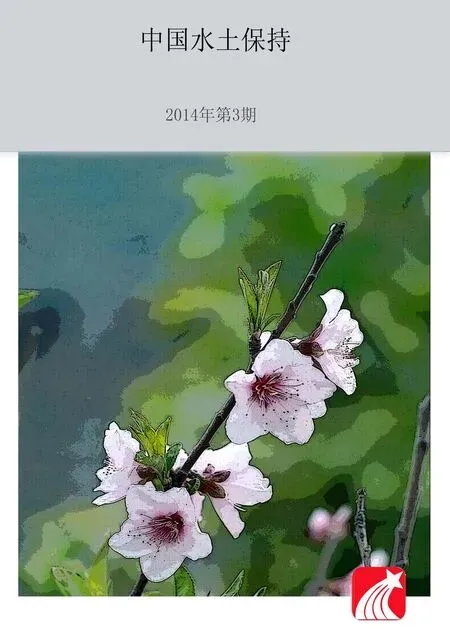黃土高原典型區降雨植被耦合對侵蝕產沙影響的臨界研究
汪明霞,王衛東,張鵬飛
(1.黃河水利職業技術學院 水文與水資源系,河南 開封 475001;2.水利部黃土高原水土流失過程與控制重點實驗室,河南 鄭州 450003; 3.區域水土資源高效利用研究中心,河南 開封475001)
降雨、植被、土壤、坡度等是影響土壤侵蝕的重要因子。坡度、土壤物理性狀是長期地質作用形成的,不易改變,而被覆度和降雨在空間和時間上卻有較大的變化,且由于植被的存在,使得降雨和侵蝕之間的關系十分復雜。降雨植被耦合對侵蝕產沙影響的研究是地表過程領域重要的科研內容,目前我國許多學者開展了黃土高原降雨植被耦合對侵蝕產沙影響的研究,但大部分研究屬大尺度范圍或是以流域、以縣為單元進行的[1-4],針對典型地區在時間上展開的降雨植被耦合對侵蝕產沙影響的研究尚屬空白。本研究應用黃河水利委員會西峰水土保持科學試驗站南小河溝流域的徑流場實測資料,從微觀角度揭示草業用地降雨-植被耦合對土壤侵蝕的影響,并獲得相應的臨界值,以期為指導黃土高原典型區水土流失治理提供參考。
1 研究區概況、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西峰水土保持科學試驗站徑流場布設于慶陽市西峰區的南小河溝流域。南小河溝系涇河支流蒲河左岸的溝道,地理位置為107°37′E、35°42′N,海拔1 050—1 432 m,屬隴東黃土高原溝壑區。流域地貌主要有塬面、坡、溝谷3種類型,塬面坡度平緩,多在5°以下,坡是連接塬面與溝谷的紐帶,其坡度一般為10°~20°,溝谷坡度一般在25°以上。流域內除下游溝床有白堊紀砂巖出露外,其他地面全部為黃土覆蓋。流域年均降雨量534.4 mm,年均氣溫9 ℃,無霜期160 d左右。
1.2 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西峰水土保持科學試驗站于1954—1963年布設的22個自然草地徑流場、1957—1963年布設的7個人工牧草徑流場以及1957—1986年觀測時間最長的李家臺人工牧草徑流場,總計發生產流降雨310次。牧草品種主要為紫花苜蓿和草木樨。觀測時,人工草場、自然草場徑流場記載每次降雨總量、徑流總量、泥沙總量、牧草名稱、植被覆蓋度、次平均雨強、每分鐘最大雨強等。
由于植被的作用,使得降水和土壤侵蝕產沙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一般而言,植被類型不同其防蝕能力也不同,喬木、灌木與草3種植被,以灌木的防蝕效果最佳,牧草次之,喬木最差(陳永宗,1983年)。根據徑流場實際情況,本研究選取人工牧草及天然荒坡徑流場為研究對象。牧草植被生長迅速,枝葉茂盛,枝葉冠層截留降雨、削減雨滴動能、防止雨滴直接打擊地面,削弱水流對土壤的沖刷破壞,同時牧草根系網絡固結土壤,改善土壤理化性狀,提高雨水入滲,因此牧草植被的存在改善了土壤的抗蝕力。但是,土壤侵蝕產沙強度同降雨量、降雨強度、降雨動能等降雨特征也有著密切的關系:當次降雨量較大時,降雨產生的侵蝕力也較大,可能會導致較高的侵蝕強度;而如果植被的抗蝕力也較大,這又可能導致較低的侵蝕強度。相反,如果某次降雨侵蝕力起主導作用,植被抗蝕作用居于次要地位,這又可能導致較高的侵蝕強度。因此,為了定量地揭示降雨-植被耦合與侵蝕產沙之間的關系,本研究引入植被覆蓋度作為植被抗蝕力指標,同時引入次降雨侵蝕力作為描述次降雨特征的又一指標。降雨侵蝕力等于在野外測定的降雨能量E和最大30 min降雨強度I30的乘積。降雨能量E的測定非常困難,故常采用下列經驗公式計算黃土高原次降雨侵蝕力[5],即
(1)
式中:R為次降雨侵蝕力,m·t·cm/(km2·h);P為次降雨量,mm;I30為最大30 min降雨強度,mm/h。
I30是一個重要指標,然而在西峰水土保持科學試驗站整編的徑流場資料中,并沒有從當時的降雨量過程線上摘錄出這一指標,因此根據現有資料情況采用田杏芳等的研究成果[6],引入降雨強度復合因子(I平均I最大)代替I30表征降雨侵蝕力。
2 結果與分析
2.1 侵蝕產沙量與降雨的關系
將1972—1985年人工草地李1徑流場(黃土母質,坡度8°,面積187 m2,種植紫花苜蓿)和1959—1963年魏8徑流場(紅土母質,坡度8°55′,種植苜蓿)汛期次產流降雨量與侵蝕量數據點繪如圖1。從圖1可以看出,侵蝕模數與次產流降雨量散點圖關系不明確,這是因為即使在坡度一定的情況下,水土流失仍是降雨量、降雨強度、植被覆蓋度等綜合影響的結果。參考以往關于無植被覆蓋情況下的研究[7]可以知道,同土壤侵蝕量相關程度較好的復合因子有降雨量、次平均雨強(I平均)、最大30 min雨強(I30)。I平均能反映單次降雨的總特征,I30體現的是降雨過程集中程度的差異性。西峰水土保持科學試驗站徑流場整編資料中沒有從當時的降雨過程線上提取出I30這一指標,因此將I最大(每分鐘最大雨強)作為復合因子之一,分析有植被覆蓋情況下降雨復合因子(PI平均I最大)與土壤侵蝕的相關性,其相關分析結果見表1。

圖1 次產流降雨量與侵蝕模數的關系

表1 不同植被覆蓋度下的降雨量、每分鐘最大雨強、次平均雨強相關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在植被覆蓋度較低的情況下,土壤侵蝕同次降雨量、每分鐘最大雨強、次平均雨強具有良好的相關性,這也進一步說明除最大30 min雨強外,影響侵蝕的重要指標也可以用次平均雨強、每分鐘最大雨強來表征。隨著植被覆蓋度的增加降雨復合因子(PI平均I最大)與侵蝕量相關系數在減小,但均通過了F0.05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在植被存在的情況下侵蝕量同降雨復合因子(PI平均I最大)仍相關,只是植被覆蓋度越高其截留降雨、減小雨滴擊打動能的能力就越強,對侵蝕量的影響也就越大。
2.2 植被覆蓋度與產沙的臨界響應關系
將1957—1963年7個人工牧草徑流場及1954—1963年22個天然荒坡徑流場的230場次產流降雨植被覆蓋度同侵蝕量的關系點繪如圖2。從圖2看出,次侵蝕模數與草地覆蓋度之間的散點關系不明確,但這些散點中一些相對較大的侵蝕模數與植被覆蓋度卻呈現較好的規律性,即當植被覆蓋度為10%時出現次侵蝕模數最大值,植被覆蓋度<10%時相應植被覆蓋度的較大侵蝕模數隨著植被覆蓋度的增加而增大,這說明當植被覆蓋度<10%時植被對阻止侵蝕基本無效。當植被覆蓋度>10%時一些相對較大的侵蝕產沙數據與植被覆蓋度之間呈現出較好的冪函數關系。該現象表明,在一定的草地覆蓋度條件下,其極大侵蝕模數受到草地覆蓋度的制約,但不是每次降雨都一定能夠產生如此高的侵蝕量,當降雨強度、降雨量等其他條件不充分時,相同覆蓋度條件下出現相對較小的侵蝕模數的現象是常見的。因此可知,牧草覆蓋度決定著研究區的極大侵蝕模數。由此引出一個新的物理概念即極端侵蝕模數。從圖2還可以看出,當植被覆蓋度達到70%時,徑流場極端侵蝕模數趨于零(基本不發生侵蝕),這說明當植被覆蓋度>70%時,植被抗蝕作用達到最大且趨于穩定。

圖2 植被覆蓋度與侵蝕產沙的關系
2.3 降雨植被耦合與產沙的臨界響應關系
為了進一步研究植被對降雨侵蝕的影響,將>10%的植被覆蓋度與次極端侵蝕模數、降雨侵蝕力與次侵蝕模數點繪如圖3。由圖3可知次降雨侵蝕力和次侵蝕模數呈正相關,植被覆蓋度同極端侵蝕模數呈負相關,并且兩條關系曲線具有一個臨界點,即極端侵蝕模數為710 t/km2、植被覆蓋度為25%。這一臨界點說明當極端侵蝕模數<710 t/km2、植被覆蓋度>25%時,植被抗蝕力占主導作用,降雨侵蝕力占次要地位;當極端侵蝕模數>710 t/km2、植被覆蓋度<25%時,發生極端侵蝕模數的次降雨植被抗蝕力起次要作用,降雨侵蝕力占主導地位。這一臨界點的現實意義是如果使某覆蓋度對應的次降雨極端侵蝕模數降至710 t/ km2以下,且發生極端侵蝕模數時植被抗蝕力起主導作用, 則植被覆蓋度不能低于25%。 同時由于植被覆蓋度達到70%時極端侵蝕模數趨于穩定,因此如果要使植被抗蝕力起絕對主導作用、植被抗蝕力達到最優效果,則植被覆蓋度至少要達到70%。

圖3 降雨植被耦合與產沙的臨界響應關系
3 結 語
(1)盡管研究區植被覆蓋度對侵蝕模數影響既非線性也非指數型關系,但植被覆蓋度>10%時極端侵蝕模數同植被覆蓋度之間卻存在著良好的函數關系。
(2)根據次降雨侵蝕力、植被覆蓋度、侵蝕模數臨界點和拐點的變化,在慶陽地區生態建設中,除因地制宜地選好人工牧草外,要使人工牧草起到有效的抗蝕作用,其覆蓋度應不低于10%;若要使牧草植被的抗蝕力達到最優效果,其覆蓋度至少要達到70%。
(3)南小河溝小面積的坡地徑流場為從微觀角度研究降雨植被耦合對侵蝕的影響提供了重要的數據,但整個試驗中缺乏植物根部對土壤抗蝕作用、土壤物理、化學抗蝕性及30 min最大雨強數據,使得試驗資料的應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時試驗主要是對天然降雨的觀測,輔助的人工降雨試驗不足,且忽略觀測過程。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應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新的徑流小區布設,進一步開展土壤物理、力學、化學性質及植物根部消能減蝕作用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陳浩,陸中臣,李忠艷,等.流域產沙中的地理環境要素臨界[J].中國科學:D輯,2003,33(10):1005-1012.
[2] 許炯心.降水-植被耦合關系及其對黃土高原侵蝕的影響[J].地理學報,2006,61(1):57-65.
[3] 彭少明,黃強,陳愛紅,等.黃河流域水資源多維臨界調控研究[J].人民黃河,2003(9):32-37.
[4] 王隨繼.黃河中游多沙粗沙區侵蝕產沙與植被相互作用的臨界現象[J].水土保持學報,2004,18(4):20-28.
[5] 王萬忠,焦菊英,郝小品.黃土高原降雨侵蝕產沙數據圖集[M].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1991:133.
[6] 田杏芳,賈澤祥,劉斌,等.黃土高塬溝壑區典型小流域水土流失規律及水土保持治理效益分析研究[M].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08:32.
[7] 陳曉安.黃土丘陵溝壑區坡面土壤侵蝕規律與坡面侵蝕經驗模型的研究[D].武漢:華中農業大學,2010:7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