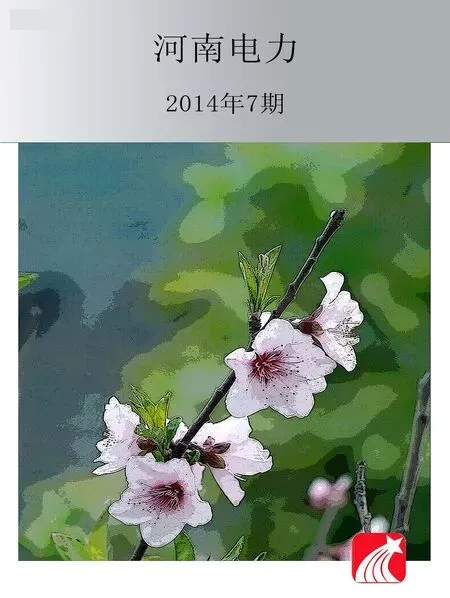滕國杰:相機就是我的“眼”
張 潔
推開滕國杰辦公室的門,就看到桌子上的兩臺相機,他穿著攝影用的馬甲,一副隨時準備出去的樣子。見有人進來,他放下正在處理的照片,起身露出一個微笑。
“攝影,就是感悟人生的積極向上,體現平淡人生的內涵。我想快樂攝影,也想把這份快樂帶給大家。”這是他對攝影的感悟。
在變革中成長
1980年,滕國杰被分配到洛陽熱電廠工作,每月工資20多元。第二年,他用積攢的400多元錢,買了人生第一臺相機。對工作剛一年的滕國杰而言,攝影,只是打發單身時光的小愛好。那時的周末,他騎著自行車,幾乎跑遍了洛陽所有著名景點,光是龍門他就去了幾十趟。因為喜愛,所以他不知疲倦。后來,廠里為了支持他這個愛好,將他調動到有暗房的保衛科。那些手法略顯青澀的老照片,最早都是在那間凌晨還透出紅光、作為暗房使用的辦公室里沖洗出來的。
說起膠片時代,他略顯感慨:“那時候花費多大啊,我一個月工資才20多塊,一卷彩色負片最便宜也要10多塊,還只能拍十幾張。”但是,那時的他明白,多拍,才能在這條道路上進步更快。上世紀90年代,隨著數碼時代來臨,攝影的門檻更低,要求卻更嚴。攝影界的大變革來了,只有跟上這股潮流,才不會被時代拋棄。
當談到他是怎樣從一名愛好者走上了攝影師的道路,他哈哈笑著說,因為他對攝影“有貪心”,總是想從別人那里學習更多,總是希望自己拍得更好。為了在拍攝時捕捉到最佳光線,滕國杰總是早上三四點就出門,下午三四點再出去,起早貪黑地拍。漸漸地,光圈優先還是速度優先、用大光圈還是小光圈、用不用超景深、用不用超焦距,他在腦海里瞬間就能判定,像條件反射一樣。
隨著技術進步、積淀加深,他的攝影狀態已從開始簡單地展現畫面,轉變為深入地表現內心。
用照片講故事
2013年的國慶節,滕國杰去了一趟內蒙古額濟納旗,那真是一個出照片的好地方。有保存最完整的西夏、元代古城——黑水城,還有屈曲盤旋著虬枝的胡楊林。
在一個沙坡后面,他發現了一小塊紋理清晰的斷壁,但高度不足一米,怎樣才能體現出它曾經的雄偉、風云變幻的滄桑?經過正午的曝曬,沙子頗有些燙手,但他渾然不知。趴在沙子上拍了幾張,感覺效果不夠好,他就向前匍匐了兩下,再拍。最后,他是趴在這個“城墻”腳下,下巴抵在沙子上,仰著脖子,用一種很別扭的姿勢,拍出了沙漠中“高大雄偉”的古城墻。
“胡楊,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走在胡楊林中,他被這凝重的不屈所感染。于是,他將它們高舉著“斷臂”的吶喊,珍而重之地留在了鏡頭中。
這張是在東北拍的,這張是在特高壓工地拍的,這張是在太行山,在三門峽,在廈門,在婺源,在上海……在向筆者展示他的作品時,他總是先屏住呼吸,再輕輕地呼一口氣,好像每翻開一張照片,就是又一次地按下快門。
瑰麗風景讓滕國杰胸懷寬闊,心態平穩。而小人物的辛酸苦辣,讓他對人生有更多感悟。
剛工作的拮據大學生,回工棚的疲憊民工,為了兒女第二次打工的退休老人,風吹日曬的街邊攤主……他們雖然不驚天動地,卻更能見證一座城市的變遷,一個社會的成長,以及一些夢想的實現。夜幕降臨的時候,他背起相機,行走在充斥著小攤販的街道上。一盞盞昏黃的燈下,總有他駐足的身影。這些鏡頭下的小人物有的很靦腆,有的很疲憊,但更多的是匆匆忙忙,就像這個城市的發展速度一樣。
心手合一拍作品
作為一名攝影講師,滕國杰在業余攝影班的授課表排得滿滿的,顯然,他享受著拍攝的快樂,也享受著分享的快樂。因為學員大部分是水平不錯的愛好者,怎樣幫助大家更好地進步、拍出更優秀的作品是他正在努力追求的。
每次上課,滕國杰都堅持用自己的片子,他說:“這樣避免了分析誤差,能更準確地傳達我當時的感受、選擇手段的原因。”每張照片,從涉及的基礎知識,到復雜的后期處理,他都會細細講授。“反復學習基礎,才能熟練運用,也會更容易突破瓶頸。”比起等待靈感,滕國杰更愿意相信扎實的基礎。
聽到有人說“玩單反窮三代”,滕國杰擺了擺手笑道:“那是初期玩器材的階段。一開始需要好的手段,所以會需要各種鏡頭,一旦拍多了,知道了表現方式,器材就變得次要了。”
滕國杰鐘愛灰色。在實際拍攝中,由于各種原因,拍出來的照片常出現灰色調。他認為在攝影中,白色包含所有顏色,而灰是白和黑的過渡,所以灰就會含有50%的各種顏色。后期將灰色調處理掉很容易,那么在分層次顯現各種顏色后,就會得到意想不到的突出效果。“一看片子就知道是他拍的,他就是這種風格,能將韻律帶入到作品當中。”一位影友輕易地就認出了他的作品。
團隊拍攝時有人會問他,“老師,為什么您拍的和大家都不一樣?”
“要理解光,注意構圖,觀察現場,突出主體,多多抓拍。別放棄模糊或灰暗的照片,通過后期的調整,也能化腐朽為神奇。”他總是笑著,語速不快,但就是這種淡然的沉穩,讓人愿意聽他講更多,“要成為好的攝影人,就要反復地學習攝影基礎知識。在按下快門的一瞬間,要用頭腦去分析,將自己真實的感悟通過作品表達出來。”
在他眼里,懂得生活的人,自然會喜歡上攝影。簡單的攝影就是按一下快門,真正的攝影師卻不那么簡單地操作。他們對鏡頭的擺放、對角度的偏向、對取景的要求都是特別講究的。要在歲月的打磨中,在朝朝暮暮的堅持中,在持之以恒的操練中,用攝影之眼,看百味人生的不同風景,用獨到手法,提取自然的純粹作為肉眼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