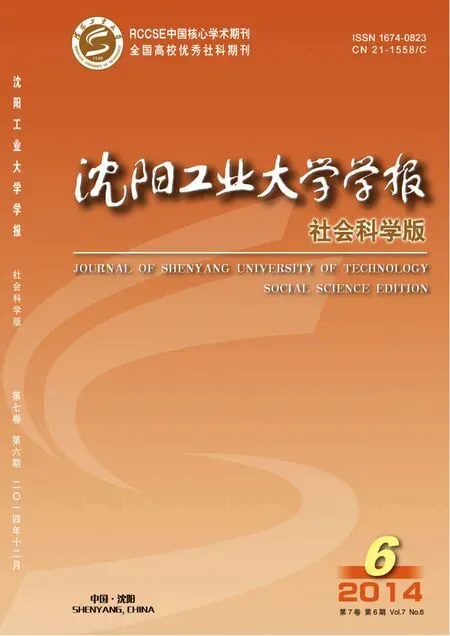中國憲法傳統中的里程碑*
——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
楊 蓉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法學院, 北京 100038)
中國憲法傳統中的里程碑*
——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
楊 蓉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法學院, 北京 100038)
諸多事件的組合以及各種歷史片段所形成的力量的斗爭與力量的消長,最終促成了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通過對此會議前后所綻出的各歷史片段所形成的諸多力量的分析,說明何種力量才是當時國家發展最需要的力量,為什么這一力量所支持的建國模式以及在實踐中形成的法律系統與法律傳統會繼續發展與延續。同時據此指出,面對今天國家的建設與發展,什么才是最合適的方式。
憲法; 政治協商會議; 法律傳統; 新民主主義; 三民主義; 資本主義
歷史不是一個單向的直線的過程,而是一個個片段的綻出,每個綻出事件的力量斗爭的結果是諸多力量的爆發[1]。我們今天看到的現實不是單向發展的結果,而是諸多事件的組合,其中要重視的一個事件就是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這一事件反映出諸多力量的斗爭,回顧歷史時重要的就是要看到這些事件背后的力量。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召開,與會各黨派就五大內容達成協議,建國藍圖勾勒完成,這似乎預示著中國將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然而隨后國民黨的態度迅速變化,以致最終建國藍圖付之東流,民主聯合政府的建立以失敗告終。
這段歷史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它之前一個個歷史片段的綻出所形成的各種力量斗爭的結果:黨國體制的形成發展及影響,戰時統制經濟的產生發展與影響,三民主義文化的產生與變遷,社會階級的分層,共產黨政權的產生發展與演變,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國共兩黨軍事實力的此消彼長,逐漸成長為以調解國共矛盾為主要任務的中間勢力的產生,國際戰爭環境的變化與反法西斯同盟逐漸取得優勢,美蘇對華政策的變化與美蘇在華利益的爭奪,重慶談判的實現,聯合政府的提出等。這些歷史的片段所形成的力量的斗爭與力量的消長,最終促成了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并形成了建國藍圖。
無論“藍圖”結果如何,圍繞“藍圖”實現的斗爭過程,本質上是當時各大力量尋求民主與憲政這一現代立國標準的中國實現方式。本文通過對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前后所綻出的各歷史片段所形成的諸多力量的分析,試圖最終說明何種力量才是當時國家發展最需要的力量,為什么這一力量所支持的建國模式以及在實踐中所表現的法律系統與法律傳統會繼續發展與延續。同時試圖指出,面對今天國家的建設與發展,什么才是最合適的方式。這些似乎能從歷史中得到啟迪。
一、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協議給國家法律傳統帶來的新發展
中國國土面積廣大,有著其特定的歷史傳統與文化背景,在戰爭這一特殊的歷史環境中,國土被瓜分,不同的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國傳統似乎在廣大的國土上出現了不同層面的斷裂,但似乎又根深蒂固。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上,三大力量對民主憲政的不同主張就表現出了這一現象,但最終都圍繞一個主題——西方正統的民主憲政思想如何與中國現實相結合。一方主張尊重傳統(國民黨),一方主張全盤西化(第三方力量或稱中間勢力,即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贊同走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路線的人士的統稱),一方則采取中庸之道(共產黨)。既然產生了不同的觀點,那么三方對于民主憲政的實現方式自然有著以自我觀點為中心的設計,在國家政權建設與鞏固的實踐中最終表現為法律系統的建構與法律傳統的形成,它們因為基本觀點的不同而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法律傳統形成之后,由于其在經濟基礎、政治構成和文化表現上都具有深刻的歷史性和延續性,因此如果要進行改革將會是一場巨大的變革,完成這一變革所需要的力量也是巨大的。
就擁有政權實踐的國民黨與共產黨而言,國民黨政權所形成的法律傳統維護的是以三民主義為指導的、訓政時期黨國體制模式的國家政權,即使是發生變革,也應按照孫中山所設計的憲政實現權能分治;共產黨政權所形成的法律傳統維護的是按照新民主主理論構建的新民主主義政權,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強調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即使正在向人民民主過渡,共產黨的領導也是最基本的原則。而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結果恰好是中間黨派所主張的資產階級改良派路線,其需要的維護國家政權穩固發展的法律傳統是英美民主憲政國家的法律傳統,這一法律傳統于中國當時既有的兩大法律傳統而言都不可能自然發展形成,因此,協議一旦付諸實踐,就要求國家的法律傳統發生變革,這種變革是一種質的轉變。
這種質變于國家實踐是否具有可行性,是接下來本文詳細分析的問題。概括而言,一方面,從根本上來說,如同毛澤東等共產黨人的分析,中國的現實國情是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并不具有西方國家強大的工人力量,農村經濟也沒有現代化,國家產生“白色”、“紅色”兩種政權有其存在的歷史必然性,因此國家革命既不會如美英一樣,也不會完全等同于蘇聯。另一方面,從擁有法律傳統的兩方力量來說,首先,國民黨內的政治強人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也需要利用這些擴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即使按照原有的傳統開始實施憲政,國家法律傳統只要延續,實際上就有利于他們的發展。但是,走資產階級改良路線就相當于否定了原有的法律傳統,而新形成的法制主要是要限制他們,所以這些政治強人必然全力反抗。其次,共產黨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形成的新民民主主義理論強調的就是共產黨的領導,即使在組成聯合政府時還不具有領導的力量,成為領導也必然成為其未來努力的方向。走資產階級改良路線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原來的新民主主義路線,但是在有可能取得領導權的情況下,且可以表示同意,只是這一同意與國民黨的態度緊密聯系。如前所述,從本質上國民黨內是不會贊同走資產階級改良路線的,所以共產黨就只能堅持自己的新民主主義路線以保存實力。
總體上說來,從國家發展的需要來看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結果雖然主要是兩大力量妥協的結果,但還是符合當時國家發展需要的。但是歷史的契機在國民黨強大的阻力下失去,未來中國憲政國家的發展是必然趨勢,共產黨人肩負起了這一發展的責任,最終推廣全國的是新民主主義理論。這一理論不同于國民黨訓政黨治理論,也不同于資產階級改良路線理論,法律傳統的延續是按照新民主主義法制建設的發展而延續,因此,最終民主憲政的選擇必然不同于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這一歷史的片段。
二、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三大力量建國協議的理想狀態
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順利召開并且形成了具有三方力量共識的協議,這一方面在國際上贏得了一定的贊譽,獲得了國際上各大國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國內給向往民主和平的人民帶來了希望。根據當時歷史資料的記載,舉國歡慶,沉浸在民主政府即將構建的喜悅之中。
1. 國民黨在沒有黨內激烈爭斗情況下所可能達到的民主
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前,國民黨政府的執政狀態是一種壟斷性的權力運行模式,這種壟斷從表面形式上來看是個人(蔣介石)的權威,并且無論是國家根本法或者國民黨黨章都確認了個人(蔣介石)的領袖地位,實際上卻是幾大派系博弈的官僚資本壟斷狀態,而其中主要不愿意放棄既得利益的是CC一派。按照根本法與黨章,從理論上來說,這些政治強人應該是愿意服從于蔣介石權威的,在這樣一種黨國體制下,國民黨的執政走向會是一種怎樣的民主呢?
從蔣介石對國家權力認識的角度來看,蔣介石不愿意承認共產黨分權是一個必然趨勢。在國民黨六大中,蔣介石聲稱他的責任是:“要鞏固本黨的基礎,制止共黨篡竊的陰謀。”[2]186,224他還強調,與中共的斗爭無法妥協,國民黨的“急務”在于創造對中共斗爭的“優勢與環境”[3]。但是,到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前,雖然他極力爭取所希望的優勢與環境,形勢卻已經越來越不利于他。在美蘇主要是來自美國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作出讓步,雖然在其強烈要求下共產黨沒有采取聯合政府的提法,但是實際上政治協商會議的實現在實質上已具備了黨派會議的性質,各黨派并非簡單地、如政府所愿地參加政府,政府實質上是接受了改制,在改組政府這一問題上,這等于是在實現共產黨提出的民主聯合政府構想。如果雙方力量對比始終保持當時的狀態,蔣介石個人縱有一萬個不愿意,但是在他的妥協下作出讓步后,歷史的車輪就不是一黨幾派的力量所能夠控制的。但關鍵是這里我們作了一個理論上的假設——國民黨內沒有激烈的派系斗爭。現實中,蔣介石的黨團改革等方案的出臺實際上都是明顯感覺到個人的權威不夠,力圖改變受制于派系的狀況。也就是說,實際上政治強人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未必愿意在這個時候作出讓步。
2. 共產黨所期望的理想狀態
在蔣介石看來,共產黨具有高度的權威,所以毛澤東能夠順利地指導當時的共產黨并貫徹他的思想。但是從毛澤東本人對權威的解釋來看,他所說的權威是分為權力和威信兩個部分的,并且權威建立的基礎并非某個人超凡的魅力,而是建立在團體的基礎上的[4]69-70,從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視角來看,即建立在無產階級充分信任基礎上的政權。當時毛澤東實踐這一路線所依靠的無產階級主要是廣大工農群眾,因此相關政策需要一定的靈活性。這個靈活性是由放棄城市路線的客觀條件所決定的。但是,從共產黨最開始的路線可以看出,國家政權僅僅依靠農村是不夠的,城市是必然需要的,從當時的條件來看國共談判是必然的趨勢。為了避免以往國共談判的結果,毛澤東堅信:“槍桿子里面出一切東西。從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學說的觀點看來,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并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5]547因此,在談判的大趨勢下既要取得國家政權,又不喪失已有的權威,最好的方式就是采取民主聯合政府的形式。
按照毛澤東對共產黨主張的說明:“我們主張在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6]1056這也說明,共產黨的各項實踐經驗及理論指導所要求的民主可以不提民主聯合政府,但絕對是黨派分權的政府而非參與到國民黨政府之中,更不可能沒有軍權的保障。這樣一種民主,在改組政府的條件下,共產黨雖然由于力量的不足而暫時失去領導地位,但是不排除新民主主義國家制度實現的可能性。最關鍵的是一旦改組的臨時政府成立,就解決了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兩大難題。
3. 各民主黨派所主張的狀態
第三方力量勢力形成后,一直致力于調解國共之間的矛盾,民盟的形成更是深感力量微弱而聯合的結果。一個政黨形成之后,在沒有軍隊力量奪取政權的情況下必然希望參與政權以表達自身結社的愿望。長期以來受制于國民黨的“黨禁”,在終于得到承認之后,各民主黨派必然更加積極地參與政權。特別是對于政府改制,第三方力量自身有強烈的參與政權的愿望,政府改制將是第三方力量所極力想促成之大事。這也說明第三方力量會積極參與到黨政分離的政府改制運動中,從而天然地站在了共產黨一方。重慶談判的效果業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重慶談判結束后第三方力量就積極討論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說明第三方力量十分期待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因而他們自然會積極促成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而在政治協商會議上,第三方力量所表達的民主思想不會偏離自我參政的想法,那么只要不剝奪第三方力量的參政權,第三方力量所期望的民主狀態就能得以實現。
只是理想終歸是理想,假設在實踐中往往并不成立。蔣介石一人能作出讓步,但是已經存在的政治強人并不能作出讓步,既得利益對于資本家來說是很難放手的,更何況安插位置和形成政治地位的過程還有大量的成本在里面。成本與效益之間,資本家需要追求的是邊際效益的最大化,就算是從政治參與地位及權力保持的角度出發,政治資本家亦會在兩者之間作出盡量不損及其經濟利益的選擇。這也就決定了國民黨政府的發展不可能完全順從蔣介石的想法,更何況蔣介石本人也并非真的愿意聯合。因此在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后,重慶談判中未解決的政治問題和軍隊問題依舊可能成為難題,并且會議前的戰事也充分證明了會議召開的不情愿性,加之難題無法解決,會議的結果更多的只能是妥協。妥協就有可能形成雙方均不得利而第三方受益的狀態,但是若受益的第三方并不具備保持政權的能力的話,那么這一形成的妥協就只能淪為空談。
三、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三大力量建國協議的現實分析
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后的祥和氣氛下卻隱藏著巨大的危機,蔣介石最終撕毀協議,與共產黨開戰,政治協商會議的成果付之東流。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于1月31日正式閉幕,政治協商會議第十次大會全體一致通過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憲法草案等“五案”。概括而言,三大力量對這“五案”的觀點是:國民黨主張以“三民主義”*注意這里的三民主義與孫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義有一定的區別,這里的三民主義是國民黨蔣介石加強訓政所宣傳的三民主義。為基礎的建國模式,共產黨主張新民主主義的建國模式,各民主黨派則以參與政權為目標希望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實際上是改良路線)。比較而言,國民黨的主張還是圍繞著以黨治國這一中心,國民黨的領導地位不能動搖;共產黨的主張雖然可以認為是建立資本主義民權國家之主張,但是新民主主義有一個核心命題即共產黨的領導,要實現共產黨的領導,必然要撼動國民黨的領導,這樣看來國共兩黨之間的主張是完全背離的。但是,既然是協商會議就會存在妥協,所以會議能否成功的關鍵在于國共兩黨能否妥協。從政治協商會議閉幕簽訂協議的結果來看,國共兩黨都進行了一定的讓步,相當于最終形成了一個折中的結果。各民主黨派自民盟成立后以調和國共矛盾為主要任務,參與政治協商會議后,他們雖然也表達出自我參政的愿望,但這些都依靠國共矛盾的解決,所以在政治協商會議上各民主黨派的主張還是希望能夠調和國共矛盾。能夠調和國共矛盾的方案最好是一個不偏不倚的居中方案,因此,各民主黨派的資產階級改良路線方案在這樣一種條件下產生了。這種方案實質上是一種折中的路線,從本質上來講,它與政治協商會議的結果最為相近,實際上各民主黨派成為政治協商會議最大的贏家。這主要表現在對他們提出的方案國共兩黨所表示出的基本贊同的態度,只是各民主黨派對于保障協議的實施并不具備相當的實力,所以協議的最終實施還是有賴于國共兩黨的態度。最終的事實證明,國民黨不愿意實踐協議,共產黨依照國民黨的態度迅速轉變方案,各民主黨派再次調解失敗并出現內部分化。這些都是歷史事件的表現形式,其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各大力量所堅持理念之間的巨大差異。
1. 協議與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
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目標概括而言是建立以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為主要力量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其中共產黨發揮著領導作用。也就是說,如果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首先是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但這里的革命階級有特殊的指向,即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封建地主與大資產階級是斗爭的對象;其次是民主集中制,即要注意各階級在革命斗爭中的地位能適合表現民意和指揮斗爭,這里實際上突出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因此,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社會兩部分內容,其實現的核心是強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的領導。
按照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案政府組織案的規定:“國府委員名額之半由國民黨人員充任,其余半數由其他各黨派及社會賢達充任,其分配另行商定。”[7]270這說明共產黨參加政府后實際上仍屬于政府的少數派,需要和第三方力量聯合才有可能爭得國府委員中不到一半的席位(因為其中包括親國民黨的第三方力量成員)。如同胡繩所言:“在這個政府里,當然不會是共產黨占主導地位,即使加上第三勢力,也只有相當的地位,主要的還是國民黨。”[8]13也就是說,按照協議,雖然國家也可以稱為各階級聯合專政,但是專政的階級發生了變化,在新民主主義政治中居于領導地位的共產黨及其所帶領的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成為被領導的對象,在國家政權中居少數派,而原來定義的被斗爭的對象成為現在協議政權的領導階級。即使在憲政國家建立后共產黨可能取得領導地位,但那時共產黨領導的各階級也不是原來新民主主義定義的各階級了。因此在這點上,政治協商會議協議中所確立建國形式還是與共產黨的新民主義建國模式存在區別的。
前面已經說明,協議中的建國模式走的是一條資產階級改良路線(折中路線),因此它既反映三民主義建國理論,也吸收新民主主義政權建設的經驗。這從有關憲法的協議中可以看出:第一,依舊承認國民大會問題中國民黨所堅持的國大原區域及職業代表一千二百名,但將憲法的通過定為須經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第二,五權構成方式依舊,但是為防止總統獨裁,采取提升五院地位的方式擴大部分權力,例如:“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選民直接選舉之,其職權相當于各民主國家之議會;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如立法院對行政院全體不信任時,行政院或辭職或提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長不得再提請解散立法院。”[7]280第三,承認地方自治,確定省為地方自治之最高單位,中央與地方均權,由下而上普選,確保人民自由權利,在一定程度上給解放區政權留下了空間,有利于繼續發展新民主主義。所以,雖然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在性質上與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有很大的區別,但是這也是由共產黨當時在國內政治領域內的力量大小所決定的。不過對于共產黨而言,實踐政治協商會議協議,對其在新組政權中的地位,特別是保存既有解放區政權方面沒有巨大的傷害,只是相當于在取得新民主主義勝利的道路上延長了期限,因為共產黨在政治領域中何時能取得領導地位將是一個未知數。但既然是妥協,共產黨還是有讓步準備的,所以共產黨對政治協商會議的評價是:“雖與新民主主義還有很長的距離,但如按照政協做下去,則是向新民主主義的方向發展。”[9]256同時,共產黨也做好了一旦蔣介石撕毀協議如何進行應對的準備。1946年2月12日,毛澤東在病后出席的第一個會議上即表示:“美蔣要以統一來消滅我們,我們要逃脫。”[10]這里指出的是先交軍權的危險性,劉少奇隨即也表示,在政治民主化的前途還不清楚的情況下,不能把軍隊交出去,否則的話,“蔣對我們軍隊要比對其他雜牌軍還要不客氣,對我們黨也要比對民主同盟還要不客氣。蔣要怎樣便怎樣,民主化反而沒有希望。”[10]254-255也就是說,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在性質上不同于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但是只要能有向新民主主義發展的可能性,共產黨將堅決實踐協議。但是,要向新民主主義方向發展就必須保證協議首先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實現,最后才涉及交出軍權的問題,其主要原因是必需以軍權作為保障自我主張的力量。如果國民黨不實踐政治與法律上的變革,共產黨自然是不會主動走法國路線*即主動交軍權的路線,在國內民主憲政運動高漲時期毛澤東雖然有過類似的想法,但是與國民黨屢次合作失敗的經驗使得毛澤東清楚地認識到軍權的重要性以及交軍權的危險性,因此,共產黨是不可能主動交軍權的。的。
2. 協議與國民黨的三民主義
按照政治協商會議協議,三民主義是建國的最高指導原則,但是在最終結果上,國民黨卻極為不滿有關實施憲法的各項協議,可見政治協商會議雖以三民主義為指導原則,但是在許多問題上還是區別于國民黨所認定的三民主義的。這主要表現在政權問題上,與之相關的有國民大會、憲法草案問題,即圍繞憲政選擇所展開的問題。
政治協商會議對戰后中國的制度設計集中體現在憲法草案協議(以下簡稱憲草協議)所規定的12條憲草修改原則之中[11]205-217,采取了“保全五權憲法之名,運用英美憲政之實”對制度作了議會制混同內閣制和省自治的設計[12]145-159。第一,關于國民大會問題,按照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理論,國民大會擁有實質上的“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但是政治協商會議憲草協議用“另以法律規定”[7]284,實質上將國民大會從本應掌握政權的機構變成了一個沒有任何權力的虛設機構。第二,在中央五院設計上,名義上保留了孫中山的五權劃分的五院建制,實際上通過改變五院的職權與地位,設計了具有西方代議制度特征的三權分立、相互制衡和責任內閣的制度。例如,立法院不是五權憲法中的立法技術部門,而是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的國家最高立法機關,職權類似于西方國家的議會,可以對政府監督和對國家財政進行管理;監察院超越治權具備了議會上院的權力與立法院相互制衡;行政院成為對立法院負責的部門等。這從本質上改變了總統集權的五院相互平等不受牽制的治權。第三,地方自治問題,政治協商會議憲草協議強調省為地方自治的核心,省得制定省憲,但不得與國憲抵觸[7]284。這類似于西方民主憲政國家的聯邦模式,完全不同于孫中山有關地方自治理論對于省的定位。按照孫中山的地方自治理論,縣是地方自治的核心,省只是起到于中央與縣之間承上啟下的作用。這樣一來,憲草協議一則拋棄了孫中山權能分治的整體設計,二來將孫中山五權憲法所規定的中央機構五權分立的合作關系改變為西方三權分立的制衡關系,三則在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處理上采用了類似于聯邦的處理方式,而非孫中山的均權主義。
所以從根本上來講,政治協商會議憲草協議完全不同于國民黨一直以來堅持的“三民主義”,特別是一旦實施這一協議,將對國民黨的統治地位產生很大的撼動,必將受到國民黨內握有實權者的強烈反對,蔣介石也在其中。當然,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所主張的“三民主義”也未必完全等同于孫中山本意的“三民主義”,具體可以從《五五憲草》、《政治協商會議憲草協議》和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的對比中得出結論。概括而言,國民黨蔣介石所同意的《五五憲草》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上沒有遵從孫中山之遺教的均權主義,采用的是中央集權;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所規定制度的原則不是五院分權,而是以行政院為“治權”的重心,以立法院和監察院限制或監督行政院,司法院和考試院比較獨立。與《五五憲草》相比,其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上采用了均權主義,但是沒有突出縣自治。
其實從國民黨的態度可以看出,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才反映了國民黨所可能接受的國家改革模式,《政治協商會議憲草協議》之所以遭到國民黨的抵制,可以從二者的區別中找到原因:第一,國民黨為保證其領導地位,蔣介石為保證其領袖地位,不會贊同類似于西方民主國家的普選制度,國民大會必須是“有形國大”,憲法修改權歸屬于可控的國民大會。第二,國民黨蔣介石不會將自己置于虛位(類似于英王的狀態),要掌握實權,因此五院的設計必須保障總統的權力,蔣介石可以同意提高立法院、監察院的地位,但這些都以不削弱總統權力為原則。第三,承認省為地方自治單位,但并不確認為最高單位,實際上是否認聯邦制。
3. 協議與民主黨派的改良資本主義
由于第三方力量并沒有政權實踐的經驗,其能否參政始終依托于掌握政權一方的同意。同時,他們沒有軍權的支撐,所以只能以中間力量的角色出現。作為第三方力量,如同毛澤東的分析,他們具有不穩定性*具體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中間力量的詳細論述。在不同時期,毛澤東對中間力量的作用都有一定的說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說明是對中間力量問題的一個總結。,容易因為利益的改變而改變方向。但是第三方力量又是一支不能忽視的力量,所以需要抓住他們的特點,團結他們,最終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政治協商會議談判開始后,國共兩黨最終誰能在協議結果上占有優勢地位,主要依靠第三方力量的支持。第三方力量在否認國民黨一黨專制和蔣介石個人獨裁以及主張中國走政治民主化道路方面與共產黨是一致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對國民黨蔣介石政府進行改制是眾望所歸。第三方力量多具有較高的學識,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受過正統的西式教育,并且對于西方的民主憲政十分推崇,因此在如何改革國民黨政府的問題上,他們制度設計的靈感必然深受西方民主憲政思想之影響。不過,也因為他們缺乏政權建設的實踐,所以要實現他們的憲政構想必須獲得國民黨或者共產黨支持,那么就只能局限在現有的制度上進行發揮。本質上來說,第三方力量十分向往完全西化的民主憲政國家,但國民黨所推崇的孫中山建國理論對國家的設計卻帶有很強的個人色彩,并且從法律傳統的角度來說,權能分治、五權憲法已經深入人心,所以改革只能在這一基礎上進行。盡管如此,第三方力量還是充分發揮了他們的智慧,最終實現了運用英美憲政之實,可以稱之為改良資本主義路線。
這一路線本身就是考慮到國民黨的傳統妥協而來的,使國家朝民主憲政方向發展是這一路線的最終目的。因此,只要是能夠改革現狀使國家成為民主憲政國家的協商結果,都是符合第三方力量所期望采取的改良資本主義路線的。從政治協商會議協議案來看,它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共同讓步而形成的妥協案,第三方力量自己都承認:“共產黨的讓步多,蔣介石的苦惱大,民盟的前途好。”[13]231這主要是因為,在國家統治方面結束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蔣介石的個人獨裁,在國家性質上既不同于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國家,也不同于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在修改憲法草案中確立了國家的議會制、內閣制和省自治等,這些實際上構成了資產階級改良路線所設計的國家模式。因此,可以說政治協商會議協議的結果完全符合第三方力量的改良資本主義主張。
四、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結果對國家發展的啟示
從前述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可以看出,歷史是諸多力量的爆發,在這諸多力量之中,傳統占有一個席位,并且是依附于各個力量之上的席位。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還是其他可能的力量在其深層次上都具有傳統延續性,這里并不是把任何問題都歸結到傳統中去,而是強調事物發展所具有的延續性。確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模式的法律系統與國家政權建設實踐共同發展,通過一段時間的延續,最終會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法律傳統。
發展到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時的中國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政權模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法律系統,如果要在國家范圍內形成統一的法律系統,最有效的方法是選擇兩者之一進行改革從而吸納另外一方。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的目標正在于此,它選擇修改的是國民黨的法律傳統,形成的結果是走改良資本主義路線——運用英美憲政之實解決中國問題。對國民黨的法律傳統進行革新十分必要,并且國民黨自己改革的力度受到其本身所代表的階層的限制并不到位,因此借助外力就顯得十分重要了。只是這個外力需要恰到好處,主要是不能觸動國民黨長期以來所確立的統治地位。從政治協商會議的結果來看,它偏偏就是要結束國民黨的專制統治,更有可能觸動國民黨的統治地位,所以對于國民黨來說這個外力過于強大而不能接受,其所能接受的改革都寫在了后來的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之中。因此,在國民黨一方,從根本上來說是不會支持政治協商會議的政治藍圖所帶來的民主憲政的。
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的改革選擇吸納的是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法律傳統,它運用英美憲政之實的方法從妥協的層面上為共產黨提供了發展新民主主義的可能性,但這一可能性是一個不定期的概念,關鍵在于共產黨何時能夠取得領導地位。因此,共產黨一方會支持政治協商會議的政治藍圖所帶來的民主憲政,但這取決于國民黨的決心。國民黨的決心很明顯,他們是不會支持這一改革藍圖的,所以共產黨從本質上來說不是不支持這一改革藍圖,而是必須反對國民黨的專制。反對國民黨專制的政治解決方案已經遭到國民黨的否定,最終剩下的方式只能是通過軍事斗爭的方式。共產黨取得軍事斗爭的全面勝利,實際上是取得了領導地位,那么取得領導地位后的共產黨目標就十分明確了,即實現新民主主義社會,最終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在這個時期再提出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方案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因此,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提供了一個民主憲政國家發展模式的契機,錯過了那個時機,歷史的車輪還在前進,國家始終要向現代化發展。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再次討論民主國家建立問題之時,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的政治藍圖只具有借鑒作用,并不具備現實的可行性。當然,其所吸收的一些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經驗以及它所關注的一些問題還是給1949年政治協商會議及新中國的發展以一定的啟示。
[1] 福柯.尼采、譜系學、歷史 [J].蘇力,譯.社會理論論壇,1998(4):19-24.
[2] 朱匯森.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45年5—7月 [M].臺北:臺灣國史館,1987.
[3] 章百家.對重慶談判一些問題的探討 [J].近代史研究,1993(5):4-8.
[4] 約翰·布萊恩·斯塔爾.毛澤東的政治哲學 [M].曹志為,王晴波,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5]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編寫組.政治協商會議資料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8] “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課題組.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 [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9]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11]秦立海.民主聯合政府與政治協商會議:1944—1949年的中國政治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2]蕭公權.憲政與民主 [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13]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 [M].北京:中華書局,1961.
AmilestoneofconstitutionaltraditioninChina:PoliticalConsultativeConferencein1946
YANG Rong
(Law School,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China)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held in China in 1946 is promoted finally by the struggle and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power form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many events and the various fragments of histo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many forces formed from the various fragments of history occur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Conference,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which power was the most needed power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and why the foundation model supported by the power and the legal system and tradition shown in practice can be developed and continued. At the same time, what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way in the face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oday is pointed out according to it.
constitution;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legal tradition; New Democracy;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Capitalism
2014-06-2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資助項目(2014JKF01030)。
楊 蓉(1984-),女,湖南長沙人,講師,博士,主要從事憲法學與行政法學等方面的研究。
* 本文已于2014-09-23 11∶15在中國知網優先數字出版。 網絡出版地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40923.1115.002.html
10.7688/j.issn.1674-0823.2014.06.03
D 911.02
A
1674-0823(2014)06-0494-07
(責任編輯:郭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