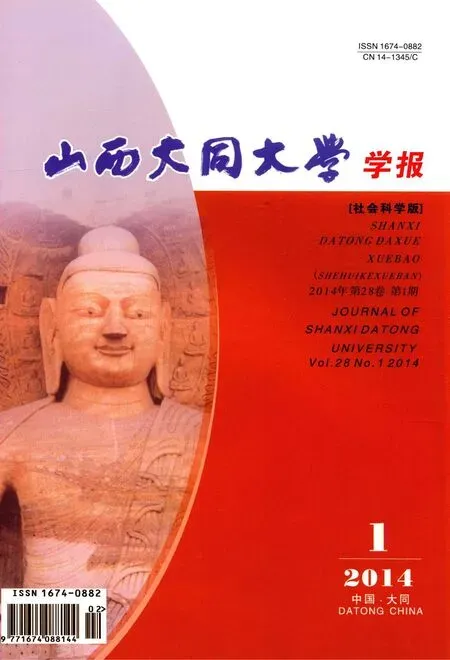“村改居”社區(qū)治理中面臨的困境
李 鑫
(西華師范大學(xué)政治與行政學(xué)院,四川 南充 637009)
隨著城市化進(jìn)程的加快,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我國(guó)逐步開(kāi)始了“村改居”的工作,農(nóng)村地區(qū)開(kāi)始卷入城市化的浪潮之中。所謂“村改居”是指農(nóng)村地區(qū)建制實(shí)施“農(nóng)轉(zhuǎn)非”,農(nóng)民的農(nóng)業(yè)戶籍轉(zhuǎn)變?yōu)榉寝r(nóng)業(yè)戶籍,將村民委員會(huì)這一基層自治組織改變?yōu)樯鐓^(qū)居民委員會(huì)。“村改居”是城市化過(guò)程中發(fā)展起來(lái)的一種新社區(qū)模式,這種社區(qū)模式需要新的社區(qū)治理方式,雖然已經(jīng)披上了一層城市的外衣,但是不同于城市社區(qū)居民治理的模式。“村改居”的這些社區(qū)自治走在一個(gè)分叉路口,是要沿用原來(lái)的村民治理的模式,還是套用城市社區(qū)居民治理模式,這些社區(qū)在治理問(wèn)題上面臨困境。本文試從“村改居”社區(qū)的特點(diǎn)切入,分析這些新型社區(qū)與城鄉(xiāng)社區(qū)的不同之處,進(jìn)而引出所面臨的治理困境,提出一些解決辦法和建議。
一、“村改居”社區(qū)的興起及其特點(diǎn)
“村改居”工作興起于本世紀(jì)初,它是中國(guó)城鎮(zhèn)化過(guò)程中所特有的現(xiàn)象。改革開(kāi)放后,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平均增長(zhǎng)速度達(dá)到10%,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進(jìn)一步推進(jìn)了“村改居”的工作。尤其在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地區(qū),農(nóng)村的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質(zhì)的變化,基本擺脫了傳統(tǒng)第一產(chǎn)業(yè)的束縛,非農(nóng)經(jīng)濟(jì)已成為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的主體。在城市建設(shè)的過(guò)程中,農(nóng)村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和生活方式在城鎮(zhèn)化的進(jìn)程中發(fā)生著巨大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卷入城市化的洪流中。據(jù)國(guó)家統(tǒng)計(jì)局統(tǒng)計(jì),我國(guó)城鎮(zhèn)化率從2000年的32.6%增長(zhǎng)到了2012年的52.6%。北京、上海是城鎮(zhèn)化比較成熟的代表,北京的城鎮(zhèn)化發(fā)展尤為迅速,城鎮(zhèn)化率增加近20個(gè)百分點(diǎn)。除北京、天津外,其他省份城鎮(zhèn)化發(fā)展也處于加速階段,從1995年到2008年,福建、江蘇、浙江三省城鎮(zhèn)人口比重均增加25個(gè)百分點(diǎn)以上。[1]城鎮(zhèn)化的迅猛發(fā)展,使得一些省市“村改居”工作發(fā)展迅速,如膠州灣海底隧道建設(shè)占地使4個(gè)村的村民集中安置,直接由農(nóng)村村落變?yōu)槌鞘猩鐓^(qū)。到2004年底,濟(jì)南市“村改居”數(shù)量已經(jīng)達(dá)到了102個(gè),占城市社區(qū)居委會(huì)總數(shù)的25%。[2]
“村改居”的興起主要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城市化的推動(dòng)下的產(chǎn)物,有其自身的特點(diǎn)。一是社區(qū)居委會(huì)職能的逐漸轉(zhuǎn)變。城鎮(zhèn)化的發(fā)展,使原來(lái)的村委會(huì)掛起了社區(qū)居委會(huì)的牌子,但它并未成為城市居民委員會(huì),而是邁入純城市社區(qū)建制的過(guò)渡階段。“村改居”的社區(qū)具有“亦城亦村”的特點(diǎn)。原來(lái)村委會(huì)的工作重心在經(jīng)濟(jì)上,村長(zhǎng)在總結(jié)工作時(shí),總是把修路挖井等事情的處理狀況放在第一位,而把一些公共事務(wù)放在比較次要的位置,比如村務(wù)公開(kāi)、教育事業(yè)等,現(xiàn)在“村改居”的社區(qū)居委會(huì),逐漸進(jìn)行從發(fā)展經(jīng)濟(jì)到社會(huì)公共事務(wù)管理的轉(zhuǎn)變,例如社區(qū)共建。社區(qū)注重聯(lián)系居民,按時(shí)為居民發(fā)放社會(huì)保障補(bǔ)助,模仿城市居民組織選舉,積極發(fā)展社區(qū)聯(lián)系居民的機(jī)制,定期走入貧困家庭并進(jìn)行一定的扶持,以及社區(qū)居委會(huì)“村改居”后原來(lái)農(nóng)村集體財(cái)產(chǎn)的安置,社區(qū)居民的就業(yè)和權(quán)益保障等問(wèn)題。從現(xiàn)實(shí)來(lái)看,這些問(wèn)題涉及原來(lái)村民直接的利益,處理這些問(wèn)題更加棘手。“村改居”后的社區(qū)居委會(huì)面臨新的考驗(yàn)。二是居民與居委會(huì)關(guān)系的逐漸轉(zhuǎn)變。相比從前,村委會(huì)側(cè)重于對(duì)“有關(guān)集體土地的使用、鄉(xiāng)村事務(wù)的管理、征繳稅費(fèi)及鄉(xiāng)村整體發(fā)展的決策”。[3]村民和村委會(huì)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頻繁,村民對(duì)村委會(huì)更具有依賴性。“村改居”后,社區(qū)居委會(huì)的職能逐漸轉(zhuǎn)變,它更多地把工作重心放在了環(huán)境衛(wèi)生、文藝活動(dòng)、計(jì)劃生育等事務(wù)上來(lái),社區(qū)與居民的經(jīng)濟(jì)利益關(guān)系削弱,而社會(huì)保障的社會(huì)化,使居民與社會(huì)有了更多的聯(lián)系,居民對(duì)居委會(huì)的依賴性變小。
二、“村改居”社區(qū)治理的困境
城市化的發(fā)展,使原來(lái)的村落成為城市社會(huì)中的一員,這些“村改居”的社區(qū)初入城市,在社區(qū)自身治理上面臨著一些困境。
(一)社區(qū)居委會(huì)行政化色彩偏重 “村改居”社區(qū)是農(nóng)村社區(qū)向城市社區(qū)的過(guò)渡階段,這些社區(qū)行政化色彩偏重,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gè)方面:
1.“村改居”社區(qū)被納入城市居委會(huì)后,管理體制行政科層化,居委會(huì)人員的任職條件等都由街道確定,很多事情唯街道辦馬首是瞻。以前村委會(huì)財(cái)政由集體經(jīng)濟(jì)承擔(dān),但是進(jìn)入城市轉(zhuǎn)制以后,由街道撥付,并且經(jīng)費(fèi)減少,造成社區(qū)有事時(shí)無(wú)經(jīng)費(fèi)的困境,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區(qū)對(duì)街道的依賴。
2.工作方式行政化,命令化。政府的職能部門(mén)經(jīng)常把任務(wù)推給街道,但“下任務(wù)不下權(quán)”、“下事情不下錢(qián)”。[4]以前的村委會(huì)出面協(xié)調(diào)本村的大小事務(wù),基本顧忌到每個(gè)人的利益,但是在城市中,社區(qū)充當(dāng)了服務(wù)者的角色,上級(jí)政府職能部門(mén)把任務(wù)委派給街道,街道下放任務(wù),把社區(qū)作為自己的派出機(jī)構(gòu),社區(qū)成了上級(jí)部門(mén)的“一條腿”,把引導(dǎo)變成了指導(dǎo)。社區(qū)疲于應(yīng)付上級(jí)任務(wù),而忘記了自己服務(wù)的功能。蘭州的“村改居”居委會(huì)工作人員反映,“村改居”后的社區(qū)仍然沿用原來(lái)村委會(huì)管理模式,上級(jí)部門(mén)每年把社區(qū)衛(wèi)生、計(jì)劃生育等工作作為社區(qū)的考核標(biāo)準(zhǔn),在檢查工作組到來(lái)之前,這些社區(qū)為了考核優(yōu)秀,幾乎讓全社區(qū)的工作人員加入到衛(wèi)生大清潔的工作中去,社區(qū)居民去社區(qū)辦事,找不到負(fù)責(zé)相應(yīng)事務(wù)的工作人員。“村改居”社區(qū)重視行政管理模式而忽視服務(wù)的理念,管理模式單一,無(wú)法適應(yīng)城市社區(qū)的管理模式。
(二)居民參與不足,社區(qū)自治能力不強(qiáng) “村改居”社區(qū)治理中,行政化效應(yīng)仍然占據(jù)著重要的地位,社區(qū)居民的自我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服務(wù)意識(shí)淡薄,社區(qū)動(dòng)員能力不足,弱化了社區(qū)自治的能力。撤村后,雖然村民在戶籍身份上變?yōu)槌鞘芯用瘢瑓s因?yàn)槿鄙傩碌穆?lián)系紐帶而出現(xiàn)疏離化的傾向,這樣更加需要新的組織載體對(duì)其進(jìn)行服務(wù)和管理。同時(shí),外村人及外地人口作為城市新的人口群體,打破了原來(lái)農(nóng)村的“半熟人”社會(huì),居民之間的熟悉感降低。這些社區(qū)居民離開(kāi)了原來(lái)的村落,脫離了原來(lái)的村委會(huì)的管理,對(duì)現(xiàn)在的社區(qū)缺乏認(rèn)同感。多數(shù)村民進(jìn)入城市后,有事還是會(huì)找原來(lái)的村干部或者大隊(duì)長(zhǎng),很多村民雖“居”在社區(qū)中,但沒(méi)有真正“生活”在社區(qū)中,在心理上還沒(méi)有完全接受現(xiàn)有的“村改居”社區(qū)治理模式。當(dāng)問(wèn)到“你是否關(guān)心社區(qū)的事情”時(shí),大多數(shù)村民認(rèn)為沒(méi)什么事情找社區(qū),平時(shí)也很少關(guān)心社區(qū)的事情,社區(qū)工作人員有事叫就去,沒(méi)事就不去社區(qū)。當(dāng)問(wèn)到“社區(qū)選舉時(shí),你去嗎?”村民的態(tài)度是叫了就去,去了以后也只是舉舉手。大多數(shù)“村改居”居民的政治參與意識(shí)強(qiáng)烈,可是政治參與行為不高。除此之外,“社區(qū)治理是基層多元利益主體進(jìn)行集體行動(dòng)和選擇的過(guò)程,社區(qū)治理需要協(xié)調(diào)多方的利益與關(guān)系,現(xiàn)代社區(qū)分化為功能各異的各類現(xiàn)代社會(huì)組織,與傳統(tǒng)社區(qū)相比具有高度的分化性”。[5]受主客觀影響,“村改居”社區(qū)居民對(duì)現(xiàn)有社區(qū)共同利益關(guān)心較少,社區(qū)共同意識(shí)不強(qiáng),缺乏認(rèn)同感和歸屬感,社區(qū)的很多活動(dòng)都是由賦閑在家的老年人參加,年輕人都忙于工作。社區(qū)由于參與主體的局限性,再加上居民參與意識(shí)不強(qiáng),導(dǎo)致社區(qū)自治能力不強(qiáng)。
(三)社區(qū)自治組織發(fā)展相對(duì)緩慢 當(dāng)前“村改居”社區(qū)自組織的發(fā)展面臨一些困境。“村改居”后的居民主要由原來(lái)的失地農(nóng)民組成,39.7%的調(diào)查對(duì)象文化程度是在“初中及以下”,有29.3%的調(diào)查對(duì)象文化程度為“高中(中專、中技),[6]這些居民大多數(shù)年歲較大,文化程度普遍低,參與意識(shí)不高,參與行為缺乏,對(duì)于社區(qū)的規(guī)章制度也不是很了解。缺乏參與社區(qū)事務(wù)的前提和動(dòng)力,是目前阻礙社區(qū)自組織發(fā)展的主要障礙。大多數(shù)“村改居”居民在受訪中談到,社區(qū)的事務(wù)自己也搞不懂,上面下放任務(wù),自己按章辦事。再者,“村改居”后,大量外來(lái)人口涌入社區(qū),對(duì)社區(qū)事務(wù)關(guān)注度不高。“村改居”的社區(qū)居民發(fā)展自組織也只是局限于有共同愛(ài)好的一群人,他們組織興趣協(xié)會(huì)和文化活動(dòng),但這些自組織沒(méi)有制定相關(guān)的組織制度和人員編排,主要是靠熟人之間的情感維系,這種維系具有很大的易變性和不穩(wěn)定性,如果處理不當(dāng),會(huì)造成組織的解體。蘭州某些“村改居”社區(qū)中,有共同愛(ài)好的人組成秧歌隊(duì)或者合唱團(tuán),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社區(qū)文化生活,陶冶了個(gè)人的生活情趣,但是這些組織在參與社區(qū)事務(wù)的能力上卻顯得后勁不足,它只是靠共同愛(ài)好來(lái)維系,一旦核心人物不在,這些組織可能長(zhǎng)期癱瘓。
三、解決“村改居”社區(qū)困境的路徑
“村改居”后的社區(qū)是我國(guó)轉(zhuǎn)型時(shí)期的一種特殊產(chǎn)物,但是“村改居”社區(qū)出現(xiàn)較晚,許多社區(qū)工作沒(méi)有系統(tǒng)的規(guī)制,而是盲目進(jìn)行,在實(shí)施操作中出現(xiàn)了問(wèn)題,這就需要我們?cè)趯?shí)施中不斷進(jìn)行探索。
(一)逐步理清“村改居”社區(qū)居民委員會(huì)與政府的關(guān)系 當(dāng)前,許多城市社區(qū)和街道辦事處的關(guān)系是被領(lǐng)導(dǎo)和領(lǐng)導(dǎo)的一種關(guān)系,“村改居”社區(qū)效仿城市社區(qū)的運(yùn)行機(jī)制,直接承擔(dān)上級(jí)指派的任務(wù)。應(yīng)按照“政事分開(kāi)、政社分開(kāi)”的原則和“小政府、大社會(huì)、大服務(wù)”的要求,理順政府與社區(qū)的關(guān)系。社區(qū)居委會(huì)協(xié)助、配合上級(jí)政府管理社區(qū)事務(wù),不是一級(jí)行政機(jī)關(guān),其主要的職能是行使社區(qū)居民賦予的自治權(quán),為社區(qū)居民服務(wù),應(yīng)進(jìn)一步理順基層政府、街道辦事處和社區(qū)的關(guān)系,可嘗試在基層政府與社區(qū)之間建立一種委托——“代理式契約關(guān)系。[7]政府作為上級(jí)領(lǐng)導(dǎo),對(duì)社區(qū)事務(wù)應(yīng)該給予指導(dǎo)、協(xié)調(diào)、動(dòng)員、監(jiān)督,在財(cái)力物力上給予相應(yīng)的支持,而不是參與干涉社區(qū)事務(wù)。社區(qū)居委會(huì)作為其代理人,按照上級(jí)指示完成各項(xiàng)工作,以此有效地推進(jìn)兩者平等合作的關(guān)系。除此之外,社區(qū)作為自治的載體,應(yīng)該廣開(kāi)渠道,積極配合,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wù)創(chuàng)造條件,讓居民感受到自我管理、自我服務(wù)的甜頭。關(guān)乎到社區(qū)重大事件時(shí),可以召開(kāi)居民聽(tīng)證會(huì),制定相關(guān)制度來(lái)提高工作的透明度,使居民參與到社區(qū)管理之中。社區(qū)居委會(huì)不再是上級(jí)政府的“一條腿”,而是幫助上級(jí)政府更好地進(jìn)行基層治理。
(二)建立社區(qū)居民參與的制度規(guī)范,逐漸完善居民自治 隨著我國(guó)基層民主的發(fā)展,黨和政府越來(lái)越重視居民參與的一系列問(wèn)題,比如參與方式、參與對(duì)象、參與途徑等,加快“村改居”居民參與的建設(shè)。在“村改居”后,需要建立社區(qū)居民參與的長(zhǎng)效機(jī)制,必須用制度來(lái)明確不同參與主體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提供方便便捷的參與渠道。各個(gè)“村改居”社區(qū)應(yīng)根據(jù)本社區(qū)的實(shí)際狀況,制定詳細(xì)的參與程序,讓居民一目了然。
“實(shí)行居民自治,制度建設(shè)是根本”。[8]要加強(qiáng)居民自治的制度保障,居民可以直接或者間接進(jìn)行居委會(huì)選舉,由居民集體討論的自治章程可作為民主管理制度,準(zhǔn)時(shí)無(wú)誤地公布社區(qū)的重大事務(wù),向居民公開(kāi)民主監(jiān)督制度。這樣既可以使居民自治有制度的保證,也給居民自治提供了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在對(duì)“村改居”的居民進(jìn)行采訪時(shí),居民們對(duì)有權(quán)力選舉居委會(huì)班子感到滿意,大多數(shù)居民認(rèn)為選舉過(guò)程還是比較公正的,通過(guò)選舉可以選出好的領(lǐng)導(dǎo)。
(三)發(fā)展社區(qū)自組織 “國(guó)家太大,社會(huì)成員之間不可能建立面對(duì)面協(xié)調(diào)機(jī)制,社區(qū)較小,居民之間可以而且事實(shí)上存在面對(duì)面協(xié)調(diào)機(jī)制;市場(chǎng)信奉‘沒(méi)有免費(fèi)的午餐’,市場(chǎng)不信眼淚,而社區(qū)提倡鄰里互助,關(guān)愛(ài)弱勢(shì)群體”。[9]由此看來(lái),社區(qū)自組織是國(guó)家和市場(chǎng)的補(bǔ)充,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發(fā)揮著不可小覷的作用。社區(qū)自組織優(yōu)于“被組織”,在自組織環(huán)境下,社區(qū)居民的生活關(guān)聯(lián)度、熟悉程度都比較高,它內(nèi)在的規(guī)范能夠讓居民無(wú)形地自組織起來(lái),降低了社區(qū)治理的成本。
如何實(shí)現(xiàn)社區(qū)治理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需要社區(qū)外部力量的支持,也需要社區(qū)居民自組織對(duì)社區(qū)內(nèi)部事務(wù)的整合配置,從而實(shí)現(xiàn)社區(qū)的“善治”。目前,“村改居”社區(qū)最主要的自組織是文體娛樂(lè)組織。許多居民自發(fā)組織形式多樣的協(xié)會(huì),不僅豐富生活,而且為社區(qū)居民之間的交往提供了一個(gè)平臺(tái)。社區(qū)自組織和社區(qū)治理的目標(biāo)是相一致的,發(fā)展社區(qū)自組織,是為社區(qū)治理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提供一種新的社會(huì)力量,大力培育發(fā)展社區(qū)自組織是衡量社區(qū)治理狀況的一個(gè)重要指標(biāo)。
[1]代 帆.中國(guó)城鎮(zhèn)化發(fā)展的地區(qū)差異及與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關(guān)系研究[D].北京:首都經(jīng)貿(mào)大學(xué),2011.
[2]高靈芝,胡旭昌.城市邊緣地帶“村改居”后“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濟(jì)南市的調(diào)[J].2005(09):110.
[3]羅伯特·貝涅威克,朱迪·豪威爾.社區(qū)自治:村委會(huì)與居委會(huì)的初步比較[J].上海城市管理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3(01):21-25.
[4]郭榮茂,許斗斗.關(guān)注村改居后失地農(nóng)民就業(yè)保障問(wèn)題[J].發(fā)展研究,2007(03):110.
[5]藍(lán)宇蘊(yùn).都市里的村莊——一個(gè)“新村社共同體”的實(shí)地研究[M].北京:三聯(lián)書(shū)店,2005.
[6]唐亞林,陳先書(shū).社區(qū)自治:城市社會(huì)基層民主的復(fù)歸與張揚(yáng)[J].學(xué)術(shù)界,2003(03):15.
[7]鄧敏杰.創(chuàng)新社區(qū)[M].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出版社,2002.
[8]陳偉東,李雪萍.社區(qū)自組織的要素與價(jià)值[J].江漢論壇,2004(03):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