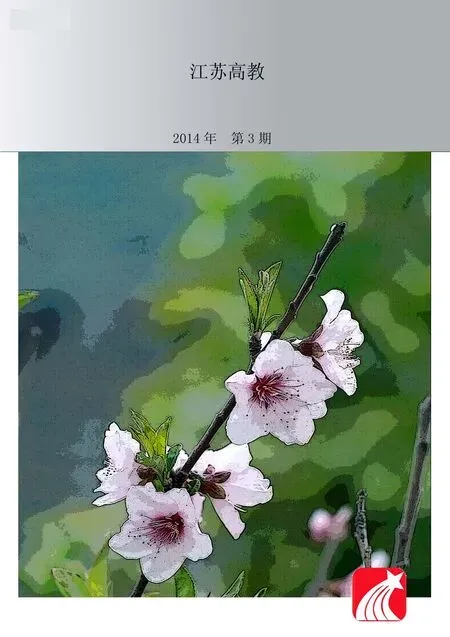大學學術權力運行的組織支持、現實困境與匡扶路徑
謝凌凌
(1.清華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北京 100084;2.廣西財經學院 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南寧 530003)
一般而言,學術權力表征的是學術權力中的組織權力,反映的是學術權力的組織表達強度和運行效能。我們關注的問題是,現實中學術權力的實然表達如何,有哪些組織支持模式?學術權力的組織表達強度又如何,它與行政權力之間的張力關系怎樣?這些問題目前還沒有一個系統的解釋和回答。有鑒于此,筆者認為,研究大學學術權力的運行內涵、組織支持模式及其強度與限度,對于全面把控學術權力運行特性和充分發揮學術權力的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一、大學學術權力運行的邏輯內涵及其組織支持模式
(一)學術權力運行的邏輯內涵
伯頓·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系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一書中認為,學術權力是“對學術事務決策、控制和統治的能力”,其中“誰統治高等教育”、“由誰來安排議程和由誰來告訴其它人做什么——決策”或“以某些方式支配他人”是關鍵[1]。一般而言,大學中的學術事務有兩種形式:學者獨立從事學術事務或在組織中從事學術事務。依此推演,大學學術權力運行的邏輯自然可歸結為學術權力的個體表達和學術權力的組織表達兩種方式。
所謂學術權力的個體表達,意指教師從事個體學術活動的權力,如自主決定教學內容、教授方式、自由選擇科學研究的領域和方向,以及在社會服務過程中自主決策的權力等[2]。而學術權力的組織表達則體現為教師從事學術管理過程中的權力,主要是通過民主的方式對學術事務進行集體決策的權力。這意味著,前文述及教師群體或者代表參與高校管理的權力在本質上表征的就是學術權力的組織表達。
(二)學術權力運行的組織支持模式
由于政治對教育的規制和滲透,中國高校內部學術事務的決策模式明顯呈現出政治視野中“行政組織決策和管理權力由若干人組成的委員會共同行使”的樣態,其按照少數服從多數或協調一致的原則集體決定、共同負責的組織體制高度契合委員制模式的運行特征。作為委員會制的學術權力架構通常也就具有了這種組織形式下的三種支持模式:
1.集權式學術權力組織支持模式。意指通過設置學術委員會來管理學校學術事務。這種組織形式使學術權力基本集中于學術委員會,例如,學科、專業的設置,教學、研究計劃的制定,相關學術事項的決策權都掌握在學術委員會手中。學術委員會對學術事務進行決策時,一般不進行垂直分權和水平分權,不單設分委員會機構,在最大限度上保證了形式簡單、命令統一、權責分明和溝通方便。不過由于學術委員會委員不一定全部且適時了解學校的一切工作,因此學術決策非全面性的缺點也相對凸顯。
2.分權式學術權力組織支持模式。主要依托行政組織設置校、院、系三級學術組織形式,共同分享學術權力[3]。學術權力在校級層面主要集中在校學術委員會,而處在亞科層的教務處、科技處等職能機構兼具行政管理性質和學術管理性質,通過相關的學術委員會提供決策咨詢;院系層次也設有相應的院學術委員會、學術小組和教研室等[4]。校級學術組織對院系學術組織進行指導,并對重大學術事務進行協調與決策。院、系學術組織分工負責各學科的學術事務,并對學術事務進行管理。校級學術委員會不干涉院系分委會的決定,而主要對其進行咨詢、指導與監督。
3.混合式學術權力組織支持模式。主要依據學術活動的類型或特點設置學術組織形式,混合行使學術權力。這些學術組織一般可分為審議機構和咨詢機構,兩者根據工作需要或獨立或混合行使學術權力。通常,審議機構包括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職稱評審委員會、學術機構設置評議委員會等組織,咨詢機構則包含學科專業建設委員會、教學指導委員會、師資隊伍建設委員會、實驗室建設委員會、圖書館工作委員會等部門。
二、大學學術權力運行的特點及困境

高校學術權力組織表達的部分類型、內涵及范圍
權力的運行可以理解為權力在行使過程中所能達到的最大范圍和所能發揮的最高效力,通常可通過權力的組織表達得以外化。在強度上由于其主要受權力主體作用和權力使用范圍的影響,一般可從弱到強劃分為咨詢(接洽商量)、審議(查閱討論)、審核(考察核定)、評議(評斷仲裁)、決定(規定確認)五個等級。在大學組織內部,學術權力的表達一方面體現出類似慣常權力運行的五種不同強度,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其與行政權力之間的特殊張力關系。歸根結底,乃源于高校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對峙統一,既相互牽制又彼此依存,雙方各自的權力表達形式和權力釋放強度共同決定著高校的治理模式,影響著高校內部治理結構的框架與趨勢。一般而言,學術權力的組織表達強度越高,行政權力的組織表達強度就低;反之,行政權力的組織表達強度越高,學術權力的組織表達強度就越低。除此之外,在學術權力的表達過程中,不同類別的學術權力表達組織具有不同強度的權力,其行使權力的具體內容和范圍也不盡相同。為了全面了解我國大學學術權力的組織表達狀況,本文選取一些高校中具有代表性的校級學術組織的內涵與職責進行歸納分析。
從表格中可以看出,當前語境下的中國高校學術權力,幾種學術組織在校級層面看似彼此平行,但相互之間并未顯示出清晰的職責邊界。例如,學術委員會是對學術事項進行審議、評議、論證和決策的最高學術權力機構,但其他幾類學術組織也各自擁有并獨立行使“審議”、“決策”、“指導”、“咨詢”等職能。加上未列入表中的諸如崗位設置委員會、學術道德建設委員會、教授評議會等名目繁多的學術組織,可謂五花八門錯綜復雜。這種積久弊生的狀況從上至下,一直延伸至院系二級或三級學術組織:
其一,從作用對象看,目標群體多元化導致學術權力運行范圍和界限不明確,學術權力運行呈分散、交叉趨向。學生、學術和學者作為大學學術權力的作用對象,各自有不同的目標追求和極為復雜的價值選擇。這些目標中,有臨時性的也有常規性的;有綜合性的也有專門性的,呈現出對象價值的多元化,以致學術權力在實際運行中常常出現誤判和失效。加之學術權力表達組織作為擔負大學學術管理職能的一個分系統,其目標的模糊性往往受制于大學組織目標的模糊性(李春梅,2005)。往復循環,這種縱橫交錯的目標需求不明朗最終強化了學術權力行使范圍和界限的模糊。從上表我們對相關高校章程的文本分析就可以看出,不少高校學術權力組織表達的目標定位混沌不清,校、院、系等眾多學術權力表達組織的職責權限費解不明,學術事務和行政事務經常攙雜糾纏,并在權力的行使過程中出現與行政權力交叉表達的現象。
其二,從系統構成看,組織結構復雜化導致學術權力運行過程產生一定重復性,學術權力運行呈重疊、分割狀態。盡管支持學術權力運行的學術組織類型都是根據學術工作的條塊來設置,但學術組織機構的職責和任務往往限定于學校的現實需求,缺乏整體聯動意識,處于分離零散狀態,各自為政,此消彼長。比如,表中顯示學術委員會的職責包括對學位進行評定、對教學質量進行監督、對學科專業進行建設等,幾乎涵蓋所有重要重大學術事項,這顯然與學位評定委員會、教學指導委員會和學科專業建設指導委員會等學術組織的職能與權力的表達存在多處交叉和重疊。如果強化學位評定委員會、教學指導委員會等學術組織的職能和權力,必然會分割校級學術委員會的職能和權力。換言之,支撐學術權力運行的咨詢、決策、執行、監督、反饋等系統并不“明確且各司其職”,以致于現實中學術權力的各表達組織設置重疊化、職能重復化、效能分割化的現象比比皆是,從而大大降低了學術權力的運行效率。
其三,從資源配置看,“精英控制”及“票決悖論”導致學術權力分配缺乏公平,學術權力運行呈虛化、失衡態勢。客觀而言,大學中從事教學科研的學者都可以視為學術權力的主體,學術權力也應賦予學術共同體中的每一個成員。然而在實際的權力運行過程中,“精英控制”在學術管理中有著重要影響。大學學術系統是一個金字塔式的結構,它注定只有少數而不是全部學術從業者能夠成為精英,這個由精英主導的學術系統體現了明顯的分化特征和分明的等級的結構。正如馬爾凱(Michael?Mulkay)所言:“在共同體內部成員間關于重要獎賞和設備設施條件的分配上,少數有特權成員間相互的社會紐帶聯系要比其他成員強大得多,而辨識這種特權成員的標準是他們對稀缺資源的控制,以及相互間的關系網絡;這些具有精英資格的人們有能力對他人的活動實施控制和引導,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未來精英的挑選”[5]。盡管大學中的學術組織大多在形式上以“票決制”的方式實現學術權力的表達,但是“票決制”存在著“非同行票決”的問題,尤其在一些重大學術事務的決策如教師招聘、崗位設置、職稱評審、學科專業建設等中,大多采取的是“大評委”制模式,意在從各個學科中遴選出具有較高學術聲望的教師作為代表參加“大評審”,對重大學術事務進行評議和決策,這直接導致了“非同行票決”,看似公平的“大評委”票決制實則成為學術權力分布不均衡的障眼法。換言之,在大學組織權力的縱向結構中,“上層”權力可以制約“下層”權力,一部分學者已掌握和履行學術組織中的公共權力,并逐步走向“制度化、合法化”。
其四,從表達強度看,行政化傾向導致學術權力運行偏離大學組織活動特性,學術權力運行呈弱化、依附特征。從上表中學術權力的表達內涵及范圍來看,體現“咨詢”、“審議”、“審核”職能的較多,彰顯“評議”、“決定”效能的較少,學術權力的組織表達強度明顯較低。實際上,在很多大學章程中,對學術組織的“評議”、“決定”等具有實質性學術權力表達強度的規定并沒有確切表述,很多規定僅體現“咨詢”、“討論”等低權力效力。現實中,通過“審核”、“評議”的學術事務幾乎難以“決定”,即便已經經過“決定”,也仍需上報校學術委員會“定音”;校學術委員會的“定音”能否“發聲”,最終還需要經過校長辦公會或者黨委會“裁奪”,權力的最終落腳點依然在上級行政組織。如果說這是學術組織的行政化傾向,那么組織中的“主體”也同樣如此:很多高校的學術委員會成員都具有行政實職職務,一些高校甚至“發文”規定二級院系的黨政領導自然成為校級學術組織的成員,沒有行政職務的學術人員實際上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學術組織及其主體的行政化在一定程度上阻滯了學術權力表達的民主性、獨立性和自由性,導致學術權力難以按照自身規律健康運行。
三、匡扶大學學術權力持續健康運行的路徑選擇
與其他組織一樣,大學學術組織的生命力也在于職、責、權的有機統一。通過完善制度保障、構建學術體系、明確行使邊界、給予文化支持以形成穩定開放的學術生態系統,是匡扶大學學術權力健康運行的重要路徑選擇。
(一)以法規制度為保障,明確學術組織(主體)的獨立性及學術權力運行的有效性。盡管現行的《高等教育法》、高校章程對大學學術機構、學術人員參與或決策學術事項作了相關規定,但這些規定明顯剛性不足。比如,沒有具體規定校、院(系)兩級學術委員會應如何組成,沒有對學術委員會的產生辦法,學術委員會委員的任職資格、任期、增補等作強制性法律規定,因此高校在校級學術委員會的成員構成、程序安排、內容設定等方面往往具有相當自由且寬泛的裁量權,行政權力擠占學術權力的情況常有發生。追根溯源,必須要通過法律法規的制度設計來確立和規范學術權力行使的地位和邊界,制定詳細的保障學術權力表達的法律條款,尤其是要具體規定權力行使的操作程序和方式方法,以增強法律的適用性,并對權力表達的主體對象、運行程序、職責權限等做出明確具體的規定,進而提高學術權力的效力強度。在具體操作層面,可酌情適當修訂《高等教育法》或制定專門的《大學法》,又或完善高校章程的實施細則等,通過法規制度來確保學術主體的真實學術權力,理順學術權力表達組織的層次關系,強化學術組織對學術事務的決策權,真正建立起學術本位的高校內部治理結構。
(二)構建以學科為基礎、以研究為主導、以學術為本位的基層學術組織體系。伯頓·克拉克曾就大學作為知識任務中心的事實指出,“學科和院校的聯系方式都會聚在基層操作單位。學系、講座或研究所既是學科的一部分,也是院校的一部分,它們將兩者合而為一,并從這種結合中汲取力量。這種結合使得操作部門既能顯示出強大的勢力,又能成為系統的核心。”[6]換言之,探索建立多樣化的基層學術組織不僅能夠順應大學發展的學術責任和學者們的信念追求,更重要的是能夠通過組織表達來優化權力的資源配置,促進學術權力的持續、健康運行。構建完備的高校基層學術組織體系,可以使基層學術組織置于院(系)之下,成為集人、財、物為一體的實體機構,并享有一定的資源配置權、處事權及裁量權,同時明確基層學術組織負責人的責、權、利及聘用與考核辦法;保持基層學術組織結構的彈性,使不同的基層學術組織可以基于不同目標組建不同的研究基地、平臺、實驗室和跨學科的研究中心;引入績效管理的理念以規避基層學術組織資源分散、資源浪費、效率低下等阻礙學科發展的深層次問題。通過釋放基層學術組織的活力,促進高校治理重心的下移,不僅有利于高校治理結構的調整,而且能夠從根本上凸顯學術權力在高校治理中的地位及效能。
(三)厘清學術組織的表達邊界,確保學術權力的運行強度。大學是以學科為基礎的一種典型的松散結合體組織,學術組織的復雜性和差異度決定了學術管理的多樣性和靈活性。因此,明晰學術權力的表達邊界有助于增強學術組織的地位、權威及其運行強度。如果權力表達的主體主要集中在某一權力表達組織而弱化其他學術組織的權力,不但會使決策結果缺少全盤籌劃,而且會造成學校管理中的相互扯皮現象,難以處理好各系科、各專業之間的關系,也必然會使學校的學術管理處于進退維谷的境地,從而難以提高學術管理的質量和效率(顏丙峰,2004)。在前文表格的分析中,多種學術組織的表達目標及范圍的重復與交叉就很好地說明了學術組織內部間的表達邊界問題。實際上,在當前大學組織體系中更重要的是要區分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各自運行邊界,應該通過明確這兩種權力的各自表達范疇,形成一種分工、協作與互補制約的關系。正如有學者提出行政權力需嚴格遵守“法制邊界、專業邊界和價值邊界”[7]一樣,也應區分學術組織在不同表達邊界下的運行效能,以增強其實際運行強度。比如,對專業化程度較高的學術事務,行政權力應體現出為增強學術權力組織表達強度“保駕護航”的姿態,除了確保學術組織具有咨詢、評議等職能,更要賦予其決策職能,促使各級學術組織在其合理的權力表達邊界中變成真正的學術咨詢、評議和決策機構,通過法規制度和權力讓渡等多種方式確保學術組織的獨立性及其學術事務決策力,以不斷增強學術權力的運行強度。
(四)形成學術權力的組織文化支持機制,增強學術權力組織表達的內在張力。為了使各類學術權力組織在系統構成及其資源配置間達成平衡,特別是在權力的決策、執行和監督上達致均衡,需要保持學術權力組織之間必要的張力,形成學術權力運行過程中的“彈性效應”,最終凝結為學術組織的“權力合力”。比如,可以整合學校的各類型學術組織,建立一個核心的、權威的主體學術組織機構,更好地發揮整體聯動的效應。由于學校學術組織的復雜性及多樣性,校、院、系學術組織要整合成一個強大的學術權力表達系統,需要構建一種規范體系及文化認知框架,以減少組織間的“內耗”。這種文化支持機制應該以規范學術權力運行的目標、價值、路徑為導向,比如公開透明的會議式運作,非“精英控制”的民主選舉,非利益性的一人一票式民主決策,自下而上的意見整合、靈活多樣的非正式溝通、獨立性的網絡化監督,以學術為唯一標準的專業評判等。著力推動大學組織文化內核由科層文化向學術文化轉變,使學術權力的運行能夠獲得健康持續的組織文化支持。
[1]伯頓·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M].王承緒,等譯.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120-123.
[2]Mary Henkel.Academic identity and autonomy in a changing policy environment[J].Higher Education,2005,(49):155 -176.
[3]葉飛帆.大學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分離:三級組織二級管理模式[J].教育研究,2011,(2):64 -68.
[4]李 雯.論我國高等學校組織內部權力問題[D].西安:陜西師范大學,2007:22.
[5]Mulkay Michael.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scientific elite[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6(3/4),Special Issue:Aspects of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Papers from a Conference,University of York,UK 16 - 18 September 1975(Sep.,1976):445 -470.
[6]伯頓·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統— —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M].王承緒,等,譯.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124,37.
[7]龍 耀.論教育行政權力的邊界——基中國高等教育行政化問題的研究[J].中國高教研究,2011,(6):43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