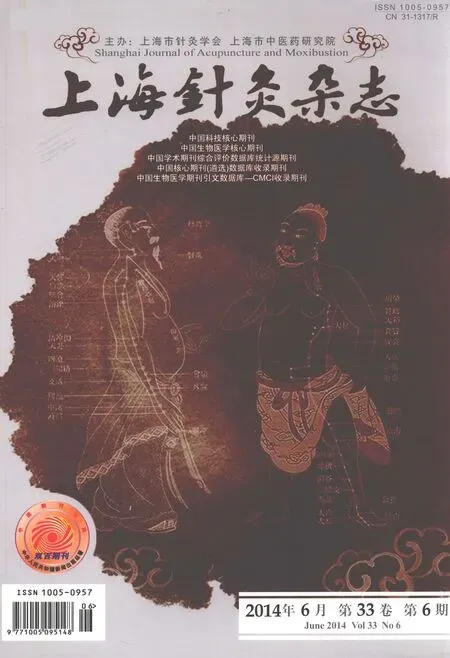經(jīng)絡(luò)切診發(fā)展概況及展望
龍杞,王詩(shī)惠,劉清國(guó)
(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針灸推拿學(xué)院,北京 100029)
經(jīng)絡(luò)切診是指醫(yī)生在經(jīng)絡(luò)理論指導(dǎo)下,運(yùn)用手指指腹以適當(dāng)?shù)牧Χ葘?duì)相應(yīng)的經(jīng)絡(luò)循行之體表部位和腧穴所在處進(jìn)行觸摸、循按、推運(yùn),以感覺(jué)患者的異常變化,如皮膚的溫度和濕度變化或者隆起、凹陷,皮下結(jié)節(jié)、條索等陽(yáng)性反應(yīng)物,軟組織的軟硬度、拘攣、壓痛等,進(jìn)而確定疾病的病位、病性的辨證方法[1]。
經(jīng)絡(luò)切診是醫(yī)生了解患者經(jīng)、穴狀況最直接的手段,具有較大的深入研究?jī)r(jià)值和改進(jìn)空間,現(xiàn)對(duì)其作簡(jiǎn)單梳理如下。
1 理論基礎(chǔ)
人體的五臟六腑、四肢九竅通過(guò)經(jīng)絡(luò)聯(lián)屬而形成一個(gè)有機(jī)整體。當(dāng)機(jī)體內(nèi)部發(fā)生病變時(shí),可在相應(yīng)的經(jīng)絡(luò)上出現(xiàn)各種異常反應(yīng)[2]。反之,醫(yī)生可通過(guò)診察體表相關(guān)經(jīng)絡(luò)、腧穴的異常變化對(duì)機(jī)體內(nèi)部的疾病進(jìn)行診斷。正如《靈樞·海論》:“夫十二經(jīng)脈者,內(nèi)屬于府藏,外絡(luò)于肢節(jié)。”
針灸是直接刺激經(jīng)脈腧穴的治療方法,病邪的多少,氣血的盛衰,臟腑經(jīng)脈的相互聯(lián)系和影響,各人秉賦的不同,使得疾病在經(jīng)脈穴位上的反應(yīng)不盡相同,因此對(duì)相應(yīng)經(jīng)絡(luò)、腧穴的診察必不可少。就切診而言,“獨(dú)取寸口”對(duì)于針灸臨床顯然遠(yuǎn)遠(yuǎn)不夠,必須運(yùn)用《黃帝內(nèi)經(jīng)》所強(qiáng)調(diào)的“全身遍診”進(jìn)行診斷。
1.1 古代典籍論述
對(duì)經(jīng)絡(luò)切診論述最多、最早的是《黃帝內(nèi)經(jīng)》。《靈樞·九針十二原》[3]:“五臟有疾也,應(yīng)出十二原。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睹其應(yīng),而知五臟之害矣。”《素問(wèn)·繆刺論》[4]:“凡刺之?dāng)?shù),先視其經(jīng)脈,切而從之,審其虛實(shí)而調(diào)之。”《靈樞·官能》:“查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溫,何經(jīng)所在。”《靈樞·刺節(jié)真邪》:“用針者,必先察其經(jīng)絡(luò)之實(shí)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yīng)動(dòng)者,乃后取之而下之。”《靈樞·經(jīng)水》:“審、切、循、捫、按,視其寒溫盛衰而調(diào)之。”
《黃帝內(nèi)經(jīng)》通過(guò)反復(fù)論述,高度強(qiáng)調(diào)了經(jīng)絡(luò)切診在針灸治療中不容忽視的地位,認(rèn)為經(jīng)絡(luò)切診是審查邪正盛衰、辨別疾病性質(zhì)、明確病位以及疾病與臟腑間關(guān)系的基本方法,是進(jìn)行針刺前必不可少的前提。《黃帝內(nèi)經(jīng)》所載審、切、循、按、捫等主要診查方法一直沿用至今[5]。
1.2 歷代醫(yī)家論述
此后歷代醫(yī)家在《黃帝內(nèi)經(jīng)》基礎(chǔ)上,對(duì)經(jīng)絡(luò)切診提出自己的認(rèn)識(shí),對(duì)經(jīng)絡(luò)切診的診察思路和方法有不同程度的補(bǔ)充和發(fā)揮。
唐代醫(yī)家孫思邈《千金方·卷二十九·灸例》[6]:“有阿是之法,言人有病痛,即令捏其上,若里當(dāng)其處,不問(wèn)孔穴,即得便快或痛處,即云阿是,灸刺皆驗(yàn),故曰阿是穴也。”可見(jiàn),阿是穴是疾病的反應(yīng)點(diǎn),當(dāng)人體生病時(shí),醫(yī)生用切壓的方法進(jìn)行診察,患者感到疼痛或舒適的部位就是阿是穴。而“阿是之法”就是指運(yùn)用經(jīng)絡(luò)切診等方法尋找特異性敏感穴位,從而指導(dǎo)選穴的方法[7]。“阿是穴”及“阿是之法”的提出是對(duì)《內(nèi)經(jīng)》經(jīng)絡(luò)切診理論的繼承與發(fā)揮,至今仍對(duì)臨床有指導(dǎo)意義。
明代著名醫(yī)家張景岳認(rèn)為經(jīng)絡(luò)切診可診查“周身之病”,《類(lèi)經(jīng)》[8]:“臟腑在內(nèi),經(jīng)絡(luò)在外,臟腑為里,經(jīng)絡(luò)為表……故可按之以察周身之病。”汪機(jī)在《針灸問(wèn)對(duì)》[9]中說(shuō):“《素》、《難》所論針灸,必須察脈以審其在經(jīng)在絡(luò),又須候氣以察其邪之已至未來(lái)。”“察脈盛衰,以知病在何經(jīng),乃可隨病以施針刺也。”對(duì)經(jīng)絡(luò)切診的高度重視,可見(jiàn)一斑。他還對(duì)當(dāng)時(shí)人們不重視經(jīng)絡(luò)切診的現(xiàn)象進(jìn)行了抨擊:“世之專(zhuān)針科者,既不識(shí)脈,又不察形,但問(wèn)何病,便針何穴,以致誤針成病疾者有也。”
1.3 現(xiàn)代科學(xué)研究印證
20世紀(jì)50年代,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廣泛探討了內(nèi)臟疾病時(shí)在表出現(xiàn)的特異性反應(yīng),經(jīng)過(guò)大量的臨床和實(shí)驗(yàn)研究,提出了經(jīng)穴-臟腑相關(guān)理論[10]。該理論認(rèn)為經(jīng)脈穴位與臟腑間存在雙向聯(lián)系,即臟腑生理病理改變可通過(guò)多種形式反映到體表相應(yīng)經(jīng)絡(luò)、穴位上,而診查、刺激體表經(jīng)絡(luò)和穴位又可診治相應(yīng)臟腑的疾病。劉澄中[11]對(duì)循經(jīng)性疼痛和異樣感現(xiàn)象作了大量研究,以證實(shí)古人論述的循經(jīng)癥候群客觀存在。張軍等[12]認(rèn)為各種疾病在一定程度上,均可以通過(guò)麻感或痛敏的形式反映在體表經(jīng)線(xiàn)上。經(jīng)穴-臟腑相關(guān)理論從實(shí)驗(yàn)研究的層面為經(jīng)絡(luò)切診提供了理論支持和科學(xué)依據(jù)。
2 現(xiàn)代臨床應(yīng)用概況
2.1 診斷疾病
某些體表經(jīng)、穴的異常反應(yīng)往往對(duì)相應(yīng)的疾病有診斷意義。有學(xué)者通過(guò)大量研究發(fā)現(xiàn),運(yùn)用經(jīng)絡(luò)切診尋找異常反應(yīng)點(diǎn)診斷內(nèi)臟疾病具有較高的檢出率和可靠性。對(duì)于某些癥狀不明顯的早期患者,其診斷價(jià)值更顯重大。
蓋國(guó)才[13]依據(jù)經(jīng)絡(luò)理論,探索了現(xiàn)代病與中醫(yī)穴位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總結(jié)了一套比較完善的“定位穴”和“定性穴”,經(jīng)過(guò)篩查和驗(yàn)證,在人體穴位中確定了195種常見(jiàn)病的配穴,創(chuàng)立了“穴位診斷法”。并且運(yùn)用這一方法,經(jīng)過(guò)大量臨床試驗(yàn)發(fā)現(xiàn),新大郄穴(承扶、委中中點(diǎn)向外5分,再下5分)和新內(nèi)郄穴(承扶、委中中點(diǎn)向內(nèi)5分,再下5分)壓痛明顯時(shí),提示患有腫瘤[14]。曲生健等[15]對(duì)183例以腹部病痛為主癥的患者以足三里、條口、上巨虛、下巨虛、陰谷、陽(yáng)陵泉、委陽(yáng)、三陰交等為基礎(chǔ)穴位,循經(jīng)尋找并記錄壓痛敏感點(diǎn)。結(jié)果,診斷符合率為95.1%。吳秀錦[16]通過(guò)經(jīng)絡(luò)切診發(fā)現(xiàn),疾病的輕重與相關(guān)穴位的壓痛和穴位下面出現(xiàn)的陽(yáng)性反應(yīng)物有平行關(guān)系。朱豫人[17]在臨床診療神經(jīng)衰弱時(shí)發(fā)現(xiàn),四診八綱辨證結(jié)合壓痛點(diǎn)進(jìn)行診斷并靈活辨證治療其效果是特別令人滿(mǎn)意的。毛品恕[18]利用經(jīng)穴壓痛診斷法對(duì)急性上頜竇炎進(jìn)行診斷,發(fā)現(xiàn)28個(gè)病例的壓痛點(diǎn)均能被檢查出來(lái)。孫國(guó)杰等[19]報(bào)道,十二指腸潰瘍病患者其中脘、右梁門(mén)和右胃?jìng)}旁開(kāi)2寸處均有明顯壓痛,觀察109例,有107例與X線(xiàn)診斷相符。鄒賢德等[20]對(duì)120例患者進(jìn)行了按壓膽俞穴對(duì)膽道疾病的臨床診斷觀察,得出凡屬膽道疾病,膽俞穴都有明顯壓痛的結(jié)論。奔卉等[21]觀察了22例胃潰瘍、21例胃炎患者相關(guān)體表反射區(qū)敏感點(diǎn)與疾病的關(guān)系,結(jié)果胃潰瘍組患者壓痛點(diǎn)及敏感點(diǎn)主要集中在腹部足陽(yáng)明胃經(jīng)的不容、梁門(mén)、滑肉門(mén)段,及背部的脾俞、胃俞、胃?jìng)}區(qū)域。陳文光等[22]報(bào)道在足陽(yáng)明胃經(jīng)上發(fā)現(xiàn)冠心病敏感點(diǎn)。并對(duì)臨床70例心絞痛患者對(duì)照心電圖進(jìn)行沖陽(yáng)下穴對(duì)冠心病診斷和治療的觀察。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對(duì)于癥狀不明顯的早期冠心病患者,沖陽(yáng)下穴的診斷率明顯高于心電圖且比其他穴位具有特異性,對(duì)冠心病的診斷具有一定的價(jià)值。
不僅如此,經(jīng)絡(luò)異常反應(yīng)的不同表現(xiàn),對(duì)疾病性質(zhì)、病情輕重亦有一定提示作用。例如肝陽(yáng)上亢的頭痛,常在太陽(yáng)、頭維、率谷等穴處出現(xiàn)血絡(luò)怒張、隆起、跳動(dòng)加強(qiáng)的現(xiàn)象,這是實(shí)則必現(xiàn)的反應(yīng),而久瀉久痢的患者,不但寸口脈沉伏細(xì)微,按之難及,甚至全身絡(luò)脈都不易尋找,這是虛則必下的結(jié)果[23]。姚軍等[24]在對(duì)癭病經(jīng)絡(luò)診察的臨床研究中發(fā)現(xiàn),結(jié)節(jié)、條索物柔軟不痛為虛,結(jié)節(jié)、條索物硬脹壓痛為實(shí);酸脹麻木多為虛;郄穴反應(yīng)多為實(shí),原穴反應(yīng)多為虛。閻冬梅[25]對(duì)變形性膝關(guān)節(jié)炎患者進(jìn)行壓痛點(diǎn)觀察分析發(fā)現(xiàn),變形性膝關(guān)節(jié)炎的壓痛點(diǎn)具有遠(yuǎn)離病灶的特征,壓痛點(diǎn)的數(shù)量、閾值與病變輕重程度有關(guān)。祝總驤等[26]報(bào)道對(duì)475例胃、肝、肺、腸、心及腎病的患者進(jìn)行了穴位檢查,穴位反應(yīng)隨病情的轉(zhuǎn)化而變化,病愈時(shí)則反應(yīng)消失。
2.2 指導(dǎo)治療
經(jīng)絡(luò)切診中出現(xiàn)的異常反應(yīng)點(diǎn)往往是治療的關(guān)鍵點(diǎn),有時(shí)運(yùn)用常規(guī)取穴療效甚微時(shí)通過(guò)經(jīng)絡(luò)切診尋找異常反應(yīng)點(diǎn),對(duì)其或按壓、或針刺、或艾灸通常會(huì)有立竿見(jiàn)影的效果。黃聰陽(yáng)[27]治療緊張性頭暈頭痛癥,在頭部循經(jīng)按壓、循摩,以指下的筋結(jié)、條索狀物或產(chǎn)生的麻痛感為陽(yáng)性反應(yīng)點(diǎn)進(jìn)行針刺治療,總有效率為96.1%。曲衍海在治療肩痹以肩部最敏感的痛點(diǎn)或索狀攣急反應(yīng)物作為針刺部位,收到良效[28]。楊光福等[29]對(duì)70例中風(fēng)患者采取辨病中何經(jīng)而選穴,觀癥所在而配穴,突破固守某經(jīng)某穴的方法,在降低病殘率方面取得良效,總有效率為95.7%。戴文軍等[30]治療肩周炎局部選穴可在肩背部尋找壓痛點(diǎn)或肩關(guān)節(jié)周?chē)⑹茄?或是在上臂活動(dòng)時(shí)尋找最痛點(diǎn),均具有非常好的療效。郭長(zhǎng)青等[31]大致總結(jié)了經(jīng)筋病中“阿是穴”多分布在肌肉、韌帶等軟組織的應(yīng)力集中點(diǎn),人體功能活動(dòng)的應(yīng)力集中點(diǎn)等處,對(duì)這些點(diǎn)進(jìn)行相應(yīng)治療,每取得滿(mǎn)意療效。陳子富[32]曾于常規(guī)取穴治療牙痛效果不理想的情況下,運(yùn)用經(jīng)穴壓痛診斷手法,按得患者厥陰俞痛點(diǎn),刺之立刻見(jiàn)效,乃知此心主代神明之府而行令所致也。
2.3 預(yù)防針刺意外
通過(guò)切診可以確切知道病變組織在骨、在筋、在肉或在皮,而在針刺時(shí)能夠深淺適宜,防止針刺意外的發(fā)生,做到“刺皮無(wú)傷肉,刺肉無(wú)傷脈,刺脈無(wú)傷筋,刺筋無(wú)傷骨”。
2.4 總結(jié)經(jīng)驗(yàn)穴
通過(guò)循經(jīng)診查找到的非穴反應(yīng)點(diǎn)若經(jīng)過(guò)大量臨床驗(yàn)證確有實(shí)效則成為實(shí)用的經(jīng)驗(yàn)穴,在一定意義上拓寬了選穴范圍,豐富了治療手段。如陳文光等總結(jié)的治療冠心病的經(jīng)驗(yàn)穴“沖陽(yáng)下穴”,蓋國(guó)才總結(jié)的對(duì)腫瘤有特異性診斷作用的“新大郄穴”、“新內(nèi)郄穴”等。
3 思考與展望
3.1 研究現(xiàn)狀及問(wèn)題
綜觀經(jīng)絡(luò)切診的研究現(xiàn)狀,可以看出目前經(jīng)絡(luò)切診的發(fā)展主要受以下 3方面因素的束縛。首先,檢測(cè)指標(biāo)沒(méi)有客觀量化依據(jù),不夠科學(xué)、客觀[33],如蓋國(guó)才的“穴位壓痛診斷法”對(duì)壓痛點(diǎn)疼痛級(jí)別的量化標(biāo)準(zhǔn)為,一般壓痛“﹢”,明顯壓痛“﹢﹢”,有皺眉、呼痛“﹢﹢﹢”,疼痛拒按者“﹢﹢﹢﹢”,這種量化標(biāo)準(zhǔn)受醫(yī)生的判別經(jīng)驗(yàn)及感覺(jué),患者的體質(zhì)、敏感程度等諸多主觀因素影響較大,缺乏信度。并且由于判別標(biāo)準(zhǔn)的模糊性和主觀性,往往造成疾病辨證方面的分歧,同時(shí)給中醫(yī)學(xué)的教學(xué)工作也帶來(lái)了很大的困難[34];其次,研究過(guò)程中干擾因素(如職業(yè)等)的控制不夠好、樣本量不夠大等,數(shù)據(jù)及結(jié)論的說(shuō)服力不足,如奔卉等對(duì)胃潰瘍和胃炎患者皮膚壓痛閾及體表敏感點(diǎn)的觀察。最后,不容忽視的是,如今臨床醫(yī)生及科學(xué)工作者對(duì)經(jīng)絡(luò)切診的重視程度日顯淡化的趨勢(shì)。臨床方面,有的針灸醫(yī)生重治療、輕診斷,將中醫(yī)診斷置于可有可無(wú)的境地,有針灸治療簡(jiǎn)單化的傾向[35]。理論研究方面,檢索文獻(xiàn)不難發(fā)現(xiàn),對(duì)于穴位診斷法的報(bào)道只有十余篇,近10年來(lái)的文獻(xiàn)僅8篇。本法研究力量之薄弱顯而易見(jiàn),現(xiàn)狀不容樂(lè)觀。
3.2 改進(jìn)方法
針對(duì)上述問(wèn)題,筆者認(rèn)為可從以下幾個(gè)方面探索改進(jìn)。第一,改進(jìn)測(cè)試方法,建立客觀的量化標(biāo)準(zhǔn)。借助現(xiàn)代科學(xué)相關(guān)概念、技術(shù)、儀器(如壓痛閾[36]、信息熵、溫度測(cè)試儀[37]等),進(jìn)行系統(tǒng)化、大樣本的臨床現(xiàn)象觀察研究,提高傳統(tǒng)經(jīng)絡(luò)切診的信度和效度,對(duì)經(jīng)典著作中的論述在驗(yàn)證繼承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完善和發(fā)展。第二,經(jīng)絡(luò)切診主要用于針灸臨床對(duì)疾病的初步診察,對(duì)于進(jìn)一步確定該疾病性質(zhì)類(lèi)別,仍需借助現(xiàn)代診察方法。第三,本法可與其他診斷手法共同使用,在拓寬其臨床運(yùn)用范圍的同時(shí),使得其信度也有所提高。
4 結(jié)語(yǔ)
綜上所述,經(jīng)絡(luò)系統(tǒng)構(gòu)成復(fù)雜網(wǎng)絡(luò)[38],經(jīng)絡(luò)切診是將傳統(tǒng)經(jīng)絡(luò)理論運(yùn)用于針灸臨床的重要體現(xiàn),也是聯(lián)系現(xiàn)代解剖知識(shí)與中醫(yī)傳統(tǒng)經(jīng)絡(luò)理論的重要橋梁。長(zhǎng)期的針灸臨床實(shí)踐證明,經(jīng)絡(luò)切診有著不可替代的臨床價(jià)值。然而挑戰(zhàn)與機(jī)遇同在,由于缺乏客觀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及大樣本研究,其臨床普及嚴(yán)重受制,若能結(jié)合現(xiàn)代科學(xué)的相關(guān)概念和方法開(kāi)展大樣本系統(tǒng)化的深入研究,相信經(jīng)絡(luò)切診將更好地服務(wù)于臨床。
[1]田麗芳,田陽(yáng)春.經(jīng)絡(luò)切診在針灸臨床中的應(yīng)用[J].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3,26(5):87-封3.
[2]黃建軍.經(jīng)絡(luò)腧穴學(xué)[M].北京:中國(guó)中醫(yī)藥出版社,2011:18.
[3]靈樞經(jīng)[M].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05:3.
[4]黃帝內(nèi)經(jīng)素問(wèn)[M].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05:124.
[5]徐振華,符文彬,劉建華.《內(nèi)經(jīng)》經(jīng)絡(luò)診察體系及臨床應(yīng)用[J].江西中醫(yī)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7,19(2):46-48.
[6]孫思邈撰,高文柱,沈澎農(nóng)校注.備急千金要方[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332.
[7]田麗芳,田陽(yáng)春.論阿是穴與阿是之法[J].中國(guó)針灸,2003,23(12):756.
[8]張介賓.類(lèi)經(jīng)[M].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1965:43..
[9]汪機(jī).針灸問(wèn)對(duì)[M].江蘇:江蘇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1981:6.
[10]張露芬.實(shí)驗(yàn)針灸學(xué)[M].北京:化學(xué)工業(yè)出版社,2010:45.
[11]劉澄中.循經(jīng)性疼痛與循經(jīng)性異感[C].全國(guó)針灸針麻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論文摘要,1979:243.
[12]張軍,李定忠.論體表-內(nèi)臟相關(guān)性與經(jīng)絡(luò)的聯(lián)系[J].中國(guó)針灸,1995,15(2):27.
[13]蓋國(guó)才.穴位診斷法發(fā)展概況[C].第二屆全國(guó)針灸針麻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論文摘要,1984:175.
[14]蓋國(guó)才.中國(guó)穴位診斷學(xué)[M].北京:學(xué)苑出版社,1997:52-55.
[15]曲生健,呂美珍,王秋月,等.對(duì)曲衍海經(jīng)絡(luò)腧穴診斷經(jīng)驗(yàn)的臨床觀察[J].針灸臨床雜志,2011,27(7):75-77.
[16]吳秀錦.內(nèi)臟體表聯(lián)系的觀察——136例胃、肝疾病的穴位反應(yīng)[J].廣東醫(yī)藥資料,1979,17(2):46-49.
[17]朱豫人.經(jīng)穴壓痛點(diǎn)對(duì)神經(jīng)衰弱的診斷與治療[J].黑龍江醫(yī)刊,1959,2(7):60-62.
[18]毛品恕.經(jīng)穴壓痛法診斷急性上頜竇炎[J].山東醫(yī)刊,1958,2(8):27-31.
[19]孫國(guó)杰,盛燦若,嚴(yán)潔.針灸學(xué)[M].上海:上海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1997:36.
[20]鄒賢德,周世珍,周興祥.壓膽俞穴對(duì)膽道病的臨床診斷觀察[J].四川中醫(yī),1995,14(9):53.
[21]賁卉,榮培晶,李亮,等.胃潰瘍和胃炎患者皮膚壓痛閾及體表敏感點(diǎn)的觀察[J].上海針灸雜志,2012,31(2):128-130.
[22]陳文光,王端義,張?chǎng)稳A.冠心病與足陽(yáng)明胃[J].山東中醫(yī)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80,11(4):17-19.
[23]李敏,賴(lài)新生,徐國(guó)峰.論切診與針灸療法[J].中國(guó)針灸,2004,24(6):443.
[24]姚軍,王居易,楊會(huì)道.中醫(yī)癭病經(jīng)絡(luò)診察的臨床研究[J].中國(guó)針灸,2000,20(10):607-613.
[25]閻冬梅.針灸壓痛點(diǎn)治療變形性膝關(guān)節(jié)炎[J].國(guó)外醫(yī)學(xué):中醫(yī)中藥分冊(cè),2003,25(5):286-287.
[26]祝總驤,郝金凱.針灸經(jīng)絡(luò)生物物理學(xué)[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189.
[27]黃聰陽(yáng).經(jīng)絡(luò)切診與針刺治療緊張性頭暈頭痛癥 26例[J].中國(guó)針灸,1998,18(11):674.
[28]解樂(lè)業(yè).曲衍海針刺治療肩痹的經(jīng)驗(yàn)[J].山東中醫(yī)雜志,1993,12(3):51-52.
[29]楊光福,盧智,魏風(fēng)菊,等.辨經(jīng)論治治療中風(fēng) 70例療效觀察[J].中國(guó)針灸,1997,17(7):437.
[30]戴文軍,葉小雯,李蘭錚.穴位注射結(jié)合溫針治療肩關(guān)節(jié)周?chē)?60例療效觀察[J].新中醫(yī),2002,34(5):45-46.
[31]郭長(zhǎng)青,劉乃剛.經(jīng)筋病阿是穴分布特點(diǎn)探析[J].中國(guó)中醫(yī)基礎(chǔ)醫(yī)學(xué)雜志,2011,17(8):899-900.
[32]陳子富.經(jīng)絡(luò)切診驗(yàn)例五則[J].北京中醫(yī)雜志,1985,4(1):51-52.
[33]施誠(chéng).現(xiàn)代化、系統(tǒng)化、客觀化、規(guī)范化是中醫(yī)與針灸走向世界的基石[J].甘肅中醫(yī),1994,7(4):16-20.
[34]劉保延.關(guān)于建立針灸臨床診斷及療效評(píng)價(jià)體系的思考[J].中國(guó)針灸,2004,24(4):223-225.
[35]沙巖.提高針灸臨床診斷水平的重要性及其方法的思考[J].中國(guó)針灸,2007,27(9):691-694.
[36]王寧華,張傳漢,南登崑.實(shí)驗(yàn)痛評(píng)測(cè)方法之一:壓痛閾[J].國(guó)外醫(yī)學(xué):物理醫(yī)學(xué)與康復(fù)學(xué)分冊(cè),2004,24(3):97-98,105.
[37]佘延芬,宋佳杉,朱江.穴位體表溫度研究進(jìn)展評(píng)述[J].針灸臨床雜志,2010,26(10):73-76.
[38]Zhang C, Yang L, Yang WB, et al. Preliminary properties of meridian system as a complex network[J]. J Acupunct Tuina Sci, 2008,6(5):3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