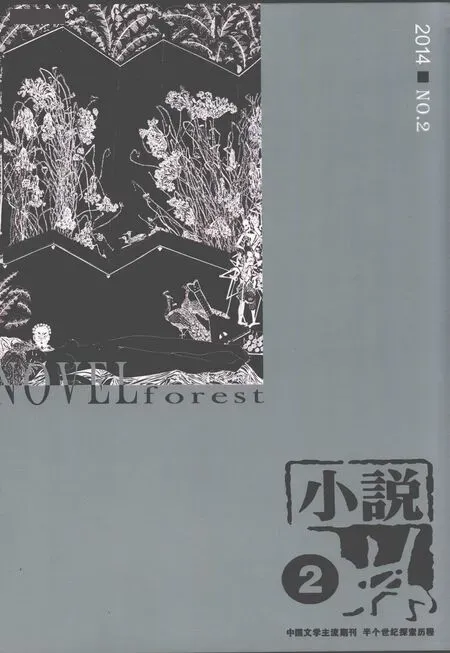田埂上的小提琴家
◎林苑中
田埂上的小提琴家
◎林苑中
0、寫在前面的話
這是我寫作的篇什里相對比較奇怪的一篇,它由自序、再版序、日文版序以及修訂版序言組成,分別由小說家董欣賓自己、《安宜日報》副刊主編、評論家劉長風以及老年的董欣賓來完成,修訂版序言則是董欣賓的女兒寫就,這篇小說最后一個部件就是一個以年代為線索的簡譜。如此小說的組件意圖主要是想從故事外圍去包抄故事的核心。這樣的嘗試帶給我的樂趣是有的。這使我想起小時候,奶奶將我襯衣上虱子捉到放在我的拇指甲蓋上,奶奶教我用兩個拇指甲蓋互相擠壓,會迸發出咯嗒一聲脆響出來。
1、自序
如果冬不拉先生還健在的話,他絕對是這篇序言的不二人選。他是一個奇才,通曉多國語言,風度翩翩,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一個私營小書店里,他當時坐在一個藤椅上翻看一本魯迅先生的小說。他時而低頭翻書,書頁在日光里嘩啦嘩啦響,時而抬頭跟在一旁的書店小老板說上幾句。我喜歡上他翻書和評點書的態度,他定是一個極度喜愛書的人。從他將被讀者翻看時折起的書頁理平可以看出,書店里經常有一些人站在書架前取下翻看,然后折疊做個記號,下次再來時可以接著看下去。書店是老字號了,老字號的好處就在于它具備了洞悉讀者的智慧,任由讀者取閱。有一種云卷云舒的瀟灑姿態,因此我是那兒的常客。聊了幾句,便熟悉起來。冬不拉先生曾經在湖南工作,現在是告老還鄉。曬曬太陽,翻翻書,拿他的話來說,自是愜意的逍遙日子。他眉長,眼睛一點兒不像一個年近古稀之年的人。我后來想,之所以他后來一直令我難忘,主要是他的那雙眼睛:清澈見底。之所以我能得出他風度翩翩的印象,也完全來自他的這雙眼睛。我對他的了解僅僅就是書店老板的偶爾提及,和我的幾次有限的觀察,而這個從某種程度上點燃了我想象的熱情。對一個人的一生激烈地去想象,填充,豐滿,那將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雖然我最初的寫作熱情并不是源于此,但是他卻能使我想象的翅膀由薄翼變成廣赤一片,并且能感受到這個變化的激動人心,可以說這部小說正是一個有力的佐證。冬不拉經歷坎坷,豐富,復雜。他的家庭在我們縣可以算上大族人家,北門街幾乎大半邊街都屬于他輝煌的祖上。雖然祖上留的基業后來只剩下區區幾間,但是人家輝煌歷史是不能淡忘的。他大概偶爾跟書店老板說過,書店老板自然和我多了些談資。有段時間我因為忙著結婚所以去的少了,我家庭成分不好,結婚遲,三十歲才結婚。也就是這一年開始寫作,我喜好讀書,并沒有想過自己也要做一位作家。作家在我的心目中地位是很崇高的。
我的愛好起初是很廣泛的,譬如我愛集郵,愛看書,愛打毛線衣等等。當然包括拉小提琴。我拉小提琴完全是自學成才,和小說中的常樂樂不同,常樂樂他出生在一個音樂之家,父親是一個小有名氣的二胡演奏家,他的祖父則是有名的笛王。他家里的女眷們也都是音樂能手。就是這樣的環境催生了一個音樂天才。為了寫這個人物耗費了我的想象力,當我寫完后我覺得自己虛脫了。當小說在雜志發表后,引起了爭議。人們爭議的焦點是小說中性愛的描寫。這個我還是從近期的報紙上得知的。引起爭議總歸是好事,就怕石子落水沒有聲響。好壞不由己,我自己只是努力地完成了。
常樂樂在下放改造的時候,經常鬧笑話,還挨人欺之類的,是一個標準的書呆子。我在生活中也是一個書呆子,但是他卻能在田埂上拉小提琴,多少改變了人們對他的一些看法。這個多少摻入了我的一些經歷,但是大半出于想象和編造。田埂上的小提琴家,常樂樂由此有了一個新的名字。起初我想,常樂樂肯定是出于排遣寂寞(或許是因為愛情)開始偷偷拉小提琴的,那個時候多在下工之后,“田野上人散盡,猶如豌豆回莢”。闊闊大大的原野上只有他一個人,他將小提琴藏在一個草垛里。他躲在草垛里和河邊的蘆葦蕩里拉過,音樂聲賦予了一個個美妙的夜晚。我相信他的小提琴聲為很多人所記憶,因為那是美的。就在一周前,一次返城知青周年紀念聚會時,還有人提起當初第一次聽見的感覺。有一個姓呂的女同學說,當時一下子我們感覺天空變成一種淡淡的紫羅蘭色。

插圖/王藝雯
小說中的常樂樂比我的境遇要差多了,他被迫砸壞了好幾把小提琴,要比我瘋狂得多。他要求人們安靜下來,當時人們寂寞而躁動,吵架,流血,斗毆,甚至通奸。有段時間他幾乎處在瘋癲狀態。我和小說中的眾多人物一樣都以為他已經走火入魔,認為音樂已經有了治病的功效了。有時候他要求道上的一只鵝,兩只野狗安靜下來。他瘋癲的樣子惹來幾個女人的同情,有一個還義無反顧地愛上了他,但更多的是人們的譏笑,嘲諷和習以為常。當然關于常樂樂的愛情史,我以為是小說中的重頭戲。我試圖讓他們生長在音樂里。但是有人總是將這個愛情史,理解成情愛史。如此一顛倒是大大的不同的,美妙變成露骨,就像當前報紙上一些批評家所說的那樣。我難以茍同,但是并不影響他的觀點繼續存在。
冬不拉先生大概聽過我跟他提過常樂樂的故事,是的,從我返城后,常樂樂就在我腦海里形成了。我只是一點點地積累完善他。冬不拉先生很感興趣,他還常在小書店的藤椅上,曬著太陽說,田埂上的小提琴家,很美,很有內涵。冬不拉先生還說,小董的書如果能寫出,我倒真的可以給他寫個序的。這些話基本是書店老板的轉述,可以想見。只是遺憾的是那會兒我正在新婚燕爾。小說當時已經差不多快要完成。當我真正的完成小說,意欲見到他時,老人已經仙去了。我到書店去,我總感覺到書店少了一些什么,后來我才明白在我的記憶中,藤椅里的冬不拉先生已經是書店剪影里的一部分了。
他死了好幾個禮拜了。書店老板說。
我悵悵地“哦”了一聲,便沒有話說。
我在書店里徘徊了一陣子就回家了。夜深人靜,我還能聽見書店老板的聲音在我的身后響著:老頭子早年是一個小提琴家,正兒八經留過洋的呢。
我為此回味良久。現在書出來,我只能自己寫這篇所謂的序。我似乎明白人與人的遭際就如兩個海洋,就像我和小說中的常樂樂,我和冬不拉先生,他們遺世獨立,卻又息息相通有一個溫暖的通道。正由于此,想象力得以飛翔,令人快慰平生。
董欣賓寫于1984年6月撣帚齋
2、再版序言
一個遙遠的下午,有一個青年人站在一條鄉村小道上,他的下巴抵著琴臺,眼光看著遠處那邊,好像炊煙剛起。他的腳邊有一只白鵝,他開始運弓拉動琴弦。于是小提琴旋律響起,聲音輕越,穿透了這個下午,甚至連那個青年的身影都顯得輕靈起來。他開始走動,挽著褲管,一兩只白鵝也走走停停。遠處的村莊顯得很靜寂,似乎被音樂提前陶醉入了夢鄉。
這個場景是若干年前的一幕,發生的背景是那個特殊的年代。那個青年,小提琴,田埂,還有鵝,這個是不是屬于真實的場景呢?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了,但是至少是這本小說給我還原了那段映像或者準確地說是記憶,使我似乎更為真切地認識了常樂樂這個人。當時在大劉莊,我們那兒的確有這么一個人,不過此人并不姓常,而是一個復姓叫歐陽,單字一個春。歐陽春愛音樂幾近癡迷,至于家學淵源,這點倒和小說描寫吻合,包括長相,董欣賓在文字上也是盡量遵照原型。歐陽春是一個瘦高個,戴副眼鏡,和那個時代的書呆子氣的人一樣,指甲修長,因為聰慧敏內而嫌木訥。這個人如果不是因為喜歡拉小提琴,他幾乎難以從記憶碎片里凸現出來。有一年,愛樂樂團到安宜來,我愛人不知道從哪兒搞來的票拉我去,我就在那次第一次真正地聽到完整的小提琴。并且一聽之后使我陶醉得不行,并且影響了我后來的評論文字的寫作。有人說,我的評論文字有樂感。我想或許就是從這個開始的。盡管我這些文字不登大雅之堂,只在《安宜日報》的副刊上出現。
也是在那天,我回憶起了知青下放那段日子,那段日子在回憶中有點兒甘甜的味道,這個讓我費解。明明那個日子煎熬萬分,為什么還會有這種感覺呢?或許因為時間和回憶的因素。有時候我的腦海里會闖進一個人來,那就是歐陽春。也是因為他會拉小提琴的緣故,我們那會兒叫他田埂上的小提琴家。他后來的經歷是我們那撥人陸陸續續談論中完整起來的。他的經歷很慘,到他真正回城時候已經是孤身一人了,他的父親下落不明。母親病在床榻上,死了好幾天之后才有人發現。他的姐姐被所在的大隊部的一個混蛋強奸后受了刺激,常發瘋病。令人遺憾的是他后來并沒有走上專業的音樂道路,而是去了機關。至于什么機關,有的說是公安局,有的說是郵政局,大家也是道聽途說。當然后來證實他去了郵電局。
他的人生道路顯然和小說中的常樂樂有所區別,但是他喜歡音樂,喜歡拉小提琴。確實是那個時候給我們留下一個鮮明印象的人。除了他,還有一個叫李琦清的人會背誦地圖,地圖上的縣市和集鎮他了如指掌,令人稱奇。歐陽春身上沒有什么傳奇之處,但是由于一把小提琴在手,他就顯得有點兒卓爾不群,有點兒和我們所有人不一樣了。或許是因為小提琴和田埂、雞鴨鵝的鄉村不相協調的因素?還是本身他氣質的緣故?
總之誰也沒有想到,就是這個歐陽春后來成為董欣賓的筆下人物,就連董欣賓本人也始料不及。董欣賓是潮州人氏,因為很奇怪的家族因素(據說是過繼給遠方姑媽)來到了安宜,很小的時候也就是大概董欣賓四五歲的樣子,他父親實際上就是他的姑父去了潮州把他帶回來。董欣賓身上有股潮州人的執拗精神,由于安宜的水土和文化氛圍,他從小安靜,喜好讀書寫字。他當時和我在一個組,我們住在同一戶人家。董欣賓其實和常樂樂在日常生活中并沒有多少交鋒,即便有,也僅僅限于幾次路上的相遇。他們甚至沒有說過話,這個我可以作證。董欣賓和常樂樂都是那種不擅言辭的人,屬于悶葫蘆的類型。顯然小說中的常樂樂有很多部分源自董欣賓的再創造,他的虛構能力可見一斑。至于董欣賓在自序里說他自己也喜好小提琴,并且是自學成才,這讓我吃驚,我敢肯定這是后來的事情。
我個人覺得常樂樂是一個令人欣喜的形象,他的身上那股執拗我在董欣賓身上找到了對應。還有他的癡迷勁兒。有一位詩人(記不清楚是哪位了)曾經說過:每個人其實是一個小宇宙。我覺得說的太好了。我現在相信那個時候的歐陽春,或者說是常樂樂的原型,他愿意生活在他自己的那個小宇宙里。那個小宇宙里就只有一把小提琴,有著女人一樣的曲線,猶如天堂一般的音樂。他每天在下工之后,很多人都從田地回去,他就會扔下笨重的鋤頭,奔到他藏匿小提琴的地點:或者大草垛或者蘆葦蕩或者干溝或者草叢里。然后開始沉浸在自己抒發的音樂里。
有時候我會在洗腳的時候斷斷續續地能聽見小提琴的聲音,那聲音的確很甜美。甜美得就像是假的一樣。至于故事主人公的愛情,無論哪本小說也無法忽略掉的。愛情多么迷人的字眼,多么美妙的事情啊,怎么能忽略不計呢。常樂樂的愛情開始就注定是一個悲劇,他愛上了大隊部書記的女兒。這個愛情格局的確有點俗套,但的確是真實的,唯一和現實生活稍有區別的是歐陽春愛上大隊部的一個會計的女兒。常樂樂拉琴的很多動機似乎是和這場愛情有關,或者說是他求愛的時候小提琴派上了用場。
“他站著,就那么站著,身子微微前傾。過了一會兒,常樂樂不知道從哪里來的勇氣,一把抓起蔡紅娟的手,此時的蔡紅娟有點兒緊張又有點兒興奮,她第一次見到,甚至叫不出這個東西的名字。雖然作為村干部的女兒比別家女孩子要見多識廣得多,但是對于這個,她真是第一次見到。她甚至是第一次近距離地看到一個男孩子的臉上有點兒羞澀的表情。他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手掌,她并沒有滑脫的意思,任由對方將握住她的力量逐漸地轉移到手指上。她的一個手指被常樂樂捏住,然后他將她導引著。那種神情既肅穆又自然,她感覺到一個變冷的曲線,還有分明的棱角。驀然間,她感覺自己的手指被一個細長的東西勒進。她被起先充盈著的那種堂皇的感覺轉而慢慢地衍化成了一個個顫抖的聲音。這個聲音是因為自己的手指的觸動。空氣中忽地響起來的聲音,使她的眼神一顫,她的眼睛在一剎那間增加了亮彩,她看著他,他那鼓勵她的目光里依然含著一絲羞澀,好像她撥動的不是他的琴弦,而是他身體的某個部位。”
董欣賓的描述使我沉浸在男女愛情的氛圍里,這個細節的描寫是常樂樂第一次讓蔡紅娟見識小提琴的那個黃昏時分。
董欣賓能從事專業寫作,對我來說跟他能拉小提琴一樣讓我覺得不可思議。這么說的基礎是因為我覺得這些玩意是需要天賦的,而董欣賓在我看來,或者在我的潛意識里,他一直是一個商場里的售貨員。他后來因為寫作的成績調離商場(那會兒還叫百貨公司)去了安宜市的文聯。這是他的某種人生意義上的勝利。他無疑要比歐陽春,甚至也比他筆下的人物常樂樂要幸運得多。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講,他找到了自己,而大部分人是一直在找自己,有的人一輩子也沒有找到。
我和董欣賓曾經同甘共苦過,后來進了城之后,事實上聯系很少,后來文化系統的會議多起來,我們的碰面機會才多起來的。有一天在一次文化下鄉前期籌備會議的間隙,他端著茶杯走過來,眼睛閃著亮光,他說,你還記得那個歐陽嗎?當時我一時還真沒有想起來。經他提醒說拉那個小提琴的我才醒悟過來。他這么告訴我的目的是說他在寫一部小說,說的就是當年的事情和當年的人。
記得當時,董欣賓還向我求證,那天晚上是否蔡紅娟(其實他應該說袁菊花才對) 在場。我們的記憶發生了點兒分歧。我說蔡紅娟是不在場的,因為當時我在蔡家(事實上就是現實中的大隊部會計袁家)幫忙,看見蔡紅娟(現實中是袁菊花) 沒有離過家一步。而他則認為在場。難道我的記憶出了問題?或許是,也或許是董欣賓出于虛構的需要。關于那個晚上,董欣賓基本在小說里交代清楚了,這個晚上發生的一切對于他的故事來說無疑是很重要的。但是需要說明的是,常樂樂并沒有得到蔡紅娟,蔡紅娟另嫁他人的前晚就是董欣賓小說里一個高潮部分,也是事先董欣賓跟我談及的那個晚上。我記得是臨近中秋了,蔡家忙著喜事(現實生活實有此事)。蔡紅娟和常樂樂在一個他們相會的老地方見面了。就這個我質疑過董欣賓,董欣賓不置一詞。
或許他們的確見了面。就時間上來說,他們并沒有做愛的現場和可能。那么后來蔡紅娟被新婚丈夫退還蔡家是怎么回事情呢?小說里寫了他們兩個人見面,并且在時間上做了處理。在這段上,董欣賓染上了現代文字的流弊,過于具化床笫之事。這個已經引起過討論,我在此不贅言了。一個藝術品因為有瑕疵才是完美的,真實的,而挑不出刺的東西肯定不是好貨。這僅僅是我的觀點。
那么當時的情形,我說的是退親一節和現實生活原型的情形有點兒出入的。蔡紅娟被退還了蔡家,這個在當時是一件很丟丑的事情。蔡紅娟破了苞,這可是一個驚天動地的事情。后來蔡紅娟投河自殺了。那么她到底有沒有和常樂樂有過肌膚之親,按照常理推論是沒有的事情,因為她基本出不了門的。或許董欣賓更懂得生活的秘密,他這么處理筆下的人物自有他的道理。
蔡紅娟投河一節,寫得令人肝腸寸斷,令人同情,常樂樂隨著打撈隊的情形更是動人心魄。
蔡紅娟的原型是那家大隊部會計的女兒姓袁,叫袁菊花。她投了河,幸運的是被救活了。她以投河自盡來表明自己沒有和歐陽春有染。這是她的一種與世俗對抗的方式,也是一種人生賭博,賭注是她的一條命,結果是她賭贏了。她的丈夫特地用拖拉機將袁菊花拉回家。毫無疑問,這對歐陽春打擊自然很大,但是他們之間的事情就這么完結了。他們的轟轟烈烈表現在最初階段:袁菊花喜歡聽歐陽春的琴聲。歐陽春后來回了城,或許已經忘記了這個女人,或許還在內心深處藏匿著。而小說中的蔡紅娟不一樣,作為小說家的董欣賓似乎更相信悲劇的力量,他把她寫死了。她第三天才在距生產隊很遠的河里被發現,已經被水泡腫了,臉幾乎認不出來。當她被放在草垛旁的空地上的時候,當場的所有人都為之動容。
而常樂樂就在那個時候受了刺激。他不跟人講話,自言自語,要跟腳的狗或者鵝安靜下來諸如此類的舉動,所有人沒有人不認為他有點兒瘋癲。我在一次和董欣賓的聊天中,他坦白地說是將歐陽春姐姐的經歷嫁接到了常樂樂的身上。
那個夜晚的描寫讀來使我如置身當年,從記憶深處多少喚醒了我。為此我應該感謝董欣賓。
這本書出版于一九八四年,實際上成書時間稍早,董欣賓花了兩年時間,但按照他的說法遠遠不止兩年時間。記得當時董欣賓為此找過我,要我寫序,他人很實在,一點兒也不掩飾,說如果那個老先生在,也就是他提及的傳奇的冬不拉先生,就不勞大駕了。其實我劉長風這個人最好說話,也不是擺架子。的確我當時被一件頭疼的事情纏繞得焦頭爛額,沒有答應下來。后來書出來我才發現他自己寫了篇自序。
我一直認為對那個特殊的年代,我們的文字工作者一直是戴有色眼鏡的,沒有一個公正客觀的歷史目光打量。董欣賓的小說我覺得從某種程度上已經逼近或者說吻合了我們那個時代。至少我這么認為。這本小說能再版,說明其生命力。董欣賓這次找到我的時候,我無法推卻。關于一篇序,第一次找我和第二次找我之間相隔了十四年,這個時間段里,白云蒼狗,人間變幻多少事啊。時間真讓人慨嘆不已。那個時候董欣賓還是風華正茂年富力強的青年人,而此時的他已經被大家一口一個叫做“老董”了。
拉拉雜雜說了這么多,是為序。
劉長風
一九九八年十月
安宜西郊十八筒子樓
3、日文版序
一天下午,我的妻子王芝清正在街上走著,迎面遇見一個女子向她問路。妻子是一個熱心人,她看出對方是一個外地人,就一直把她送到富達路的路口。
在路口,那個女子忽然問她,你認識董欣賓先生嗎?
我妻子說,你可真找對人了。我不但認識,還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呢。
這個問路的女子就是我的小說《田埂上的小提琴家》日文版的翻譯小澤慧。小澤慧找到我費了一番周折,先是通過出版社找責任編輯柳芳春,可是柳芳春患肺癌在千禧年已經棄世而去。柳芳春名字看上去像女的,其實是一個男的,北方大漢,內蒙古赤峰人氏,之所以說他棄世是因為他自己自殺:或許因為是癌癥帶來的絕望。找出版社其他人都說這個只有責編清楚,甚至有的人不大知道這本小說,他們都說,是不是很久了啊。雖然如此,她并不死心,決定一定要找到作者。后來她托朋友找作家協會,一級一級地查,最后才如愿以償。
“費了老勁了。”小澤慧還夾雜著一句中國北方口音。這讓我莞爾一笑。因為從說話口氣和打扮上看,一點兒也看不出坐在我對面的是一個日本女子。
“那已經是八年前了。”小澤慧告訴我她第一次看見這本書也不知道誰給她的,塞在她的旅行包里,她覺得像是一種冥冥中的緣分。小澤慧是隨著日本一個文化團來訪問的,隨后在飛機上一口氣看完了這部小說,她下定決心翻譯它。中間一直沒有斷過,雖然只有三十五萬字,但是她斷斷續續地翻譯完了。她以前沒有做過任何翻譯,在大學教書是主業,喜愛音樂純屬業余。她翻譯完也不知道應該交給誰出版,她說她抱著試試看的態度由朋友轉給講談社。沒有想到這么快就列入出版計劃。小澤慧這次完全可以不來,因為她所任教學校還有一攤事情等著她,她還是來了,她想和我見見面。她說,純粹是好奇,因為以前沒有這樣的經驗。按照錢鐘書的說法,吃了雞蛋為何要見這個下雞蛋的雞呢。小澤慧告訴我她也知道這句話,就在她出發來中國的前夜,她丈夫還跟她說了這句錢氏名言呢。
“當然,因出版社要求,作者寫一篇序,就是給日本讀者說些心里話。”小澤慧的眼光很真摯誠懇地看著我,我當然答應。
她坐在客廳的沙發里,身子筆直,顯得很謙恭。我以前也接觸過日本人,他們大部分是這樣。小澤慧的漢語說得非常好,她告訴我她的丈夫就是中國人,他們是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候相識相戀的。她還去過揚州以及蘇錫常一帶。
在談話中,我一直頻頻抱歉,因為我身體欠佳,不斷地咳嗽。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有相逢遇知己的感覺。我本想請小澤慧去附近的一蘋軒吃飯,但是她堅決要求家宴。我為她下廚做了幾個拿手菜,揚州獅子頭,宮保雞丁,蝦米煮干絲。在飯桌上,她問我有無新作。
我遺憾地搖搖頭,因為什么呢?她這么問我,我也答不出所以然來。如果真要問為什么,以結果論,那就只有一個回答:江郎才盡。
其實,我在寫作上盡管還有雄心,但是力不濟我了。這個跟我的身體有關。
這次能以冥冥中的機緣,出版日文版本,我感到非常高興。作為一個作者,自然希望更多的人讀到它,喜歡它。在此前我是不奢求這樣的美事的,雖然我也知道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會有可能有這個故事的知音,但是你不可能奢想到所有的人能讀到它。這個只能看機緣。
一本書和一個人也是需要緣分的。小澤慧非常同意我這句話。
我對于日本很是向往,有一次單位組團去日本,也是一個文化訪問團的性質,據說他們去了富士山,看了櫻花,還去了湯泉,去了川端康成的故所。那次因為別的事情很遺憾沒有去成。但是現在我的文字帶著我去訪問,去滲透到那摻和著櫻花香陣的另一片豐饒的特別的土壤。我感到莫大幸福。
或許有一天夢里,我會夢見在櫻花香氣里見到有一個人走過來,對我說,我就是常樂樂。
或許真的會這樣,誰說得清楚呢。
董欣賓
二〇〇六年六月
4、修訂版序言
說實話,編輯找到我的時候,說要寫一篇修訂版序言。我真的不知道如何下筆。編輯說,可以寫點生活中的那個“董先生”。這個對讀者是有吸引力的。編輯很年輕,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幾歲。他說這部小說是他編輯生涯的第一本書,因為是初入出版業,所以社里交給他的就是這個再版書的任務。他說他希望這本書跟柳芳春老師(前責任編輯)的思路不一樣,包括裝幀設計之類。當時他約我在外館斜街一家肯德基見面,他看見我很為難的樣子,說,想到什么就寫什么就可以了。這么一說,我自然就放松下來了。可是一回家,坐下來想,還是無從下筆。
爸爸應該說是一個比較乏味的人,當然也不是說他沒有趣味,總而言之,他就是一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男人。我習慣叫我爸爸老頭,在家里跟爸爸沒大沒小的,他從不批評打罵我們,我弟弟更是寶貝得不得了。有了弟弟之后,爸爸按照媽媽(改口前一直叫王姨)的話說才有點兒生機,他在生活中給我們的印象好像作家都應該是這個樣子,因此媽媽在我填寫大學志愿的時候無論怎么著也不讓我填寫中文系。因此,我讀的是機電工程。弟弟說將來他要做記者,將來也不會去弄文學,而是要學新聞。
其實這個可能是因為爸爸的性格因素帶來的特別印象,因為我發現有的作家還是很有幽默感的。記得大三的時候,我們學校請一個姓林的年輕作家來做文學講座,那個作家嘴角含笑,歪戴著一鴨舌帽,穿一身夾克,在臺上一站談笑風生,全場不時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也就是說,一個人與另一個人是不同的,那么一個作家與另一個作家也是不同的。
總之,我爸爸能寫作好像在我們的印象中,就該如此的樣子。實際上,他只有一部作品有點兒名氣,也就是這部《田埂上的小提琴家》,至今為止出版社加印了好幾次,且翻譯成了好幾國的文字。其中日文版本就是去年三月份的事情,當時翻譯家小澤慧來我們家的時候,我們還在學校里。
小澤慧女士回到日本之后,開始時通過書信來往,后來就經常通電子郵件了,我爸爸不會上網,收發郵件等基本是我幫助他。電子郵件往來主要是討論書中的某些細節,為了讓日本人了解歷史和風俗,爸爸在電子郵件里回復了很多關于風俗以及一些特定歷史時期的問題。當然基本是我打字,譬如風俗上的如臘八放河燈,忌日焰口,以及一些鄉村游戲猜草窩之類。這次在修訂本里也同樣遵照這樣的編輯體例,作了些頁面注。這次重新修訂,除了在文字上糾正了一些錯別字之外,增加了將近八幅插圖。這些插圖是國內比較有名氣的版畫家蕭元勝先生畫的黑白版畫,我覺得和文字很是和諧。
當時插畫的建議就是爸爸提出來的,不是因為和蕭元勝先生私交甚好,而是完全因為這些版畫作品太合適了。按照爸爸的說法,蕭叔叔也是一個了不得的小說家,只不過他是用畫筆寫而已。爸爸的提議得到了出版社的認同。記得當時爸爸和蕭叔叔還有編輯一起在茶館談定了這個事情。從茶館回來之后第二天,爸爸的身體就每況愈下。
但是他的離去還是令我們吃驚,我們覺得很奇怪,或者說,爸爸是不是有預謀這樣做。我弟弟也同意我的猜測,雖然他才是一個十來歲的小屁孩:爸爸是自己用煤氣殺死了自己,而不是大家都那么認為的死于一次煤氣中毒,一次純粹的意外。
王姨,也就是我弟弟的媽出門去買菜了,爸爸說他上午在家寫作,需要清靜。王姨也沒有在意,就像往常一樣去附近一家美容店做了一個面膜之后就打算去菜場買點兒菜。沒承想,她在美容店的按摩床上睡著了。醒來的時候匆匆趕到菜市場旋即回家,遠遠地看見樓下聚集了很多的人。有人說什么煤氣中毒的話。王姨說她當時就感覺不對勁,三步兩步走過去,看見兩個人將一個人往下抬,穿著褲衩,身上蓋著一個毛巾被,看不見臉。王姨從褲衩一眼就認出來了,她連忙撲上去。旁邊的人說,別哭了,趕快送醫院,董老師還有一口氣。
其實緊趕慢趕送到醫院,人已經沒有救了。事到今天快一年了,王姨她想想就哭,怪自己竟然睡著了,如不睡著,回去早就不會出現洗澡煤氣中毒的事情了。小澤慧遠在東瀛,自然不知道這邊發生的事情,她還繼續發來電子郵件請教這個請教那個。我不得不回郵件告訴了她實情。
在那封電子郵件里我還講了爸爸和媽媽的愛情,我覺得爸爸媽媽他們那輩人雖然活得很辛苦,但是他們比我們幸福,因為他們有愛情,真正的愛情,而我們這個年代的人沒有。我們所謂的80后,有的是消費。
媽媽也是商場售貨員,和爸爸的柜臺隔著好幾個柜臺,但是爸爸說,雖然如此,隔臺相望,“覺得你媽媽就一直離我很近”。起初媽媽是一點兒沒有注意過他。媽媽喜歡讀書,拿現在的話說是一個鐵桿文藝青年。媽媽的眼睛很漂亮,雙眼嘀咕會說話,但是從沒有抬頭看過爸爸。她那眼睛天生的就是看字的。
爸爸開始追求她,整個商場的人都知道,我有時候遇見原來商場的人他們還記得當年爸爸追求媽媽的情形,譬如爸爸寫情書在柜臺上傳,譬如爸爸在柜臺外拉小提琴等等。他們也有一把年紀了,對別人的愛情記憶得很清楚。后來爸爸贏得媽媽的芳心是因為爸爸開始寫書調離商場之后,或者媽媽覺得爸爸開始有了前途。爸爸的出頭之日也就是1980年,他和媽媽結婚了,且在農歷七月初七生下了我。那會兒爸爸就發表了很多文章,還沒有一本書。
我四歲的時候,這個年歲對爸爸來說是悲喜交加的一年。悲的是,他的愛妻也就是我的媽媽病故,喜的是出版了他平生第一本書。當然時間順序上是書出版在先。
后來我爸爸一直沒有新作問世,是不是跟媽媽的離世有關系呢?媽媽是爸爸的第一個讀者,第一個評論家。她不在了,他就沒有動力了,或許是這樣的。有人說王芝清阿姨很像我媽媽,可是我覺得不像,我對照過照片。爸爸和王芝清阿姨結婚時我已經十四歲了。那會兒,王阿姨也就是二十五歲的樣子。他們走到一起也夠寫本書的,可惜爸爸沒有去寫。
有陣子爸爸好像又開始寫作了,好像找回了那臺久久不用的發動機。那個時候我每天晚上幾乎都能聽見爸爸筆尖在稿紙上沙沙的聲音。這個聲音可能是我少女時代最難以忘懷的,也是弟弟的童年里不會忘卻的音樂。爸爸出版的作品包括《政府》、《與無名少女的一次郊游》,還有一本《以夢為馬》的散文集。前段時間我在整理他的稿子時候發現了他早年寫給我媽媽的信(其中包括給王芝清的)還有很多詩歌,這些很是珍貴,我跟責任編輯說過,但是責任編輯從出版市場的角度出發要我暫時放一放,雖然他這么說,我還是希望能結集出版。爸爸似乎預料到會出版這一天,連名字都似乎準備好了,這些稿子放在一個大信封里,信封上寫著三個大字:滴石集。
我期待著更多的人來了解他,不僅僅是這本書,還有其他的作品。
董芳菲
二〇〇七年十月
5、附錄:董欣賓簡譜
1950年 2月,出生在廣東潮州。后過繼給安宜縣姑父家。
1980年 團結商場當售貨員,結婚生女,取名芳菲。
1983年 寫作數篇通訊報道和散文。一時小有名氣。
1984年 春天,調往市作家協會,出版《田埂上的小提琴家》。妻病故。
1985年 出版《政府》,反響平平。
1986年 出版《與無名少女的一次郊游》,之后鮮有小說作品問世。
1994年 與王芝清女士結婚。王芝清二十五歲。1998年 小說《田埂上的小提琴家》再版。1999年 寫作隨筆散文,集結《以夢為馬》出版。
2006年 《田埂上的小提琴家》日文版出版,小澤慧翻譯。
2007年 5月,董欣賓患病,煤氣中毒而亡,疑為自殺。
2008年 2月,《田埂上的小提琴家》修訂版出版,
7月,新銳導演韋前改編拍攝同名電影獲亞洲電影節競賽單元新人獎。
作者簡介:林苑中,男,本名張華,1974年10月生,小說家、詩人。江蘇揚州人。1993年畢業于江蘇高郵師范學校,1997年畢業于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2000年開始正式寫作,以中篇小說《鐵皮鼠》登上文壇,受到王蒙、北村、韓東等大家關注。先后在《收獲》、《鐘山》、《山花》、《芙蓉》及《今天》(北島主編)等國內外文學雜志發表中短篇小說,著有長篇小說《雨語者》,中短篇小說集《沙發上的月亮》、《跑步的但丁》等。有作品入選《中國詩歌年選》、《中國詩人》、《詩選刊》、《70后詩人詩選》、《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以及多種中國年度最佳小說選本等。系江蘇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曾先后供職于江蘇揚州教育學院中文系高郵校區,十月雜志社等,2005年移居北京,從事影視與出版工作。代表作有《韋鎮小道》、《鐵皮鼠》、《婚后的卡夫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