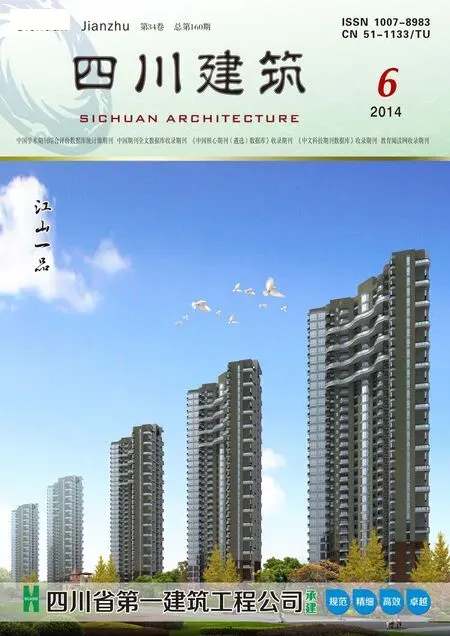由綠色建筑設計趨勢所觸發的再思考
———對兩次綠色建筑設計競賽獲獎的討論
付保俊
( 西南交通大學建筑學院,四川成都611756)
1 綠色建筑理念在中國
對于綠色建筑的理念源起,比較公認的地點是歐洲。從倫敦零能耗建筑研究——貝丁頓社區開始,到英國BREEAM綠色評價標準的出現,綠色建筑的設計理念,從英國傳至全歐洲,直至成熟、發展和完善。
對于設計界的探索還處于發展與嘗試中的中國,新興事物總能帶來新的思路和理念。有趣的是,綠色建筑理念在國內的傳入,并非來自于建筑設計界,而是通過建筑的關聯行業如太陽能、風力發電行業的觸動而引發的思維變化。在這些關聯行業里,由于光伏光熱一體化、太陽能風力應用及可持續低碳的技術發展與普及需要與建筑專業相協調,同時歐洲零能耗實踐與展覽所激發前沿人士心底觸動,因而漸漸開始在中國的建筑設計師頭腦中發生綠色建筑的理念萌動。但總的來說,這個時期中國的建筑界對新興的綠色建筑設計思維還處在觀望、探索和初步了解的階段。
有人說商人的嗅覺總是敏銳的,容易察覺到不被常人所感知的機會,同樣在綠色建筑市場,綠色理念被投機商整理、包裝而成為一個感染力強、效果甚好的噱頭。而建筑界也不甘落后,開始進行綠色建筑技術的試驗、標準的編制、示范工程的建設。如某大學低能耗生態樓,某建科院生態辦公樓。然而事物發展的初始時期總是曲折和困難的,過于強調技術的應用,使得示范工程成為堆砌綠色建筑技術的房子,而非真正意義上的綠色建筑。所以,這個時期中國建筑界對于綠色理念的探索是盲目和目的不明確的,但從某種層次上來說,這成為了后續發展階段的鋪墊,有效并迅速積攢了一定意義上的經驗。
2 國內綠色建筑設計發展
國內綠色建筑設計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實踐與形成,是從北京奧運綠色策略的實施開始。在確立中國北京成為第29屆奧運會舉辦城市后不久,相關單位研究、制定并編寫了《奧運綠色建筑標準及評估體系》,奠定了中國綠色建筑評價標準的基礎性技術規范及標準。同時引入美國LEED評價標準,將主動尋求評估并滿足相關條件要求的建筑授予星級認證,一方面是對現有成果的肯定,另一方面是對綠色評價標準積極推廣的促進帶動。
然而技術總是帶有一定的自我局限性,并且無法真正意義上替代自然與人文的角色地位。毫無疑問,建筑的綠色評估是一項高度復雜的系統工程,特別是社會及文化因素很難確定其評價指標,從而更難量化。所以,綠色評價標準還有很長一段路程等待完善與充實。
不過如今英國的BREEAM、加拿大GBC等評價體系都已使用有關機構制定出的權衡系數,相信不久將來能更加全面地運用具有全方位、多面性的綠色建筑評價結果來達到綠色建筑設計的目的。
3 設計競賽的啟示
筆者曾在兩次全國性質綠色建筑設計競賽中參賽并分獲不同獎項,希望借此作出發點,闡述對于國內綠色建筑發展的個人觀點。在兩次設計競賽中,不乏有許多優秀的作品出現。從設計師工作室到學生團隊再到個人,都爭取在最終成果方案圖紙上表達出對于綠色建筑設計理念的詮釋與探究。后將眾多備選方案與獲獎方案作對比發現,設計思路呈現兩種分化狀態。一種以高技術的廣泛、全面應用為代表,一種以地域性的適宜技術結合被動式技術應用為代表。而獲獎方案則主要集中在第二種綠色建筑設計策略應用的方案上,由此可以判斷,對于綠色建筑概念與設計策略的理解,在一定意義上存在著誤區。
筆者認為,對于建筑設計,方案的理念是貫穿整個方案的思路,為設計者提供了可參考并且具有信服力的設計依據,而綠色建筑的設計方案比普通設計方案更為復雜,它需要設計者在初始階段就必須考慮到綠色技術的應用,包括主 動式策略的利用、被動式策略的應用或者主動與被動結合策略的使用,這就要求設計者必須對綠色建筑手法有深入的了解,必須知道在我國不同氣候分區中房屋使用者的特別需求與能源消耗之間的關系,以及在不同地區有哪些技術策略可以使用并且在眾多策略中進行相關特性的對比,選擇最為合適的進行配合設計。當然,在設計時候一味地追求高技術是過于盲目的,因此應當在設計前期以被動為主,主動為輔,盡可能地利用自然界力量對建筑室內外環境進行最大化調節,在實在無法滿足舒適度與節能的條件下可以適當考慮主動式技術策略的應用。
而目前我國建筑師的綠色建筑設計水平還處于較低的階段,雖然已經從“泛綠”過渡到“淺綠”的層面,但是與國外相比仍相距甚遠,過于系統性、全面性地揉合主動式技術而過少地考慮實際使用效果是目前應該及時改善并提高的。
4 設計競賽所引發新的思考
從我國綠色建筑的發展與完善過程以及競賽中得到的啟示可以看出,綠色建筑設計逐漸成為未來建筑設計的趨勢與必然,而之前所探討與論證的均是建筑意義層面的設計思考。對于逐漸將自然與人文因素作為評價因子的綠色建筑評價標準的完善趨勢,能判斷出綠色建筑的實踐正在成為一項被廣大民眾所認知和認可的社會工程。需要在整個社會層面包括城市規劃、居住區規劃、建筑設計、建筑管理及綠色行為之上集各界力量從而達到全民共識,形成綠色價值消費基礎。而這種受共同認可的方式,是必定符合自然界和諧與人類自我發展的規律。因此,綠色建筑的理念普及,設計策略應用,在本質上是尋求自然與人類的平衡點,從而達到天人合一,和諧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