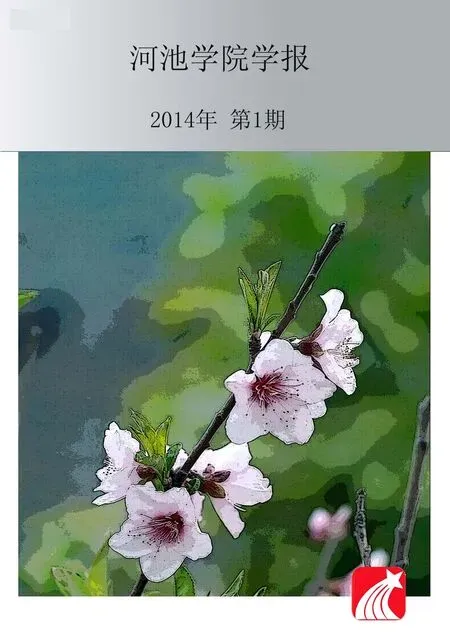黃遵憲日本詩的改革創新思想
鄧國琴
(河池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廣西 宜州 546300)
黃遵憲一生致力于倡導革新,在其少年時便有“別創詩界”之說。在其《日本雜事詩》中,革新意識鋒芒四溢,強國思想也一覽無余。從政治、經濟到軍事、文化、教育等,無不囊括其中。他以詩紀事,闡述了其意欲革新之學說。他在《日本雜事詩自序》中坦言,他創作的動機就在于網羅舊聞,為中國勢在必行的改革提供參考。因而在《日本雜事詩》中,黃遵憲以新事物、新意境、新理念入詩,無處不彰顯出其革新意識,表達出其強國思想。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黃遵憲革新國家形態的思想
改革舊制,力舉新法,促行新政。俗話說:窮則思變,變則通。黃遵憲自出使日本,目睹了日本因明治維新帶來的驚人變化,他說:“乃及閱歷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1]1095堅定了他革舊制,開新政的信念。
在明治維新之前,德川幕府時期的日本,閉關鎖國相當嚴重,甚至到了因噎廢食的程度。“幕府以鎖國為要旨,貿易商務之不發暢亦因其所”。[2]172與西方各國的商貿,除荷蘭之外,一概禁絕。西方各國為了謀求各自的利益,相繼率兵而來,以武力迫使日本開放港口。幕府的無能導致了倒幕運動,于是“在20年的時間內挑戰者們就把舊的政治結構掃除掉,開始為一個新時代奠定基石”。[3]280這就是日本的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的口號是“尊王攘夷”,即“王政復古,驅逐夷狄”。然而在復古的旗幟下,日本走的卻是一條全新的道路。明治初年天皇親政之后馬上廢棄了封建制度,采用了西方的政治組織形式,君主立憲制開始萌芽。這一變化,讓倒幕派始料不及。于是各藩主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紛紛樹立黨羽,并成立了不同的政黨。如詩所言:“呼天不見群龍首,動地齊聞萬馬嘶。甫變世官封建制,競標名字黨人碑。”[1]1099這一狀況,也出乎西方人的預料。如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所述:“似乎毫無跡象表明這個不喜歡革命的國家日本會改弦易轍,會順應西方模式,更不用說五十年后竟能與西方國家爭雄競長。但這一切還是發生了。”[4]52事實就擺在眼前,不由得人不信。不僅廢除了封建制度,而且還大行西學,倡導民權自由之說。正是:
劍光重拂鏡新磨,六百年來返太阿。
方戴上枝歸一日,紛紛民又唱共和。[1]1098
政體的改變帶來了日本全方位的變化,不僅國家安定民眾擁護,更使得經濟面貌煥然一新。黃遵憲不由得贊嘆“玉墻舊國紀維新,萬法隨風倏轉輪。杼軸雖空衣服粲,東人贏得似西人。”[1]1101贊美之情溢于言表。這既表明了新政對國力的促進,也說明了商貿對國家面貌的改變,更表現出黃遵憲改革政體以增強國力,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狀況的迫切愿望。
海外所見,使黃遵憲意識到,一味地閉關鎖國只能被動挨打,終屈辱于強敵之下。既然萬世一系的日本都能變,何獨中國不能呢?對日本明治維新所帶來的新面貌的歌頌,寄寓了黃遵憲政治革新的思想意識。如何革新?在黃遵憲看來,首要之事,就是要像日本一樣,廢除封建專制,實行君主立憲制。這種思想,不僅在他的詩歌中表現出來,而且他還多次明確強調中國非行新法而不能自立自強。光緒十六年庚寅(1890年),黃遵憲跟隨薛福成出使英國、法國、意大利和比利時四國,在到達英國之后,考察了英國的政體,認為中國的政體,非學習英國不可。具體做法是“欲取租稅訟獄警察之權,分之于四方百姓。欲取學校武備交通之權,歸之于中央政府。盡廢督撫藩臬等官,以分巡道為地方大吏,其職在于行政而不許議政,上至朝廷,下至府縣,咸設民選議院,為出治之所。而又將二十一行省分劃為五大部,各設總督,其體制如澳洲、加拿大總督。中央君主,權如英主。共統轄本國五大部,如德意志帝之統率日耳曼全部,如合眾國統領之統轄美利堅聯邦”。[1]1201他認為只要實行了君主立憲制,那么于內則能使民生安,于外則能與各國交好,如此一來,也就能使中國自立于世界之林了。而在光緒二十三年丁酉(1895年)六月初六,黃遵憲在與當時的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的談話中,再次強調了君主立憲的主張。而且說,這種想法已經在他的心里醞釀了十多年,但從未對人提起過。由此可見,黃遵憲的政治革新意識并非一時一地的想法,而是由來已久且持續不斷的。而在《日本雜事詩》中,這種意識的表露是一覽無遺的。
二、黃遵憲對民權和民主的思考
推進自治,提倡民權,欲保民生。黃遵憲曾經研讀過盧梭、孟德斯鳩的學說,知道要想擁有太平盛世必定要發揚民主。因此他主張打破一人專權的政體形式,把權力下放給民眾以促進人民思想的開化,把舊官吏的權力也適當分配給國民以促進民生的發展,認為如能成功實施,那么君主的權力及民眾的權力得以合理分配,民主之治也就得以實現了。他還說,自從他跟隨何如璋、薛福成等出使東西各國,大致考察了各國政治學說的核心,發現判斷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都是以國民思想的開化程度作為標準的。要在世界上主張一個國家的權力,沒有民族的強盛,就如皮已消失而毛無以依附一樣不可能,國家也就無法自立于世界之林。因此他想通過提倡民權,保護民生來推進國家民族的強盛。而他認為,要確保民生,增強民眾的精氣神,沒有地方自治是難以實現的。并指出,成立府縣一級的會議,是當務之急。
黃遵憲大力推行民眾自治。他希望地方民眾能把地方事物當成自己的事,積極參與到地方自治中。有利之事就去振興,有害之事就去革除。如改革學校教育,籌措水利,興辦商務,治理農事,發展工業,追捕盜賊等等都應該努力去做。把因傳教滋生的禍害當做自家的災難,將匪徒結盟鬧事作為自己的憂慮,事先做好相應的計劃,才能在有事發生時應對自如。他認為在自治中,警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警察的職責,在于保民為國,防患于未然。
時檢樓羅日歷看,沈沈官屋署街彈。
市頭白鷺巡環立,最善鳩民是鳥官。[1]1110
記述的就是日本警察巡行街道,保民促安的情景。詩人的創作都是發之所想,黃遵憲不僅肯定了警察在國家發展、社會穩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更表明了警察制度創建的必要性這么一種思想。
黃遵憲認為,一個國家要達到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一定是從設立警察開始的。因為,“今者泰西諸大,無一國無一處不設警察,……余聞歐美諸國,入其疆皆田野治,道途修,人民和樂,令行政舉。初不知其操何術以致此,既乃知為警察吏之功。”[5]393在他看來,中國地廣人多,要想使得國治民安,非設警察不可。并認為,如果把中國原有的衙役、汛兵等都撤換為警察,給他們以優厚的俸祿并嚴格規定他們的權利,那么所帶來的好處是不可勝數的。他在給梁啟超的書信中也曾強調指出,警察局是各種政策、各種事務得以順利實施的根本,如果能夠讓官府和民眾合力設置,聽憑民眾自籌經費,允許民眾自己籌辦,那么地方自治的規模就已經蘊含在其中了。這必然會使得民眾思想日益開化,而民眾的權利也因此得到伸張。所以他認為,警察是治理民眾最有力的力量。
于是他力主設立保衛局。他認為,以民眾自己的力量來保護、捍衛民眾自己,這種防務形式在中國,必將帶來社會的太平,國家的昌盛,到那時這種形式也一定會在東西方各國得到推行。而梁啟超在《嘉應黃先生墓志銘》中也提到過,黃遵憲最為關注和極力籌措的就是保衛局。保衛局約略模仿外國警察制度,凡是與民生疾苦相關的,而以地方民眾自身的力量又能辦理的,都歸保衛局管轄。如《日本雜事詩》所載:
火齊珠懸照夜光,粉墻碧瓦第相望。
白桑板記公卿姓,紫邏途聯左右坊。[1]1110
按區管理,日常巡防,有利于國治民安。黃遵憲認為,這種管理模式,不僅適用于日本,同樣適用于中國,因此,應該大力提倡并積極實踐。
完備的法律,是一國治國之基礎,民主民權之保障。日本古來無法律,對有罪之人,先用神祓之法除之,后借用大明律,明治維新之后轉而用法蘭西律。如《日本雜事詩》所書:
拜手中臣罪祓除,探湯剪爪仗神巫。
竟將老子篋中物,看作司空城旦書。[1]1109
又有:
《棠陰比事》費參稽,新律初頒法未齊。
錫盟干旱少云,日照充足,太陽能資源豐富,年日照時數為2 800~3 200h,日照率64%~75%。根據1991-2006年16年間全區太陽輻射觀測數據,以錫林浩特市為代表的內蒙古中部月總輻射,僅次于自治區西部的額濟納旗,年變化大致呈正弦規律狀態,即以4-9月太陽能資源最為豐富,另半年較少[3]。年降水量與年太陽能輻射呈正相關,最大值是6月,最小值是12月(如圖2所示)。但是,年蒸發量是降水量的10~20倍,特別是近年來,5-8月份的降水量持續呈下降態勢,利用光伏提水,可以彌補降水的不足,滿足人畜飲水和少量植物灌溉。
多少判官共吟味,按情難準佛蘭西。[1]1109
正是由于緊跟時代步伐,關注歷史現狀,制定了較為完備的法律,日本逐步走上了法治的國家發展道路,促進了日本社會的全面發展。在黃遵憲看來,日本的經驗同樣值得中國借鑒。他認為,雖然大清的律例頗為詳盡,但自古以來,中國都不太注重法制建設,所以法律例律不能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也就達不到以法治國,以法安國的目的。并且中國自古以來都是注重道德的修養而輕視刑法的作用,認為刑法是微不足為道的,這不利于國家的發展,也不利于民權民生的踐行。因而他贊同日本學習西方法律,并希望中國也能借鑒。他看到,西方人喜歡談論權限二字,在西方人的諸多法律書中,所反復推敲闡釋的,也不外乎所謂的權限。因而在西方,人無論尊卑,事情無論大小,都被賦予相應的權力而得到應有的自由,但同時又受到必要的約束,從而全國上下無一例外都受到法律的管治,不管是正名定分,還是息爭弭患,一概以法律為準則進行裁定。因此黃遵憲認為,這正是保民生的一大舉措。因為當民眾的思想日益開化之后,各人就會想著如何去保護自己的權利,如此一來,訴訟就不可能不出現,而法律也就不得不嚴密了。這也就是西方人為什么將刑法作為治國保家的工具加以推崇,并將它當做圣經一般來尊重的原因。
三、從黃遵憲的改革理路看其目的論
振興經濟,增強實效,以強國力。這是19世紀的中國要自強御侮的關鍵所在,也是黃遵憲“網羅舊聞,參考新政”的目的所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的發展關系著國家命脈。而經濟發展又有其自身規律,逆而行之只能適得其反。如盧梭在《愛彌兒》開卷就說到:“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人的手里,就全變壞了。”[6]5盧梭對現代性的批判包含著關注人類福祉的社會關懷,這也是黃遵憲的期望所在——國強民安樂。在當時,晚清政府閉關鎖國的經濟政策,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也造成了國力的衰微。黃遵憲清楚地看到,日本進步之神速,是古今各國所沒有的,認為與其遠道去學習西歐歷經轉折,不如就近學習日本,那么迅速取得成效是指日可待的。中國的物產并非不豐富,產品價值也并非不高,而在于不懂利用。因此他主張學習日本的經濟發展模式,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
廣開商貿以促進國家的收益。“明治政府夙知擴充商務之要。元年置通商司,獎勵公司銀行之興起,扶護造船航海及他制作業以圖國產輸出之增加。嗣后貿易逐年昌盛輸出輸入漸增其數。”[2]173又從各行業中選派人員到國外學習,凡是有可以開拓商業、收獲利益的方法,都學習模仿并一一實行。如此一來,日本憑借著桑茶等物產的出口獲得了極大的利益,因此,在《日本雜事詩》中,黃遵憲以一種新穎的筆調,寫到了日本的出口貿易,表明他的贊賞和學習之情:“采取頭春到尾春,猩紅染色樣翻新。自過谷雨茶船到,先揀龍團贈美人。”[1]1154
輸出的物產,以絲茶最為大宗。物品遠及歐洲及美國。商貿的發展使得日本全國上下的風氣為之一變,為其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力的日益增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正是“杼軸雖空衣服粲,東人贏得似西人。”[1]1101不僅如此,黃遵憲認為,銳意通商還使得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為緩解錢荒而發行的國債得到償還成為可能。于是他寫道:
鑄山難得礦常開,永樂錢荒不再來。
海外有商爭利藪,國中何地筑謻臺?[1]1109
盡管作者在詩中對獲利與否提出了疑問,但其贊賞之情還是顯而易見的。在黃遵憲看來,閉關鎖國,就完全沒有獲利的可能。而開關通商,發展商貿,就帶來了希望。他認為,中國的絲茶傳統悠久,制作工藝精湛,產品質量高,同樣可以通過出口,獲得像日本那樣的經濟利益,甚至能比那更大,所以大力發展商貿是非常必要的。
制定完備的財政管理制度以增加經濟效益。規范的國家財政制度,能使國家各項收入支出皆有據可循,有法可依,這對于國家經濟的發展是大有裨益的。黃遵憲看到,明治維新之后,日本政府積極地聘用外國顧問和雇員來幫助發展新的管理和教育制度,以及新的商業和工業。由于明治政府善于博采歐美各國的長處,采用其大的綱要而根據實際從細處進行修正實行,因而日本的財政得以改變舊的面貌,并利用先進的文明開創了一個新的基礎,各種財政制度日漸完備。日本的經濟由此得到了適時地發展,即便是較重的稅收,由于有了制度保證,使之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收支皆有依據,公眾也都清楚,既避免了國家財政的紊亂,又不會引起國家的動亂,更沒有苛政猛于虎的慨嘆。認識到國家理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黃遵憲自然大力推舉,并以西方各國的理財之法來強調此舉的重要。他說他曾考察過西方各國的理財之法,發現都是征收有制度作為依據,收入支出都遵循一定的程序,支銷也都有確切的數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既公平又清楚,得到全國上下的信任。從歐羅巴到美利堅,不論國大國小,所采用的制度無一不是這樣的。而相比之下,清朝疏于理財,導致了國衰民怨。因此黃遵憲大力提倡國家理財,尤其重視統計和稅收。
握要鉤元算不差,網羅細碎比量沙。
旁行斜上同周法,治譜誰知出史家?[1]1111
詩中所記載的日本統計之大略及習用之法,也正是黃遵憲認可、提倡并希望付諸中國實踐的。
統計之于國家,其重自不待言。而稅收之于國家,其重又更甚。稅收乃一個國家財政的基礎,沒有稅收,國家的一切預算都流于形式,國家的財政大廈也就坍塌了,統計也就失去了實際意義。日本明治政府認識到稅收制度的修訂完善對于國家經濟的發達是非常有利的,于是不斷地制定各種稅收政策以規范稅收制度增加國家財政。明治六年七月,制定了耕地稅。十二月,確定華、士族的個人所得稅。七年七月,頒布了印花稅規則。八年二月,收取煙草稅、車馬稅、酒麴稅。等等。大凡能獲利之事,皆征稅。在《日本雜事詩》中,黃遵憲對此進行了頗為詳盡的記錄。
六干五均官盡備,踦零都數法俱嚴。
禁煙禁酒工言利,獨握牢盆不道鹽。[1]1108
稅收名目繁多,凡一切經營,無不置于稅收之列。不遵守稅制的,不僅不允許經營,而且還要被罰以重金。黃遵憲認為,中國要發展經濟,增強國力,也應該像日本那樣制定詳備的稅收制度,以規范經濟活動,最大限度地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他還特別注意到了日本的耕地稅。
減租恩詔普醲膏,碩鼠疲民敢告勞。
歸語老農吾土樂,寬仁長戴帝天高。[1]1107
此詩記錄了日本所實行的耕地稅。在小注里,黃遵憲將日本的田地租稅與中國相比較,慨嘆中國田地租稅之輕,嘆息之下,實乃對中國稅制不完善所帶來的后果的憂慮。究其根源,是不能根據時代的變化而采取相應的稅收之法,沒有制度保證,以至于稅收雖輕卻招致民怨。因此,他指出,中國的耕地稅改革勢在必行。
此外,黃遵憲對日本使用印紙、界紙(類似于現今的稅票)收稅也很是贊賞。
剪紙頻將花樣翻,司農用印不辭煩。
法同手實名頭會,絕少催租吏到門。[1]1108
由于稅收行之有度,不僅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而且促進了社會的發展。
黃遵憲看到,日本一個島國,僅國家每年所收稅款就多達五六千萬圓,另外各府縣的費用又有數百萬,這個稅收數目是相當重的。然而在日本明治維新中,那些不喜歡新法的人對各種政策頗多指責,而獨獨沒有因為稅收而指責過執政當局。可見,稅收制度的制定和實施是為眾人所接受的,因為其民眾認為稅收是收取自己國家的財物來治理自己國家的事務,最終仍然是用在民眾身上。非但沒有害處,反而能折損富人的財富以利于窮人,調節盈余來填補不足,因此是有好處的。故而黃遵憲認為,應該審時度勢,完善國家稅收制度以利國家的發展。因為在當時,大清國財政已陷入困頓是天下皆知的事實。他認為,由于時代已經改變,在康熙、乾隆統治的盛世年代可以減免的田租賦稅,當今已不能再實行。而國家之所以能成為國家,不是象一人一家擁有恒定的資產就能做到的,想要用一個國家的財力來治理這個國家,除設立租稅之外就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了。他主張仿照西方國家的做法,擇選其主要的方式加以實施,也可從舊有的方式中選取利于當今的方法去進行,以便去除中飽私囊的弊病,將稅費全部收歸國有并向天下公布,這樣就能使各項事業得以振興,使貧民得到救濟,因此不是不能實行的。
學習實施新的農業種植技術以獲取更多的農業收益。在黃遵憲的意識中,農業也是一個國家經濟的基礎,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長久以來實行小農經濟的國家里。而他認為,光靠傳統的農業,不足以推動經濟的發展,所以他倡導引進他國的新品種新技術,發展新農業。
一望高高下下田,旱時瑞穗亦云連。
歸裝要載良苗去,倘學黃婆種絮棉。[1]1154
詩中寫到日本旱稻的種植,認為推廣旱稻可有助于糧食增收。在該詩的小注里他表示,等回國時,一定要購買諸如占城之稻、印度之棉等植物種子帶回,認為就算不能獲利無窮,只要有一點好處,也應當傳播推廣。而且還希望有心進行農業生產的人進行試驗。可見其倡施新農之心。
明治維新之后,日本政府對農業的發展也相當重視。開設了農務局,主要的職責就是勸農務。局中還開設有農學校,專門教授農事之法。日本農業因此呈現出一派新景象。而且日本還翻譯了西方的農事書,學習其農事之法,增加了農業產值。
重譯新翻樹畜篇,勸農官舍榜書懸。
新來學得雞桴粥,夸與人前說秘傳。[1]1153
此外,還從歐洲學得氣筒、樹枝偃曲法、雌雄配合法(即人工授粉)等植物種植之法,推動了日本農業的發展。
初胎花事趁春融,祝語丁寧休洗紅。
一道裙腰頻結束,盡將桃杏嫁東風。[1]1154
由于政府的重視及大力推廣,日本的農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強盛。“早期明治增長的最基本方面,是農業產量和生產力的持續增長,這使得人口得以增長,也使將更多的社會資源用于其他方面成為可能。”[3]306
在黃遵憲看來,日本農家向來墨守陳規,已經相襲了千百年。但維新之后卻由于國家開辦了勸農局,設立了植物園,時時將新法刊登出來告知民眾,而使得日本的農業風氣大為改變,這不由得令人驚嘆。黃遵憲在詩中對日本農業狀況的描摹和感嘆,寄寓了他改革傳統,發展新型農業的思想。
采用西法開掘礦產以增強國家財力。明治維新之后,采礦業得到了更多的重視,礦產被視為對政府收入、貨幣、出口物資及工業生產和機械等具有基礎作用的產業。明治政府不僅將礦山收歸國有,還大力推進技術改良。他們聘用外國顧問來幫助他們完成這個任務,創辦了技術學校來培訓采礦和冶金工程師。由于采用了西方的開掘之法,日本的礦產量大增,為國家增加了收入。
石墨沈沈陰火紅,赤丹成澒出金銅。
百年千歲莫枯竭,下告黃泉上碧穹。[1]1155
在黃遵憲看來,日本的礦產開掘之法非常值得中國學習。因為開掘礦產,既能彌補國家財政收入的不足,也是發展國家經濟的手段之一。他認為,礦產是自然界的造化,自古以來的豐厚積累,為的就是有朝一日供急需之用。清朝的國庫空虛,農業的發展又已進入困境,無法獲得更多的財富,惟有自然形成的礦產能利用。只要學習西方的開采方法,從礦產中獲利是相當容易而且是穩超勝券的,這是個能讓國家富強的機會。況且中國鐵、金、銅等礦藏含量豐富,居于五大洲之首。因此他認為,中國發展礦業,勢在必行。就如眾多饑窮餓的乞丐虎視眈眈于一個積蓄千萬箱財物的富豪之家,就算始終閉門不出,最后也會被破門而入的,這是形勢使然。
革新是為了強國。然而革新并不意味著完全否定,黃遵憲倡導革新,同時也主張發揚國粹,認為古今中外凡一切利于強國之事物皆可借而用之。“潘內伯格在此對基督教末世論的意義加以了新的詮釋。在他看來,古代救贖史所反映的啟示僅是神啟的部分顯現,而位于歷史之中的當代人對啟示亦是一種歷史性認知。人們因歷史的連續性而可追溯過去,覓見其與現今的關聯;但歷史仍在向未來延伸而又使人們不可能窮盡這一認知,故有一種對末世的期盼和等待。”[7]201黃遵憲的希望恐怕也正在于此。
黃遵憲二十一歲時就喊出別創詩界的口號,提出了一系列獨特的見解。認為自《詩經》以來的各種經史傳略、諸子百家作品以及各名家的注疏,不論是官方典籍還是方言、俗語、諺語,凡符合當今的名物,都可以用來入詩;即便是古人創作中未涉及的事物,或者未描寫的意境,凡是自己耳聞目睹的,亦可寫入詩中。這就是他詩歌創作的新主張: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于是在《日本雜事詩》中,他引入了許多新事物、新意境,開拓了詩歌表現的范圍。《日本雜事詩》一改律詩寫景抒情的傳統,用以紀事。以詩的形式,記載了日本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從國勢、天文、地理到政治、文學、風俗、服飾及至技藝、物產等,都書之筆下:大到國家的創建、歷史的演變、政治的興衰、經濟的發展,小到街頭巷里、雜耍游樂,等等。詩歌的筆觸涉及之廣,對于前人來說是不可想象的。另外,黃遵憲還主張詩歌的寫作技巧和表現手法也要不拘一格。既要善于學習古代名家乃至同時代人的創作手法,又要根據實際而有所突破,以達到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否則就不能形成自己的風格而無法自立。這些新主張所帶來的新風格,在《日本雜事詩》中也是顯而易見的。他高擎詩界革新的旗幟,給中國詩壇吹入強勁的新風。而這種革新,在《日本雜事詩》中已可見一斑了。
因此可以說,《日本雜事詩》不僅僅是對日本諸事的記錄,更是黃遵憲革新意識的載體,寄寓他借他國之事變革中國社會的理想,而創作的實踐又體現出其詩歌革新的主張。所以《日本雜事詩》是考察黃遵憲思想及其創作的不可忽視的作品。
[1](清)黃遵憲,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日)大隈重信.日本開國五十年史[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
[3](美)康拉德·托特曼.日本史(第二版)[M].王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美)魯思·本尼迪克特.菊與刀[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5](清)黃遵憲.日本國志(上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6](法)盧梭.愛彌兒[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7]卓新平.當代西方新教神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