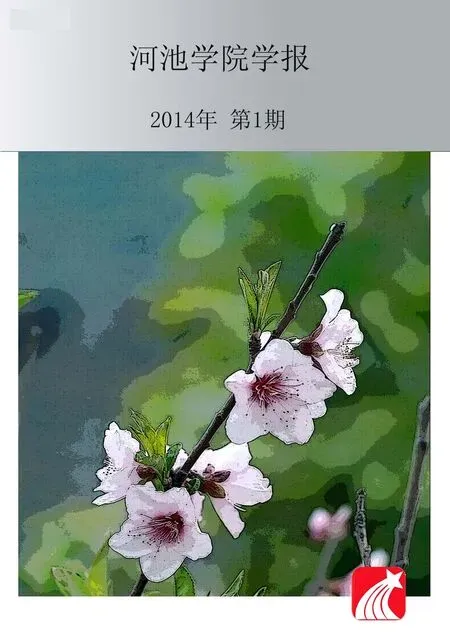文化翻譯視角下探討民族地區非英語專業學生英漢翻譯能力培養
李艷飛
(河池學院 外國語學院,廣西 宜州 546300)
翻譯離不開文化,要想做好英漢翻譯,首先要從較為系統的學習西方文化開始。由于桂西北民族地區非英語專業學生的英語文化背景知識較薄弱,缺乏對文化深層次內容的探究,跨文化英譯漢翻譯能力較差,因而在進行跨文化英漢翻譯時,存在很多弊端,導致翻譯水平低、翻譯文本不理想。本文著重從文化翻譯的視角下,研究如何提高他們的跨文化英譯漢翻譯能力。
一、文化翻譯與跨文化翻譯
關于文化翻譯的定義,謝建平認為:“文化翻譯是指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來考察翻譯,即對各民族間的文化及語言的‘表層’與‘深層’結構的共性和個性進行研究,探討文化與翻譯的內在聯系和客觀規律。”[1]徐珺認為翻譯是“在兩種語言交流的同時進行文化交流”[2]。而楊仕章對文化翻譯則給出了更加簡潔明了的解釋,即“翻譯的實質是跨文化信息傳遞,是譯者用譯語重現原作的文化活動”。[3]因此,在對桂西北民族地區非英語專業學生進行跨文化翻譯培養時,教師需以文化翻譯觀作為指導。
二、非英語專業學生特點英漢翻譯
(一)英語文化背景知識薄弱
作為桂西北民族地區唯一的普通高校,河池學院非英語專業學生在大學期間只安排兩年英語課程的學習。在這兩年的學習中,他們使用的教材主要是兩類——讀寫教程和聽說教程。就讀寫教程而言,無論是《21世紀大學英語》還是《新世紀大學英語系列教材綜合教程》,教材的主要構成均為文章加習題。每個單元談論一個話題,文章是獨立的文章,文章之間缺乏系統的關聯性。對文化背景知識的介紹,也只是片段性的,缺乏整體和系統的介紹。而聽說教材,更是以簡短的對話和文章為主,很難讓學生對英語國家的文化有一個全面清晰的認識。從而導致了學生在這方面知識有限。
由于教材結構的限制,英語教師在課堂上補充的文化背景知識內容,也只能是片段性的。只能針對教材內容,添加與之相關聯的文化背景。由于受課時和教學內容所限,即使教師想要系統的傳授文化知識,也很難做到。
以上兩個原因均導致學生的文化知識輸入較少,加之學生所面臨的考試只有兩類: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和期末考試。而這兩類考試側重點都為語言本身,很少涉及文化,從而使學生學習英語的側重點示為語言本身。
(二)缺乏對文化深層次內容的探究
由于受到課堂教學內容、期末考試、四六級考試等限制,學生無暇顧及文化中深層次內容的學習。比如對古希臘神話、圣經故事、經典文學作品的研讀,除了個別學生出于興趣愛好品讀外,大多數學生是很少涉獵的。圣經故事和古希臘神話等,是西方文化的基石,隨時隨地都會反映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說很普通的名字,如Mary、Mathew、Abraham,都可以在圣經中找到,都代表著某種意義。而在非英語專業學生的知識結構中,這方面的文化內容十分溥弱,導致了在進行英漢翻譯時,英語文化知識“營養不良”,原文表層和深層的含義很難被全面徹底的翻譯出來。
(三)跨文化英譯漢翻譯能力較差
對于與漢語句子結構相似的且不包含文化內容的句子翻譯,學生做得比較好,如“He never acts on his own judgment,but merely waits passively for others to tell him what to do.”這里面,只有“waits passively”翻譯時,需要調換位置,而其他的基本和漢語語序相同。但是當學生遇到如“It is a wise father that knows his child”這類諺語,很容易想當然譯成“知子莫若父”,而實際意義正好與其相反。
其實這里涉及到中國傳統家庭文化和西方家庭文化的差異。中國家庭文化,更注重家長對孩子的教育,“養不教父之過”,由于家長在子女的教育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而“知子莫若父”也就順理成章。而西方文化著重培養的是孩子的個性,強調“individualism”(個人主義)。因此該諺語應譯成“再聰明的父親也未必了解自己的孩子”。
三、翻譯能力培養策略
(一)努力營造英語文化環境,提高對影視翻譯的重視,將更多優秀的影視作品引入課堂教學
如今互聯網上的外文影視作品是學生最容易接觸到的,之前網絡上在線觀看的外文影視作品字幕大都為中文字幕,而且字幕較小。隨著英語逐漸普及,為了迎合觀眾的需求,有的作品的字幕也從中文字幕變為中英文字幕、小字幕變為大字幕。有選擇性的選取合適的外文作品用于課堂教學,是讓學生們了解西方文化的最簡單、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以《Modern Family》(譯作《摩登家庭》)為例,從只有中文字幕到中英文字幕同時出現,字幕也從小字體轉變為大字體,這體現著觀眾的需求,即翻譯的社會需求屬性。隨著英語的逐步普及,人們對外國電影的需求亦不再停留在“只是看個熱鬧”——看著中文字幕了解劇情,觀眾更多的將注意力轉移到中文字幕的翻譯是否準確、是否合乎劇情。英文字幕同時出現,首先解決的是觀眾對英語學習的渴望,其次為某些英語水平更高的人,提供了研究字幕翻譯的機會。同時,也為課堂教學使用提供了前提。
《摩登家庭》的內容比較積極健康,比較適合非英語專業的學生由淺入深的了解美國文化。該劇主要表現的是三個家庭每天發生的事情,所涉及的語言是日常用語,所涉及的文化是美國的家庭文化和社會文化,深入淺出、淺顯易懂,即使在語言上有障礙,這種障礙也會隨著劇情和人物的表演而被化解。而且,大到美國的社會形態,小到美國人的家庭觀念、生活方式、父母對子女在學習方面的態度等,都可以通過觀看該片,形成一定的印象,有助于非英語專業的學生漸入式的了解美國文化。
(二)加強文化里深層次內容的教學
在課堂教學中或課后作業中引入《圣經》故事、古希臘神話等,他們是西方文化的源頭,就像漢語的成語典故一樣,無時無刻不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比如,為什么西方人用“鴿子”和“橄欖枝”象征和平,這涉及圣經《創世紀》中“諾亞方舟”的故事。再比如說英語單詞“narcissus”和“echo”,本意是“水仙花”和“回聲”,但追根溯源,這兩個詞源于古希臘神話里的兩個人物,前一個因為自我陶醉而最終變成一個水仙花,始終孤芳自賞,最后成為“自戀”的代名詞。“echo”的源頭是古希臘神話中的一個森林女神,因為得罪了赫拉,而被施以法術,只能重復別人說過的話,最終演化成“回聲”的意思。若將此類內容引入大學英語課程中來,既能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又對翻譯能力的培養打下堅實的根基。
(三)課堂教學以異化翻譯為主,由異化轉向歸化
“歸化”(domestication)和“異化”(foreignization)是翻譯中常碰到的兩個概念,前者是以目標語言文化為主,后者是以原文語言文化為主。如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的翻譯,David Hawks主要采用歸化譯法,而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則采用異化譯法。
課堂教學以異化翻譯為主,由異化轉向歸化,進行翻譯的二次跳躍,可以加強學生對西方文化、習慣表達的認識,增強學生英譯漢的能力。
首先,從句子結構角度講,英文行文的語序在很多情況下,與漢語大不相同。如《新世紀大學英語系列教材綜合教程》第5單元Text A中第三段的:“A peculiarly honest answer came out of my mouth before I could think”。先譯成:“一個特別誠實的答案溜出了我的口中,在我思考之前”。雖然,這樣的譯文,讀起來比較別扭,也不太符合漢語語法習慣,更像是字對字的生硬的機器翻譯。但這樣的翻譯,對于學生來講,更有助于理解英文行文的習慣。而后,再根據第一次的譯文,讓學生們將這句話,用更符合漢語表達習慣的語言翻譯出來,即為“我不假思索,老老實實地答道”。完成翻譯的二次跳躍,由歸化轉為異化。
其次,從表達形式看,英漢也有很大差異。如這篇文章第7段中的:“The man’s face remained as blank as a clear summer sky”,參考譯文譯成“那人的臉上仍舊一片茫然”。在進行課堂教學時,這句話可以先譯成“那人的臉像晴朗的夏日天空一樣空白”,這樣的譯文更貼近原文的表達,也可以讓學生知道,外國人是如何表達“一臉茫然”的,接著再讓學生進行二次加工,他們很容易會像參考譯文那樣翻譯。
四、結語
桂西北民族地區非英語專業學生跨文化英譯漢翻譯能力培養離不開英語文化背景知識的增強,只有在文化翻譯的指導下,學生跨文化翻譯的能力才能有所提高。
[1]謝建平.文化翻譯與文化“傳真”[J].中國翻譯,2001,(5).
[2]徐珺.古典小說英譯與中國傳統文化傳承[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責任有限公司,2005.
[3]楊仕章.文化翻譯觀:翻譯者悖論的統一[J].外語學刊,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