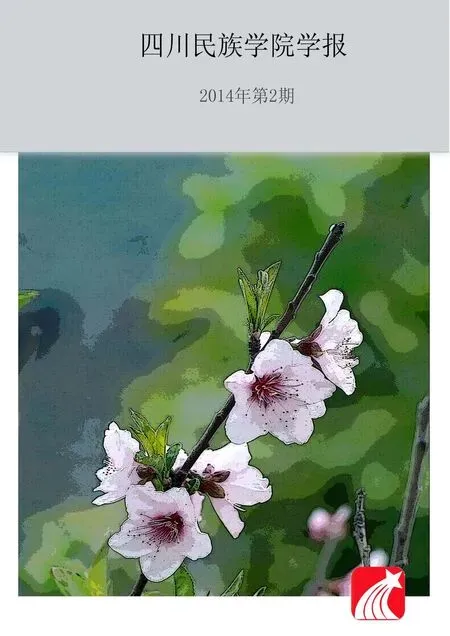從經濟活動看民族同化與認同
楊麗云 董新朝
一、引 言
民族社會學是以民族的特殊社會文化來研究不同民族的社會形態、結構、組織、功能、發展和民族間關系的一門學科,它是由民族學、社會學、社會人類學發展而來的。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它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就研究范式來看,從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角度有民族本身、風俗習慣和社會意識,從西方社會學的民族關系研究來說包括社會的互動、關系、分層和流動。
經濟活動是人類社會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具有多樣性、復雜性的形式和意識表達,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經濟表達,如在經濟類型上就有采集-漁獵、刀耕火種農業、鋤耕山地農業、游牧、畜耕灌溉農業、機耕農業、現代工業農業的區分。經濟作為一個循環流通的制度體系,不只是物質層面的積累和流動,更是一定的社會結構和關系的組織與構建,它不僅涉及生產力諸要素的配置與利用,更是民族社會中人文要素借以傳達文化信息的意義符號,如民族間的同化與認同現象就伴隨著經濟活動而存在。
在民族的經濟活動中,各民族之間為滿足自身的生存需要和經濟要求,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接觸和交流。人的文化屬性總是教人做選擇,我們常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它不一定適應所有的社會事實,但我們卻不能忽視此種現象的存在,在不斷的接觸過程中,不同民族間會相互學習和借鑒,以達成當時所需的社會性本質的一致或相似,并為尋求共同體的保護而努力,這便是各個民族進行的有益選擇——同化并認同。
在民族過程中,民族間的同化和民族共同體的認同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民族現象,是不同人類共同體間進行的一種互動,體現著不同群體的社會意識和社會關系,因而是民族社會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下面我們就從經濟活動來看民族同化與認同現象。
二、同化——理性的“經濟”選擇
百度百科對同化的解釋是這樣的:“同化,是指文化環境不同的個人或團體,與另一不同的文化模式相接觸,融合成為同質的文化”[1],這是一種片面的認識,它將同化視為一種簡單的模式取代現象,含有早期進化論的色彩,也就是“先進的”必將取代“落后的”,是種族中心主義的又一體現。此外,相關的還有依附理論或中心-邊緣模式的提出,即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西方發達國家處于先進的、發達的、擁有話語權的支配地位,而非西方發展中國家則處于邊緣的、落后的、受支配的地位,它們要依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來發展自身,不斷向其靠近,這否定了不同民族自身的發展權力和發展潛能。
然而,同化不只是一個簡單的“高級”取代“低級”的過程,社會學中對同化作的一個有影響的定義來自羅伯特·帕克和歐內斯特·伯吉斯:“同化是一個相互滲透和溶合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個人和團體獲得了其他個體或群體的記憶、情感以及態度,并通過分享它們的經歷與歷史而與它們整合進入到一種共同的文化生活中”[2]。從這點來看,民族同化就是共同體尋找再適應的生存契機的文化手段和意識表達,是一個創造新文化形態的歷史構建過程。
追本溯源,民族同化最初是由生存需求和經濟需要引起的。我們常說沒有誰能夠脫離其他人而獨立存活下去,民族也如此。并不是完整地、封閉地保留了自己所有的文化習慣的民族才是強大的,只有那些在眾多的交流和沖擊中,“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的民族才是真正的“勇士”,也才有活下去的機會,因為它們有著強大的適應機制。一個民族,要想在民族之林中獲得一席之地并長久地存在下去,首先最不可缺的就是物質基礎,而經濟活動就是獲得這一資本的手段,并使之不斷地積累、流動和升值。
一個民族能夠獲得的進步機會取決于它與其他民族接觸的多寡。常言道“三人行必有我師”,在人類社會的經濟文化交往中,共同體各有長短,那些善于學習、借鑒他人優秀之處的民族往往進步的速度都很快,且能夠很好地調整機制以應對變化著的環境。而在這個借鑒和學習的過程中,同化也就隨之發生了。如云南的蒙古族,在脫離蒙古草原的大背景后,缺乏相應的資源使之承續傳統的畜牧業,便轉而向周邊的漢族、彝族等其他民族學習定居農業,形成了一套適應當下環境的生計方式和生存知識體系,得以在云南“定居”下來。再有,我們知道回族是與漢族文化共通點最多的民族,它擅長經商,在與漢族人進行經濟交往的過程中,它學習漢語,使用漢文,仿效漢族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習慣,長此以往下來,它的民族社會性不斷向漢族靠攏,與漢族的差異不斷減少,最終成為在中國各地均有分布、占據很大人口比重的民族,且經濟水平普遍較高,當然,這并不只是漢化的成果,它也與該民族經商的傳統和精明的商業頭腦有關。
民族同化有自然同化和強迫同化兩種,就民族同化的經濟性來看,它應屬于自然同化,是本民族為尋求生存和發展機會的自愿性行為,是在生存與消亡之間所做的理性選擇。民族的同化過程,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是一個客觀的存在,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民族相互間都在進行著同化行為,也不意味著所有的民族都同化為一個模式,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主體的選擇起著重要的作用。同化既是民族主體自主選擇的道路,也是他們積極適應環境的體現,是他們賴以存在和存活的橋梁。
三、認同——理性選擇的主觀確認
在民族共同體的發展進程中,同化是民族對自身“利益最大化”所做的選擇,而認同則是對這種選擇的主觀確認,它是人們在自然環境脆弱性和人類群體脆弱性面前急需找尋的一種心靈歸屬。所謂主觀確認,其實就是人們的社會性要求其對一定的社會儀式、風俗習慣、價值觀、行為模式等有一致性的尋求,最終形成具有“利益共同性”和“意義共同性”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獲得更多更好的社會機會,以滿足其發展的需要。認同伴隨同化出現,或是同化之后的獨立產物,或是在同化過程中作為維系的媒介材料,它與同化相互關聯又相互分離。
“認同是一個來自于心理學的詞匯,經埃里克森的使用,表示自我與他人的關系。從這層意義出發,學者們才把民族、國家等一些客體對象納入到認同理論研究中。認同主要有三層含義:一是‘同一’,一個事物的性質和屬性沒有發生改變;二是‘歸屬’和‘確認’,一個群體的成員通過共同特征的辨識而歸屬于某一個群體;三是‘贊同、同意’。”[3]由此看來,認同是人們主觀意愿的表達,但卻是一個客觀的過程。它由一系列的行為組成,這些行為都是服務于自身的利益需求的。認同有多種不同的表達,就認同的情境來看,可分為歷史性認同、場景性認同,就認同的對象來看,有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公民認同和社會認同,而從條件來看,可包括記憶認同、符號認同、地域認同、權力認同和利益認同。
歷史性認同和記憶認同相關,它們都是基于本民族的歷史性記憶而存在,如湖南桑植白族對大理白族的認同就是基于它們對祖先的記憶而實現的,是以追溯的方式來鋪展尋找相通點的道路,并在此基礎上借助文化符號而得以表達集體意識,形成認同。
場景性是主體在不同的情況下為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進行的一種認同選擇,它具有不穩定性,是民族搖擺心理的一種體現。就邊境民族來說,場景性認同多與其所在或相鄰國家所施行的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相關,它會選擇現下對自己有利的一方來進行認同,更多的是一種國家認同。在國內的某些民族地區,場景性認同也普遍存在,如在怒江丙中洛地區,因獨龍族、怒族人數較少,所得的優惠政策較之傈僳族多,因此部分傈僳族在進行民族成分登記時會說自己是獨龍族或怒族,問及原因,回答說它們所得的以直接的經濟利益為代表的優惠政策更多,或許,在其他情況下,它又堅持自己原本的民族成分。
國家認同是一個政治概念,它是公民對自己歸屬的國家的一種認知以及構要素的一種評價和情感,是族群認同和文化認同的升華。“公民認同是國家認同的核心,對維系國家凝聚力的至關重要”[4],影響著國力的消長和國家的穩定,包括多民族國家中人口少數、文化弱勢民族的認同,也包括多民族國家中人口多數、文化優勢民族的認同。社會認同是指個體認識到自己屬于特定的社會群體,也認識到群體成員給他的情感和價值意義,是社會成員共同擁有的價值、情感和行動取向的集中體現,注重歸屬感,是一種集體觀念的升華和泛化。民族認同是社會成員對自己所歸屬的民族的一種自覺認知,側重于文化層面的認同,是一個民族力量的源泉。
人們一般會借助一定的媒介來達到認同的歸途,如文化符號、記憶、地域、權力和利益等,而在其中各因子又不是絕對獨立存在的,如記憶就依賴于符號而存在,利益也離不開權力,地域內部包括了符號、記憶、權力和利益等,它們共同作用組成了認同賴以存在的基礎。總之,認同不單單只與其中一點相關,它處于巨大的交錯繁雜的網絡中并由此凝結而成。
認同是為了組成一個具有利益共同性和意義共同性的共同體,其目的在于更好地應對各種公共危機,表達使自己成為環境的主人的生存意識,重塑自身的身份,建構一個適于所在環境的關系網絡,保護各參與人員的權利和利益,使其積極參與公共生活,遵循共同體一致的社會性,并在其中自為自在地發揮自己的潛能,實現發展的需要。
四、一些問題與思考
本文主要以經濟活動為切入點來展開對民族同化與認同問題的探討,以上分別對同化與認同作了討論,但個人思忖覺得還有些問題需要交代,在此便一一列出。
第一,民族同化與認同是涵蓋內容廣泛的概念范疇,涉及政治、文化、信仰、民間文學等方面,單從經濟角度來講是有失偏頗的。本文以經濟活動為切入點,只是想表達筆者的一些思考,因此邏輯混亂與材料支撐欠佳之處甚多,還望海涵。
第二,認同是一種文化心理的再現與構建,是在認知的基礎上實現超越,“對民族文化心理認知是民族跨文化交際的必須過程,實現民族文化心理的超越是目的”[5],要在跨文化交流中自主地進行自我認同的“生產”。它并不是一個表面的認同現象,但目前大多經濟活動中的認同仍是一種片面的認同,是在物質層面上對個人利益的一種選擇,有別于內在因素的制度性分解和重組,缺乏深層的自我反思。
第三,我們不能簡單、片面地來看民族同化與認同現象,不能只從經濟層面來實現,更不能為了實現經濟的發展而忽略文化和社會的因素,在實現基礎性物質層面的發展時,我們也要重視文化的多樣性和社會內涵的多元性。社會性本質的統一并不意味著所有共同體完全成為同一模式的復制品,而是為實現自身和群體的更好發展而進行的一種平行、同質行為的認可與確定,是一個仍需保持多元生機的意識表達。
第四,民族認同是一種較低層次的認同,它需與區域認同合作而最終達到國家認同的層面。“多民族國家中的民族認同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個體同時擁有兩種 (甚至多種)不同形式的認同,而是在于在個體的認同層次結構中,把何種歸屬置于優先的級序,并以此作為自己效忠、盡義務和責任的歸屬單位”[3],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建構,就相對于作為中華民族的各組成部分的民族認同而言,它是一個高層次的民族意識認同,也是在國家層面實現國家認同的體現。
[1]百度百科詞條——同化 [EB/OL] .http://baike.baidu.com/view/183587.htm
[2]馬戎.西方民族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p91-112
[3]高永久、朱軍.論多民族國家中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J].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p28、p31
[4]都永浩.民族認同與、公民、國家認同 [J].黑龍江民族叢刊,2009年第6期
[5]劉世理、范葳葳.民族文化心理的認知與超越[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p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