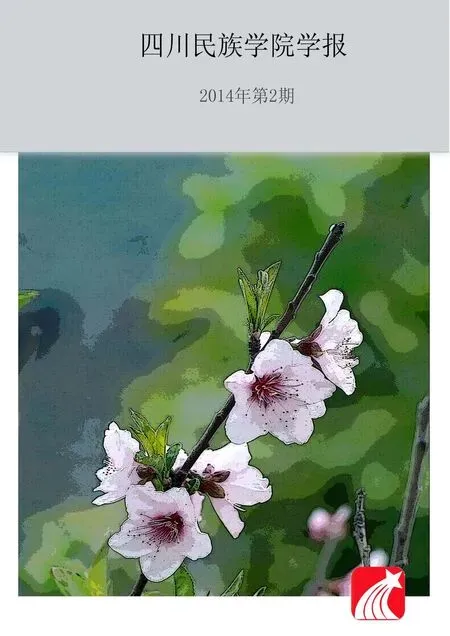漢代詩歌中“蕩子”之意淺析
高 山
蕩子 (或作宕子、游蕩子)是漢代詩歌的一個較為常見的形象。一直以來,研究者多沿用《文選》李善注的解說,認為蕩子與游子意義相同,通指遠游之人。但筆者在閱讀中發現李善注值得商榷,蕩子與游子之間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差異,對于這種差異的準確把握,對于理解詩歌真正涵義十分重要。本文擬對漢代蕩子一詞進行辨析,指出其在漢代的真實含義為征役之人。
關于蕩子的解釋,最早見于李善注《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列子》曰:‘有人去鄉土游于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狂蕩之人也。’”[1]由于李善注的巨大影響,使后人多理解蕩子為游子,一直缺少異議。雖然中國古代多采用物之別名以顯文雅不落窠臼,如以菡萏、芙蓉指稱蓮花。但蕩子與游子文雅無別,似乎沒有不用游子而另生蕩子一詞的必要。《列子》一書雖然《漢書·藝文志》有著錄,但是在后代影響不大,直到晉代方有張湛作《列子注》。且其序曰:“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并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并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于是唯赍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馀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2]在這里可以看出,雖然《列子》一書有傳,但并不為人所重,而且多有缺失,需要多種版本方能一睹全貌。這與六經及《老》《莊》形成鮮明的對比。而且從漢魏時期的注疏上看,《列子》也基本可以忽略。《隋書·經籍志》更是沒有收錄此書,雖然原因不明,但也表明當時此書并不受士人重視。《列子》一書并不普及,那么詩歌作者與讀者未必能夠了解,選取這一形象可能還需要對讀者群體進行一番文化普及,這也是詩人未必能夠采用《列子》一書的原因。而且今存漢代記載蕩子多為樂府詩,樂府詩本就多是漢代的謠諺,屬于民間創作,漢末詩語多淺顯直露、口語混雜即是較好的證明,這與后代征引僻典以炫耀自己文化修養是不同的。馬茂元先生關注蕩子與游子不同的問題,認為“‘蕩子’,指長期浪漫四方,不歸鄉土的人,與游子義近而有別“認為游子是“東漢王朝為了加強其統治,一開始就繼續奉行并發展了西漢武帝劉徹以來的養士政策,在首都建立了太學。……在這種政策和制度下,當時的政治首都洛陽就必然成為求謀進身的知識分子獵取富貴功名的逐鹿場所。《古詩十九首》里的游子,就是這樣背井離鄉,漂流異地的。”其后又云:“《十九首》里所反映的游子生活,正是漢代知識分子飄蕩四方的傳統的‘游學’生活方式。”[3]馬茂元先生看到了游子與蕩子的差距,對游子進行了重新解讀,其實質也是贊同了李善注關于蕩子一詞的解釋。
我們看看漢代詩歌中關于蕩子的記載。樂府古辭《東光》曰:“諸軍游蕩子,早行多悲傷。“逯欽立先生引《古今樂錄》云:“張永《元嘉技錄》云:‘《東光》舊但弦無音,宋識造其歌聲。’”認為“似此曲西晉前尚無歌辭,宋識始造新詩,應再考”[4]。雖然此詩所作時間不能確定,但游蕩子在這里很明顯是指代從軍服役之人。《雞鳴》:“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4]這里的蕩子似乎也應為從軍之人解,否則后面的“天下方太平”一句便不好解說。《樂府解題》作:“初言‘天下方太平,蕩子何所之。’”[5]那么“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也可以理解為倒裝句式,即其語序可解為“天下方太平,蕩子何所之”,這樣就更容易理解。以游子解釋,不論是經商或是游宦,天下太平正是其遠游的最佳時機,似乎不應該出現這兩句所表現出來的疑問或是擔心的口氣。而作服役之人則意義自明:如今天下太平,你這樣的從軍之人還要去哪里呢?雖然漢樂府存在“前后辭不相屬,蓋采詩入樂合而成章邪?抑有錯簡紊亂邪?后多放此”[4],但一般兩句之間的聯系是緊密的,此處作服役應比作游子解更為合理。最能提供參考的是《烏生》一詩:“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唶我。秦氏家有遨游蕩子,工用睢陽強蘇合彈。左手持強彈兩丸。出入烏東西。唶我。一丸即發中烏身,烏死魂魄飛揚上天。”[4]這里烏是在秦氏家的桂樹間被秦氏家的游蕩子所射殺,也就表明秦氏家的游蕩子是在家的。那么這里的游蕩子很明顯不能作游子解,或者說不能作《列子》中所謂的“狂蕩之人”解。因為“狂蕩之人”是“游于四方而不歸者”,是沒有歸家之人,游子含義也是離家未歸之人,在家是不應該被稱作游子或者“狂蕩之人”的。
對蕩子進行較為明晰解釋的為五臣注:“‘今為蕩子婦’,言今事君好勞人征役也。婦人比夫為蕩子言夫從征役也。臣之事君亦如女之事夫,故比而言之。”解釋“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二句為:“言君好為征役不止,雖有忠諫,終不見從,難以獨守其志。”[1]五臣注與李善注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即五臣認為蕩子是指征夫,即從軍之人,這與李善所認為的游子之意不同。而五臣注的蕩子一詞即應是對前代文獻梳理所得,而不是李善僅指明其疑是出處,而不明其在詩歌中的特殊含義。按照五臣注的說法,就區分了蕩子與游子的區別,即蕩子雖然也有遠游之舉,但卻是征役驅使,與游子自覺性地背井離鄉有較大不同。雖然五臣注可能由于發揮性或者說對于詩歌的義理解釋未必完全正確,但對于蕩子的解釋應該是比較符合漢代蕩子的真實含義的。
漢代的賦稅多與軍隊相關。《漢書·刑法志》云:“稅以足食,賦以足兵。”[6]《食貨志》云:“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7]則賦是專門以供軍用者。不僅要出錢糧,還需要有輸作[8],漢代對此有較為清楚的記載。賈誼《新書》云:“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長久也。……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之為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令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跡也,竊以為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強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履蹻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9]由于賦稅為提前知曉,所以才能出現在家而被稱為蕩子者。從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可知,筑城之人亦可視為軍士,故云其為“卒”,而且說“男兒寧當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長城”,這都說明當時的征役也是與征兵相通的。
而游子一詞則較為明晰,是指離家遠游之人,而且《漢書·高祖本紀》載:“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招故人父老子弟佐酒。……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后吾魂魄猶思沛。’”[10]《文選》注游子一詞時均引此說,這就為游子的思鄉內涵定下了基調,漢代文獻中出現的游子都具有這一特性,所以有些詩歌在處理思鄉時并不直言,而是采用較為委婉的寫作方法。如《古詩十九首》其一: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馀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此詩“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返”句六臣注皆謂“浮云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毀忠良。故游子之行,不顧反也”,并引“《文子》曰:日月欲明,浮云蓋之。陸賈《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云之鄣日月。《古楊柳行》曰:讒邪害公正,浮云蔽白日。”此詩乃是以游子喻貶謫之臣,以朝廷喻故鄉。其中游子思鄉之意化在“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二句之中。李善注引《韓詩外傳》曰:“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1]也就是說此篇游子用作比興手法,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其思鄉的內涵。而蕩子則沒有這種文化承載,所以出現蕩子時多是以妻子懷念的口吻,或者說,蕩子雖然也多為離鄉之人,但著重并不在思鄉,而在于家人 (主要是妻子)對其的懷念。可能就是因為蕩子并沒有思鄉的內涵,所以常常是以婦人的口吻埋怨其不歸。這樣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詩歌內容。詩歌中出現游子多是以游子身份著眼,著重表達其思鄉之情。而出現蕩子則是以其妻子身份著眼,著重表達不歸的怨恨之情。《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云:
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全詩處處以倡家女著眼,并無一句言及蕩子的思鄉之情,甚至從字里行間感受到的是妻子認為蕩子樂不思蜀,缺少鄉情的埋怨。這與游子的精神內涵是不同的。
托名蘇武的《燭燭晨明月》云:“征夫懷遠路,游子戀故鄉。”對于此句一直少有關注,這其實對于理解漢代詩歌的思想有很大的幫助。游子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對家鄉的思念,其描寫的角度一般是以思鄉為主。“征夫懷遠路”則與游子不同,對于征夫的描寫雖然也表達其對家鄉的眷戀,但更多是對夫妻之情的懷念,這其實也是游子與蕩子不同的所在。
漢代之后的蕩子形象,基本均出自《青青河畔草》,與思婦相關。如曹植《七哀》詩云:“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嘆有余哀。借問嘆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愿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11]曹植此詩明顯出自《青青河畔草》,宕子即為蕩子。庾信《蕩子賦》其序即曰“陳思王詩曰: ‘借問嘆者誰?云是蕩子妻。君行十余年,孤妾常獨棲。’故作蕩子賦,乃離別之辭也”[12]。庾信的離別之辭概括了《青青河畔草》的本質。《青青河畔草》雖然采用了蕩子與思婦的形象,但不能清楚表達蕩子的征役身份。所以曹植所擬也只是離別,而無蕩子的身份描寫。庾信《蕩子賦》將此離別具體化,或者說是將蕩子的身份具體化:“蕩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隴水恒水合關山惟月明,況復空床起怨娼婦生離。”將蕩子定義為征役之人。而且《燕歌行》亦曰:“自從將軍出細柳,蕩子空床難獨守。”[12]將思婦的思念特定為征戍之人,這也是征夫思婦主題的形成。與庾信同時的蕭綱《雉朝飛操》:“少年從遠役,有恨意多違。不如隨蕩子 (或作游蕩),羅袂拂臣衣。”[4]此詩可作兩解,一為從役之人與蕩子相對。一為從役之人即是蕩子。前者從役與遠游并無實質區別,基本不太成立。而后者則較為合理,且又有作“不如隨游蕩”,雖然如此里面就不顯示蕩子一詞,但總體意思也是承接上文,而沒有轉折之意,也就是表達閨婦希望隨夫從軍,而不是與游子作比。雖然《青青河畔草》中只是表達了離別之愁緒,對于蕩子的身份沒有做具體的描寫,但后代其實還是將其理解為征夫思婦之作,六臣注《文選》時很可能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
蕩子應為服役之人,尤其多為軍中服役,與游子有較大的區別,似不應等量觀之。《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一詩也應為思婦懷念征人之作,而非簡單的思念游子之作。
[1]蕭統編,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選 [M].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p538
[2]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全晉文[M].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p2256
[3]馬茂元.古詩十九首初探[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p113、p19、p21
[4]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九 [M].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p256、p257、p257、p258、p1915
[5]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八[M].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p406
[6]班固.漢書·卷二十三[M].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p1081
[7]班固.漢書·卷二十四[M].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p1120
[8]呂思勉.秦漢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9]王明洲、徐超.賈誼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p115-116
[10]班固.漢書·卷一[M].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p74
[11]趙幼文.曹植集校注 [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p313
[12]倪璠、庾信、許逸民.庾子山集注 [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p91、p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