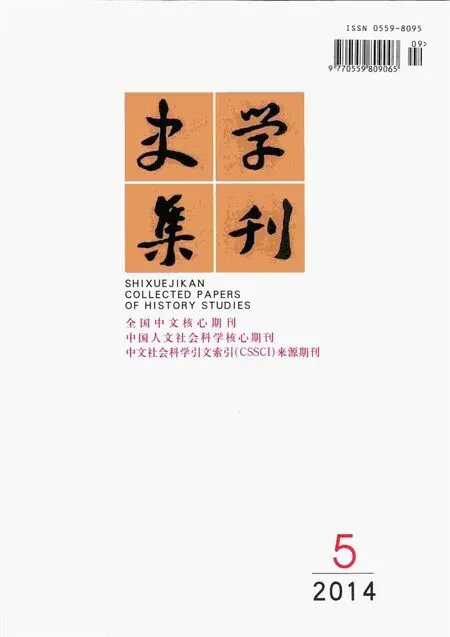從歐洲國際體系到全球性國際體系——基于歷史和理論的雙重視野
孫麗萍
(吉林大學文學院,吉林長春130012)
歷史學和國際關系學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一方面,歷史離不開理論的指導,理論的總結和升華有助于歷史學家從龐雜的歷史現象中提煉出深層的機理;另一方面,歷史理解是國際關系研究的基礎,國際關系的歷史論述、思考和解釋對理論研究有著重要意義。羅伯特·杰克遜和喬格·索倫森強調,“歷史不但是研究國際關系的起點,也是國際關系理論必不可少的指南和矯正”。①[加]羅伯特·杰克遜、[丹]喬格·索倫森著,吳勇、宋德星譯:《國際關系學理論與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頁。赫德利·布爾指出,“歷史研究是理論研究自身的主要伴侶”。②[英]赫德利·布爾《1919-1969年的國際政治理論》,[美]詹姆斯·德·代元主編,秦治來譯:《國際關系理論批判》,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頁。作為連接兩者的引橋,國際關系史的編纂需要歷史和理論的雙重支撐。歐洲國際體系擴展為全球性國際體系是國際關系歷史演進中的一個關鍵節點,這一轉變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國際關系的歷史演進有兩個最為重要的動因:第一,國際體系主導單位的變化,部落、城邦、帝國、主權國家等人類組織形態的演進是推動國際關系嬗變的核心動力;第二,交往方式是衡量國際關系變革的另一標準,互動規模擴大、互動模式多樣化及互動能力的提升是國際關系變革的先聲。如果依據這兩個標準,發端于歐洲的主權國家的全球擴張和互動能力的提升是推動歐洲國際體系發展為全球性國際體系的核心動力。
主權國家本質上是一種歐洲現象,但在其早期形式絕對主義君主國出現后的幾個世紀當中,它與中東、亞洲的古老帝國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酋長制、部落制、王國等人類組織形態共存于同一時空。直至19世紀下半葉,隨著主權國家形態從主權在君的絕對主義逐步轉變為主權在民的國家形式,人民由臣民轉變為公民后,主權國家實力大增并迅速崛起為歐洲人創造的全球國際體系中的主要單位類型。1500年,歐洲人控制了全球陸地面積的7%。到1800年,他們控制了35%的陸地面積。到1914年,他們實質上已改變了三大洲的人口分布(南北美洲和澳洲),并控制了84% 的世界陸地。③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 -1990,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p.183.民族主義的產生和傳播是促成早期絕對主義國家轉變為主權在民的現代民族國家的關鍵要素。作為一種現代性的政治意識形態和行動,民族主義于18世紀末和19世紀在歐洲發展起來,時間上與工業化的興起緊密相關。民族主義帶來了國家形態的一場革命,“通過統一市場、行政管理體系、稅收與教育,民族主義打破各種形式的地方主義,方言、習俗與宗族,有利于創建強大有力的民族國家”。①Anthony D.Smith,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A Critical Survey of Recent Theories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New York:Routledge,1998,p.1.
民族主義與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共同提升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實力,為歐洲國際體系的全球擴張提供了關鍵性的物質權力。隨著民族主義的高漲,普遍義務兵役制應運而生,人口成為衡量一個國家軍事實力的重要指標,19世紀末歐洲各個大國人口出生率的變動成為衡量其國力的關鍵要素之一。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是一場全新的、革命性的技術變革,它以電力的廣泛應用、內燃機和新交通工具的創造、新通訊手段的發明和化學工業的建立為主要內容。它產生的結果之一,是歐洲國家實力的大幅度提升。保羅·肯尼迪指出,截至1900年,歐洲的工業資本與1750年相比增加了18倍之多,而當工業化成果轉化為軍事用途時,實力差距即被進一步拉大,使歐洲國家的軍事資源數十甚至百倍于落后地區。②Kenneth Waltz,“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XVIII,No.4(1988),pp.149-150.現代民族國家是一種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比其他任何單位更有效率的新單位,正如安東尼·吉登斯所言:“民族-國家是擁有邊界的權力集裝器,是現代時期最為杰出的權力集裝器。”③[英]安東尼·吉登斯著,胡宗澤等譯:《民族-國家與暴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45頁。
在歐洲國際體系向全球性國際體系轉變中,互動能力的進步和提高是至關重要的。“互動能力是指圍繞體系投送人員、物資、信息、貨幣和軍事力量的能力。由馬力和帆船等農業技術所主導的體系與以鐵路、輪船、電訊和飛機為內容的工業技術所主導的體系相比,互動能力要差很多”。④[英]巴里·布贊、喬治·勞森著,顏震譯:《重新思考國際關系中的基準時間》,《史學集刊》,2014年第1期。19世紀的輪船、鐵路、運河和電報極大地促進了歐洲現代民族國家互動能力的增長,使得距離和地理因素不再是國際體系的主要決定性因素,并推動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以不同尋常的速度和強度全球傳播與深化。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個在地理空間上囊括全球、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為基礎、歐洲現代民族國家為主導、歐洲外交慣例為規則的全球性國際體系初步形成。與歐洲國際體系相比,它具有以下的特點:
首先,歐洲不再是現代國際關系權力的唯一中心,美洲體系和東亞太平洋體系開始興起。全球性國際體系形成之初,并不僅僅是一個擴大了的以歐洲為唯一中心的體系,以美國為中心的美洲體系和較為復雜的東亞體系對歐洲國際體系事態的發展開始產生重要影響。美日兩國均為現代國際體系中的非歐洲國家,并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同時崛起為太平洋海上強國。如果說美國是歐洲的“衍生物”,日本則是歐洲的“仿制品”。美日的崛起表明這兩大體系不再被動地接受歐洲權勢大國的權力政治和秩序安排,它們不僅對各自的區域秩序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美歐亞三大體系的互動還直接促成了整個歐洲國際體系的轉變。這是自1648年歐洲現代國際體系產生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作為新大陸的美洲和古老文明之一的東亞的事態對歐洲體系產生了重大和深遠的影響。
當歐洲權勢大國將現代國際關系體系擴展到全球之際,其自身的多極均勢格局卻日益走向衰落。德國的崛起打破了歐洲內部的權力平衡,歐洲已經無法憑借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全球性國際體系所面臨的諸種問題。一戰后建立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是一個雜糅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和英、法政治家傳統現實主義的產物。作為第一個全球性國際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存在著諸多問題,傳統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形態及其主導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危機問題、大國權力失衡問題等,特別是德、日、意這三個“修正主義國家”,它們對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不滿,要求改變現狀,重新確立其國家在戰后經濟和政治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諸種問題交織在一起,并最終演變為德日意法西斯主義、英美新自由資本主義和蘇聯式社會主義的矛盾與沖突,新自由資本主義和蘇聯式社會主義聯合起來戰勝了法西斯主義,美蘇對抗的兩極時代來臨。
其次,國際關系主導單位——現代民族國家形態日益多元化,多種意識形態和大國權力沖突劇烈。1870年之后,由于工業化的不斷發展和工人階級作為一種社會政治力量的崛起,西北歐國家和美國內部的政治民主化進程開始漸進式發展。但是,英美式新自由資本主義并不是現代民族國家唯一可能的形態,20世紀30—40年代,英美式新自由資本主義、蘇聯社會主義和德意日法西斯主義之間展開了激烈的沖突和較量。最為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在二戰后演變為多個社會主義國家聯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國家治理和意識形態的矛盾和沖突在二戰后凸顯并主導了20世紀后半期全球性國際關系歷史的進程。
第三,全球化時代國際關系的治理規則開始從歐洲無政府狀態下的多極均勢轉變為大國合作下的集體安全,一戰后的國際聯盟和二戰后建立的聯合國都是集體安全的產物。同時,國際關系也開始悄然突破以民族國家為中心,主要關注戰爭與和平的歷史敘事,開始關注非國家行為體出現及其在國際關系中發揮的作用。從1865年第一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電信聯盟成立,1909年世界上的國際組織共有213個,這一趨勢在二戰后進一步增強。
最后,非西方世界開始了爭取民族獨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并以主權平等的身份加入現代國際體系中,這是全球性國際關系中一個新的內容。日本是非西方世界中第一個成功現代化的國家,其他的殖民地和半殖民人民也學習西方的政治革命、科學與技術革命,一戰特別是二戰后一大批亞非拉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它們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現代化模式之間進行了選擇或者嘗試建立新的國家發展模式。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在部分接受西方主導的現代國際關系規則和慣例的同時,也嘗試反抗或改造現有的國際規則和機制。
綜上,全球性國際關系史的研究內容極為豐富,它上承多元并存的前現代國際關系,下啟后冷戰時代國際關系的轉型與裂變,是一座需要深度挖掘的學術知識礦藏。唯有借助多重視角和多種理論工具,研究者才能探尋到其中的智慧資源,思考歷史,體察現實,預知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