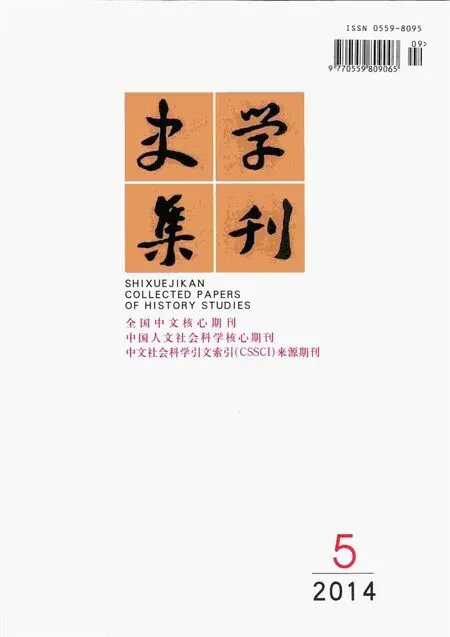論中國古代史籍對四夷的體系化記述模式
關志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北京100081)
中國古代有著深厚的民族歷史撰述傳統,古人留下了數量浩瀚、形式多樣的民族史著作。雖然有些民族也以漢字或本民族文字記述本民族的歷史,但這些著作出現的時段較晚,數量也相對有限,從整體上看,現存的民族史文獻的撰述主體是中原地區的官員或學者,他們主要是從華夏、中國或中央王朝的視角來進行歷史撰述的。經過漫長的發展,民族史撰述形成了比較穩定的記述模式,其中對四夷的體系化記述最具有代表性,它主導了歷代民族歷史的記述方式,并對古代政治觀念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一定意義上說,理解四夷的體系化記述模式是研究中國古代民族史學史的一個核心問題。
一、商至春秋時期的華夷分際
從傳世及出土的文獻來看,商人關于周邊各族群的記述就已經與地理方位聯系起來。商人稱周邊民族政權為“方”,商人的記述中有“多方”,包括土方、羌方、鬼方、人方、井方等,①孫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603-617頁。這些“方”是相對于“中商”、“中土”而言的。在商甲骨卜辭中還出現了“四方”、“四土”、“四單”等詞匯,與中央的大邑商相對應,這大致構成了五方的輪廓,成為商人觀念中的政治空間結構。商的政治中心地位通過“方”或“多方”來突出、體現,商“祭祀、宇宙中心‘王族祖先’通過異族世系來進行對比、襯托。方與四方明確了商之政治、宗教中心性,把‘中心’和‘異類’、‘外部’、‘邊緣’區分開”。②參見王愛和著,金蕾、徐峰譯:《中國古代宇宙觀與政治文化》第二章“四方與中心:晚商王族的宇宙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頁;另見邢義田:《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征意義》,《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86-94頁。周人繼承了商的宇宙觀,強化了中心對四方政治統御的觀念。在先秦典籍所記載的以周王室為中心的五服制、九服制③參見蔡沈:《書經集解》卷二《禹貢》,《四書五經》本,中國書店1985年版,第37-38頁;(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彭林整理:《周禮注疏》卷三九《職方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9頁。中,蠻夷、戎狄也被安置在邊緣的位置,對五服制較典型的記述如《國語·周語》云:“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諸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雖然周時現實的政治空間未必如此整齊,但可以確定的是,周人以周王室中心建構了一個以禮制為表現形式的等級化政治體系,而蠻夷、戎狄等異族則被置于這個體系的邊緣。①參見羅志田:《先秦的五服制與古代的天下中國觀》,《學人》第10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周人的祖先后稷原為夏部落聯盟的一員,商滅夏后,周人竄入戎狄之間,但周人以夏自稱,克商后,封建武王兄弟之國及姬姓之國有數十個,這些封國遍及中央平原地區,它們有共同意識,自稱“有夏”、“區夏”,如《尚書·康誥》云:“惟乃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尚書·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書·立政》云:“……帝欽罰之,乃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西周國家是一個由不同成分構成的綜合體,它不僅僅包含了周,同時還接納了有著不同種族背景和文化傳統的人群。在周人看來,未納入分封體系,不尊周人禮儀的人群都可能是異類,相對周邊族群,諸夏共同體意識逐漸形成。
春秋時,在與周邊族群的資源競爭過程中,諸夏的認同感逐漸增強,華夷分際日益明確,諸夏開始講究華夷之別,認為華夷有其天然界限,不能混淆,這是各諸侯皆認可的基本政治原則。如《左傳·僖公二十一年》云:“蠻夷猾夏,周禍也。”《左傳·僖公二十五年》云:“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左傳·定公十年》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華夏與各民族都通過對方來認識自身,主要以禮儀、語言、飲食、衣服等方面的差異為標準。華夏以自身的禮制為標準對周邊民族進行描述,實際上,夷有自己的禮,只不過不為華夏所認同。如周夷王之時,楚君熊渠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②《史記》卷一四《楚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692頁。《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載:“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發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了晉國范宣子與戎子駒支的一段對話,戎子駒支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論語·憲問》云 :“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但這種相互認識不是對等的,華夏占據了主導方面,華夏強調“非我族類,其心必異”,③(戰國)左丘明撰,(西晉)杜預集解:《左傳 (春秋經傳集解)》成公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72頁。文獻中對戎狄的評價基本是負面的,如“戎狄豺狼,不可厭也”、④(戰國)左丘明撰,(西晉)杜預集解:《左傳 (春秋經傳集解)》閔公元年,第214頁。“狄無恥”、⑤(戰國)左丘明撰,(西晉)杜預集解:《左傳 (春秋經傳集解)》僖公八年,第266頁。“戎狄無親而貪”⑥(戰國)左丘明撰,(西晉)杜預集解:《左傳 (春秋經傳集解)》襄公四年,第817頁。等。周人基于華夏意識蔑視蠻夷戎狄之人,周的太史史伯就明確表示:“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夷、戎、狄之人也。”⑦徐元浩撰,王樹民、沈長云點校:《國語集解》卷一六《鄭語》,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461-462頁。
春秋時期,中原地區一度是華夷雜居的狀態,隨著周王室控制力的衰弱,一些諸侯國開始通過戰爭擴展自己的疆域,并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華夏的集體認同意識不斷強化,華夏與周邊族群的戰爭不斷,這些少數族群或被同化,或被驅逐到邊遠之地,同時,華夏的認同需要一些“敵對的他者”來強化其邊緣。⑧王明珂:《華夏邊緣》(增訂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頁。華夷的地域之分也逐漸清晰起來,華夏勢力也逐漸向周圍延伸,四夷在空間上逐漸被邊緣化,在此基礎上,當時的華夏諸侯開始有意識地建構記述民族問題的理論體系。
獨特的地理條件對中國早期的人群分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中原地區尤其是黃河中下游地區適于農耕,而周邊的山地、草原的環境不如中原地區優越。①后世也強調民族分布的地理意義,《周書·異域》:“是知雁海龍堆,天所以絕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舊唐書·狄仁杰傳》記載了狄仁杰也曾上表論說了這種關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新唐書·天文志》提出了“兩戒”的概念,“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并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夏、商都占據了中央平原地區,就西周而言,其政治中心是渭河谷地,后來又在東部營建了行政與軍事中心洛邑,其在東部平原上的封國是基于地緣政治上系統規劃的結果,在渭河谷地至洛邑的權力中軸線上,眾多的諸侯封國呈放射狀向外分布。②李峰著,徐峰譯:《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頁。中原地區農業發達,在此基礎上形成較大的民族共同體,而周邊的少數族群由于地理因素,居住相對分散,社會形態、經濟生活都落后于中央地區。
中原地區的華夏諸國以漢字記載歷史,在涉及周邊族群時表現了濃厚的華夏主體意識,以華夏的視角記述其他民族的情況。從現存文獻看當時民族種類繁多,如夷、蠻、戎、狄、苗、貊、荊、氐、羌、獫狁、葷粥等。具體某一民族也種類復雜,如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蠻等,同時,夷有淮夷、東夷、萊夷等,戎有昆戎、山戎、犬戎等,狄有赤狄、長狄、白狄等,文獻記述中這些民族稱謂的變化逐漸具有了一定規律性,夷、蠻、戎、狄頻繁出現,泛指某一部分的少數族群,同時也出現了蠻夷、戎狄等名詞,甚至以“四夷”一詞作為華夏以外民族的代稱。春秋晚期夷、蠻、戎、狄逐漸脫離具體的民族稱謂,成為泛指某一區域民族的名詞,并逐漸與東、南、西、北方位聯系起來。③參見童書業:《夷蠻戎狄與東南西北》,《童書業著作集》第二卷,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519頁。
二、四夷體系化的理論建構
從戰國至西漢,在商周宇宙觀的基礎上,關于中央與四方的政治觀念進一步完善。占據中央位置是正統地位的象征,如《呂氏春秋·慎勢》云:“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相對于中央的是四方、四極、四荒、四海等,而這些邊緣地帶都是與民族相聯系的,如《爾雅·釋地》云:“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國,南至于濮鈆,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春秋時,“中國”觀念開始出現,“中國”是相對“四方”、“四夷”而言的。《尚書·梓材》云:“皇天既付中國民。”《詩經·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戰國時期,中國觀念進一步發展,居于中原的人群有較強的文化優越感,他們認為“中國”的文化是先進的,蠻夷應向中國學習詩書、禮樂、技藝等,如《戰國策·趙策》云:“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圣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戰國時期的諸侯兼并愈演愈烈,中原地區有政治抱負的諸侯皆“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④朱熹:《孟子集注》卷一《梁惠王章句上》,《四書五經》本,中國書店1985年版,第7頁。能對四夷進行有效的統治,使四夷賓服,是當時各諸侯政治功業的象征。
“中國”與“四夷”被相提并論,逐漸成為華夏進行民族歷史敘述的觀念基礎。戰國時期,中原地區已不存在蠻、夷、戎、狄等族群,它們或被同化,或被驅逐,“四夷”與“四方”相配的觀念日趨固定化、體系化。所以關于周邊民族的記述中,夷、蠻、戎、狄的稱謂逐漸固定,并與東、南、西、北四個方位搭配起來,并成為華夏認識、記述周邊族群的基本框架,如《墨子·節葬下》云:“昔者堯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東教乎九夷。”《管子·小匡》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莫不賓服。”⑤《管子》為戰國中期成書,參見胡家聰:《管子新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頁。《禮記·王制》對民族分布進行了具有典型性的論述,中國與四夷并稱為“五方之民”,五大地理區域的民族都具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特征,“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這從語言、習俗、飲食、居處等方面概述了不同地理區域的民族特征,形成了記述民族的基本框架,對后世民族歷史撰述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①《淮南子·墜形訓》把五方之人的形象、性格與五官、五色、五臟及五方相配,形成了一個整齊的觀念體系,也表明了西漢時期對各區域人群的抽象認識。
先秦經典著力探討一個理想的政治秩序,那就是以禮的原則按一定階序安排各種政治群體,《禮記》記述了一個圍繞明堂而舉行的政治儀式,在天子、三公、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后,是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九采,即“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②(唐)孔穎達,呂友仁整理:《禮記正義·明堂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8-1259頁。在這個秩序中,蠻、夷、戎、狄與東、南、西、北相配,可見,華夏基于自身的文化優越意識,通過對禮儀的描述表達了一個理想的、嚴密的政治等級體系,也更加明確了“四夷”在這一政治秩序中的邊緣位置。③另見《逸周書·王會解》中的《四夷獻令》,按地理方位劃分四夷,根據地理方位記述了每一地區的民族及所貢方物:“伊尹受命,于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剪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鰂之醬,鮫鼥、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己、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氐、韯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駼騠、良弓為獻。”參見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970-983頁。
秦漢時期,隨著華夏的進一步凝聚,中原王朝國力的增強,郡縣制逐漸向周邊地區推行,中原地區建立了同質化的社會,漢人主體意識開始出現,漢代四夷體系的理論建構逐漸完備。④參見[日]渡辺信一郎著,徐沖譯:《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從日中比較史的視角出發》第二章“天下的領域結構——以戰國秦漢時期為中心”,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60-65頁。同時,中原地區與周邊族群的交流逐漸增加,中原人收集到了更豐富的各民族信息,對各地區民族的認識更為深入,并有意識地對各民族進行了分類,開始明確地按蠻、夷、戎、狄來記述各民族的情況。如東漢應劭按地理方位劃分了各民族,記述了各區域民族種類及文化特征,《風俗通義》記載:
東方曰夷者,東方仁,好生,萬物抵觸地而出。夷者,抵也,其類有九: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 (一作蒲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南方曰蠻者,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一曰天竺,二曰垓首,三曰僬僥,四曰跂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脊。
西方曰戎者,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
北方曰狄者,父子叔嫂,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⑤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87-488頁。
這無疑是對四夷體系化、類型化的記述,正式構建了一個完整的四夷分類體系,這種體系化的記述方式為后世傳承并不斷強化,主導了歷代民族記述的基本框架,也是古代認識民族問題的基本標準之一。對四夷記述逐漸體系化、模式化的過程也是華夏族逐漸壯大的過程,這在歷代史籍中民族歷史記述的發展上有直接的體現。
三、歷代史籍對四夷的體系化記述
對四夷的體系化記述方式在戰國至秦漢建構完成后,成為中原王朝記述周邊民族歷史的基本理論框架,為歷代修史者所傳承,指導了正史以及其他體例史籍中關于民族的記述,也影響了中國古代關于民族的基本認識方式。
1.正史中的四夷體系化記述
秦漢以后,周邊族群在中原王朝的政治中舉足輕重,尤其是北方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肘腋之患,民族歷史是歷代正史不得不專門記載的內容。 《史記》、 《漢書》中還沒有形成整齊的“四夷傳”,《史記》的六部少數民族列傳依次為《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朝鮮傳》、《大宛列傳》,《漢書》的民族列傳為《匈奴傳》、《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西域傳》,兩書對民族的記載大致按圍繞中原的地理方位順序而展開,雖然未完全采用四夷的模式,但開創了以后正史四夷列傳的基礎。
從魏晉到隋唐,正史中四夷的體系化記述模式逐漸形成。南宋范曄撰《后漢書》,開始突出了各民族的方位次序,以此為標準對民族進行了分類,《后漢書》卷八五至卷九〇記述的民族依次為東夷、南蠻、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烏桓、鮮卑。《梁書》卷五四為“諸夷”,分海南諸國、東夷、西北諸戎三部分來記述。在唐代的正史修纂中,完整的四夷的體系化記述正式確立了。《晉書》卷九七為民族列傳,修史者正式把這一記述民族歷史的部分稱為“四夷”,其中東夷包括夫余國、馬韓、辰韓、肅慎氏、倭人、禆離等十國;西戎包括吐谷渾、焉耆國、龜茲國、大宛國、康居國、大秦國;南蠻包括林邑、扶南;北狄即匈奴。值得注意的是,在漢代才開始接觸的西域各城邦國家,已逐漸納入既有的四夷框架之中。 《隋書》卷八一至卷八四分別為東夷、南蠻、西域、北狄。《南史》卷七八“夷貊”上記述了海南諸國、西南夷,卷七九“夷貊”下記述了東夷、西戎、蠻、西域諸國、北狄。《北史》卷九四至卷九九為民族列傳,其按語稱:“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今各編次,備《四夷傳》云。”其卷九四為高麗、百濟、新羅、勿吉、奚、契丹、室韋、豆莫婁、地豆干、烏洛侯、流求、倭;卷九五為蠻、獠、林邑、赤土、真臘、婆利;卷九六為氐、吐谷渾、宕昌、鄧至、白蘭、黨項、附國、稽胡;卷九七為西域;卷九八為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高車;卷九九為突厥、鐵勒。正史對西夷的體系化記述模式的確立,說明在漢末以后300余年的分裂后,重新統一,隋唐是一元化天下秩序的再建與定型時期,①高明士:《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討——以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頁。為在意識形態上強化一元化天下秩序,正史修纂者也有意識地在觀念上建構了一個四夷體系。
唐以后,四夷記述的體系化在正史中得以延續并不斷完善,《舊唐書》卷一九四至卷一九九,先是單卷記述了對唐朝構成重要威脅的突厥、回紇、吐蕃,然后是分南蠻西南蠻、西戎、東夷、北狄四部分介紹其他民族的歷史。《新唐書》卷二一五至卷二二二,也先是重點介紹突厥、回鶻、吐蕃、沙陀的歷史,然后分北狄、東夷、西域、南蠻四部分記述其他各族的歷史。歐陽修《新五代史》更是以《四夷附錄》把這一體例推向極端,為突出宋朝的正統地位,把四夷置于全書的附錄位置。
在各部正史中,四夷附于全書之末,在整個史書結構中也處于邊緣地位,而史學的體例正是現實民族觀念與分布格局的反映。
2.雜史、政書、方志中的四夷體系化記述
歷代正史對四夷的體系化記述影響了其他體例史書的編纂,最有代表性的是唐代杜佑所撰典制體史書《通典》中的《邊防典》。杜佑在安史之亂后,出于總結歷代邊防策略的撰述宗旨,在《邊防典》中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敘述各民族歷史,《邊防典》序中也引用《禮記·王制》等經典來論證劃分四夷體系的必要性,在這一體系下,杜佑對前代正史及當時所能收集的民族資料進行統一的編纂。《邊防典》凡16卷,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四部分敘述各族歷史,從邊防策略的角度總結各地區民族的特征。每一部分開始都有“序略”,對四個區域的民族特征進行了宏觀的概述,共收入民族百余種,確定了典制體史書中民族史編纂的模式,以后的典制體史書基本延續了這一撰述體系。《邊防典》是較為完善的四夷體系的表述,所記載的民族如下:
東夷朝鮮、濊、馬韓、辰韓、弁辰、百濟、新羅、倭、夫余、蝦夷、高句麗、東沃沮、挹婁、勿吉又曰靺鞨、扶桑、女國、文身、大漢、流求、閩越。
南蠻盤瓠種、廩君種、板楯蠻、南平蠻、東謝、西趙、牂牁、充州、獠、夜郎國、滇、邛都、筰都、冉駹、附國、哀牢、焦僥國、樿國、西爨、昆彌國、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僰濮、松外諸蠻。(嶺南蠻獠)黃支、哥羅、林邑、扶南、頓遜、毗騫、干陀利、狼牙修、婆利、盤盤、赤土、真臘、羅剎、投和、丹丹、邊斗、杜薄、薄剌、孛攵焚、火山、無論、婆登、烏篤、陀洹、訶陵、多蔑、多摩長、哥羅舍分。
西戎羌無弋、湟中月氏胡、氐、蔥茈羌、吐谷渾、乙弗敵、宕昌、鄧至、黨項、白蘭、吐蕃、大羊同、悉立、章求拔、泥婆羅、樓蘭、且末、杅彌、車師高昌附、龜茲、焉耆、于闐、疏勒、烏孫、姑墨、溫宿、烏秅、難兜、大宛、莎車、罽賓、烏弋山離、條支、安息、大夏、大月氏、小月氏、康居、曹國、何國、史國、奄蔡、滑國、嚈噠 (挹怛同)、天竺、車離、師子國、高附、大秦、小人、軒渠、三童、澤散、驢分、堅昆、呼得、丁令、短人、波斯、悅般、伏盧尼、朱俱波、渴盤陀、粟弋、阿鉤羌、副貨、疊伏羅、賒彌、石國、女國、吐火羅、劫國、陀羅伊羅、越底延、大食。
北狄匈奴、南匈奴、烏桓、鮮卑、軻比能、宇文莫槐、徒河段、慕容氏、拓跋氏、蠕蠕、高車、稽胡、突厥、鐵勒、薛延陀、仆骨、同羅、都波、拔野古、多濫葛、斛薛、阿跌、契苾羽、鞠國、俞介、大漠、白霫、庫莫奚、契丹、室韋、地豆于、烏洛侯、驅度寐、霫、拔悉彌、流鬼、回紇、骨利干、結骨、駁馬、鬼國、鹽漠念。
“十通”的其他各書基本上沿襲《通典》這一體例,只是在民族史資料上根據時代發展而有所補充,尤其以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最具代表性。在這些史籍中,對民族歷史的記述部分無論是名為“邊防”、“四裔”還是“四夷”,其對周邊各民族的體系化、類型化的敘述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
北宋太平興國年間,樂史編纂了一部地理總志《太平寰宇記》,全書共200卷,其中卷一七二至卷二○○為“四夷”,其體例基本沿襲了杜佑的《通典·邊防》。與此同時,李昉等纂《太平御覽》全書1000卷,以天、地、人、事、物等分為55部,其中卷七八○到卷八○一為《四夷部》,共22卷,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四部分來敘述各民族歷史。在每部分之前都有“敘”,引經據典對各部民族歷史的源流進行概述。
在元末戰爭中,為了加強反元的號召力,朱元璋領導的農民軍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口號。明朝建立,恢復了“中華”的正統地位。在明代的民族歷史撰述中,為突出“中華”的地位,以“四夷”為名的著作較多,如葉向高《四夷考》、鄭曉《皇明四夷考》、慎懋賞《四夷廣記》、鄭大郁《四夷考》等。這些著作基本上沿襲了歷代正史所確立的四夷體系,如葉向高撰《四夷考》按地理方位順序敘述明代各民族的歷史,該書卷一為朝鮮考、日本考、安南考;卷二為女真考、朵顏三衛考;卷三為哈密考、赤斤蒙古、安定阿端、曲先、罕東罕東左;卷四為西番考、吐魯番考;卷五為北虜考。
明萬歷年間,羅曰褧撰《咸賓錄》,此書共分八卷,按地理方位劃分為《北虜志》一卷、《東夷志》一卷、《西夷志》三卷、《南夷志》三卷,所記民族的分布地域超越了前代,開始向外延伸。嚴從簡于萬歷二年 (1574)撰成《殊域周咨錄》,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四部分來敘述各民族情況。東夷包括朝鮮、日本、琉球;南蠻包括安南、占城、真臘、暹羅、滿剌加、爪哇、三佛齊、浡泥、瑣里、古里、蘇門答剌、錫蘭、蘇祿、麻剌、忽魯謨斯、佛郎機、云南百夷;西戎包括吐蕃、拂菻、榜葛剌、默德那、天方、哈密、吐魯番、赤斤蒙古、安定、阿端、曲先、罕東、火州、撒馬兒罕、亦力把力、于闐、哈烈;北狄包括韃靼、兀良哈。《殊域周咨錄》專列“東北夷”記述女真歷史,這表明了明中期以后女真對明朝東北邊防的壓力不斷增強,成為朝野上下關注的焦點,不得不予以特別記述。
清康熙年間陳夢雷主持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分為6編32典,其中《方輿匯編》包括坤輿典、職方典、山川典、邊裔典。邊裔典共140卷,按四夷分類體系把歷代民族分為542部,每部分為總論、匯考等,把歷代有關民族的記述編纂到一起,在一定意義上邊裔典是中國古代最為完備的民族通史。
在中國古代民族歷史的撰述中,雖然一些少數民族也形成了本民族歷史的撰述傳統,但從整體來看,華夏、中國或中原王朝一直是記述主體,為了強化華夏、中國或中原王朝的地位,民族歷史的撰述承載了政治意識形態的功能,這一記述歷史模式塑造了一個環繞華夏或中國的邊緣地帶。這一歷史敘述體例在正史、典制體史書、方志、專著之間文本與文本的模仿與復制,表明了民族歷史記述之間的具有一種同構的敘述模式。①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37頁。
四、各民族政權對四夷體系化記述模式的認識
中國古代關于四夷的體系化記述模式是以華夏或中國為中心的歷史敘述,但建立中原王朝的民族并不必然是華夏或漢族,在歷史上,各民族政權或交替,或并立,有的占據中原,有的立于中原之外,偏安一隅,但也以中國自稱,在歷史編纂上也復制了這一民族歷史記述模式,以此來強調自身的正統地位。
中原漢族王朝理所當然認可這一民族歷史撰述模式,在歷史記述中抬高華夏的地位,同時強化四夷的邊緣地位。《通典·邊防典》以華夏為核心,分四夷敘述各民族歷史,但重在宣揚華夏的正統地位,《通典》總序云:“覆載之內,日月所臨,華夏居土中,生物受氣正。”北宋《太平寰宇記》把“西夷”列于全書之末,其《四夷總序》云:“自是以降,唐史所書,推其土域所存,記其名號之變,載于國史之末,以備華夏之文。……凡今地理之說,蓋定其方域,表其山川,而四夷之居,本在四表,雖獫狁之整居焦獲,陸渾之處于伊川,其人則夷,其地則夏,豈可以周原、洛邑謂之夷裔乎!”②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二《四夷·四夷總序》,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296頁。歷代修史者所構建的四夷體系的作用就是突出華夏或中原王朝的地位,如明代萬歷年間何喬遠撰《名山藏》,為一部明朝史,全書分37記,書末的卷一○五至卷一○九為《王享記》,分東南夷、北狄、東北夷、西戎等四部分來記述與明朝有朝貢關系的少數民族,借此來宣揚明朝的上國地位,《王享記》序高度贊頌了永樂年間四夷來賓的盛況,其云:“四夷君長,執贐獻琛,頂踵相望。賜宴之日,有忭舞天日,稽首闕庭,嘆未嘗有。”③(明)何喬遠:《名山藏·王享記》,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3頁。
在西晉末期,北方各民族政權蜂起,經過激烈的角逐,拓跋鮮卑最后占領中原地區,建立了北魏,北魏統治集團十分重視通過修史論證自身的正統地位。 《魏書》稱北魏是“中國”、 “皇魏”、“大魏”,并宣稱魏乃“神州之上國”,而稱東晉為“僭晉”,稱南朝宋、齊、梁為“島夷”,稱十六國諸政權為“私署”“自署”等。④參見張莉:《〈魏書〉在民族史撰述上的成就》,《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在此觀念的指導下,《魏書》卷九五至卷九九為西晉末至北魏各族政權創建者的傳記,卷一○○至卷一○三按東、南、西、北的方位順序記述了北魏周邊各族歷史。《魏書》基本上認同了漢晉以來民族歷史的撰述模式。
宋、遼、金、西夏并立時期,各族政權也通過對四夷歷史的記述來強調自身的正統地位。宋朝面對異族政權的壓力,統治上層在觀念上嚴夷夏之別,在民族歷史記述中強化四夷體系。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將民族歷史部分附于全書之末,稱為《四夷附錄》,其按語稱:“嗚呼,四夷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于弦弓毒矢,強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四夷之于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嘗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但遼朝統治者對《新五代史》列契丹于《四夷附錄》的反應比較強烈,遼壽隆二年 (1096年),史臣劉輝向遼道宗建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貶訾。且宋人賴我朝寬大,許通和好,得盡兄弟之禮。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意。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跡,詳附國史。”道宗嘉其言,遷其為禮部郎中,任史館修撰。⑤《遼史》卷—〇四《劉輝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455-1456頁因為遼朝統治集團也自認為是中國,與宋是兄弟之國,也是正統的中國王朝。⑥參見趙永春:《試論遼人的“中國”觀》,《文史哲》,2010年第3期。
元、清兩朝為蒙古、滿洲所建立,兩朝所修正史中沒有按照四夷體系來撰述民族歷史,把以前的四夷的一部分民族名為“外國”,可能出于避諱本民族出自前代中原王朝所稱的東夷、北狄的考慮,但仍稱南方民族為“蠻夷”。但在兩朝修纂的其他體例的史書中仍沿襲了這個四夷體系。
元朝的疆域空前遼闊,把更多的民族納入其統治之下。《元史·地理志》云:“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梗于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故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所以《元史》雖立有《外夷傳》,但所記不是境內的民族,而為高麗、耽羅、日本、安南、緬、占城、暹、爪哇、瑠求等與元朝有貢屬關系的諸國,對境內東北、西南等地區諸民族,主要在《元史·地理志》中有所記述。
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記述民族歷史的部分為《四裔考》,實質上是以中國的角度記述四夷歷史,如記載女真歷史至南宋紹興九年,這是因為女真所建金朝“自晟至守緒凡八世而亡,其事跡具見國史,以其既竊有中原,故事跡不入四裔之錄云”,①(元)馬端臨編撰,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所、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所點校:《文獻通考》卷三二七《四裔四》,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9010頁。可見是否占據中原成為判定華夷的標準。
作為清朝統治上層的滿洲人,本為明代史書所稱的“東北夷”,但統治上層在占領中原之后便以中國之主自居。乾隆中期以后,在清朝皇帝看來,中國已不是中原漢族地區的狹義的“中國”,在清朝明確的疆界內,既有漢族所居的中原內地各行省,更包括廣闊無垠的邊遠地區。②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國觀》,《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但清朝統治集團也認同了歷史編纂中對四夷的體系化記述,清朝的官修史書甚至將四夷范圍延伸得更遠。清朝鼎盛的乾隆時期編纂了《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其總案語云:“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環,其緣邊濱海而居者,是謂之‘裔’。海外諸國,亦謂之‘裔’。 ‘裔’之為言,邊也。三代以降,中原幅員,視主德為廣狹,四裔遠近亦隨時轉移。懿惟我國家統一函夏,四裔賓服,列圣經營,宅中馭外,百余年來,聲教覃敷,梯航洊至。皇上繼承鴻烈,平定準夷、回部,開疆二萬余里。前代號為寇敵者,皆隸版籍,重譯貢市,規模益遠。”③《清朝文獻通考》卷二九三《四裔考》,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第638冊,2005年版,第579頁。這表明了清朝統治集團“宅中馭外”以求“四夷賓服”的政治構想,關于“四裔”的記述也是這一觀念在史學上的系統表述。
在此基礎上,清代“四裔”的內涵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對內屬的蒙古、西藏、回部等不再稱之為夷,四夷的范圍在地理位置上繼續向外擴展,《清朝文獻通考》記述的四夷,東為朝鮮、日本、琉球;南為安南、南掌、廣南、緬甸、葫蘆、暹羅、港口、柬埔寨、宋腒、柔佛、亞齊、呂宋、莽均達老、蘇祿、文萊、馬辰、舊港、曼加薩、噶喇巴、意達里亞、博爾都噶爾、英吉利、干絲臘、荷蘭、佛郎機、瑞國、嗹國;西為東西布嚕特、安集延、霍罕、納木干、瑪爾噶朗、塔什干、巴達克山、博羅爾、愛烏罕;北為俄羅斯、左右哈薩克、齊齊玉斯、諤爾根齊。④《清朝文獻通考》卷二九三《四裔考》,第579-580頁。清朝統治集團認為已將歷代四夷地區納入了版圖,其疆域超出歷代上百倍,相應的,四夷所處的位置就應該向更遙遠的地方延伸,所以在歷史記述中對四夷進行了新的建構,這也是四夷體系自然發展的過程。正如許倬云所說,出現于東亞的“中國”,有其自身發展過程,自商周以來,掌握文字記錄及擁有豐富資源的“中原”自以為中心,視周邊各處為“邊陲”,不斷地通過“他者”界定其自身,這一“自—他”的相對地位,又具有“中心—邊陲”的互動。“中心”不斷因為擴張而改變其范圍,“邊陲”也相應地變化。原來的“邊陲”可能融入“中心”,而在周邊又有更遙遠的地區成為新的“邊陲”。⑤許倬云:《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2頁。
結 語
中國古代史籍對四夷的體系化記述是在獨特的地理生態與政治環境下形成的。商周時期,中原的農耕人群創造了發達的文明,形成了相對于四方族群的優越意識,春秋時期諸夏更強調華夷之別,為了加強華夏的凝聚力,華夏或中原王朝通過對各區域民族進行體系化、類型化的記述塑造了一個環繞華夏的邊緣,以此來加強華夏的凝聚力,從而確立了民族歷史記述的基本模式,并主導了中國古代認識民族問題的思維方式。歷代各民族建立的王朝也認同這一記述方式,不斷傳承、復制這一民族歷史記述模式,通過對四夷的體系化記述以強調各自的正統地位,并按地域總結各地理區域民族的特征,探討制四夷之道。
晚清,較早具備世界眼光的官員、學者在介紹世界各國歷史的著作中依然保留著“四夷”這一記述方式,把西方國家放在既有的四夷體系中來認識。但在現實政治中,列強逐漸向清朝邊疆民族地區滲透,在日、俄、法、英等的挑唆下,周邊民族有脫離清朝管轄之勢,甚至,作為四夷體系中“東夷”之一的日本,積極宣揚“脫亞入歐”,要在觀念上擺脫這一體系的影響。甲午戰爭中清朝被“東夷”日本擊敗,持續兩千年的四夷體系遭遇了空前的危機。同時,隨著西方地理學、民族學等著作的傳入,也動搖了既有的關于民族歷史的知識體系,在學術觀念上,四夷的體系化記述方式逐漸發生轉化。人們開始審視自己的傳統,新的國家觀、民族觀逐步確立。中華民國建立后,中國民族史的研究與撰述迅速發展,這需要重新形成自身的理論體系,新的民族史觀及撰述模式開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