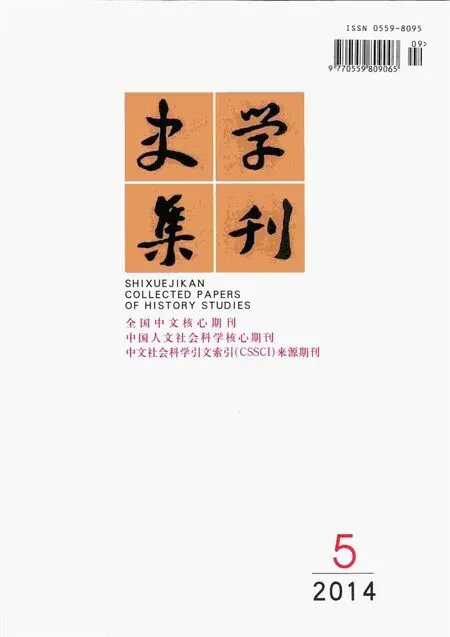北魏洛陽寺院園林營建考——以《洛陽伽藍記》為中心的考察
張鶴泉,趙延旭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吉林長春130012)
北魏時期佛教昌盛,社會各階層大多數人都篤信佛教,所以造成立寺造塔的風氣非常盛行。由于這種風氣的盛行,寺院園林的營建也隨之發展起來。這種寺院園林與皇室園林、私家園林成為北魏社會存在的三大主體園林。實際上,在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在首都修建的寺院園林數量更多。因而,探討北魏洛陽寺院園林的修建狀況不僅對認識古典園林的發展特點是必要的,同時,也是考察北魏時期佛教傳播對園林營建產生的重大影響不可或缺的內容。前人雖然對北魏洛陽寺院園林的植物景觀做了一些研究,①薛瑞澤:《讀〈洛陽伽藍記〉論北魏洛陽的寺院園林》,《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年第2期。但對洛陽寺院園林的營建問題的闡釋卻并不多見。有鑒于此,本文擬以《洛陽伽藍記》的記載為中心,并結合其他的文獻資料,對北魏洛陽寺院園林的營建的相關問題做一些研究,希望能夠對北魏寺院園林的特征的認識有所裨益。
一、洛陽寺院園林營建興盛的原因
北魏是中國古典園林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當時寺院園林與皇室園林、私家園林一樣,都處于發展的時期。特別是北魏都城洛陽寺院園林的發展盛況。史載,北魏時期洛陽城中“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②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五《城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49頁。并且其中大部分寺院都有園林的修建,這就使洛陽的寺院園林數量之多,達到驚人的程度。北魏首都洛陽寺院園林的發展盛況自然有其重要的社會原因。
首先,北魏首都洛陽興建寺院園林風氣的盛行與佛教在北魏廣泛的傳播以及信奉者的人數眾多有密切的關系。眾所周知,佛教自西漢末葉傳入中國,迄至西晉末年,黃河流域社會動蕩、戰亂頻仍、人民朝不保夕,佛教宣揚的“因果報應”、“輪回轉世”等觀念恰恰滿足了苦難中的各階層民眾對來世美好生活的渴望,從而得以迅速傳播。逮及十六國時期,后趙、前秦、后秦、北涼等政權君主紛紛崇信佛教、優遇僧徒,更推動了佛教在北方的進一步發展。佛教在北方的這種傳播狀況,當然要影響到北魏國家對佛教的吸納。
在鮮卑拓跋氏居于代北之時,尚不知曉佛教,正如《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說:“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可是,在道武帝建國后,由于經略中原,開始了解佛法,“所逕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嚴格實行了保護寺院、禮敬沙門的政策。并且,在遷都平城后,立即下詔“于京城建飾容范,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并“作五級浮圖、耆阇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繢飾,別構講堂、禪堂及沙門座”,開始營造佛教寺院。明元帝又“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太武帝即位之始,亦“歸宗佛法,敬重沙門”,常“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然而,到他統治后期,“得寇謙之道,帝以清凈無為,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遂下詔毀法滅佛,誅殺僧徒、焚破佛像,使佛教受到了沉重的打擊。然而,由于“素敬佛道”的監國太子拓跋晃“緩宣詔書”,使“四方沙門,多亡匿獲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濟。金銀寶像及諸經論,大得秘藏”,從而為佛法復興保存了力量。及至文成帝即位,下詔復法,“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寺,仍還修矣”,①以上參見《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030、3033、3032、3033、3035、3036頁。佛教迅速恢復并再度興盛。此后即位北魏諸帝以及曾實際掌握政權的馮太后與胡太后皆篤信佛教。孝文帝“善談老莊,尤精釋義”。宣武帝“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胡太后“姑既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經大義”。“上既崇之,下彌企尚”,北魏信佛、崇佛風氣大盛,佛教發展空前繁榮,“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余”,②《魏書》卷七下《孝文帝紀下》,第187頁;卷八《宣武帝紀》,第216頁;卷一三《皇后·宣武靈皇后胡氏傳》,第337頁;卷一一四《釋老志》,第3042、3048頁。信徒人數則更為眾多。
佛教在北魏不僅廣泛傳播,并且,在崇佛的方式上也與南方有不同之處。特別是,在太武帝滅佛之后,大批擅玄名僧攜其所學南渡江淮,從此義學南趨,南北佛學風氣為之一變,南方專精義理,北方則偏重行業。所以北魏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饒益……造像立寺,窮土木之力,為北朝佛法之特征。③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84頁。北魏諸帝及皇后熱衷于營建佛寺、浮圖,遷都洛陽后尤甚。孝文帝建報德寺,宣武帝立景明、瑤光、永明三寺,靈胡太后營永寧、秦太上公、太上君寺。在統治者的影響下,北魏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平民,崇信佛教、營造佛寺風行于時,“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舍資財若遺跡。于是昭提櫛比。寶塔駢羅,爭為天上之資,競摸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披朱紫而已”。④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原序》,第1頁。顯然,在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后,首都營建佛寺的風氣更盛。為了體現對佛寺興建的重視,自然要使佛寺建筑更加富麗堂皇,這樣,也就更促進了洛陽寺院園林修建風氣的盛行。
其次,孝文帝遷都洛陽后,洛陽不僅成為國家的政治、經濟中心,也成為文化的中心,因而,洛陽在文化上所處的特殊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寺院園林的營建。事實上,在北魏遷都洛陽之前,東漢、曹魏以及西晉政權均定都于洛陽,在長達近三百年悠長的歷史時期中,洛陽在文化上一直占據著特殊的地位。其中表現很明顯的就是,在佛教傳入中國后,洛陽特殊、優越的文化地理位置,使其成為異國佛教僧侶東來傳法的首選之地。在東漢桓靈之世,西域名僧安清、支讖皆止于洛陽,譯經說法,聽者云集,二者對后世中土佛教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外,安玄、竺朔佛等亦集于此,譯經著述,洛陽成為漢代譯經唯一之地點。⑤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47頁。洛陽佛法由此轉盛。三國時期,洛陽作為曹魏政權都城所在,西域諸國高僧攜經典接踵而至,中土僧徒朱士行等也由此地西行求法,洛陽成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重鎮。及至晉朝建立,洛陽佛法更盛,竺佛圖澄、耆域等西域高僧均前來弘法傳教,寺廟圖像崇于京邑,“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①《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3029頁。很顯然,在北魏遷都洛陽前,洛陽已經擁有悠久的佛學傳統,并且積淀了很深厚的佛教文化,崇佛氛圍濃重。誠如湯用彤先生所言,“洛中自漢以來,已被佛化”。②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96頁。
正因為如此,北魏遷都后,洛陽便迅速恢復了北方佛教中心的地位,吸引大批異國沙門“負錫持經,適茲樂土”。③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四《城西·永明寺》,第235頁。正是在這種佛教文化氛圍的影響下,使北魏國家和不同階層的民眾都非常重視佛寺的營建。當然,在佛寺的營建過程中,也就要帶動寺院園林的發展。因為寺院園林實際是佛教文化的明顯體現。從這一點來看,不能不說北魏洛陽寺院園林的興盛,與洛陽長期的佛教文化傳承的影響有著很密切的關系。
再次,洛陽寺院園林營建風氣的興盛,與北魏社會上層統治者奢靡成風也有重要的關系。北魏平城時期,也就是北魏前期,當時國家的物資匱乏,鮮卑貴族還保留一些部落時代質樸遺風,因此他們的生活并不很奢華。可是,北魏遷都洛陽之后,由于當時社會較為安定,物質財富迅速增加,當時人稱,“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于廊者,不可較數”。④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四《城西·河間寺》,第208頁。因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就使鮮卑貴族的生活狀況也得到極大改善。與此同時,孝文帝推行全面漢化政策,通過“定姓族”以及與漢族世家大族聯姻等措施,推動了鮮卑貴族的世族化,因而使他們擁有的政治、經濟特權可以長期傳襲。實際上,鮮卑貴族世族化的過程帶來的負面效應,正是加速了他們日益的腐朽化。鮮卑貴族集團的腐朽化,也促使了漢族官僚與世族的腐朽化。因而在當時洛陽城中,到處彌漫著這種腐朽的風氣。
洛陽社會上層奢侈腐化的明顯表現之一,便是大肆興修宅第園林。“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縹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煢獨不見牛馬之衣。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夸競”。⑤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四《城西·河間寺》,第206頁。可見擁有大量的園宅成為社會上層具有豐厚財富與很高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洛陽城中王公貴族競相修建宅第園池,并使其極盡奢侈華麗。諸如北海王元祥“建飾第宇,開起山池,所費巨萬”。⑥《魏書》卷二一上《獻文六王上·北海王祥傳》,第561頁。廣平王元懷“堂宇宏美,林木蕭條,平臺復道,獨顯當世”。清河王元懌“第宅豐大,踰于高陽……土山釣臺,冠于當世”。⑦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二《城東·平等寺》,第105頁;卷四《城西·沖覺寺》,第185頁。與鮮卑貴族相同,漢族官僚也競修園宅。例如王椿“僮仆千余,園宅華廣”。⑧《魏書》卷九三《恩悻·王睿附王椿傳》,第561頁。張倫“齋宇光麗,服玩精奇,車馬出入,逾于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⑨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二《城東·正始寺》,第100頁。由此可見,這些鮮卑貴族和漢族官僚營建的園宅,都有奢華的園林。這種園林正是供他們享受的私家園林。
由于這一時期洛陽城中私家園林的迅速發展以及這些社會上層貴族、官僚對佛教信仰的虔誠,因而在當時社會中出現了“舍宅為寺”的風氣。所謂“舍宅為寺”,就是這些貴族、官僚及其他社會群體將他們擁有的私家園林無償地捐贈給佛教寺院,以此體現他們崇奉佛教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正是這種風氣的出現,就使洛陽城中很多的私家園林也就轉變成為寺院園林。例如“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舍宅所立也”。[10]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四《城西·宣忠寺》,第191頁;卷二《城東·平等寺》,第100頁。因此,可以說北魏洛陽城中“舍宅為寺”風氣的興盛,直接造成了寺院園林的大量出現。而這種狀況的出現,當然都是北魏遷都洛陽后,奢侈風氣的加劇而產生的重大社會影響的結果。
總之,北魏洛陽寺院園林的大量出現是以佛教在北方廣泛的傳播以及民眾對佛教的崇奉為社會基礎的。佛教在洛陽長期的傳播而使其具有特殊的文化地位,則是營建具有濃厚的佛教文化特色的寺院園林形成風氣的重要社會條件。北魏遷都洛陽后,社會上層、下層“舍宅為寺”風氣的興盛,則更促使了洛陽的寺院園林的大量涌現。
二、洛陽寺院園林的類別
北魏洛陽寺院園林的營建,是由于佛教在社會中廣泛傳播以及社會上層和下層對佛教虔誠信仰直接影響的結果,因而,就使修建這種園林的社會群體具有了廣泛性。為了說明北魏洛陽寺院園林營建的特點,需要對這些園林加以分類。因為北魏社會的上層、下層以及境內的西域胡人的社會身份、財力以及文化心理存在差異,這些都直接影響了寺院園林的營建特色,因而,就使洛陽寺院園林具有不同的類型。所以筆者主要依據這些不同類別的寺院園林,對其營建特點做一些考察。
(一)皇帝與后妃所立寺院園林
在北魏王朝的諸皇帝中,除了太武帝外,都篤信佛教。他們都要營造佛寺、親度僧尼。這成為他們積功德、求福田的主要方式。北魏遷都洛陽之后,修造佛寺之風更盛。孝文帝“罷鷹師曹,以其地為報德佛寺”。①《魏書》卷一三《皇后·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傳》,第328頁。宣武帝則立景明、瑤光、永明三寺。北魏后妃也多崇奉佛法,興建寺院。其中宣武靈皇后胡氏最為典型。她營建秦太上公寺和太上君寺來為父母追福。而且,她還營建了永寧寺。由于這一時期社會上層奢靡風氣甚盛,因而,皇帝與后妃所建寺院不僅氣勢雄偉,并且,都興修了景色秀美的園林景觀。甚至還出現一位皇帝或后妃修建多所寺院園林的情況。
北魏遷都洛陽后,由皇帝或后妃營建的寺院園林,在規模的大小以及內部景觀上,往往存在相似之處,因而,這些寺院園林的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從皇帝或后妃所建寺院園林的規模上來看,這些園林一般都規模宏大,占地廣闊。例如永寧寺“僧房樓觀一千余間,雕梁粉壁,青瑣綺疏,難得而言”。永明寺“房廡連亙,一千余間……百國沙門三千余人”。景明寺“山懸堂觀,光盛一千余間”。如此宏大的寺院園林建筑,其占地面積之廣,是顯而易見的。史載,景明寺“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北魏“方三百步為一里”。可見,北魏皇帝或后妃所建寺院園林都超越了里坊的限制。而其他階層所建寺院園林多分布于里坊之中,甚至一里之內寺院達十余所之多。②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一《城內·永寧寺》,第3頁;卷四《城西·永明寺》,第235頁;卷三《城南·景明寺》,第132頁;卷五《城北》,第349頁;卷二《城東·瓔珞寺》,第78頁。很顯然,皇帝或后妃所建的寺院園林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占地面積上,都是其他社會階層無法比擬的。
從皇帝或后妃所建寺院園林的景觀上來看,一般都是“復殿重房,交疏對溜,青臺紫閣,浮道相通”;“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異草,駢闐階砌”。即便是園林中浮圖的裝飾也大致相似。例如永寧寺“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扉上有五行金釘,其十二門二十四扇,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镮鋪首……佛事精妙,不可思議”。這種裝飾成為以后皇帝或后妃寺院園林浮圖修飾的標準。因此當時文獻載,秦太上君寺“佛事莊嚴,等于永寧”;景明寺“裝飾華麗,侔于永寧”;秦太上公寺“素彩布工,比于景明”。③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三《城南·景明寺》,第132頁;卷四《城西·永明寺》,第235頁;卷一《城內·永寧寺》,第2頁;卷二《城東·秦太上君寺》,第94頁;卷三《城南·景明寺》,第132頁。卷三《城南·秦太上公寺》,第140頁。由此可見,皇帝或后妃所建寺院園林不僅規模宏大、景色幽美,并且,浮圖的裝飾也都是華麗無比的。因此,可以說皇帝或后妃所建寺院園林,都要在營建的規模與裝飾的標準上達到最高的水準,以此凸顯他們作為最高統治者在寺院園林營建上的特權。
(二)貴族、官僚所立寺院園林
在北魏崇奉佛教風氣的影響下,當時貴族、官僚多信仰佛教。為了表現他們信仰的虔誠,大多數人都要立寺建塔。他們修建的寺院即為私家寺院,正是他們祈福發愿的場所。這些私家寺院有辟地新建的佛寺,如“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也”;三公令史高顯洛所立招福寺,“向光明所掘地丈余得黃金百斤……顯洛遂造招福寺”。也有改建他們的宅第而成的佛寺。如愿會寺“中書侍郎王翊舍宅所立”;光明寺則原為“苞信縣令段暉宅”。④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三《城南·正覺寺》,第100頁;卷三《城南·招福寺》,第100頁;卷一《城內·愿會寺》,第55頁;卷一《城內·光明寺》,第55頁。這些貴族、官僚既可以用個人名義獨立建寺,也可聯合集資立寺。如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正始寺則為“百官等所立”。①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二《城東·龍華寺》,第75頁;卷二《城東·正始寺》,第99頁。在這些寺院中,一般都修建園林。
在這些私家寺院中,諸王所建數量很多。例如“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追圣寺,北海王所立”。當時民間號為“王子坊”的壽丘里,“列剎相望,祗洹郁起,寶塔高凌”。其中“舍宅為寺”的諸王人數也很多。如“追光寺,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略之宅也”;“大覺寺,廣平王懷舍宅也”。在諸王的這些私家寺院中,修建的園林非常華美。《洛陽伽藍記》稱:“崇門豐屋,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正說明諸王所建寺院園林的一般特點。但一些諸王對寺院園林的修建還要追求個性特點。如高陽王寺“竹林魚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河間寺“溝瀆蹇產,石磴礁峣,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閣,高樹出云”。②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一《城內·景樂寺》,第52頁;卷三《城南·追圣寺》,第158頁;卷四《城西·河間寺》,第208頁;卷四《城西·追光寺》,第224頁;卷四《城西·大覺寺》,第234頁;卷四《城西·河間寺》,第206頁;卷三《城南·高陽王寺》,第177頁;卷四《城西·河間寺》,第208頁。諸王修建的這些寺院園林,正是其奢侈腐朽生活的體現。
此外,北魏的一些宦官也修建了很多的寺院園林。這些宦官雖然是皇室家奴,但他們的社會地位卻很高,僅次于鮮卑諸王和勛貴。③陳連慶:《北魏宦官的出身及其社會地位》,《中國古代史研究》(上),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頁。實際他們擁有很大的政治權力與雄厚的經濟實力,“閽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因而,他們修建的寺院豪華奢侈,并且,園林也景色綺麗。例如宦官所建凝圓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精麗,竹柏成林”。④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一《城內·昭儀尼寺》,第54頁;卷五《城北·凝圓寺》,第248頁。
這些情況表明,北魏的貴族、顯宦在寺院園林的修建上,是不惜花費大量錢財的。這一方面要表現他們擁有雄厚的財力;另一方面,也要展示他們在敬奉佛教上所處的特殊的優越地位。
當然,由于這些貴族、官僚只是皇帝的臣下,因此他們營建的寺院園林是絕不可能超過皇帝或后妃所建園林的規模和奢華程度的。如劉騰所建長秋寺“莊嚴佛事,悉用金玉”,而彭城王元勰所建明懸尼寺則“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而且,貴族、官僚所建寺院園林也都在里坊之中。例如平等寺“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所謂孝敬里也”;正始寺“在東陽門外御道西,所謂敬義里也”。甚至一些官僚營建的寺院園林還以他們生活的里坊來命名。如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青陽門外三里御道南,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都洛邑,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為寺,因以名之”。因北魏實行嚴格的里坊制度,“方三百步為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⑤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一《城內·長秋寺》,第43頁;卷二《城東·明懸尼寺》,第73頁;卷二《城東·平等寺》,第104頁;卷二《城東·正始寺》,第99頁;卷二《城東·景寧寺》,第116頁;卷五《城北》,第349頁。所以,貴族、官僚營建的寺院園林,自然有益于他們在里坊中崇佛的活動,并且,因敬佛活動具有均等性,也就使同一里坊中的平民與貴族、官僚一樣,也都具有了在這些寺院園林中敬拜佛祖的機會。
(三)平民所立寺院園林
北魏時期,平民崇信佛教的人數眾多。這些虔誠奉佛的平民也仿效貴族、官僚紛紛立寺建塔以求福祉。他們寺院的修建多采用改建的方式,也就是實行“舍宅為寺”的做法。例如靈應寺本為京兆人杜子休的宅第,“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嘆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子休遂舍宅為靈應寺”。又如開善寺原為京兆人韋英之宅,位于“千金比屋”的準財里。“(韋)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約河內人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傳說韋英化為厲鬼,迫使前妻“梁氏惶懼,舍宅為寺”。⑥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二《城東·靈應寺》,第88頁;卷四《城西·開善寺》,第205頁。這些事例說明,一般平民的寺院園林,多是由“舍宅為寺”而成的。
因平民所建寺院園林原為其宅院,因而也多分布于里坊之中。當然,由于他們的社會地位不高,自然與皇帝或后妃以及貴族、官僚所立的寺院園林在規模上差別很大。不過,由于這些寺院園林多為平民中的富人所立,因而園林的景致也很別致。正如《洛陽伽藍記》所說:“層樓對出,重門啟扇,閣道交通”;“果菜豐蔚,林木扶疏”。①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四《城西·開善寺》,第205頁;卷二《城東·靈應寺》,第89頁。然而并非平民所立寺院都有園林。《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稱:“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很明顯,這時平民為逃避國家徭役,合家奉佛的情況大量涌現。由此導致了洛陽城內出現“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為一寺。梵唱屠音,連檐接響,像塔纏于腥臊,性靈沒于嗜欲,真偽混居,往來紛雜”②《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3048、3045頁。的混亂局面。這類由貧苦平民所立的寺院只有幾尊佛像、若干僧房而已,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園林的修建。
(四)西域胡人所立寺院園林
在北魏洛陽的西域胡人,也有修建寺院的。西域胡人在中土修建寺院歷史久遠。早在東漢明帝時,“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及至西晉懷帝永嘉年間,西域高僧竺佛圖澄“欲于洛陽立寺”,③釋慧皎:《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52、345頁。后因戰亂“志遂不果”。迨至北魏,君臣上下崇信佛教,遷洛后奉佛之風更盛,“時佛法經像,盛于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批西域胡人前來洛陽弘法修行,其中部分西域胡人還在洛陽修建佛寺,諸如“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法云寺,西域烏場國胡沙門僧曇摩羅所立”。④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四《城西·永明寺》,第235頁;卷三《城南·菩提寺》,第173頁;卷四《城西·法云寺》,第201頁。這些西域胡人所建佛寺,多有園林的營建。
西域胡人在洛陽營建的寺院園林特點鮮明。一方面,西域胡人要使所建寺院園林適應大多數漢人供奉佛教的需要。例如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并且,在樹木和花草的種植上,“伽藍之內,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這與北魏上層人士所建的寺院園林是相似的。另一方面,他們所建寺院園林也保留一些西域建筑的特色,“佛殿僧房,皆為胡飾,丹素炫彩,金玉垂輝”。顯然,這種類型的寺院園林是西域與北魏文化相互結合的產物。正因為如此,西域胡人所建的寺院園林在洛陽城中別具一格,所以京師中喜好西域佛法的漢族僧人“皆就摩羅受持之”。⑤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三《城南·菩提寺》,第173頁;卷四《城西·法云寺》,第201頁;卷四《城西·法云寺》,第201頁。可見西域胡人所建寺院園林對心儀佛事的漢族信徒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三、洛陽寺院園林的景觀營建
由于佛教在北魏的傳播非常廣泛,因而也就使寺院園林的營建出現了繁榮的局面。當時洛陽佛寺鱗次櫛比,“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⑥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五《城北》,第349頁。在這些寺院中,到處可見土山釣臺、珍草香木,加之浮圖聳立、洞房周匝,顯然洛陽寺院的園林建造已經很普遍。因此,可以說北魏時期洛陽寺院與園林的營建基本實現了一體化,這樣,也就形成獨具特色的寺院園林景觀。
(一)寺院園林中的建筑物營造
寺院園林中的建筑物是其景觀構成的重要組成部分。據前人的研究,城市寺院園林主要包括兩種情況:一為毗鄰寺院而單獨建置的園林,二為寺院內各種殿堂、庭院的綠化或園林化。⑦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清華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頁。筆者將寺院園林中的建筑物視為景觀的組成部分,正是指后一種情況而言的。所以,寺院中的浮圖、佛殿、僧尼房、講堂等都屬于寺院園林建筑。所謂浮圖,就是寺院中的佛塔。實際上,北魏時期的佛寺建筑,正處于以塔為中心的布局結構向以佛殿為中心過渡的重要階段。因此,洛陽寺院園林中的浮圖便是標志性的建筑。從當時寺院園林的建筑情況來看,除部分貴族、官僚與平民“舍宅”所立的寺院,由于受原有宅院建筑格局和空間的局限而使修建浮圖受到限制,大多數辟地新建的寺院園林都立有浮圖。依據當時建筑使用的材料,可以將浮圖分為木制與磚制兩類。洛陽永寧寺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而大覺寺則有“磚浮圖一所”。靈應寺也以“所得之磚,還為三層浮圖”。①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一《城內·永寧寺》,第1頁;卷四《城西·大覺寺》,第234頁;卷二《城東·靈應寺》,第89頁。
這些浮圖層級則“從一級至三、五、七、九”②《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3029頁。不等。九級為北魏浮圖的最高層級。洛陽的永寧寺即為九級。因為它是北魏皇家佛寺,所以層級最高。胡太后所建景明寺,則為七級浮圖。顯然與皇帝所建浮圖存在差別。實際浮圖的層級成為修建者特權身份的一種象征。不過,《洛陽伽藍記》中所見最多的,則為五級浮圖。這一層級的浮圖多為皇室與諸王所立。如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有五層浮圖一所”;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中有五層浮圖一所”;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有五層浮圖一所”。這說明,五級浮圖的營造,為北魏皇室與諸王所壟斷。洛陽的三級浮圖著名的,則有明懸尼寺、王典御寺。明懸尼寺“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王典御寺“門有三層浮圖一所”。可見能夠營造三級浮圖的佛教信徒,一般沒有嚴格的等級限制。就是說,除了國家官員能夠營造之外,一般平民也可以修建。比如平民杜子休舍宅而立的靈應寺,就用“所得之磚,還為三層浮圖”。③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一《城內·瑤光寺》,第46頁;卷二《城東·秦太上君寺》,第94頁;卷四《城西·融覺寺》,第230頁;卷二《城東·明懸尼寺》,第73頁;卷四《城西·王典御寺》,第195頁;卷二《城東·靈應寺》,第89頁。
不過,由于北魏營建理念開始有了變化,所以也使洛陽寺院園林的格局發生了一些改變。一般寺院的布局雖依舊,但皇室高第的建置則日趨繁雜。最明顯的就是,浮圖的中心地位開始發生動搖,甚至出現先建復殿重房,后補造浮圖的現象。④宿白:《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39、242頁。如平等寺“堂宇宏美,林木蕭條,平臺復道,獨顯當世……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篡大業,始造五層塔一所”。大覺寺“廣平王懷舍宅所立……永熙中,平陽王即位,造磚浮圖一所”。此外,大量附屬建筑此時出現于寺院園林之中,如佛殿、僧尼房、講堂等。北魏洛陽寺院園林中的附屬建筑往往規模宏大、氣勢壯觀。永寧寺“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僧房樓觀一千余間”。景明寺“山懸堂觀,光盛一千余間,復殿重房,交疏對溜,青臺紫閣,浮道相通”。景林寺“講殿疊起,房屋連屬”。即便是“舍宅”而立的寺院,雖不立浮圖,但也多有佛殿、講堂。如建中寺“以前廳為佛殿,后堂為講室”。⑤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二《城東·平等寺》,第108頁;卷四《城西·大覺寺》,第234頁;卷一《城內·永寧寺》,第2頁;卷三《城南·景明寺》,第132頁;卷一《城內·景林寺》,第62頁;卷一《城內·建中寺》,第39頁。這些情況的出現,說明早期寺院以塔為中心的建筑格局開始有了一些改變。然而,由于洛陽佛教園林的格局是對傳統佛教文化的繼承,所以以浮圖為中心的營建布局,仍然在當時占據主流的地位。
(二)寺院園林中的山、水修建
在寺院園林景觀中,假山、水池是其構成的重要要素。北魏洛陽寺院園林的營建,一般都注意到假山、水池的修建。例如,景明寺“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沖覺寺“土山釣臺,冠于當世,斜峰入牖,曲沼環堂”;河間寺“溝瀆蹇產,石磴礁峣”。⑥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三《城南·景明寺》,第132頁;卷四《城西·沖覺寺》,第185頁;卷四《城西·河間寺》,第208頁。可見,當時營建寺院園林,大都使假山、水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北魏洛陽寺院園林的營建能夠使山、水很好地結合,自然是因為洛陽特殊的地理位置與自然環境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從北魏洛陽城的環境來看,它北依邙山,南臨熊耳,西連峣山,東傍嵩岳,四面環山,從而使采石筑山成為可能。如宣武帝時,曾于天淵池西修筑假山,就“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⑦《魏書》卷九三《茹皓傳》,第2001頁。說明寺院園林中的山石多得之于附近群山。洛陽周圍的河流也很多。城北有谷水、金谷水;南有伊水、洛水。并且,洛陽地勢,北高南低、西高東低,谷水、金谷水于洛陽西北合為一流,而后分為東、南兩支,順勢而下,環城一周,最終于洛陽城東南,匯入洛水。這樣谷水便成為洛陽天然的護城河,為城內用水提供了引入水源。東漢張純就已成功將谷水引入洛陽城,“上穿陽渠,引洛水為漕,百姓得其利”。①《后漢書》卷三五《張純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192頁。北魏繼漢、魏引谷水于城中的水系基礎,重新整治,形成了三條橫貫東西的水道:其一北入大夏門,穿華林園,東達建春門;其二西入閶闔門,經西游園,東至東陽門;其三起自西明門,橫城而過,東至青陽門。②王鐸:《北魏洛陽規劃及其城史地位》,《華中建筑》,1992年第2期。洛陽城內外水道密集,不僅為居民日常生活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且,為營建寺院園林引水造池創造了優越的條件。因為要適應寺院園林景觀對引水的需要,所以一些洛陽寺院多依水而建。諸如明懸尼寺“在建春門外石橋南,谷水周圍,繞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長秋寺“寺北有蒙氾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秦太公東、西兩寺“并門臨洛水”。③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二《城東·明懸尼寺》,第73頁;卷一《城內·長秋寺》,第43頁;卷三《城南·秦太上公寺》,第140頁。很顯然,洛陽充足的水源為寺院園林景觀的營造提供了重要的保證。
(三)寺院園林中的植物栽培
在寺院園林景觀的營造中,植物的栽培可以使其具有別致的秀美景色。北魏洛陽寺院雖不具備郊野寺院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但仍非常重視用人工在寺院內外栽培植物。這種對植物的人工栽培,就使洛陽寺院多“青槐蔭陌,綠樹垂庭”。如秦太上公寺“林木扶疏,布葉垂陰”;高陽王寺“芳草如積,珍木連陰”。④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三《城南·龍華寺》,第161頁;卷三《城南·秦太上公寺》,第140頁;卷三《城南·高陽王寺》,第177頁。
為了使洛陽寺院園林的景色更秀美,在寺院園林內外栽培的植物種類繁多。統計文獻中的記載,北魏洛陽寺院園林栽培的植物,大致可以分為樹木、果樹與花草三類。寺院園林中常見的樹木有栝樹、柏樹、松樹、椿樹、桑樹、槐樹、檉樹等。其中,栝樹即為檜樹,又稱刺柏。《爾雅· 釋木》:“檜,柏葉松身。”檉樹則是檉柳,也稱三春柳或紅柳。這些樹種均屬常綠或落葉喬木,其共同點就是姿態挺拔,葉茂蔭濃,能夠為寺院增添了肅穆幽玄的色彩,同時,高大的林木可以將寺院與嘈雜紛亂的外界隔離開來,產生“雖云朝市,想同巖谷”⑤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一《城內·景林寺》,第62頁。的效果。如永寧寺“栝柏松椿,扶疏檐溜”;“四門外,樹以青槐”。正始寺“青松綠檉,連枝交映”。此外,寺院園林中也栽植一些常綠灌木。如瑤光寺就種植“牛筋、狗骨之木”。所謂牛筋“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⑥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一《城內·永寧寺》,第3、4頁;卷二《城東·正始寺》,第99頁;卷一《城內·瑤光寺》,第46頁;卷一《城內·瑤光寺》注引《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第49頁。而狗骨又稱貓兒刺,其株型緊湊,葉形奇特,且四季常青,二者均為優良的觀賞樹種。由于在寺院園林的植物栽培上,喬木、灌木相互交錯,因而增添了寺院園林非常別致的美感。
果樹也是洛陽寺院園林中廣泛栽培的植物。當時文獻稱:“京師寺皆種雜果”。⑦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三《城南·龍華寺》,第158頁。實際洛陽寺院園林中種植的果樹主要有桃、李、梨、柰、葡萄等。如白馬寺“柰林葡萄異于余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河間寺“素柰朱李,枝條入檐”。其中一些寺院出產果實很出名。如“報德之梨,承光之柰”;“白馬甜榴,一實值牛”。甚至一些南方果樹也移植到洛陽寺院園林之中。如昭儀尼寺“堂前有酒樹面木”。⑧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四《城西·白馬寺》,第196頁;卷四《城西·河間寺》,第207頁;卷三《城南·報德寺》,第146頁;卷四《城西·白馬寺》,第196頁;卷一《城內·昭儀尼寺》,第54頁。《南史》卷七八《頓遜國傳》稱:頓遜國“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⑨《南史》卷七八《頓遜國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952頁。可見酒樹即為南方的樹木。
在當時洛陽的寺院園林中,還種植了大量的花草,可謂“花林芳草,遍滿階庭。”其中較為常見的有蘭、菊等。如大覺寺“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花。”在寺院園林中,還多有芳草的種植。芳草又稱香草,是多種芬芳植物的統稱。除香草外,還有白芷、杜若等。史載,景明寺“竹松蘭芷,垂列階墀”;景林寺“芳杜匝階”。[10]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二《城東·秦太上君寺》,第95頁;卷四《城西·大覺寺》,第234頁;卷三《城南·景明寺》,第132頁;卷一《城內·景林寺》,第62頁。由于洛陽寺院園林中多有水池河渠,所以也種植很多的水生花草。如景明寺“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寶光寺“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菼被岸,菱荷覆水”;河間寺“朱荷出池,綠萍浮水”。①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三《城南·景明寺》,第132頁;卷四《城西·寶光寺》,第199頁;卷四《城西·河間寺》,第209頁。在瑤光寺中還有種植“雞頭草”的記載。所謂“雞頭草”,即是芡,屬于睡蓮科水生植物。顯然,在寺院園林中,陸地花草與水生花草的栽培是交錯在一起的,因而,不僅使寺院中充滿了芬芳,也使寺院的景色更加雅致和美觀。
綜上可見,北魏洛陽寺院園林的營建,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建造技藝上,都已經達到很高的水準。不過,由于受當時奢靡風氣的影響,大多數寺院園林的營建都追求華美、奢侈,因而,在寺院園林的建筑、山水、植物等景觀上,都呈現了一種虛化的外在美。這與早期佛教寺院的樸實無華的建造風格是完全相悖的。由于在寺院園林營建上的窮極精麗,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因而也就成為北魏國力的衰竭的重要因素。宋人李格非說:“園圃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侯也,且天下之治亂,侯于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侯于園圃之興廢而得也。”②李格非:《洛陽名園記》,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13頁。李氏所言,是頗耐人尋味的。
結 語
北魏洛陽的寺院園林的大量出現,并在洛陽城中廣泛分布,成為當時佛教文化的一大特色。這一特色的出現具有深刻的社會原因。從北魏國家占據的北方地區來看,由于西晉末年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就使處于煎熬中的漢族民眾紛紛皈依佛教,期盼受到佛法的普度。在漢族崇奉佛教的影響下,北方少數民族統治者也信奉佛教,倡導佛教。北魏道武帝建國后,也效法十六國少數民族統治者的做法,大力推廣佛教。除了太武帝一度滅佛之外,崇信佛教成為北魏國家的國策。正因為如此,在北魏社會中,無論社會上層,還是社會下層,崇奉佛教的人數眾多,也就使在北魏境內修建佛寺的風氣特別興盛。這種風氣的興盛,正是寺院園林修建可以在北魏發展的基礎。而北魏首都洛陽,是一個積淀著濃厚佛教文化的城市。實際洛陽不僅接受佛教文化很早,并且也是佛教文化傳播的中心。當然,佛教園林在洛陽的大量出現,還與北魏不同階層的人士對佛教的狂熱的尊奉具有直接的關系。實際上,為了表現他們對佛教的虔誠信仰,甚至不惜采取“舍宅為寺”的做法。這種做法的出現,明顯擴大了洛陽寺院園林的來源。
北魏洛陽寺院園林的營建規模和特點,是與修建者的身份和地位聯系在一起的。雖然在北魏社會中信奉佛教的群體是十分廣大的,但是,這個群體的身份地位是有等級劃分的。這種等級劃分直接影響到寺院園林的營建。從皇帝、后妃、貴族、官僚所建的寺院園林來看,其規模是宏大的。特別是,作為最高統治者皇帝營建寺院園林的規模,是其他階層無法相比的。一般平民修建的寺院園林不僅規模很小,有的甚至沒有園林建設。因此,洛陽寺院園林的營建,實際也是不同社會階層的身份地位的表現。由于北魏與西域在文化上的廣泛聯系,在洛陽也出現西域胡人營建的寺廟園林。這種寺廟園林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因而,受到當時佛教信徒的青睞。
北魏洛陽寺院園林景觀的營建特色,主要表現在建筑物的修建、假山和水池的營造以及園林內外植物的栽培上。在建筑物的修建上,主要以浮圖,即佛塔的營造作為等級的標志。在假山和水池的建造上,則盡力追求秀美與清澈。在植物的栽培上,則要保證栽培植物的多樣化,進而使寺院園林的景觀更為雅致和精美。北魏洛陽寺廟園林的景觀所表現出的這種狀況,雖展示出很高的建造水平,然而,卻是當時社會興盛的奢靡風氣直接影響的結果,因而,帶來的只能是大量的社會財富的浪費。所以這種寺院園林景觀的營造,實際并沒有更多的積極社會意義,反而是加速了北魏國家走向衰敗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