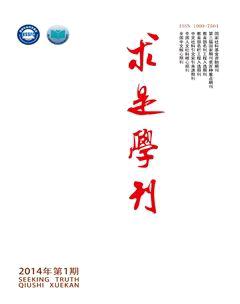利奧·施特勞斯對(duì)斯賓諾莎解經(jīng)方法的誤讀
摘 要:施特勞斯認(rèn)為,斯賓諾莎在解讀《圣經(jīng)》時(shí)沒(méi)有真正貫徹他提出的以經(jīng)解經(jīng)的原則,因?yàn)樗官e諾莎借助歷史資料來(lái)解讀《圣經(jīng)》,引入外部原則整理《圣經(jīng)》,對(duì)于《圣經(jīng)》中各主題事物的定義超出了《圣經(jīng)》的范圍,由《圣經(jīng)》本質(zhì)上的不可理解性得出必須根據(jù)《圣經(jīng)》理解《圣經(jīng)》,并且超越《圣經(jīng)》作者的本意去理解這些作者。施特勞斯的這些批評(píng)其實(shí)是對(duì)斯賓諾莎解經(jīng)方法的誤讀。
關(guān)鍵詞:施特勞斯;斯賓諾莎;《圣經(jīng)》解釋?zhuān)灰越?jīng)解經(jīng)
作者簡(jiǎn)介:黃啟祥,男,山東大學(xué)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暨哲學(xué)與社會(huì)發(fā)展學(xué)院副教授,從事西方近代哲學(xué)、美國(guó)哲學(xué)及西方宗教哲學(xué)研究。
基金項(xiàng)目:山東大學(xué)自主創(chuàng)新基金青年團(tuán)隊(duì)項(xiàng)目“經(jīng)典詮釋與哲學(xué)創(chuàng)新”,項(xiàng)目編號(hào):IFYT1213
中圖分類(lèi)號(hào):B565.5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0-7504(2014)01-0044-08
理解斯賓諾莎不僅對(duì)于一般讀者來(lái)說(shuō)是一件困難的事,對(duì)于一個(gè)猶太哲學(xué)家來(lái)說(shuō)也不容易。利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對(duì)斯賓諾莎的誤解或許就是一個(gè)例子。施特勞斯是20世紀(jì)著名哲學(xué)家,也是最重要的斯賓諾莎研究者之一,他對(duì)斯賓諾莎著作的解釋已經(jīng)被西方哲學(xué)界視為經(jīng)典,正因?yàn)槿绱耍麑?duì)斯賓諾莎的誤讀尤其值得我們關(guān)注。
施特勞斯在《如何解讀斯賓諾莎的〈神學(xué)政治論〉》一文中說(shuō),理解他人的話(huà)語(yǔ)意味著兩種不同的情況,即解釋?zhuān)╥nterpretation)和闡明(explanation)。解釋是確定言者所言以及言者實(shí)際上如何理解其所言,而闡明則是確定未被言者所意識(shí)到的含義。施特勞斯認(rèn)為,解釋必定先于闡明,而要確定對(duì)給定文本的理解要求何種程度或者何種準(zhǔn)確的解釋?zhuān)仨毷紫攘私庾髡叩膶?xiě)作習(xí)慣或?qū)懽鞣绞健Kf(shuō):“一般說(shuō)來(lái),人們?cè)鯓娱喿x就怎樣寫(xiě)作。……因此,通過(guò)研究一個(gè)作者的閱讀習(xí)慣,我們也許預(yù)先就會(huì)知道他的寫(xiě)作習(xí)慣。”[1](P144)如果一個(gè)作者明確地論述了讀書(shū)的正確方式,或者明確地論述了他對(duì)某本書(shū)已經(jīng)進(jìn)行了大量的研究,那么我們就會(huì)由此而獲知他的讀書(shū)方式。斯賓諾莎在《神學(xué)政治論》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來(lái)論述如何解讀他曾非常仔細(xì)地反復(fù)閱讀的《圣經(jīng)》,由此,為了確定如何解讀斯賓諾莎,我們應(yīng)該研究他閱讀《圣經(jīng)》的方法。
人們是否怎樣閱讀就怎樣寫(xiě)作?一個(gè)作者論述了閱讀一種書(shū)的方法是否就意味著他用這種方法閱讀所有的書(shū),并進(jìn)而運(yùn)用這種方法進(jìn)行寫(xiě)作?對(duì)于這些一般性的問(wèn)題,本文不想泛泛地討論。本文關(guān)注的是施特勞斯對(duì)斯賓諾莎的解經(jīng)方法的解讀,至少根據(jù)他的上述觀點(diǎn),這關(guān)系到他對(duì)斯賓諾莎的解釋是否正確。因?yàn)椋绻`解了斯賓諾莎解讀《圣經(jīng)》的原則和方法,他就誤解了斯賓諾莎的寫(xiě)作方法,從而也就不能正確地解釋《神學(xué)政治論》,更不可能對(duì)它進(jìn)行正確的闡明。
一、以經(jīng)解經(jīng)是否不需要?dú)v史材料
斯賓諾莎在《神學(xué)政治論》中一再?gòu)?qiáng)調(diào),必須完全根據(jù)《圣經(jīng)》解釋《圣經(jīng)》,只有清楚地出自《圣經(jīng)》本身的教導(dǎo)才能被看成是《圣經(jīng)》的教導(dǎo),關(guān)于《圣經(jīng)》的所有知識(shí)都必須出自《圣經(jīng)》本身。[2](P9-10,P98-101,P104-105,P108-109,P114-115,P181-182,P190-191)1我們把這個(gè)解經(jīng)原則簡(jiǎn)稱(chēng)為“以經(jīng)解經(jīng)”。對(duì)于斯賓諾莎來(lái)說(shuō),這是解釋《圣經(jīng)》的唯一正確原則。施特勞斯認(rèn)為,斯賓諾莎對(duì)于自己的這個(gè)解經(jīng)學(xué)原則的闡述“沒(méi)有準(zhǔn)確地表達(dá)他實(shí)際上所要求的東西”[1](P145-146)。這實(shí)際上是在說(shuō),斯賓諾莎在解釋《圣經(jīng)》時(shí)超出了這個(gè)原則,他在理解《圣經(jīng)》時(shí)還運(yùn)用了《圣經(jīng)》之外的東西。首先,施特勞斯說(shuō),《圣經(jīng)》的語(yǔ)言知識(shí)最初絕非出自《圣經(jīng)》,而是源于某種傳統(tǒng)。其次,有關(guān)作者的生平以及他們所寫(xiě)的書(shū)的歷史遭遇等,雖然我們可能從《圣經(jīng)》獲得部分知識(shí),但是我們沒(méi)有理由說(shuō)只能從《圣經(jīng)》獲得這些知識(shí)。斯賓諾莎本人對(duì)任何可以澄清這類(lèi)問(wèn)題的外部信息都表示歡迎。
這里的問(wèn)題是,在斯賓諾莎那里,以經(jīng)解經(jīng)是否就要完全拋開(kāi)有關(guān)《圣經(jīng)》的歷史材料,或者說(shuō)以經(jīng)解經(jīng)與運(yùn)用歷史材料解釋《圣經(jīng)》在斯賓諾莎的解經(jīng)學(xué)中是否相互抵牾?
斯賓諾莎說(shuō):“解釋《圣經(jīng)》的方法與解釋自然的方法沒(méi)有什么區(qū)別,它們是完全一致的。解釋自然的方法是,首先要搜集整理自然的歷史,作為確實(shí)可靠的材料的來(lái)源,由此推出自然事物的定義。解釋《圣經(jīng)》也需要準(zhǔn)備一部明晰的《圣經(jīng)》歷史,作為確實(shí)可靠的材料和原理的來(lái)源,由此通過(guò)合法的推理推出《圣經(jīng)》作者的本意。如果用以解釋《圣經(jīng)》和討論《圣經(jīng)》內(nèi)容的原理和材料都來(lái)自《圣經(jīng)》自身及其歷史,那么我們對(duì)《圣經(jīng)》的解釋就能夠免于錯(cuò)誤。”[2](P98)這可以視為斯賓諾莎解經(jīng)學(xué)原則的完整表述,他在別處把它簡(jiǎn)稱(chēng)為只根據(jù)《圣經(jīng)》來(lái)解釋《圣經(jīng)》或者關(guān)于《圣經(jīng)》的所有知識(shí)都必須出自《圣經(jīng)》本身。
我們看到,斯賓諾莎說(shuō)得很明白,解釋《圣經(jīng)》首先要準(zhǔn)備一部明晰的《圣經(jīng)》史,正如解釋自然首先要搜集整理自然事件和活動(dòng)的歷史一樣。以經(jīng)解經(jīng)就是根據(jù)《圣經(jīng)》自身及其歷史來(lái)解釋《圣經(jīng)》。稍后,他在下文中進(jìn)一步明確地說(shuō):“解釋《圣經(jīng)》的普遍規(guī)則是不要把我們沒(méi)有從它的歷史中清楚地認(rèn)識(shí)的東西歸之于它的教導(dǎo)。”[2](P99)接著,他具體地?cái)⑹隽私忉尅妒ソ?jīng)》所需要的必須是什么樣的歷史,它主要與什么相關(guān)。首先是完備的《圣經(jīng)》語(yǔ)言知識(shí),《圣經(jīng)》的原文是希伯來(lái)語(yǔ)和希臘語(yǔ),其中希伯來(lái)語(yǔ)尤其重要。其次,所有的先知書(shū)和每一個(gè)歷史記載被保存的詳情,每卷書(shū)的作者是誰(shuí),他的生活、性格如何,他關(guān)注何事,他因何而寫(xiě),在什么時(shí)間寫(xiě)的,為誰(shuí)寫(xiě)的,用什么語(yǔ)言寫(xiě)的。再者,還必須包括每卷書(shū)的命運(yùn):它最初是如何被接受的,落到了誰(shuí)的手里,關(guān)于它有多少不同的解讀,它是出于誰(shuí)的考慮而被承認(rèn)為圣書(shū)的,現(xiàn)在被人們公認(rèn)為神圣的這些卷書(shū)是如何統(tǒng)一成一體的。根據(jù)斯賓諾莎對(duì)于以經(jīng)解經(jīng)原則的解釋?zhuān)覀兦宄乜吹剿f(shuō)的以經(jīng)解經(jīng)也就是根據(jù)《圣經(jīng)》的歷史解經(jīng)。
“關(guān)于《圣經(jīng)》的所有知識(shí)都必須出自《圣經(jīng)》本身”是斯賓諾莎解經(jīng)原則的概括表達(dá)形式,其含義要通過(guò)對(duì)它的具體闡釋來(lái)展開(kāi)。以經(jīng)解經(jīng)的原則和對(duì)它的具體闡釋是內(nèi)在統(tǒng)一而不可分割的。施特勞斯把這兩者加以割裂,然后用后者反對(duì)前者,得出斯賓諾莎對(duì)于這個(gè)原則表述不準(zhǔn)確的結(jié)論。他在這個(gè)問(wèn)題上對(duì)斯賓諾莎的誤解是令人遺憾的,有些咬文嚼字式的苛求,更像斷章取義式的挑剔。類(lèi)似這種制造矛盾的誤讀在施特勞斯那里不止一處。比如,施特勞斯說(shuō)《神學(xué)政治論》的許多地方都明確地或暗含地認(rèn)為“啟示和預(yù)言作為超越人的理性能力的某種確定知識(shí)是可能的”,“而有一些段落則完全否認(rèn)任何超理性知識(shí)的可能性”,因此,“斯賓諾莎在我們可稱(chēng)為其著作的主題上自相矛盾”。[1](P169)艾倫·唐納根 (Alan Donagan)稱(chēng)之為不可原諒的肆意解讀。[3](P369-370)但是,我們看到施特勞斯對(duì)于斯賓諾莎以經(jīng)解經(jīng)原則的過(guò)于苛刻的理解完全沒(méi)有道理。如果我們完全拋開(kāi)《圣經(jīng)》之外的一切知識(shí),《圣經(jīng)》是根本無(wú)法解釋的,因?yàn)橹辽傥覀円ㄟ^(guò)閱讀《圣經(jīng)》之前所認(rèn)識(shí)的字詞及其含義來(lái)解讀《圣經(jīng)》。
認(rèn)為斯賓諾莎的以經(jīng)解經(jīng)原則是主張不要用《圣經(jīng)》之外的語(yǔ)言和歷史資料來(lái)解釋《圣經(jīng)》,這是施特勞斯對(duì)斯賓諾莎的一大誤解。實(shí)際上,施特勞斯對(duì)斯賓諾莎以經(jīng)解經(jīng)的原則做了更狹隘的理解:“鑒于《圣經(jīng)》有眾多不同的作者,我們必須根據(jù)每位作者自身來(lái)理解他們。”[1](P145)就是說(shuō),他認(rèn)為根據(jù)斯賓諾莎以經(jīng)解經(jīng)的原則,我們不但不能利用《圣經(jīng)》之外的材料,而且即便在《圣經(jīng)》之中,也不能用一個(gè)作者的話(huà)解釋另一個(gè)作者的話(huà)。而斯賓諾莎以經(jīng)解經(jīng)的內(nèi)在含義卻是根據(jù)《圣經(jīng)》的歷史來(lái)確定清楚明白的經(jīng)文的含義,然后根據(jù)清楚明白的經(jīng)文解釋暗昧不清的經(jīng)文。這種方法的運(yùn)用絕不限于一個(gè)作者自身的作品之內(nèi),而是貫徹于整個(gè)《圣經(jīng)》之中。斯賓諾莎說(shuō)得很清楚,要把各卷中與同一主題相關(guān)的經(jīng)文都匯集起來(lái)進(jìn)行考察。他更通過(guò)舉例具體說(shuō)明如何通過(guò)某位作者的話(huà)來(lái)解釋另一位作者的話(huà)。例如,他用“約伯記”第31章第12節(jié)中的“火”的含義(“憤怒”)來(lái)解釋摩西的話(huà)“神是火”。[2](P100-101)
斯賓諾莎的以經(jīng)解經(jīng)原則所強(qiáng)調(diào)的是,應(yīng)根據(jù)《圣經(jīng)》的歷史而不是排除《圣經(jīng)》的歷史來(lái)解釋《圣經(jīng)》。他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根據(jù)《圣經(jīng)》的歷史來(lái)解釋《圣經(jīng)》,所針對(duì)的是邁蒙尼德等人根據(jù)哲學(xué)知識(shí)或自然知識(shí)解釋《圣經(jīng)》的做法。斯賓諾莎在解釋為什么以經(jīng)解經(jīng)是唯一正確的方法時(shí)說(shuō):“《圣經(jīng)》記述的事物,大多不能從自然之光所認(rèn)識(shí)的原則推斷出來(lái),因?yàn)闅v史敘述和啟示構(gòu)成了《圣經(jīng)》的絕大部分篇幅。而歷史敘述賦予奇跡即自然中的異常事物很高的地位,并且都是與記述它們的歷史學(xué)家的意見(jiàn)和判斷相適應(yīng)的。此外,啟示也都是與先知的意見(jiàn)相適應(yīng)的。它們都確實(shí)超出了人的理解能力。因此,所有這些事物的知識(shí)即《圣經(jīng)》中幾乎每一事物的知識(shí)必須只通過(guò)《圣經(jīng)》本身來(lái)尋找。”[2](P98-99)“《圣經(jīng)》中包含的道德教導(dǎo),是可以通過(guò)共同概念證明的,但不能通過(guò)《圣經(jīng)》用以傳布這些道德教導(dǎo)的共同概念來(lái)證明,它們只能通過(guò)《圣經(jīng)》本身來(lái)確定。”[2](P99)“神的神圣性不能通過(guò)神跡來(lái)證實(shí),更不要說(shuō)有些神跡是假先知做出的。因此,《圣經(jīng)》的神圣性只能建立在它教導(dǎo)真正的德性這樣一個(gè)事實(shí)之上,但是它是否教導(dǎo)真正的德性只能通過(guò)《圣經(jīng)》本身來(lái)確定。如果我們不能通過(guò)《圣經(jīng)》來(lái)確定這一點(diǎn),那么我們對(duì)它的相信和證明就只是一個(gè)偏見(jiàn)。因此《圣經(jīng)》的所有知識(shí)必須都從《圣經(jīng)》自身來(lái)尋找。”[2](P99)正是因?yàn)椤妒ソ?jīng)》的知識(shí)不能從自然中尋找,所以,斯賓諾莎提醒說(shuō):“如果我們要尋找《圣經(jīng)》的含義,必須非常當(dāng)心,不要一心想著我們自己的推理——建立在自然知識(shí)的原則之上的推理(更不要說(shuō)我們的偏見(jiàn)了)。為了避免混淆事物的真實(shí)含義與它的真理,必須只通過(guò)語(yǔ)言用法來(lái)尋找含義,或者只從《圣經(jīng)》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推理。”[2](P100)總之,斯賓諾莎認(rèn)為:“就整個(gè)《圣經(jīng)》而言……它的意義只取決于它自己的歷史,而不是一般的自然史,后者只是哲學(xué)的基礎(chǔ)。”[2](P185)
二、以經(jīng)解經(jīng)是否需要引入外部原則定義整理《圣經(jīng)》
施特勞斯不僅從歷史材料方面而且從解釋前提上批評(píng)斯賓諾莎沒(méi)有貫徹以經(jīng)解經(jīng)的原則,因?yàn)樗J(rèn)為斯賓諾莎在解釋《圣經(jīng)》時(shí)引入了外部原則整理經(jīng)文。斯賓諾莎在解釋如何根據(jù)《圣經(jīng)》歷史解釋《圣經(jīng)》時(shí)說(shuō):“要把各卷中與同一主題相關(guān)的經(jīng)文都收集起來(lái),并按主題加以組織,以便我們易于發(fā)現(xiàn)與這主題有關(guān)的所有內(nèi)容。”[2](P100)對(duì)此,施特勞斯說(shuō):“斯賓諾莎從未說(shuō)過(guò),關(guān)于《圣經(jīng)》各種重大主題的表述必須根據(jù)《圣經(jīng)》本身提供的原則加以編排;我們有理由相信,他自己對(duì)《圣經(jīng)》主題的排列根本沒(méi)有依據(jù)《圣經(jīng)》,而是與他所認(rèn)為的各主題的自然次序相一致。”[1](P146)
施特勞斯注意到,“斯賓諾莎從未說(shuō)過(guò),關(guān)于《圣經(jīng)》各種重大主題的表述必須根據(jù)《圣經(jīng)》本身提供的原則加以編排”。確實(shí)如此。但是他由此得出結(jié)論說(shuō)斯賓諾莎對(duì)《圣經(jīng)》各主題的排列是根據(jù)他所認(rèn)為的自然次序,則是屬于過(guò)度乃至錯(cuò)誤的解讀,兩者之間并不存在必然聯(lián)系。因?yàn)橹辽購(gòu)睦碚撋险f(shuō)還有另外兩種可能:其一,斯賓諾莎雖然沒(méi)有說(shuō)《圣經(jīng)》的各主題的排列必須根據(jù)《圣經(jīng)》本身提供的原則,但是他實(shí)際上這樣主張或者我們可以從他的明確論述中推出這個(gè)主張;其二,在斯賓諾莎那里也許根本不存在《圣經(jīng)》中各主題之間的排列問(wèn)題。
事實(shí)上,斯賓諾莎似乎從未說(shuō)過(guò)《圣經(jīng)》中各大主題的排列次序問(wèn)題。他所說(shuō)的是把與同一主題相關(guān)的經(jīng)文收集組織起來(lái),以便我們易于發(fā)現(xiàn)與該主題有關(guān)的所有內(nèi)容,由此用含義清楚的經(jīng)文解釋含義暗昧的經(jīng)文。斯賓諾莎似乎也從未說(shuō)過(guò)有排列所有這些主題的必要,因?yàn)樗官e諾莎認(rèn)為《圣經(jīng)》不是一部經(jīng)過(guò)嚴(yán)格推理寫(xiě)成的書(shū),而是不同時(shí)代的眾多人員所寫(xiě)的書(shū)匯編在一起的。人們閱讀《圣經(jīng)》,知道它在某個(gè)主題上教導(dǎo)什么就夠了,似乎沒(méi)有必要把它的各個(gè)主題編排成一個(gè)邏輯上一致的整體。而且,對(duì)于沒(méi)有接受過(guò)哲學(xué)訓(xùn)練的絕大多數(shù)讀者來(lái)說(shuō),這樣做也是不可能的。
施特勞斯認(rèn)為,斯賓諾莎是根據(jù)各主題的自然次序來(lái)排列它們的,這是出于對(duì)斯賓諾莎這個(gè)說(shuō)法的誤解:即解釋《圣經(jīng)》的方法與解釋自然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斯賓諾莎所說(shuō)的解釋自然與解釋《圣經(jīng)》方法上的一致指的是形式上和程序上的一致。從形式上說(shuō),自然知識(shí)和《圣經(jīng)》知識(shí)各自出于自己的歷史。從程序上說(shuō),解釋自然要從自然史得出事物的定義和共同概念,由之進(jìn)行推理,得出具體事物的知識(shí);解釋《圣經(jīng)》要從《圣經(jīng)》的歷史得出事物的定義和普遍教導(dǎo),由之解釋其他的經(jīng)文。但是,這種形式和程序上的一致絕不是主題或內(nèi)容上的一致,恰恰相反,斯賓諾莎通過(guò)兩種方法在形式上的一致性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恰恰是它們?cè)趦?nèi)容上的絕然不同:“《圣經(jīng)》中幾乎每一事物的知識(shí)必須只通過(guò)《圣經(jīng)》本身來(lái)尋找,就像自然知識(shí)必須通過(guò)自然本身來(lái)尋找一樣。”[2](P99)他借此劃分開(kāi)自然與《圣經(jīng)》,劃分開(kāi)自然知識(shí)與《圣經(jīng)》知識(shí)。他所強(qiáng)調(diào)的是我們不能根據(jù)《圣經(jīng)》解釋自然,也不能根據(jù)自然解釋《圣經(jīng)》,當(dāng)然也就不能根據(jù)自然的次序來(lái)排列《圣經(jīng)》的主題。所以,即便存在著將《圣經(jīng)》中各主題加以排列的問(wèn)題,施特勞斯的說(shuō)法——斯賓諾莎“對(duì)《圣經(jīng)》主題的排列根本沒(méi)有依據(jù)《圣經(jīng)》,而是與他所認(rèn)為的各主題的自然次序相一致”——也是不能成立的。而且,施特勞斯自己在這個(gè)問(wèn)題上的說(shuō)法也自相沖突,因?yàn)樗谕黄恼碌牧硗庖粋€(gè)地方說(shuō)斯賓諾莎對(duì)《圣經(jīng)》的解讀實(shí)際上是根據(jù)猶太人的傳統(tǒng)來(lái)排列各個(gè)主題次序的,即不是根據(jù)自然次序來(lái)排列的。
施特勞斯還認(rèn)為,斯賓諾莎為《圣經(jīng)》中的事物所下的定義超出了《圣經(jīng)》。“他[斯賓諾莎]認(rèn)為解釋本身在于確定《圣經(jīng)》所處理的各主題的定義,而這些定義確實(shí)不是由《圣經(jīng)》自身提供的;作為定義,它們超越了《圣經(jīng)》的范圍。” [1](P146)施特勞斯的這個(gè)批評(píng)是否有道理?
斯賓諾莎的原話(huà)是:“就像自然沒(méi)有給自然中的事物下任何定義一樣,《圣經(jīng)》也沒(méi)有給它所說(shuō)的事物下定義。因此正如自然事物的定義是從不同的自然活動(dòng)中得出的,同樣,[《圣經(jīng)》中的事物的定義]也應(yīng)從《圣經(jīng)》中關(guān)于它們的不同敘述中引出來(lái)。”[2](P99)根據(jù)斯賓諾莎的論述,《圣經(jīng)》不是以哲學(xué)的方式寫(xiě)作的,沒(méi)有為其中的事物下定義,要闡明《圣經(jīng)》的思想內(nèi)容,就要通過(guò)《圣經(jīng)》本身的材料來(lái)明確有關(guān)論題的定義,比如,《圣經(jīng)》被看成神的啟示,那么什么是啟示?它在《圣經(jīng)》中的具體含義要通過(guò)《圣經(jīng)》來(lái)確定,而不能來(lái)自《圣經(jīng)》之外。這是以經(jīng)解經(jīng)原則的體現(xiàn),解釋《圣經(jīng)》的普遍規(guī)則是不要把我們沒(méi)有從它的歷史中清楚地理解的東西歸于它的教導(dǎo)。所以,與施特勞斯的理解相反,斯賓諾莎所強(qiáng)調(diào)的恰恰是《圣經(jīng)》中事物的定義不能超越《圣經(jīng)》的范圍。如果像施特勞斯那樣,把得自《圣經(jīng)》本身的定義看成超越《圣經(jīng)》的知識(shí),那么自然知識(shí)也超越了自然,科學(xué)家對(duì)自然的解釋也不是根據(jù)自然解釋自然了。
三、以經(jīng)解經(jīng)是否要把握《圣經(jīng)》作者的本意
根據(jù)施特勞斯的解讀,斯賓諾莎所說(shuō)的解經(jīng)原則即只根據(jù)《圣經(jīng)》解釋《圣經(jīng)》,沒(méi)有準(zhǔn)確地表達(dá)他實(shí)際上所要求的東西。換言之,斯賓諾莎所說(shuō)的只根據(jù)《圣經(jīng)》解釋《圣經(jīng)》,實(shí)際上是以《圣經(jīng)》之外的材料、次序和定義來(lái)解釋《圣經(jīng)》。他由此認(rèn)為斯賓諾莎所說(shuō)的根據(jù)《圣經(jīng)》解釋《圣經(jīng)》不是要理解《圣經(jīng)》作者的本意,而是把自己的意見(jiàn)強(qiáng)加于《圣經(jīng)》。他說(shuō):“斯賓諾莎的解釋學(xué)原則是‘只根據(jù)《圣經(jīng)》本身來(lái)理解《圣經(jīng)》,我們所堅(jiān)持的原則是‘必須如其作者或匯編者所理解的那樣來(lái)準(zhǔn)確地理解《圣經(jīng)》……兩種原則之間的不同是根本的。”[1](P147)施特勞斯說(shuō),根據(jù)斯賓諾莎的解釋原則,“我們開(kāi)始搜集整理《圣經(jīng)》有關(guān)各主題的表述時(shí),關(guān)于哪些是中心主題或重要主題,什么樣的編排與《圣經(jīng)》思想一致,都沒(méi)有任何來(lái)自《圣經(jīng)》本身的指引”[1](P147)。“因此對(duì)《圣經(jīng)》的解釋不在于準(zhǔn)確地像其作者理解他們自身一樣理解他們,而是要比他們理解自身更好地理解他們。”[1](P146)這等于說(shuō)斯賓諾莎主張讀者把自己的思想讀進(jìn)《圣經(jīng)》,否認(rèn)了斯賓諾莎是根據(jù)《圣經(jīng)》解釋《圣經(jīng)》。1
斯賓諾莎明確地說(shuō)他之所以探討解釋《圣經(jīng)》的真正方法,是因?yàn)樗磳?duì)用偏見(jiàn)和虛構(gòu)來(lái)解釋《圣經(jīng)》的神學(xué),“決心毫無(wú)偏見(jiàn)地以自由的精神認(rèn)真地重新考察《圣經(jīng)》,只要不是它非常清楚地教導(dǎo)的,都不予以肯定,都不承認(rèn)為《圣經(jīng)》的教導(dǎo)”[2](P9)。如果按照施特勞斯的理解,斯賓諾莎無(wú)疑是主張用自己的偏見(jiàn)來(lái)歪曲《圣經(jīng)》,或者說(shuō)用自己的偏見(jiàn)來(lái)代替?zhèn)鹘y(tǒng)神學(xué)的偏見(jiàn)。與施特勞斯的看法相反,斯賓諾莎以經(jīng)解經(jīng)的原則所真正要求的正是要像《圣經(jīng)》的作者那樣準(zhǔn)確地理解他們,“不把過(guò)多或過(guò)少的內(nèi)容歸于作者或者作者的寫(xiě)作對(duì)象,這樣,我們所想的就正是作者心中所想的,或者那時(shí)間和場(chǎng)合所要求的”2。
施特勞斯認(rèn)為自己與斯賓諾莎的解經(jīng)學(xué)原則的根本不同在于:“根據(jù)我們的原則,翻開(kāi)一本書(shū)時(shí)首先會(huì)提這樣的問(wèn)題:它的主題思想是什么?就是說(shuō),作者如何構(gòu)思、理解其主題?他研究這個(gè)主題的動(dòng)機(jī)是什么?關(guān)于這個(gè)主題他提出什么問(wèn)題?或者說(shuō),他唯一或主要關(guān)心主題的哪個(gè)方面?只有在這些和類(lèi)似的問(wèn)題找到自己的答案之后,我們甚至才會(huì)思考作者對(duì)自己著作所討論或涉及的各種話(huà)題的編輯和安排。因?yàn)橹挥谢卮鹆松鲜鰡?wèn)題,我們才能判斷哪些特別的主題含義重大或者處于中心位置。”[1](P147)
從施特勞斯的這個(gè)表述及其對(duì)斯賓諾莎的批評(píng),我們可以推知他的一個(gè)設(shè)定,即《圣經(jīng)》是一本具有嚴(yán)格的統(tǒng)一構(gòu)思和體系的著作。正因?yàn)槿绱耍耪f(shuō)根據(jù)他自己的解釋規(guī)則,解讀《圣經(jīng)》時(shí)首先要考察《圣經(jīng)》的主題思想、作者如何構(gòu)思和理解其思想。但是,施特勞斯忽視了斯賓諾莎所一再?gòu)?qiáng)調(diào)的事實(shí),即《圣經(jīng)》不是一部科學(xué)著作,不是從定義和共同概念出發(fā),經(jīng)過(guò)一步步的嚴(yán)格推理寫(xiě)成的書(shū)。《圣經(jīng)》沒(méi)有為任何事物下定義,也不是經(jīng)過(guò)統(tǒng)一構(gòu)思的作品,而是在漫長(zhǎng)的歷史時(shí)期湊集起來(lái)的書(shū)。作為整部《圣經(jīng)》的主題思想根本不是任何一個(gè)《圣經(jīng)》作者所曾考慮的。所以,施特勞斯所說(shuō)的解釋方法并不適用于《圣經(jīng)》。
施特勞斯的這個(gè)錯(cuò)誤設(shè)定還導(dǎo)致他對(duì)斯賓諾莎的另一個(gè)觀點(diǎn)即解經(jīng)步驟的誤解。斯賓諾莎說(shuō),解釋《圣經(jīng)》首先要把握《圣經(jīng)》中到處可見(jiàn)的清楚明白的普遍教導(dǎo)。施特勞斯質(zhì)疑說(shuō):“一本書(shū)最根本的教誨有不斷重復(fù)的必要嗎?換言之,一本書(shū)最普遍最根本的教誨必然是最清楚的教誨嗎?”[1](P147)當(dāng)施特勞斯這樣說(shuō)的時(shí)候,他已經(jīng)把《圣經(jīng)》視為一個(gè)人或一個(gè)集體在同一時(shí)期寫(xiě)成的哲學(xué)著作了。而在斯賓諾莎看來(lái),正是因?yàn)闅v史上不同時(shí)代的先知向大眾教導(dǎo)同樣的東西,所以《圣經(jīng)》中的根本教誨必然會(huì)不斷重復(fù)。也許有人說(shuō),雖然《圣經(jīng)》的作者是不同時(shí)代的人,他們沒(méi)有共同的寫(xiě)作綱領(lǐng)和計(jì)劃,那些匯編《圣經(jīng)》的人應(yīng)該有自己的綱領(lǐng)和計(jì)劃,所以,刪定以后的《圣經(jīng)》應(yīng)該是一部系統(tǒng)統(tǒng)一的書(shū)了。對(duì)此,我們可以說(shuō),刪定者固然有自己的指導(dǎo)思想,斯賓諾莎也不否認(rèn)這一點(diǎn)。但是匯編者畢竟是刪定而不是創(chuàng)作歷史上的文本,而這些被匯編的文本本身及其相互之間并沒(méi)有科學(xué)著作那樣內(nèi)在一致的連續(xù)性和邏輯性。事實(shí)上,我們今天看到的《圣經(jīng)》仍然充滿(mǎn)著錯(cuò)誤與矛盾。
正因?yàn)槭┨貏谒節(jié)撛诘卣J(rèn)為《圣經(jīng)》是一部具有嚴(yán)格的統(tǒng)一體系的著作,所以他明確地說(shuō)他的解釋學(xué)原則與斯賓諾莎的解釋學(xué)原則的不同基于一個(gè)前提性的差異,即他認(rèn)為《圣經(jīng)》本質(zhì)上是可以理解的,而斯賓諾莎則認(rèn)為《圣經(jīng)》在本質(zhì)上是不可理解的。[1](P147-148)他由此認(rèn)為,正是因?yàn)樗官e諾莎認(rèn)為《圣經(jīng)》本質(zhì)上是不可理解的,所以要完全像《圣經(jīng)》的作者理解自己那樣理解他們是不可能的,理解《圣經(jīng)》的所有努力,必然是努力比《圣經(jīng)》的作者自身更好地理解他們。[1](P148)斯賓諾莎是否否認(rèn)《圣經(jīng)》本質(zhì)上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暫且不論,留待后面探討。這里的問(wèn)題是,如果斯賓諾莎不知道《圣經(jīng)》的作者如何理解自己,他如何能夠知道他對(duì)他們的理解比他們對(duì)自身的理解更好?施特勞斯這里似乎暗示,斯賓諾莎認(rèn)為《圣經(jīng)》的作者并不理解自己。而在斯賓諾莎看來(lái),雖然歷史間距所導(dǎo)致的各種解釋障礙使得對(duì)大部分經(jīng)文的準(zhǔn)確解釋都變得不可能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們?cè)诠糯彩遣豢衫斫獾模灰馕吨妒ソ?jīng)》各卷書(shū)的作者也不理解自己的話(huà)。根據(jù)斯賓諾莎,《圣經(jīng)》的作者在他們生活的時(shí)代進(jìn)行傳道時(shí)所說(shuō)的話(huà)都是非常簡(jiǎn)單明了的,當(dāng)時(shí)的普通人都能一聽(tīng)了然。事實(shí)上,斯賓諾莎從未說(shuō)過(guò)解釋《圣經(jīng)》是努力比其作者更好地理解他們,他的解經(jīng)方法的目的是把握《圣經(jīng)》作者的原意。這里還暴露了施特勞斯對(duì)斯賓諾莎的理解中的自相矛盾。他一方面說(shuō)斯賓諾莎認(rèn)為我們不可能像《圣經(jīng)》的作者理解自己那樣理解他們,另一方面又說(shuō)斯賓諾莎認(rèn)為“我們必須根據(jù)每位作者自身來(lái)理解他們”[1](P145)。而這兩方面都是施特勞斯強(qiáng)加于斯賓諾莎的觀點(diǎn)。
四、《圣經(jīng)》是否可以理解
施特勞斯說(shuō)他對(duì)斯賓諾莎的《圣經(jīng)》解釋學(xué)的所有拒斥都基于這個(gè)前提,即《圣經(jīng)》本質(zhì)上是可以理解的。“而斯賓諾莎恰恰否認(rèn)這樣的前提。在他看來(lái),《圣經(jīng)》在本質(zhì)上是不可理解的,因?yàn)椤妒ソ?jīng)》的絕大部分經(jīng)文說(shuō)的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圣經(jīng)》只是偶爾可以得到理解,因?yàn)橹挥心軌蚺迤湟饬x的一少部分材料才真正有用。事實(shí)上,《圣經(jīng)》是一本‘象形文字般的難解的書(shū);正是《圣經(jīng)》的不可理解性使人們有理由不得不用特殊的辦法對(duì)它進(jìn)行解釋?zhuān)哼@樣做的目的是開(kāi)辟一個(gè)間接通道——即通過(guò)其主題內(nèi)容——使某本不可直接理解的書(shū)得以讀懂。這暗示我們,并非所有書(shū)籍,而只有象形文字般的書(shū),要求用這種方法從根本上加以解釋?zhuān)拖衿平庾匀恢畷?shū)一樣。斯賓諾莎首先關(guān)心《圣經(jīng)》各處都清楚教導(dǎo)的東西,因?yàn)橹挥羞@樣一種普遍存在的教誨,也許可以引導(dǎo)讀者理解在《圣經(jīng)》中出現(xiàn)的所有象形文字般的段落。正是因?yàn)槠浔举|(zhì)的不可理解性,《圣經(jīng)》必須唯有通過(guò)自身得以理解:《圣經(jīng)》絕大部分內(nèi)容除非通過(guò)它本身是無(wú)論如何不可理解的東西。”[1](P148)
斯賓諾莎的確認(rèn)為,《圣經(jīng)》的絕大部分經(jīng)文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他并沒(méi)有說(shuō)只有能夠弄清其意義的一少部分材料才真正有用。根據(jù)斯賓諾莎,《圣經(jīng)》中那些不可理解的經(jīng)文雖然不能給人以真正的知識(shí),但是它們?nèi)匀豢赡苁怯杏玫模此鼈兛梢杂绊懭藗兊母星椋苿?dòng)人們遵從《圣經(jīng)》所教導(dǎo)的道德規(guī)則。
斯賓諾莎認(rèn)為,理解自然要從最普遍最清楚明白的知識(shí)出發(fā),同樣理解《圣經(jīng)》也要從最普遍的最清楚明白的經(jīng)文出發(fā),由此進(jìn)一步去認(rèn)識(shí)普遍性次一些的經(jīng)文。《圣經(jīng)》中到處都在教導(dǎo)的經(jīng)文無(wú)疑是最普遍的。斯賓諾莎還認(rèn)為,《圣經(jīng)》的普遍教誨不僅是清楚明白的、自身就可以理解的,而且從這些普遍的清楚表明的教誨可以進(jìn)一步解釋普遍性次一級(jí)的道德教誨。但是,這絕非像施特勞斯所說(shuō)的那樣,它們可以引導(dǎo)讀者理解《圣經(jīng)》中出現(xiàn)的所有象形文字般的段落。斯賓諾莎明確地說(shuō),《圣經(jīng)》中的絕大部分經(jīng)文不僅是通過(guò)其本身不可理解的,而且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理解的。
“正是因?yàn)槠浔举|(zhì)的不可理解性,《圣經(jīng)》必須唯有通過(guò)自身才得以理解。”施特勞斯這種說(shuō)法本身是難以理解的。如果《圣經(jīng)》的絕大部分經(jīng)文都是本質(zhì)上不可理解的,我們?nèi)绾瓮ㄟ^(guò)其自身來(lái)理解它們?本質(zhì)上不可理解的東西是不可能只根據(jù)其自身來(lái)理解的。唯一的途徑就是借助外部原理或權(quán)威。斯賓諾莎恰恰反對(duì)運(yùn)用來(lái)自外部的權(quán)威或理性知識(shí)來(lái)解釋《圣經(jīng)》。事實(shí)上,斯賓諾莎的意思與施特勞斯的理解正好相反。斯賓諾莎認(rèn)為,《圣經(jīng)》中存在著自身就可理解的經(jīng)文,而且只有那些自身就可理解的經(jīng)文才能夠只通過(guò)自身而得以理解,自身不可理解的經(jīng)文只有借助《圣經(jīng)》的歷史資料才可能得以解釋。所以,與施特勞斯的說(shuō)法即“《圣經(jīng)》中絕大部分內(nèi)容是除非通過(guò)它本身而無(wú)論如何不可理解的東西”不同,斯賓諾莎的意思是,占《圣經(jīng)》絕大部分的自身不可理解的經(jīng)文是無(wú)論如何不能通過(guò)自身而得到清楚解釋的,它們唯有通過(guò)《圣經(jīng)》的歷史資料才有可能加以解釋。
施特勞斯混淆了斯賓諾莎的兩個(gè)概念即解釋和理解。他把斯賓諾莎的以經(jīng)解經(jīng)解讀為只根據(jù)《圣經(jīng)》理解《圣經(jīng)》。他認(rèn)為解釋先于闡明,而解釋首先是理解。當(dāng)他這樣說(shuō)的時(shí)候意味著他假定一切文本都是可理解的,否則,理解無(wú)從談起,繼而解釋和闡明都不可能。但是,斯賓諾莎的以經(jīng)解經(jīng)則是只根據(jù)《圣經(jīng)》解釋《圣經(jīng)》。根據(jù)斯賓諾莎的論述,理解是理性對(duì)事物的真理性認(rèn)識(shí)。而“《圣經(jīng)》文本中幾乎沒(méi)有什么事情能夠確定地從自然之光所知的原則中推出來(lái),因此自然之光的力量不可能在它們的真理方面為我們確定任何東西”[2](P114)。《圣經(jīng)》不是教授自然知識(shí)的書(shū),不是以理性證明的方式寫(xiě)成的,我們不能通過(guò)《圣經(jīng)》理解《圣經(jīng)》。《圣經(jīng)》的絕大部分內(nèi)容是不可理解的,這意味著理性無(wú)法認(rèn)識(shí)這些內(nèi)容的真理性。但是,不可理解的經(jīng)文并非不可解釋?zhuān)覀內(nèi)匀豢梢酝ㄟ^(guò)《圣經(jīng)》以及相關(guān)的歷史資料來(lái)解釋它們屬于哪一類(lèi)(神話(huà)或寓言),《圣經(jīng)》中為什么會(huì)有這么多不可理解的內(nèi)容,以及它們具有什么樣的作用。
雖然施特勞斯曾說(shuō),“斯賓諾莎將《圣經(jīng)》解釋發(fā)展成一門(mén)純粹的科學(xué)”[4](P159),他對(duì)斯賓諾莎的《圣經(jīng)》學(xué)與自然科學(xué)的關(guān)系的論述卻很成問(wèn)題。他認(rèn)為,斯賓諾莎之所以要求像解釋自然之書(shū)一樣解釋《圣經(jīng)》,是因?yàn)樗鼈冊(cè)诒举|(zhì)上都是不可理解的。這使他對(duì)斯賓諾莎產(chǎn)生了雙層誤解。首先,他誤以為斯賓諾莎把自然看成本質(zhì)上是不可理解的。斯賓諾莎從未在任何地方說(shuō)過(guò)自然本質(zhì)上是不可理解的,而是在任何時(shí)候都主張自然是可理解的。根據(jù)斯賓諾莎的論述,自然知識(shí)或者科學(xué)知識(shí)都是對(duì)于自然的認(rèn)識(shí)。如果自然本質(zhì)上不可理解,我們?nèi)绾文軌驌碛凶匀恢R(shí)或科學(xué)知識(shí)?施特勞斯的這個(gè)錯(cuò)誤理解源于他誤讀了斯賓諾莎關(guān)于解釋《圣經(jīng)》與解釋自然的方法的比較,即解釋《圣經(jīng)》的方法與解釋自然的方法是一致的。根據(jù)斯賓諾莎,這種一致性表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第一,如前所述,這種一致是形式上和程序上的一致,而絕非內(nèi)容上的一致。自然是可理解的,而《圣經(jīng)》的絕大部分內(nèi)容是不可理解的,因此我們不能根據(jù)自然知識(shí)來(lái)理解《圣經(jīng)》,就像不能根據(jù)《圣經(jīng)》來(lái)理解自然一樣,而必須只根據(jù)《圣經(jīng)》來(lái)解釋《圣經(jīng)》,就像只根據(jù)自然來(lái)解釋自然一樣。
第二,前面已涉及,解釋的次序是一樣的。斯賓諾莎說(shuō):“在研究自然物時(shí),我們首先去努力研究最普遍的也是自然中共有的東西——即運(yùn)動(dòng)和靜止,以及它們的規(guī)律和規(guī)則,自然總是服從這些規(guī)律和規(guī)則并以此而連續(xù)地運(yùn)行——由此逐漸地繼續(xù)到普遍性較小的其他事物。同樣,我們首先要從《圣經(jīng)》中尋找的是:最普遍的東西,作為整個(gè)《圣經(jīng)》的基礎(chǔ)和根本的東西,以及所有先知在《圣經(jīng)》中都稱(chēng)贊的永恒教導(dǎo)、對(duì)所有人最有用的東西。”[2](P102)例如,唯一的全能的神存在,他關(guān)心所有人,他最?lèi)?ài)那些崇拜他以及愛(ài)鄰如己的人。“一旦我們正確地認(rèn)識(shí)了《圣經(jīng)》中的普遍教導(dǎo),我們必須繼續(xù)研究普遍性次一些的內(nèi)容,它們關(guān)涉我們平常如何指導(dǎo)我們的生活,它們就像溪流一樣自普遍教導(dǎo)而出。例如,所有真正德性之個(gè)別的外在行為,它們只能在給定的場(chǎng)合起作用。在這類(lèi)事情上,如果我們?cè)凇妒ソ?jīng)》中發(fā)現(xiàn)有任何模糊不明之處,都必須根據(jù)《圣經(jīng)》的普遍教導(dǎo)來(lái)解釋和決定。如果我們發(fā)現(xiàn)任何相互矛盾的經(jīng)文,我們必須要看它們是在什么場(chǎng)合什么時(shí)間寫(xiě)的,是為誰(shuí)而寫(xiě)的。”[2](P103)斯賓諾莎按照這個(gè)次序要解釋的是《圣經(jīng)》中的教導(dǎo)即普遍的道德原則、具體的道德準(zhǔn)則和道德行為,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經(jīng)文。也就是首先把握《圣經(jīng)》中最清楚的普遍教導(dǎo)來(lái)進(jìn)一步解釋普遍性次一級(jí)的教導(dǎo),而不是像施特勞斯所說(shuō)的,運(yùn)用這樣一種普遍的教導(dǎo),引導(dǎo)讀者理解在《圣經(jīng)》中出現(xiàn)的所有不可理解的段落。雖然斯賓諾莎認(rèn)為這種解經(jīng)方法是唯一正確的方法,但是,他同時(shí)看到這個(gè)方法包含的許多重大困難,比如它要求完備的希伯來(lái)語(yǔ)知識(shí)是我們現(xiàn)在無(wú)法獲得的。再者,這個(gè)方法需要《圣經(jīng)》各卷書(shū)的相關(guān)情況的歷史資料,而這些歷史資料的絕大部分是我們所不知道的。這個(gè)解經(jīng)方法還包含一個(gè)困難,即我們持有的《圣經(jīng)》的語(yǔ)言與它最初寫(xiě)成的語(yǔ)言并不是同一種語(yǔ)言。斯賓諾莎說(shuō):“這些困難是如此巨大,我毫不猶豫地?cái)嘌裕谠S多地方,我們或者不知道《圣經(jīng)》的真正含義,或者只能進(jìn)行不確定性的猜測(cè)。”[2](P111)盡管《圣經(jīng)》的絕大部分經(jīng)文的真理性是我們的理性無(wú)法理解的,在斯賓諾莎看來(lái),這對(duì)人們也沒(méi)有什么損失,因?yàn)檫@些內(nèi)容怎么理解都無(wú)所謂,只要這種理解不使人違背《圣經(jīng)》的真正道德教導(dǎo)。
參 考 文 獻(xiàn)
[1] Leo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2] Spinoza. 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 translated by Martin D. Yaffe. Newburyport, Focus Publishing, R. Pullins Ccompany, 2004.
[3] Alan Donagan. “Spinozas theology”,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pinoza, edited by Don Garret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Leo Strauss. “Cohens Analysis of Spinozas Bible Science”, in The Early Writing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ichael Zank.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責(zé)任編輯 付洪泉]
Leo Straus Misreading of Spinozas Way of Interpreting Bible
HUANG Qi-xia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Judaism and Transreligio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Straus believes that when Spinoza interprets Bible, he does not carry out his proposition of interpreting Bible according to Bible, since he borrows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interpret and introduces external principle and definition to arrange Bible. Out of the incomprehensibility nature of Bible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it according to itself and do this out of the intention of the author. The criticism of Straus is actually a misreading of Spinozas way of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Straus; Spinoza; interpretation of Bible; interpreting Bible according to Bible
1 本文引用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一書(shū)所標(biāo)注頁(yè)碼為格布哈特(Gebhardt)編輯版本的頁(yè)碼。
1 施特勞斯在另一部著作中表達(dá)了與此相反的理解:“斯賓諾莎要求《圣經(jīng)》學(xué)應(yīng)該成為一種不偏不倚地理解《圣經(jīng)》的手段。……如果解釋者將自己的洞見(jiàn)或信念帶入了《圣經(jīng)》文本……《圣經(jīng)》就沒(méi)有得到理解。”(Leo Strauss, Spinozas Critique of Religion, translated by E. M. Sinclair,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Inc., 1965, p.262)
2 Theological-political treatise, VII, p.110. 施特勞斯自己在1931年所寫(xiě)的《柯亨與邁蒙尼德》一文中實(shí)際上也承認(rèn)斯賓諾莎的歷史-考據(jù)解經(jīng)是像作者自己理解自己那樣理解作者。參見(jiàn)施特勞斯:《柯亨與邁蒙尼德》,載劉小楓主編:《猶太哲人與啟蒙》,華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