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寶玉形象與男旦文化的因緣
程宇昂,梁健榮
賈寶玉形象與男旦文化的因緣
程宇昂,梁健榮
(韶關(guān)學(xué)院文學(xué)院,廣東韶關(guān)512005)
賈寶玉是性身份障礙的同性戀者,男旦演員的娼優(yōu)合一對(duì)這一形象的創(chuàng)造有啟迪之功。清代中前期男旦文化的特殊背景是寶玉形象誕生的重要土壤,賈寶玉是男旦文化的代言人。《紅樓夢(mèng)》的傳播可能傷害男性受眾的剛健氣質(zhì)。
賈寶玉;男旦;因緣
近年來(lái)賈寶玉幾乎被定格成一個(gè)具有平民意識(shí)的叛逆者的形象。如果將其還原到形象誕生的男旦文化大背景中,從性心理學(xué)角度觀照,寶玉會(huì)以更為真實(shí)的立面現(xiàn)形,小說(shuō)《紅樓夢(mèng)》批評(píng)與接受的一些共識(shí)將面臨挑戰(zhàn)。本文參考文本為八十回《石頭記》①本文所引小說(shuō)原文均出自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5年版《脂硯齋重評(píng)石頭記》。。
一、同性戀者
《紅樓夢(mèng)》貌似描寫(xiě)一個(gè)異性戀者的俗世情緣,取舍在乎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之間。如果把一塊石頭的事跡看作心理學(xué)案例,美學(xué)的玩味和意識(shí)形態(tài)的解讀自然冰釋,寶玉昭然為同性戀者,《紅樓夢(mèng)》描述一個(gè)同性戀者內(nèi)心糾結(jié)、最終注定要逸出異性戀愛(ài)模式主宰的塵界的人生經(jīng)歷。或許這正符合脂硯齋的指引:“觀者記之,不要看這書(shū)正面,方是會(huì)看。”(十二回脂批)
弗洛伊德、靄理士、哈斯、馬莫等對(duì)同性戀各有定義。要言之,同性戀指“以同性為滿足性欲的對(duì)象”[1]的行為。同性戀作為一個(gè)醫(yī)學(xué)名詞有內(nèi)在的規(guī)定性,《中國(guó)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biāo)準(zhǔn)》第三版(CCMD-3)將其納入“性指向障礙(Sexual orientation disorders)”條目下:“同性戀:系指正常生活條件下,從少年時(shí)期就開(kāi)始對(duì)同性成員持續(xù)表現(xiàn)性愛(ài)傾向,包括思想、感情及性愛(ài)行為。對(duì)異性雖可有正常的性行為,但性愛(ài)傾向明顯減弱或缺乏,因此難以建立和維持與異性成員的家庭關(guān)系。”[2]323定義規(guī)定兩方面的判定標(biāo)準(zhǔn):第一、對(duì)異性“性愛(ài)傾向明顯減弱或缺乏”,存在與之組成家庭的障礙;第二、對(duì)同性“持續(xù)表現(xiàn)性愛(ài)傾向”。證之寶玉完全吻合。
第一,賈寶玉對(duì)釵、黛等異性性愛(ài)旨趣明顯不足。此處特指性愛(ài)旨趣,而非泛指一般友情。《紅樓夢(mèng)》彌漫著賈寶玉對(duì)少女們的泛愛(ài)情懷,他似乎是鐘愛(ài)異性的情種。其實(shí),整部小說(shuō)非常確定地描寫(xiě)賈寶玉異性性行為的文字只集中在第五、六回。第五回記錄寶玉的一次夢(mèng)遺:警幻仙姑秘授云雨之事,寶玉與秦可卿兒女繾綣,有了第一次異性性體驗(yàn)。第六回寫(xiě)寶玉夢(mèng)醒之后與襲人初試云雨情。其后,小說(shuō)再未明確描寫(xiě)其異性性行為。五、六兩回描寫(xiě)寶玉僅有的兩次性高潮是描述其異性性取向遇阻,夢(mèng)境本身即明證:交媾后,寶玉但見(jiàn)“荊榛遍地,狼虎同群”,“黑溪阻路,并無(wú)橋梁可通”,警幻仙姑勸其離開(kāi)萬(wàn)丈迷津“作速回頭”,最終寶玉被夜叉海鬼拖走。性心理學(xué)研究成果證明“在男性同性愛(ài)者的性夢(mèng)中,常常出現(xiàn)……與異性性交的恐懼”,如被卷進(jìn)漩渦等[3]109。評(píng)點(diǎn)家亦解此中真意,第八回寶釵將通靈寶玉托于掌上(通靈寶玉隱喻男性生殖器),脂批警示:“試問(wèn)石兄此一托,比在青埂峰下猿啼虎嘯之聲何如?”后七十四回描述寶玉離開(kāi)一般性愛(ài)模式回歸自性。前少數(shù)章回描寫(xiě)主人公一種生命狀態(tài),后大多數(shù)章回描寫(xiě)其另一種生命狀態(tài),這種結(jié)構(gòu)與小說(shuō)《西游記》異曲同工。
令一般讀者疑惑的是,賈寶玉作為“天下今古第一淫人”,親昵大觀園中尊貴與卑賤的裙釵,對(duì)女性尤其是少女有好感,這是其具有異性性傾向的明證。其實(shí),作者明確地將寶玉之淫定義為“淫雖一理,意則有別”的“意淫”即精神戀愛(ài)時(shí),已肯定其對(duì)異性性愛(ài)的減弱與回避,這恰是同性戀者的特征之一。正如晴雯與寶玉“有染”最終被證實(shí)“擔(dān)了虛名”,其他少女的情況不過(guò)如此。馬倫的研究表明,男性同性愛(ài)者“對(duì)女性性別的認(rèn)同程度大大超過(guò)男性異性愛(ài)者”[3]70,故寶玉作為同性戀者對(duì)少女們非性愛(ài)的親近屬于正常狀態(tài)。
第二,賈寶玉對(duì)多位同性持續(xù)表現(xiàn)性愛(ài)傾向,對(duì)象為聰俊靈秀美少男。
多人,至少包括秦鐘、蔣玉菡、北靜王、柳湘蓮。四人之中,寶玉與秦鐘、蔣玉菡的同性戀關(guān)系最為明確。第七回二人相見(jiàn)便兩情脈脈,寶玉見(jiàn)秦鐘“眉清目秀,粉面朱唇”,“心中似有所失,癡了半日”。秦鐘心生暗恨,以不能與寶玉“耳鬢交接”為“世間之大不快事”。二人表現(xiàn)正可印證“同性戀的眼神有渴望感”[4]的特征。第八回,寶玉當(dāng)著賈母面稱贊秦鐘“最使人憐愛(ài)”,賈府上下也很快接受了他,貧富障礙輕松跨過(guò)。蒙府側(cè)批曰:“‘憐愛(ài)’二字,寫(xiě)出寶玉真神。若是別個(gè),斷不可透露。”批語(yǔ)贊寶玉之真性情時(shí)為其透露同性性取向捏把汗。第九回,寶玉建議“不必論叔侄,只論弟兄朋友”,二人親密的倫理屏障消除。第十五回,秦鐘與智能交合,寶玉拿雙,秦鐘求饒:“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寶玉答:“等一會(huì)睡下,再細(xì)細(xì)的算賬。”作者賣關(guān)子:“寶玉不知與秦鐘算何賬目,未見(jiàn)真切,未曾記得,此系疑案,不敢纂創(chuàng)。”雖是一貫“甄士隱”的手法,但明確傳遞信息:二人已實(shí)質(zhì)性性交往。賈寶玉與蔣玉菡有曖昧關(guān)系,寶玉挨打的原因?yàn)椤傲魇巸?yōu)伶”等。二人首次獨(dú)自面對(duì)時(shí),“寶玉見(jiàn)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著他的手”,隨之贈(zèng)以墜扇、松花汗巾,蔣亦回贈(zèng)大紅汗巾子。蔣是忠順王府王爺“斷斷少不得”的男寵,與寶玉交往后不愿回去。賈政深知城內(nèi)十停人有八停人知道他與寶玉“相與甚厚”的語(yǔ)中之意,“又驚又氣”之下痛打?qū)氂瘛:榍镛u(píng)曰:“優(yōu)伶之名愈著,則斷袖之好愈多。蔣玉菡即琪官,名馳天下,其老斗必車載斗量。而況與寶玉初親芝采,即解茜羅,其濫于納交尤可想。”“老斗”指親昵男性優(yōu)伶的同性戀者。襲人嫁蔣玉菡時(shí)洪評(píng)又云:“內(nèi)寵外寵,旗鼓相當(dāng)。”[5]“外寵”指男色,內(nèi)寵指女色,蔣玉菡、襲人曾是寶玉性伙伴,難怪有人感慨:“蔣玉菡一男子耳,而寶玉直趨之若鶩,豈男色之移人亦同于女色乎?”[6]940小說(shuō)對(duì)北靜王、柳湘蓮與寶玉同性關(guān)系的描寫(xiě)較為隱晦,但草蛇灰線有跡可尋。寶玉、北靜王初見(jiàn)面即互為對(duì)方相貌吸引。寶玉眼中的北靜王“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北靜王眼中的寶玉“面若春花,目如點(diǎn)漆”。北靜王對(duì)寶玉多有饋贈(zèng),且有含深意者。如初見(jiàn)面時(shí)贈(zèng)以鹡鸰香串。鹡鸰,一種鳥(niǎo)類,后以之喻兄弟。《詩(shī)·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即“鹡鸰”。“兄弟”為男同代名詞之一。再次,蔣玉菡曾以大紅汗巾子贈(zèng)寶玉,這汗巾恰是北靜王贈(zèng)與蔣玉菡的,瓜田李下,北靜王隱約為同志,其與賈寶玉常常“談會(huì)談會(huì)”的親密關(guān)系很不尋常。小說(shuō)對(duì)柳湘蓮的描寫(xiě)支離破碎,但仍可見(jiàn)其與寶玉“如魚(yú)得水”的關(guān)系。最能體現(xiàn)這一關(guān)系的是第四十七回:寶玉問(wèn)柳湘蓮近日是否上過(guò)秦鐘的墳,柳湘蓮說(shuō)他也擔(dān)心秦墳為雨水沖壞,就“背著眾人”探看并“雇了兩個(gè)人收拾好”。柳湘蓮避嫌的態(tài)度此地?zé)o銀,寶玉牽掛秦鐘正與此同,祭墳、探冢都悄悄委托茗煙。三人關(guān)系蹊蹺如此。賈寶玉向柳湘蓮說(shuō)起秦鐘時(shí),脂批曰:“忽于此處柳湘蓮提及,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也。”姚燮則說(shuō)他們“同氣相投”。總之,小說(shuō)“以寶玉為中心形成了兩對(duì)循環(huán)三角戀關(guān)系”[7]:寶玉、秦鐘、柳湘蓮;寶玉、蔣玉菡、北靜王。寶玉無(wú)一例外的被四人相貌所吸引而惺惺相惜。作品對(duì)寶玉與四人關(guān)系的描寫(xiě)有隱有顯、詳略各異,這并不利于科學(xué)分析,卻是遵循文學(xué)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必然結(jié)果。
持續(xù),指寶玉與同性少年連續(xù)多年保持親密關(guān)系。若能考證出寶玉與其他四人的年齡,編出他們的交往年表,厘清他們的性交往史,科學(xué)的結(jié)論即可得出。可是,小說(shuō)家言多自相矛盾處,未遵循史學(xué)態(tài)度、方法與體例,事事坐實(shí)可能反而不科學(xué)。其實(shí)換個(gè)角度從章回入手亦可證實(shí)之。第五回“伏下秦鐘”。第七回,寶玉與秦鐘一見(jiàn)鐘情,這一安排非常微妙。第六回最后一次正面描寫(xiě)寶玉的異性性愛(ài),此回正式轉(zhuǎn)入同性戀描寫(xiě)。寶玉與秦鐘令同窗起疑并“詬誶謠諑”的熱烈交往持續(xù)至秦鐘殞命的第十六回。七至十六回,秦鐘是小說(shuō)的重要人物。秦鐘淡出前北靜王淡入。第十四回引出北靜王。第十五回又是小說(shuō)的微妙回目。此回有兩個(gè)核心內(nèi)容:其一,寶玉與北靜王一往情深的相見(jiàn)。其二,秦鐘奸淫智能事。甲戌脂批認(rèn)為,本回實(shí)寫(xiě)“秦、玉、智能幽事”。以此衡量,秦鐘的行為是對(duì)寶玉的背叛,是異性性愛(ài)與同性性愛(ài)的較量。合二事而觀之,秦鐘早夭符合文本的內(nèi)在邏輯,北靜王將取而代之。同性戀與異性戀的一個(gè)很大不同在于變更對(duì)象的頻次較高。北靜王最后一次出現(xiàn)在賈府是第七十一回,其余回目有十六回、二十四回、四十三回、四十五回等。小說(shuō)集中描寫(xiě)寶玉與蔣玉菡的關(guān)系在第二十八、三十三、三十四回,與柳湘蓮的關(guān)系在第四十四、六十六、六十七、七十回。“作者有兩意”(戚序),從同性性愛(ài)的角度綜觀整部文本,小說(shuō)先寫(xiě)寶玉異性性愛(ài)水土不服,接著隱晦而執(zhí)著、斷續(xù)而富于層次地描述了他與四位少男的同性戀情,這一過(guò)程從第七回持續(xù)至第七十一回。四人之中,秦鐘、琪官是最合適的同性情人,地位使然,同性性愛(ài)的時(shí)代境遇使然。秦鐘死,琪官別,第七十回連柳湘蓮也“冷遁了”,寶玉“似染怔忡之疾”,生命進(jìn)入垃圾時(shí)間。
不管八十回《紅樓夢(mèng)》原書(shū)是否寫(xiě)了“十五年”[8]的事情,同性戀抒寫(xiě)占全書(shū)比重之大的事實(shí)表明,賈寶玉持續(xù)的同性戀傾向是明確的,其性愛(ài)歸宿只有一個(gè):與同性相伴。可是,賈府正在衰敗,上下忙著“偷狗戲雞”,寶玉良材美質(zhì),作為男人正是賈家希望所在,其性愛(ài)取向自然無(wú)法兌現(xiàn)。結(jié)果順理成章:寶玉“得寶釵之妻,麝月之婢……棄而為僧”(二十一回脂批)。表面看是異性婚姻所娶非人,實(shí)質(zhì)上是同性性取向遭遇斷崖,男大當(dāng)婚的境地已無(wú)退路。故釵黛之爭(zhēng)不過(guò)是逃避婚姻的托辭,二玉結(jié)合同樣難以善終。
小說(shuō)雖用“橫云斷嶺法”,還是能看出同性戀抒寫(xiě)的千里伏脈。寶玉同性戀的主脈周圍,有男女同性戀者呈拱衛(wèi)之勢(shì),男如忠順王府王爺、賴尚榮、賈蓉、賈薔、邢德全、薛蟠、馮淵、喜兒、香憐等,女如伶人蕊官、菂官、藕官等。
二、性身份障礙者:不一樣的同性戀者
很多學(xué)者提及賈寶玉的同性戀行為,但很少有人深入探究其同性戀的特異之處:他是同性戀者中的性身份障礙者。
CCMD-3將性心理障礙分為三種:性身份障礙,性偏好障礙,性指向障礙。性身份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GID),舊有易性癖等多種稱謂,其特點(diǎn)是有變換自身性別的強(qiáng)烈欲望。男性性身份障礙的診斷標(biāo)準(zhǔn)是:第一、持久和強(qiáng)烈地為自己是男性而痛苦,渴望自己是女性或堅(jiān)持自己是女性,并至少有下列一項(xiàng):(1)專注于女性常規(guī)活動(dòng),表現(xiàn)為偏愛(ài)女性著裝或強(qiáng)烈渴望參加女性的游戲或娛樂(lè)活動(dòng),拒絕參加男性的常規(guī)活動(dòng);(2)固執(zhí)地否定男性解剖結(jié)構(gòu),至少可由下列一項(xiàng)證實(shí):斷言將長(zhǎng)成女人;明確表示陰莖或睪丸令人厭惡;認(rèn)為陰莖或睪丸即將消失,或最好沒(méi)有。第二、上述障礙至少已持續(xù)6個(gè)月[2]322。賈寶玉存在性身份障礙,有來(lái)自兩個(gè)方面的證據(jù):文本的客觀證據(jù),作者和評(píng)點(diǎn)者的主觀證據(jù)。
文本的客觀證據(jù),指小說(shuō)描寫(xiě)的賈寶玉的外貌、行為和心理客觀上符合男性性身份障礙者的特點(diǎn)。
首先,寶玉持久和強(qiáng)烈地為自己是男性而痛苦,拒絕參加男性的常規(guī)活動(dòng)。寶玉厭惡自己生理解剖上的男性特征幾乎與生俱來(lái)。他七八歲前就認(rèn)為“男人是泥作的”,乃“濁物”,因此見(jiàn)了男子“便覺(jué)濁臭逼人”,這讓人懷疑其抓周只抓“脂粉釵環(huán)”時(shí)可能已經(jīng)出現(xiàn)性別特征的逆反行為。濁物包括寶玉,第五回游太虛幻境,仙子們就抱怨警幻“引這濁物來(lái)污染這清凈女兒之境”,可見(jiàn)寶玉對(duì)男人的厭惡實(shí)是對(duì)自身性別的厭惡。“濁物”為譬喻,文本還多次使用明確代表男性特征的“須眉”一詞,與“濁物”連用成“須眉濁物”。內(nèi)心的厭惡外化為行動(dòng),“寶玉杜絕了進(jìn)退應(yīng)對(duì)、慶吊往還的人事”[9],遠(yuǎn)離男人當(dāng)做之事。日常生活之外,寶玉人生規(guī)劃和職業(yè)選擇與男性格格不入,“于國(guó)于家無(wú)望”。他討厭有利于求職的正經(jīng)書(shū),視有進(jìn)取心者為“祿蠹”、“國(guó)賊祿鬼”,拒絕承擔(dān)“文死諫”、“武死戰(zhàn)”的國(guó)家義務(wù)。另一方面,寶玉正符合男性性身份障礙者“對(duì)職業(yè)的選擇則與女性偏愛(ài)心理有關(guān)”[3]334的特征,“最喜在內(nèi)幃廝混”。
其次,寶玉渴望自己是女性,把自己當(dāng)成女性的一分子,專注于女性常規(guī)活動(dòng)。
行為上,他有愛(ài)紅的毛病,著紅衣,吃口紅,住怡紅院,院中景致及室內(nèi)陳設(shè)頗具女兒味。他“每日只和姊妹丫頭們一處”,十分快樂(lè)。讀的是女孩子喜歡的書(shū),游戲是“斗草簪花”,干活包括“調(diào)脂弄粉”、“描鸞刺鳳”、替女孩梳頭。他常常“無(wú)故尋愁覓恨”,據(jù)統(tǒng)計(jì),前八十回明確描寫(xiě)其哭的情節(jié)“達(dá)19次”[10]之多。總之,寶玉“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寶玉渴望成為女性,水仙庵之祭一節(jié)描寫(xiě)最為直接。寶玉灑淚祭畢,茗煙跪祝:“二爺?shù)男氖拢覜](méi)有不知道的……讓我待祝:若芳魂有靈……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lái)生也變個(gè)女孩兒。”寶玉此祭的原因小說(shuō)并未交代清楚,但厭惡“混供神混蓋廟”的他選擇此廟本身即不尋常。水仙者,洛神也,女人也。來(lái)此祭奠證明了寶玉對(duì)女性欣羨與膜拜的心理,茗煙的祈禱似諧實(shí)莊。故脂批說(shuō)“茗煙一戲直戲入寶玉心中”,靖藏說(shuō)“這方是作者真意”。
心理上,寶玉同樣討厭男性,羨慕女性并希望成為其中一員。他“并不想自己是丈夫”,外面的婆子看他“一點(diǎn)剛性也沒(méi)有”,賈母說(shuō)“想必原是個(gè)丫頭錯(cuò)投了胎”,其“女兒論”典型地體現(xiàn)了上述心理。傳言:寶玉認(rèn)為女兒這兩個(gè)字極尊貴極清靜,甚于佛祖和道教第一尊神的寶號(hào);他見(jiàn)女兒就清爽,見(jiàn)男子便覺(jué)濁臭逼人。作者:寶玉覺(jué)得“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鐘于女兒,須眉男子不過(guò)是些渣滓濁沫”。寶玉:女兒個(gè)個(gè)是好的,女人“染了男人的氣味”個(gè)個(gè)是壞的。值得注意的是,寶玉所言“須眉男子”一詞常被理解為同義結(jié)構(gòu)。證之小說(shuō)文本,當(dāng)為偏正結(jié)構(gòu),意為胡須眉毛稠秀的男子,即男性性征明顯的男子。男人一旦有女人味道就不再是濁物,秦鐘、琪官等非須眉的男子都是寶玉眼中的可人。明眼人評(píng)點(diǎn):“寶玉動(dòng)謂男子為濁物,度一面目黧黑,于思于思者耳。使溫潤(rùn)如好女,未嘗不以脂粉蓄之。”[6]270故,寶玉女兒論的實(shí)質(zhì)是肯定女性性征及女性,同時(shí)否定以“須眉”為代表的男性性征及男性。小說(shuō)使用了婉曲的表達(dá),直接陳述即寶玉厭惡自己的性器官。
從外貌、行為和心理看,寶玉在很大程度上持女性立場(chǎng),以女性自居,為性身份障礙者無(wú)疑。接著須辨認(rèn)寶玉究竟屬于男性GID的何種亞型。男性GID根據(jù)性取向不同可分為同性性取向和異性性取向兩個(gè)亞型。同性性取向者“通常從兒童時(shí)期開(kāi)始就具有相當(dāng)?shù)呐蕴刭|(zhì),包括外表和行為都比非同性性取向者更加女性化”。非同性性取向者“通常在童年時(shí)期不一定具有女性氣質(zhì),在成年后女性特征也不明顯。”[11]146寶玉與同性性取向者更為吻合,其性身份障礙開(kāi)始得早,外表女性化程度高。他“面如敷粉,唇若施脂”,眼花的老祖宗問(wèn)他是“那個(gè)女孩兒”,眼好的齡官“只當(dāng)是個(gè)丫頭”。有時(shí)隔門(mén)說(shuō)話連襲人、晴雯都聽(tīng)不出,麝月錯(cuò)當(dāng)成寶姑娘。性格上寶玉女性化程度同樣高,“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yǔ)纏綿。”其性格與男性氣質(zhì)明顯齟齬:“男性氣質(zhì)和主動(dòng)性是可以互換的術(shù)語(yǔ)。”[12]
以上客觀描述證明,寶玉是個(gè)同性性取向的男性性身份障礙者。文中同樣有很多主觀證據(jù),即作者、評(píng)點(diǎn)家多次暗示或明示其生理解剖性別與心理性別不同,可惜后來(lái)的批評(píng)者出于各種原因失察于此或不愿明察之。
以下就具有結(jié)構(gòu)性意義的主觀證據(jù)舉例說(shuō)明。
作者自云。開(kāi)篇第一回,作者回顧不成功的人生時(shí)痛定思痛:“何我堂堂須眉,誠(chéng)不若此裙釵哉?”問(wèn)句的形式顯示出深刻的思考。作者發(fā)憤著書(shū),期待“使閨閣昭傳”。本段有點(diǎn)明創(chuàng)作意圖的重要作用,作者在“須眉”與“裙釵”的比較中開(kāi)宗明義,將性別之論置于焦點(diǎn),言明崇女抑男的立場(chǎng)。此立場(chǎng)在文本中兌現(xiàn)為寶玉的立場(chǎng)。蒙府側(cè)批“受氣清濁,本無(wú)男女之別”,強(qiáng)調(diào)男女處于陰陽(yáng)消長(zhǎng)的動(dòng)態(tài)之中,沒(méi)有固定的陰陽(yáng)值。
女?huà)z煉石神話。此為引文,交代石頭由來(lái)即寶玉前世今生。女?huà)z,一般認(rèn)為其天下第一英雌。作者舍三皇五帝中眾男帝而取惟一女帝,應(yīng)與崇女旨意有關(guān)。賈府女性也是實(shí)際上的管理者。其實(shí)女?huà)z本身性別難明。清趙翼考證其“訛為婦人”,實(shí)為男性。女?huà)z、寶玉皆有性別之惑。另,女?huà)z摶土造人,“系創(chuàng)制婚姻媒妁之人”[13]。寶玉由女?huà)z煉石所化,卻是多余物,這暗示其非正常男女,也難與常規(guī)婚姻合轍。棄石落在“青埂峰下”,寶玉,寶玉所銜之玉均與青埂峰產(chǎn)生意義關(guān)聯(lián)。青埂,情根也,故脂批有“落墮情根”之說(shuō)。情根,若不舍近求遠(yuǎn),即指男性生殖器。有評(píng)點(diǎn)家恰中肯綮:“寶玉之玉即為命根。觀其式如扇墜,可大可小……又云在赤霞宮居住,靈河岸上行走,見(jiàn)絳珠仙草可愛(ài),日以甘露灌溉……試問(wèn):赤霞是何色,河岸是何地,何以又有甘露灌溉仙草?”[16]53補(bǔ)天石被棄青埂峰,暗示寶玉男性性征虛有其表。煉石神話是抱怨造物弄人,也是為寶玉性身份障礙尋找合理性。
寶玉之名。寶玉之名分姓名和綽號(hào)兩類。賈寶玉之名有假男人之意。玉為男性符號(hào)本有所自,俗謂男、女孩出生為“弄璋之喜”和“弄瓦之喜”,此俗不遲于《詩(shī)經(jīng)》時(shí)代:“乃生男子……載弄之璋。”除被棄青埂峰的描述外,小說(shuō)多有提醒文字。攜寶玉入世的茫茫大士托玉在掌,感嘆道:“形體到也是個(gè)寶物了,還只沒(méi)有實(shí)在的好處。”密友黛玉曾戲?qū)氂瘛爸翀?jiān)者是玉……爾有何堅(jiān)?”脂批叫絕:“大和尚來(lái)答此機(jī)鋒,想亦不能答也。”黛玉又稱其為“銀樣鑞槍頭”。外人同樣得窺寶玉內(nèi)里。寶玉夢(mèng)入甄府,丫鬟發(fā)現(xiàn)其“空有皮囊,真性不知那去了”。語(yǔ)中直接嵌入“性”字。既是夢(mèng),則其透露了寶玉性身份障礙的危機(jī)感。性淫的燈姑娘一改上述人等的含蓄風(fēng)格,調(diào)戲?qū)氂癫怀珊笾毖裕骸翱臻L(zhǎng)了一個(gè)好模樣兒,竟是沒(méi)藥信兒的炮仗。”寶玉“絳洞花王(主)”、“諸艷之冠”等綽號(hào),同樣與其性身份障礙相關(guān)。寶玉之玉又名通靈寶玉。通靈在“通于神靈”之外有“善于應(yīng)變”之義,該詞似乎暗示寶玉性身份突破了陰陽(yáng)之限。明乎此,俞平伯“‘情榜’六十名都是女子,卻以寶玉領(lǐng)頭,似乎也很奇怪”的話并不奇怪[14]。
麒麟與陰陽(yáng)之辯。第三十一回史湘云與翠縷有陰陽(yáng)之辯。湘云說(shuō),天地萬(wàn)物千變?nèi)f化都是“陰陽(yáng)順逆”,沒(méi)生命的扇子都有陰陽(yáng)。可是湘云不知自己所佩金麒麟的陰陽(yáng)。翠縷道:“姑娘是陽(yáng),我就是陰。”作者照例正言諧說(shuō),翠縷無(wú)意中的諧謔之言一語(yǔ)中的:湘云很有女性GID的嫌疑。她“不像個(gè)女孩兒家”,“好男子裝”,“到扮上男人好看”,“腥膻大吃大嚼”,喜“說(shuō)經(jīng)濟(jì)一事”,“從未把兒女私情略縈心上”。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藥裀”可能暗示其同性戀傾向。芍藥,俗稱雌牡丹。湘云與女性結(jié)合方才順性稱心。湘云所得雛伶葵官,大花面,乃男腳色。根據(jù)作者一貫手法,這一匹配是暗示湘云的男性性格特點(diǎn)。寶玉也有金麒麟。全府上下?lián)碛薪瘅梓氲娜耸莾晌划愋訥ID,這似非巧合。從小說(shuō)寫(xiě)陰陽(yáng)倒錯(cuò)者故事的角度看,二人乃綱領(lǐng)式人物,湘云陪襯著寶玉,金麒麟成陰陽(yáng)倒錯(cuò)者的象征。張新之解得玄奧:“湘云亦夢(mèng)中人主腦”。三十一回題目“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之意爭(zhēng)議頗多,循上文線索思考就較為清晰:雙星為寶玉、湘云,作者用金麒麟刻意將二人聯(lián)系在一起。麒麟為罕物,二人為罕人。雙星,牽牛、織女也,“白首雙星”在悲情神話基礎(chǔ)上更進(jìn)一步將姻緣難成的宿命渲染至極致;不是預(yù)示寶玉、湘云艱難成雙,小說(shuō)缺乏這方面的前奏,而是預(yù)示二人因性身份障礙各自孤守至白頭。要言之,第三十一回將寶玉、湘云拼合到一張性別太極圖上,定位在陰陽(yáng)小圓圈中,寶玉為陽(yáng)中陰,湘云為陰中陽(yáng)。寶玉、湘云因麒麟而合璧,小說(shuō)對(duì)性身份障礙的抒寫(xiě)進(jìn)入太極生陰陽(yáng)兩儀的層次,更富于張力。陰陽(yáng)之辯是從理論上探討性身份障礙。
寶玉出家。出家是對(duì)塵世的否定,是對(duì)自身生命的否定。作者安排寶玉出家可視為對(duì)其自殺傾向的溫和處理。“男性同性愛(ài)者企圖自殺的占20%,而在異性愛(ài)者中只占5%。”[15]而雷莫菲迪篤的研究表明:“有自殺傾向的與未曾有過(guò)自殺企圖的青少年男性同性愛(ài)者相比,前一類人有著較顯著的女性氣質(zhì)。”[3]228可見(jiàn),男性GID自殺比例更高,寶玉可能潛藏自殺傾向。“流露死亡的意愿是一個(gè)非常重要的自殺危險(xiǎn)信號(hào)”[16],寶玉輕言死字,兼以化灰化煙之說(shuō)。挨打后受到姐妹們的關(guān)愛(ài):“我便一時(shí)死了……亦無(wú)足嘆惜。”與黛玉賭氣:“我要是這么樣,立刻就死了!”告訴紫鵑:“我只愿這會(huì)子立刻我死了……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又:“等我化成一股輕煙,風(fēng)一吹便散了的時(shí)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寶玉出家的描寫(xiě)是為性身份障礙者無(wú)奈地尋找著歸宿。
其他如前文所論寶玉淺嘗異性戀、同時(shí)提出“意淫”概念等,都有構(gòu)建文脈的作用,勾勒寶玉的異常性取向。
總之,文本的客觀描述,作者的結(jié)構(gòu)性暗示,評(píng)點(diǎn)家的明確指引,共同確認(rèn)一個(gè)事實(shí):寶玉是性身份障礙者。他“醉魂酥骨”于黛玉身上的幽香,羨慕寶釵“雪白一段酥臂”,摩挲鴛鴦散發(fā)著香油氣的白膩肌膚,“像似淫極,然究竟不犯一些淫意”(十九回脂批),是索倫森發(fā)現(xiàn)的男性易性癖者對(duì)女性和自己的“‘女性’性別和那種柔弱氣質(zhì)有深深自我陶醉之感”[3]333。
三、賈寶玉形象與男旦文化的因緣
寶玉性身份障礙的實(shí)質(zhì)是男人陽(yáng)性質(zhì)素的貶損和陰性質(zhì)素的增益。學(xué)者進(jìn)行相關(guān)研究時(shí)將寶玉形象誕生的原因歸于“明清時(shí)期新思潮”[17]等。此類論斷雖有合理成分但畢竟大而化之。實(shí)際上,寶玉身上有男旦的影子,《紅樓夢(mèng)》濃郁的陰性氣氛與清中前期男旦文化背景的聯(lián)系可能更為直接。
(一)寶玉性身份障礙與男旦之優(yōu)的因緣
寶玉像男旦一樣陰陽(yáng)復(fù)合。隨著明清兩代逐漸禁絕官妓和女樂(lè),戲曲舞臺(tái)漸由男性主宰,飾演女性的男性演員謂之男旦。明以前弄假婦人等優(yōu)戲講究以男妝女的戲弄、夸奇等效果,明清男旦則注重性別反串的形神兼?zhèn)洹D醒輪T必須竭力摒棄天性成為“真正”的女人。寶玉與男旦演員的外貌等基本條件相當(dāng)。他在整部小說(shuō)中年齡不到二十,天生“花朵兒一般的模樣”,“直似一個(gè)守禮待嫁的女兒”(四十三回脂批)。男旦演員一般八九歲開(kāi)始學(xué)藝,最佳年齡在十三四歲到十八九歲,此時(shí)其男性性征不明顯,“女兒顏色女兒喉”[18]。寶玉愛(ài)紅,男旦演員也借“容飾”肖形于女性。衣飾、化妝之外,如果皮膚黝黑,種種“白肌法”能幫助他們“面首轉(zhuǎn)白,且加潤(rùn)焉”。白皙、潤(rùn)澤之外,“芳澤勤施,久而久之,則肌膚自香”[19]。性格上,寶玉“少年色嫩不堅(jiān)牢”(第三回脂批),男旦演員“可人性子耐溫寒”[20]9輯26冊(cè),152。柔弱材質(zhì),職業(yè)要求,加以年齒稚嫩時(shí)即開(kāi)始的嚴(yán)苛訓(xùn)練使他們具有女性性格傾向。心理方面,寶玉慕女甚至以女性自居,男旦“以其身為女,必并化其心為女……設(shè)身處地,不以為戲而以為真”[21]。
男旦演員陰陽(yáng)復(fù)合并不止于表演層面,還向日常生活延伸。好的演員舞臺(tái)上、生活中皆“婉孌如好女”[22]。明末鄧士亮有《戲贈(zèng)歌者蔣誕》詩(shī):“結(jié)束倚欄清晝長(zhǎng),蛾眉慵掃鬢慵妝。幽懷自?shī)Y風(fēng)情減,羞卻花間窈窕娘。”[20]6輯26冊(cè),19蔣為男旦,他像女子一樣描眉理鬢以打發(fā)漫長(zhǎng)清晝。此類職業(yè)習(xí)慣對(duì)演員的性心理有微妙影響。靄理士認(rèn)為:“越是把一個(gè)個(gè)體的生命史向前追溯,我們便越是接近一個(gè)雙性兩可的時(shí)期。”[23]之所以如此,人越年少越在體質(zhì)、心理方面有異性種子的存在。男旦,年少加之職業(yè)驅(qū)力的強(qiáng)化,其性身份障礙的可能性比一般人群大。如果弗洛伊德所說(shuō)童年孩子的性生活中總有一縷同性戀氣質(zhì)的論斷是對(duì)的,那么,男旦演員在很大程度上至少是境遇型的同性戀者。不僅如此,人以群分,戲班顯然是男性性身份障礙者的樂(lè)園,就像今天的夜總會(huì)等娛樂(lè)場(chǎng)合會(huì)齊聚“紅衣人”一樣。《揚(yáng)州畫(huà)舫錄》即有“生而好學(xué)婦人”[24]者的記載,該少年被其父怒而投江,最終做了男旦。《小豆棚》所記蜀伶聶小玉晚妝如婦人,與翟秋山共寢,“嬌容媚態(tài),肌膚滑澤,更非脂粉裙釵所得方其萬(wàn)一。”與一般男旦職業(yè)上的逢場(chǎng)作戲不同,正如聶小玉自己所說(shuō),他是賦男形而“實(shí)有女心”[25]。二人屬于典型的性身份障礙者。
總之,朱門(mén)紅氍毹和城市劇場(chǎng),男人們飾女妝、發(fā)女聲而作女態(tài),包括性身份障礙者和大量職業(yè)熏陶下的假性性身份障礙者,寶玉性身份障礙與他們的“曰男如女”驚人一致。
(二)寶玉同性戀與男旦之娼的因緣
寶玉形象與男旦文化的聯(lián)系不僅直接表現(xiàn)為寶玉與男旦之優(yōu)的肖似,還體現(xiàn)在與男旦業(yè)營(yíng)造的性愛(ài)風(fēng)氣的關(guān)聯(lián)上。在中國(guó),娼優(yōu)從來(lái)難以區(qū)分。他們是歌舞者,也可能是富于文藝才情的性伙伴。明清男旦在官妓非法的大背景下涌現(xiàn),大眾劇場(chǎng)之外,他們以女性身份出現(xiàn)在私家園林、酒樓酒莊及堂子中,唱曲優(yōu)觴,陪笑伴眠,實(shí)質(zhì)上兼任了妓女的工作,為樂(lè)伎。雖然一直沒(méi)有法律正式認(rèn)可他們戲曲舞臺(tái)之外的身份,但替代女伎越界經(jīng)營(yíng)從未遭受明令禁止,魯迅言“不得挾妓,然獨(dú)未云禁招優(yōu)”[26]即指此。
虛擬女伎的消費(fèi)者主要是男性,男旦業(yè)伴生的娼妓業(yè)實(shí)為男性同性戀業(yè)。同性戀在中國(guó)古代并不罕見(jiàn),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在性文化上呈現(xiàn)出一致性。不過(guò)明以前同性性取向能實(shí)現(xiàn)的人多為帝王、貴族及國(guó)柄,且實(shí)現(xiàn)概率較低。明中葉以降,中國(guó)突然成為男同天堂。“同性戀作為一種性愛(ài)的形式在這四百年左右的時(shí)期里幾乎享有與異性戀同樣的地位,而相當(dāng)一部分士人還把他視為風(fēng)流韻事而趨之若鶩。”[27]乾隆時(shí)英國(guó)人滿懷鄙夷地冷眼旁觀:“這種令人憎惡的、非自然的犯罪行為在他們那里卻引不起什么羞恥之感,甚至許多頭等官員都會(huì)無(wú)所顧忌地談?wù)摯耸露挥X(jué)得有什么難堪。這些官員們都有孌童侍候,那些漂亮的少年年齡在14至18歲之間,衣著入時(shí)。”[28]明清男風(fēng)盛行與男旦業(yè)的發(fā)展密切相關(guān),“士大夫所狎男色,半為優(yōu)伶。”[29]優(yōu)伶之中,又以男旦為最,他們是同性戀重要的被動(dòng)方。靄理士即指出同性戀的普遍與“‘相公’業(yè)的發(fā)達(dá)”[23]300有關(guān)。相公的主體為男旦。
戲曲是明清社會(huì)最重要的大眾娛樂(lè)方式之一,男旦業(yè)培育的同性戀風(fēng)氣有目共睹,此對(duì)《紅樓夢(mèng)》同性戀描寫(xiě)的啟迪功不可沒(méi)。
(三)寶玉形象與男旦文化的時(shí)間因緣
《紅樓夢(mèng)》創(chuàng)作時(shí)間約在乾隆初,一個(gè)性身份障礙的同性戀者的形象為什么誕生在這個(gè)時(shí)期?此時(shí)正是男旦時(shí)尚的一個(gè)重要時(shí)期:傳播期。時(shí)尚流行過(guò)程包括提倡、傳播、普及、下降和消失五個(gè)階段。傳播期的特點(diǎn)是:時(shí)尚開(kāi)始“獲得更多的人的承認(rèn)、贊賞、接納和模仿”[30]。么書(shū)儀有“乾隆四十四年出現(xiàn)了男旦的第一次走紅”[31]之論。么氏所論實(shí)為男旦在大眾娛樂(lè)圈的走紅。清初,男旦經(jīng)歷了走向大眾前的走紅。明代,男旦業(yè)一直處于溫和的發(fā)酵狀態(tài),男旦在民間為下里巴人,在縉紳家為金屋之?huà)桑o(wú)有力者揚(yáng)其波。入清后情況驟變,捧旦的隊(duì)伍規(guī)模大、級(jí)別高、聲勢(shì)盛。如順治間錢(qián)謙益、龔鼎孳、吳偉業(yè)等創(chuàng)作了大量詩(shī)篇為王紫稼揚(yáng)名,順治末康熙初陳維崧請(qǐng)人為鐘愛(ài)的男旦徐紫云寫(xiě)照并遍邀題詠,終于成就傳世畫(huà)作《紫云出浴圖卷》。順、康時(shí)期,文壇宗匠鼓吹出傳頌?zāi)械┑淖顝?qiáng)音,引領(lǐng)伎樂(lè)時(shí)尚。不管是否巧合,律令的執(zhí)行隨之一錘定音,雍正時(shí)官妓禁絕,城市劇場(chǎng)女伶絕跡,男旦成為娛樂(lè)場(chǎng)合不違法的公共美人的不二之選。以文人風(fēng)流方式為男旦張目的力度以前未曾有,男旦業(yè)普及的乾嘉以下也大為遜色。
傳播男旦美名是戲曲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內(nèi)在要求,也是文人以言樹(shù)碑的職責(zé)所在。在男旦業(yè)的深入發(fā)展只欠一聲吆喝的時(shí)候,詩(shī)文小說(shuō)作為當(dāng)時(shí)的傳媒傾巢出動(dòng)廣而告之。詩(shī)詞在文學(xué)諸體中能最為快捷地反映生活,笨拙的章回小說(shuō)慢人一拍,《紅樓夢(mèng)》于乾隆初編寫(xiě)“伶人最重旦色”(周廣業(yè)《過(guò)夏續(xù)錄》)的時(shí)代密碼正好應(yīng)時(shí)。另一方面,《紅樓夢(mèng)》作者恰有資格出手。從文本“比較廣”[32]地描寫(xiě)戲曲藝術(shù)看,其對(duì)當(dāng)時(shí)戲曲文化/男旦業(yè)了然于胸。寶玉四位同性戀對(duì)象中,兩位與男旦業(yè)相關(guān):蔣玉菡與柳湘蓮。蔣玉菡為男旦,其與寶玉、薛蟠等飲酒為樂(lè)是典型的男旦侑酒場(chǎng)面。柳湘蓮以串客飾小生,小生像旦腳一樣可以進(jìn)入伎樂(lè)行業(yè),薛蟠為柳湘蓮所揍即源于此類誤會(huì)。“《紅樓夢(mèng)》只能是誕生于18世紀(jì)中葉中國(guó)社會(huì)”[33]的斷語(yǔ)本意并非針對(duì)男旦文化背景,但同樣適用。雖可推定小說(shuō)作者對(duì)男旦文化了解深入,但研究缺憾明顯存在:至今無(wú)法斷定作者為誰(shuí),也就無(wú)法認(rèn)清其與男旦交往的細(xì)節(jié)。
(四)文學(xué)鍛造:從男旦到寶玉
在男旦文化最為神采飛揚(yáng)的時(shí)期,男旦之優(yōu)的戲曲表演讓《紅樓夢(mèng)》作者有幸見(jiàn)識(shí)全新的演藝可兒,男旦之娼的伎樂(lè)背景讓《紅樓夢(mèng)》作者感受著空前的同性戀氛圍。諸因素作用之下,男性性身份障礙者的形象胚胎已成,但距寶玉形象尚有一段距離。距離不僅在下等戲子與貴族公子的身份間,陰柔少年尚須風(fēng)骨的支撐和大道的熔鑄方具高格。男性性身份障礙的同性戀者在高格方面深具潛質(zhì),以下從兩個(gè)方面簡(jiǎn)而論之。
首先,男性性身份障礙者為良材美質(zhì),其良材美質(zhì)的注定被棄成就《紅樓夢(mèng)》的悲劇之美。性身份障礙者、同性戀者兩種提法在一般人心目中或許與優(yōu)美、崇高無(wú)緣,甚至可能引發(fā)不適感,但矛盾的兩面常常只隔一層紙,性心理學(xué)研究成果顯示,性身份障礙的同性戀者像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米開(kāi)朗基羅等同性戀者一樣多是良材美質(zhì):他們“心理非但無(wú)損,反而在智力與道德修養(yǎng)方面有高度成就的人身上”[3]104;“多少有幾分幼稚的狀態(tài)……面貌及體態(tài)上總見(jiàn)得比較年輕”[23]312;“抱著一種極端的審美的旨趣”[23]326;“最能博愛(ài),其對(duì)象是全人類,不只是一個(gè)人”[23]336……如此良材美質(zhì)琢磨成文學(xué)形象時(shí),若巧妙虛飾性身份認(rèn)同之“瑕”,其身上的美自然彰顯出來(lái),一個(gè)具有普世價(jià)值的智者、仁者和唯美者就此面世:美貌之外,寶玉聰明到“百個(gè)不及他一個(gè)”,博愛(ài)到見(jiàn)到燕子就“和燕子說(shuō)話”,其意淫、愛(ài)紅等行為更有審美的高度。性身份障礙者多不幸,寶玉智、仁、美的人生的毀滅兌換成小說(shuō)凝重的悲劇風(fēng)格,《紅樓夢(mèng)》的藝術(shù)品位得以提升。
其次,男性性身份障礙者良材美質(zhì)的獨(dú)特性具有獨(dú)特的文學(xué)價(jià)值。他們?cè)谌巳褐械谋壤按蟾旁?∶30 000-1∶10 000之間”[11]147,選擇比例如此之小的獨(dú)特人群作為小說(shuō)原型賦予寶玉與眾不同的“叛逆”稟賦,同時(shí)凸顯文學(xué)對(duì)人性的尊重。《紅樓夢(mèng)》使傳統(tǒng)的思想都打破了的說(shuō)法與寶玉形象的塑造直接相關(guān)。男性性身份障礙者的獨(dú)特性在于討厭男性身份而向往成為真正的女人,此本于性心理意義。性心理意義上的獨(dú)特性在文學(xué)作品中可以引申出審美意義和意識(shí)形態(tài)意義上的貴女賤男。審美意義上的貴女賤男,主要指對(duì)男性陽(yáng)剛之美的否定和對(duì)女性陰柔之美的肯定。意識(shí)形態(tài)意義上的貴女賤男,主要指尊重女性并對(duì)女性主宰社會(huì)寄予期盼,同時(shí)貶低男性并對(duì)男性主宰社會(huì)表達(dá)憎惡。寶玉人格要素,如叛逆、平民化、尊重女性、主張個(gè)性自由、憎惡須眉男子主宰的社會(huì)的一切,源頭皆在其厭男慕女的獨(dú)特性心理。更微妙的是,寶玉生逢其時(shí),形象誕生后約一個(gè)世紀(jì),一個(gè)老大帝國(guó)的百年滄桑開(kāi)始了,寶玉傾慕女性心理不知不覺(jué)間蛻變?yōu)闇嘏感灾郑爝M(jìn)華夏民族渴望溫存的心田。
總之,《紅樓夢(mèng)》是本言情的書(shū),且所言之情乃概率極小的歧情,作者試圖為之求證合理性。于是,良材美質(zhì)的另類在作者編織的語(yǔ)境中與亂疾叢生的頹勢(shì)家族、末世王朝成犄角之勢(shì),經(jīng)過(guò)巧妙點(diǎn)染與升華,一人之歧情幻化為具有廣泛社會(huì)關(guān)懷與人文關(guān)懷的曠世奇情。小說(shuō)的產(chǎn)生與清代中前期男旦文化背景有深廣的因緣,寶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男旦文化的代言人。
值得注意的是,借男性性身份障礙者表達(dá)貴女賤男理想帶有“原罪”意識(shí)。男旦演員將身上的雄性質(zhì)素剔除得越干凈就越職業(yè),男性性身份障礙者也是從根子上厭男慕女。厭男慕女并非在男女之間做適度權(quán)衡,而是以竭力消弭男性質(zhì)素為既定目標(biāo)。如此,無(wú)論是男旦業(yè)的繁榮還是《紅樓夢(mèng)》的傳播都會(huì)導(dǎo)致男性陽(yáng)剛氣質(zhì)受損和陰柔氣質(zhì)增加。與性身份障礙者或同性愛(ài)者那樣更是一種天性不同,男旦業(yè)和文學(xué)作品因商業(yè)運(yùn)作和藝術(shù)煽動(dòng)破壞著自然。從侵蝕男性受眾剛健氣質(zhì)的角度看,男旦業(yè)是帶毒的行業(yè),《紅樓夢(mèng)》是帶毒的名著。男旦業(yè)的影響主要是共時(shí)的;不朽的文字卻化共時(shí)為歷時(shí),持久影響閱讀者,《紅樓夢(mèng)》的潛在影響我們不能長(zhǎng)期失察。中華民族性別氣質(zhì)的失衡與男旦業(yè)的發(fā)展相當(dāng)程度上同步,重新審閱曾經(jīng)的時(shí)尚和將之凝成文化的文字記錄刻不容緩。《紅樓夢(mèng)》具有卓越的藝術(shù)魅力,惟其如此更須謹(jǐn)慎待之。新時(shí)期的文化轉(zhuǎn)型必須建立在大時(shí)空觀上。
[1]王玲.變態(tài)心理學(xué)[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20.
[2]陳彥方.CCMD-3相關(guān)精神障礙的治療與護(hù)理[M].濟(jì)南:山東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2001.
[3]張北川.同性愛(ài)[M].濟(jì)南:山東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1994.
[4]李銀河.中國(guó)人的性愛(ài)與婚姻[M].北京:中國(guó)友誼出版公司,2002:204.
[5]張?jiān)谥?曖昧的歷程——中國(guó)古代同性戀史[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435-436.
[6]人民中國(guó)出版社第二編輯部.紅樓夢(mèng)考評(píng)六種[M].北京:人民中國(guó)出版社,1992.
[7]施曄.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中的同性戀書(shū)寫(xiě)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41.
[8]周汝昌.《紅樓夢(mèng)》新證[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6:183.
[9]王昆侖.《紅樓夢(mèng)》人物論[M].北京:三聯(lián)書(shū)店,1983:236.
[10]林驊,方剛.賈寶玉——階級(jí)與性別的雙重叛逆者[J].紅樓夢(mèng)學(xué)刊,2002(1):124-138.
[11]陸崢.性功能障礙與性心理障礙[M].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12:146.
[12]弗洛伊德.性學(xué)三論[M].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2004:103.
[13]趙翼.陔余叢考[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299.
[14]俞平伯.《紅樓夢(mèng)》研究[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8:152.
[15]賀蘭特·凱查杜里安.人類性學(xué)基礎(chǔ)——性學(xué)觀止[M].北京:農(nóng)村讀物出版社,1987:436.
[16]劉新民,李建明.變態(tài)心理學(xué)[M].合肥:安徽大學(xué)出版社,2003:205.
[17]王富鵬.論明清時(shí)期新思潮與賈寶玉的女性氣質(zhì)[J].青海社會(huì)科學(xué),2001(1):78-81.
[18]續(xù)修四庫(kù)全書(shū)編纂委員會(huì).續(xù)修四庫(kù)全書(sh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集部1625冊(cè),383.
[19]張次溪.清代燕都梨園史料[M].北京:中國(guó)戲劇出版社,1988:624.
[20]《四庫(kù)未收書(shū)輯刊》編纂委員會(huì).四庫(kù)未收書(shū)輯刊[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21]紀(jì)昀.閱微草堂筆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77.
[22]徐珂.清稗類鈔[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6:5102.
[23]靄理士.性心理學(xué)[M].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6:312.
[24]李斗.揚(yáng)州畫(huà)舫錄[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60:131.
[25]曾七如.小豆棚[M].武漢:荊楚書(shū)社,1989:256.
[26]魯迅.中國(guó)小說(shuō)史略[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3:225.
[27]吳存存.明清社會(huì)性愛(ài)風(fēng)氣[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0:114.
[28]張杰.明清時(shí)期在華天主教在同性戀問(wèn)題上與中國(guó)的文化差異[J].中國(guó)性科學(xué),2005(5):40-43,48.
[29]王書(shū)奴.中國(guó)娼妓史[M].北京:團(tuán)結(jié)出版社,2004:306.
[30]趙慶偉.中國(guó)社會(huì)時(shí)尚流變[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3-4.
[31]么書(shū)儀.晚晴戲曲的變革[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6:125.
[32]徐扶明.《紅樓夢(mèng)》與戲曲比較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
[33]胡文彬.《紅樓夢(mèng)》與中國(guó)文化論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a Baoyu Image and Female Impersonators
CHENG Yu-ang,LIANG Jian-rong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5,Guangdong,China)
Jia Baoyu is both a gay and a GID.As actors and male prostitutes,female impersonators enlightened the creation of Jia Baoyu.He is a spokesperson of female impersonators of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amaging masculinity of male audiences,both the industry related with female impersonators and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are toxic.
Jia Baoyu image;female impersonators;cause
I207
A
1007-5348(2014)11-0045-08
(責(zé)任編輯:王焰安)
2014-10-08
教育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規(guī)劃基金項(xiàng)目“男旦與明清文化”(10YJAZH013);2013年國(guó)家級(jí)大學(xué)生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訓(xùn)練計(jì)劃項(xiàng)目“新時(shí)代文化公司模擬建立”(201310576-020)
程宇昂(1968-),男,安徽桐城人,韶關(guān)學(xué)院文學(xué)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古代文學(xué)、戲曲史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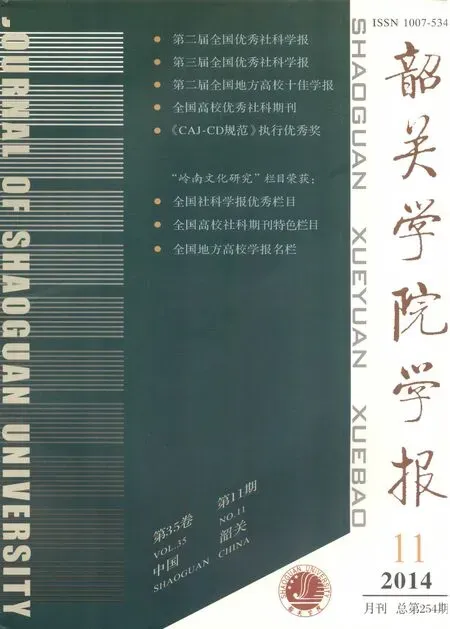 韶關(guān)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4年11期
韶關(guān)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4年11期
- 韶關(guān)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下地方高校管理類人才培養(yǎng)模式改革
- 應(yīng)用型本科院校國(guó)際金融雙語(yǔ)課程改革研究
- 大學(xué)生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教育的探索與實(shí)踐
——以會(huì)計(jì)與金融學(xué)院為例 - 積極心理學(xué)視角下高校貧困生的人文關(guān)懷
- 農(nóng)村大學(xué)生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認(rèn)同調(diào)查及教育策略
- 當(dāng)代大學(xué)生意志品質(zhì)的現(xiàn)狀與應(yīng)對(du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