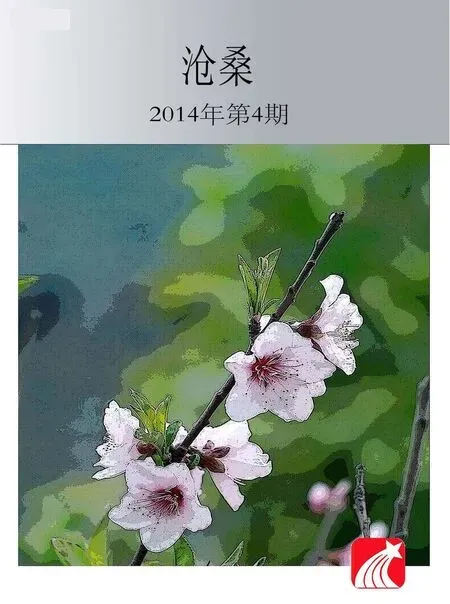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初價(jià)值觀形成分析
——基于蘇共和共產(chǎn)國際的影響
唐靜
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初價(jià)值觀形成分析
——基于蘇共和共產(chǎn)國際的影響
唐靜
政黨價(jià)值觀是政黨本質(zhì)屬性及其功能的基本界定,是包涵著政黨價(jià)值理念、價(jià)值規(guī)范和行為尺度在內(nèi)的價(jià)值體系,它具有時(shí)代性、實(shí)踐性、規(guī)范性和鮮明的政治性特征。中國共產(chǎn)黨價(jià)值觀的形成深受蘇共和共產(chǎn)國際影響,由此形成的價(jià)值取向?qū)h的行為方式產(chǎn)生重大影響。
政黨價(jià)值觀 馬克思主義 蘇共 共產(chǎn)國際
政黨必須有價(jià)值觀,價(jià)值觀是政黨形成和發(fā)展的基石。所謂政黨價(jià)值觀,它是政黨的理論基礎(chǔ)、階級性質(zhì)、政治目標(biāo)、歷史使命以及時(shí)代特征的概括和集中體現(xiàn),是政黨對自身的性質(zhì)、利益、使命和需要的一種認(rèn)知,是對自己的歷史合理性與現(xiàn)實(shí)合法性的一種回答[1]。世界上的政黨,無論是資產(chǎn)階級政黨、無產(chǎn)階級政黨抑或其他類型的政黨,自形成之日起,都毫無例外地堅(jiān)守和維護(hù)著各自的價(jià)值觀。
中國共產(chǎn)黨價(jià)值觀的形成深受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的影響。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情況,一方面,除了俄國同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shí)處境相似,當(dāng)救亡壓倒啟蒙成為中國先進(jìn)知識分子最急迫的需求時(shí),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和共產(chǎn)國際送來了俄式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由于其特殊的示范作用,很快被中國的知識分子接受和效仿;另一方面,還在于俄國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dǎo)下取得無產(chǎn)階級革命勝利的,對于當(dāng)時(shí)追求民族解放和國家獨(dú)立的中國人而言,它無疑具有榜樣的感召力和典型示范意義。毛澤東曾指出:“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jìn)分子,用無產(chǎn)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yùn)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jié)論。”[2]事實(shí)上,中國共產(chǎn)黨人“走俄國人的路”的口號,無疑從理論上宣布了要遵循俄國馬克思主義。如果說中國共產(chǎn)黨對馬克思主義價(jià)值觀的科學(xué)性(目標(biāo)層面)理解,受到的影響來自不同的文化,那么對于如何實(shí)現(xiàn)目標(biāo)的途徑和依靠力量,則深深的,甚至是唯一的受到俄國革命成功的影響,那就是只有堅(jiān)定的以高度集中、嚴(yán)密紀(jì)律的堅(jiān)強(qiáng)的黨組織為領(lǐng)導(dǎo)核心,依靠工農(nóng)這個(gè)基礎(chǔ)最廣泛的社會(huì)階級同盟,代表他們的利益,全心全意為之服務(wù),才能通過暴力革命、階級斗爭打破和粉碎舊的國家機(jī)器和社會(huì)制度,通向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形態(tài)。
然而,“一切均借俄助”也是一種缺陷。它迫使中國早期共產(chǎn)主義者一開始就不能不嚴(yán)格按照俄國人的方式來理解馬克思主義,一度失去了廣泛研究、比較、批判、鑒別,造成最終未能形成自己完整的社會(huì)主義觀的可能性。而由此帶來的結(jié)果是: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伊始,作為共產(chǎn)國際的下級支部之一,中國革命將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獨(dú)立性,其方向、道路、革命方法以及革命動(dòng)力,勢必要由俄國共產(chǎn)黨和共產(chǎn)國際來幫助選擇和提供,由此造成了中國共產(chǎn)黨把某些價(jià)值符號固化為永恒價(jià)值取向,一度背離時(shí)代社會(huì)發(fā)展實(shí)際,對中國社會(huì)發(fā)展造成了負(fù)面影響。
一、馬克思主義革命觀的影響
作為革命家的馬克思,十分重視發(fā)揮階級斗爭的作用,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明確宣布要運(yùn)用暴力手段加速資本主義的滅亡。列寧進(jìn)一步突出強(qiáng)調(diào)了馬克思暴力革命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觀點(diǎn),并相應(yīng)地提出了建立由職業(yè)革命家組織的政黨,實(shí)行集中制原則和秘密工作等一系列組織和加速革命進(jìn)程的方法。
中國馬克思主義啟蒙思想家、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李大釗就是持“階級斗爭”價(jià)值觀的,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李大釗提出馬克思主義三個(gè)組成部分即歷史唯物主義、剩余價(jià)值學(xué)說和階級斗爭學(xué)說。陳獨(dú)秀等人也旗幟鮮明地主張暴力革命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在維金斯基協(xié)助下,陳獨(dú)秀起草了《中國共產(chǎn)黨宣言》,更進(jìn)一步體現(xiàn)了這種來自俄國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深刻影響。這個(gè)宣言首次試圖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參加者和信仰者中樹立統(tǒng)一的共產(chǎn)主義概念,宣言要求中國共產(chǎn)主義者確信:俄羅斯歷史發(fā)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歷史發(fā)展的特征,俄國革命所經(jīng)歷的階級爭斗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也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得要經(jīng)過的[3]。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特別深重,所以,當(dāng)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價(jià)值觀一經(jīng)產(chǎn)生,高舉反帝反封建大旗,就以其鮮明的革命性把中國社會(huì)一切革命力量空前集結(jié)起來,組成最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激勵(lì)廣大人民同仇敵愾,浴血奮戰(zhàn),終于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極大地推動(dòng)了中國社會(huì)歷史的前進(jìn)。可以說,沒有革命便沒有中華民族的獨(dú)立和解放。所以,革命在第一代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價(jià)值觀念體系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在這一體系中,革命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用革命的方式解決問題是中國共產(chǎn)黨最主要也是最常用的方式,毛澤東同志在很大程度上是用階級斗爭的觀點(diǎn)來詮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實(shí)現(xiàn)過渡之后,毛澤東對于階級斗爭的認(rèn)識曾經(jīng)發(fā)生過一些轉(zhuǎn)變。1956年9月22日,毛澤東在會(huì)見意大利共產(chǎn)黨代表團(tuán),論及斯大林所犯的錯(cuò)誤時(shí)說:“蘇聯(lián)在階級消滅以后,當(dāng)國家機(jī)構(gòu)的職能喪失了十分之九時(shí),當(dāng)階級斗爭已經(jīng)沒有或已經(jīng)很少的時(shí)候,仍找對象,大批捉人殺人,繼續(xù)行使它們的職能。”“客觀形勢已經(jīng)發(fā)展了,社會(huì)已從這一個(gè)階段過渡到另一個(gè)階段,這時(shí)階級斗爭已經(jīng)完結(jié),人民已經(jīng)用和平的方法來保護(hù)生產(chǎn)力,而不是通過階級斗爭來解放生產(chǎn)力的時(shí)候,但是在思想上卻沒有認(rèn)識這一點(diǎn),還要繼續(xù)進(jìn)行階級斗爭,這就是錯(cuò)誤的根源。”[4]應(yīng)當(dāng)說,這一段時(shí)期的認(rèn)識是客觀的,但遺憾的是,不久之后,毛澤東的價(jià)值觀又重回“階級斗爭”學(xué)說,且程度日益激烈。至1962年8月的中國共產(chǎn)黨八屆十中全會(huì),“階級斗爭”說已達(dá)到極左,經(jīng)毛澤東修改審定的《八屆十中全會(huì)公報(bào)》指出,在無產(chǎn)階級革命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整個(gè)歷史時(shí)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chǎn)主義的整個(gè)歷史時(shí)期(這個(gè)時(shí)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shí)間)存在著無產(chǎn)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huì)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5]。之后毛澤東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階級斗爭的重要性、根本性。他先后提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以階級斗爭為綱”“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等口號。
應(yīng)該看到,階級斗爭、暴力革命這一價(jià)值觀或以此價(jià)值觀為核心的理論在特定的歷史時(shí)期、特定的民族發(fā)展歷史上具有其先進(jìn)性與合理性,但由于這一價(jià)值觀固有的強(qiáng)制性、至上性、排它性,使它非常容易走上極端,走向自己的反面,釀成災(zāi)難。長期嚴(yán)酷的階級斗爭,使得黨總是更多地從階級角度分析問題,把政治標(biāo)準(zhǔn)作為根本的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解決問題時(shí)也總是強(qiáng)調(diào)政治因素,而問題解決的結(jié)果則統(tǒng)統(tǒng)歸結(jié)到政治意義上去,用政治標(biāo)準(zhǔn)衡量判斷一切是非得失。這一評判標(biāo)準(zhǔn)是黨的價(jià)值觀愈來愈“左”傾的根源所在,斯大林主義及其政治上的大清洗和中國“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及其“文化大革命”實(shí)踐便是明證。
二、馬克思主義群眾觀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群眾觀的核心是人民群眾主體論,確立人民群眾是社會(huì)歷史主體和主人的觀點(diǎn),并進(jìn)而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尊重人民群眾主體地位的基本立場和基本觀點(diǎn)。這從本質(zhì)上決定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基本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認(rèn)識路線,決定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的基本執(zhí)政理念。
俄國十月社會(huì)主義革命勝利以后,列寧在領(lǐng)導(dǎo)國內(nèi)革命和建設(shè)事業(yè)中始終強(qiáng)調(diào)要密切與群眾的聯(lián)系,要認(rèn)真對待群眾的來信、來訪和申訴工作。他認(rèn)為,做好這些工作不僅是保障公民合法權(quán)益,堅(jiān)持和發(fā)揚(yáng)社會(huì)主義民主,同時(shí)也是使蘇維埃組織免受官僚主義毒害和糾正違法犯罪行為的可靠保證。
列寧在強(qiáng)調(diào)尊重群眾的創(chuàng)造性地同時(shí),也反對崇拜群眾運(yùn)動(dòng)的自發(fā)性。他指出:“任何崇拜群眾運(yùn)動(dòng)的自發(fā)性的行為,任何把社會(huì)民主主義政治降低為工聯(lián)主義政治的行為,都是為使工人運(yùn)動(dòng)變?yōu)橘Y產(chǎn)階級民主派的工具準(zhǔn)備基礎(chǔ)。自發(fā)的工人運(yùn)動(dòng)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聯(lián)主義,而工人階級的工聯(lián)主義政治也就是工人階級的資產(chǎn)階級政治。”[6]同時(shí)列寧還指出了正確處理群眾、階級、政黨、領(lǐng)袖的關(guān)系。
在中國長期的革命和建設(shè)實(shí)踐過程中,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關(guān)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的原理,系統(tǒng)地運(yùn)用在黨的全部活動(dòng)中,比較系統(tǒng)地闡述了黨的群眾觀點(diǎn)和群眾路線,提出了向人民群眾學(xué)習(xí)的觀點(diǎn)、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的觀點(diǎn)、干部的權(quán)力是人民賦予的觀點(diǎn)以及對黨負(fù)責(zé)和對人民負(fù)責(zé)相一致的觀點(diǎn)等。同時(shí)還形成了黨在一切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即: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毛澤東作為一個(g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其深沉濃厚的民本意識,包含有科學(xué)社會(huì)主義的豐富內(nèi)涵。具體來說,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gè)方面:
首先,毛澤東正確論述了黨的領(lǐng)導(dǎo)和群眾的關(guān)系,把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diǎn)集中概括為“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是黨的根本宗旨,是群眾路線方法的立足點(diǎn);“一切依靠群眾”,是黨的根本原則,是群眾路線方法的依據(jù);“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黨的群眾路線方法的基本點(diǎn),體現(xiàn)群眾路線方法的基本內(nèi)容。
其次,毛澤東十分強(qiáng)調(diào)人民群眾的作用,始終把人民群眾放在國家主人的位置上。毛澤東根據(jù)人民群眾是推動(dòng)歷史前進(jìn)的真正動(dòng)力這一基本原理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dòng)力”“人民群眾有偉大的創(chuàng)造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等一系列論述,把人民群眾提升到一個(gè)非常高的地位。
再次,毛澤東始終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作為我們黨從事革命活動(dòng)和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的出發(fā)點(diǎn)。毛澤東認(rèn)為,共產(chǎn)黨是無產(chǎn)階級的先進(jìn)部隊(duì),是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要永遠(yuǎn)和最廣大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lián)系,因而,為了爭取群眾,就一定要求我們的廣大黨員、特別是領(lǐng)導(dǎo)干部,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fā),而不是從個(gè)人或者小集團(tuán)的利益出發(fā)”。毛澤東指出:共產(chǎn)黨人的一切言論,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hù)為最高標(biāo)準(zhǔn)。
最后,毛澤東堅(jiān)持向人民負(fù)責(zé)的原則,以此作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得以正確制定和貫徹落實(shí)的有效途徑。毛澤東經(jīng)常強(qiáng)調(diào):我們的責(zé)任,是向人民負(fù)責(zé)。每句話,每個(gè)行動(dòng),每項(xiàng)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cuò)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fù)責(zé)。毛澤東要求黨和政府的各級領(lǐng)導(dǎo),在制定政策和實(shí)施政策的過程中,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擁護(hù)為最高標(biāo)準(zhǔn)。要培養(yǎng)干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對人民負(fù)責(zé)的意識,并把對人民負(fù)責(zé)和對上級領(lǐng)導(dǎo)機(jī)關(guān)負(fù)責(zé)統(tǒng)一起來,明確對群眾負(fù)責(zé)就是對黨和領(lǐng)導(dǎo)機(jī)關(guān)負(fù)責(zé)。而要“向人民負(fù)責(zé)”,就必須深入群眾之中進(jìn)行實(shí)際調(diào)查。這一思想,既體現(xiàn)了我們黨的實(shí)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與群眾路線的統(tǒng)一性,又表現(xiàn)為黨的群眾路線與馬克思主義認(rèn)識論的一致性。
但是任何事情走過了頭,就會(huì)走到相反的一面。革命年代,中共和毛澤東非常重視列寧在《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相關(guān)論述,然而在執(zhí)政條件下,他們并沒有處理好以下關(guān)系:黨的領(lǐng)導(dǎo)和群眾自發(fā)性的關(guān)系;科學(xué)決策、依法治國與群眾運(yùn)動(dòng)之間的關(guān)系;領(lǐng)袖個(gè)人作用和黨的組織原則的關(guān)系。這就導(dǎo)致建國之后一段時(shí)期,毛澤東忽視了依靠黨的領(lǐng)導(dǎo),過分強(qiáng)調(diào)了直接依靠群眾(主要是農(nóng)民)快速過渡到社會(huì)主義,這種帶有極強(qiáng)的民粹傾向的理論和實(shí)踐,給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造成了較大的損失。過分強(qiáng)調(diào)群眾運(yùn)動(dòng)的自發(fā)性和自覺性,忽視依法治國和科學(xué)決策,導(dǎo)致政治運(yùn)動(dòng)常態(tài)化。對無產(chǎn)階級政黨領(lǐng)袖個(gè)人作用看得太重,甚至發(fā)展到個(gè)人崇拜。
三、共產(chǎn)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的影響——塑造社會(huì)主義“新人”
革命的終結(jié)目標(biāo)并不只是建立新社會(huì),而且也要塑造“新人”:一個(gè)在斗爭中錘煉出來的、通過思想改造所升華的、以“無私”為最根本特征的集體人格,并通過塑造“新人”去創(chuàng)造歷史。俄國19世紀(jì)下半期的激進(jìn)知識分子對“新人”概念的產(chǎn)生有很大的影響。車爾尼雪夫斯基1861年的小說《怎么辦?》第一次提出了“新人”這個(gè)概念,并描繪了其基本特征。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新人”對俄國年輕知識分子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高爾基在1907年發(fā)表了長篇小說《母親》,描繪了一個(gè)目不識丁的工人家庭主婦如何轉(zhuǎn)變?yōu)橐粋€(gè)自覺的革命戰(zhàn)士。這本小說成了后來世界“無產(chǎn)階級文學(xué)”和“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濫觴,就是因?yàn)樗岢隽它h的文學(xué)的基本任務(wù):為塑造“新人”服務(wù)。列寧認(rèn)為《母親》的問世十分及時(shí),他不但向黨的干部推薦這本書,而且于同年邀請高爾基參加在英國舉行的俄國社會(huì)民主工黨的代表大會(huì)。
應(yīng)當(dāng)說,蘇聯(lián)在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和塑造“社會(huì)主義新人”中的確獲得很大的成功。早期的“共產(chǎn)主義義務(wù)星期六”,倡導(dǎo)不計(jì)報(bào)酬的忘我勞動(dòng);建設(shè)時(shí)期工業(yè)戰(zhàn)線上的“斯達(dá)漢諾夫運(yùn)動(dòng)”曾激勵(lì)千百萬人為提高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而奮斗;女拖拉機(jī)手安格林娜的事跡,也成為農(nóng)業(yè)社員的榜樣。特別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出版,受到官方的大力倡導(dǎo),保爾·柯察金成為了一代又一代蘇維埃青年的榜樣和偶像,書中的一段話:“人的一生應(yīng)當(dāng)這樣度過:回首往事,他不會(huì)因?yàn)樘摱裙怅幎诤蓿膊粫?huì)因?yàn)檫^去的碌碌無為而羞愧。”成了無數(shù)青年獻(xiàn)身共產(chǎn)主義理想信念的座右銘。在工業(yè)化年代,這些現(xiàn)實(shí)中和文藝作品中的英雄形象,無可否認(rèn)地反映了無產(chǎn)階級政黨倡導(dǎo)的價(jià)值觀和生動(dòng)內(nèi)容。到衛(wèi)國戰(zhàn)爭年代,高昂的愛國主義精神又與一些英雄人物的名字連接在一起,如用胸膛堵碉堡槍口的馬特洛索夫,卓亞的英雄事跡等,同樣發(fā)揮著英雄主義的激勵(lì)和示范作用。
新中國成立初期,蘇聯(lián)這些英雄人物的名字在中國年輕一代,特別是知識青年中耳熟能詳,當(dāng)為楷模。如傷殘軍人吳運(yùn)鐸和他的《把一生獻(xiàn)給黨》就被稱為是中國的“保爾·柯察金”,朝鮮戰(zhàn)場上的黃繼光就是中國的“馬特洛索夫”,保爾·柯察金的那段名言同樣成為新中國進(jìn)步青年的座右銘。中共隨著社會(huì)主義事業(yè)的進(jìn)展,進(jìn)一步發(fā)現(xiàn)和塑造了焦裕祿、雷鋒、王進(jìn)喜等英雄形象,產(chǎn)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們忠于黨、忠于人民、大公無私的犧牲精神有助于新風(fēng)氣、新道德風(fēng)貌的弘揚(yáng)。
當(dāng)然,也不可否認(rèn),這些“蘇維埃新人”在塑造和宣傳中同樣存在嚴(yán)重的缺陷。從“延安整風(fēng)”開始,中國式的“新人”除了共產(chǎn)主義“新人”的普遍特征(如政治忠誠和獻(xiàn)身精神)以外,強(qiáng)調(diào)的是“靈魂深處爆發(fā)革命”,用掏心式的自我解剖和苦行僧般的自我拒絕來達(dá)到徹底否定“小我”(即個(gè)人存在)的目標(biāo)。蘇維埃文化贊美的“新人”通常都沒有個(gè)人的面貌,只有整體的品質(zhì),像鋼鐵一樣堅(jiān)強(qiáng),像機(jī)器一樣整齊而有效率。其最主要的是,人作為個(gè)體的一面(個(gè)人意識、個(gè)人動(dòng)機(jī)、個(gè)人利益、個(gè)人觀點(diǎn)以及個(gè)人行動(dòng)的自發(fā)性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gè)集體的“人”和黨的“人”。雖然每一個(gè)人成為“新人”的途徑可能有所不同,但“新人”本身只有集體性而沒有個(gè)性,因此“新人”的誕生也就是個(gè)性的死亡。
四、國際主義的異化——大國沙文主義的影響
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使用“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的概念,通常只提“國際主義”。列寧提出了“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的概念,倡導(dǎo)“全世界無產(chǎn)者和被壓迫民族聯(lián)合起來!”的著名口號。列寧在不同情況下對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的內(nèi)容,做過一些具體解釋,其中最著名的有兩條:第一條是1917年在《無產(chǎn)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任務(wù)》中講的:真正的國際主義只有一種,就是進(jìn)行忘我的工作來發(fā)展本國的革命運(yùn)動(dòng)和革命斗爭,支持(用宣傳、同情和物質(zhì)來支持)無一例外的所有國家的同樣的斗爭,同樣的路線,而且只支持這種斗爭、這種路線;第二條是1920年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講的: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第一要求一個(gè)國家的無產(chǎn)階級斗爭的利益服從全世界范圍的無產(chǎn)階級斗爭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戰(zhàn)勝資產(chǎn)階級的民族,有能力有決心為推翻國際資本而承擔(dān)最大的民族犧牲。列寧的這些解釋和論述,長期以來在國際共運(yùn)中,特別是通過“大論戰(zhàn)”和“文化大革命”,已人為地“絕對化”和“神圣化”了。似乎這是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不管客觀條件和需要如何,不這樣做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背叛”。其實(shí),這是一種誤解。列寧強(qiáng)調(diào)執(zhí)行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義務(wù)要看客觀條件、需要和可能,否則會(huì)幫助反動(dòng)派,損害革命運(yùn)動(dòng)的整體利益。1918年俄共黨內(nèi)有人主張“為了國際革命的利益,即使本國的社會(huì)主義革命失敗,也要援助國際范圍的社會(huì)主義革命”。列寧認(rèn)為這是奇談怪論,他指出:這些人以為國際革命的利益要求強(qiáng)行推動(dòng)國際革命,如果是這種理論,那是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從來都否認(rèn)強(qiáng)行推動(dòng)革命,因?yàn)楦锩请S著產(chǎn)生革命的階級矛盾的日趨尖銳而發(fā)展起來的。我們作好可能喪失蘇維埃政權(quán)的準(zhǔn)備,顯然也不能幫助德國革命的成熟,反而會(huì)妨礙它。我們這樣做只會(huì)幫助德國反動(dòng)勢力,為他們效勞,給德國社會(huì)主義運(yùn)動(dòng)造成困難[7]。我們對列寧關(guān)于“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的解釋和論述,應(yīng)以全面的、歷史的、發(fā)展的觀點(diǎn)去看待,不能采取簡單化、絕對化、凝固化的觀點(diǎn)對待它。
列寧的國際主義是真誠的,但斯大林將國際主義變?yōu)榇髧澄闹髁x和民族利己主義的口號。斯大林援助過一些國家的革命和建設(shè),但是他把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與捍衛(wèi)蘇聯(lián)等同起來。他說:“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dòng)搖地、無條件地捍衛(wèi)蘇聯(lián),誰就是國際主義者。”許多其他國家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按照他的要求提出“捍衛(wèi)蘇聯(lián)”的口號,結(jié)果嚴(yán)重脫離本國群眾,也損害了這些黨的發(fā)展。斯大林在“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的旗號下推行大國沙文主義,大搞世界革命中心,曾以“共產(chǎn)國際”的名義,后來又以九國“情報(bào)局”的名義公開領(lǐng)導(dǎo)、干預(yù)、指揮甚至控制其他國家共產(chǎn)黨。勃列日涅夫則提出了“有限主權(quán)論”“國際專政論”,把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變成了“霸權(quán)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和“干涉別國內(nèi)政”的代名詞,進(jìn)一步敗壞了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的聲譽(yù),損害了整個(gè)世界無產(chǎn)階級的事業(yè)。
中國共產(chǎn)黨曾一度奉行國際主義精神,以意識形態(tài)作為標(biāo)準(zhǔn),輸出革命,大力支援其他國家社會(huì)主義革命和建設(shè)事業(yè)。抗美援朝、援越抗美、援助阿爾巴尼亞、支援亞非拉國家共產(chǎn)黨的活動(dòng)等,都無不體現(xiàn)了這種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精神。20世紀(jì)60年代初期,毛澤東大力批評“三多一少”政策是放棄中國的國際主義責(zé)任;1975年,針對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向毛澤東提出的不要和他們國家的共產(chǎn)黨來往時(shí),毛澤東回答道:不行呢,因?yàn)槲覀円彩枪伯a(chǎn)黨。哪有共產(chǎn)黨不支持共產(chǎn)黨革命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奉行獨(dú)立自主的外交原則,逐步放棄了輸出革命的理念,大力改善了我們的外部環(huán)境。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過決議指出,革命決不能輸出,它只能是各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結(jié)果;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過決議,刪除原先黨章中“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的提法。
綜上,對于中國來說,政黨是一個(gè)舶來品。從把這個(gè)舶來品移植到我國的最初嘗試到現(xiàn)在,我國的政黨政治已有一百年的歷史。翻開這段歷史,可以肯定地說,沒有哪一個(gè)政黨像蘇共那樣,對我國政黨政治的發(fā)展有如此巨大的影響。歷史造成了中共與蘇共之間的特殊聯(lián)系,也就造成了蘇共的理論與實(shí)踐對于中共的特殊影響,造成了研究這種失敗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的特殊意義。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們黨理應(yīng)從蘇共的教訓(xùn)中得到更大的收獲。
[1]袁貴仁,韓震.新世紀(jì)中國共產(chǎn)黨的價(jià)值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
[2]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1408.
[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548—550.
[4]毛澤東.同意大利共產(chǎn)黨代表團(tuán)談話記錄[M].人民日報(bào),1956-9-22.
[5]建國以來重要文獻(xiàn)選編(第十五冊)[M].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1997.653.
[6]列寧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08.
[7]列寧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02.
唐 靜 華東師范大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部講師 法學(xué)博士
(責(zé)編 高生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