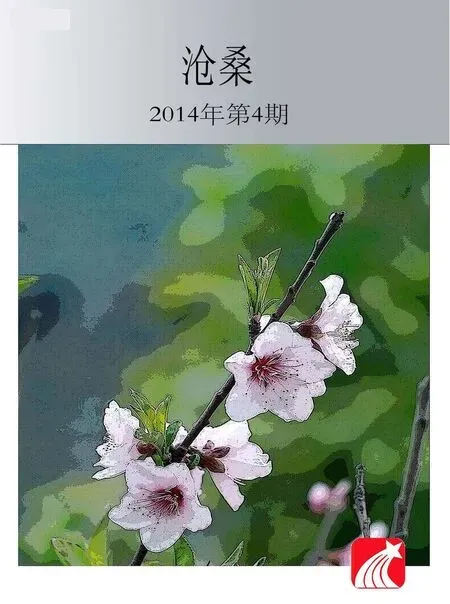抗日戰爭相持階段五戰區作戰研究
柳鵬
抗日戰爭相持階段五戰區作戰研究
柳鵬
武漢會戰后,中國抗日戰場轉入到了相持階段,期間國民黨第五戰區先后與日軍進行了隨棗會戰、第五戰區冬季攻勢、棗宜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五戰區牽制作戰、豫湘桂戰役豫中會戰、湘西會戰老河口作戰等一系列戰役,在抵抗日寇侵略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對日作戰期間,第五戰區也執行了積極反共的錯誤政策,給抗戰帶來了損害。
國民黨 五戰區 抗戰
一、五戰區的起始
1937年8月20日頒布的大本營訓令,令字第一號《大本營頒國軍戰爭指導方案訓令》[1]指導了第一、二、三、四、五戰區的作戰任務,規定第五戰區任務為“對敵強行登陸之作戰,故以立于主動地位,確占先制之利,根本打破敵軍登陸之企圖。此為作戰指導上第一要義”。戰區境地包括蘇北及魯省,戰區司令長官蔣介石兼。而在同一天頒布的大本營訓令,令字第二號《大本營頒國軍作戰指導計劃訓令稿》[2]中,對其他四個戰區的任務進行了指導,卻沒有涉及第五戰區的作戰任務。從中可以看出,在淞滬會戰期間,大本營的主要注意力仍舊放在云集重兵上海地區(三戰區),作為戰爭爆發點的華北地區(一、二戰區)及作為維系中國抗戰與外界聯系的廣東、福建地區(四戰區)。而作為淞滬戰場的側翼,阻止日軍迂回包抄淞滬地區的中國軍隊第五戰區變成了次重點。五戰區戰區司令長官一職也由大元帥蔣介石兼任,而沒有專門設置將領來擔任,沒有設立全權戰區指揮機構長官部。直至8月28日淞滬戰場越發嚴峻之時,才由桂系李宗仁將軍擔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3],駐節徐州,指揮保衛津浦路的防御戰。直轄地區計有:山東全省和長江以北江蘇、安徽兩省的大部。而最高統帥部為集中力量起見,特規定長官部的職權,戰區司令長官系直接秉承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命,并受所在地委員長行營或綏靖公署的指導,綜理轄區內的一切軍事事宜。
二、隨棗會戰
武漢會戰后,中國抗戰進入到了艱苦的相持階段。經過三年的戰斗,中國野戰軍對武漢形成層層包圍之勢,日軍決意打破中國軍隊的包圍,向五戰區中國軍隊發起進攻。武漢長江上游沙市以西一段長江江防、鄂北、豫南、皖東大別山區均被劃規第五戰區。五戰區此時已是地處國民政府中樞門戶的川東要沖,是日軍溯江西進,威逼重慶的重要戰略地域。1939年4月,日軍華中派遣軍集結第三、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師團和第四騎兵旅團約十萬人,挾輕重炮二百余門,向第五戰區進犯。
此時五戰區內中國軍隊:陸軍41個師,2個獨立旅,騎兵1個師,1個旅,游擊隊6個縱隊,獨立炮兵2個團。總兵力約20萬人。其中僅國民黨江防軍及第三十一集團軍之4個師較完整,其余25師均尚未整補,其人員裝備多不足二分之一,完整度遠不如武漢會戰[4]。
1939年4月五戰區偵查得知約2個師團日軍向鄂北集中,有向襄、宜進犯的癥候,乃向最高統帥部請求一、三、九等戰區積極配合,并增派第二集團軍南下增援。一俟增援部隊到達后五戰區即下達作戰命令:“不下三師團之敵,將以主力由浙河及其以北地區西向,有力之一部由鐘祥附近北向,夾擊我在襄河東岸之主力兵團。戰區決以主力行攻勢防御,粉碎敵之企圖,長久保持襄河東岸地區,一部渡河攻擊,竭力牽制敵之兵力,俾我主力之作戰容易。”[5]
會戰經歷了漢宜公路戰斗,襄河東岸至大洪山間地區之作戰,隨縣棗陽間地區之作戰,大洪山附近之作戰,豫鄂邊區之作戰,豫鄂皖邊區之作戰。會戰進行到關鍵時刻,五戰區長官部一度與各集團軍失去聯絡,幾完全中斷,戰局陷于被動,但五戰區最終抵住日軍攻勢。日軍戰前企圖圍殲中國主力野戰軍計劃沒有達成。且會戰后期五戰區以第二、第三十一、三十三集團軍為主力向日軍發動追擊、側擊等反攻作戰[6],給日軍有生力量以大量消耗。會戰以中國軍隊收復除隨縣外的各處失地,大體上恢復戰前雙方的態勢而結束。
中日雙方圍繞漢宜公路,襄河東岸至大洪山間地區,隨縣棗陽間地區,大洪山附近,鄂豫邊區,鄂豫皖邊區展開戰斗。這些作戰從戰斗的規模、持續的時間上都很難稱之為戰役,盡管中國守軍多在這些戰斗中頑強進行了抵抗,但是最終多以中國軍隊轉移陣地,實行逐次抵抗而告終。而且日軍參戰第三、十三、十六等師團,十三師團屬于二等乙類師團,三、十六師團雖作為一等甲類常備師團,但其后來的補充兵員素質和抗戰初期的日軍兵員素質也是有差距的。而常備師團的聯隊基層官兵也多被抽調,組建新的師團,這樣的兵員素質和徐州會戰時號稱王牌的第五、第十師團等常設師團,是有差距的。從殺傷日軍的質量來看,隨棗會戰與之前的徐州會戰、武漢會戰中大量的殺傷日軍、重創或是殲滅日軍是無法相比的,而且從戰斗規模、雙方持續作戰的時間、整場戰役或是會戰的意義等諸多方面,棗宜會戰也是很難達到之前在徐州、武漢會戰的高度。隨棗會戰斃傷日軍1.3萬余人,日軍遺尸5000余具。而徐州會戰時,即殲滅了日軍1萬多人,斃傷2.6萬余人。從隨棗會戰的戰斗時間來說,前后不及三周。但是站在歷史宏觀的大背景下,隨棗會戰殲滅斃傷大量日軍,對中國抗戰所做出的貢獻還是不可磨滅的。
三、第五戰區冬季攻勢
國民政府在南岳召開第二次軍事會議認為“我國的抗戰局勢,已臨到勝利的一個大轉機,國際外交形勢,亦隨之一天一天好轉”“足以助成我抗戰的勝利”。接著提出今后的抗戰戰略,指出:“此次湘北之戰(指剛結束的第一次長沙會戰),戰略上起初本非采取攻勢,而僅為防御的戰略,后來乘勢轉進,竟獲得此決定的勝利,可知敵力已疲,我們進攻的時機已到。”[7]“為使敵人徹底失敗,仍須給予以致命打擊,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為此,特抽調第一線部隊,實行整補訓練,試以春季攻勢,再試以夏季攻勢,再試以秋季攻勢,乃策定次冬季攻勢大舉的攻擊計劃,對敵全面發動全面攻勢,以破壞敵人的戰力,而予以致命的打擊”[8]。
此時中國第一線部隊的第二期整訓已大體完成。1939年11月19日蔣介石下達冬季攻勢命令:“(一)國軍以消耗敵人導國軍爾后作戰有利之目的,以本會直轄部隊主力,加入第二、第三、第五、第九各戰區,實行主攻;(二)為牽制敵之兵力,俾主攻方面奏功容易,其余第一第四第八及魯蘇,冀察各戰區,向當面敵人實施助攻,策應主攻方面之作戰;(三)攻勢開始日期,除第五、第九戰區限于十一月寢日以前實施,其余助攻方面概限于十一月底,主攻方面概限于十二月上旬,如期分別實施。”[9]可以看出即使是擔任主攻,五戰區和九戰區在冬季攻勢中的作用也是要優于其他戰區。而第五戰區具體戰斗指導,“掃蕩平漢線南段信陽、武漢間之敵,進取漢口,并向漢宜路之敵攻擊,截斷敵襄花、漢宜兩路之交通”[10]。
這次冬季攻勢的規模及其戰斗意志遠遠超過日軍的預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戰區的反攻極為激烈”[11],“而在12月12日四周敵人一齊向軍所有正面出擊而來,其規模之大未曾有過的,我第一線部隊幾乎都成了一個個孤立的小部隊,在敵重兵包圍中孤軍作戰,缺糧少彈,傷亡很大,官兵忍耐著困苦盡力防守作戰。敵人的進攻意志極為頑強,其戰斗力量不可輕視。在戰術上,鼓勵采取夜戰,隱蔽中接近和包圍我軍據點,善于利用工事和以手榴彈進行近戰。武器彈藥充足,補給能力也很強”[12]。第五戰區當日第十一軍“傷亡合計也約達八千,付出的犧牲是過去作戰不曾有過的”[13]。
此次冬季攻勢最大遺憾是未能攻克具有極重戰略價值的要地,國民黨戰役后統計工作不詳殊為一大遺憾。“第五戰區襄河東岸之戰,各軍或進或退,勝敗之數前后異詞,其所得戰果雖較比其他各戰區為優勝,但亦難于詳查當時敵我兵力與態勢以及戰后我方死傷與俘虜之確數,然此次該戰區發動權利而未能克復鐘祥與信陽之任何一據點,實未達到其任務”[14]。
四、棗宜會戰
隨棗會戰后,第五戰區在當時轄地最廣。即魯南、蘇北名義上亦屬第五戰區戰斗序列[15],是當時最大的戰區。作戰區域包括中國長江以北,黃泛區(鄭州花園口決堤,黃河河水泛濫河南、安徽、江蘇三省四十四縣五萬四千平方公里區域)以南,津浦鐵路以西的豫鄂皖三省廣大地區。所轄部隊,當時計有七個集團軍,另十個軍,合計六十九個師的兵力。五戰區戰斗任務:首先確保宜昌、沙市地區,屏護中樞門戶;其次則為保持鄂北地區,鞏固中樞外翼,并相機反攻武漢[16]。
前期作戰方針:戰區以一部取廣正面,分路挺進敵后方,積極施行襲擾,主力適宜控置于后方,相機以先發制敵行動。于棗陽以東或荊,當以南地區與敵決戰[17]。
戰區初期兵團部署:江防軍,司令郭懺,轄第二十六軍,第七十五軍,第二軍,第八軍,第十八軍,第三十二軍,第一補訓處,第一二八師及宜萬區要塞指揮部,渝萬區要塞指揮部。江防軍以一部擔任潛江、高石牌間漢水西岸陣地之守備,主力控制當陽、宜昌及江防地區。右兵團,兵團長張自忠,轄第三十三集團軍之第五十九軍,第七十七軍,第五十五軍,第二十九集團軍之第四十四軍,第六十七軍,警備四個旅。右兵團擔任高石牌、宜城間漢水西岸及大洪山陣地之守備。中央兵團,兵團長黃琪翔,轄第十一集團軍之第八十四軍,第三十九軍,第二十二集團軍之第四十一軍,第四十五軍。中央兵團擔任大洪山東北翼經隨縣城西側之桐柏山東南麓間陣地之守備。左兵團,兵團長孫連仲,轄第二集團軍之第三十軍,第六十八軍,豫鄂邊區挺進軍。左兵團擔任桐柏山東南至信陽外圍陣地之守備。大別山游擊兵團,兵團長李品仙,轄第二十一集團軍之第七軍,第四十八軍豫鄂皖邊區挺進軍及地方部隊。大別山游擊兵團擔任鄂東及皖中敵后之作戰。
棗陽失陷后,國民政府調整軍事部署:一、第五戰區應以確保宜昌、襄樊之目的,以襄河兩岸部隊,從西北向東南對渡犯襄河之敵側背攻擊,壓迫于襄河及湖沼地帶而殲滅之。二、第五戰區分為左右兩個兵團,左兵團轄孫連仲、孫震、湯恩伯、劉汝明各部,兵團長由李長官兼任;右兵團轄馮治安、王攢緒及江防軍各部,兵團長派陳誠兼任[18]。
會戰戰報:敵交戰兵力約三十五萬人,遺棄尸體約六萬三千一百二十七具,被俘為四千七百九十七人。繳獲武器:野炮十一門,山炮十二門,機關炮二門,迫擊炮五十三門,高射機關槍三挺,重機槍一百二十四挺,輕機槍四百十七挺,步槍九千六百八十四支,各種槍炮子彈約為一千二百萬發。日軍損失:戰死一千四百零三人(內將校一百零六名),負傷四千六百三十九人(內將校二百零三人)[19]。
盡管中國統帥部在棗宜會戰中期修正了自己的作戰計劃,調整了軍事部署,但是還是未能挽回失敗境地。宜昌失守不啻為對五戰區一個重大的打擊。中國軍隊失去了戰略重鎮宜昌,使日軍可以以此為跳板窺探重慶。五戰區中樞重慶最重要的外圍屏障的作用,亦被后來設立的第六戰區所取代,六戰區轄境包括鄂西、鄂中、鄂南、湘北及湘西、川東、黔東等地。而且蔣介石在重大場合中,當眾提出“軍事第一,第六戰區第一”[20]的口號。可以看出,在當時整個抗日戰場形勢下,六戰區責任使命的重要性。五戰區的重要性相對有所降低。而且棗宜會戰給了“當初戰斗意志旺盛的第五戰區部隊,在精神上、物質上極大的打擊。在重慶很快傳出‘日軍逼近重慶’的風聲,日中戰爭八年中,蔣介石總統最感到危機的時刻,就是宜昌作戰的時候”[21]。
五、第二次長沙會戰——五戰區配合作戰
棗宜會戰之后,五戰區的作用被進一步的弱化,而在“軍事第一,第六戰區第一”的口號下,六戰區的作用進一步的突出,其地理位置身處要津,所處地位關系甚大。在此后的作戰計劃、電令中,一再要求各戰區(包括第五戰區)配合第六戰區做好反攻作戰的準備。后期抗日戰場上五戰區大規模的作戰在減少,僅有第二次長沙會戰五戰區配合作戰,豫湘桂戰役豫中會戰,湘西會戰老河口作戰等。
這些作戰活動,五戰區都是處于一種配合作戰的境地,而不是單獨一個戰區完成作戰任務。五戰區作戰不再是支撐整場會戰的高度,而是下降到會戰中某次戰役的層面。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第五戰區發動配合作戰,進攻湘北之日軍,強渡汨羅江,威脅長沙。第五戰區于1941年9月21日奉軍事委員會電令:“第五戰區應向長江沿岸,平漢鐵路,襄花,京鍾,漢宜各公路當面敵人發動全面游擊。相機攻擊據點,并應以重點指向漢宜公路,截斷荊宜敵人后方,阻敵轉移兵力至第六戰區。”[22]9月25日,第五戰區奉軍事委員會電令要旨:“該戰區應以協力第六戰區相機收復宜昌之目的,各集團軍除照所下命令使用兵力外,應全線發動攻擊,并切實切斷襄河以西敵人后方,以利第六戰區之作戰。為使沙宜攻勢作戰容易,河西集團軍(第三十三集團軍)歸第六戰區指揮。”[23]
第二次長沙會戰中,五戰區不但要配合九戰區長沙會戰,還要阻止當面日軍向第六戰區移兵增援,在戰役中要與第六戰區協力收復宜昌,一部分的部隊還要歸屬六戰區指揮。抗戰初期五戰區在會戰中起到突出性的決定作用,但在抗戰進行到了相持階段之后,一場會戰的進行多是幾個戰區共同的協調配合,而五戰區這時多充當重要的參與配合者角色。
六、余論
國民黨第五戰區抗戰中有英勇抗敵的事跡,但是第五戰區也有積極反共歷史。皖南事變發生后,全國各地均掀起了反共新高潮,國民黨第五戰區當局即開始部署進攻鄂豫邊區。1941年1月,由國民黨新二軍3個師共同糾結獨立第十四、十五旅,由桐柏山配合第二十二集團軍,進犯白兆山根據地。1943年5月,蔣介石親自下令以國民黨第五戰區部隊為主力,與鄂豫皖三省地方頑軍“協同進剿”新四軍第五師,并限令于6月底以前“清剿”完成。5月下旬第五戰區向新四軍發起進攻,新四軍被迫自衛反擊,驅逐蔣頑軍,取得了浠白水石山戰斗的勝利。6月國民黨第五戰區不甘失敗,糾結第三十九軍大部和一個保安團、兩個游擊縱隊,并勾結偽軍第十一師,再次侵犯新四軍根據地。同年7月至8月底,國民黨第五戰區連續向新四軍發起“進剿”侵入黃岡、岡麻等地,瘋狂屠殺迫害根據地軍民,中國共產黨在堅持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上,做了最大讓步,但不放棄自衛反擊的權利,多次粉碎頑敵的進攻,保衛了根據地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最終迫使國民黨頑固派停止了新的反共高潮。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將各戰區陸續撤消,改編為綏靖區、綏靖公署軍政長官公署等,第五戰區也一同退出了歷史的舞臺。盡管在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國民黨內部頑固勢力抬頭,抗戰日趨消極,反共摩擦日漸積極,但第五戰區抗戰中在政治軍事上仍然發揮了巨大作用,在隨棗會戰、冬季攻勢、棗宜會戰中消耗了大量日軍,發揮了舉足輕重的歷史作用,對于國民黨第五戰區抗戰中所具有的歷史地位,還是應該予以肯定。
[1][2][17]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M].鳳凰出版社,2005.34,39,988.
[3]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記[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719.
[4][22][23]蔣緯國.國民革命戰史抗日御辱(第三部第七卷)[M].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92,156,163.
[5][9][1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M].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190, 667,300.
[6]郭汝瑰,黃玉章.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M].江蘇人民出版,2002.924.
[7]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作戰時期.第二編作戰(一)[M].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 1981.193.
[8][10]張其昀.抗日戰史[M].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1966.127,127.
[11][12][13]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華民國資料叢稿譯稿——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 (第三卷第一冊)[M].中華書局,1983.80,86,94.
[1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機密作戰日記[M].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100.
[15]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M].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0.546.
[16]薛岳等.武漢會戰[M].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 324.
[19][21]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三卷第二分冊[M].中華書局,1983.28,28.
[20]陳誠.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拱衛陪都第一節第六戰區第一,東方出版社.
柳 鵬 遼寧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碩士研究生
(責編 高生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