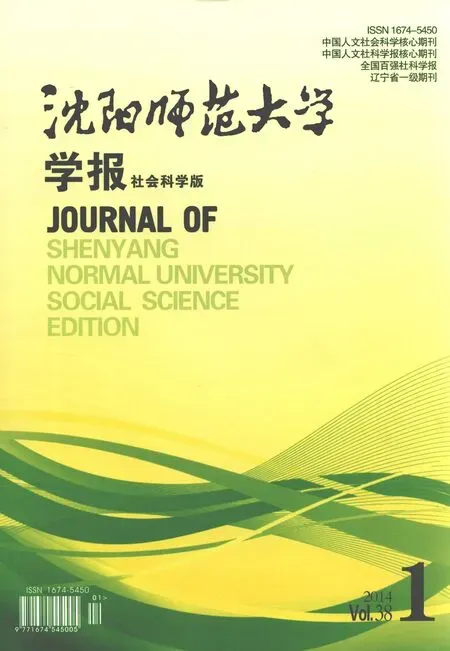論庫切對《魯濱遜漂流記》的改寫
韓亞君
(沈陽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論庫切對《魯濱遜漂流記》的改寫
韓亞君
(沈陽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庫切的《福》是對英國18世紀經典小說《魯濱遜漂流記》的大膽改寫。庫切主要從敘述聲音、主奴關系、作者權威等方面對《魯濱遜漂流記》進行了大膽改寫,顛覆了主流文化范式,表現了庫切對弱勢群體話語權力的關注及對中心權威的對抗。其改寫具有重大的顛覆價值。
庫切;《福》;《魯濱遜漂流記》;改寫
庫切(J.M.Coetzee,1940-)是當代世界文壇上一位著名的南非白人作家,2003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庫切出生于南非,并深受周圍環境的影響,他的大部分作品的主題涉及犯罪、種族分裂、性暴力和殖民主義,充滿了矛盾沖突和斗爭。諾貝爾授獎詞這樣評價他的作品:“以結構精致、對話雋永、思辨深邃為特色……沒有兩部作品采用相同的創作手法。”[1]獨特的寫作特色和變化多樣的創作風格還為庫切贏得了除諾貝爾獎之外的其他很多重要國際獎項,如CAN獎、愛爾蘭時報國際獎、法國費米那獎、耶路撒冷獎和英國布克獎等。他是唯一一位兩次獲得當代語小說的最高榮譽獎布克獎的作家。如此多的獎項足可以說明庫切在當今世界文壇的重要地位。
庫切的作品通常關注邊緣人群,正如高文惠所言:“他的作品主要是對源自身份的危機意識、從邊緣對中心的顛覆、對文化權威的挑戰、對種種形式的暴力的反復描寫……”[2]《福》(Foe,1986)是庫切的第五部小說,無論是在思想內容還是在寫作形式上都是對傳統文學的批判,是對18世紀英國經典小說《魯濱遜漂流記》(The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的改寫。庫切以游離于歐洲和非洲文化之間的獨特混雜的文化經驗,在《福》中采用后殖民視角改寫經典文本《魯濱遜漂流記》,反映與批判性別、種族、階級上的權力問題,對抗中心權威,顛覆主流文化。本文將從敘述聲音、主奴關系、作者權威三個層面解析《福》對歐洲經典文本《魯濱遜漂流記》改寫背后隱含的對殖民文化霸權的顛覆和抵抗。
一、敘述聲音的改寫:蘇珊與克魯索
《魯濱遜漂流記》通篇采用的是白人男性主人公克魯索以第一人稱講述歷險經歷的敘述模式。“在殖民文學中,男性是帝國形象和價值的體現,是文學中的核心人物,而女性則因性別因素而被置于邊緣的位置……有時甚至消失在文本之外。”[3]克魯索是一個萬能的敘述者,是一個積極面對生活,敢于挑戰各種生存困境,幾乎無所不能的英雄。但在他的敘述視角下女性則位卑低賤,在小說中我們幾乎找不到任何有地位的女性。她們基本是無關緊要的陪襯人物。女性是異己的他者,對于克魯索而言女人就像物品一樣或者說只是繁衍后代的工具,“我載了一些日用品、牲畜和七個婦女過去,這樣我的臣民們就可以繁衍后代了”[4]。《魯濱遜漂流記》中對女性人物的處理方式以及克魯索對女人的態度,揭示了男性殖民者在父權制庇護下的話語霸權。
庫切在小說《福》中則采用女性蘇珊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小說圍繞她的所見、所聞和所感展開敘述。在第一章,蘇珊講述了她漂流孤島的經歷。為了尋找被拐賣的女兒,她離開英國前往巴西。但在途中遭遇船難,她就漂流到克魯索和星期五生活的荒島上,與克魯索主仆二人共同生活了一年多。就像《魯》中把女性當弱者來看的克魯索一樣,他對蘇珊說“不要隨便離開他的城堡,因為島上的猿猴可不會像怕他和星期五那樣怕一個女人”[5]15。而蘇珊心想:“難道對于猿猴來說,女人是和男人不同的生物?”[5]15這種女性挑戰男性主宰的聲音在文本中幾乎到處可見。后來他們被一艘船只救起,在船上她對船長講述了她的經歷,船長還鼓勵她“應該將故事寫下來交給出版商”[6]35。蘇珊接受了船長的建議,但是由于她認為自己缺乏寫作技巧,便求助于男性作家福幫他書寫荒島故事。
從《福》整個文本來看,“庫切通過女性乘船遇難者—蘇珊所建構的女權主義的話語實際上與性的關聯很少,蘇珊的女性身份更多顯的是邊緣反對中心、無權威性的言說反對權威性的言說的相對文化力量”[7]238。所以,庫切更多的是利用蘇珊的邊緣位置來發言。《魯濱遜漂流記》是男權體制下的殖民者魯濱遜的自我敘述,是來自權力中心的自我表述,這種敘事策略掩蓋了權力關系中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和主體性,如女性和土著這些他者的存在。《福》要做的就是對這種遮蓋進行揭示,讓被迫沉默的次等公民發出聲音。“男權社會的權力話語淹沒了女性的歷史,要想獲得男女兩性的平等對話,就要恢復女性的主體性。”[7]133庫切讓被壓抑在歷史權威之下的邊緣女性說話,改變《魯濱遜漂流記》中沒有女人的局面。用女性敘事作為打破帝國文學經典中白人男性主導話語權的策略。《福》通過采用蘇珊的女性敘述聲音,揭示了中心對邊緣的壓抑和控制。就像高文惠在《后殖民文化語境中的庫切》中所說,庫切“站在女性他者的位置言說,就是通過不可見的變成可見來實現社會的公正,實際上發揮著從邊緣拆解中心的顛覆功能”[7]128。
二、主奴關系的改寫:星期五和克魯索
《魯濱遜漂流記》中克魯索和星期五之間是主奴二元對立的權力關系。首先,在《魯濱遜漂流記》出版后的將近三百年中,世人認定克魯索是一個精明能干、敢于冒險、按照現代文明的模式塑造的英雄形象。而星期五沒有自己的名字,他作為身份代碼的名字是克魯索以救他的日期所定的,他說的是克魯索教給他的語言。因此他對主人惟命是從,忠心耿耿,接受主人對他所有的安排。這種關系表征的是西方以理性文明所標識的歐洲中心主義思想和種族優越感。其次,從殖民角度來看,克魯索和星期五的這種主奴關系體現的就是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二元對立關系。克魯索是殖民者的代表,代表著歐洲的自我,是文明、理性和權力的象征。相反,星期五則是被征服的種族的代表,是邊緣的他者,也是野蠻、沉默和黑暗的象征。在這種二元對立的關系中,西方殖民者自然而然地成為主宰者,而后者則成為被馴服的對象。關鍵的是,星期五是一個愿意接受克魯索對他進行文化改造的他者形象,就是殖民者進行殖民統治的理想模式。
在《福》中克魯索和星期五的主奴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顛覆了《魯濱遜漂流記》中笛福對歐洲和非洲形象的建構。首先,在庫切的筆下,以往的資產階級英雄不復存在,《福》中的克魯索是一個頹廢、衰弱、缺乏自信、安于現狀、沒有動力、記憶力衰退的老人,“他給我講的關于他的故事有好幾個版本,各個版本之間如此不一致,以至于我越來越覺得年紀和獨居已經抽走了他一部分的記憶力:他已經不知道什么是真相,什么是想象”[5]11。如果說笛福的克魯索是無所畏懼、不斷進取的英雄,那么《福》中的克魯索視野狹隘,個性固執,連離開孤島的欲望都沒有。當蘇珊說她的欲望就是獲救時,克魯索說“我對于你內心的欲望一點興趣都沒有”[6]31。他沒有信仰,更沒有殖民者的開拓精神,他唯一的追求就是為活著而勞作,所以和星期五日復一日地壘梯田。用他的話說:“在我們的這個島上,我們要勞動才有吃的,除了這個戒律,沒有任何其他法律。”[5]36其次,在笛福作品中那個忠實順從的仆人星期五,在庫切的改寫文本中則發生了更大的變化。在笛福作品中,星期五是一名加勒比有色人種,而在《福》中,他則變成了一名黑人。星期五的膚色改寫更適合于南非的社會現實,讓人們想起歐洲對非洲的殖民史。除了改寫星期五的膚色外,更重要的是,《福》中的星期五是沉默的,因為他是一個被割掉舌頭的、失去話語權的仆人。這樣《福》中克魯索就不能像《魯濱遜漂流記》中那樣讓星期五叫他主人,利用語言對星期五進行殖民思想灌輸。他的沉默是殖民霸權下受壓迫種族的代表,是防止異族文化壓制的一種反抗方式,是對殖民者無聲的抵抗和譴責。而且星期五身上存在諸多之謎:吹六音符、畫眼睛和腳之謎、寫無數個字母“O”之謎、向海中拋撒花瓣之謎等。星期五通過這些別人不懂的音樂、舞蹈和文字,回歸到自己民族的文化與精神世界之中。這些謎體現的就是非洲文化,庫切再現了《魯濱遜漂流記》中被淹沒的非洲文化。
另外,《福》消解了《魯濱孫漂流記》中以克魯索為代表的中產階級男性白人殖民者的話語權力。克魯索所占比例的減少說明他的話語權力的減弱。在《魯濱孫漂流記》中,克魯索貫穿整部小說的首末;而在《福》中第一部分,克魯索就死在了返回英國的船上。死亡則深刻暗示了白人帝國主義殖民者統治權威的喪失。而且作為西方“他者”象征的星期五并沒有被描寫成像《魯濱孫漂流記》中具有殖民特點的“自我”與“他者”二元對立的性格,而是通過星期五身上的諸多之謎暗示“他者”的存在。庫切以他的死作為轉折點,宣告了由克魯索所構建的殖民帝國的結束。小說《福》改寫了克魯索和星期五這兩個主要人物以及他們二人之間的主奴關系,主要是揭示原笛福殖民文學所構建的殖民體系的不合理性。通過對作品中主要人物白人殖民者代表克魯索和黑人被殖民者代表星期五的形象和性格的改寫以及主奴二元對立關系的分化,消解了中產階級男性白人殖民者的話語權力,顛覆了以白人為代表的帝國主義殖民霸權。
三、作者權威的改寫:福還是笛福
《魯濱孫漂流記》是笛福在殖民主義思想主導下創作的作品,敘事昭示著大英帝國的海外擴張和掠奪的殖民意識。雖然是克魯索一直在說話,但他是笛福的代言人。笛福與克魯索之間是認同關系。《魯濱遜漂流記》被譽為英國第一部現實主義小說,笛福被稱作現實主義小說之父,在他的許多小說的序言之中他都反復強調他小說故事的真實性,比如在《魯濱孫歷險記》的序言中,他說:“編者相信,這一自述是事實的忠實記載,其中絕無虛構之處。”[8]
而《福》中作者的權威不斷地被消解。雖然故事的講述者是蘇珊,但作者是福,而且福為人物出現在小說內部。蘇珊與福之間是依賴與對立的動態關系。在《福》中,多次挑戰福的作者權威。蘇珊是魯濱遜及星期五荒島生活的體驗者,她就讓男性作家福幫她寫她親身經歷的真實的荒島事件。而福則任意篡改蘇珊講述的內容,選擇將克魯索作為故事的敘述主體,塑造了一個成功的資本主義英雄,但將小人物蘇珊完全隱去。他還想加入一些事實上并不存在的海盜和食人族的情節來吸引讀者。故事的真實性成為騙局,正如福說:“只要我們提醒自己那是個真實的故事,就不會覺得故事乏味了。”[5]127不僅如此,福還虛構了女兒尋母的故事。對此,蘇珊對那個女孩說:“你是父親所生,你沒有母親。”[6]81意味著女孩是出自作者權威的想象,不是真實的事實,是不顧真實而隨意虛構的蘇珊的人生故事。在《福》中,蘇珊為獲得自己的主體性權利堅持不懈地和作家福周旋,與他爭辯,并堅信自己是故事作者的身份,以此消解以福為代表的作者權威。在段楓和盧麗安的文章《一個解構性的鑲嵌混成:<仇敵>與笛福小說》中寫道:“當《福》進入第三部分的時候,作家福也由被第二人稱指代的你變成了第三人稱指代的他。”[9]這一變化似乎說明弱勢群體向權力中心討回發言權,蘇珊將不再依附福作為小說家的權威,開始自己面對讀者。
我們不難發現作者福的思想和笛福的思想完全一樣,福要寫的荒島故事就是我們讀到的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是蘇珊提供了“笛福寫故事所需的原始素材”。[10]所以這兩個荒島故事的作者都是笛福一人,福就是笛福。“根據史料記載,笛福本姓Foe,為表示自己有貴族頭銜,在自己的姓前加了一個貴族頭銜:De改姓為Defoe。”“這個名字本身就是庫切對作者的解構,對歷史的一個反諷。”[7]148福是小說中的作者,庫切在小說中解構了福的作者權力,某種程度上解構了笛福的作者權威。庫切將原作者笛福轉化為小說《福》中的一個與蘇珊相抗衡的角色,意在通過邊緣女性對言說權力的不斷抗爭來顛覆作者權威所建構的現實。這樣蘇珊與福的對立就具有顛覆以笛福為代表的作者權威的意義。
結語
綜上所述,《福》從后殖民視角對《魯濱遜漂流記》的改寫具有重大的顛覆價值,表達了對一直掙扎在壓迫之下的女性與黑人等弱勢群體的同情,顛覆了歐洲經典文本背后的殖民文化霸權意識。小說開放式的結尾也在暗示一個文本有不同的解決方式,“有關這個文本的重讀重寫還遠遠沒有結束,自由的閱讀應該處于開放的狀態”[11],這也是顛覆的真正目的。
[1]庫切.青春[M].王家湘,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191.
[2]高文惠.后殖民文化語境中的庫切[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5.
[3]張勇.殖民文學經典與經典改寫[J].國外文學,2011(1):152-158.
[4]Defoe,Daniel.The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8:391.
[5]Coetzee,J.M.Foe[M].London:Penguin,1986.
[6]庫切.福[M].王敬慧,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7.
[7]高文惠.后殖民文化語境中的庫切[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8]丹尼爾·笛福.魯濱遜歷險記[M].黃杲忻,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
[9]段楓,盧麗安.一個解構性的鑲嵌混成:《仇敵》與笛福小說[J].當代外國文學,2004(4):48-54.
[10]Kossew,Sue.Pen and Power:A Post-colonial Reading of J.M.Coetzeeand Andre Brink[M].Amsterdam:Rodopi,1996:163.
[11]任海燕.探索殖民語境中再現與權力的關系——庫切小說《福》對魯濱遜神話的改寫[J].外國文學,2009(3):86-90.
I106.4
A
1674-5450(2014)01-0090-03
2013-08-22
韓亞君,女,遼寧凌源人,沈陽師范大學英美文學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 詹 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