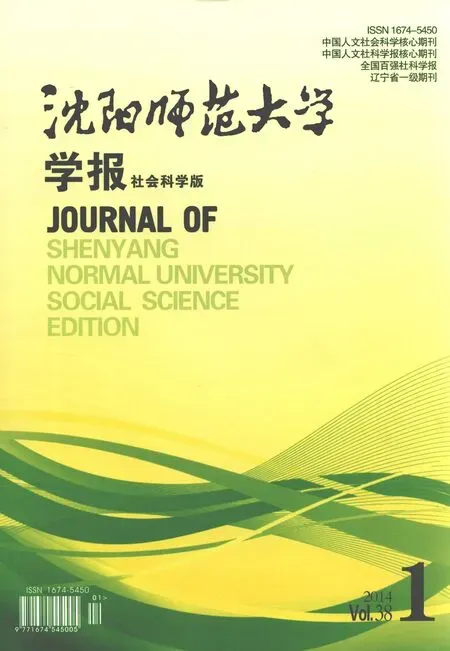從“朦朧詩論爭”看“精英”與“大眾”的話語分歧
王靜斯
(遼寧大學 文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
從“朦朧詩論爭”看“精英”與“大眾”的話語分歧
王靜斯
(遼寧大學 文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
20世紀80年代是論爭的年代,至今為止,“80年代”所彰顯出來的對于理想的追求,對于信念的堅守,對于公共事務的執著仍然久久鐫刻于知識分子的內心并成為了只可想象而不可重臨的“烏托邦”。“朦朧詩論爭”作為新時期文學中最持久而尖銳的一次論爭,其論爭的批評方式一直潛隱于后來的批評格局中。目前,文學界存在著“精英話語”與“大眾話語”疏離的窘境,因此從“朦朧詩論爭”這一角度入手,分析“朦朧詩論爭”的某些特點如何影響“精英話語”與“大眾話語”的對立。
朦朧詩論爭;“精英話語”;“大眾話語”
朦朧詩論爭作為新時期文學領域內規模最大,同時也是最尖銳的一次論爭,共持續了九年的時間(1979—1988),期間中國社會無論從經濟、政治還是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隨著論爭的逐漸深入,論爭的范圍也漸次由最初的局限于詩歌領域或者說僅在文學領域內進行的“純文學”的探討延伸和發散到了社會領域,上升到了政治意識形態層面,那么朦朧詩論爭也就由最初的“文學論爭”層面的懂與不懂的問題演變成了“社會論爭”中資本主義道路或是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問題。如果說以上是從共時性層面分析朦朧詩論爭影響的話,從歷時性方面,當朦朧詩論爭的熱潮過去之后,其論爭過程中所形成的話語特點和批評方式也對后來乃至新世紀的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擬從對比“朦朧詩論爭”中的雙方和“大眾”與“精英”這兩組關系中,試圖分析一種固定的批評思維和模式如何延續并作用于新世紀文學批評中,探討這種批評方式的不足以及如何走出這種固化的模式。
一、“朦朧詩論爭”中的批評模式
朦朧詩從最開始的由于晦澀難懂等原因被傳統詩人以及詩歌批評家所詬病,到后來的逐漸為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識到它的價值所在,再到“新的美學原則崛起”的合法性確定,應該說其被接受的過程是艱難和曲折的。其作為向“政治敘事”、“國家敘事”、“一元的價值標準”提出挑戰的具有先鋒性質的“事件”,應該說在新時期的意義是重大的,甚至有些研究者將其看做先鋒文學的傳統之一。很多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對此次論爭進行了闡釋,主要是從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以及兩輩詩人之間不同的詩學觀念等角度切入分析。本文認為梳理和探討此次論爭的全過程已沒有過多的意義,而意義在于經由此次論爭之后,留下的具有代表性的批評話語特點以及批評方式對于后來文學批評的影響,這也是朦朧詩論爭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的彰顯。程光煒在《批評對立面的確立——我觀十年朦朧詩論爭》中指出:“詩歌的批評,也許就在于對批評的‘對立面’的確立過程之中,這是人們對詩歌批評‘獨特性’的一種常見的理解。”也就是說,在朦朧詩的論爭過程中,朦朧詩的支持者是通過與對方的論爭,甚至是批評和找出對方的弱點來確立和證明自己立場和理論正確性的。這正如拉康的鏡像理論,依靠對方的存在,在對方的“鏡像”當中發現自身,確證自身,使自身被凸顯,即在“他者”中建構起自己的價值。而這種“他者”一旦消失,自己的理論和觀點也沒有了任何的立足點和存在的基礎。也就是說,朦朧詩作為新興事物,作為一種新的文學思潮,它要確立自己的合法地位,就要通過極力地駁斥對方來完成。應該說,這是自“五四”以來我們形成的一種傳統,“五四”時期要提倡新文化,彰顯白話文的重要性,那么其對傳統采取的方式是激烈的和極端的,他們將中國的傳統文化無論精華或糟粕都批判得一文不值,態度之堅決,大有不把對方置于深淵,自己就無法立足,就無法凸顯自己的氣勢,其實這也是“革新”的必經之路。正如孫紹振所說:“沒有對權威和傳統的挑戰甚至是褻瀆的勇氣,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性的空話。在當藝術革新潮流開始的時候,傳統、群眾和革新者往往有一個互相摩擦、甚至互相折磨的階段。”徐敬亞在其《崛起的詩群》中,為了彰顯“朦朧詩”的價值,甚至將批評的觸角伸向了中國的古詩。
朦朧詩相對于傳統詩歌而言具有革命性的改變,它從根本上改變了詩歌的表達方式,在主題和內容方面將關注點深入到人的內心,挖掘人內心的孤獨、苦悶、猶疑和彷徨。在表達技巧方面也大量地運用了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技巧,運用了語言陌生化等現代派的表達方式。這些主題和表達方式與傳統詩歌中的“贊歌式”的、“國家民族式”的、“明晰簡單式”的風格截然不同。但從批評話語的領域考察卻存在“文革”期間的“論戰式”的批評模式的痕跡,這種批評模式中體現出的是情緒性和非學理化的特征。這種方式是將對方的論點歸納出來,找出對方的某種缺陷,最終以將對方否定來確立自己理論權威地位為目的的批評方式。有研究者將此種批評中呈現出來的思維稱之為“本質化思維模式”。本文認為這種批評的主要特征就是批評立場的預設性和批評的武斷性,不能認真地分析對方理論的優勢和不足,而是為了確認自己立場的正確性,抓住對方弱點攻擊,大有拋棄一切傳統和文化底蘊,“重打鼓,另開張”的意思。這種批評方式具有明顯的本質化思維的色彩。學者晉海學指出了本質化思維的嚴重危害性,“如果缺乏對由‘朦朧詩論爭’所呈現出來的‘本質化思維模式’的自覺抵制能力,我們不僅會失去進入那段歷史的契機,同時也無法有效地反省自身,乃至于中國當代文學雖始終在一種徘徊狀態里掙扎,卻一直苦于無法找到發展自身的動力”。應該說這種“本質化思維模式”一直延續,而在新世紀文學批評中起到或隱或顯的作用。本文認為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權威式批評,是情感批評和不及物的批評,這種批評是溢出文學問題邊界的批評,是社會意識形態內話語權的爭奪,而非文學領域內的論爭。正如西方學者分析中國的“朦朧詩”與西方意象派之間的異同時指出:“與意象派相反,朦朧詩人是政治社會的一部分,并且認為他們的詩歌就是參與那個政治社會。”本文認為朦朧詩之于傳統詩歌的對峙,“崛起派”批評之于反對派的論爭,在此過程中所呈現的糾結和摩擦,其所采取的確證自己的方式,在新世紀的批評格局中完全呈現于“精英”(精英文學或精英批評)和“大眾”(大眾文學或民間的批評之聲)的兩種文學形態的對峙中。
二、“反叛傳統”批評方式的延續:“精英”與“大眾”的分歧
這種批評之于“五四”運動與“崛起派”都是以批判傳統的方式展開的,本文稱其為“反叛傳統”的批評。這種批評的慣性思維潛隱在新世紀的批評中,像是在演繹一種歷史的循環。與論爭不同,新世紀“精英”與“大眾”的對立主要表現為后者對前者的漠視。目前,精英話語和大眾話語作為兩種主要的話語方式,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尷尬、疏離甚至是對峙的,它們之間的分歧與朦朧詩論爭中的分歧是形式不同而本質相同的。實際上,這種論爭在新世紀已經愈加地由文學觀念的分歧逐漸演變成為了話語權力的爭奪,甚至成為了一種對“話語霸權”的向往和渴求。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新媒體和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精英文學走進了一個相對狹隘的空間,受眾群體逐漸變小,而社會對于純文學理論和精英文學作品的探討也逐漸地止步于研究生課堂或者專門的學術會議,“圈子化”和“小眾化”的特征凸顯。如20世紀80年代對文學充滿理想和激情的年代已經不再,人們街頭巷尾議論的是官場文學、言情小說、網絡文學,大眾熱衷的是于日常生活中具有功利性和直接性作用的話語方式。對于“精英文學”或者說“學院文學”的探討,對于哪部文學獲得了“茅盾文學獎”等高端文學領域問題的關注逐漸淡化。從某種程度上說,大眾話語的發展跟“崛起派”的反傳統相似,它們通過解構精英話語彰顯自身,它們的話語是戲謔的,是充滿反諷、戲仿、反叛、先鋒等后現代的話語方式的,它將受眾的旨趣作為第一要義,這一領域充斥的關鍵詞是日常生活、碎片、散亂、無中心和價值多元。這之于精英話語對于精神的挖掘、對于信仰的堅守、對于意義的建構呈現出大異其趣的態勢。那么,“大眾”對于“精英”的反叛正如“崛起派”之于“贊頌式”的、“簡單明晰式”的傳統詩歌的支持者一樣,“崛起派”解構的是傳統詩歌中的“贊頌”“國家民族”;“大眾狂歡”解構的是終極價值,應該說它們都是一種“反叛傳統”的批評話語方式,某種程度上都是從批判對方的過程中建構自身的。那么在新世紀,建構自身的背后更表現出話語權的爭奪,目前,大眾話語也逐漸建立起了另一種層面上的權威。
三、批評方式“歷史循環”的深層探究
這種批評方式與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到“朦朧詩崛起”確認自身的方式是相似的。“反叛傳統”真的能確立自身嗎,應該說,“朦朧詩”合法性的確立,“大眾”話語與“精英”話語分庭抗禮局面的形成,其更源于深層的社會歷史原因。一種文學思潮能夠如魚得水,順利發展依賴于整個社會中大的文學體系和制度,“崛起派”的外在表征是一種對新的話語表達方式的認同,是對一種新的審美情感的支持,然而其內在的本質卻是與社會發展進程中對于“現代化”的訴求相一致的。也就是說“朦朧詩”中對于西方現代派技法的應用,對于西方“意識流”小說中對于挖掘內心情感的借鑒,這種文學上對于“現代性”的認同正好契合了整個社會發展進程中對于“現代化”的追逐和訴求。也就是說,“崛起派”的觀點契合了整個社會的文化環境,與“大歷史”背景下文化體系的標準和內核是一致的,雙方達成了“合謀”的關系。因此,“崛起派”所支持的“朦朧詩”的新奇的、有創新性的表達方式,和脫離“國家敘事”、脫離“頌歌式”的表達,才能夠在“反叛傳統”中獲得優勢,并使“三個美學原則的崛起”作為合法性的美學標準被人接受并確定下來。而在新世紀“精英”與“大眾”話語的對峙中,“大眾”話語在與“精英”話語磨合與對峙的過程中,“大眾”話語顯露出的無法阻擋的發展之勢,這正與社會的轉型、經濟的發展以及科技的進步背景下對于整個社會文化體系多元化標準的轉變密切相關。經濟的轉型、傳媒的發展促使國家意識形態由原來的“政治關注”轉移到了“經濟關注”,主流意識形態放松對文化控制提倡多元化的同時,人們的生活節奏也不斷加快以及接收信息的渠道也更加多元化,因此,“快餐文學”“大眾文學”那種“直擊眼球”的不需要花費多少精力閱讀同時能夠使人迅速放松的,沒有任何沉重感和終極價值追求的文學大行其道,其也正好契合了整個時代發展的多元文化體系。因此,無論是“崛起派”的成功,還是“大眾話語”的盛行,其成功的深層原因都是其表達了與社會發展路向的趨同,是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先進”戰勝“倒退”的不證自明。因此,歷史的循環產生于文學與政治互相纏繞的變化關系中。
通過批評對方來確認自身這種“反叛傳統”的批評方式應該是由來已久的,這種批評方式是數百年來我們積累起來的文化經驗,在與傳統的意識形態和文學理念的糾纏與掙扎中推動歷史的前進。而這種批評的缺陷顯而易見,這種批評方式很容易從文學領域擴展到政治意識形態領域,發展為話語權的爭奪。在“精英”與“大眾”磨合與糾纏的過程中明顯表現出了此種態勢,與朦朧詩論爭中的“崛起派”不同,大眾話語在其論爭的過程中采取的是另一種“反叛”,比如大眾文學中的網絡文學,其具有廣泛的群眾影響力,有穩定的受眾群體和擁護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如前所述,這種新興的話語方式的發展過程仍然沒有脫離“反叛傳統”的批評模式,只不過這種反叛不是通過激烈的言語辯論來實現的,而是通過漠視傳統與忽略權威的方式展開的。而忽略權威同時又建立起了另一種權威,正如“朦朧詩論爭”的目的不是在文學領域的革新,而是致力于社會領域,是一場“政治事件”一樣。應該說,大眾文學在反叛傳統的過程中也建立起了另一種權威,是一種“去政治的政治”。也就是說,無論是“朦朧詩”最初的對于“純文學”的標榜還是大眾話語等對于民主和自由的彰顯,其表面“去政治”,擺脫政治干擾的過程實際帶來了一種“再政治”化的結果。正如目前網絡文學所建立起來的網絡話語、建立起來的各種“小圈子”,人人網、微信、微博、空間等等,使不了解網絡技術,不懂得網絡基本話語的人難以進入這個團體和圈子,這何嘗不是另一種權威和話語權的建立,是“大眾”領域內的政治,是另一種形式的“傳統”,是另一種形式的“鐵板一塊”,這就是“反叛傳統”批評模式的某種弊端的呈現。
針對以上問題,本文認為要在批評的過程中避免過分的情感因素,應該在學理化的層面上,在全面分析了解對方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批評意見,而避免一知半解的、武斷的、社會政治層面的歸納總結。因為某種在雙方互不了解的層面上,站在自己固有立場上進行的不及物的論爭也只能算是批評領域的一場鬧劇,或者僅僅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獲得勝利,而談不上產生任何的學術增長點以及理論的縱深和延展。只有理性的反思這種“依靠對手”存在的武斷的、固化的、缺少理論根基的批評才能夠更好地推動批評的發展。
[1]程光煒.文學講稿:“八十年代”作為方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85-188.
[2]孫紹震.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J].詩刊,1981(4):55—57.
[3]何同彬.晦澀:如何成為“障眼法”?[J].文藝爭鳴,2013(2):90-91.
[4]王愛松.朦朧詩及其論爭的反思[J].文學評論,2006(1):113—118.
[5]李怡.艾青的警戒與中國新詩的隱憂[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1(3):61-63.
[6]段宏鳴,羅崗.當代文藝思潮.與“朦朧詩論爭”[J].南方文壇,2011(2):71-74.
[7]晉海學.論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朦朧詩論爭”[J].貴州大學學報,2008(5):61-62.
I235.1
A
1674-5450(2014)01-0103-03
2013-09-12
王靜斯,女,遼寧朝陽人,沈陽師范大學教師,遼寧大學文藝學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 詹 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