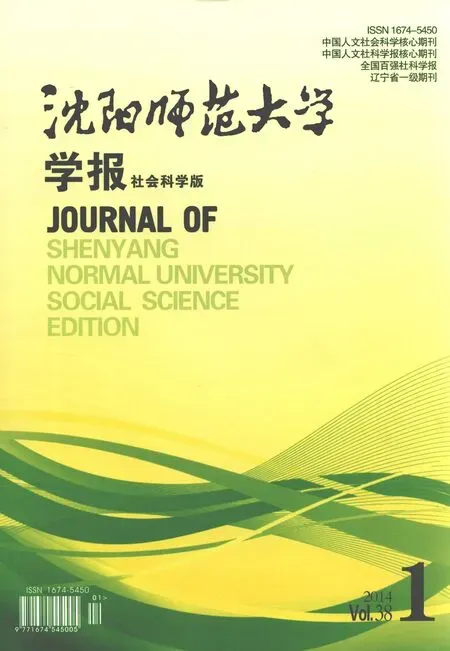音樂美學學科建設的新視角
軒小楊
(沈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遼寧沈陽 110034)
音樂美學學科建設的新視角
軒小楊
(沈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遼寧沈陽 110034)
近三十年,西方文藝思潮一浪接一浪地涌進國內學界,沖激進而占據很多學者的思維及話語。如今浪潮漸漸退去,人們開始重新思考并嘗試建立屬于自己的學科內涵以及話語范式,音樂美學就處在這樣一個發展階段上。從其哲學性質、人類學事實、藝術學前提這三重屬性看,音樂美學與人的生存實踐、生活樣態、生存境界有著難以割裂的關系。因此,人的生存實踐就成為音樂美學學科建設不可忽視的新視角。
音樂美學;學科建設;生存實踐
第九屆全國音樂美學學術研討會(2011年)的中心議題,是關于當代中國音樂美學學科的主話語及話語范式。各方學者圍繞現代性進程、多元化語境、跨學科策略等當代中國音樂美學的生態環境,以及改革開放以來音樂美學學科的發展歷程各抒己見,針對時下學科建設所面臨的基本問題與相關實踐問題展開激烈交鋒,使與會者對中國音樂美學的未來發展充滿希冀,同時勃發使命感。時隔年余,思緒漸趨沉實,深感音樂美學的學科性質乃至音樂美學的中國化建設的問題尚需澄汰。畢竟,這是學科建設的根本問題。本人贊同韓鐘恩先生提出的“音樂美學的哲學性質、人類學事實與藝術學前提”[1]等觀點,并在此基礎上,再從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的角度談些意見。
一、從人的生存實踐追問音樂美學的哲學性質
哲學究其根本屬性乃在于對人的生存實踐的反思、追問與回答。所謂音樂美學的哲學性質,就是用哲學的思維與視角來研究音樂,回答音樂是什么?人與音樂存在怎樣的關系?音樂具有怎樣的價值和功能?這些價值和功能的存在形態及其判斷標準是什么等等關于音樂藝術的根本問題。而這些問題不僅是音樂美學學科的基本問題,更是對音樂之于人的存在的本質追問。
首先,音樂美學的哲學性質,意味著音樂美學的理論根基應建立在人的生存實踐上。無論是研究“音樂(的)美學”,還是研究“音樂美(的)學”[1],思維的出發點與目的地都應落實在人的生存這一基本問題上面。有了這樣的認識基礎,音樂美學的學術研究才會始終具有明確的方向與目標,即如何有效地提升音樂在人的生存實踐中的意義與價值;也才會有繽紛的話題及話語的涌出,即如何多角度多維度地思考并構建音樂與人的合理性關系。盡管兩百多年前,德國詩人、音樂家舒巴特的著作《論音樂美學的思想》出版,音樂美學才以學科的面貌出現,但音樂美學思想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光芒璀璨。眾所周知的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就已經圍繞音樂的本質、音樂的社會功用、音樂的審美標準等核心問題給予深具時代色彩與文化因緣的反思、追問與回答。不論是儒家的倡行禮樂,還是道家的推崇自然,抑或墨家的“非樂”,這些主張共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立足于人,立足于人的生存實踐,而這正是中國文化、中國哲學的特點,即所謂的“實踐理性”[2]。
其次,音樂美學的哲學性質,意味著以對音樂的哲學追問來觀照現實的音樂實踐。理論的生成源于實踐,生成的理論也要能作用于實踐。當我們聆聽西方所謂后現代音樂時,對于其中的反形式、反美的美學傾向以及隨意拼貼、什么都行的音樂概念泛化,這一方面讓我們看到,是現代社會中人的信仰危機所導致的審美逆反心理、現代科技廣泛制造的虛擬空間所促生的對無機世界的審美探求、現代工業環境下藝術品的批量生產所帶來的普遍的審美飽和等復雜因素,造成了人的審美活動的異化、音樂的異化;另一方面,音樂的美作為人的本質需要,美的音樂的基本元素何以傾覆,追根究底,是關于音樂是什么、音樂與人的合理性關系是怎樣的這些基本認識被遮蔽,才使得在追求新異的旗號下制造出令人難以卒聽甚至無以為聽的“音樂”產品。這是理論研究與實踐需求、音樂本質與人的生存實質背離的必然的結果。
最后,音樂美學的哲學性質,最終意味著音樂美學的學科構建,是立足于人的生存實踐上,以理論追索引領藝術實踐。音樂美學的發展不僅是理論家的事業,同時是音樂家的事業,無論音樂家還是理論家都應有理論與實踐兩方面的綜合素養。音樂家的藝術實踐不僅是在外部世界的召喚下發生的,更應是在內心世界對音樂哲學的深刻追問中發生的。縱觀歷史上的偉大音樂家,無不是以深邃的藝術思想撼人心魄,同時以生動的音樂作品扣人心弦。
總之,音樂美學的哲學性質首先在于對音樂是什么、音樂與人的關系的思考,堅守這樣的終極關懷,音樂才有意義,音樂的學術才有意義;這樣的哲學追問更是學科構建的前提與基礎,所謂學科話語缺失、話語范式零亂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二、從“田野工作”語境探討音樂美學的人類學事實
作為音樂美學的姊妹學科,音樂人類學的學科性質一般被定義為:“研究文化中的音樂,或研究作為文化的音樂。由于其內涵不斷擴展,近年來西方學術界又將學科主流傾向定義為:在地方性、區域性、或全球性的背景中,研究音樂的社會和文化方面。”[3]250顯然,音樂美學與其有很大的交叉疊合處。韓鐘恩先生曾引述趙宋光先生在《歷史引發的美學思索》中提出的音樂學東西方研究的三個區別及需要注意的五對范疇,以及在《為在北京舉行的2009音樂美學專題筆會擬訂的討論題綱》的相關內容,其結論是,“毫無疑問,這里提出的三個區別和五對范疇完全不限于美學論域,至少,有向哲學與文化人類學擴充的趨向”;“很顯然,此討論題綱已然越出傳統音樂美學論域,不乏有諸多跨學科意義的藝術學前提與人類學事實。”[1]文本信息尤為顯明: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與音樂美學交叉疊合。如此,便涉及到對“田野工作”的再認識。
這里引據王耀華主編的《音樂學概論》對“田野工作”的描述:田野工作是指觀察處在原地的人……早期曾研究口頭傳統的民族民間形式、異族農民社會的音樂、異國或原始民族的音樂、東方古典音樂體系,這些現在仍舊是流行的主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課題日益豐富,既有內地遙遠的少數族群,也有現代化、西方化的城市音樂生活、流行音樂和音樂工業。田野可以是地理區域或語言區域;一個族群;一個村莊、城鎮、郊區或都市;沙漠或叢林;熱帶雨林或北極凍原。對歷史研究者而言,檔案館和圖書館也是田野[3]251。
音樂美學的人類學事實決定了其對田野工作的依賴。但是,現如今有一個不可回避的現象:音樂美學的田野工作開展得不充分,甚至存在很大誤區,留下很多盲區。比如,對少數族群的音樂研究大都交給了音樂人類學,對流行音樂、音樂工業的研究更多扔給了音樂社會學,至于當下城市音樂生活也似乎游離在研究者的視線之外,與如火如荼的“回饋”“反哺”等等藝術實踐難相匹配的是理論研究的清冷。殊不知,現代都市音樂生活眾相紛紜,亟待做出理論高度的澄清與梳理。比如,層出不窮的“超男”“快女”,排山倒海的大眾粉絲,艷若曇花的勁歌慢曲,以及華山論劍般的歌手才藝大PK。凡此總總,營造出一個全民性的審美假象。之所以說“假象”,是因為,人們迷戀的,與其說是音樂,莫若說是傳播媒介打造出的歌手的風光抑或風光的歌手;與其說媒體在推出歌手的同時,也在傳播音樂,莫若說媒體借助音樂的審美之外的實用功能來實現收視率的攀升。當代媒體的強勢使得音樂的廣告宣傳、移情宣泄等實用價值被強化更被漫衍,以至湮沒了單純的音樂審美功能,并在大眾中引發廣泛誤讀。再如,KTV練歌廳成了人們業余時間蝸居的主要場所;廣告音樂的審美趣味、藝術品質及其價值追求不期然地影響到廣大的人群;鄉土文化、民間音樂在城市化進程與學院派演繹中悄然發生著改變……這些紛繁復雜的音樂現象,理應引起音樂美學研究者的深度關切,成為音樂美學研究的課題。如果研究者通識本學科的人類學事實,就不會有“議題危機”的出現,更不會有田野工作的閑置。從根本上說,音樂美學言說的對象就包括人類學所面對的此時、此地、此人(群)的真實的存在,這些構成音樂美學不竭的話語;音樂美學的話語范式就生成于與此相貫通契合的語言邏輯,成為立足于生活實在、構架于邏輯推演、成就于終極關懷的話語現實。
三、從人的生存境界確認音樂美學的藝術學前提
如前所述,中國文化、中國哲學的特點,在于所謂的“實踐理性”,即立足于人,立足于人的生存實踐。既如此,人的生存境界以超拔于生存實踐的心靈體悟,成為中國文人的理想追求及中國文化的顯明特點。
《樂記》是中國古代重要的音樂理論文獻,其中不乏這樣的表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4]此論不僅表達了對以“聲”“音”“樂”為指稱的不同藝術層次的認知,更指認了由“知聲”“知音”而“知樂”所代表的不同審美層次,進而指示出對“眾庶”與“君子”不同人格境界的評斷與取向。顯然,《樂記》的思想立足于人,力圖在眾相紛擾的現實中撥云見日,引領眾人走向更高的生存境界。若剝離歷史的外衣視其思想的內核,其智慧及努力堪可稱道,實則指明了為今人所困惑的音樂美學本該堅守的一個研究方向,亦即探討音樂之于人生的指引力量。
在中國歷史上,無論是因于文人的自覺還是始于為政的理性,在社會生活中,音樂怡情悅性以至移風易俗的“教”與“化”的功能均受到重視并引以實踐。先賢孔子每日“弦歌不衰”,以樂成性,實現其“從心所欲不愈矩”[5]12的人生境界,而成就人世豐碑;其“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的智識其影響又何止千年。
在如今多元開放的中國,音樂產品層出不窮,大眾品賞也是隨心所欲,應和了一般藝術理論所謂藝術生產與藝術鑒賞的雙重“主體性”,亦即《樂記》所云“眾庶知音”“君子知樂”。然而,面對時下藝術生產中泛濫的怪異、低俗之“音”與單薄、勢弱之“樂”,以及藝術消費潮流中的“審丑”趨向,音樂理論工作者卻未能及時有效地發出像古圣先賢“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5]164“惡鄭聲之亂雅樂”[5]187般的感慨與疾呼,而彰顯文人的智慧與擔當。當然,必須澄清的是,“放鄭聲”的主張自有其歷史局限,其狹隘與保守早已為世人所洞見。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在當時社會生活中所發揮的引導作用以及對后世文化所發生的深遠影響。反觀現今,在紛繁復雜的音樂現象面前,當代音樂理論工作者卻失語了,音樂美學的這一方價值與意義被自我懸置。
進入21世紀,古老的中華文明走向復興。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神舟”飛船相繼升天,倫敦奧運會獎牌總數世界第二,世界富豪排行榜中有不斷增加的中國人的身影……一系列的數字表明,中國的綜合國力以及百姓的生活水平正在節節攀升。與此同時,一連串的事件卻極不和諧地充斥眼前與耳畔:小悅悅事件、彭宇案件、地溝油、染色饅頭、致癌牛奶等現象頻頻發生,讓人們不得不正視所面臨的人心疏離、情感扭曲、誠信缺失、道德錯位、文化貶值、金錢至上的社會問題,并開始意識到,這些在記憶中本來屬于“西方自由國度”的現象,而今已悄無聲息地就在自己的身邊,甚至在心靈深處落腳了。肩負社會先進文化的引領者之重責的文人,對此是否有所反思?又該有怎樣的作為?如果說,我們曾經一如眾多國人,面對改革大潮席卷而至的西方各種哲學思潮、文藝流派以及生活方式、價值觀念,長期閉鎖的心靈被撞擊,過去不曾質疑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被撼動,于是沉陷其中,“與狼共舞”,那么,狂歡過后,我們是否還能拾回一絲冷靜,復蘇一度休眠的心靈觸覺?
音樂,作為藝術家族中的一員,不論對其作怎樣的“感性的抽象”[1]的新表述,抑或“藝術的先驗性”[1]的再思考,其“感人至深,化人最速”的基本特性,尤其需要人們對其如何發揮“興、觀、群、怨”[5]185等無可替代的社會功能給予高度重視。當然,經歷了歷史的淬煉,人們早已明了,樂教不是政治的代言,音樂的選擇本該從屬于個人的價值取向,但為什么我們不能以理論先導的力量,以文人對文化的自省、自覺與自信,引領大眾在享受音樂的同時提升審美品格,從而提升其生存境界呢?所以,對于韓鐘恩先生提出的“藝術家是不是人類奢侈品的最后生產者?藝術學家又是不是人類奢侈品的最后消費者?”[1]的設問,我的回答,或許應該說,我的理想答案是否定的。
由此可見,音樂美學的學科建構,既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無論是音樂美學哲學性質的追問,還是人類學事實、藝術學前提的探討,都應立足于人的生存實踐,在人與音樂的關系、音樂對于人的價值與功能的實現等基本問題上展開持久而深入的研究。理順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一個廣闊無比、蘊藏深厚的學術世界。
[1]韓鐘恩.音樂美學的哲學性質、人類學事實與藝術學前提以及音樂本質力量的先在性——由2011第九屆全國音樂美學學術研討會議題引發的三個討論與進一步問題[J].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2011(9):5-12.
[2]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288.
[3]王耀華.音樂學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注譯[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4:276.
[5]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5.
J601
A
1674-5450(2014)01-0159-03
2013-11-25
軒小楊,女,遼寧彰武人,沈陽師范大學副教授,文藝學博士。
【責任編輯 趙 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