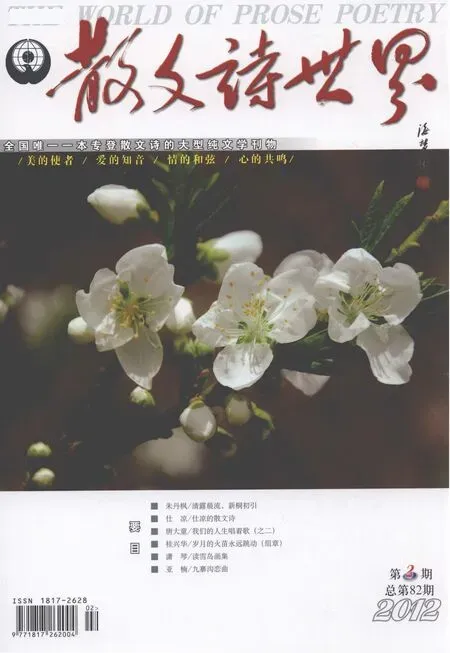拜水九寨藍(lán)(組章)
四川 蔓 琳
2012年冬,“九寨溝國際冰瀑節(jié)”和“‘藍(lán)冰——暖陽’九寨溝國際散文詩筆會(huì)”在九寨溝舉行,九寨溝的瀑布也在這個(gè)季節(jié)凝結(jié)成冰,彩色的自然呈現(xiàn)另一種風(fēng)情……
藍(lán)色沉默
九寨溝,在我離開你無數(shù)個(gè)日子以后,我,開始想你。
我開始想你,想你那泛著幽幽藍(lán)色的深度,蒼翠的樹木在鋪天蓋地的潔白里扎根,柔弱的水在陡峭的懸崖赫然站立,童話的精靈攜著你的思緒,以玲瓏剔透的純凈飛翔于我的夢(mèng)境。
你的寧靜是藍(lán)色的,你沉默的藍(lán)色牽引著我心底的愛慕,讓淙淙的流水在這個(gè)季節(jié)堅(jiān)硬起來。這是一個(gè)透明的世界,塵世的喧囂在你的心情之外戛然而止。
我不能不去想你,那些單純的山,靜穆的樹和純粹的水;我不能不去想你,那些冰凌里盛開的水晶的寒冷。它們?cè)谝粭l狹窄的溝壑里,浩浩蕩蕩地演繹著世間最復(fù)雜的情感與最簡單的哲理。
銀色的樹枝是你的長袖嗎,在那樣的湛藍(lán)里朝我深情地飛舞。
擁我在你懷中吧!讓冰清的欲望冷藏這個(gè)冬季;用陽光將我與冰雪一同融化吧!我愿意躺在你的懷中,細(xì)數(shù)你的水紋。我愿意用我潔白的思想,聆聽你滴滴答答的雨露喚醒酣睡的春風(fēng),然后在你的沉靜中凝視生命的律動(dòng)。
藍(lán)色無言,靜謐的海子懷抱著深邃的幽藍(lán)。
邂逅諾日郎
當(dāng)我第一次見到你,你的世界就已經(jīng)寒徹心扉。
我不知道是怎樣的寒風(fēng)吹過你曾經(jīng)溫暖的晶瑩?是怎樣的冰雪封凍你曾經(jīng)奔涌的激情?我不知道你曾經(jīng)擁有怎樣彩色的夢(mèng)幻?也不知道你曾經(jīng)怎樣風(fēng)光地在歲月里翩翩舞蹈?
不去說你湛藍(lán)的寂寞,不去渲染你澎湃的過往,不去詢問你絢麗的色彩,也不去打探你深藏于心底的每一種疼痛。
我愛上你了,從第一次聽到你的名字,從第一眼看見你的容顏。上天注定的宿命,我的愛戀明明白白地在我的眼中流淌。
我曾是怎樣驕傲的女子啊!此刻,卻在你洶涌的情懷里丟失了自己。
我心甘情愿地丟失了自己,我所有的美麗和矜持在你面前變得無足重輕。而你,以千軍萬馬的豪情朝我涌來,坦坦蕩蕩而纖塵不染,凝結(jié)成冰也定格成奔騰的氣勢(shì),在燦爛的陽光下灼灼生輝。
從此,我們的世界變得溫暖,我們的心靈因?yàn)楸舜说臒釔鄱彳浧饋怼6覊m封的柔情,被你一瀉千里的澎湃掠走,我的夢(mèng)想,追隨著你的排山倒海呼嘯而去。
因?yàn)閻郏谀愕纳砗螅覠o比謙卑。
風(fēng)景里的長海
我拍下一張與你的合影,在九寨溝最高的海子邊。
一路風(fēng)霜已經(jīng)停息,雪開始融化,那些被冰雪覆蓋的花兒開始對(duì)春天滿懷期待。
我曾是一個(gè)不羈的女子,在繁雜的塵世中堅(jiān)守信仰。我不刻意追逐春風(fēng),也不畏懼風(fēng)冷霜寒。
而此刻,我被你攬入懷里,靜靜地聽你的呼吸,你沙啞的耳語如梵音低唱。那棵站了千年的老人柏,就是為了今天見證我們此刻的相許。
雪山還在,依然是層層疊疊的雨霧迷朦,依然是甜甜蜜蜜的心事凝結(jié)。遠(yuǎn)處的山峰有蒼郁的樹木挺立,而我們,就在這肅穆的風(fēng)景里深情擁抱。
聽不見風(fēng)聲與燕啼,看不到煙塵和喧囂,那些來來往往的腳步也忽然淡出了視線。我的心緒如沉靜的海子,被風(fēng)卷起萬頃碧波。
多么慶幸能夠在此刻與你相擁,心里騰空的地方,滿滿地裝著你的笑容……
拍下一張與你的合影,滄桑的歲月在照片里漸漸模糊。
上天可以作證:我們緊緊相擁在此刻的風(fēng)景里,而風(fēng)景之外,云淡風(fēng)清。
貪戀珍珠灘
我本是雪寶鼎萬年不化的冰川,因?yàn)殛柟獾纳縿?dòng),一路漂泊而來。
已然看過太多山的阻隔,聽過無數(shù)風(fēng)的挽留,卻在這陡峭的山谷與你不期而遇。
于是你成為我的出路,洶涌向前是我們今生堅(jiān)定的誓言。因?yàn)槟悖@重重疊疊的山峰豁然開朗,那些曾經(jīng)嶙峋的石頭變得溫馨而圓潤。我的追求因你的激情而在流水的枝頭與浪花一道綻放,珍珠的花蕊,即便寒冬襲來,我也能將鋒利的冰凌盛開成美麗的芬芳,讓寒冷的時(shí)令春意盎然。
別誤解我是你追逐的財(cái)富,我就是山澗自由流動(dòng)的喜悅,我就是溝壑隨意含苞的花蕾。
然而,我仍然期待匆匆的腳步停下來,在這里聽聽樹上的鳥語,在這里曬曬干凈的陽光。
因?yàn)樨潙倌愕膽驯В疫€是情不自禁地在你的胸口枕流欲眠,于是,就在季節(jié)轉(zhuǎn)身的一瞬,嘩嘩啦啦流了一地的珠玉,便在懸?guī)r邊紛紛墜入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