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區(qū)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與農(nóng)牧民收入增長(zhǎng)關(guān)系分析——以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為例
劉尚榮
(青海大學(xué)財(cái)經(jīng)學(xué)院,青海 西寧 810016)
目前,在我國(guó)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快速發(fā)展的進(jìn)程中,民族地區(qū)農(nóng)牧區(qū)依然存在明顯的金融約束現(xiàn)象,經(jīng)濟(jì)發(fā)展仍然缺乏足夠的金融資源,農(nóng)牧戶和企業(yè)仍然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信貸約束,金融供給難以滿足其特殊的金融需求,金融機(jī)構(gòu)對(duì)農(nóng)牧區(qū)信貸資金投放不足的現(xiàn)狀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變。如何通過(guò)農(nóng)村金融的發(fā)展來(lái)促進(jìn)農(nóng)牧民收入的增長(zhǎng),成為縮小其與城鎮(zhèn)居民以及其他發(fā)達(dá)省份的差距,實(shí)現(xiàn)農(nóng)牧區(qū)和諧穩(wěn)定的關(guān)鍵。
一、文獻(xiàn)綜述
國(guó)外對(duì)金融發(fā)展與農(nóng)民收入增長(zhǎng)的研究,是部分學(xué)者在關(guān)注金融發(fā)展與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關(guān)系時(shí)所涉及的一個(gè)研究領(lǐng)域。Greenwood&Javanovic,Bencivengahe&Smith等以建立內(nèi)生增長(zhǎng)模型的方式分析了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對(duì)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不同影響,討論了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金融發(fā)展與收入分配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Bolton、Matsuyama等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金融發(fā)展與收入分配的演化過(guò)程。Calor&Zeira的分析認(rèn)為,由于金融資源配置不合理,利用金融中介的成本會(huì)比較昂貴,窮人無(wú)法支付這一成本因而無(wú)法得到金融支持,而富人則會(huì)更加方便地通過(guò)金融渠道獲得資金,在取得信貸方面的不平等待遇會(huì)導(dǎo)致二元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從而擴(kuò)大了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
國(guó)內(nèi)在研究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與農(nóng)民收入增長(zhǎng)的過(guò)程中,理論界也更多地是從金融發(fā)展與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關(guān)系中進(jìn)行探討的。王丹、張懿(2006)基于金融發(fā)展與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理論,應(yīng)用ECM誤差修正模型實(shí)證檢驗(yàn)了1991-2005年安徽省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與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之間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實(shí)證結(jié)果表明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引致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變動(dòng)。許崇正(2005)則從影響農(nóng)民收入的幾個(gè)關(guān)鍵因素入手,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進(jìn)行驗(yàn)證,認(rèn)為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對(duì)農(nóng)民收入增長(zhǎng)曾經(jīng)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總的來(lái)講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對(duì)農(nóng)民增收不利。王虎、范從來(lái)(2006)運(yùn)用1980-2004年的數(shù)據(jù)實(shí)證研究了金融發(fā)展與農(nóng)民收入之間的相關(guān)性關(guān)系,認(rèn)為金融發(fā)展對(duì)農(nóng)民收入有促進(jìn)作用,但其影響作用是復(fù)雜的。李林、張穎慧和羅劍朝(2010)運(yùn)用時(shí)間序列分析方法對(duì)1978-2004年間金融發(fā)展與農(nóng)民收入增長(zhǎng)的關(guān)系進(jìn)行實(shí)證研究,研究結(jié)果顯示,農(nóng)民收入增收狀況隨著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fàn)顩r改變而發(fā)生相應(yīng)變化,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是中國(guó)農(nóng)民收入增長(zhǎng)的格蘭杰原因。
國(guó)內(nèi)外的研究成果表明,金融發(fā)展與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及農(nóng)民收入水平提高具有正效應(yīng),對(duì)進(jìn)一步探索金融支持農(nóng)牧民增收具有重要的指導(dǎo)意義。但是,眾多的研究卻忽略了地域的特殊性,尤其是對(duì)經(jīng)濟(jì)欠發(fā)達(dá)的民族地區(qū)來(lái)說(shuō),如何通過(guò)金融發(fā)展來(lái)促進(jìn)農(nóng)牧民收入的增長(zhǎng),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少。
二、金融支持農(nóng)牧民增收概況
近年來(lái),海北藏族自治州金融機(jī)構(gòu)認(rèn)真貫徹落實(shí)青海省金融工作會(huì)議精神,充分發(fā)揮金融業(yè)對(duì)經(jīng)濟(jì)的“推手”作用,努力改善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的資金“瓶頸”問(wèn)題,緊緊圍繞農(nóng)牧業(yè)增效、農(nóng)牧民增收、農(nóng)牧區(qū)發(fā)展主線,在支持農(nóng)牧民增收中一方面堅(jiān)持用好用足金融優(yōu)惠政策,另一方面根據(jù)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特殊性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通過(guò)增加支農(nóng)再貸款、推廣農(nóng)戶小額貸款和聯(lián)保貸款、廣泛開(kāi)展信用戶創(chuàng)建活動(dòng)、增加農(nóng)業(yè)保險(xiǎn)保費(fèi)代償力度等,不斷加大對(duì)農(nóng)牧業(yè)的信貸支持力度,保證了農(nóng)牧區(qū)的信貸資金需求,取得了一定成效。截止2011年,涉農(nóng)貸款余額達(dá)10.54億元,占全部貸款總額的比重為54.72%。金融機(jī)構(gòu)在遵循“一次核定、隨用隨貸、余額控制、周轉(zhuǎn)使用”原則的同時(shí),根據(jù)農(nóng)牧民申請(qǐng)貸款意愿,結(jié)合資金用途確定單筆貸款的期限,簡(jiǎn)化貸款手續(xù)、提高服務(wù)質(zhì)量,解決了農(nóng)牧戶發(fā)展生產(chǎn)申請(qǐng)貸款手續(xù)繁雜、貸款難和資金周轉(zhuǎn)難的“兩難問(wèn)題”。在金融部門(mén)的大力支持下,農(nóng)牧民積極投身于農(nóng)作物種植、接羔育幼、牛羊育肥販運(yùn)、集約化經(jīng)營(yíng)等農(nóng)牧業(yè)各個(gè)生產(chǎn)領(lǐng)域,金融在促進(jìn)農(nóng)牧民增收致富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顯。但不容忽視的是,現(xiàn)階段金融支持農(nóng)牧民增收依然存在一些突出問(wèn)題:一是貸款的額度增長(zhǎng)不大。目前農(nóng)戶貸款平均額度為5萬(wàn)元左右,最少者0.5萬(wàn)元,基本上以2~5萬(wàn)元居多,難以滿足規(guī)模化經(jīng)營(yíng)的需要。二是農(nóng)牧民借款無(wú)抵押品成為金融機(jī)構(gòu)給農(nóng)牧民辦理貸款時(shí)遇到的最大問(wèn)題,加之擔(dān)保比較困難,在一個(gè)村里如果農(nóng)戶都貸款時(shí)擔(dān)保困難現(xiàn)象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致使農(nóng)戶貸款額度增幅緩慢,這也從側(cè)面印證了農(nóng)戶貸款難、難貸款的事實(shí)。三是農(nóng)戶的借款渠道較為單一。從農(nóng)戶借款來(lái)源看,農(nóng)村信用社成為農(nóng)牧民生產(chǎn)和生活借款的主要渠道,雖然海北州所屬的縣域除農(nóng)信社以外,還有農(nóng)業(yè)銀行、郵政儲(chǔ)蓄銀行等金融機(jī)構(gòu),但農(nóng)牧民所需的貸款90%以上是靠農(nóng)信社提供的,其他金融機(jī)構(gòu)很少向農(nóng)戶貸款。四是農(nóng)牧業(yè)保險(xiǎn)依然是依靠?jī)煞N傳統(tǒng)的風(fēng)險(xiǎn)保障途徑,即民政部門(mén)的災(zāi)害救濟(jì)和保險(xiǎn)公司的商業(yè)保險(xiǎn),對(duì)農(nóng)牧業(yè)的風(fēng)險(xiǎn)補(bǔ)償能力較弱。五是農(nóng)業(yè)貸款的高風(fēng)險(xiǎn)導(dǎo)致金融機(jī)構(gòu)支農(nóng)貸款增速緩慢。這些問(wèn)題的存在,使得金融支持農(nóng)牧民增收的功效未能全面顯現(xiàn)出來(lái)。
三、實(shí)證分析
西方經(jīng)典的生產(chǎn)函數(shù)理論中提到:在其他條件不變時(shí),增加資本投入能增加總產(chǎn)出。按照這個(gè)理論,其他條件不變時(shí),增加農(nóng)村信貸投入就能增加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總產(chǎn)出,進(jìn)而提高農(nóng)民的人均收入。從一些國(guó)內(nèi)外研究的成果也可以看出,各個(gè)國(guó)家或地區(qū)、各個(gè)時(shí)期農(nóng)村金融市場(chǎng)發(fā)展情況與農(nóng)民收入水平之間均存在一定關(guān)系。文章以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為個(gè)案,利用Eviews6.0軟件對(duì)民族地區(qū)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情況與農(nóng)牧民收入水平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行檢驗(yàn)。
1.模型構(gòu)建及說(shuō)明
根據(jù)柯布-道格拉斯生產(chǎn)函數(shù)(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可將我國(guó)農(nóng)村金融與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產(chǎn)出的關(guān)系表達(dá)為如下函數(shù):

其中,Y代表總的經(jīng)濟(jì)產(chǎn)出,K代表資本投入,L代表勞動(dòng)力投入。我國(guó)學(xué)者溫濤、冉光和與熊德平(2005)將金融發(fā)展水平作為一項(xiàng)“投入”引入生產(chǎn)函數(shù)分析框架中,研究了金融發(fā)展與農(nóng)民收入增長(zhǎng)關(guān)系,則(1)式可寫(xiě)成:

其中,F(xiàn)代表金融發(fā)展水平。
據(jù)Parente and Prescott(1991)及溫濤、冉光和等(2005)提出的分析框架,若勞動(dòng)力投入達(dá)到最大生產(chǎn)能力,經(jīng)濟(jì)產(chǎn)出就不再受勞動(dòng)力增加的影響,則總的經(jīng)濟(jì)產(chǎn)出就取決于金融發(fā)展水平與資本投入。此時(shí)(2)式可變形為:

其中,m表示勞動(dòng)力數(shù)量。
求公式(3)的全微分,可得:

國(guó)際上通常采用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和麥金農(nóng)(Mckinnon)提出的兩種指標(biāo)來(lái)衡量金融發(fā)展水平。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了衡量一國(guó)金融結(jié)構(gòu)和金融發(fā)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標(biāo),其中最主要的是金融相關(guān)比率(FIR)。它是全部金融資產(chǎn)價(jià)值與全部實(shí)物資產(chǎn)(即國(guó)民財(cái)富)價(jià)值之比,這是衡量金融上層結(jié)構(gòu)相對(duì)規(guī)模的廣義指標(biāo)。戈德史密斯認(rèn)為:金融相關(guān)比率的變動(dòng)反映的是金融上層結(jié)構(gòu)與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結(jié)構(gòu)之間在規(guī)模上的變化關(guān)系,它大概可以被視為金融發(fā)展的一個(gè)基本特點(diǎn)。因?yàn)樵谝欢ǖ膰?guó)民財(cái)富或國(guó)民產(chǎn)值的基礎(chǔ)上,金融體系越發(fā)達(dá),金融相關(guān)系數(shù)也越高,所以可以推斷,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過(guò)程中金融相關(guān)比率必然會(huì)逐步提高,而且可以根據(jù)金融相關(guān)比率來(lái)衡量金融發(fā)展達(dá)到何種水平。人們常常將其簡(jiǎn)化為金融資產(chǎn)總量與GDP之比,來(lái)衡量一國(guó)的經(jīng)濟(jì)金融發(fā)展水平。麥金農(nóng)(1973)采用貨幣存量與GDP之比來(lái)衡量貨幣化程度。由于金融資產(chǎn)和M2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不完整,因此文章選用修正后的指標(biāo)來(lái)衡量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水平。根據(jù)海北藏族自治州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的現(xiàn)狀,文章對(duì)該地區(qū)金融發(fā)展水平的度量主要選取金融發(fā)展規(guī)模和金融發(fā)展效率,函數(shù)關(guān)系式:


其中,μ為隨機(jī)誤差項(xiàng)。
鑒于難以獲得總資本增長(zhǎng)(dK)的相關(guān)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因此文章忽略總資本增長(zhǎng),選擇的模型如下:
其中,F(xiàn)R表示農(nóng)牧民人均純收入,RLG表示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的規(guī)模,RLD表示金融發(fā)展的效率,μ為隨機(jī)誤差項(xiàng)。
由于差分量只不過(guò)是水平量前后期的差值,根據(jù)(8)式不難證明FR的水平量與RLG和RLD的水平量之間同樣存在穩(wěn)定的關(guān)系。因此,文章為了便于實(shí)證檢驗(yàn)農(nóng)民收入水平值與金融發(fā)展各指標(biāo)水平值之間的關(guān)系,設(shè)定了如下的向量自回歸模型予以實(shí)際分析:
2.數(shù)據(jù)來(lái)源
農(nóng)業(yè)貸款余額(RL)、農(nóng)業(yè)存款余額(RD)以及農(nóng)牧民人均純收入(FR)的數(shù)據(jù)均來(lái)自《海北統(tǒng)計(jì)年鑒(2012)》。農(nóng)業(yè)GDP(RG)用第一產(chǎn)業(yè)增加值表示。
3.數(shù)據(jù)的統(tǒng)計(jì)性描述
文章使用農(nóng)業(yè)貸款、農(nóng)業(yè)存款代表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水平來(lái)衡量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與農(nóng)民收入間的關(guān)系。指定選取如下:
(1)農(nóng)牧民收入指標(biāo)。文章采用農(nóng)牧民人均純收入(FR)指標(biāo)來(lái)衡量農(nóng)牧民收入情況。農(nóng)牧民純收入是指其當(dāng)年總收入和總支出的差額。純收入主要用于再生產(chǎn)投入和當(dāng)年生活消費(fèi)支出,也可用于儲(chǔ)蓄和各種非義務(wù)性支出。農(nóng)牧民人均純收入即按人口平均后得到的純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一個(gè)地區(qū)或一個(gè)農(nóng)戶農(nóng)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
(2)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水平和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效率指標(biāo)。1969年戈德史密斯首創(chuàng)金融相關(guān)率(FIR)指標(biāo)并用它來(lái)衡量金融資產(chǎn)規(guī)模水平。它的表達(dá)式為(M2+L+S)/GNP,式中M2表示貨幣存量,L表示貸款,S表示有價(jià)證券的總值。考慮到發(fā)展中國(guó)家國(guó)內(nèi)信貸的作用,Arestis等學(xué)者又設(shè)計(jì)了一個(gè)新指標(biāo)L/GDP來(lái)反映金融發(fā)展規(guī)模,該指標(biāo)被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廣為采用。李廣眾(2002)和史永東(2003)多次采用農(nóng)村貸款余額與農(nóng)業(yè)GDP之比衡量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水平。由于民族地區(qū)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水平相對(duì)落后,缺乏有價(jià)證券和M2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在分析金融發(fā)展水平時(shí)無(wú)法直接使用金融相關(guān)比率這個(gè)指標(biāo)。為此,文章采用農(nóng)業(yè)貸款余額與農(nóng)業(yè)GDP之比,即RLG=RL/RG作為金融相關(guān)比率的一個(gè)替代指標(biāo)來(lái)揭示農(nóng)村金融的總體發(fā)展水平;同時(shí)用貸款與存款之比反映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效率。這是因?yàn)樵谵r(nóng)牧區(qū),金融資產(chǎn)主要表現(xiàn)為金融機(jī)構(gòu)的資產(chǎn),其他金融工具并不多,所以利用存貸款數(shù)據(jù),基本可以揭示出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水平。
(3)農(nóng)業(yè)GDP數(shù)據(jù)。由于缺乏農(nóng)業(yè)GDP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鑒于以前文獻(xiàn)多用第一產(chǎn)業(yè)增加值代替農(nóng)業(yè)GDP。因此,文章亦采用第一產(chǎn)業(yè)增加值代替農(nóng)業(yè)GDP。
4.實(shí)證分析
由于所釆用的數(shù)據(jù)均為經(jīng)濟(jì)變量時(shí)間序列數(shù)據(jù),通常不平穩(wěn)。為避免“偽回歸”現(xiàn)象,需要進(jìn)行單位根檢驗(yàn)來(lái)判斷變量是否平穩(wěn),文章采用ADF檢驗(yàn)。若為平穩(wěn)變量,可直接進(jìn)行回歸分析;若為非平穩(wěn)變量,還需通過(guò)差分將其變?yōu)槠椒€(wěn)時(shí)間序列;再通過(guò)協(xié)整分析來(lái)檢驗(yàn)變量間是否存在長(zhǎng)期均衡關(guān)系。
(1)平穩(wěn)性檢驗(yàn)。首先對(du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無(wú)量綱化,對(duì)各變量取對(duì)數(shù),以實(shí)現(xiàn)數(shù)據(jù)的可比性。由于RLG和RLD都小于10,因此log(RLG)和log(RLD)都小于0,而負(fù)數(shù)無(wú)法進(jìn)行后續(xù)檢驗(yàn),所以,均乘以100以使它們的對(duì)數(shù)為整數(shù)。由1990-2009年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可知,海北藏族自治州金融發(fā)展的規(guī)模和效率與農(nóng)牧民人均純收入變化趨勢(shì)存在著一致性。幾乎所有的宏觀經(jīng)濟(jì)變量都是非平穩(wěn)性的(即序列的矩,如均值、方差和協(xié)方差隨時(shí)間而變化),具有時(shí)間趨勢(shì),所以需要對(duì)變量進(jìn)行單位根平穩(wěn)性檢驗(yàn)。利用Eviews6.0軟件,對(duì)各變量進(jìn)行單位根檢驗(yàn),以確定變量的平穩(wěn)性。下面采用的ADF統(tǒng)計(jì)量,對(duì)變量的本身進(jìn)行ADF檢驗(yàn),分別在1%,5%和10%的置信水平下的臨界值進(jìn)行比較。單位根檢驗(yàn)方程存在截距項(xiàng)和趨勢(shì)項(xiàng),且變量的滯后序數(shù)都取2。
根據(jù)ADF統(tǒng)計(jì)量的性質(zhì),從表1中可看出log(FR)、log(100RLD)和log(100RLG)均為非平穩(wěn)序列。因此,需要繼續(xù)對(duì)模型變量log(FR)、log(100RLD)和log(100RLG)進(jìn)行一階差分處理。
(2)差分處理。進(jìn)行一階差分后,從表2中可看出,log(100RLG)和log(100RLD)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變量的t值小于Mackinnon臨界值,log(FR)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變量的t值小于Mackinnon臨界值,故各序列含有一個(gè)單位根,是一階單整序列。因此可以進(jìn)一步進(jìn)行協(xié)整檢驗(yàn)。

表1 模型變量ADF檢驗(yàn)結(jié)果

表2 模型變量一階差分的ADF檢驗(yàn)結(jié)果
(3)協(xié)整檢驗(yàn)。由上文分析可知log(FR)、log(100RLD)和log(100RLG)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因此這些同階單整序列可能存在協(xié)整關(guān)系,即從長(zhǎng)期來(lái)看各變量可能存在均衡關(guān)系。于是對(duì)log(FR)、log(100RLD)和log(100RLG)進(jìn)行協(xié)整檢驗(yàn),并對(duì)金融發(fā)展與農(nóng)民收入水平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行分析。
第一步,用OLS方法對(duì)回歸方程進(jìn)行估計(jì),得到回歸結(jié)果:

常數(shù)項(xiàng)和log(100RLD)和log(100RLG)均通過(guò)了t檢驗(yàn)。
(10)式表明了在1990-2009年上述三個(gè)變量之間所存在的長(zhǎng)期均衡關(guān)系。從模型的回歸結(jié)果可以看出,就長(zhǎng)期而言,農(nóng)牧民收入與金融發(fā)展效率呈正向關(guān)系,與金融發(fā)展規(guī)模呈負(fù)向關(guān)系。這說(shuō)明1990-2009年,青海藏區(qū)金融發(fā)展效率不斷提升,有利于農(nóng)牧民收入增長(zhǎng);而金融發(fā)展規(guī)模對(duì)農(nóng)牧民收入的增長(zhǎng)顯然是不利的因素。
第二步,殘差序列平穩(wěn)性檢驗(yàn),對(duì)其進(jìn)行ADF單位根檢驗(yàn),檢驗(yàn)結(jié)果如表3。

表3 回歸方程殘差平穩(wěn)性檢驗(yàn)結(jié)果
由表3可知,回歸方程殘差序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shè),接受不存在單位根的結(jié)論,則D(RESID01)是平穩(wěn)的,所以log(FR)、log(100RLD)和log(100RLG)之間存在協(xié)整關(guān)系,即農(nóng)牧民收入與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規(guī)模與效率間存在長(zhǎng)期均衡關(guān)系。雖然,回歸分析中l(wèi)og(100RLD)和log(100RLG)均通過(guò)了t檢驗(yàn),但回歸的擬合優(yōu)度很低,說(shuō)明金融發(fā)展水平不能對(duì)農(nóng)牧民收入起到很好的促進(jìn)作用,農(nóng)牧民收入的增加主要靠農(nóng)畜產(chǎn)品價(jià)格上漲、財(cái)政補(bǔ)貼等轉(zhuǎn)移性收入。這與目前農(nóng)村金融的信貸結(jié)構(gòu)和功能與農(nóng)牧民增收的實(shí)際資金需求不太協(xié)調(diào)的實(shí)際情況是相吻合的。
四、結(jié)論及建議
通過(guò)對(duì)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與農(nóng)牧民收入關(guān)系的分析來(lái)看,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效率與農(nóng)牧民收入增長(zhǎng)之間呈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而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規(guī)模與農(nóng)牧民收入增長(zhǎng)之間則呈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說(shuō)明一方面農(nóng)村金融機(jī)構(gòu)對(duì)農(nóng)牧業(yè)的支持力度不斷加大,但另一方面由于地區(qū)金融發(fā)展水平滯后,對(duì)農(nóng)牧民收入增長(zhǎng)的促進(jìn)作用不明顯。實(shí)證分析表明,金融支持是農(nóng)牧民增收的重要因素,金融發(fā)展有利于農(nóng)牧民收入的增長(zhǎng)。但是目前民族地區(qū)金融發(fā)展相對(duì)滯后,突出表現(xiàn)為:農(nóng)村金融服務(wù)體系不完善、金融服務(wù)單一、投資理財(cái)類(lèi)產(chǎn)品進(jìn)展緩慢、農(nóng)牧業(yè)擔(dān)保體系不完善等,致使金融對(duì)農(nóng)牧民收入增長(zhǎng)的貢獻(xiàn)度不高,需要根據(jù)民族地區(qū)發(fā)展實(shí)際,推進(jìn)農(nóng)村金融體制改革進(jìn)程,完善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的市場(chǎng)體系,實(shí)現(xiàn)農(nóng)村金融資源的高效配置,進(jìn)一步促進(jìn)農(nóng)牧民收入的增長(zhǎng)。
第一,培育多層次的農(nóng)村金融服務(wù)體系,提升金融支農(nóng)覆蓋面。積極推動(dòng)金融機(jī)構(gòu)空白鄉(xiāng)鎮(zhèn)服務(wù)覆蓋工程,促進(jìn)農(nóng)牧區(qū)金融服務(wù)均等化建設(shè),建立健全符合“三農(nóng)三牧”發(fā)展要求的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金融服務(wù)體系。大力培育村鎮(zhèn)銀行、貸款公司、農(nóng)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農(nóng)村金融組織,開(kāi)發(fā)新的貸款品種,拓寬新的經(jīng)營(yíng)模式。
第二,組建農(nóng)牧業(yè)信用擔(dān)保機(jī)構(gòu),切實(shí)解決農(nóng)牧民融資難問(wèn)題。在國(guó)家政策許可的范圍內(nèi),地方政府出臺(tái)優(yōu)惠政策和管理制度,積極發(fā)揮財(cái)政杠桿作用,建立以財(cái)政資金、商業(yè)資金、社會(huì)資金等為主的涉農(nóng)擔(dān)保基金運(yùn)作體系。鼓勵(lì)其他各類(lèi)擔(dān)保公司為農(nóng)牧業(yè)企業(yè)提供擔(dān)保業(yè)務(wù),降低農(nóng)牧業(yè)龍頭企業(yè)和專(zhuān)業(yè)大戶的融資難度和成本,形成國(guó)家、社會(huì)、合作成員與農(nóng)戶多主體分擔(dān)的農(nóng)牧業(yè)信貸擔(dān)保機(jī)制。
第三,鼓勵(lì)各類(lèi)金融機(jī)構(gòu)加大對(duì)農(nóng)牧業(yè)和弱勢(shì)群體的支持力度,以市場(chǎng)化方式引導(dǎo)資金有效返回農(nóng)牧區(qū)。賦予農(nóng)信社較大的存貸款利率浮動(dòng)權(quán)限,緩解農(nóng)村資金外流。
第四,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農(nóng)牧民的保險(xiǎn)意識(shí),增強(qiáng)抗風(fēng)險(xiǎn)能力。保險(xiǎn)機(jī)構(gòu)和相關(guān)部門(mén)應(yīng)進(jìn)一步加大宣傳力度,向農(nóng)牧民灌輸風(fēng)險(xiǎn)防范意識(shí),講解可保風(fēng)險(xiǎn)的范圍、風(fēng)險(xiǎn)防范方法以及保險(xiǎn)的保障作用,使農(nóng)牧民真正了解保險(xiǎn)、認(rèn)識(shí)保險(xiǎn)、依靠保險(xiǎn),增強(qiáng)農(nóng)牧民的承保意識(shí),為農(nóng)牧業(yè)保險(xiǎn)的全面推進(jìn)創(chuàng)造良好的條件。同時(shí),依靠各級(jí)政府的大力支持,加快完善農(nóng)牧業(yè)政策保險(xiǎn)體系,通過(guò)健全的體系和優(yōu)質(zhì)的服務(wù)為農(nóng)牧業(yè)生產(chǎn)保駕護(hù)航。
第五,逐步加大金融投資理財(cái)產(chǎn)品營(yíng)銷(xiāo),拓寬農(nóng)牧民增收渠道。金融機(jī)構(gòu)要通過(guò)各種形式加大業(yè)務(wù)宣傳力度,使農(nóng)牧民和企業(yè)能夠充分了解金融機(jī)構(gòu)推出的各種金融產(chǎn)品和服務(wù),采取方便靈活的營(yíng)銷(xiāo)手段,擴(kuò)大金融投資理財(cái)產(chǎn)品的銷(xiāo)售規(guī)模,增加農(nóng)牧民的財(cái)產(chǎn)性收入。
第六,創(chuàng)新農(nóng)村金融產(chǎn)品和服務(wù),加大對(duì)新型農(nóng)牧業(yè)經(jīng)營(yíng)主體的信貸支持。金融機(jī)構(gòu)應(yīng)根據(jù)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主體金融需求的特征,結(jié)合農(nóng)牧業(yè)發(fā)展實(shí)際創(chuàng)新差異化金融產(chǎn)品。農(nóng)業(yè)保險(xiǎn)機(jī)構(gòu)要優(yōu)化保險(xiǎn)服務(wù),引導(dǎo)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主體參保,保障農(nóng)業(yè)持續(xù)平穩(wěn)發(fā)展。
[1]溫濤,冉光和,熊德平.中國(guó)金融發(fā)展與農(nóng)民收入增長(zhǎng) [J].經(jīng)濟(jì)研究,2005(9).
[2]姚耀軍.金融發(fā)展與城鄉(xiāng)收入差距關(guān)系的經(jīng)驗(yàn)分析 [J].財(cái)經(jīng)研究,2005(2)
[3]許崇正,高希武.農(nóng)村金融對(duì)增加農(nóng)民收入支持狀況的實(shí)證分析 [J].金融研究,2005(9).
[4]婁永躍.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與農(nóng)民收入增長(zhǎng)問(wèn)題研究 [J].金融理論與實(shí)踐,2010(5).
[5]徐鐿菲.我國(guó)農(nóng)村金融發(fā)展的收入分配效應(yīng)—基于面板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研究 [J].金融理論與實(shí)踐,20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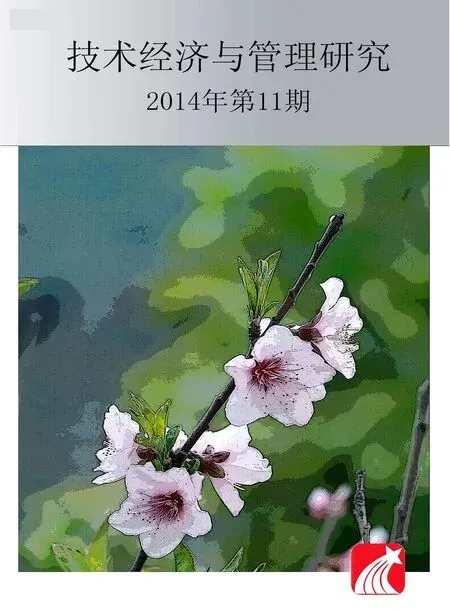 技術(shù)經(jīng)濟(jì)與管理研究2014年11期
技術(shù)經(jīng)濟(jì)與管理研究2014年11期
- 技術(shù)經(jīng)濟(jì)與管理研究的其它文章
- 哈薩克斯坦銀行制度轉(zhuǎn)軌研究——基于對(duì)中國(guó)的視角
- 融資融券對(duì)股價(jià)的影響——基于滬市A股的經(jīng)驗(yàn)研究
- 兩岸金融合作的成長(zhǎng)與波動(dòng)——來(lái)自壽險(xiǎn)市場(chǎng)的證據(jù)
- 進(jìn)入管制行業(yè)的集聚效應(yīng)和社會(huì)福利——基于航空航天制造業(yè)的實(shí)證研究
- 企業(yè)自主研發(fā)與產(chǎn)學(xué)研合作創(chuàng)新的互動(dòng)研究——基于能力互補(bǔ)和吸收能力的視角
- 中小物流企業(yè)聯(lián)盟伙伴選擇——基于PCA-BP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