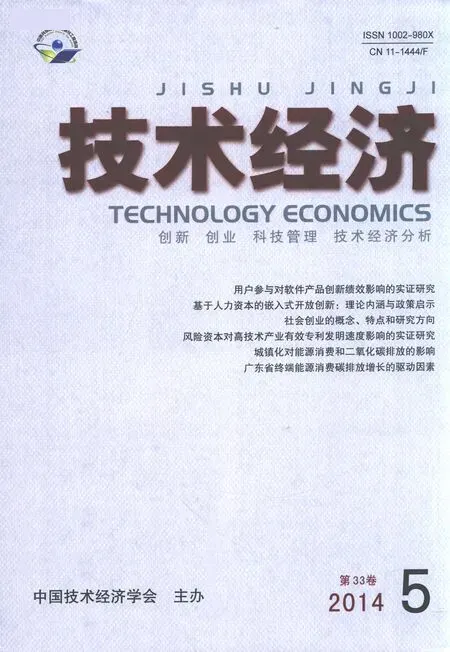創(chuàng)新環(huán)境對(duì)校企協(xié)同創(chuàng)新作用的實(shí)證分析
鄭艷民,張言彩
(1.南京理工大學(xué)經(jīng)濟(jì)與管理學(xué)院,南京210094;2.淮陰師范學(xué)院經(jīng)濟(jì)與管理學(xué)院,江蘇淮安223001)
校企協(xié)同創(chuàng)新是指企業(yè)與大學(xué)或科研院所進(jìn)行創(chuàng)新合作,這種合作意味著大學(xué)或科研院所要向企業(yè)傳遞有形或無形的技術(shù)知識(shí)。在這個(gè)知識(shí)傳遞過程中,大學(xué)和科研院所通常是知識(shí)創(chuàng)新的主體,而企業(yè)則是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主體。它們聯(lián)合開展創(chuàng)新活動(dòng)使得技術(shù)成果得以轉(zhuǎn)化為產(chǎn)品,進(jìn)而有效促進(jìn)了企業(yè)乃至整個(gè)地區(qū)的創(chuàng)新能力的提升。
大學(xué)通常被描述為“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引擎”,大學(xué)創(chuàng)造的知識(shí)和研究成果是企業(yè)產(chǎn)品創(chuàng)新的來源,在某些工業(yè)領(lǐng)域更是如此[1]。企業(yè)對(duì)新知識(shí)的渴求[2]、大學(xué)對(duì)財(cái)務(wù)經(jīng)費(fèi)的需求促使雙方相互依賴[3]——這也是兩者協(xié)同的強(qiáng)大驅(qū)動(dòng)力。政府和研究機(jī)構(gòu)正在尋求多種途徑促進(jìn)校企之間的協(xié)同創(chuàng)新,以期實(shí)現(xiàn)提升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能力、增強(qiáng)地區(qū)和國(guó)家的整體競(jìng)爭(zhēng)能力的目的。
有效執(zhí)行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核心和關(guān)鍵在于搭建協(xié)同創(chuàng)新平臺(tái)。協(xié)同創(chuàng)新平臺(tái)的建立不僅需要中央進(jìn)行財(cái)政投入,穩(wěn)定支持、培育具有產(chǎn)業(yè)技術(shù)綜合競(jìng)爭(zhēng)實(shí)力和較大產(chǎn)業(yè)化價(jià)值的研發(fā)組織,而且需要治理支持,加強(qiáng)與現(xiàn)有人才發(fā)展規(guī)劃、計(jì)劃和工程的銜接,吸引和聚集優(yōu)秀的創(chuàng)新人才,開展廣泛的國(guó)際國(guó)內(nèi)交流與合作。創(chuàng)新環(huán)境是區(qū)域內(nèi)部各要素在長(zhǎng)期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以增強(qiáng)創(chuàng)新能力為目的的、相對(duì)穩(wěn)定的網(wǎng)絡(luò)系統(tǒng),它包括基礎(chǔ)設(shè)施水平、勞動(dòng)力素質(zhì)、市場(chǎng)需求、金融環(huán)境和創(chuàng)業(yè)水平等要素。一個(gè)成熟的、完善的創(chuàng)新環(huán)境有助于協(xié)同創(chuàng)新平臺(tái)的創(chuàng)建,進(jìn)而影響協(xié)同創(chuàng)新能力的提升。
1 研究現(xiàn)狀
一般認(rèn)為,大學(xué)是知識(shí)創(chuàng)新系統(tǒng)中的執(zhí)行主體[4]。實(shí)際上,Adams[5]認(rèn)為,大學(xué)更像是一個(gè)探索性的組織者,它擁有強(qiáng)大的再組織能力,將來自市場(chǎng)和技術(shù)領(lǐng)域的知識(shí)整合在一起。大學(xué)的這種特性使得它理所當(dāng)然地成為參與企業(yè)R&D活動(dòng)、幫助企業(yè)生產(chǎn)創(chuàng)新性產(chǎn)品并保持可持續(xù)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的合作者。
大學(xué)除了承擔(dān)傳統(tǒng)的教書、育人的使命外,還應(yīng)該承擔(dān)“第三使命”——將自己與產(chǎn)業(yè)發(fā)展需要相聯(lián)系[6]。這種聯(lián)系的發(fā)生方式不盡相同,如表現(xiàn)為畢業(yè)生進(jìn)入產(chǎn)業(yè)領(lǐng)域就業(yè)、聯(lián)合產(chǎn)業(yè)研究項(xiàng)目、聯(lián)合申請(qǐng)專利或聯(lián)合出版等[7-8]。在這些聯(lián)系中,人們將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在校企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上,即雙方訂立和約、承諾共同進(jìn)行研發(fā)活動(dòng)。大量研究文獻(xiàn)關(guān)注大學(xué)和企業(yè)的特征對(duì)校企協(xié)同的影響。學(xué)者們提出了一系列影響和支持校企協(xié)同研究的基礎(chǔ)要素。例如:Veugelers和Cassiman[9]以比利時(shí)的748家制造業(yè)企業(yè)為研究樣本,通過研究證明了公司規(guī)模、行業(yè)類型、政府扶持和創(chuàng)新活動(dòng)的涉入度正向影響企業(yè)與大學(xué)建立R&D協(xié)同關(guān)系的意愿;Bercovitz和Feldman[10]檢驗(yàn)了公司的創(chuàng)新戰(zhàn)略對(duì)其與大學(xué)協(xié)同創(chuàng)新程度的影響,發(fā)現(xiàn)探索性行為和R&D活動(dòng)的集權(quán)式組織與企業(yè)與大學(xué)建立協(xié)同關(guān)系積極關(guān)聯(lián);與之類似,Laursen和Salter[11]認(rèn)為,采用開放性開發(fā)戰(zhàn)略和對(duì)R&D投入較多的公司更可能與大學(xué)建立協(xié)同關(guān)系。
從大學(xué)一方來看,創(chuàng)業(yè)導(dǎo)向、技術(shù)轉(zhuǎn)移辦公室(technological transfer official,TTO)的成立和效率、大學(xué)自主開辦的新公司和一些環(huán)境要素被認(rèn)為是影響它們與產(chǎn)業(yè)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的最重要因素①。制度規(guī)范、動(dòng)機(jī)、大學(xué)聲譽(yù)、中介機(jī)構(gòu)特征被認(rèn)為是使大學(xué)變得更具創(chuàng)業(yè)意識(shí)的要素[12-13]。TTOs是大學(xué)與產(chǎn)業(yè)建立關(guān)聯(lián)的一種正式方式,其效率取決于組織結(jié)構(gòu)和員工素質(zhì)、技術(shù)轉(zhuǎn)移機(jī)制、技術(shù)的本性和發(fā)展階段以及大學(xué)體制等環(huán)境要素[15]。大學(xué)自主創(chuàng)辦的公司被認(rèn)為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變革的關(guān)鍵驅(qū)動(dòng)力。就此而言,大學(xué)的科技政策、現(xiàn)有技術(shù)水平、團(tuán)隊(duì)運(yùn)行效率和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都積極影響校企協(xié)同的發(fā)展趨勢(shì)[16]。另外,創(chuàng)新網(wǎng)絡(luò)、科技園區(qū)的功能、企業(yè)孵化器的有無及其地理位置等環(huán)境要素也顯著影響大學(xué)與產(chǎn)業(yè)協(xié)同的意愿[17]。
盡管學(xué)者們對(duì)校企協(xié)同的研究興趣日益高漲,但是仍有一些問題需要關(guān)注,特別是大學(xué)等研究機(jī)構(gòu)研究目標(biāo)的偏離和研究產(chǎn)出的使用和分配不公。有人提出過分關(guān)注大學(xué)對(duì)產(chǎn)業(yè)需求的滿足將導(dǎo)致大學(xué)自由研究的喪失,會(huì)使大學(xué)的研究活動(dòng)變得日趨功利性,這導(dǎo)致企業(yè)過分追求為企業(yè)提供管理咨詢和解決實(shí)際問題,偏離大學(xué)既定的教書育人的目標(biāo)。另外,大學(xué)與企業(yè)聯(lián)合創(chuàng)新必然引發(fā)知識(shí)擴(kuò)散,一些企業(yè)將加強(qiáng)對(duì)創(chuàng)新成果的管理,以防止專利和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泄露。
就中國(guó)的校企協(xié)同創(chuàng)新而言,Motohashi[18]通過分析中國(guó)的專利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目前中國(guó)企業(yè)與大學(xué)的協(xié)同關(guān)系變得更加緊密,而與研究機(jī)構(gòu)的關(guān)系卻慢慢變得松散。Chen[19]研究了中國(guó)的專利產(chǎn)出,探索了校企合作對(duì)企業(yè)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貢獻(xiàn),發(fā)現(xiàn)校企合作創(chuàng)新能力在國(guó)家整體創(chuàng)新能力中占據(jù)重要位置,并進(jìn)一步比較分析了中國(guó)大學(xué)和美國(guó)大學(xué)在專利轉(zhuǎn)化上的差異。
目前國(guó)內(nèi)的協(xié)同創(chuàng)新研究處于起步階段。劉煒、樊霞和吳進(jìn)[20]結(jié)合國(guó)家自然科學(xué)基金委管理科學(xué)部認(rèn)定的30種管理科學(xué)重要學(xué)術(shù)期刊以及北京大學(xué)圖書館提供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08年版),選取了42種學(xué)術(shù)期刊為數(shù)據(jù)檢索源,對(duì)1992—2011年在這些期刊上發(fā)表的621篇學(xué)術(shù)論文進(jìn)行分析,發(fā)現(xiàn)目前還未出現(xiàn)成熟度較高的研究熱點(diǎn),博弈、績(jī)效和聯(lián)盟是目前的研究熱點(diǎn)。
專利是反映技術(shù)創(chuàng)新能力的重要指標(biāo),表征著一國(guó)和地區(qū)技術(shù)市場(chǎng)的發(fā)達(dá)程度,反映了一國(guó)和地區(qū)的科技競(jìng)爭(zhēng)力,它是增強(qiáng)企業(yè)核心競(jìng)爭(zhēng)力的核心要素。鑒于此,一些學(xué)者在研究校企協(xié)同創(chuàng)新時(shí)使用專利數(shù)據(jù)庫中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但是,他們大多關(guān)注知識(shí)流動(dòng),而研究國(guó)家和地區(qū)層面的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文獻(xiàn)較少。本文借助國(guó)家專利局的專利數(shù)據(jù)庫,從國(guó)家層面解讀校企協(xié)同創(chuàng)新與國(guó)家創(chuàng)新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
2 研究設(shè)計(jì)及數(shù)據(jù)來源
章立軍[21]基于Porter的創(chuàng)新體系結(jié)構(gòu)理論,認(rèn)為創(chuàng)新環(huán)境的五大組成要素包括基礎(chǔ)設(shè)施水平、勞動(dòng)力素質(zhì)、市場(chǎng)需求、金融環(huán)境和創(chuàng)業(yè)水平。在創(chuàng)新能力體系研究中,創(chuàng)新能力與創(chuàng)新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是其重要內(nèi)容。總體來說,學(xué)者們[22]對(duì)于創(chuàng)新環(huán)境對(duì)協(xié)同創(chuàng)新能力的正向促進(jìn)作用已達(dá)成一致。隨著以高科技為特征的信息化的發(fā)展,高等院校成為培養(yǎng)高科技人才的重要基地。同時(shí),大部分高校教師不僅是高精尖的科技人才,而且肩負(fù)著教育、培養(yǎng)中國(guó)高級(jí)人才的重任,是中國(guó)科研活動(dòng)、創(chuàng)新活動(dòng)的主體。由此,本文認(rèn)為協(xié)同創(chuàng)新效果受到高校人才培養(yǎng)質(zhì)量和本校教師創(chuàng)新活動(dòng)的影響。市場(chǎng)需求是企業(yè)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重要推動(dòng)力之一,企業(yè)會(huì)根據(jù)自身經(jīng)營(yíng)對(duì)技術(shù)的需求適時(shí)地開展創(chuàng)新活動(dòng),這些創(chuàng)新活動(dòng)有利于企業(yè)形成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同時(shí),企業(yè)亦由于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和獲得超額利潤(rùn)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開展研發(fā)創(chuàng)新活動(dòng)。這一切基于需要的內(nèi)在動(dòng)力,促使企業(yè)積極尋找高等院校作為合作伙伴,進(jìn)行協(xié)同創(chuàng)新活動(dòng)。創(chuàng)新活動(dòng)總是伴隨著大量資金投入、需要金融系統(tǒng)的支持,因此,金融環(huán)境優(yōu)越、越有利于系統(tǒng)創(chuàng)新活動(dòng)的開展,協(xié)同創(chuàng)新能力越強(qiáng)。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shè):
創(chuàng)新環(huán)境越優(yōu)越,校企協(xié)同創(chuàng)新能力(用聯(lián)合申報(bào)專利表征)越強(qiáng)。
專利數(shù)據(jù)已成為公認(rèn)的衡量創(chuàng)新能力的主要指標(biāo)之一,Margherita和Andrea[23]也將其用于測(cè)量校企創(chuàng)新能力。基于此,本文也采用校企聯(lián)合申請(qǐng)專利數(shù)(PUE)作為因變量。由于專利數(shù)據(jù)具有申請(qǐng)流程面向公眾全面放開、管理過程標(biāo)準(zhǔn)化、時(shí)序性較好的優(yōu)點(diǎn),因此本文先對(duì)國(guó)家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局的數(shù)據(jù)庫進(jìn)行檢索以建立二次數(shù)據(jù)庫,再利用二次數(shù)據(jù)庫中的數(shù)據(jù)進(jìn)行研究。筆者下載了1991—2012年期間的校企聯(lián)合申請(qǐng)專利,具體操作過程如下:在國(guó)家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局網(wǎng)站上的“專利檢索與服務(wù)系統(tǒng)”的表格檢索入口輸入“專利申請(qǐng)人”一欄輸入“大學(xué)(學(xué)院、學(xué)校)and公司”,所得的檢索條目包括公開號(hào)、申請(qǐng)?zhí)枴⒐_日、申請(qǐng)人、分類號(hào)和發(fā)明人等;利用得到的檢索條目建立二次數(shù)據(jù)庫,二次數(shù)據(jù)庫中不包括國(guó)外校企合作在中國(guó)申請(qǐng)的專利、其他研究院所和企業(yè)合作申請(qǐng)的專利以及公司已宣告破產(chǎn)前與高等院校聯(lián)合申請(qǐng)的專利。
創(chuàng)新環(huán)境指標(biāo)的選擇基于如下假設(shè):創(chuàng)新能力取決于基礎(chǔ)設(shè)施水平、政府支持、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人力資本和市場(chǎng)制度等創(chuàng)新環(huán)境要素。鑒于很難直接測(cè)度創(chuàng)新環(huán)境指標(biāo),本文借鑒戴淑芬、張亦楠和于婧[24]的做法,采用間接指標(biāo)反映創(chuàng)新環(huán)境:
①政府支持力度(SG)。用政府科技三項(xiàng)經(jīng)費(fèi)占財(cái)政支出的比重測(cè)量該指標(biāo)。
②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特征(SI)。用輕工業(yè)產(chǎn)值占工業(yè)總產(chǎn)值比重衡量該指標(biāo),該指標(biāo)反映了一個(gè)地區(qū)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和集群結(jié)構(gòu)的特點(diǎn)以及工業(yè)結(jié)構(gòu)對(duì)創(chuàng)新能力的效應(yīng)。一般來說,輕工業(yè)的創(chuàng)新發(fā)生頻率高于重工業(yè),輕工業(yè)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周期短于重工業(yè)。
③人力資本條件(HC)。用教育經(jīng)費(fèi)占當(dāng)?shù)谿DP比重衡量該指標(biāo)。校企協(xié)同創(chuàng)新活動(dòng)需要大量高素質(zhì)的科技人才參與,如此才能將知識(shí)轉(zhuǎn)化為創(chuàng)新生產(chǎn)力,因此,地方政府投入的教育經(jīng)費(fèi)越多,該地區(qū)的人力資源越豐富,參與創(chuàng)新活動(dòng)的人員越多,當(dāng)?shù)氐膭?chuàng)新能力就越強(qiáng)。
④市場(chǎng)制度(MI)。用貿(mào)易專業(yè)化指數(shù)(msi)表征該指標(biāo),貿(mào)易專業(yè)化=(出口額-進(jìn)口額)/(出口額+進(jìn)口額)。該指標(biāo)為正(或負(fù))值,表示貿(mào)易順差(或貿(mào)易逆差)。該指數(shù)值越小,表示企業(yè)越可能通過參與國(guó)際貿(mào)易獲得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知識(shí)和先進(jìn)技術(shù)。
上述創(chuàng)新環(huán)境變量均為比例或比率形式,其描述性統(tǒng)計(jì)結(jié)果如表1所示。
本文的數(shù)據(jù)來源為政府官方公布的相關(guān)資料,主要包括《中國(guó)統(tǒng)計(jì)年鑒》(2012)、《中國(guó)科技統(tǒng)計(jì)年鑒》(2001—2012)、《中國(guó)高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統(tǒng)計(jì)年鑒》(2002—2012)。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jì)結(jié)果
3 回歸分析
基于第2章中提出的研究假設(shè)——?jiǎng)?chuàng)新環(huán)境越優(yōu)越,校企協(xié)同創(chuàng)新能力越強(qiáng),本文構(gòu)建如下創(chuàng)新環(huán)境對(duì)校企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作用模型:

其中:yPUE為校企聯(lián)合申請(qǐng)專利數(shù);xSG為政府科技三項(xiàng)經(jīng)費(fèi)占財(cái)政支出比重;xSI為輕工業(yè)產(chǎn)值占工業(yè)總產(chǎn)值比重;xMI為貿(mào)易專業(yè)化指數(shù)。
在具有多個(gè)變量的多元線性回歸方程中,各變量之間存在嚴(yán)重的多元共線性將直接影響回歸結(jié)果的精確性。鑒于此,本文首先對(duì)以上5個(gè)變量進(jìn)行相關(guān)性分析,結(jié)果如表2所示。從表2可以看出,除了人力資本條件變量(HC)與其他變量顯著相關(guān)外,其余變量之間的相關(guān)性并不非常嚴(yán)重。因此,在建立回歸方差時(shí)剔除了變量HC。各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值(見表3)也說明,變量之間的共線性在可接受范圍內(nèi)。

表多元回歸方程中變量的相關(guān)系數(shù)
創(chuàng)新環(huán)境對(duì)校企協(xié)同創(chuàng)新作用的回歸結(jié)果如表3所示。從表3可知,政府支持力度(S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特征(SI)和市場(chǎng)制度(MI)對(duì)校企聯(lián)合申請(qǐng)專利數(shù)(PUE)有正向的促進(jìn)作用。其中,政府科技三項(xiàng)經(jīng)費(fèi)占財(cái)政支出比重每增加1%,校企聯(lián)合申請(qǐng)專利增加35.9件;輕工業(yè)產(chǎn)值占工業(yè)總產(chǎn)值比重每增加1%,校企聯(lián)合申請(qǐng)專利增加89.1件;貿(mào)易專業(yè)化指數(shù)每增加1%,校企聯(lián)合申請(qǐng)專利增加23.1件。

表3 創(chuàng)新環(huán)境與校企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回歸結(jié)果
4 結(jié)語
本文利用1991—2010年中國(guó)的創(chuàng)新活動(dòng)數(shù)據(jù),構(gòu)建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實(shí)證分析了創(chuàng)新環(huán)境因素對(duì)以校企聯(lián)合申報(bào)專利數(shù)表征的校企協(xié)同創(chuàng)新產(chǎn)出的影響。檢驗(yàn)結(jié)果顯示:政府支持力度(S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特征(SI)和市場(chǎng)制度(MI)對(duì)校企協(xié)同創(chuàng)新產(chǎn)出(PUE)有正面的促進(jìn)作用。總體來看,校企協(xié)同創(chuàng)新能力(用聯(lián)合申報(bào)專利測(cè)量)受外界創(chuàng)新環(huán)境要素的影響,國(guó)家創(chuàng)新環(huán)境的完善有助于促進(jìn)校企協(xié)同創(chuàng)新。然而,與本文的實(shí)證研究結(jié)果相悖的是,表征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特征的輕工業(yè)產(chǎn)值占工業(yè)總產(chǎn)值比重卻逐年下降——由1991年的48.8%下降至2010年的28.64%。可見,中國(guó)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仍需調(diào)整,以支持企業(yè)與大學(xué)之間協(xié)同創(chuàng)新活動(dòng)的開展。
本文的研究不足在于:受限于數(shù)據(jù)的可得性,本文僅對(duì)政府支持力度(S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特征(SI)和市場(chǎng)制度(MI)與校企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關(guān)系進(jìn)行了研究。在未來研究中,應(yīng)盡量多地考慮各種環(huán)境要素與校企協(xié)同創(chuàng)新產(chǎn)出的關(guān)系,并就其交互性進(jìn)行深入探討。
[1]龐文,韓笑.高校R&D與區(qū)域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關(guān)系的實(shí)證研究[J].技術(shù)經(jīng)濟(jì),2010(11):30-36.
[2]SCHARTINGER D,RAMMER C,F(xiàn)ISCHER M M,et al.Knowledge interaction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y in Austria:sectoral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J].Research Policy,2002,31(3):303-328.
[3]GEISLER E.Industry-university technology cooperation:a theory of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J].Technology Analysis &Strategic Management,1995,7(2):217-229.
[4]AGRAWAL A K.University-to-industry knowledge transfer:literature review and unanswered quest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2001,3(4):285-302.
[5]ADAMS S B.Stanford and Silicon Valley:lessons on becoming a high-technology region[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05,48(1):29-51.
[6]ROTHAERMEL F T,AGUNG S D,JIANG L.Un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a taxonomy of the literature[J].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07,16(4):691-791.
[7]王文亮,劉巖.校企合作創(chuàng)新網(wǎng)絡(luò)運(yùn)行機(jī)制調(diào)查分析——以河南省為例[J].技術(shù)經(jīng)濟(jì),2011(8):32-38.
[8]GIULIANI E,MORRISON A,PIETROBELLI C,et al.Who are the researchers that are collaborating with industry?An analysis of the wine sectors in Chile,South Africa and Italy[J].Research Policy,2010,39(6):748-761.
[9]VEUGELERS R,CASSIMAN B.R&D cooperation between firms and universities:som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Belgian manufactur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05,23(5/6):355-379.
[10]BERCOVITZ J E L,F(xiàn)ELDMAN M P.Fishing upstream:firm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university research alliances[J].Research Policy,2007,36(7):930-948.
[11]LAURSEN K,SALTER A.Searching high and low:what types of firms use universities as a source of innovation?[J].Research Policy,2004,33(8):1201-1215.
[12]陳勁,陽銀娟.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驅(qū)動(dòng)機(jī)理[J].技術(shù)經(jīng)濟(jì),2012(8):6-11.
[13]GAUGHAN M,CORLEY E A.Science faculty at US research universities:the impacts of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affiliation and gender on industrial activities[J].Technovation,2010,30(3):215-222.
[14]ANDERSON T R,DAIM T U,LAVOIE F F.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J].Technovation,2007,27(5):306-318.
[15]BERCOVITZ J,F(xiàn)ELDMAN M.Entpreprenerial universitie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knowledge-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06,31(1):175-188.
[16]DI GREGORIO D,SHANE S.Why do some universities generate more start-ups than others?[J].Research Policy,2003,32(2):209-227.
[17]LINK A N,SCOTT J T.Opening the ivory tower's door:an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formation of U.S.university spin-off companies[J].Research Policy,2005,34(7):1106-1112.
[18]MOTOHASHI K.Catching up or lagging behind?Assessment of technological capacity of China by patent database[J].China Economic Journal,2009,2(1):1-24.
[19]CHEN S H.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foreign R&D:the case of Taiwan[J].R&D Management,2007,37(5):441-453.
[20]劉煒,樊霞,吳進(jìn).我國(guó)產(chǎn)學(xué)研協(xié)同創(chuàng)新研究的文獻(xiàn)計(jì)量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3(1):9-14.
[21]章立軍.創(chuàng)新環(huán)境、創(chuàng)新能力及全要素生產(chǎn)率——基于省際數(shù)據(jù)的經(jīng)驗(yàn)證據(jù)[J].南方經(jīng)濟(jì),2006(11):43-56.
[22]PONDS R,OORT F V,F(xiàn)RENKEN Y K.Innovation,spillovers and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an extended knowledge 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0(10):231-255.
[23]MARGHERITA B,ANDREA L.University-industry interactions in applied research:the case of microelectronics[J].Research Policy,2006,35(10):1616-1630.
[24]戴淑芬,張亦楠,于婧.我國(guó)區(qū)域創(chuàng)新環(huán)境省際差異——基于面板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研究[J].技術(shù)經(jīng)濟(jì),2012(8):12-18.
- 技術(shù)經(jīng)濟(jì)的其它文章
- 小企業(yè)信用評(píng)價(jià)體系構(gòu)建方法——基于顯著性判別原理①
- 產(chǎn)業(yè)技術(shù)創(chuàng)新實(shí)現(xiàn)路徑的“黑箱”過程——基于路徑依賴視角的分析
- 政府財(cái)政行為對(duì)勞動(dòng)收入占比的影響——基于2004—2011年中國(guó)省級(jí)面板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分析
- 國(guó)際外包影響因素的實(shí)證研究——基于測(cè)算方法的差異
- 城鎮(zhèn)化對(duì)能源消費(fèi)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基于1995—2011年中國(guó)省級(jí)面板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研究
- 廣東省終端能源消費(fèi)碳排放增長(zhǎng)的驅(qū)動(dòng)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