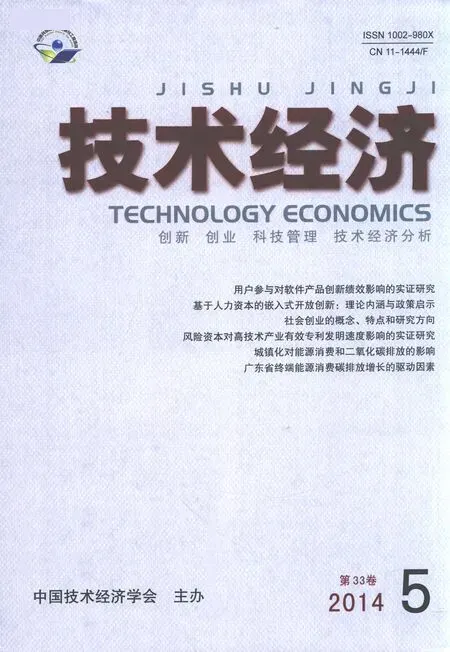組織學習能力、雙元性創新與企業績效間關系的實證研究①
張徽燕,何 楠,高遠輝
(電子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成都611731)
在高速變化的信息時代,組織學習能力是一個企業生存的基礎和發展的動力[1]。組織要想在未來競爭中獲得有利地位,需要做到:第一,所擁有的知識多于其競爭者;第二,擁有比其競爭對手更高的組織學習能力[2]。組織學習能力是收集、整合和加工知識,進而轉化為實際運用的能力,體現在組織創新過程中。組織創新包括探索性式創新和利用性創新(即雙元性創新)。探索性創新是一種大幅度、不依靠現有知識和技術基礎的革新性的創新,其目的在于得到突破性的變化[3-4];利用性創新是一種幅度小、依靠現有知識和技術基礎的漸進性的創新,其目的在于改進目前現狀[5]。
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經濟中,如果企業不思進取、不重視組織學習能力的培養,那么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我國企業已逐漸意識到,要想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要想使組織能在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就要不斷提高組織的學習能力,通過不斷積累學習組織內外部知識來充分提升自身的創新能力[6]、實現探索性創新和利用性創新,最終促進企業績效不斷提高。
以往研究主要圍繞組織學習能力和雙元性創新兩個方面各自展開,極少涉及組織學習能力、雙元性創新與企業績效的關系。組織學習能力如何影響雙元性創新,進而對企業績效發生作用?在動態環境下,這種作用過程和力度是否會發生變化?本文運用中國企業樣本對上述問題進行實證研究,以期揭示組織學習能力與企業績效的關系。
1 文獻回顧
1.1 組織學習能力與雙元性創新
組織學習能力是組織作為一個整體不斷獲取知識、改善自身行為和優化組織體系以在不斷變化的內外環境中實現可持續生存和保持健康、和諧發展的能力[7]。組織學習能力由發現、發明、選擇、執行、推廣、反思、獲取、輸出和知識管理等能力組成。進一步而言,組織學習能力是組織學習發現和選擇機會的能力以及獲取和分享知識的能力。通過組織學習從內部和外部獲得和創造新的技術、知識,通過整合機制將技術、知識的管理與企業的發展戰略相聯系,如此能夠培養出更強的創新能力[8]。顯然,組織學習能力是實現創新的要素之一,尤其在知識密集型產業中組織學習能力的作用更為明顯[9]。
雙元性創新中的探索性創新是幅度大、激進的一種創新行為,其目的是為了實現突破性變化。企業要不斷改變目前狀況、提高自身競爭力,就需要通過探索來開發新產品和開拓新市場等[10-12]。探索性創新就是搜索、變異、試驗和冒險,具有投入大、高風險和高回報的特性。利用性創新更多的是在原有基礎上進行改進,是對原有知識和資源的再利用。相對于探索性創新,利用性創新的成本較少、回報較少。然而,探索性創新和利用性創新對于企業而言均是必不可少的,兩者相結合才能得到更好的組織創新效果。探索性創新和利用性創新均與組織學習能力密切聯系,都需要獲取、整合、消化和吸收知識才能實現,組織學習能力對組織績效的影響更多的是通過影響探索性創新和利用性創新來實現的。
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組織學習能力與雙元性創新顯著正相關(H1);
組織學習能力與探索性創新顯著正相關(H1a);
組織學習能力與利用性創新顯著正相關(H1b)。
1.2 組織學習能力與企業績效
企業要想在競爭中獲得有利地位,往往需要做到以下3點:需要提供更出色的顧客價值;需要創新;需要建立組織學習系統,并培養能發展多種運用的能力[13]。企業的組織學習能力越強,做到上述三方面的可能性就越大。組織學習能力是衡量一個組織的有效性、創新性及成長潛力的重要指標[14]。具有較強組織學習能力的企業在面對復雜的外部環境時總能使內部或員工對新信息的理解達成一致,從而有利于企業更有效地實施方案[15]。學習型企業不斷分析、探討企業績效所反饋的內容,通過改正不足之處來更好地促進企業績效的提高。市場機會始終存在,然而并非人人都能獲得,這取決于企業是否及時發現機會、恰當地選擇機會并有效配置企業資源。組織的學習能力也反映了組織在學習承諾、分享愿景和開放心智上的程度,這種程度越高,企業從外界吸收的知識就越多,企業越能適應甚至預測環境的變化[16]。
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組織學習能力與企業績效顯著正相關(H2)。
1.3 雙元性創新與企業績效
組織創新的內容包括產品創新、服務創新和流程創新等,不同學者基于不同的理論和視角對組織創新進行了不同的劃分。按照創新的程度和幅度,組織創新可劃分為探索性創新和利用性創新。盡管探索性創新與利用性創新的著眼點不同,且兩者在組織內部會產生資源爭奪,但是現實中的確存在探索和利用活動能夠在一個組織內部共存的情況。Cac和Gedajlovic的研究表明,兩者之間存在既矛盾(雙元性平衡)又統一(雙元性交互)的關系[17]。研究表明:雙元性創新與銷售快速增長顯著相關[18];企業的雙元性創新顯著影響其創新績效[12];同時開展探索性創新活動和利用性創新活動的企業較不開展這兩類活動的企業具有更強的生產能力和更好的財務績效,并且這些創新活動能夠有效提高組織的學習和創新能力[19]。探索性開發活動和利用性開發活動的相互協同集成所帶來的競爭優勢,遠遠超越了單純進行探索性或利用性開發活動所取得的競爭優勢。
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雙元性創新與企業績效顯著正相關(H3)。
1.4 雙元性創新的中介作用
企業要將學習到的新知識進行實際運用,需要具備對新知識進行收集、整合和加工的創新能力,這種創新能力集中表現為探索性創新能力和利用性創新能力。企業通過提高組織學習能力、學習現有知識以及不能被明確表達的隱性知識[20],可以提高探索性創新和利用性創新的水平,進而促進企業績效的大幅增長。
企業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中只有充分運用組織學習能力,準確地發現并識別知識源,并根據知識的不同特性選擇最佳的知識獲取方式和分享路徑,才能很好地利用內外部知識來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6];企業通過有效開展創新活動來促進新思想、新產品、新服務和新技術的產生,并利用內外部的各種渠道使之進入市場以實現商業化,從而實現企業績效的提升。
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雙元性創新在組織學習能力與企業績效之間發揮中介效應(H4)。
1.5 環境的動態調節作用
動態的環境對雙元性創新提出更高要求。當外部環境變化大且競爭激烈時,企業開展雙元性創新活動比較頻繁,這更利于企業績效的提高[21]。企業面臨的環境越惡劣、外部競爭越激烈,環境對企業的影響就越大,此時企業開展雙元性創新的可能性越大[22]。環境因素對企業雙元性創新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企業的外部環境直接影響企業開展雙元性創新活動的可能性;企業的外部環境在組織學習能力與雙元性創新之間起調節作用;企業的外部環境在雙元性創新與企業績效之間起調節作用。
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環境動態性在組織學習能力和雙元性創新與企業績效之間起調節作用(H5)。
2 研究方法
2.1 問卷設計
本文引用成熟的國外量表度量組織學習能力、企業績效、雙元性創新和環境動態性。具體操作如下:首先,對國外量表進行回譯,以防止在使用成熟量表時存在翻譯不準確的問題;然后,通過討論來修改調查問卷;接著,在成渝兩地的生物、制藥和通信等行業選擇有代表性的企業進行調查問卷的預測試;最后,根據反饋和建議修改某些題項,在此基礎上形成最終的調查問卷。
2.2 數據收集
問卷填答者為在職或已畢業的MBA、EMBA、MPM、EDP、DBA班的學生。樣本來源于我國西南地區、東南地區和華北地區。由于本研究是組織層面的研究,因此針對一家企業發放一份調查問卷。為了保證問卷調查能準確地提供企業的雙元性創新、組織學習能力和企業績效等信息,要求問卷填答者必須為企業的中高層管理者。本次調研共回收問卷850份,剔除質量不合格(如存在過多缺失項目、作答不認真等)的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782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2%。
通過對782份有效問卷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發現:樣本企業涉及的行業包括電子/通信/計算機/軟件業、制造業、房地產業、能源/采掘業、醫藥/衛生業、金融/保險業、運輸/郵政/租賃業、教育/文化業以及批發和零售業等,其中以電子/通信/計算機/軟件業和制造業的企業為主,分別占20.2%和18%,兩者共占38.2%。在樣本企業中,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企業占33.8%,民營企業或民營控股企業占44.9%,兩者共占樣本總數的78.7%,因此樣本企業能較好地體現中國企業的特質;80.4%的樣本企業的成立時間在5年以上;79.1%的樣本企業處于成長階段或成熟階段;70.8%的樣本企業具有中等及以上規模,即200人以下的樣本企業占37%,201~500人的樣本企業占17.5%,501~1000人的樣本企業占12.1%,1001~2000人的樣本企業占11.5%,2001人以上的樣本企業占19.2%。從782份有效問卷中隨機抽取391份有效問卷(以下簡稱樣本1)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其余391份有效問卷(以下簡稱樣本2)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
2.3 變量測量
所用測量問卷均采用7點Likert量表進行打分,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合”,“7”代表“完全符合”,請被試者根據自己所在企業的情況判斷每個題項的符合程度。
1)組織學習能力。本文采用陳國權開發的組織學習能力量表測量組織學習能力[7]。該量表包括9項簡化條目,每個條目對應一個學習分能力。首先檢驗利用樣本1的數據是否能對組織學習能力的各題項做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為0.902,表明組織學習能力量表的各題項適合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從而得到較穩定的組織學習能力二因子結構——發現與選擇機會的能力和獲取與分享知識的能力,累積方差解釋率達到72.58%。然后利用樣本2的數據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指標結果如下:χ2/df=2.73;RMSEA=0.067;GFI=0.98;CFI=0.99;NFI=0.99。組織學習能力量表中各測量題項的因子載荷值都顯著,表明組織學習能力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
2)雙元性創新。采用He和Wong[18]開發的雙元性創新量表。該量表包括2個子維度——探索性創新和利用性創新。其中,探索性創新對應4個題項,分別是:①企業經常嘗試引進新產品(或服務)的生產方式;②企業經常嘗試增加新產品(或服務)種類;③企業經常嘗試開拓新的市場領域;④企業經常嘗試進入新的技術領域。利用性創新對應4個題項,分別是:①企業努力改進現有產品(或服務)的質量;②企業采取各種方式努力提高現有產品(或服務)的適應性;③企業采取各種方式努力降低現有產品(或服務)的生產成本;④企業采取各種方式努力提高現有產品的產量或提供更多的服務。首先檢驗利用樣本1的數據是否能對雙元性創新的各題項做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為0.86,表明雙元性創新量表的各題項適合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從而得到探索性創新和利用性創新兩個因子,累積方差解釋率達到74.23%。然后利用樣本2的數據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指標結果如下:χ2/df=3.96;RMSEA=0.089;GFI=0.94;CFI=0.97;NNFI=0.96。雙元性創新量表中各測量題項的因子載荷值都顯著,表明雙元性創新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
3)企業績效。本文主要借鑒Dyer和Reeves[23]、程德俊[24]和張方華[25]等的量表,從人力資源績效、財務績效和創新績效等維度綜合測量企業績效。首先檢驗利用樣本1的數據是否能對企業績效的各題項做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為0.86,表明企業創新量表的各題項適合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從而得到較穩定的企業績效三因子結構。然后采用樣本2的數據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指標結果如下:χ2/df=3.88;RMSEA=0.086;GFI=0.95;CFI=0.98;NNFI=0.97。企業績效量表中各測量題項的因子載荷值都顯著,表明企業績效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
4)環境因素。本文參考Miller和Friesen[26]以及Priem、Love和Shaffer[27]等的研究成果,從產品發展、市場變化和骨干員工流失3個維度衡量環境的動態性。
5)控制變量。本文主要參考Arthur[28]和Guthrie[29]等的研究,選取所有制性質、所屬行業、成立年限、生命周期、企業規模、員工數量和企業戰略作為控制變量。
3 實證結果
3.1 相關分析
各變量的Pearson相關系數值如表1所示。從表1可知:組織學習能力與企業績效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值為0.636(p<0.01);組織學習能力與雙元性創新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值為0.693(p<0.01);雙元性創新與企業績效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值為0.581(p<0.01)。

表1 變量的Pearson相關系數
3.2 回歸分析
為進一步驗證前文提出的假設,本文利用Baron和Kenney[30]提出的檢驗中介作用的方法,在考慮控制變量的影響下,采用逐步回歸方法對變量進行線性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表2中各模型變量的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值均在1~2之間,因此回歸分析過程不存在變量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第一步,分別以組織學習能力和企業績效作為因變量,輸入控制變量,從而形成模型1。模型1的回歸結果顯示:所有權性質、所屬行業、生命周期和企業規模對企業績效有顯著影響;成立年限、員工數量和企業戰略對企業績效沒有顯著影響。
第二步,在模型1的基礎上,即在考慮控制變量影響的情況下,再加入組織學習能力作為自變量,以企業績效作為因變量,從而形成模型2。模型2的回歸結果顯示:ΔR2的值顯著,F=72.037(P<0.001),組織學習能力對企業績效的標準化回歸系數β=0.621(P<0.001),即組織學習能力越高、企業績效越高,因此假設H2得到驗證。
第三步,以雙元性創新作為因變量,輸入控制變量,從而形成模型3;在模型3的基礎上,再加入自變量組織學習能力,從而形成模型4。對比模型4與模型3可知,在加入自變量組織學習能力后,因變量的解釋力顯著增強,組織學習能力的標準化回歸系數β=0.669(P<0.001),即企業的組織學習能力越強、員工的雙元性創新水平越高,從而假設H1得到驗證。
第四步,在考慮控制變量的情況下,以企業績效作為因變量,輸入中介變量雙元性創新,從而形成模型5。模型5的回歸結果顯示:ΔR2值顯著,F=57.284(P<0.001),雙元性創新對企業績效的標準化回歸系數β=0.585(P<0.001),表明雙元性創新對企業績效具有正向影響,從而假設H3得到驗證。
第五步,在考慮控制變量和自變量組織學習能力的情況下,以企業績效作為因變量,輸入中介變量雙元性創新,從而形成模型6,以驗證雙元性創新的中介作用。通過對比模型6與模型2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加入雙元性創新變量后,組織學習能力對企業績效的標準化回歸系數由β=0.621(P<0.001)變為β=0.451(P<0.001)。雖然回歸系數依然顯著,但是數值有所下降,即雙元性創新在組織學習能力與企業績效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從而驗證了假設H4。

表2 雙元性創新為中介的回歸分析結果
3.3 環境動態性的調節效應
在考慮控制變量的情況下,以企業績效為因變量,分別引入中介變量雙元性創新的子維度——探索性創新與調節變量環境動態性的乘積項以及利用性創新與調節變量環境動態性的乘積項,最終分別形成模型7和模型8,其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模型7的回歸結果顯示,探索性創新與環境動態性的乘積項對企業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26,P<0.001),表明環境動態性在探索性創新與企業績效之間確實起到正向的調節作用。模型8的回歸結果顯示,利用性創新與環境動態性的乘積項對企業績效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314,P<0.001),即環境動態性在利用性創新與企業績效之間起到正向的調節作用。綜上,假設5得到驗證。
4 結語
本研究結果表明:第一,組織學習能力對雙元性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第二,組織學習能力對企業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與Dess和Bell的研究結果一致,即組織學習能力的提高能夠引導和促進企業績效提升;第三,雙元性創新對企業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企業的雙元性創新能力越強、企業績效越高;第四,雙元性創新在組織學習能力與企業績效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五,環境動態性在組織學習能力、雙元性創新與企業績效之間起到正向調節作用。
本研究的理論意義在于:首先,為組織學習能力對企業績效作用機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證據,同時驗證了前人研究成果在中國情境下的適用性,為揭開組織學習能力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黑箱”做出了貢獻;其次,以探索性創新和利用性創新為切入點,探討了組織學習能力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及其中介作用的實現方式,是一種更為系統化的研究思維,豐富了探索性創新和利用性創新的相關研究;再次,雙元性創新在組織學習能力與企業績效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進一步說明開展探索性創新和利用性創新能使企業獲取更高的績效;最后,本研究發現探索性創新和利用性創新對企業績效的提升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本研究的實踐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本研究結果表明,提高組織學習能力有助于企業績效的提高。企業提高組織學習能力可在財務績效、人力資源績效和創新績效3個方面獲得相應的回報,因此企業管理者在管理方式上應與國際企業的管理方式接軌,重視企業組織學習能力的培養,注重提升發現與選擇機會的能力和獲取與分享知識的能力。例如:在外部環境不斷變化的情況下,組織需要培養能夠給企業帶來機遇與挑戰的能力;當外部環境快速發展時,組織需要培養具有對新措施和方案進行優化和選擇的能力等。
第二,本研究可幫助企業管理者深入理解促進雙元性創新的方法。在復雜多變的競爭社會環境中,如何提高組織整體的創新能力是企業管理人員面臨的重要課題。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組織學習能力能夠顯著影響雙元性創新,同時雙元性創新在組織學習能力影響企業績效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中介作用。從管理實踐角度講,雙元性創新是企業獲取競爭力的源泉,有效提高組織學習能力既是促進創新發展的重要方法,也是提高企業績效的重要途徑。企業應針對不同的發展階段與需求,注意把握、調整探索性創新與利用性創新的平衡關系,以達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第三,本研究揭示了環境的動態性對企業而言既是壓力也是動力。企業只有不斷學習才能不斷推動創新,從而培育并形成動態競爭能力,才能對動態的、不確定的環境變化做出迅速反應;企業只有不斷增強組織學習能力,才能更易獲取各種知識和資源,進而創造機會和價值,最終不斷促進企業績效的提高。
[1]FULMER R M.A model for changing the way organizations learn[J].Planning Review,1994,22(3):20-26.
[2]SENGE M P.The Fifth Discipline.Doubleday[M].Beijing:China CITIC Press,1990:16-89.
[3]LEVINTHAL D A,MARCH J G.The myopia of learning[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3,14(S2):95-112.
[4]BENNER M J,TUSHMAN M L.Process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photography and paint industries[J].Administration Science Quarterly,2002,47(4):676-706.
[5]LEWIN A Y,LONG C P,CAROLL T N.The coevolution of new organizational forms[J].Organization Science,1999,10(5):535-550.
[6]林向義,羅洪云,紀鋒,等.企業開放式創新中外部知識獲取能力評價[J].技術經濟,2013,32(7):18-23.
[7]陳國權.組織學習和學習型組織:概念、能力模型、測量及對績效的影響[J].管理評論,2009,21(1):107-116.
[8]HITT M A,IRELAND R D,LEE H.Technological learning,knowledge management,firm growth and performance[J].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0,17(3):231-246.
[9]STAT R.Organizational learning:the key to management innovation[J].Sloan Management Review,1989,30(3):63-74.
[10]DANNEELS E.The dynamics of product innovation and firm competences strategic[J].Management Journal,2002,23(12):1095-1121.
[11]JANSEN J P,VAN DEN BOSCH F A J,VOLBERDA H W.Exploratory innovation,exploitative innovation,and performance: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 and environmental moderators[J].Management Science,2006,52(11):1661-1674.
[12]BENNER M J,TUSHMAN M L.Exploitation,exploration,and process management:the productivity dilemma revisited[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3,28(2):238-256.
[13]DAY G S.The capabilities of market-driven organizat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1994,58(4):37-52.
[14]JEREZ-GóMEZ P,CéSPEDES-LORENTE J,VALLECABRERA R.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apability:aproposal of measurement[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5,58(6):715-725.
[15]DESS G.Measuring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 the absence of objective measures:the case of the privately held firm and conglomerate business unit[J].Strategic Manage,1984(5):265.
[16]王鐵男.組織學習、戰略柔性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J].管理科學學報,2010,13(7):42-60.
[17]CAO Q,GEDAJLOVIC E,ZHANG H.Unpacking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dimensions,contingencies,and synergistic effects[J].Organization Soienc,2009,20(4):781-796.
[18]HE Z,WONG P K.Exploration vs exploitation: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ambidexterity hypothesis[J].Organization Science,2004,15(3):481-494.
[19]ADLER P,BORY S B.Two types of bureaucracy:enabling and coercive[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6,41(1):61-89.
[20]何郁冰,曾益.開放式創新與企業競爭優勢間關系研究書述評[J].技術經濟,2012,31(12):28-32.
[21]VAN LOOY B,MARTENS T,DEBACKERE K.Organizing for continuous innovation: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s[J].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5,4(3):208-221.
[22]JANSEN J P,VAN DEN BOSCH F J,VOLBERDA H W.Exploratory innovation,exploitative innovation,and ambidexterity: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and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J].Schmalenbach Business Review,2005,57(11):351-363.
[23]DYER L,REEVES T.Human resource strategies and firm performance:What do we know and where do we need to go?[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1994,6(3):656-670.
[24]程徳俊.高績效工作系統對企業績效的作用機制研究——組織信任的中介作用[J].軟科學,2011,25(4):96-105.
[25]張方華.知識型企業的社會資本與技術創新績效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04.
[26]MILLER D,FRIESEN P.Strategy-making and environment:the third link[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3,4(3):221-235.
[27]PRIEM R L,LOVE L G,SHAFFER M A.Executives’perception of uncertainty sources:a numerical taxonomy and underlying dimensions[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2,28(6):725-746.
[28]ARTHUR J B.Effects of human resource systems on 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 and turnover[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4,37(3):670-687.
[29]GUTHRIE J P.High-performance work practices,turnover and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New Zaland[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1,44(1):180-190.
[30]BARON R M P,KENNY D A.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1(1):1173-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