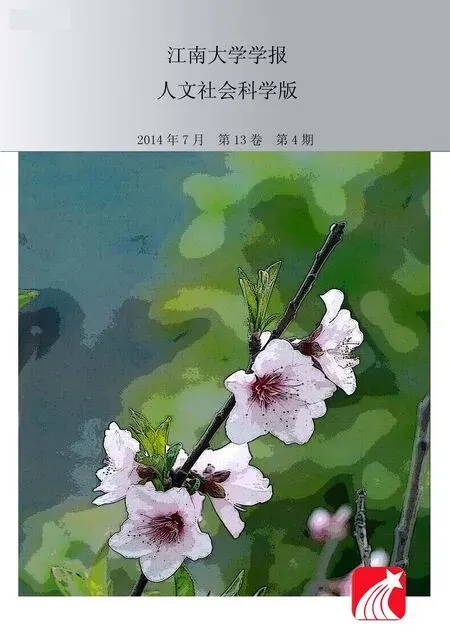從“直覺”到“理性”
——梁漱溟哲學方法論的轉向考察
陳永杰
(江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無錫 214122)
梁漱溟用力于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和選擇世界文化的未來出路上,其長處是將與道德有關的直覺意蘊揭橥得較為清晰,對工具理性、理智之蔽的揭示準確到位。但由于其所理解的直覺傾向于本能,德性成了先天具足、已然完成的東西,導致儒家仁智勇并舉的修身進路中的智與勇付之闕如。其后,他發現了問題所在,主動進行了理論轉向。轉向后的梁漱溟揚棄了柏格森生命哲學和泰州學派中強調本能沖動的方面,融進了儒家的理性的內容,這是其哲學方法論轉向的關鍵。這種轉向客觀上也推進了中國近代哲學。然而,從學理上來考察,其方法論依然存在較多弊病和缺憾。與其說這種方法論轉向是理性分析的結果,不如說是一種信仰、情感的偏執和對傳統文化的眷戀。
一、即體即用的本能直覺
依照梁漱溟,東西方文化的對立實為直覺與知性的對峙,知性思維、工具理性的片面發展是造成西方文化危機的根源,惟有直覺的生活才符合生命本性,因此需要直覺來救治。所以,其哲學方法論是以顯揚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為旨歸,表現出了對傳統的依戀和對現代性價值的置疑。就探尋人類自身存在意義的方法而言,在梁漱溟那里,直覺即本體即方法,是本體與方法的一體化;直覺既是本體即價值之源,亦為通達形上本體的方法,“要認識本體非感覺理智所能辦,必方生活的直覺才行,直覺時即生活時,渾融為一個,沒有主客觀的,可以稱絕對。”[1]406。顯然,直覺被梁漱溟提高到了本體論的高度,賦予了本體的意義,成了超越的普遍的存在,也是人的行為的形上依據。
所謂“渾融一體”、“沒有主客的絕對”就是梁漱溟即本體即方法的直覺。本體論意義上的直覺,梁漱溟將其等同于儒家的道德本體——仁或良知良能,“孟子所說的不慮而知的良知,不學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們謂之直覺……此敏銳的直覺,就是孔子所謂仁。……人類所有一切諸德,本無不出自此直覺,即無不出自孔子所謂‘仁’,所以一個‘仁’就將種種美德都代表了。”[1]454儒家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被梁漱溟詮釋為“任直覺”、“隨感而應”,人遇事原不須你操心打量的,當下的隨感而應就是對的。顯然,依梁漱溟之見,人們的生活應該率性、順著本能去走,只要聽任直覺,從心所欲,就自然通達、流暢活潑。追問其思想出處,我們發現梁漱溟沿襲了“本能沖動即道德”的泰州學派思想,因此,經過他的現代轉化,直覺成了沿著這個理路,梁漱溟主張唯有直覺才可以體認宇宙的生命,內里生命與外面通氣的只有經直覺這個窗口。其直覺就又被賦予了方法論意義。依據梁漱溟,從直覺自身的規定性來說,直覺不同于現量(感覺)對事物純客觀的反映,也不同于比量(理智)對感覺所得進行分析綜合得到關于客觀對象的必然性知識。直覺中包含著主體的意味、感受、情趣、價值判斷等非理智的因素,相對于運用理智的方法得到的純客觀認識而言,直覺不是隔絕于經驗的感性規定,避免了存在成為缺乏現實品格的抽象存在。相反,直覺能將人理解為包含多方面規定的具體存在,所以,唯有直覺才是真正的玄學方法。過度依賴理智分析乃是誤入了唯科學主義的路徑,“宇宙的本體不是固定的靜體,是‘生命’、是‘綿延’,宇宙現象則在生活中之所現,為感覺與理智所認取而有似靜體的。直覺所得自不能不用語音文字表出來,然一納入理智的形式即全不對,所以講形而上學要用流動的觀念,不要用明晰固定的概念”[1]406。如果用理智的方法加以肢解分割、靜態地分析生命,那么所得只能是僵硬的、支離破碎的、毫無生趣的東西。
梁漱溟早期的哲學方法論受柏格森哲學影響頗深,梁漱溟激賞柏格森哲學,“邁越古人,獨辟蹊徑”,認為只有其才能與孔子的精神生活相比擬。柏格森繼承的是叔本華、尼采貶抑理性、頌揚直覺,認為理性只能認識凝固的物質概念,而萬物和人都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的表現。梁漱溟將柏格森的直覺方法和中國傳統哲學中的“仁(天理)”、“人欲”疊加起來,使直覺獲得了在柏格森那里所沒有的本體論意義和方法論意義,建立起了以道德情感為本體的形而上學。那么,直覺順理成章地不僅僅只是單純抽象理智的對立面,并且成了“良知良能”。[2]雖然梁漱溟也認可理智的價值,但主張理智本質上不是人的本質規定性,而是反本能的,并不能承當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不過是利用厚生之工具而已。他將近代以來出現的“精神迷失”、“存在困惑”、“意義危機”通通歸咎于理智的生活態度,只有復活儒家的直覺性的生活,使人生生趣盎然、生命深厚富有,才能克服近代人面臨的“精神迷失”。其所謂“以直覺的情趣解救理智的嚴酷”,正是此意。梁漱溟不遺余力地揭示理智方法的有限性,與他對科學主義的批評立場是一致的。
不難發現,梁漱溟具有自覺的方法論意識。他斷言哲學形而上學的方法只能是直覺,因為直覺不違背宇宙生命之真,所得非對象性的知識,體悟到的是一種形上境界。建立在實證科學基礎上的宇宙觀必然導致把宇宙看作外在于人的靜態實體,而實際上我們置身于其中的生活過程即為宇宙的內容,非此還有別的宇宙,這是一個活潑潑的、動態的、生生不息的創造性過程,是生命的發用流行。因此,直覺作為“玄學的方法”可以體悟生命的形上意義,體察“內里生命”的唯一通路。這種理解是梁漱溟的創見,富含理論價值。但可惜沒有深入細致地研究直覺本身,“始終只限于描寫直覺生活如何美滿快樂,未曾指出直覺如何是認識‘生活’及‘我’的方法”[3]。
二、對關于其本能直覺的批評
顯然,梁漱溟對直覺的這種本能式理解有濃厚的理想化意味。在本體論維度上,梁漱溟視直覺為一種與人的生命共同健動不息、活潑靈動的東西,即原初的善的本體。在方法論意義上,直覺也是體悟本體的方法,因為直覺所得異于抽象靜態的概念,是一種“活形勢”,能呈現宇宙生命的本性。這是一種道德形而上學的立場,目的是體悟德性的良知本體,而非客觀本體之真,依賴本能直覺就能直達德性本體。事實上,儒學既非一個狹義的知識論系統,亦非單純的思辨哲學,儒學所崇尚的與其說是如何思考,不如說是如何踐履、如何生活。在儒家那里,行動遠比思考重要,實踐高于知識,為人重于為學。儒家的目標是去體悟生活世界無限豐富的倫理道德意義,實現人生的理想追求,最終達到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作為當代新儒家的發軔者,梁漱溟亦未違背儒家哲學的基本關懷,所關注的也是直覺的實踐品格,強調直覺首先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具有實踐力的本能。應該說,就儒學的實踐性而言,梁漱溟的把握比較到位。
然而,進一步的問題是,梁漱溟只注意到了具備善本能的直覺銳敏地“隨感而應”,忽視了德性在實踐中的提升和進階,也遮蔽了理智的思辨以及各種具體情景下的修身工夫,那么,儒家的仁是先天具足的嗎?若如此,儒家的知就變得可有可無,修身的工夫將如何安放?在梁漱溟那里,直覺是本能的、已然完成的東西,直覺與理智相對峙而存在,憑人的自然本性率性而為美德就能實現,一切的惡都出于直覺的麻痹遲鈍。如此一來,我們發現,梁漱溟一開始就將反對唯科學主義與批判所謂“害仁”的理智當作同一回事來處理。這種做法本身還有諸多討論的余地。因為按照梁漱溟的邏輯,可以推出“無私欲”與“仁”是等同的,如是,其理論之蔽是將十分復雜的問題做了草率地簡單化處理。此說理由如下:其一,任直覺、無私欲只是成“仁”的充分條件,而不能自動成就“仁”;其二,“仁”是一種理想目標,人欲能否去盡、人欲是否都應該去除、人欲是否等同于惡?這些問題的復雜性說明不應把“去人欲”無批判無反省地等價為“仁”;其三,梁漱溟強調了“人欲”與“仁”不共戴天,去除了人欲也只是條件,道德良知不會自動發動人的行為,理想人格也不會自動實現,其間還需要很多工夫才能達到“仁”。其實,在儒家那里,把為“仁”的責任放在自己身上,用工夫從根本上消除惡之源,并不排斥理智,依靠內在領悟即“直覺”以及性情氣質的修養,通過日常踐履中的綜合,即知識、情感、意志、思考和價值追求的一體平鋪、活潑無礙,才是儒家經過工夫而通達良知本體的向善之路。
進而言之,在方法論的層面,梁漱溟對儒學的這種“純任直覺、隨感而應”的詮釋也與儒學體系存在諸多捍格之處。他將儒學的人性論理解為性善是既成的、絕對的,道德先天地存在于個體中,只要祛除“算計”的生活,不計較利害,回歸人的先天本能,“純任直覺”就能達到“仁”。事實上,人的德性自我只是一種潛在的可能性,而不是已然實現的東西,只有通過一系列轉化工夫過程,才能將其實現,其中起關鍵作用的轉化工夫就是修身。在先秦儒家那里,已明辨承認一個義務與能履行義務并非一事。儒家將修己的工夫非常緩慢艱苦,是個漫長細致的過程,甚至還要經歷生死的考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論語?學而》) 如此方能成就德性完善的圣賢君子。即便孔子也不敢輕言已具備德行,這充分說明儒家歷來重視成圣過程的艱辛并視之為人存在的方式,而并非梁漱溟所謂完全聽憑本能的直覺,自然就能不失規矩而“合天理”。
因此,梁漱溟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是直覺是否可以脫離理智而獨立存在?理智進行認識活動時產生的主客二分的確帶來割裂人的整體性之憂,但人恰好是在理智認知的過程中展現自身,呈現自我。德性之完成亦非單純的主觀內在性領域之事,必然要在“成己成物”、“開物成務”的理智的客觀性活動中才能實現。當然,固執于理智,產生的只是關于人的各種外在的規定性,人自身是被遮蔽的,這就需要通過直覺體悟來揚棄理智的各種規定性。但揚棄不意味著全盤拋棄,而是超拔出理智僵硬的規定性,復歸于人的本真。在這個意義上,直覺是對理智的揚棄和消解而復歸統一的過程,即消解理智和顯揚人的本真是一體之兩面,這也說明了直覺與理智處于一種統一的張力關系之中,都不可或缺。如果拋棄理智單純強調直覺體悟,就破壞了這種張力,變成獨斷論的變相。
三、轉向的動因
作為當然之則的天理不是通過理智計算出來的,這一點梁漱溟是有所見的。然而,早期的梁漱溟為了凸顯中西文化的差異,將是否運用理智上升為兩種文化的分水嶺。這個說法本身大可置疑。有學者就批評道,他為了為自己的文化哲學思想尋找方法論依據,因此過分壓抑了理智的作用,而隨意抬高了直覺的地位。在此兩者之間的褒貶抑揚清楚地反映了其理論創作上的偏頗隨意。 這種批評雖然稍顯嚴厲,卻有一定的說服力。因為,在梁漱溟看來,中國哲學是排斥理智的,視理智為人之所以被分離的根源,進而對象化的活動導致人之本真被遮蔽。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其目的是要以一種獨斷的方式說明:直覺為善,理智為惡。他大體上是把“惡”的起源歸結為理智,由于理智的分別作用而產生了物我、人我種種計較,私心人欲隨之而起,由此得出“人之不免于錯誤,由理智”的結論。
早期的梁漱溟主張人的本能沖動順暢流行發動就好,反對加以抑制摧殘,抑制本能會使人生缺乏活力,人生要順著本能欲望走。在受佛學唯識學的影響之后,梁漱溟漸漸發現了本能欲望的不自覺的一面,即其天然的盲目性、機械性和被動性。當人的欲望強烈之時,生死非所顧,更何談利害得失?也就是說,人生所有種種之苦皆從欲望來,必須去除本能欲望才消除了苦,達于徹底無欲之境。顯然,此時的梁漱溟對本能中蘊含著先天的善的觀念產生了動搖。當下的隨感而應卻導致人生的苦,是他始料未及的。這對鮮明的矛盾使梁漱溟意識到了過度強調直覺的先天本能這一度的缺陷所在,誠懇地進行了自我反省、擇善而從之,“單明孔家走一任直覺隨感而應的路還未是,而實于此一路外更有一理智揀擇的路,如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便是要從過與不及里揀擇著走。……前后這許多話我現在都愿意取消。現在更鄭重聲明,所有這一段話我今愿意一概取消。”“而我在此書中談到儒家那里,尤其喜用現在心理學的話為之解釋。自今看去,卻大半都錯了。”[5]321-324所謂的揀擇其實就是一種理智的分析和判斷工夫,這樣,原本就包含在儒家思想里的智的因素,在被梁漱溟簡單化地剔除之后又重新納入了其理論視野之中。
晚年的梁漱溟逐漸修正了自己的哲學方法論的疏漏,指出早年(寫作《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時期)同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義一樣只注意到了人們欲望的自覺層面。后來卻發現人也有不自覺的一面,認為“研究人類心理正應當向人們不自覺,不自禁,不容己……的那些地方注意。于是我乃大大看重了本能及其相應不離的感情沖動。”[5]603這可以看作是早期哲學方法論中非理性傾向的由來。梁漱溟承認自己濫以本能一派的心理學為依據,去解釋孔學上的觀念和方法論,卻大半都錯了。于此,他將早年對人性的論證劃歸為社會本能,屬于“自然我”的范疇,然后另立了與理智相對的“理性”概念,確立了人類生命體中“自然我”(本能)、“功利我”(理智)與“道德自我”(理性)三分的模式,以理性與理智來說明東西方文化之異,構建了“人之所以為人在于理性”的道德本體論。他認為這樣就既能堅持原有理論對良知本心的那種“情意之知”的理解,同時也清除了早期“直覺”觀念中混入“本能”的思想因素。這種理論上的變化可以視為梁漱溟對受歐洲大陸哲學中非理性主義及深層心理學影響之后的一種轉向,轉向其實就是一種回歸,回歸到了先秦儒家成就理想人格的仁智勇并舉的進路上。
此時的梁漱溟(寫作《人心與人生》時期)主張,理智是相對物理而言的,指認識客觀之理,而理性是指情理,偏于主觀;理性與理智是體與用的關系,從本能到理性的歷程中,必然要經過理智這一階段。“從生物進化史上看,原不過要走通理智這條路者,然積量變而為質變,其結果竟于此開出了理性這一美德。人類之所貴于物類者在此焉。世俗但見人類理智之優越,輒認以為人類特征之所在。而不知理性為體,理智為用,體者本也,用者末也;固未若以理性為人類特征之得當。”[5]618也就是說,一方面,沒有理性的產生,人類永遠不能真正脫離動物界,而人類的理智也無以正常使用。另一方面,沒有理智,就不會產生理性,理智是理性的充分條件,理智為理性進行選擇和判斷提供了抽象思維的基礎和能力。如果沒有理智將本能松開,“本能突出而理性若失者,則近于禽獸”,人類便不能開出所謂“無私的感情”,也不可能從動物式的本能生活中解放出來。理性的含義非常復雜,梁漱溟認為儒家的理性是一種道德理性,與西方的思辨理性、科技理性不同,儒家的理性核心是“仁”和“良知”,是人之為人的本質規定性,人內在精神的完善和充實,須臾不可疏離。要把握“理性”,向外尋覓是無濟于事的,深切真實地向內用力才是正途。因為,人從來都不是一架邏輯嚴密的機器,而有血肉、有意志的、既有理又有情的復雜系統。
四、舍棄直覺而轉向“理性”
轉向后的梁漱溟以“無私的情感”界定理性,主張理性作為情意表現是一種“不失于清明自覺的情感”,也包涵“知”、“理”,但理性之知與理智之知不同,是以情的觀照所體現出來的知、一種自覺的澄明狀態。理性之情感表現是無限向上的“通”,與生命相通而無隔。理性雖為人心所本有,卻必須經由修為工夫才能呈現。就他對理性的界定來看,顯然與西方文化中的理性迥異。在他那里,理性有兩種:物理和情理。物理是科學之理,是靜態的知識,沒有發動人的道德行為的力量;情理卻有這種力量,指示著人們行為的方向。情理盡管是抽象的,沒有特指當前某人某事,卻有巨大的驅人向善的力量。
按照梁漱溟,理智是靜以觀物,其所得為物理,不夾雜感情(主觀好惡)。理性反之,要以無私的情感為中心,即從不自欺其好惡而判斷,其所得為情理。如正義感,就是對于正義欣然接受之情,而對于非正義則嫌惡拒絕。離開此感情,能得到所謂正義嗎?一切情理雖然一定在情感上表現,卻不是沖動,而是一種不失于清明自覺的感情。無私的感情一發動,此即一體相通、一體平鋪、無所隔礙的偉大生命表現。無所隔礙的感情雖秉賦自天,為人所同具,然而往往此人此時具有活潑性,而其他人卻不盡然;甚至同一個人也是時而發動,時而不發動,情感的狀態是雜多不一的。這與動物本能顯然不是一事,而恰好是由本能解放出來的自由活動,這種爭取自由、爭取主動不斷向上奮進的本性,只有人類身上才出現過。在梁漱溟看來,既然本能、理智的兩分法失之于簡單,不足以說明問題,于是就在理智之外增加理性這個詞代表從動物式本能解放出來的人心之情意。理性與理智雙舉,豈可少乎?
依梁漱溟之見,相對于西方文化而言,儒家的“仁”是超越了理智分別和思慮計較的敏銳感通的情感。而“仁”即為感通流行形上之體,亦為孟子所謂“良知”、“良能”;情感作用盛之時,是“良知”、“良能”的發用流行,仁或良知由體而發用,亦即為“情”的流行與感通。梁漱溟聲言孔家相信恰好的生活中最自然,最合宇宙自己的變化——謂之“天理流行”,即情感的流行感通,方能體證“天理”。梁漱溟稱此為“心安”。所謂“安”與“不安”,就是道德情感的一種表現。梁漱溟強調的是以“天理”面目出現的本能情感,依他之見,儒家所謂性善,實質為情善,只要順著天理自然流行,情與理皆善。梁漱溟的論證是否周延和嚴密我們暫且不論,但通過其對“仁”與直覺的關系的論述,以不安、情感、不計較、不算賬、生意盎然來釋“仁”,應該說,展現了孔子的“仁”的要義,是對 “仁”的詮釋的一種推進。
梁漱溟自信地宣稱,中國人精神之所在,即是“人類的理性”。顯然,他將“情理”的內容注入理性之后使得理性概念具有明顯的人文色彩,與西方的理性主義有所不同。西方的理性主義的“理”較多地討論事理,是知識論意義上的“理”,雖與行為有關,相對人而言,是個獨立存在的實體;而中國人的理性主義的“理”,則是有力量的活動性,能夠發動行為的“情理”。由于滲透著情感,就具有引發行為的力量,人的思考、言行乃至于價值取向亦如此。中國人的這種“不教通曉而有情”的理性主義,實際上就是儒家的道德智慧。應該說,中國人的理性主義遠比西方認識論意義上的理性主義復雜,中國人的“理”傾向于任何事物都秉有的天理,是天地萬物之所以然者、全體大用之理,為一、為整體,而具體事物的分理“萬殊”則是由此“一理”化分出來,是天理之流行,為其所規定。
大體上我們可以把梁漱溟的問題歸結為:人的行為是理性發動的呢,還是被一種內心的情感、通過反省時自然而然地呈現的某種情感所驅動?根據梁漱溟哲學,認知意義上的理性只能發現這些義務,卻不能產生這些義務,而儒家的理性是人的理性的整全有發動行為的力量。那么,一個行為、一種觀念有德還是無德,如何判斷?梁漱溟依據的是看見這個行為時產生的快樂與不快的情感,只要說明產生情感的理由,就能區分德與不德,有德是由于一個行為、一種觀念帶來的一種特殊的快樂。無疑,轉向后的梁漱溟難以避免關于德性與情感關系的討論,只是他沒有深入思考,尚待我們繼續探究。
結論:當梁漱溟發現人們由直覺而行并非都趨向于善,直覺難以承當引導人們生活方向的職責,自然地,理智和理性進入其視野,將理性作為概括中國人特殊的認知方式與價值觀念。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梁漱溟的方法論中提到了理智的功用,但依然將理智界定為“算計”之用,只有“理性”的生活才符合生命本性。他視理性為一種道德情感生活的真理,不欺好惡而判別自然明切者。理性即儒家所謂的“良知良能”、“仁”,儒家思想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尋找內心的“理性”,并視之為最后準則,“道德的根本在理性”。我們大致可以說,梁漱溟哲學方法論的選擇從“直覺”到“理性”的過渡和延展,昭示了其思想走向成熟的歷程。然而,梁漱溟對“理性”概念的分疏和清理還不令人十分滿意。迄今為止,關于直覺、理性的本質的研究還在進行中。
[參 考 文 獻]
[1]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2] 郭齊勇.梁漱溟哲學思想[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3] 賀麟.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4] 胡軍.中國儒學史:現代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5]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