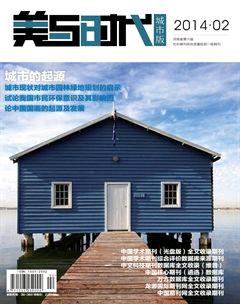淺析中國傳統園林創作的文學思維
董穎
摘要:中國傳統園林藝術與中國文學繪畫同宗同源,一脈相承,對其影響至深的首推中國的文學。中國園林設計思維與西方比較有較大的差異,西方強調理性分析,分析空間的功能、性質、和形態。而中國園林創作的基本理法和設計思維則是遵循著由一部《詩經》確立的“賦、比、興”的文藝思維體系,并具有著其環境空間藝術的特殊性。
關鍵詞:傳統園林藝術 ;天人合一;中國文學;立意
中國的傳統文化土壤,孕育和培植了根深葉茂的造園學,結出奇葩異果的園林藝術。中國傳統園林藝術,早在18世紀就引起西方建筑師的重視,英國錢伯斯(SirWilliamChambers,1723~1796年)深感中國園林的藝術境界,“是英國長期追求而沒有達到的”。德國濕澤(LudwigA·Unzer)贊揚中國園林可為一切造園藝術的模范。這些評價,較之今天我們只能欣賞園林的形式美而言,在認識上深刻得多。本文意從中國文學思維形式來解讀中國傳統園林藝術創作過程,目的在于領會中華民族傳統園林藝術之精髓。
一、中國古典園林藝術是文學家的藝術作品
中國建筑中的“園林建筑”和現代西方的所謂“景觀建筑”在內容上似乎相近,但在性質上和基本概念上,二者之間是有一定的距離的。中國的園林建筑不但是一個獨立項目,而且在發展上成為與一般建筑相平行的另一個體系。中國古典園林的設計,并非“景觀建筑”或“景觀設計”,而是指那些獨立的、自成一體、純然另成一種自我性格的“小天地”。[1]
中國的園林建筑是中國建筑歷史特殊條件下發展起來的一種特殊產物。由于中國建筑技術和藝術這成熟和普及,中國很早就出現了“沒有建筑師的建筑”,中國文學家、畫家認為建筑是按一定的形制而建,并不是一種藝術創作。中國文學家占風氣之先,自己為自己設計建筑,規劃園林,他們和泥木工、山子匠常能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建筑和園林設計工作,往往做出“個性”突出、格調高雅的園林藝術作品來。自然而然,園林藝術的創作與中國文學藝術的關系密切起來,可為休戚相依。中國文學方面也有不少詩詞歌賦歌頌贊美建筑、園林,《詩經》已啟其端。我們后人也從不少中國文學作品中品味到中國建筑金殿玉樓的壯美和中國園林的“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自然意境美。
二、中國古典園林創作理法 是按照文學創作的思維模式
中國的園林藝術與中國文學繪畫同宗同源,一脈相承,對其影響至深的首推中國的文學。一部《詩經》不僅確立了“賦、比、興”的文藝思維體系,而且中國古典園林創作的理法也基于此脈,不過另具有其環境空間藝術的特殊性而已。
文學思維是指文學形式所特有的思維方式,是一種基于形象思維之上的更高層次的更富有綜合性的專為文學創作所需的思維模式。文學思維亦稱“藝術思維”或“形象思維”,其思維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積累和搜集素材;構思,擬定計劃或提綱;然后經過寫作將其變成文學作品。同樣,中國古典園林創作理法中的明旨、立意、布局、借景等環節正是體現著中國文學思維的影響。[2]
(一)明旨:文學性的美學思想為總綱——“天人合一”境界
所謂明旨,就是首先明確興造園林的目的。劉敦楨先生在分析“蘇州古典園林”時首先就分析造園目的。中國園林的最高境界和追求目標是“雖由人作,宛自天開”。[3]美學家李澤厚從美學概括中國園林為“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中國人把大自然稱為“真”,人造自然稱為“假”。“有真為假”的另一含義是根據自然來造園,這樣才能達到“做假成真”的藝術效果。明計成大師的《園冶》中論假山有“有真為假,做假成真”之說。概言之,從園林方面反映了中國人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中國的宇宙觀和傳統文化總綱“天人合一”通過文學與繪畫發展而來,也是中國園林形成的歷史原委。“天人合一”見諸于中國文學反映在追求“物我交融”的境界,創作手法主要是“賦、比、興”;中國繪畫則反映在“貴在似與不似之間”的境界,創作方法為“外師造化,內得心源”。中國古典園林追求的最高境界:“雖由人作,宛自天開”,依據就是由中國文學思想所定的崇尚大自然的美學思想。
《園冶·識語》所言:“以人工之美入天然,故能奇,以清幽之趣藥濃麗,故能雅。”中華民族的祖先很早就認識了綠色生態環境,“天人合一”的文化總綱決定了中國人在對待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主張“人與天調”,尊重自然生態規律,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今日園林雖發展為單體的城市園林或風景名勝區、城市綠地系統規劃和大地景物規劃三個層次,園林創作內容雖然擴大了,但園林的本質并沒有發生變化,仍然是為了滿足人類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對自然環境的需求,強調人與自然的協調,注重人的社會生產活動與人居的自然環境協調發展。
(二)立意:以“意在筆先”的文學觀念構思園林意境
造園之初除了確定用地性質所牽動的科學技術性構思以外,由于中國園林歷史上長期受中國文學與繪畫的影響,與其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以“意在筆先”的觀念構思作品意境,即園林設計理法中的立意。借“意”而具內蘊而發揮園林神形兼備的藝術效果。
清代錢泳在《覆園叢話》中說:“造園如作詩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應。最忌堆砌,最忌錯雜,方稱佳構。”一言道破造園與作詩文無異,從詩文中可悟造園之法,而園林又能興游以成詩文。造園如同作詩一樣重意境表達:對設計者而言,足以言抒懷;對游覽者而言,足以觸景生情。湯顯祖所為《牡丹亭》中“游園”、“拾畫”諸折,不僅是戲曲,也是園林文學,又是教人怎樣領會中國園林的精神實質。“遍青山啼紅了杜鵑,那荼靡外煙絲醉軟”、“朝日暮卷,云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其興游移情之處真曲盡其妙。是情鐘于園,而園必寫情,文以情生,園固相同。
造園總體要立意,局部造景也要立意。一些古典名園甚至連室內的幾案、擺設用品無不通過題刻、書畫等創造的意境來表達創意。中國園林就是:文理相得,以藝馭術。其創作目的就是要遵循中國文化傳統中“天人合一”的總綱以及藝術理論“物我交融”的哲理,運用形象思維,借助文學藝術的“比興”手法和繪畫藝術的“外師造化,內得心源”的理法,結合園主與環境特色加以融會貫通。由此,園林的意境便會從無到有,從朦朧走向明朗。意境也正是中國園林設計的靈魂所在。
(三)借景:中國文學“比興”手法的傳統
首先,借景秉承了中國文學“比興”手法的傳統,也傳承了中國文化“物我交融”、“托物言志”等優秀傳統觀念。借景的理論由造園、造景等實踐而來,并再三以實踐證明是造園藝術的真理。這又從一個方面證明了中國園林與中國文學藝術一脈相承的特色所在。
按《辭海》解釋,比興為傳統文學創作中的兩種手法。“比”是比喻,朱熹說:“以彼物比此物也。”“興”是寄托,即托物言志,朱熹說:“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借景是文學藝術的比興手法在園林藝術中衍生的新葩。借因造景、藉因成景,其二元因素的根本代表是物、我,即自然與人。借景的托物言志,體現在將自然的擬人化過程中。
計成大師最終師納出借景的訣竅在于“巧于因借,精在體宜。”而在園林設計的主要理法方面也是從文學“比興”演變而來的借景,其來源還可以追溯到創造中國文字之首要的“假借”理法。借景是中國風景園林傳統涉及理法的核心內容,主宰了中國園林設計的所有環節。計成在《園冶》中說:“夫借景,林園之最要者也。如遠借、鄰借、仰借、俯借、應時而借,然物情所逗,目寄心期,似意在筆先。庶幾描寫之盡哉!”。目寄心期的統一必然動之以情,以景觸動游人的情感。可謂又回到了中國園林的以景抒情、天人合一的美學思想上來。
三、園林的立意和格調要通過文學形式表達
園林創作中的立意要通過“問名”以及題額、楹聯來具體表達,也正顯明了中國文學與風景園林相輔相成、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關系。
(一)問名
中國人重視問名,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把正名提到成敗之關鍵。中國園林是以文學為基礎,強調詩性思維,問名在此顯得尤為得重要。因名解意的過程稱為“問名心曉”。[4]
蘇州有一私家園林名為“退思園”,其意為“退而思過”。園主人任蘭生是清光緒年間官員,被彈劾解職后掛甲歸田,延請袁龍為他設計了這退思園。園門背后上方磚雕額題:“云煙鎖鑰”,既反映出江南水鄉煙云繚繞的地理特點,也映射出園主人遭貶之后的處境與心態,一語雙關。園內主體建筑名曰“退思草堂”,正是中國傳統文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寫照。院內建筑的延展仿效八股文“起、承、轉、合”的章法:以“水香榭”為“起”景,九曲廊起到銜承的作用。九為最高之數,使人感受到主人愁腸百轉的郁悶心情。園中假山,下穿洞上安亭,景名“眠云亭”,意在“欲知花乳清冷味,須是眠云臥石人。”其實此處顯示出園主人在造園時并非看破紅塵,而對入世還暗存眷顧。賞景人如果沒有如此得中國傳統文學修養,恐怕是賞不出此園林的深層意味來的。
從“問名心曉”過程可以了解到“頤和園”是取“頤養沖和”之意,是皇帝為孝敬太后所建。同一主題中,而上海建于明代的豫園,意卻取自“豫悅老親”,故名“豫園”。在江蘇、四川等地的眾多園林都體現著不同的中國文化及造園者的“物我交融”、“托物言志”的景名,不勝枚舉。又如:蘇州的“曲園”,取意《老子》中“曲則全”之句,將園子命名為“曲園”,于曲折中生出新意,于至簡中見出深情,寥寥幾筆,人生的意蘊盡含其中。
通過園中問名,主、客觀經碰撞后在心靈上產生共鳴效果,在景物以外產生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境界。園林的“問名”過程,可以說是將地理景觀文學藝術化的過程。文學中的詩是言志。中國園林將自然美和社會哲理結合為藝術美,沒有文學的升華是不可能產生“寓教于景”的藝術效果的。問名,相當于文學創作中的命題。作文要按題行文,行文綱舉目張。園林造景藝術猶如文學創作,是講求章法和理法,要按題造景。問名主要是闡明造園目的,點出造的特色,或表明地域所在,或借名抒情。
(二)題額、楹聯。園林中所蘊含的文學藝術不僅表現在問名
由于園景組成的因素主要是地形地貌、植物、建筑、水體、山石、假山、園路、場地以及小品等。除了青蛙、鳴蟬、飛鳥等小動物以及流水、清風外,其他組成因素都屬默聲者。因此,設計者的立意及意境也有借題額、楹聯和摩崖石刻等文學形式表達。于是衍生出園林微觀鑒賞的“三絕”:文法、書法和刀法。額題,既可“千錘打鑼,一錘定音”地點出園林藝術的特色,又給游人以提高欣賞水平的啟示。諸如蘇州拙政園腰門里面的“左通”、“右達”,獅子林入口內的“讀畫”、“聽香”等。但凡有中國傳統文化底蘊的人看到“讀畫”,便可聯想到蘇東坡評王維:“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王維也是造園家,他親自經營建造的輞川別業是一個占地很大的私家園林,他的相當一部分的詩歌和繪畫作品描寫的景象都是他在輞川別業中的生活。他的園林設計也充分體現他回歸自然,物我一體,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因而能達到與世無爭隨遇而安的思想境界。而中國園林設計思想也正是這些文人畫家的追求自然的儒道思想的一種形像化展現,這又回到了文學上來。所以,楊鴻勛先生說中國園林是用詩畫創造空間。這正是中國傳統古典園林特色與魅力所在。
楹聯較之題額有更大的篇幅可以抒發胸意。京口古城以三山依傍長江的美景著稱,金、焦二山居于江上,北固山虎踞江岸,三山之上古剎環宇,林深水渺,是相互借景的極則。乾隆南巡時,留詩一首:長江好似硯池波,提起金焦當墨磨,鐵塔一支堪作筆,青天夠寫幾行多?乾隆以一問句點出三山名勝,將比興、借代等文學化手法,運用到極致,讓天人之境、人文名勝相互交融,極富天人合一的韻味。
四、結語
清.錢詠在《履園叢話》一文中曰:“造園如作詩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應、最忌堆砌、最忌錯雜、方稱佳構。”道破了中國文學和園林的關系。中國古代造園遵循的一個總的原則是“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它是中國園林接受文學藝術普遍規律影響所反映的特殊屬性。
深刻的文化內涵、深邃的意境情趣使中國園林藝術著稱于世。中國園林藝術不僅體現出我們的生活品味,更反映出我們先人留下的精神追求和民族特質。隨著城市建筑、園林事業的蓬勃發展,如何學習、如何繼承和發展中國風景園林的民族傳統是從事風景園林設計者們經常思考和付諸實踐的命題。我們不僅要吸收外國的先進經驗和技術,或許也應注重繼承和發揚我中華民族傳統園林的精髓。我們以現代生活為內容,按自然與人文交融的“天人合一”總則行事。可謂“從來多古意,可以賦新詩”。
【注釋】
[1]李允鉌.華夏意匠[M].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05.5,第305頁
[2]孟兆楨.園衍[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2.10,第17頁
[3]孟兆楨.園衍[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2.10,第18頁
[4]孟兆楨.園衍[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2.10,第23頁
【參考文獻】
[1]孟兆楨,園衍[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2
[2]李允鉌,華夏意匠[M],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05
[3]方曉風,羅哲文.中國古代建筑園林[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1
[4]張良皋,匠學七說[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2
[5]張家驥,中國造園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單位:黃河科技學院工學院建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