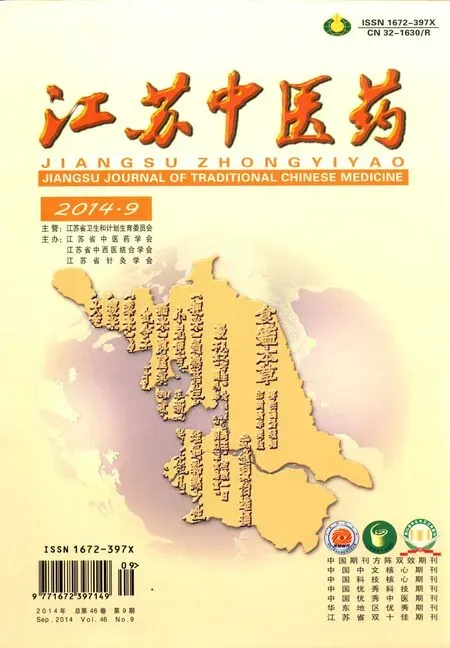以小補脾湯與小瀉脾湯為例試析《輔行訣》中補瀉的含義
李崇超
(南京中醫(yī)藥大學中醫(yī)藥文獻研究所,江蘇南京 210029)
以小補脾湯與小瀉脾湯為例試析《輔行訣》中補瀉的含義
李崇超
(南京中醫(yī)藥大學中醫(yī)藥文獻研究所,江蘇南京 210029)
補瀉是中醫(yī)最重要的術語之一。在中醫(yī)的發(fā)展過程中,補瀉的含義也有所變遷。《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一書中的補瀉概念,與通行的補瀉概念有所不同。通過對書中“小補脾湯”和“小瀉脾湯”補瀉概念的研究,認為其補瀉與五行的生克制化有關,與通行的補瀉氣血陰陽的觀念不同,但是通過對方證的梳理,依然可以找到其與通行醫(yī)學理論的相通之處,使補瀉理論能夠更好地豐富中醫(yī)學理論和臨床。
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 補瀉 方證
《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以下簡稱《輔行訣》)署名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原藏于敦煌藏經洞,20世紀初重新面世。《輔行訣》中收錄方劑56首,并表明這些方劑是錄自《湯液經法》,而且是《湯液經法》中的核心方劑。《輔行訣》中有五臟大小補瀉湯共24首,補瀉成為《輔行訣》一書中最核心的術語之一。正如書中開頭所說:“一依五臟補瀉法例,服藥數(shù)劑,必使臟氣平和。”值得重視的是,《輔行訣》中的“補、瀉”,和我們較為通行的補瀉術語,有不同之處,值得我們進行思考和研究,進而豐富我們的方劑理論和中醫(yī)理論。
1 《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補瀉理論的疑問
1.1 “補”“瀉”在方劑中的一般含義中醫(yī)方劑中,有很多以補瀉命名的方劑,但是,這些方劑的補、瀉,都有具體的補瀉內容。
比如按照目前流行的中醫(yī)學理論,提到補,就會想到是補氣血陰陽的某一方面,而且根據(jù)臟腑的生理特征,已經形成了較為固定的氣血陰陽的補瀉術語,如對于肺臟來講,就只有補肺氣、瀉肺氣,而很少提到補肺陽、瀉肺陽;對脾臟來講,就只有補脾氣,補脾陽,而很少有補脾陰、補脾血。一些以補、瀉命名的方劑,也有具體的所指。如《醫(yī)方集解》中的龍膽瀉肝湯中的“瀉肝”,專指瀉肝經的濕熱;《小兒藥證直訣》中的瀉青丸,指瀉肝經的郁火;而其中的瀉黃散,又瀉的是脾胃的伏火。而輔行訣中的“補”“瀉”,似乎就是補瀉的某臟之氣。
1.2 “小補脾湯”和“小瀉脾湯”方名的疑問《輔行訣》中“小補脾湯”和“小瀉脾湯”,分別是我們熟悉的經方理中湯和四逆湯。理中湯為小補脾湯還好理解,但四逆湯由附子、干姜、甘草三味藥組成,全都是溫補的藥物,何以言瀉?而且和“小補脾湯”相比,補瀉之間的區(qū)別并不明顯,因此這里的補瀉,與通行的補瀉理論有很大的不同。
關于“小瀉脾湯”的得名,已經有學者提出了疑問。叢春雨先生主編的《敦煌中醫(yī)藥全書》中收錄《輔行訣》,他在小瀉脾湯后面的按語上說:“此‘小瀉脾湯’與《傷寒論》中的‘四逆湯’組成相同。此方主治‘脾氣實’,其主癥皆脾氣虛寒之象,名‘瀉脾’,實則峻補脾之陽氣,其古今理意不同乎?”[1]
馮世綸先生在《〈傷寒雜病論〉再溯源》[2]一文中指出:“小瀉脾湯,方藥組成為附子一枚(炮),干姜、甘草(炙)各三兩。治脾氣實,下利清谷,里寒外熱,肢冷,脈微者。而小補脾湯,方藥組成為人參、甘草(炙)、干姜各三兩,術一兩。治飲食不消,時自吐利,吐利已,心中苦饑,無力,身重,足痿,善轉筋者。從八綱辨證來看,兩方都用于里虛寒,都是溫陽重劑,但前者稱為瀉脾,后者稱為補脾,實際溫補重于后者,到底補什么瀉什么讓人難以理解。故張仲景避道家之稱,把小瀉脾湯改稱四逆湯……如按五臟補瀉辨證,補脾、瀉脾很難對應。”
正是因為“小補脾湯”“小瀉脾湯”命名上的這些疑問,且這兩方又可以在通行的方劑中找到對應,因此,以此入手,將其補瀉規(guī)律研究清楚了,可以說是研究《輔行訣》大小五臟補瀉湯這部分方劑的一個鑰匙,也是對“補”“瀉”這一術語含義變遷的研究,可以豐富中醫(yī)學理論。
2 從《輔行訣》自身理論看補瀉的依據(jù)
理解《輔行訣》中方劑補瀉的命名,還要從本書自身的理論來看。因為《輔行訣》中有很多理論是獨特的,和通行的中醫(yī)藥學理論有不同之處,也可能是已經失傳了的中醫(yī)藥理論,其在五行、五味、五臟的補瀉關系中,十分嚴密合理。
《輔行訣》中給出了二十五味“諸藥之精”:“經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五氣,化生五味,五味之變,不可勝數(shù)。今者約列二十五種,以明五行互含之跡,以明五味變化之用,如左:味辛皆屬木,桂為之主,椒為火,姜為土,細辛為金,附子為水。味咸皆屬火,旋覆為之主,大黃為木,澤瀉為土,厚樸為金,硝石為水。味甘皆屬土,人參為之主,甘草為木,大棗為火,麥冬為金,茯苓為水。味酸皆屬金,五味為之主,枳實為木,豉為火,芍藥為土,薯蕷為水。味苦皆屬水,地黃為之主,黃芩為木,黃連為火,白術為土,竹葉為金。此二十五味,為諸藥之精,多療諸五臟六腑內損諸病,學者當深契焉。”
并且列出了五臟苦欲補瀉的內容,這些內容與《內經》相似:“肝德在散,故經云:以辛補之,酸瀉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德在耎。故經云:以咸補之,苦瀉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德在緩。故經云:以甘補之,辛瀉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德在收。故經云:以酸補之,咸瀉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辛以散之,開腠理以通氣也。腎德在堅。故經云:以苦補之,甘瀉之。腎苦燥,急食咸以潤之,至津液生也。”
《輔行訣》中補瀉方的組成,就是依據(jù)這兩段內容而來。其中“補”方的組成,是以“二補一瀉一急食”的規(guī)律,而“瀉”方是以“二瀉一補”的規(guī)律組成的。我們來看看“小補脾湯”和“小瀉脾湯”的組成規(guī)律。
“小補脾湯:治飲食不化,時自吐利,吐利已,心中苦饑。或心下痞滿,脈微,無力,身重,足痿,善轉筋者方。人參,甘草(炙),干姜各三兩,術一兩。小瀉脾湯:治脾氣實,下利清谷,里寒外熱,腹冷,脈微者方:附子(一枚,炮),干姜,甘草(炙),各三兩。”
從方劑的命名及其與書中的補瀉配伍規(guī)律來看,補瀉的命名規(guī)律是這樣的:補某臟者,必為該藏之本味,瀉某臟者,必用克該臟之味。小補湯的組方規(guī)律是“二補一瀉一急食”,小瀉湯的組方規(guī)律是“二瀉一補”。比如脾臟的補瀉湯,小補脾湯,五味五行配屬中的土之本味藥——人參(甘補之),這正是小補脾湯中的第一味藥為人參的原因,然后用甘味的甘草(甘補之)、辛味的干姜(辛瀉之),再加上一個苦味的白術(急食苦以燥之)。
那么小瀉脾湯,就用五味五行配屬中的木之本味藥——附子(辛瀉之),這也是小瀉脾湯的第一味藥用附子的依據(jù)。而用辛味的干姜(辛瀉之),再加上一個甘味的甘草(甘補之)。這些組方規(guī)律也體現(xiàn)了瀉中有補,補中有瀉的思想,在《輔行訣》的內部理論中,小補脾湯與小瀉脾湯的命名是非常相配的。
可見,補瀉脾湯的之補瀉,要從五行生克制化平衡角度來進行認識,與通行的補瀉氣血陰陽的觀念有所不同。
3 小補、瀉脾湯之“補”“瀉”術語分析
雖然《輔行訣》中的補瀉與通行的補瀉有不盡相同之處,用目前通行的方劑配伍理論不太好解釋其含義。但是我們需要知道,雖然配伍的模式不同,但其方劑在使用層面上,應該是統(tǒng)一于整個中醫(yī)的理論之中的。就像計算機軟件的編寫語言不一樣,但是卻應該能夠顯示出相同的功用一樣。那么,我們就從《輔行訣》中的小補、瀉脾湯作為入手點,來看一看《輔行訣》方劑與目前通行醫(yī)學理論的相通之處。從臨床上講,這里講的補脾、瀉脾有沒有依據(jù)?和脾的生理病理功能有何相關?
3.1 “小瀉脾湯”之“瀉”“小瀉脾湯”在《傷寒論》中叫“四逆湯”,那么四逆湯的方證是否和《內經》中脾的生理病理特征有關呢?
中醫(yī)認為“脾主四肢”,而四逆湯方證的主要指征就是四肢厥冷,其“四逆”的“四”就是就四肢而言。在《素問·痹論》中有:“脾痹者,四肢解墮。”清·汪宏的《望診遵經》里也談到了脾氣實會引起腿的疾病:“足不收者,脾氣虛,足不舉者,脾氣實。”小瀉脾湯體現(xiàn)了脾與四肢的關系。
小瀉脾湯所對應的癥狀:“脾氣實,下利清谷,里寒外熱,腹冷,脈微者。”而“大瀉脾湯”所對應的癥狀:“腹中脹滿,干嘔不能食,欲利不得,或下利不止者。”也就是說《輔行訣》中認為,脾氣實就會產生上述癥狀。而《素問·脈要精微論》中指出:脾氣實則腹脹,不足則為溏瀉。指出脾氣實則腹脹的癥狀。清·吳謙《傷寒心法要訣》中有:“腹?jié)M痛,太陰有余證也。”指出太陰有余則腹?jié)M痛。
我們也應該想到,既然是瀉,那么肯定是有余才瀉,脾有余、脾氣實、太陰有余、歲土太過這些相關論述,也會給我們提供小瀉脾湯的得名依據(jù)。因為,太陰和脾土是相聯(lián)系的,自然界的“歲土太過”,在人體上反映出來也是脾土太過的病證,體現(xiàn)了天人同構。
《素問·氣交變大論》中:“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樂……”這和四逆湯的主治癥狀很吻合。脾主土,歲土太過,也可以說是天行的脾土太過,因此反映在人身上,就會發(fā)生人身的脾土太過的癥狀,太過則需要瀉。通過這些論述可以看出,《輔行訣》中方劑所言的補瀉,不是像后世講的補陰補陽,補氣補血,而是補瀉這個臟器本來的氣。
在這一點上,李東垣有一段話可以供我們參考。《醫(yī)學綱目·脾胃部》錄有李東垣的一段話:“太陰所至為蓄滿辨云:脾為陰中之太陰。又云:脾為陰中之至陰,乃為坤元亙古不遷之土。天為陽,火也。地為陰,水也。在人則為脾,同陰水之化。脾有余則腹脹滿,食不化,故無陽則不能化五谷,脾盛乃大寒為脹滿。故《脈經》云:胃中寒則脹滿。大抵此病皆水氣寒濕為之也。治宜大辛熱之劑,必愈。然亦有輕重。”這里指出了脾為陰中之太陰,“脾盛乃大寒為脹滿”,指出脾臟的本性就是大寒,其盛則“大寒為脹滿”,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小瀉脾湯的組成用的是大辛大熱的藥物。
3.2 “小補脾湯”之補在《輔行訣》中,小補脾湯方證為:治飲食不化,時自吐利,吐利已,心中苦饑;或心下痞滿,脈微,無力,身重,足痿,善轉筋者方。
小補脾湯就是后世的理中丸,一直都是用來溫補中焦脾胃,原名為小補脾湯,很好理解。察醫(yī)經中的“歲土不及”下人會出現(xiàn)的病癥:歲土不及……民病飧泄霍亂,體重腹痛,筋骨繇復,肌肉酸,善怒,臟氣舉事,蟲早附,咸病寒中。
后世經常用理中丸來治療霍亂,亦可看出其“小補脾湯”原名之含義。如《傷寒論·辨霍亂病脈證并治法第十三》“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這里霍亂的主要癥狀就是嘔吐和下利,與小補脾湯中的癥狀“時自吐利”以及大補脾湯中的“嘔吐下利”相同。《類經·疾病類·五臟虛實病刺》指出脾臟:“虛則腹?jié)M腸鳴,飧泄食不化。”《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太陰……不足,病脾痹。”關于脾痹,《素問·痹論》篇中有:“脾痹者,四肢解墮發(fā)咳,嘔汁,上為大塞。”清代高士宗解釋為:“脾主四肢,故脾痹者,四肢懈惰;土灌四旁,痹則上氣不灌,氣惟上逆,故發(fā)咳。入胃之飲,借脾氣以散精,痹則不能散精,故嘔汁。”
4 結論
“補”“瀉”是中醫(yī)最重要的術語之一。不管是方劑還是針灸,都是用補瀉來使人體達到平衡,達到《內經》中講的“以平為期”。通過對“小補脾湯”和“小瀉脾湯”中“補”“瀉”含義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輔行訣》中的補、瀉脾湯的方證,和脾的生理特性是緊密對應的,其余四臟的補瀉方劑亦是如此。因此,《輔行訣》中的方劑與《內經》是密切相關的,這也可以反映出醫(yī)經家和經方家的學術思想并非是兩個體系。(2)《輔行訣》中的補瀉,與五臟、五行的生克關系密切相關,其補瀉的目的就是使得五臟之間的生克關系重新達到有序,達到《金匱要略》中的:“五臟元真通暢,人即安和”的目的,其中的五臟與五行的用藥規(guī)律值得我們重視。(3)《輔行訣》中的補瀉,在方證層面,與通行的中醫(yī)理論是相通的。對《輔行訣》中方劑組成理論的重新認識和研究,可以豐富中醫(yī)學的理論和臨床。
[1]叢春雨.敦煌中醫(yī)藥全書.北京:中醫(yī)古籍出版社,1994:107
[2]馮世倫.《傷寒雜病論》再溯源.中國中醫(yī)藥報,2003-12-15(4)
R242文獻識別碼A
1672-397X(2014)09-0066-03
李崇超(1979-),男,博士,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方劑文獻。lcc311js@126.com
2014-05-05
編輯:韋杭吳寧
江蘇省教育廳2012年度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2012SJB74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