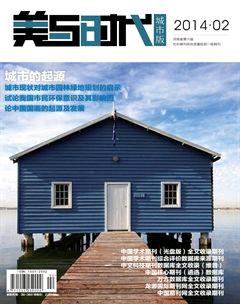筆墨蔥籠 淳趣盎然
鄧凱
俞德生出生于長江南岸的江陰縣城,幼時即開始學畫,童年臨摹的《芥子園畫譜》把頗顯靈氣的他帶入了中國畫的藝術長江之中。是江南的的水土養育了他,是江南的環境浸潤了他,是江南的美景觸動了他稚嫩的心靈。那些樹木田舍,縱橫河道,絲瓜花,扁豆花爛漫的景色,是他小時候的真實生活環境,把這些景色畫得優美一點,漂亮一點,是畫家對美好環境的祈愿。這些早年的田園生活,成了其后半輩子創作關注的焦點,成了其日后作品產生的夢工廠。及至少年,其在畫畫上已顯露天賦,初中畢業,在眾多考生中脫穎而出考入南京藝術學院附中學習,后又復考入南京藝術學院本科學習,與著名畫家賀成、王為政等皆為同門同學。在諸多南藝大師的教誨下,他勤而時習之,通過八年的學院體系化培養奠定了他的深厚功底,當年這些“厚積”的功底,成為其日后“薄發”的創作源泉。
俞德生大學畢業以后分配在燈芯絨廠搞花樣設計,“薄發”了很多創作靈感,“薄發”了多項榮譽的獎項,也“薄發”了他的國畫創作熱情,這些“薄發”的活水疏浚了他對故園的的思念之渠,引來了他“江南情思”的活水。這些活水潑灑到畫卷上就成了“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春未老,風細柳斜斜。試上超然臺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煙雨暗千家。”的春色江南;就成了“閑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蕭蕭,人語驛邊橋。”的夏夜江南;就成了“雨徑綠蕪合,霜園紅葉多”的秋意江南;就成了“自從雪里唱新曲,直到三春花盡時。”的冬日江南;就成了“平生不識五老峰,且寫吾鄉一奇觀”,“客樹回望成故鄉。”的夢中江南,他所濃墨淡彩的畫中客樹,鋪陳畫面的夢里水鄉,都是他腦海中故鄉的倒影,是江南美景的詩意顯現,春花秋樹、垣墻舟橋,映帶左右也都是江南民俗的自然再顯。
“自然”一直以來就是中國畫最為依賴的物質支撐和精神支柱。在傳統國畫中使用的筆、墨、紙、硯,所謂的文房“四寶”,皆取自于自然。國畫所普遍描繪的對象也來自于“觀物取象”、“度物象而取其真”的自然。國畫的傳統理論,從耳熟能詳的王維《山水訣》:“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到孫過庭《書譜》中所言“同自然之妙有。”,再至石濤的“搜盡奇峰打草稿”,盡管時間跨越千年,但皆體現出一種自然情節。
在今天“自然”本身也產生了巨大的改變,農耕社會的田園自然被侵削,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自然”也有了工業化、都市化的色彩。諸多新生事物出現在人們的視野里、生活中。自然的“天人合一”的田園牧歌式的生存環境正逐漸淡出我們的記憶。俞德勝將“自然”作為與我們在心理上漸行漸遠的越來越有距離感的“故土”、“家園”進行描繪以喚醒我們的記憶。把環繞在其周遭的仍然遺存的鄉村風景放入了他的山水畫中,這些風景不是描繪人工打造的新景,是樸實無華原生態的身邊之景,又有些似乎是在記憶中帶有傳統文化痕跡的近代之景,有些畫面比較清凈平淡,有些畫面比較亮麗鮮活。這些畫面或多或少似乎帶有現代文學創作的的一種“底層敘事”的現實傾向。是現代都市人心靈遙馳的桃紅柳綠、山水風光,郊外景致;是躺在沙發上體會物外高隱,無限愜意的追夢遐思;是坐在茶幾前啜茗味淡、暢懷舒嘯、憑窗對景的清朗樂趣。讓喧囂的都市人在思緒繁雜的現代社會里,在奔波忙碌的快節奏中領略到“望秋云、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的一種情懷。
俞德生在描繪自然山水時顯得更追求古典一點、平靜一點、出世一點。相反,其在對人物的繪畫表現上卻注重筆墨的感覺,突出松動的閑適表達,而不局限于形態的真實,更強調人物的時代感、舒適感和閑適感,顯得更現代一點、樂活一點、入世一點。這些是他個人的追求和情懷,旁人也許看不出來,但從他的畫面里述說出來,通過藝術的語言表達出來,我們是可以聽得到的。當然,這樣的二元對立,也是可以在俞德生的畫中體悟到的。既可見到其在山水描繪中對自然的深深依戀,又可見其對人物勾畫形式上創新的高度自覺。前者體現了畫家及其我們民族對文化傳統的夙慕;后者則由時代激活,具有鮮活的時代特征,在兩者間俞德生能就熟駕輕、騰挪自如,是他一直把中國唐代畫家張璪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理論用于他的藝術創作實踐。
寫生是藝術實踐的重要過程。一個好的畫家除了基本功外,還要注重寫生,只有通過寫生才能畫出有生氣的畫來,才能突破程式化、概念化的桎梏。俞德生非常重視寫生。一方面是他作為教師常常要帶上學生一起出去寫生,是工作使然。另一方面也由于其親近自然的天性所定,寫生是他貼近自然,融入自然,描繪自然的重要途徑,他用心去感知天地山川的生命躍動,體會身邊的自然環境,眼簾中的自然美景,發現自然之美,他以樂觀喜悅的態度去描繪自然的優美,是他陶然自怡的內心的表現。他遍歷大江南北,深入三山五岳,足跡遍天下,寫山川之自然,繪四時之變化,搜集奇峰異巒,窮極造化,縱情山水,把對自然的感悟融入到山、水、云、石、樹、草的寫生之中,積累了大量的寫生手稿。可以看到這些博觀約取的手稿為他的畫帶來了創新氣象,注入了勃勃生機。
生機的產生還來自于他不斷地采風。在采風中他常常為自然的優美風景所觸動,先后畫過長江山峽,西雙版納,桂林漓江,及至后來作為教師又常常帶學生出去采風、寫生,更多地接觸了江南的蘇南、皖南等地。一摸黛瓦粉墻的農舍,一團鄉村林間飄蕩的霧氣,這些畫家熟悉的山水對于他來說視乎格外親切,他憑借著自然景物對自己最真切的觸動。思緒在自然中獲得寧靜與充實,正如日本著名風景畫家東山魁夷在《旅之環—自傳抄》中寫道:“對于我來說,即使站在荒無人跡的冬季的高原上,在我身邊也充滿了遠比都市中心更為親切的東西。”他看到了一些別人沒有看到的東西,他用別人沒有注意的觀察悟性去發現了這個美。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有的人去轉了轉可能沒有發現這個美,拍了些照片就走了,我發現了這個樸實的普通的美,這個是我骨子里的平民意識的流露,對于那些大山大水,名山名水,覺得不太想去畫,又常常為內心深處的江南所牽引,這些身邊熟悉的山水對于我來說似乎格外親切,自覺不自覺的畫了一張又一張的江南山水”。這些一張又一張的山水畫來自于他向先賢學,向傳統學,向自然學,來自于他樸實的情懷,來自于他的不斷創新。
俞德生除向自然學習外,還博覽群書,執著地探索傳統繪畫之奧秘,對歷代山水畫多有研究,如:顧愷之的《畫云臺山》,李思訓的《江帆樓閣圖》,關仝的《關山行旅圖》和《山溪待渡圖》,范寬的《溪山行旅圖》、《雪景寒林圖》;董源的代表作《瀟湘圖》、《夏景山口待渡圖》和《龍宿郊民圖》;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和《六峰雪薺圖》都不斷臨摹、研究。他繼承先賢畫風,能“師其意,而不師其跡”,這些師意在他的畫中仔細體嗅出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的清逸之氣,體察出“元四家”的布衣精神。體會到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以及張宏為代表的“吳門”生活氣息、文人情懷。體悟到滿清的王時敏、王鑒、王原祁、王翚等“四王”和石濤的畫中節奏韻律、筆墨張力。對于這些前輩畫家的理論和實踐圖冊他均有追隨,從中汲取營養。及至現代,他又與時俱進地向當代的山水畫大師如黃賓虹、李可染、張大千、傅抱石、關山月等學習,領會現時新階段山水畫《革命搖籃井岡山》、《龍盤虎踞》、《江山如此多嬌》等山水畫的現實表現手法,從而博取眾家之長。在此基礎之上他的現時圖畫山水,有題材、有筆墨、有表現手法,并不斷探索開拓,逐漸形成自家的形神兼備的風格面貌。
他自成一格的山水畫沒被傳統山水范式中形式主義的八股套路所束縛,而是將傳統的程式作為其登攀的階梯。他兒時臨摹的畫譜中常見有這樣的程式:氣勢雄偉的全景山水構圖之上,座座大山,陡峭絕壁、重巒疊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個老頭拄拐或站于山腳邊的小道上,或行于溪流平緩的小橋上。這種傳統山水畫,數千年來畫的人實在是太多了,即使有些變化也是大同小異,要創作出區別于傳統山水大山大河的全景式構圖,現在如何創新?就需要換個角度去思考、去取景、去描繪,這真是他所嘗試的。他說:“我最早是在蘇州的東山、西山畫銀杏樹,畫了冬天過了是春天七張畫的樹,當時想畫一張輕快一點,顏色鮮艷一點的一張放在七張畫的中間,畫了很多都沒有畫好,偶爾把一張反過來,看到了透過宣紙映出來的效果覺得不錯,就按這個添了些船、網、樹在上面,感覺比較空靈,這樣就組成了八張畫。后來到安徽寫生就用了這樣的筆法,再加入了一些中國書法的線,再加上貫氣,通過一大片的樹反映秋色,筆墨有些濃淡枯濕的變化,畫面感很好”。“后來,為了辦展,看看那些畫過的畫,發現都是秋天,都是赭色調,就又畫了六尺對開的四條幅,畫了亂草亂樹叢中的野花,畫的也比較生動,相對于傳統山水的嚴謹而言,顯得更為輕松自在”。
透過他表面輕松的畫面,我們可以看到他自在的基本功和不俗的畫面駕馭能力。無論是運筆走勢的布控還是畫面位置的經營,其秉承了中國山水畫散點透視的法則,在作品隨意的無序有序的形式構成上,保持了傳統中國畫意韻的同時,將感性與理性、繼承與創造、傳統與現代,在看似漫不經心的揮灑和諧融合中,表現了他的審美理想和個人風格。這種風格與畫家有較豐富的花樣設計功底,是分不開的,在其畫中就時有流露如散點紋樣、塊狀紋樣、線條紋樣、墨染紋樣等紋樣布景效果,這樣的布景似乎是普通人能接受的視角景色。在位置經營上相對于有些專業視角的取景而言,他的畫相對有些直觀,貌似沒有太條理化的景色布置,其實是運思精妙亂而有序,繁而不塞,繁密中更見寬綽,更見深遠,近景密密扎扎的線條之間,還可隱約透視出中景的田野建筑,遠山一抹,色彩淋漓,墨意酣暢,不著顏色而墨色益鮮,不著人物而意境更幽,景物隱而不顯,則更見筆墨之靈動,更覺意境之無窮,遠景的山川、飛鳥、云霞,與近景之間的聯系則通過梵寺藏露、舟渚巧設、樹木掩映、前后承接,自然過渡,流露出滿紙的溪麓煙霏、平淡真實的江南景色。其所畫山巒,也頗具長江中下游一帶江南的地理特征,坡陀起伏,土丘微隆。溪中小船蕩漾,遠帆近舟,寥寥數筆,稚氣生動,筆墨工夫之好罕有匹儔。在他狀物寫景的圖畫里秉承著寫實主義的風格,兼具有印象畫的水墨效果,注重神韻,講究筆觸,追求色彩的細微變化,并且在立意與構圖上汲取中國畫的精髓。他的作品既蘊涵渾厚質樸的古典美,又洋溢著蓬勃創新的時代精神。尤其是在近幾年,俞德生創作了一批反映江南風貌的國畫,無論是從氣韻、構思還是手法上都顯示了其老到的藝術功力。
藝術功力還體現在俞德生線條的嫻熟妙用上。這是因為線條是中國繪畫的主要表現手段之一,是國畫構成的民族特征。不管是在南齊謝赫在《古畫品錄》中提到的“六法”,還是在實際的繪畫過程中用筆畫線,勾取物象輪廓,在國畫里都強調線條的作用。線條的長、短、粗、細變化,往往又與表達的形式美密切相關,俞德生繪畫技法上的不拘古人,使抽象的線條保持了充實與豐滿,為整個畫面掌控著平衡。能以濃淡不同的圓融筆墨如中國書法般寫出枝干葉蕊,岸石屋宇的生動畫面,不僅在于他對線條的掌握,更在于他在傳統國畫線條的運用基礎之上又前進了一步,加入了西方美術的用線意識,使線的外在表達更豐富。他用大團緊密的線來代替面,用短促的虛化的線來代替點,在描繪對象的輪廓、明暗、轉折處大量使用線條來表現,在需要皴、擦、點、染的地方也時有用線來代替。在注重這些線條的外在表現運用時,他也不斷創新對線條本身內在藝術魅力的挖掘與呈現。追求線條的的“濃淡”、“曲直”、“潤澀”感,體現所要表達的韻味,如樹木運筆講究潤澀、曲直變化,通過濃淡沖和的妙得,表現干與枝的關系。他嫻熟老到而又豐富的線條之美,美在其或凝重、或輕靈、或剛健、或婀娜。如晉顧愷之的線條“緊勁聯綿,循環超忽”;如南朝陸探微的線條般“精利潤媚,新奇妙絕”;如唐吳道子的線條那樣“虬須之鬢,數尺飛動。”富有運動感、節奏感。再如西方馬蒂斯人體線描似輕松隨意,漫不經心,實際卻恰到好處,內緊外松,線條豐潤飽滿且剛柔相濟,韻態綽約之中蘊含著極為流暢的美感。他的運筆線條、筆墨秀潤、圓渾純樸,不疾不徐、不驕不作,平淡自然、筆意沖融,以書法的線條寫就著畫家對山水的敬意。這些線條變化中求統一,豐富中見協調,給人以清新典雅、致密圓融出神入化的獨特藝術享受。這些線條看似無意揮灑,實則筆筆到位,是外在形態和內在價值的和諧統一,這些線條的聚散變換,巧妙交融,如音樂符號的墨點與周密融通的線條組成了一曲悠揚的江南小調。這首小調唱出了畫家對藝術的敬仰之情,唱出了江湖間草木暢茂,煙嵐蓊郁、野怡之致的江南情調。
這些帶著樂感的線條常被他用以描繪大幅鋪蓋畫面的濃樹密枝,遮蔽天日的濃墨的樹頂墨葉,把整個畫面貫穿起來,組成了通幅黑、白對比強烈而又氣韻生動和諧的基調。樹枝、樹葉的濃密則通過濃墨線條的交錯表現來獲得,簡單幾勾,草草數點,樹木若隱若現,在這些枝葉的空隙處,透出如云似煙的深遠處的叢林枝葉蕊蕾,層次分明而又交錯而成。在樹葉的處理上,采用了層層積點,遍遍漬染,諸種墨色兼施并加正渲沖反水漬等多種藝術表現手法,使一組組樹冠,層層密密,仿佛在密林深處,嗅到了沁人心田的甘淳。樹葉的設色明暗變化得當,林木深處渲染得虛實得宜,顯出了密林深處的松動。整個畫面滿幅靈氣,墨色多變,線條活潑、恣肆瀟灑、閃現著蓬勃的生命活力。
畫面活力的體現是他活力在手的把握,他一筆在手,輕重緩急,提按頓挫,節奏自現,生氣自展,濃淡枯濕,點線暈染,筆法靈活而有彈性,他筆下的這些江南樹木花草,疏密有致,樸拙形象,顯勃勃生機,盎然之氣,真如郭沫若所言:“你的枝條是多么的蓬勃。”似乎在畫面上顯現出了樹木枝椏的水分和植物生命的蓬勃和嫩枝的彈性神韻來,如若在江南的春天里,伴隨著和煦的春風搖曳舞蹈。根據春夏秋冬隨季賦彩,表現出四季江南山水的煙雨迷茫、草木變化,流露出春草初發時的朦朧與午后小憩般的恍惚。
正如袁武所說:“人要有人趣,物要有物趣,自然要有天趣,畫也要有畫趣。”俞德生的畫構圖位置,筆墨修養,用色把握、意境營造、環境渲染都充滿了畫趣。這從其所作山水筆墨蔥蔥蘢蘢,密密層層,意境滋潤,氣韻秀美中是體會得到的。他深明“得之于心,以心狀物”的中國藝術精神所在,強調“格體精微,下筆無妄”。用筆自然下接地氣,中有情懷,上有意趣,繼承并發揚了“不裝巧取、皆得天真”的五代南唐畫家董源之風。畫面上各式各樣的野花野樹遍紙滿框,雜亂卻極其賞心悅目。無盡的墨色渲染了一幅無邊的畫卷,可謂是景色怡人,畫趣天成。
這些妙成的畫趣自然也與其人生態度是息息相關的。在事業上,他能認定一條藝術探索之路而矢志不渝,不管是在工廠從事花樣設計,還是在學校教書育人。都腳踏實地,不存取寵之心,堅守著藝術的執著,慘淡經營,通過觸動自己來感動別人,用美化圖畫來美化世界。他的許多作品以及其上的題鑒就是他心靈和憧憬的真實寫照。俞德生在平常的生活中隨和暢達,淡泊陶然,樂觀善良,深受學生和同仁們的愛戴和欽敬。他對你爭我奪的名利,看得很淡,骨子里總是隱藏著傳統文人的“清高”、“雅逸”和“超脫”的意趣,在創作時強調“須養得胸中寬快,意思悅適,如所謂易直子諒,油然心生。”表現于其作品中,畫趣就成了藝術意趣,之所以為意趣,當然是只可意會而難以言傳的,這正如明代袁中郎所言:“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這些意趣植根于他作為生與斯長與斯成于斯的江南畫家,對地緣文化的獨特熱愛。
俞德生的畫作遠觀有意,中看有景,近察有形。筆下山水畫的江南總是表現出在一片生機的土地上孕育的生態自然,樹林密植景色清幽,極富田園詩意。但都不失“畫如其人”的江南雅逸之氣。俞德勝也曾畫過不少美妙的四季山水圖,但是,我卻更覺得不管畫的是何時何地它們都似江南春季的景色。他的畫筆墨活力十足,畫面、色調、筆觸和所表現的熱情與活潑,反映出水墨兼色的別樣情趣,充滿著希望、歡樂,閃爍著能使四季都變成春季,萬物萌動著勃發之情。妙手得來,舉重若輕甚得各界贊賞和好評,為中國山水畫創新面貌做出了貢獻。
俞德生近七十年來,對其身邊的真山真水的真情未變;作為一個真真的藝術家他追求的是在藝術上不斷攀登,體會的是上下求索,樹立的是彪炳史冊的千秋筆墨。俞德生的畫作為視覺藝術首先還是源于他的視覺吸引和美的感受,其次是在描繪這種自然景色背后所蘊含的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再次是這其中的地域文化價值才會呈現出來,所以我認為獨特的視覺享受和意味是其作品魅力所在。俞德生的水墨從這里發現了一個既尊重傳統,又能表達現實的水墨語言方式。從外在的視覺的美感中實現了傳統水墨語言在繼承中的創新與發揚,其內在的精神是畫家虔誠的心態和樸質的現實主義創作態度,對現實題材的把握與視角的著眼點以及國畫精神的自覺拓展。他的作品追求繼承和發展的完美結合,融匯中西,為風景添彩,為山河傳神,自然而然地達到了景致與情懷,傳統與個性的高度和諧統一,而這真令畫者折服,觀者贊嘆。
【作者單位:常州紡織服裝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