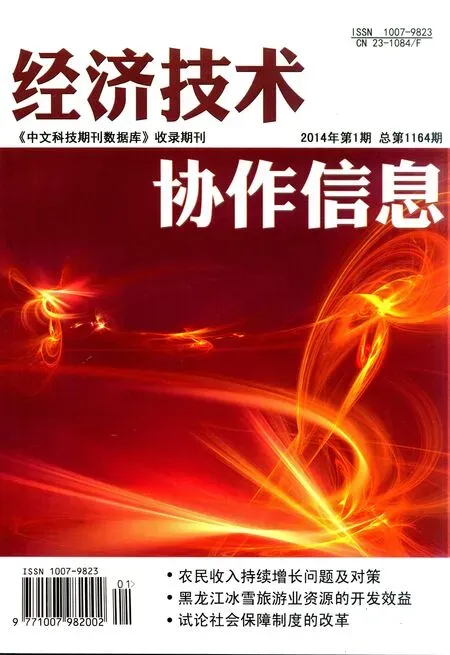進一步加強森林經營的科學管理
張秀榮/龍江縣海洋林場
進一步加強森林經營的科學管理
張秀榮/龍江縣海洋林場
一、前言
一個民族在土地的經營中記錄下自己的歷史,一種文明也在土地的經營中留下自己的烙印,中華文明源于繁茂的森林和河流,我們的先人在森林的庇護下生長,在森林孕育的河流兩畔的沃土上開始耕作,農業文明使人類逐步離開了采獵社會的基礎——森林,在農耕的體育中加速了社會的聚合與發展。工業文明又使人類又重新回到森林之中,但不是采獵而是采伐,并把自然生長的森林改造為可更好地滿足自己愿望的人工林:一種按農業的模式設計的樹木耕作體系,大量使用速生樹種,高密度種植,設計盡可能短的采伐周期、甚至人工施肥等,以期得到最大的利潤回報。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開始感到多年生的林木耕作不像農業耕作那樣穩定,可重復利用、可控制,人工林和天然林之間是有些不同。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隨著對空氣污染,土地酸化、病蟲流行、洪水泛濫沙塵肆虐等痛苦的直接體驗,人類也開始感到自己對森林的需求不止是木材紙漿等物質原料,還有燦爛的陽光、新鮮的空氣和潔凈的水,還有森林與生俱有的防風固沙、保水保土、保護生物多樣性等對人類生存環境的保護功能,而這些“森林產品”對社會的作用正在超過其直接物質原材料生產的作用,這就是人類社會從工業文明階段向生態文明階段進步的標志。
在21世紀開始的時候,人類社會正經歷著從工業文明階段向生態文明階段的過渡,可持續發展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成了具有世界意義的兩個主題,突顯出人們對自然環境脆弱性的深切關注,一種對賦予了人類恩惠的地球的關注。我國整體文明的發展也使得社會對保護生活質量和生活空間的需求也變得十分強烈,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環境問題的嚴重性,認識到保護森林與保持全球可持續發展之間密不可分的內在關系和重大意義。
林業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是可持續的森林。唯此,才會有與之相關的森林產品和服務功能的持續,所以,森林首先必須是有生命力的生態系統,然后才能作為有生產能力的作業對象;另一方面,森林又是陸地生態系統的主體,也就是自然成為社會對自然關注的最主要的承載物。這對林業研究和林業實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要確保森林的近自然特性、保持生物多樣性和多型性,并在實現這些目標的過程中還要可持續地帶來效益,包括木材生產、環境保護和休憩服務等效益。這就是可持續林業的基本特征,就是多功能生態林業的基本要求。
以促進我國林業在多功能生態經營目標導向下的發展,本文總結和分析了我國林業發展的歷史和當前的主要經營管理模式,希望能夠有拋磚引玉和作用,使我們的林業在可持續發展目標指導下努力探索廣袤多樣國土上適應于各種自然和社會條件的多種森林經營模式,并通過這種積極探索使我國的森林生態系統質量和功能進一步提升,為社會快速而可持續的發展奠定堅實的生態環境和再生資源基礎。
二、我國林業的歷史回顧
回顧我國人與森林的歷史,中華文明的初期源于繁茂的森林和河流,我們的先人在森林的庇護下生長、在森林孕育的河流兩畔的沃土上開始耕作,農業文明使祖先逐步離開了采獵社會的基礎——森林,在農耕的體系中加速了社會和聚合與發展。工業文明又使我們重新回到森林之中,但不是采獵而是采伐,無序的采伐和征戰的破壞導致主要人口集聚地區的天然森林資源消失殆盡。
新中國成立后造林努力有了很大成效,但是我們在廣袤的、多樣化土地資源上長期地推廣了一種過于單一的人工林經營模式:一種按農業耕作模式設計的樹木耕作體系,大量使用速生樹種、高密度種植、設計盡可能短的采伐周期、甚至人工施肥等,以期得到最大的的利潤回報。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開始感到在大部分地區的多年生林木耕作不像農業耕作那樣穩定、可重復和可控制。幾十年后我們發現,我們森林的平均蓄積量還不到每畝6個立方米,大部分地區森林病蟲害流行、土地退化嚴重、林木生長不良甚至停止,這些地區幾乎沒法實現最初設計的經營目標。
隨著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隨著對空氣污染、土地酸化、病蟲流行、洪水泛濫、沙塵肆虐等痛苦的直接體驗,我們也開始感到自己對森林的需求不止是木材紙漿等物質原料,還有燦爛的陽光、新鮮的空氣和潔凈的水,還有森林與生俱有的防風固沙、保水保土、保護生物多樣性等對人類生存環境的保護功能,而這些“森林產品”對人口密集地區的作用正在超過其直接物質原材料生產的作用。我們的社會正在從工業文明階段向生態文明階段進步,單一的人工林經營的模式卻完全不能適應這種發展對林業的要求。
旨在保持環境、經濟、社會協調狀態和連續進程的可持續發展模式,是我國社會生態文明階段的主要特征之一,生態林業被認為是我國林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生態林業的基本要求是,通過一切可能的途徑來優化森林結構和功能,永續充分利用森林最佳的產業,這個產業的基礎就是在空間和時間上都必須持續存在的,由多種成分和相互關系構成的森林生態系統。
回顧國際和國內的林業歷史,我們是否可看到在中國從南到北的土地其實包含了一個全球的尺度,在這個尺度上其實不可能以一種局部有效的模式來“放之四海”!例如在目前還存在天然森林保護或掠奪性的皆伐作業都是不可行的,而近自然森林經營模式是否可能是這些地區的一種可行模式?
我們中華民族有著深遠的文化傳統,對人類與森林關系的思考和研究也非常先進,其實“近自然林業”的原始理念早在公元前300年間就已經出現,可考證的如《孟子》所曰:“斧斤以時人山林,樹木不可勝用也;……,樹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引自《孟子:寡人之于國也》)。先人的意思是,若懂得適時適量地進入山林采伐林木,森林資源是可以持續利用的;若懂得在庭院之內種植桑樹,則到老不愁穿戴衣帛;林木若實現持續利用,人民生活即有了一生可靠的保障。孟子一言“斧斤以時入山林,樹木不可勝剛也”,道出了近自然和多功能可持續林業的基本內涵,也道出人類一直追求的“通過利用而經營森林”之近自然林業的最高境界。
但是,這個森林與人類基本關系的核心內涵卻在我們歷史發展的長河中被逐步淡化,以至于當今我國的林業經營管理和實踐中幾乎失去了這種先人智慧與科技發展的歷史鏈接,給人們留下“中國林業科技的歷史不足60年”這樣一個的錯誤的印象,才會出現從先人“斧斤以時入山林,樹木不可勝用”的早期智慧與當今的“可持續林業理論與技術研發”之間缺乏基本的技術歷史關聯的尷尬局面。
三、反思和啟示
面對人類社會從工業文明階段向生態文明階段發展的時代,我們的確應該反思和比較歷史,并從這種反思和比較中對面臨的森林問題找到一些答案。
是否我們現在缺乏的就是對面森林和自然細致耐心地“觀察、記錄、思考和領悟”之原始創新的基本方法?是否我們的先人在提出“樹木不可勝用”的結論前也就是用這樣一種最原始的方法?是否我們林業還可以在“五大林種”功能定義和“公益林”、“商品林”兩大概念的界定之后找到其他更為精細的可行的操作空間?比如目前普遍實行的采伐限額管理在南方集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