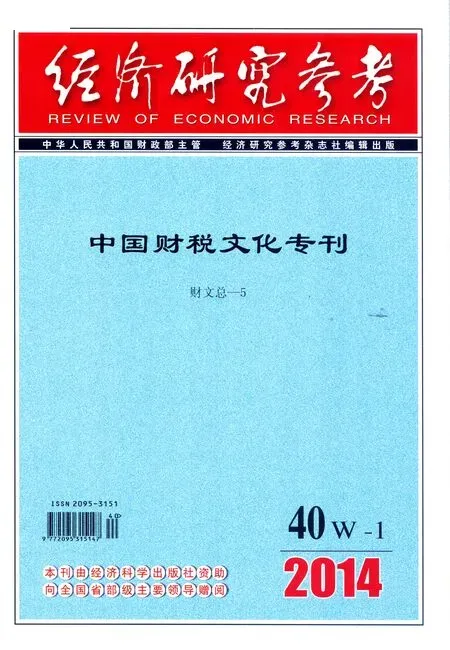略論中央蘇區的稅收工作
中國財稅博物館 余冰玉
略論中央蘇區的稅收工作
中國財稅博物館 余冰玉
在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央蘇區系統的稅收工作開始了,并很快成為了蘇區財政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央蘇區的稅收種類主要有商業稅、工業稅、農業稅等,在一定時期內對蘇區經濟起著促進作用。然而由于局勢的變化和“左”的錯誤,蘇區稅收政策發生了變化并產生了一些不良后果。不過從整體看來,中央蘇區的稅收實踐仍然有著十分深刻的歷史意義。
中央蘇區;稅收政策;局限;意義
一、中央蘇區稅收的發端
作為一種典型的政府行為,稅收工作并不是在根據地形成的第一天就出現的。事實上,自1927 年秋至1931 年秋,根據地的財政收入主要靠紅軍籌款自給,其中包括打土豪籌款和戰爭繳獲兩部分,物資給養是由前線供應后方。因為在根據地尚不鞏固,土地革命尚待深入,廣大農民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的情況下,向土豪地主籌款,既不會增加窮人的負擔,又能解決部隊的給養。當時,不僅現款完全靠打土豪籌得,就是一些因敵人封鎖而得不到的物資,也可以通過打土豪籌款的方式得到。因此從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始,毛澤東就把主力紅軍籌款自給列為紅軍的三大任務之一,提出“紅軍必須同時負起打仗、做群眾工作和籌款……的三位一體的任務”。a《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83頁。雖然在這一時期贛西、閩西等根據地已經出現了初步的稅收行為,但從總體上看仍是零星的、不成系統的,尚未成為根據地財政的主要組成部分。
依靠著從前線獲得的給養,紅軍在1927年至1931年的4年間先后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三次“圍剿”,根據地面積不斷擴大。這一事實證明,在根據地革命初期,在根據地尚不鞏固、經濟又比較落后的情況下,在敵人的嚴密封鎖和不斷“圍剿”的環境下,奉行主力紅軍籌款自給、以前方養后方的財政工作路線是正確的,也是在“向著一切國民黨區域去擴大我們的財政收入,向著一切剝削分子的肩上安放著蘇維埃財政的擔子”。a《江西社會科學》編輯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文件選編》,《江西社會科學》發行科1981年內部出版,第112頁。然而隨著根據地面積和紅軍規模的擴大,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無論是軍隊的給養還是根據地的建設,這二者對財力的消耗越來越大,可根據地之前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卻在逐漸萎縮,因為土豪畢竟是“非可再生資源”,無法持續性的為根據地提供收入,各地分散獨立的稅收制度和辦法逐漸不適應根據地的新變化,面對這樣的形勢,根據地和紅軍的財政收入模式必須轉型,否則革命無以繼續進行。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及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這不僅標志著中央蘇區的正式建立,也意味著根據地系統性稅收工作的開始。畢竟,只要有政權的產生,就必然有稅收的存在,不可能存在不征稅的政權,也不可能存在脫離政權的稅收。合理的稅收積極地促進了根據地的經濟建設,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鞏固和發展,保障革命戰爭供給和蘇維埃政權經費的需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二、中央蘇區的稅收政策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很快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通過了關于頒布暫行稅則的決議,正式頒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按照這一《暫行稅則》的規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行統一累進稅制,在稅種方面則分為商業稅、農業稅、工業稅三種,不過由于蘇區工業力量較為薄弱,為促進當地工業發展,蘇區政府暫時免收工業品的出廠稅,因此“現在簡單的兩方面實行,這就是商業稅與農業稅”。b《江西社會科學》編輯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文件選編》,《江西社會科學》發行科1981年內部出版,第111頁。這項稅則第一次統一了中央蘇區所轄范圍的稅收種類和政策。
中央蘇區的商業稅具體分為關稅與營業稅,其中營業稅是針對商業資本征收的營利所得稅。這一稅種是在工農民主政權比較鞏固的城鎮,經過一段時間的經濟恢復之后,在1932年或1933年才陸續開征的。根據《暫行稅則》規定,營業稅以商家資本規模為劃分依據,從200元至10萬元分為十三個等第規定稅率,其中第一等為資本200元至300元者,稅率2%,按照收入逐級累進,至第十三等為資本8萬元至10萬元者,稅率18.5%。c江西省稅務局等:《中央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頁。10萬元以上的稅率另定。對肩挑小販及農民直接出賣其剩余生產品者一律免收商業稅。另一方面,中央蘇區為了打破經濟封鎖,調節進出口貨物,促進經濟發展,1933年3月中央財政委員會決定在中央根據地開辦24個關稅處,由此建立了關稅制度。蘇區的關稅分為三種,即對有蘇區運往白區的貨物征收出口稅,對由白區運進蘇區的貨物征收進口稅,對白區之間通商貨物經過蘇區邊境的征收通過稅,按照蘇區的不同需要,不同品種貨物關稅稅率有著較大的差別。例如對于急需的食鹽、米谷、石灰等物資,根據地是免收關稅的,而對于當地盛產物品如竹木,或對根據地建設毫無助益的物品如迷信品,則征收高達100%的關稅。d江西省稅務局等:《中央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頁。
農業稅在根據地又稱為土地稅或公益捐,分為田地稅、山林稅等稅種。在農民得到土地,蘇區的生產力有了較大發展,農民生活也有了較大改良的情況下,蘇維埃政府依照農民的經濟狀況,開始征收農業累進稅,起初蘇區政府并未統一規定農業稅的起征點與稅率,而是讓各地根據當地的經濟情況各自規定起征點與稅率。在附《暫行稅則》后作為參考的《江西省農業稅征收辦法》中,有對貧農中農和富農征稅的不同稅率:貧中農農產品平均每家每人收獲量以干谷4 擔以上計算開始征收,最低一級稅率是4擔抽1%,最高一級稅率是15 擔抽16.5%。對于富農從2 擔起即抽1%,最高一級稅率為15擔抽20.5%。e江西省稅務局等:《中央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58頁。
關于豁免納稅一項,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關于經濟政策的決議案中對此有專門的規定:“蘇維埃政府應該豁免紅軍戰士、工人,鄉村與城市貧苦群眾家庭的納稅,如遇意外災害,更應豁免或酌量減輕一切稅額。”a《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七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 年12 月版,第484 頁。其目的是為了貫徹黨的階級原則,減輕紅軍家庭和工農群眾的負擔,同時也是為了保障根據地農業生產的發展。
三、稅收體系的調整及其局限
中央蘇區自1931年開始初步建立了一套稅收體系,這一嘗試雖然為紅軍尋找到了一些新的收入來源,但在接下來的大半年時間里,主力紅軍的自主籌款仍是蘇區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面對急劇變化的形勢,初生的蘇維埃政權對其稅收政策做出了不甚成熟的改變。
1932年5月蔣介石針對蘇區發動第四次 “圍剿”之后,面對嚴峻的防衛形勢,加之王明“左”傾錯誤的影響,蘇區中央局于1932年6月27日通過決議,要求“紅軍的主力必須集中,必須最大限度的迅速行動;要努力做到解除紅軍主力‘分散籌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務(當然不是說紅軍不做群眾工作),使紅軍用全力于決戰方面。”b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送審稿),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編寫組1978年內部出版,第1336頁。因此中央決定從1932年7月起,主力紅軍不再執行籌款任務,其開銷全部由中央財政負責支付。此外,主力紅軍此時不僅不再向蘇區輸血,還在“左”的錯誤指導下盲目擴張,進一步加劇了中央蘇區財政緊張的狀況。面對這樣的情形,為增加稅收收入以充實作戰經費,蘇區政府于1932年7月頒發《關于修改暫行稅則問題》的命令,與前比較,稅率和減免規定做了較大的調整,然而這一新稅則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修改后的《暫行稅則》決定提高農業稅稅率,并降低起征點。加重了貧雇農的負擔。貧農中農之農業稅從3 擔起征,最低一級稅率是4%,最高一級稅率是15 擔抽18%;對富農取消起征點,1擔即征4%,最高稅率為22%。c《紅色中華》1932年7月14日。但是即便如此仍無法解決紅軍巨大的戰爭開銷,還是需要通過其他手段募集資金,例如1934年1月面對第五次“圍剿”時,土地稅征收入庫不及半數,部隊和機關食米不夠,中央政府不得不于1934年兩次預征農業稅:一是6月借谷24萬擔,規定在當年土地稅中歸還;二是7月借谷60萬擔,規定在1935年與1936年土地稅中歸還。這種過量的征收與預支給農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這種轉嫁后的稅收要求,對當地的農業生產產生了負面的影響,既沒有完成預期的征收要求,也脫離了群眾,稅收資源受到了破壞。
其次,新《暫行稅則》規定了較高的所得稅率,損害了從事工商業的小資本商人的利益。與1931年11月通過的《暫行稅則》比較,新稅則加重了工商業者的負擔,商業稅起征點從200元下降到100元,眾多的本是從事小本經營的小商販由原來免稅變為必須承擔6%的稅負;資本201元至300元的小商人,稅率由2%提高到7%,負擔增加2.5 倍;資本3001元至5000元的中等商人,稅率由6.5%提高到12%,負擔增加84.5%;資本80 001元至100 000元的大商人,稅率由18.5%提高到23%,a《紅色中華》,1932年7月14日。負擔增加24.3%。如此一來,原本逐級遞增的征稅標準變得本末倒置,資本較小的小商人反而要承擔更多的稅負,數量眾多的小商販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沖擊了他們的經營。
多年以后的1947年12月,毛澤東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中共中央召集的會議上指出,“對于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經濟成分采取過左的錯誤的政策,如像我們黨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間所犯過的那樣(過高的勞動條件,過高所得稅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業者,不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為目標,而以近視的片面的所謂勞動者福利為目標),是絕對不許重復的”。b《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51頁。經過了那段艱苦的歲月,回過頭來看這種特殊時期的政策,過高的稅率加上過“左”的勞動政策侵犯了蘇區工商業者的利益,給企業的資金運轉帶來了困難,一大批私人企業因此倒閉、停業、轉遷,這都不利于蘇區工商業的健康發展,也給整個經濟帶來了傷害,政策縫隙中殘存的工商業舉步維艱地生存。
四、中央蘇區稅收實踐的意義
雖然中央蘇區后期的稅收工作出現了因不成熟而產生的偏差與錯誤,但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稅收實踐的歷史意義仍是不應忽視的,也是我國稅收史上的重要環節。
第一,盡管有著種種不足,中央蘇區的稅收保障了革命戰爭的物資供給,解決了紅軍和政府工作人員的給養問題。戰爭年代中革命需要的物資是一切工作的保障基礎,統一的稅收制度,團結了當地人民,利于積極開展土地革命,建設蘇區,保衛了紅色武裝政權,這種不全面的稅收也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政策。
第二,中央蘇區的稅收為蘇區整個經濟發展提供了政策性指導,恢復并逐步發展區域經濟、為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敵人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造成的嚴重困難面前,中央蘇區的稅收積極發揮了調控作用,實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對蘇區緊缺的日用品和軍需品實行進口減免稅,鼓勵商人販運日用必需品輸入蘇區,收購蘇區農產品銷往白區,調劑蘇區生產品與消費品之需求與供給,最終目的是為促進經濟發展。在這種特殊時期下,在稅收的扶持下,發展了較多的中小型工商業、合作社,利用有限的資源改善地區生活,調節了蘇區工業品和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鞏固了工農聯盟,破除了敵人的經濟封鎖,促進了蘇區國民經濟發展。
第三,中央蘇區稅收為新中國的稅收奠定了基礎,培養了一批稅收干部,堅持了“依法治稅”的精神。在艱苦卓絕的歲月里,中央蘇區各級稅務機關和廣大稅務工作者不僅卓有成效地開展了各項稅收工作,富有開拓精神地從斗爭中創造嶄新局面,制定切實有效的稅收政策,堅持“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民主與法制傳統,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艱苦創業謀發展,一心一意干革命。蘇區的歲月為我們培養了艱苦創業廉潔高效的奮斗精神,堅持中國革命必然勝利的理想信念,這種精神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第四,中央蘇區稅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的雛形,中央蘇區稅收工作者開創的蘇區稅收工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的預演。在蘇區進行的稅制建設、稅收征管,設立稅務機構,培養稅務干部隊伍,為新中國的稅收工作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和借鑒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稅收工作制度、辦法、措施大多可以在中央蘇區稅收實踐中尋找到歷史的根源和軌跡。
F812.9
A
2095-3151(2014)40-005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