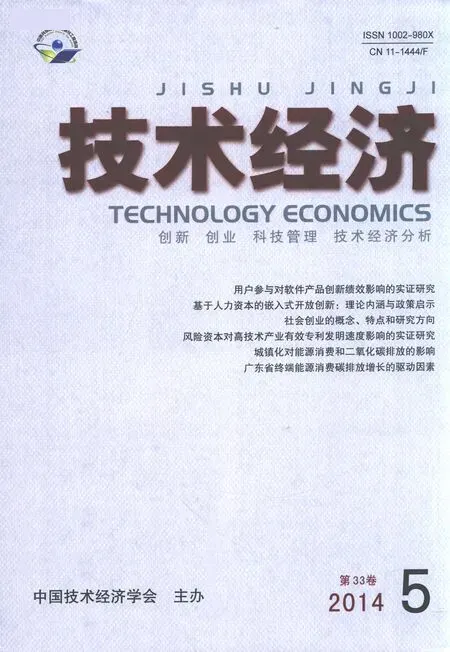智力負債研究述評
曾潔瓊
(武漢紡織大學會計學院,武漢430073)
近30年來,學者們對智力資本的研究興趣大大增加,因為智力資本是企業價值創造和持續競爭力的來源。通常認為,智力資本多多益善。但Caddy認為此觀點有些過于“樂觀”,因為智力資本的創造和發展具有正面和負面影響[1]。大家往往將智力資本與財富創造相聯系,但如果對智力資本管理不善,也存在財富毀滅的風險,即智力資本具有毀壞價值的潛在性。然而,學者們在研究智力資本時往往忽略了智力負債與毀壞價值的潛在相關性[2]。智力負債是智力資本研究文獻中被研究得最少或者說被避免的主題[3]。盡管目前智力資本的“資產方”處于研究的“第三階段”[4],但是智力負債研究仍高度分散,智力負債的確認、計量和管理仍被認為是不確定的[3]。
本文對現有的智力負債研究文獻進行系統性綜述,總結智力負債研究的現狀,并對未來相關的理論和實踐研究提出一些猜測,以期豐富智力資本研究,同時為學術界和實務界進一步開展相關研究(如對智力負債進行確認、計量和管理等)打下堅實的基礎、提供有用的參考。另外,本文展現了智力資本“高風險”的一面,有助于增強智力負債存在的意識,幫助實務界認識和解決智力負債方面的管理或信息披露問題,從而更好地管理智力資本。
1 國內外智力負債研究文獻的統計和特征分析
筆者以“智力負債”(intellectual liability)“無形負債”(intangible liability)“智力資本風險”(intellectual capital risk)“無形風險”(intangible risk)和“智力資本負債”(intellectual capital liability)為關鍵詞,使用Emerald數據庫、Elsevier數據庫、Wiley數據庫和Google學術搜索引擎進行檢索,檢索時間為2000年1月至2013年4月,檢索語言限定為英語。檢索結果顯示,相關論文并不多,只有26篇。然而,此期間有關智力資本研究的期刊論文有2662篇[4]。①由于關于智力負債的國內論文非常少,在期刊網上以“智力負債”和“無形負債”等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只檢索到2篇文獻,即譚勁松的《試論無形負債》(《云南財貿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以及邱國棟和朱宇的《智力資本的二分法——從資產和負債兩個角度看待智力資本》(《財經問題研究》2003年第1期),因此本文基本上闡述的是國外研究現狀。
Harvey和Lusch是最早以智力負債為主題進行研究的學者。他們指出需要平衡智力資本的賬面價值[5],但其研究局限于智力負債與智力資本的比較。
有關智力負債的研究文獻主要致力于概念界定和普及智力負債存在的認識,偏重宣揚智力資本管理的好處[3],卻忽視了智力資本管理的另一面——如果管理不當,智力資本也可能毀壞價值[6]。此情況表明,智力負債研究仍處于初級階段,對智力負債的計量和管理缺乏研究,特別是尚未構架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橋梁,也未提出經過充分檢驗的計量和管理方法和工具。
從研究方法看,與智力負債有關的概念、方法和工具的研究主要是理論研究。很少有研究采用實證方法,即使使用也只是案例研究,目的在于突出智力負債是相關的但在實踐中被忽視的主題。
從時間角度看,智力負債研究并不是連續進行的:第一波研究文獻發表于1999—2003年,共10篇;第二波研究文獻發表于2009—2013年,共15篇;還有1篇發表于2006年。由此可見,以智力負債為主題的研究并不像有關智力資本資產方的研究那樣是連續進行的、受到學術界和實務界的關注。
從發表期刊看,大部分智力負債研究文獻發表在《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上,此外還有刊發關于智力資本研究的期刊——《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Costing》和《Accounting and Vine》。智力負債被認為是非常具體的,只有智力資本領域的學者和實踐者感興趣,沒有像智力資本的資產方那樣能征服廣大群眾、被學術界和實務界所接受[4]。
Petty和Guthrie認為,智力資本研究包括確認、計量和管理3個主要階段,本文據此對智力負債的研究現狀進行系統性分析。
2 智力負債的定義和確認
正如上文提到的,有關智力負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義和確認方面。有關智力負債的研究普遍認為最重要的是增強智力負債存在的意識,故首先必須要弄清智力負債的定義——何況其計量和管理實踐方面的研究也需要定義來支撐。
迄今為止,研究者們提出了智力負債的兩個主要概念:一是認為智力負債是智力資本價值的折舊[1,7];二是認為智力負債是風險或非貨幣性的義務[2,5]。
還有一些學者提出了智力負債的一些其他特征,但是沒有得到智力資本研究界的認同。目前主要有3種主要觀點:Caddy、Guthrie和Petty引入了“孤立知識”概念,即組織已丟失的、處于游離或隔離狀態的知識,認為孤立知識不是智力負債(不確定它是否直接損害企業價值),而是抑制企業潛在增長的一個因素[8];相反,Chapman和Ferfolja提出了“有缺陷的心理模型”(flawed mental model)概念,即未能做出有效的或正確的決策并可能導致不良的結果(即損害企業的人力資本)[9];Abeysekera提出了“情感負債”概念,即能夠消耗智力和有形資產進而減少企業價值的情感因素[7]。
下面詳細評述智力負債的兩個主要定義。
1)智力負債是智力資本價值的折舊。
一些學者認為智力負債是智力資本價值的折舊。企業市場價值與賬面價值的正差通常被認為是智力資本,以此類推,負差就應是無形負債[2]。據此,Caddy認為,當好事變成壞事時就是智力資產減值[1]。Abeysekera認為,智力資本是能產生未來利益的“未被記錄的資源”,而智力負債則是在財務報表中未被確認的、減少企業價值的那些無形義務[7]。
上述這些想法主要來自基于會計角度的智力資本研究,強調智力資本是一個借貸不平衡的賬戶,即與以前確認的資產方相對應的負債方。如此以來,在年度報告中就可以貨幣形式確認智力資本和智力負債[1,7]。Garcia-Parra等認為此定義遠離經典的負債定義,因為它試圖識別出與無形資產有關的價值損失的原因,這些原因可能是使用壞主意、缺乏忠誠和能力或損失關鍵員工[2]。
此定義的優勢主要:提出了一種能增強智力負債存在意識的直接方法;將智力資本作為一個整體看待;引入了“凈智力資本”概念(智力資本儲備時是智力資產,智力資本赤字時是智力負債);符合傳統財務會計的邏輯——按照資產、負債和所有者權益并用貨幣價值來表示。
但是,此定義存在一個根本缺陷,即智力負債缺乏“自己的身份”,采用加總法和財務估價原理來計量智力負債的價值[2]。具體而言:加總法無法設計或應用任何已設計的分類模型來弄清和理解所調查的經濟現象,即使這些想法建立在財務報表報告智力負債的意愿上,加總信息的有用性也值得懷疑[10];所用方法以財務估價法為重點,該方法與現有的大多數智力資本計量方法和工具形成對照——它們通常用于解析智力資本以進行智力資本管理和相關信息披露。
2)智力負債是義務或風險。
在關于智力負債是義務或風險的定義中,智力負債存在3個主要的子定義:第一,智力負債是企業未來經濟資源的流出或為其他實體提供服務的責任,或智力負債是劣質盈利能力的反映[5];第二,智力負債是與現在或過去不適當的決策或行為相關的非貨幣義務[2];第三,智力負債表示與智力資本相關的風險[11,17]。將智力負債作為義務或風險而非折舊是從管理角度來考慮的,目的不是在年度報告中報告智力負債,而主要是對其進行管理。Burnold和Durst認為,為了管理企業的智力資本,管理者需要全面理解與智力資本相關的風險及其對企業的潛在影響[11]。要做到這些,需要使用不同的計量方法進行分析以掌握其屬性和表現。換句話說,不同于之前的流派,此方法關注的是相關的分類模型和其計量方法。
相應地,一些分類模型應運而生。Harvey和Lusch提出了一種模型,先將智力負債分為內部智力負債和外部智力負債,在此基礎上分為流程問題、人力問題、信息問題或結構問題等維度[5]。此研究需要改進之處是應對智力負債進行可操作的分類,以便可以積極地管理每個類別中的突發事件。Stam提出了一種模型,將Harvey和Lusch提出的內部/外部智力負債與智力資本的三維(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和關系資本)相結合進行劃分[12]。內部負債是指造成組織價值創造來源惡化的原因(如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和關系資本);外部負債是指來自外面的、組織無法控制的惡化原因(如“不可抗力”和市場責任)。智力負債的第三種分類方法是由Burnold和Durst[11]提出的,其模型建立在通常使用的智力資本三維度(即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和關系資本)的基礎上。為了對智力資本每個類別的可能風險進行識別和分類,他們區分了人力資本風險、關系資本風險和結構資本風險。其基本想法是:如果智力資本投資可以提高組織的生產力,那么損失重要的智力資本就會威脅組織的有效運作。即使智力負債的計量依賴復式記賬的基本原理,與“智力負債是折舊”的定義不同的地方是,智力負債與智力資產分開估值,而不是作為智力資本的一個獨特項目。有些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將智力負債定義為與智力資本相關的風險;有些研究關注某個類別的智力負債[13];有些研究關注智力資本整體[10]。然而,這些研究僅僅停留在定義介紹上,沒有設計和使用具體的智力負債指標平衡智力資本。
與將智力資本作為折舊的定義相比,此定義更具有分析性、更精確并提出了分類模型。相應地,一些新的概念也隨之出現。就像智力資本一樣,學術界和實務界對之沒有達成共識(如智力負債是風險、義務等)。智力負債的一個主要定義是“智力負債是智力資本風險”,從該定義可感覺到兩種主要用意:一是試圖設計有關智力資本研究的新概念、方法和工具;二是嘗試采用風險計量和風險管理領域中的一些概念、方法和工具來管理智力資本。基于智力資本研究方法的概念,傾向于確認與“資產方”兼容的項目和分類模型,類似于人力、結構和關系負債之間的區別。這樣智力資本的正(資源)負(負債)方就具有一致性并遵循基于資產、權益和負債的傳統報告方法。而倚重風險管理研究而提出的項目和分類模型與智力資本三維模型的就不那么密切相關了,但與針對管理而提出的不同方案或地圖有關[17]。該方法可以依托更堅實的理論和方法,因為風險研究比智力資本研究更為成熟,但也可能出現“老規則對新對象”的問題[14]。
3 智力負債的計量
3.1 基于“智力負債是折舊”定義的量度方法
一些研究者認為,如果基于“智力負債是折舊”的定義量度智力負債,即對智力資本和智力負債分開量度,則度量結果會存在不可靠的風險,因此智力資本和智力負債應是一個聚合項,即應將它們看作一個整體——某一時點的知識集合(即智力資本)客觀地表示為市場價值與凈賬面價值之差。因此,關注的不是單獨的智力資本和智力負債,而是“凈智力資本”,即凈智力資本為正時為“智力資本儲備”、為負時為“智力資本赤字”[7]。
Caddy[1]認為,盡管似乎很難對智力負債總體進行衡量,但是在有些情況下可以很容易計量。例如,當智力負債是“企業已投資項目的失敗”時,智力負債=y+z+a。其中:y表示投資涉及的金額;z表示項目的重置成本;a表示失去的總機會成本的估計值(包括現在的和未來的、采用適當的折現率計算的機會成本)。然而,運用這種度量方法時需要對有些指標(如折現率)進行估計和推測。
上述度量方法是智力資本研究的第一支流派的進化,即智力資本是市場價值與賬面價值之差[14]。但是,以市場價值與賬面價值之差來定義和測度“凈智力資本”這一做法還是冒低效的風險,因為市場價值受太多與智力資本/智力負債無關的因素影響[2]。同時,市賬差的計量結果不詳細無益于企業管理,管理需要易于理解、控制業績的度量方法。此外,從報告角度看,“智力資本儲備”或“智力資本赤字”類似于商譽,被看做管理的黑箱[15]。
由上文分析可知,雖然此方法存在各種問題,但是在年度報告中報告智力負債的思路是正確的和相關的,有助于企業進行管理,因為智力負債如此重要,以至當它們發生時或許會導致企業破產[5]或至少會引起財務危機[16],而且該度量方法非常實用和容易理解。
此法演化為Abeysekera[7]開發的智力資本計分卡。Abeysekera明確表明將智力資本報告整合到企業的主流報告(即損益表,資產負債表和現金流量表)中。智力資本項目通過影響對損益表和資產負債表而被確認,通過構建比率來表明它們對企業智力資本的貢獻(正面和負面)。
總的來說,“智力負債是折舊”這一定義的好處是,提出了量度智力負債的方法且該方法與現有的會計框架兼容。但是,該方法在量度的有用性方面受到限制。
3.2 基于“智力負債是義務或風險”定義的量度方法
基于“智力負債是風險”定義而提出的模型更關注能夠反映智力負債不同維度的指標,不僅僅是其貨幣價值。因此,這些模型建立在敘事、財務和非財務指標的基礎上。基于此定義的文獻依賴于格言“你管理你測量”,因為如果風險是無法計算的或在技術上預防的,他們就不能被評估和管理[17]。所以,簡單地評估風險是不夠的,企業需要基于成功的可能性積極評估和計劃活動。無形風險管理不但專注于最小化風險和成本,而且要確保機會能被最優利用[17]。總之,計量智力負債對于理解智力資本創造和發展的“副作用”是有意義的,并能得到充分管理。
然而,智力負債的計量仍存在問題。由于智力負債的計量仍然是面向資產方進行的,因此其計量結果無法充分支持無形資源的管理。這可能是由如下因素造成的:
第一,缺乏可靠的、經過檢驗的智力負債計量工具,因此需要考慮具體的指標。同時,計量提供的智力資本信息與智力負債信息不媲美,提出的智力資本聲明是一個獨立的、包括不對立的兩部分的報告,其中智力負債部分無法作為專注于智力資本部分的對立面。事實上,量度智力負債的指標(如勞動周轉率、大客戶比例等)的值往往是依據完全不同的參考數據計算得來的,與智力資本指標(如能力水平,客戶保持率等)所使用的參考數據不一樣。
第二,智力資本的風險管理是若干管理者和風險管理者本身的部分任務,他們通常不監控智力資本風險[17]。
第三,對組織內智力負債引起的潛在的或真實的價值毀滅缺乏理解[15],即管理者通常不談論和不管理智力負債。一提到管理智力負債就會使人想起智力資本編纂的模糊性[3],但智力資本的“模糊性”必須被保持,因為管理者更可能通過將其應用于企業所關注的事情來理解和運用它。智力資本從而被制定并被作為解決問題的途徑[3]。同樣,智力負債和其計量似乎也是含糊不清的,有些既可以是資產也可以是負債。例如,當“人員流動率”指標的值較低時,就是智力資本指標(企業人力資本的穩定性),當其值較高時就是一種負債(失去競爭力的風險)。
Giuliani[6]試圖通過對智力資本的資產方(即通常認為的智力資本)和負債方(智力負債)采用一致的分類模型和計量方式來使企業的“無形財富”作為一個整體被表示。雖然這樣做不可能弄清資產與負債的代數差,但是有助于理解智力資本是什么和做什么的問題。他提出了“智力權益”的概念,即智力資本與智力負債的邏輯差。上述做法在分析和計量方面保持了智力資源和負債的個性,但是將它們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和理解實質上是將智力負債整合到智力資本中并讓智力權益有形化。
4 智力負債的管理
如何管理智力負債更是被忽略的問題,只有少數文獻提到該問題,相關研究主要基于“智力負債是風險”的定義。
Kupi、Sillanpaa和Ilomaki[17]認為,雖然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存在管理智力資本的程序和方法,但是通常采取非正式方法管理智力負債。他們還認為,智力負債管理既不屬于智力資本實踐的一部分,也不是風險管理程序。同時,這種非正式方法主要存在兩個局限性:第一,如果風險是無法被計算的或無法在技術上進行預防的,那么智力負債就不能被評估和管理;第二,智力資本的風險管理往往被不同的管理者所承擔(如風險經理、人力資源經理等),而他們會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和方法。這意味著不同責任區域對智力負債的管理缺乏互動,不利于實現智力負債事件鏈的管理[17]。
分析的缺乏和全面視角的缺失阻礙了深入了解組織內部的智力負債——它們是如何摧毀價值的。Kupi等[17]提倡采用風險管理研究領域中的風險管理程序來支持智力負債系統風險的識別和評估。而Giuliani[6]卻表明,因果圖可作為有用的工具用以討論智力負債、揭示智力資本和智力負債以不同方式影響價值創造的過程。他認為:從管理角度來看需要考慮創造和發展智力資本的正面和負面影響以便對其進行充分管理;為了有效地調動智力資本,考慮智力負債的影響與考慮智力資本的影響是同樣重要的。
除了將智力負債作為一個整體開展研究外,還有些研究只關注智力負債的某個方面。例如:Rosett研究了智力負債影響財務困境的可能性和程度[16]。M?enp?和Voutilainen分析了人力資本風險管理中保險的使用問題,認為有些保險提供了人力資本管理中所存在的一些風險的解決方案,有些保險具有先發制人的風險管理工具的功能和激勵所需行為的能力,而其他保險在預先確定的不良事件發生時具有補償投保人的功能[13];Caddy等[8]研究了孤立知識。上述研究旨在定義一個模型來識別和恢復孤立知識以避免或至少減少重復過去錯誤的風險。
總的來講,目前尚不清楚如何管理智力負債,也不知道哪種工具可以支持智力資本的“另一邊”(即相關的風險和義務)的管理。雖然存在這些困惑,但是最重要的是智力負債需要管理,需恰當地進行控制和最小化。為了管理好智力負債,可能參照目前已有的智力資本管理實踐、借用風險管理的理念。根據現有研究可知:必須管理智力負債,而且管理智力資本需要探討智力負債,這有助于企業理解和減少價值損失的風險。
5 結語
5.1 結論
本文旨在揭示、分類和解釋關于智力負債的現有研究,對智力負債的研究現狀進行分析,并為未來研究提供堅實的基礎。本文所得結論如下:
第一,與智力資本的研究文獻相比,智力負債的研究文獻很少且高度分散。智力負債問題往往被忽視,研究者更喜歡討論智力資本的“資產方”[3]。
第二,幾乎所有的研究集中于智力負債的定義或“意識提高”上,只有極少數聚焦于智力負債的計量或管理。目前智力負債的定義主要有兩個:從會計角度將智力負債作為折舊;從管理角度將智力負債作為義務或風險。
第三,盡管存在智力負債不同方面的研究,但是很少有文獻專門研究智力負債的計量模型,只是確定了一些特別的模型工具,但這些模型往往依賴會計基礎或風險測量。如何衡量智力負債仍處于研究的起步階段。
第四,智力資本也可以摧毀價值的事實往往被忽視,因此在實踐中沒有對智力負債進行管理,此方面的研究還未開始。換句話說,學術界和實務界對智力資本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作用進行了廣泛研究,但卻很少關注其在價值毀滅過程中的角色。
第五,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截至目前大部分研究是理論性的,僅有的實證分析也只是案例研究,其內容主要是智力負債是怎樣被感知和管理的。這意味著智力負債概念似乎沒有架起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橋梁,因此提出的大部分概念以及測量和管理智力負債的相關方法和工具沒有得到檢驗或應用。換句話說,智力負債研究似乎處在十字路口,就像10年前的智力資本研究一樣。
5.2 未來研究展望
智力負債屬于智力資本的另一方,其研究應類似于智力資本研究,應既有理論研究又有實證研究,因為智力資本運動來源于實踐,其理論和研究是以實踐為指導的。研究內容應關注加強智力負債的意識以及微觀層面的(即組織特定的)智力負債對資本行為和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方面。具體研究內容可包括:
第一,智力負債的概念、方法和計量很少被驗證和應用,因此采用更多的實證方法進行研究,使其定義、計量和管理方法既有理論價值又有實踐意義。
第二,需要更深入地調查智力負債對組織的影響、了解其影響機理,以便明白應如何管理智力負債并對其進行控制以使其影響最小化。
第三,就像智力資本管理一樣,應關注組織內部不同類別智力負債的結構和如何管理。現有研究主要關注人力資本風險,而管理者如何看待智力負債、在管理中如何使用智力負債等都是有價值的研究問題。
第四,關于智力負債披露問題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開展:一是如何有效地報告智力負債;二是這些信息如何被利益相關者使用。對此,需要考慮智力資本披露的慣性,并且要考慮這樣一個事實——這些信息的利用是有問題的。
第五,為了提供企業無形財富的全景圖,應研究智力資本和智力負債的計量是否應結合和使用以及如何結合和使用。
[1] CADDY I.Intellectual capital:recognizing both assets and liabilities[J].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2000,1(2):129-146.
[2] GARCIA-PARRA M,SIMO P,SALLAN J M,et al.Intangible liabilities:beyond models of intellectual assets[J].Management Decision,2009,47(5):819-830.
[3] DUMAY J.The third stage of IC:towards a new IC future and beyond[J].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2013,14(1):5-9.
[4] GUTHRI J,RICCERI F,DUMAY J.Reflections and projections:a decade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accounting research[J].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2012,44(2):68-82.
[5] HARVEY M G,LUSCH R F.Balancing the intellectual capital books:intangible liabilities[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1999,17(1):85-92.
[6] GIULIANI M.Not all sunshine and roses:investigating intellectual liabilities"in action"[J].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2013,14(1):127-144.
[7] ABEYSEKERA I K.Accounting for intellectual assets and intellectual liabilities[J].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Costing &Accounting,2003,7(3):7-14.
[8] CADDY I,GUTHRIE J,PETTY R.Managing orphan knowledge:current Australasian best practice[J].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2001a,2(4):384-397.
[9] CHAPMAN J A,FERFOLJA T.Fatal flaws:the acquisition of imperfect mental models and their use in hazardous situations[J].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2001,2(4):398-409.
[10] J??SKEL?INEN A.How to measure and manage the risk of losing key employe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ing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2011,8(1):63-75.
[11] BURNOLD J,DURST S.Intellectual capital risks and job rotation[J].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2012,13(2):178-195.
[12] STAM C D.Intellectual liabilities:lessons from the de
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J].VINE:Th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2009,39(1):92-104.
[13] M?ENP??I,VOUTILAINEN R.Insurances for human capital risk management in SMEs[J].VINE:Th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2012,42(1):52-66.
[14] STEWART T A.Intellectual Capital[M].New York: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1997.
[15] GIULIANI M.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value:the intellectual capital cycles[C].The 4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apital,Helsinki,2012.
[16] ROSETT J G.Labour leverage,equity risk and corporate policy choice[J].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2003,12(4):699-732.
[17] KUPI E,SILLANP??V,ILOM?KI K.Risk management of intangible assets[C].IFKAD-International Forum on Knowledge Asset Dynamics,26-27June,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