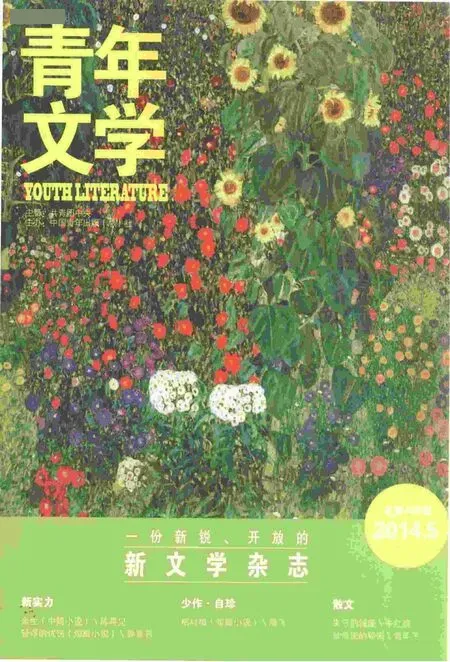輕浮的憂傷
文/薛喜君 [短篇小說]
凌晨四點半,火車停靠在博克圖。它老氣橫秋的喘息聲,令我想起李斯民躺在床上靠吸氧和胰島素活著的媽。
冷風如刀子似的颼颼飛過來,我的臉仿佛是一張被水浸濕的紙,瞬間就被凍僵了。我甚至懷疑,臉會不會脫下一層皮。我焦急地朝出站口的方向逡巡,一個胖墩墩的男人在暗黃的燈光下,雙手舉著“毛小毛”的黃紙殼,臉貼在鐵柵欄的空隙里,宛若探監似的向站里張望。我想他就是我預訂的家庭旅館的老板劉鎖柱吧,我宛若找到組織的地下黨,快步地走過去,說我是毛小毛。一個穿紫紅色羽絨服的女人,撲上來接過我的行李箱,她說:“慢車慢得真像老牛。”
一股煙味撲過來,我憋了一口氣,我知道她就是那個叫楊秀紅的老板娘。我們在電話里打過交道。若不是穿得厚,楊秀紅兩只碩大的奶子就會從緊繃的羽絨服冒出來。劉鎖柱靦腆地看了我一眼,哧地笑一聲,手里的黃紙殼仿佛雞翅膀似的耷拉下來。他接過楊秀紅手里的行李箱,隨手把“毛小毛”交給了她。“我們家住上坎,有一段路呢,快走幾步,這時候正冷得尿尿都得拿著棍。”楊秀紅肆無忌憚地笑,在寂寥的凌晨突兀得像烏鴉的叫聲。
我哆嗦著跟在劉鎖柱兩口子的身后,仿佛是他們夫婦手中牽著的一條流浪狗。我映在雪地上的影子宛若一根冷風中的干樹杈,我看著那根寥落的樹杈,心頭涌上一股悲涼。楊秀紅好像怕我像鳥似的飛走,她不時地回頭招呼我跟上。她說回家給我做小雞燉榛蘑,蒸兩合面饅頭。我氣喘吁吁地跟著他們。早先,我還以為走雪地不會累,原來跋涉在雪地里跟走在泥潭里差不多。幸虧我手上除了一個筆記本電腦,就只有一個拎包。拎包里除了兩瓶保濕水和面霜,還有幾包衛生巾和一袋面包。我有很多漂亮的衣服,可我卻把它們都留在了家里。李斯民把我的心都掏空了,我還帶著他給我買的衣服干什么呢。睹物思人,我走出來就是為了忘卻。
“嗚——汪”,我被突然嗚咽的叫聲嚇一跳,扭頭發現我身后竟跟著一條黑狗。我倏地冒出一身冷汗,咯噔地站住了,黑狗也站住了。它哀怨憂傷的眼神瞬間就擊中了我的心,我差點掉下眼淚。黑狗仿佛是專門來車站接我的,它在風中瑟瑟發抖,冷風還吹起它搟氈的毛。我們對視了一會兒,它又沖我嗚咽兩聲,仿佛是問我怎么才到?那聲音柔軟得像一個嬰兒,溫暖得像與我久別的情人。我想,它或許與我一樣,被公狗拋棄了,就流浪到這個陌生的地方。我蹲下身子,撫摸著它的頭,從背包里掏出夾著火腿腸的面包放到地上,它低頭聞了聞,又抬起頭看著我,輕輕地晃動著尾巴。“吃吧,只有肚子里有食,才能抗住傷害,才能有活下去的理由。”我狂奔而出的淚水,瞬間就被凍在了臉上。
行李箱的滑輪耍賴,在將近半尺厚積雪的路上徹底地失去了作用。劉鎖柱只能把它扛在肩上。他扭頭叫我快走兩步,說前面第一趟房把東山頭有光亮的那家,就到了。劉鎖柱的話被張著血盆大口的冷風吞噬了一大半,我含胸埋頭地緊走著。我隨著劉鎖柱夫婦到家時,天已經蒙蒙亮了。楊秀紅在門口跺了跺鞋上的雪,才推開房門,一只飛出來的水杯正砸到她的胸脯上。她“啊”地叫出聲。
“你兒子夜夜睡我老婆,你連頓像樣的飯菜都不給我吃,熬白菜連片肉都不放。打種的老公雞肉硬得能硌掉牙,還一股騷氣,叫人怎么下咽?我才是這家的功臣,沒有老子,開旅店能不繳稅嗎?”是男人的聲音。
一個身板硬朗的老太太,拎著鍋鏟子站在門口正和屋里的男人對罵。看我們進來,老太太瞥了一眼楊秀紅,說:“你倆剛出去,他就號叫著說我虐待他。”老太太呸了一口唾沫,又轉向東屋,“你這么癱巴,伺候你吃伺候你喝。你還挑肥揀瘦,你想把我兒子累死啊?”
我尷尬地站在那兒。
劉鎖柱放下行李箱,他抹了一把眉毛胡楂兒上的霜,霜瞬間就變成米粒大小的水珠。我發現他的臉紅得如豬肝,不知道是被寒風吹的,還是被剛才的話嗆的。他抱住老太太的胳膊,說:“媽你咋又跟病人一般見識,生些閑氣干啥。”老太太被他推進了西屋。
楊秀紅氣哼哼地白了一眼劉鎖柱,沒好氣地扯開羽絨服的扣子,兩個奶子宛若被圈了一宿的雞,抖落著翅膀從緊繃的羽絨服里鉆出來。她掐著腰站在當地,“我們倆累死累活,就是想讓你們過上好日子。老的不像老的,少的不像少的,整天雞吵鵝斗。”
西屋的老太太沖了出來,她指著楊秀紅說:“你少指桑罵槐,把你癱巴老爺們管好得了。你們一家三口吃我們娘倆的肉,喝我們娘倆的血……”
我震驚了,這個家庭到底是什么狀況,怎么屋里還躺著一個老爺們,還誰睡誰老婆?
緊里間小屋的門霍地被推開了,一個十六七歲的男孩走出來。“吵、吵,睜開眼睛就吵,還說讓我學習,我怎么學?”男孩把手里的碳素筆摔出去。屋子里立刻靜了下來,老太太不聲不響地低頭在案板上揉面。楊秀紅一屁股坐到西屋的沙發上,呼呼地喘氣。劉鎖柱要拉男孩回屋,男孩一甩胳膊,他扭頭發現屋里還站著我,就轉身走進里間,還咣當地鎖上門。吃早飯時,我對楊秀紅說請她幫忙租一間獨門獨戶的房,只要不冷就行。楊秀紅驚愕地看著我,說:“這里有這么多床位還不夠你住,干嗎非要租房呢?還指望掙你兩個床費,給小文交補課費呢。在這里住多好啊,我們家人多熱鬧。”
我勉強擠出一絲笑容,說是寫劇本需要安靜,只有安靜下來,我才能很好地構思故事情節和細節。劉鎖柱在桌下捏了一下楊秀紅的腰,說:“小毛妹子要租房就聽她的。吃完飯,你到西頭老邢家問問,他家兒子結婚時住的西屋一直空著,那屋有火炕還有火墻。”楊秀紅噘著嘴說:“要問,你去問,我可不想把到嘴的肥肉吐出來。”
我知道楊秀紅不想白白失去到手的生意,就說:“我雖然租房子在外頭住,但是在你們家吃飯。反正一趟房,無非東頭西頭,也走不了幾步路。不用特意為我做,你們吃啥我就吃啥,到時候一起交伙食費。”
“嘻嘻,這還差不多,這樣的話,小文寒假的補課費也就有著落了。”楊秀紅毫無掩飾的笑聲又戛然而止,她嘀咕著說,“起個大早,凍得跟茄子皮似的,卻給老邢家接個財神,真不劃算。”
我怕楊秀紅反悔,急忙說:“我不會虧著你們。”
楊秀紅這才笑了。每月八百塊錢,水電另算。房價是楊秀紅替我講下的。她說啥都要替我去交房租,她從我手里接錢時臉色有些不自在,我裝作沒看出來,還對她道了辛苦。楊秀紅又嘖嘖咂嘴地惋惜我不住她家,白白地把租金送給了別人家。再說一個人住著多孤單,還是人多好,過日子就是要人多才能興旺。進屋冷清得像墳塋,有啥意思啊。楊秀紅伏在我耳畔,悄聲地說:“別看我們家有時候吵鬧,可我們不分心。”
我不自在地笑了笑,心里卻很贊賞自己租房的決策,跟雞零狗碎攪和在一起,心情會更加惡劣。楊秀紅又怕我單獨開火,就一再對我說千萬別做飯,這女人一旦沾染上煙火氣,就變成一個黃臉婆了。她還不惜拿自己說事兒,她說:“要不是整日煙熏火燎,我下眼袋哪能耷拉得像魚泡。”楊秀紅沒心沒肺的笑聲宛若掛在馬脖子上的銅鈴,清脆而有質感。
出租房里一應俱全,除了被褥和洗漱用具什么都不用準備。再說,我的要求也簡單,只需一個睡覺的地方,再有一張桌子就夠了。下午,楊秀紅先到出租屋打掃了衛生,還為我燒了火炕和火墻。又從她家客房里拿過電熱壺和暖水瓶,她說,一看我就是寒涼的體質。熱炕頭烙上兩宿,再喝兩碗姜糖水,來例假肚子都不疼。
當晚,我就住到了出租屋。我一進門,一股熱氣撲到臉上,我的臉頓時就返燒了。楊秀紅給我拿來一套嶄新的被褥,她說,這套被褥是貨真價實的軟緞被面,里子也是純棉布的。她和劉鎖柱都不舍得蓋,還想留給小文結婚用。先給我蓋,沾沾我的才氣,將來給小文的孩子蓋。孫子要是學習好了,也好飛出這個地方。楊秀紅說話像崩豆,干脆利落。我被衛生球的味道嗆了一下,哈啾哈啾地打噴嚏。楊秀紅看著我哈哈地笑,她說越活越覺得老話說得對,紅顏薄命,長得好看還有才的女人就不像我們這些粗人,吃啥都香,喝涼水都長肉,腦袋一挨枕頭就睡。我抹了一把鼻涕眼淚,淚眼蒙眬地微笑。
楊秀紅抽了一下鼻子,又抹上炕,拉上了窗簾。“我們這里睡覺很少拉窗簾,連雞鴨鵝狗都不用做記號,就知道是誰家的。你是外來的,又長得有模有樣,晚上再招來好色的黑瞎子,還是擋嚴實吧……”我猜楊秀紅說的黑瞎子,應該是狗熊。聽著她啪嗒啪嗒的腳步聲遠去,我緊繃著的身心一下子就松懈下來。坐了一宿火車,白天也沒睡覺。再加上昨天抽筋斷骨的折磨,我疲乏得快要死了。我匆忙地洗漱之后就躺下了,可能是屋里太暖和的緣故,我一鉆進被窩就睡了過去。子夜一點多,我從心悸中醒來,腿腳綿軟得仿佛從我身上分離了出去。我捂住胸口,呼呼地噓氣,大概十幾分鐘我才從心悸中緩過來。我披衣坐起來,撩起窗簾的一角。夜晚深邃得一片死寂,滿天的星星宛若一盞盞秦淮河水中的祈福燈。從窗縫兒刺進來的風,也讓心悸和緩了一些。我倚在墻上,在黑暗中打量著房間。
突然置身到一個陌生的黑暗中,我有些不能適應。盡管我知道連脊房子的間壁墻都是單磚,但我還是緊張。后窗戶有嘶嘶的響聲,我豎著耳朵細聽一會兒,不像是老鼠。我拉亮電燈,披著衣服下地,原來是從窗戶縫兒溜進來的風,吹著釘在窗戶上塑料布的聲響。我關上燈又鉆進被窩,想再舒服地睡上一覺。可李斯民卻像一個鬼魅,在黑黢黢的屋子里晃來晃去。
王立強若是知道李斯民不要我了,他一定會解氣地喝上半斤燒酒,然后指著我的鼻子說,毛小毛,你到底從一只火烈鳥變成燒雞了吧。還是到我的懷里來吧,只有我才能為你梳理羽毛,讓你美麗起來,讓你做最幸福的女人——我才不要王立強的憐憫,哪怕化成灰燼也不會到他的懷里。我想,只有寒冷才能不讓我潰爛化膿的傷口蔓延,才能凍住洇洇涌出的鮮血。也只有寒冷才和我此時的心情匹配。于是,我義無反顧地在網上訂了一張向北的慢車票。我打點行裝,扔下李斯民留在我房間的氣味,也關上了母親苦苦哀求的啜泣聲。
我想,沒了李斯民,我落腳哪里都是家。我三十歲那年認識的李斯民,我當時正處在失戀的痛苦中,所以李斯民的懷抱令我覺得溫暖,僅僅是溫暖而已。可是半年后,我就癡迷于他的懷抱了。他從認識我那天起,就不斷地給我承諾,他說,如果家里那個神經質的老婆死掉,他就順理成章地娶我。跟我做了三次愛,他說就算那個神經質的女人不死,他的事業穩固之后也會娶我。我毫不懷疑李斯民的承諾,并堅信他是一個有擔當的男人。
李斯民腦袋挨上枕頭就睡,連夢都不做一個。我跟李斯民在一起五年的時間里,從沒聽見他說過失眠。用他的話說,即使是遭遇房倒屋塌的地震,他也是在香甜的酣睡中被埋在廢墟下。也就是說,他一定在無知無覺甚至在幸福中死去。李斯民告訴我,他在認識我之前喝酒比對做愛有興趣,他說只有跟我在一起才有男人的沖動。在他那個神經質的老婆身邊,他從來都是蔫軟不舉。有時候他老婆纏著他,還興師動眾地質問他外面是不是有人,他說一聽見老婆說這些話,恨不能揮刀自宮……我真愚蠢,每次聽到這些話時,我都把李斯民的頭放在懷里,母獸般地安慰他。可是,這樣的時候多半是白天,夜晚,李斯民又要回到那個神經質的女人身邊,雖然那個女人令他不舉。李斯民惆悵地說,無論他人在哪兒,心都在我這里。我對李斯民的話堅信不疑。但是,一到夜晚我就哀傷起來。我想,一個女人最大的悲哀莫過于不能擁有相愛男人的夜晚,不管那個男人的愛有多熱烈,都不能溫暖夜晚的悲涼。
那天,李斯民清晰地表明了態度,我還愚蠢地追問他:“你不要我了嗎?”李斯民干脆地說:“可以這么理解。”我當時哇的一聲就哭了,還跌坐在地上。李斯民在我的哭聲中離去。我爬起來趕緊去拽他,合上的門擠扁了我的手指。我顧不得疼也根本不知道疼,操起電話按下那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號碼,可是,任憑我無數次地撥過去,他都不接。再后來,就是秘書臺小姐溫柔冷漠的提示音了。其實,早在半年前,我就察覺到了李斯民的態度,只是我自己掩耳盜鈴罷了。一想到我自取其辱的下場,疼痛的淚水一直流到耳朵眼里。

清晨,隔著窗簾,我知道太陽出來了。可我卻沒能起來,不但全身肉疼,連骨頭都酸疼。我想我是病了。斷了一夜的煙火,火墻和火炕都漸漸地涼了。我蜷縮在冰冷的被窩里,茍延殘喘得宛若一只瀕臨死亡的野狗。我極想喝一杯熱水,就顫巍巍地爬起來,水太熱,沒能喝下去,我把水放到炕沿上涼著。我冷得直打哆嗦,我想,如果我死在這個陌生地方,不讓李斯民知道,也算找回一點自尊。我昏昏沉沉,不知道是睡著還是醒著,李斯民幽靈似的在我的枕邊繞來繞去。我說你別轉來轉去的,弄得我頭暈。
李斯民說,該起來了,你看看,這都幾點了。
我孱弱地睜開眼睛,原來是楊秀紅大聲小氣地敲著窗戶。“都燒成火炭了,還非得要一個人住,這要是有個好歹的我可咋向你的父母交代啊。”楊秀紅仿佛跟我認識了多年的朋友,或者就是我的親姐姐。她邊幫我穿衣服邊數落我,“回咱家炕上躺著,我給你熬兩碗姜湯,再讓劉鎖柱他媽給你拔火罐,祛祛風寒,保管你下晚就退燒。晚上給你燉一鍋羊蝎子,保管你吃得你脖臉淌汗,明天就像只活蹦亂跳的小狗。”
我咧嘴笑了,眼前仿佛有一只搖尾乞憐的小狗在蹦跶。
我在楊秀紅家躺了三天,這三天楊秀紅像我親媽似的給我端湯拿藥。三天后,我雖然腳下還像踩在棉花上,但我還是堅持著回到出租屋。楊秀紅又趁機提出讓我搬到她家住,她和劉鎖柱他媽好能照顧我。我堅持著說自己有夜晚寫作的習慣,再說,寫劇本需要孤獨。我還向她保證不會再生病,要盡快給她寫一部好看的電視劇,她這才哈哈地笑了。楊秀紅堅決要我在她家等著,她先去把出租屋的火墻和火炕都燒熱,免得我再著風寒。劉鎖柱呵呵地笑出聲,他說楊秀紅就是嘴碎,其實心眼極好。
“遭雷劈的,你們在那屋有說有笑的,存心想渴死我……”東屋炕上的癱子扯著嗓子叫罵起來。
劉鎖柱伸了一下舌頭,三步并作兩步跑過去。
回到出租屋,我躺進被窩才打開手機。我換了一個只有我媽和李斯民知道的號碼。自從家里出來,我就沒開機,但我設置了秘書臺留言。我期待著能看到李斯民思念我的短信,或者找我的電話。可是,除了開機時的音樂聲,電話死寂一樣地沉默著。等了半天,才有兩個提示音。我調動了全部體力,給我媽回了電話。怕聽到我媽哀求的哭聲,我報了平安就趕緊掛了。我罵自己,真是個賤人,李斯民冷漠地表明了態度,把你傷得體無完膚,你還念念不忘地想著他。
我妄想用睡眠驅逐李斯民,可他就像我的影子似的,姍姍從遠處走來,還穿著我給他買的那套銀灰色西裝。看到他的身影,我哭了。他快步地奔跑過來,我抖成一團地等著他來抱我。不想,一條大黑狗鉆出來,咬住了他褲管。李斯民極力地要甩掉黑狗,可黑狗就像一塊膠皮糖似的叼著他的褲管不放。我撿起一根木棍,費了好大的力氣才跑過去。我卻看見黑狗流出的眼淚,我咯噔地站住了。李斯民喊,毛小毛,你為啥不打它,難道你和黑狗有私情,它睡了你嗎?我手中的木棍還沒舉起,就啪嗒地落在地上。我哭著喊,“李斯民,你太惡毒了。我怎么能跟一條黑狗睡覺!”
我痙攣般地打了一個哆嗦,醒了過來。原來,手機掉在地上。我撿起四分五裂的手機,發現自己全身大汗淋漓。我再也睡不著,聽著鉆進窗戶縫兒的風哧哧地叫,淚水又不可遏制地流了下來。難道是心臟出了問題?我家族有心臟病史,我爺爺我爸爸我叔叔都死于心梗。李斯民最擔心我心臟。去年,他聯系了一家上海大醫院,強烈督促我去做了心臟造影。檢查結果出來,我第一時間告訴了李斯民。他笑呵呵地說,沒問題就好,沒問題就好。我從上海飛回來,李斯民去機場接我。我們像小別的夫妻,緊緊地擁在一起。那晚,我們就在機場附近找了一家賓館住下。李斯民摟著我,他說有一種活在世外桃源的感覺,仿佛天地間就剩下了他和我。我被他摟得透不過氣,就喃喃地說,我四十歲以前一定要生個孩子,以后萬一你不在我身邊,你的孩子也能終生陪伴我。不知道為什么,說這些話時我有些哽咽。李斯民又一次死死地摟著我。他說:“你可真是個傻丫頭,你看我是那種不負責任的人嗎?再等一年,頂多一年,就接你回家。上有老下有小,事業才又剛到了一個高點上,總得先穩固事業再料理了家事,才能讓你跟著我享福啊。”
李斯民的話讓我熱淚盈眶,也讓我更加死心塌地地愛他。
李斯民早年喪父,他又是家中的長子。他的婚姻是母親一手包辦的,從他結婚那天起,母親就一直跟著他生活。李斯民有一個兒子,去年大學畢業直接讀了本校的研究生。他老婆早早地從企業退休了,在家陪著他媽。李斯民除了本能地與老婆生了孩子,別的從來沒體會到。他還說,他早有離婚的念頭,只是一直沒能遇到心上人,再加上他媽身體也一天不如一天。這些年,他除了孝敬他媽,就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事業上。所以,仕途才節節攀升。李斯民說他不愿意回家,若不是母親每天晚上都要吸氧打胰島素,他干脆就不回去了。他說他最不愿意看到他老婆那張烙餅似的圓臉。
那晚,我們說了一夜的話。
我仿佛被施了魔咒,對李斯民的話從來都沒有半點懷疑。王立強說我是傻瓜,他說,只有他最了解李斯民。他斷言,李斯民是我的克星,早晚把我傷得連骨頭渣兒都找不到。我說王立強你夠陰毒的了,你知道李斯民是那種惡毒的人,還把他領到我面前。王立強嘻嘻地笑,隨后他又憂傷地說:“我一直以為你心里有我,誰想到,你們倆一見面就像狼見到羊。你還有理了,我憋屈跟誰說去。”王立強還說我中了毒,甘愿鉆進李斯民下的蠱里,迷得魂兒都丟了。“早晚有一天,你這只驕傲的火烈鳥會被李斯民傷得體無完膚,還不如一只煺毛的雞。算了,我也不難受了,等你崩潰,我再給你疊壩。到時候你就知道了,我才是最愛你的那個人,只有我才能把碗里的最后一口飯給你吃。”他信誓旦旦地說,“毛小毛,我的心門永遠都為你敞開著,我的懷抱永遠都是你最安全的港灣。”
我上挑起眉毛,說:“王立強,白瞎李斯民對你那顆心了。”
王立強嘁了一聲,“我從來沒忘李斯民對我的提拔,我也用另一種方式回報了。你問問他,他身上穿的戴的除了你買的,有一多半是我孝敬的。他家換水龍頭,通下水道的活兒都誰干的?”他梗著脖子盯著我,“一碼是一碼,他幫了我,我會回報他。可我還不至于低賤到用我的感情做交換,再說,我可以什么都沒有,但不能沒有你。”
“哼,王立強你就等著喝我和李斯民的喜酒吧,我們倆一定修成正果,以實際行動粉碎你的陰暗和齷齪。”王立強還沒反應過來,我就走了。
王立強和李斯民是同鄉。王立強大學畢業留在這個城市,而李斯民卻是從部隊轉業來的。可李斯民的仕途宛若猴子爬竿一樣地往上躥,而王立強卻停止在副科級的門檻上。李斯民幫他打開了關口,王立強邁進正科級的門里,還到一個權力部門當了科長。我曾開玩笑地說,他們倆好得穿一條褲子。李斯民笑,說我想象力可真豐富。王立強瞟我一眼,沒說話,但我看見他嘴角上的不屑。王立強十年前離的婚,兒子被前妻帶去了美國,前妻很仗義,說離婚歸離婚,但如果你愿意來美國,我也想辦法幫忙。畢竟你是兒子的爹。王立強用沉默拒絕了前妻。后來,王立強一臉虔誠地告訴我,他留下來就是為了好好照顧我,呵護我。王立強說:“毛小毛,現在像你這么真誠的人都死絕了,像你對感情這么投入的人也絕種了。可你卻誤入歧途,我是男人,李斯民一張嘴我就知道他要說啥。他比你大十幾歲,他怎么能為了你放棄家庭,他把仕途看得比命都重。”
我當時還呸了王立強一口唾沫。
我不再流淚了,但我的心卻在滴血。
我想,我要努力適應沒有李斯民的生活,還有,要盡快進入創作狀態。我除了去楊秀紅家吃三頓飯,其余的時間都在出租屋里寫劇本。原本我沒有吃早飯的習慣,但是我在這里不能不吃,如果我不吃早飯,楊秀紅就不厭其煩地敲窗戶叫我。我不能太任性,她不是我媽,我與她只是主雇關系。楊秀紅家的飯桌上只有我們四個人吃飯,小文從來不上桌,他都是陪著癱子在東屋吃飯。昨晚,豬骨頭燉酸菜,我看見楊秀紅把肉多的骨頭都盛給了炕上的癱子,滿滿的一小盆。吃飯時,劉鎖柱他媽疑惑地問,肉多的骨頭咋都沒有了。我急忙接過話茬,說肉都爛在了鍋里,我啃骨頭不愛吃肉,就愛吃骨頭上的筋頭巴腦。要吃肉的話,哪天就燉一鍋肉可勁吃。劉鎖柱他媽吧嗒吧嗒嘴,沒說話。楊秀紅感激地看我一眼,還把一塊骨頭夾到我的碗里。吃罷晚飯,楊秀紅又往我手里塞兩個雞蛋,她說晚上寫電視劇時會餓。我指了指東屋,示意給炕上的癱子或者給小文留著。楊秀紅擺擺手,還把手指放到嘴唇上,做出噓聲狀。
小文從不跟我說話,有時候和我迎頭碰上,他也低下頭快步地走過去。我能看出來,這個男孩有一肚子心事。癱子的屋我從來沒進去過,但我熟悉他的聲音。我從小文的相貌上也辨別出癱子些許的模樣,我想,癱子曾經一定是一個棱角分明的男人。是疾病磨去了他男人的資本,連同他的聲音都粗糙得有了毛刺。
劇本寫到第十三集時,我說啥都進行不下去了,就像被魚刺卡住了喉嚨。我憋得難受,就穿上大衣想在近處走走。就在我走出房門的當口,隔壁家的窗簾宛若一塊幕布,嘩地落了下來,院子里一下子就和黑夜野合了。我一個人圍著房前屋后轉著圈,刺骨的風并沒能讓我的心靜下來。前年,李斯民借著考察的名義去了澳大利亞,回來給我帶一條玫瑰紫色的澳毛圍巾。我歡喜得不得了。我說,你看人家澳大利亞的東西就是好,顏色純正不說,這毛也一點雜質都沒有。李斯民說,他就買了一條,只有這個顏色這個質地才能襯托出我高貴典雅的氣質。我幸福地笑出了聲。我說過,我對李斯民的話從來都深信不疑。那年冬天,李斯民帶他們單位機關的幾個部門,去撫遠看打冬網。他支支吾吾地說,這次出行讓帶家屬。他還說很想帶我去,這對我創作劇本有幫助,他說冬網可壯觀了,如果運氣好,一網下去就能打上十幾萬斤的魚。這次就讓那個神經質的女人去吧,反正她去就是看個熱鬧,再說,一年她也出不了幾次門,沖她伺候我媽的分兒上,就讓她看回熱鬧。我含酸捏醋地說,我是有身份證沒有身份的人,連看熱鬧的份兒都沒有。李斯民尷尬地咧嘴笑了,然后就不住聲地哄我。我心里雖然不好受,但李斯民走的那些天,我喪膽游魂得什么都干不下去。
一聽說他回來了,我立刻就跑到辦公室去看他。我剛進屋,辦公室主任給李斯民送來了照片,還鑲上了藝術框。李斯民和他老婆親密地挽著手,他老婆穿著一件泛著亮光的黑色皮草,看上去雍容華貴,脖子上圍著一條跟我一模一樣的玫瑰紫色的澳毛圍巾。
我轉身走出李斯民的辦公室。
沒過幾日,我就消氣了。我想,我前輩子一定是欠了李斯民的債,或者真如王立強所說,被他灌了迷魂藥。但我并沒有因此吃一塹長一智,而是依然對他的話深信不疑。我認為李斯民偶爾騙我是情有可原,是迫不得已。那日,王立強買了一大堆帶魚對蝦螃蟹來家里看我媽,我拿出澳毛圍巾跟他顯擺。王立強說:“毛小毛你可真讓我鄙視,瞅你那個嘴臉,好像撿了狗頭金。你好歹也是一編劇啊,有點自尊好不好。”
我媽說:“立強這個孩子,是刀子嘴豆腐心。”
我又跟李斯民的影子糾纏了一夜。
傍晚,我去楊秀紅家吃晚飯,一進門就發現氣氛不對。劉鎖柱和他媽不在家。我里外屋踅摸了一圈,小文端著一碗豆腐燉肉,和兩大碗米飯進東屋了。楊秀紅唉聲嘆氣地坐在西屋的炕桌前,“哼,娘倆一起走了,有能耐別回來,看老娘能不能過。”她說完嚶嚶地哭起來。
“哭啥哭?他走了,沒人摟你睡覺了是不,真不要臉——”癱子惡狠狠地罵。
楊秀紅的哭聲戛然而止,兩眼紅腫地盯著窗外。我猜想又是因為東屋的癱子,全家鬧不樂呵了。我瞥一眼楊秀紅,悄悄地走到院子里,給劉鎖柱打了電話,我說你快回來吧,紅姐想你都想哭了。家里沒有你哪能行,沒有老太太也不行啊。劉鎖柱猶豫了一會兒,說他和他媽到海拉爾看望老鄰居,他媽歲數越來越大了,老鄰居們也都一天比一天老。今年看一眼,明年就可能看不著了。劉鎖柱說,讓他媽跟老鄰居們多親近幾天,過些天就回來。我又悄悄地告訴楊秀紅,說劉鎖柱帶他媽回家看望老鄰居,過兩天就回來。楊秀紅撇了撇嘴,笑了,可她馬上收斂笑容,說:“愛回不回,誰想他啊。”
那晚,我從楊秀紅家回來都半夜了。吃完飯,楊秀紅說啥都不讓我走,再著急寫劇本也不差這一會兒。她說屋里少了兩人,心空落得發慌。楊秀紅讓我坐炕頭,她隨手給我拿過裝瓜子的笸籮,說坐著也是坐著,嘴別閑著。楊秀紅一支接一支地抽煙。我最不能接受女人抽煙,可她抽煙的姿勢令我著迷。楊秀紅人胖,卻長一雙修長的手,她夾著香煙的手一點都不做作。不像我在很多場合看到抽煙的女人,她們夾煙的手都故意翹著,如果身邊有男人,女人做作得不像抽煙,倒像搔首弄姿似的勾引人。我問楊秀紅今天煙癮咋這么大,是不是柱子哥沒在家,心里不好受借煙消愁?楊秀紅說一天沒怎么抽了,劉鎖柱沒在家,沒人給她點煙。我哧地笑出聲,說你也太擺譜了,抽煙還得柱子哥給你點。楊秀紅望著窗外,說小毛你不了解我和劉鎖柱。我期待地看著她,希望她能給我解開他和劉鎖柱,還有東屋那個癱子之間的秘密。可她突然轉過頭,問我電視劇寫多少集了?我說寫一半了。楊秀紅說:“我看寫電視劇也沒啥難的,你咋寫得那么慢。電視劇里的人跟博克圖的人也差不多,都是家長里短,兩口子打架,婆婆和媳婦鬧別扭,再就是‘第三者’插足什么的。我們這兒也一樣,只是我們這兒的事兒沒人寫。對了,我在電視里還沒看過像我們家這樣的事兒。”
“唉,你要是把我寫成電視劇,保管全世界的人都愛看。算了,說我也沒啥意思,我不過就是個苦命的人。對了,小毛,你跑到博克圖,是躲什么吧?是別人占了你的窩,把你擠出來了,還是你占了別人的窩,被人家給轟出來?”楊秀紅突然像不認識似的盯著我。我被她盯得發毛,就說困了。我宛若被人攆著追打的野狗,夾著尾巴跑出了楊秀紅家。
事實上,我還沒占窩,就被李斯民一腳踢開了。我曾經無數次地想過,萬一哪一天李斯民的老婆找上門,我就說,是我勾引的李斯民,是我甘愿做他的情人。但有一句話我必須要告訴她,先別責怪男人出軌,想想男人為什么出軌。我要保護李斯民,讓他體面地走出家門。可是,李斯民沒給我機會,輕輕地一句話,就把我打發了。說起來,我早就有察覺,只是我太相信李斯民了。大概半年前,我撥李斯民的手機,正說得纏綿,他辦公室的座機響了,我聽到好似讓他多穿衣服之類的話。我問李斯民是誰的電話,他支吾著說是一個部門主任,又馬上更正說是他們家那個神經質的女人。我雖然疑惑,但是沒往深里想。直到那天,聽到李斯民那句“可以這么理解”的話,我又想起那個電話。我想,李斯民的窩可能從來沒有空過。
這一夜,我幾乎沒合眼,把我和李斯民的事從頭到尾地捋一遍。我不想再跟李斯民的影子睡覺,我的心被他撕得千瘡百孔。我狼狽得像一只流浪的狗,憔悴得宛若一只被剔了肉的雞骨架。我不能跟著他的影子,悲傷地過一輩子。
一個星期后,劉鎖柱和他媽回來了。楊秀紅過來叫我,她說晚上做小雞燉蘑菇,鯽魚燉豆腐,讓我早點過去吃晚飯。我說,我把這一集寫完就過去。她樂顛顛地走了。天擦黑時,我走出出租屋。一天一地的雪宛若穿著孝服的女人,一下子就撲到我懷里,雪也讓我想起靈棚前掛著的白色燈籠。我抿嘴笑了,我的心情卻由此好了起來。我推開楊秀紅家的房門,一股熱氣就撲在臉上,我說人多就是好,連屋里都有熱乎氣。楊秀紅白了劉鎖柱一眼,哈哈地笑。那晚上我吃了一小碗紅豆二米飯,我對楊秀紅說:“哪天,我們再燉酸菜大骨頭吧。我去買那種肉多的骨頭,你腌的酸菜酸脆爽口。”我們倆對視了一眼,她哈哈地笑了。
吃完晚飯,我手插在大衣兜里,慢悠悠地往出租屋里走。我饒有興趣地聽著腳下的雪嘎吱嘎吱地響。我想我該走出李斯民的影子了,我不能一輩子都活在他的影子里。博克圖只是我治療憂傷的圣地,而不是我長久生活的落腳地。我要盡快地完成電視劇最后十五集,回家孝敬我媽。這晚,我一覺睡到大天亮。到博克圖以來,我第一次睡了一個安穩覺。早上我神清氣爽地到楊秀紅家吃早飯,一進門,我疑惑地問她怎么不見劉鎖柱。楊秀紅喜滋滋地告訴我,她想吃蒜燒鯰魚,劉鎖柱趕早市去了。我乜斜她一眼,說:“還是柱子哥心疼你吧。”
“那是。”楊秀紅說完,瞥了一眼東屋,嘆口氣。

劉鎖柱不但買回了鯰魚,還帶回了王立強。我夢游似的盯著眼窩塌陷眼珠充血的王立強,他悠然地點了一支煙,還給劉鎖柱和楊秀紅每人一支。他噗地吐出一口煙,說:“你以為你躲到這兒,我就找不到你了。”他又狠狠地吸一口煙,用手指點著我喊,“毛小毛,你怎么凈往我心口上捅刀子,你不聲不響地就走,你還讓不讓我活?”
劉鎖柱和楊秀紅知趣地進了西屋。我瞥了一眼他們的背影,咬住下嘴唇沉吟了一下,我惡毒地說:“不想活就死,難道你跑到博克圖殉葬來了?”王立強的臉一下子就軟得像蛋黃,他笑嘻嘻地說:“我這不是惦記你嗎?行了,別慪氣了,少了李斯民還不活了呀。我就住在劉鎖柱家,陪你些日子。你也待差不多了,跟我一起回去。”
我走出劉鎖柱家時,砰地關上房門。
我買了兩袋方便面和熟食,在王立強沒離開的日子,我不準備去楊秀紅家吃飯。可是,只隔了一天,楊秀紅就和劉鎖柱他媽來找我了。劉鎖柱他媽拉著我的手,說閨女,兩口子哪能生真氣。我說,我和他只是朋友。劉鎖柱他媽笑呵呵地說:“別看我人老眼花,可我心沒瞎。現在的男女都說是朋友,還不是為了避人耳目。這樣糊弄人,就是為了有朝一日把自己當成大閨女再嫁給另一個男人。”劉鎖柱他媽擤了一把鼻涕,又說:“閨女,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別再鬧了,跟他回去生個孩子吧。”
我無奈,只好如常去楊秀紅家吃飯。我必須要面對王立強,找個時間,我要再次跟他表明心態。責任是男女雙方的,我以前對他沒什么承諾,以后也不能。因為,我不能對他負責任。只有讓他徹底死心,才能割舍。李斯民若不是讓我徹底絕望,我還會神魂顛倒地往他的被窩里鉆,我還會整天渾渾噩噩地祈求他給我恩賜。一個不能擁有男人夜晚的女人已經很悲哀了,若是再等著男人施舍愛,就悲涼得沒有溫暖可言。我有些激動,我要對王立強盡快說出我的想法,不能讓他像我一樣受折磨。
那晚,天上的月光和地下的雪交相輝映,一天一地的素白。雪夜里,我故作堅定地迎著王立強的凝視。我說:“你應該明白,即使你追到博克圖也是徒勞。”
“愛不愛我,是你的事,我愛你是不能改變的。”我差點被王立強氣吐血。我使勁地咬住嘴唇,半天才說:“那好吧,你打算在這里住多久,什么時候回去都跟我沒有一毛錢的關系。”
王立強走的前一天晚上,他來出租屋里找我,問我可不可以和他一起吃頓飯。我說,我們不是天天都在一個飯桌上吃飯嗎,你看看你,都快成劉鎖柱家的上門女婿了。王立強皺著眉頭說:“毛小毛,我就那么令你討厭,連單獨吃頓飯都讓你惡心嗎?”他抽了抽鼻子,“為了找你,我熬得臉都綠了,你還把手機關了。哼,只要你偶爾開一次,我就是鉆進地洞里也能把你挖出來。”
王立強找了一家魚館,說這家魚館的嘎牙魚好吃,他請劉鎖柱在這兒喝過酒。我白了他一眼,沒說話。我要了四瓶海拉爾啤酒,我喜歡喝啤酒,每次和李斯民吃飯,他都給我要四瓶啤酒。他知道我喜歡喝涼啤酒,每次一進飯店的門,就叫服務員給冰鎮上。我已經好久沒喝啤酒了,甚至都快忘了啤酒的滋味了。博克圖可真是一個天然的大冰柜啊,喝進嘴里的啤酒如一條線,涼哇哇地落到胃里。我的胃宛若一個蕩婦,張狂地迎接。我咂了咂嘴,為自己滿上。王立強搶下酒瓶子,說:“非得喝吐血是吧,你那胃怕涼不知道啊,還不如喝一缸子白酒呢,又舒筋又活血。”他仰脖干了杯子里的白酒,“我不在,你怎么喝我都管不著,當著我面你不能禍害自己。我們倆這一輩子恐怕都不能在一股道上走,原來我以為李斯民是我們中間的一堵墻。在博克圖的這些日子,我終于想明白了,有沒有他,咱倆也是兩股道上的車。我也想開了,但我對你的心這一輩子都不變。有一點,我可以保證,無論你什么時候需要我,我都會第一個出現。這就是我的命。”他直視著我,又說,“我這輩子就是為呵護你才來的,我也想愛別的女人,哪怕從你身上離開那么一陣子,我的心也不會這么疼了。可是,我做不到,真的做不到……”王立強眼睛里先是盈著淚花,沒一會兒,兩行淚水就流了下來。
我被王立強的傷感打動了,但我又能做什么呢。除了愛情,我什么都能給他。我故意不看他,埋頭吃魚,仰頭喝酒。那晚,王立強流著淚喝了七兩“悶倒驢”。我們哩溜歪斜地走出魚館,走到上坎,他往東頭的劉鎖柱家,我回西頭的出租屋。王立強突然叫住我,他近乎哀號地說:“毛小毛,男人的眼淚不完全是哀傷,還有絕望。”
我咯噔地站住了,沉吟了一下說:“王立強,有時候執拗的愛,傷害自己也傷害別人。你離開我,一定能找到一個好女人。”
“不可能,我的心在你的身上太久了。”
王立強走了,我堵在心口上的一塊大石頭也沒了。可他近乎號叫的聲音,在我耳邊響了好幾天。沒有王立強,我又從容地去楊秀紅家吃飯了。楊秀紅咂著嘴感嘆,她說,真不明白你們這些大城市里的人,那么好的男人送上門還不要,要是我早就抓住不放了。我呵呵笑,我在心里說,可惜我不是你。
臘八那天晚上,楊秀紅家又吵翻了天。
在北方流傳著“三九四九,棒打不走;臘七臘八,凍掉下巴”的諺語。所以,一到這個日子,博克圖的家家戶戶都吃黃米飯,意在粘住下巴。楊秀紅早上就泡上了一盆大黃米,她問我,是吃葷油拌黃米飯,還是吃白糖拌黃米飯。我說你們怎么吃我就怎么吃,反正入鄉隨俗嘛。楊秀紅嗔怪地說,你倒是好伺候。楊秀紅做飯絕對是把好手,她燜黃米飯時還放了紅豆。黃米飯又黏又泛著豆香,我搛了一筷子黃米飯放進嘴里,我說原汁原味才能吃出米香。劉鎖柱他媽說,早年間吃黃米飯拌葷油拌白糖,是那時候的人肚子里也沒油水,現在想吃肉就吃肉,冬天還能吃到茄子辣椒,簡直就像做夢。劉鎖柱呵呵地笑,他說別給小文他爸拌葷油了,他這兩天肚子不好,拉稀。楊秀紅說也行,把豆腐里的肉多給他盛些,爺倆都是肉食動物。劉鎖柱剛把飯菜端過去,癱子就叫罵起來:“你們合起伙來欺負我這個癱巴,你們是存心要苛打死我。以前,我吃黃米飯都是拌葷油,現在連白糖都沒有。干脆給我一包老鼠藥得了,你們倆好快活。”
劉鎖柱和楊秀紅面面相覷,楊秀紅的臉騰地紅了。劉鎖柱他媽嘁了一聲,說這日子真沒法過了。她轉身回到自己屋里,砰地關上門。
“啪嚓——”一碗黃米飯摔到門上。嵌著紅豆的黃米飯宛若一個吊死鬼,悠蕩著粘在門板上,大花瓷碗卻落到地上兩瓣兒了。楊秀紅哇的一聲號啕起來,她一邊哭一邊數落:“你躺在炕上吃香的喝辣的,還罵聲連天。也就攤上劉鎖柱吧,給你端屎倒尿,還得受你謾罵,換個人早走了。他走了,你死在炕上生蛆都沒人管……”
“好你個胳膊肘往外拐的娘們,還幫著野男人擠對我。”一只碗又飛出來,豆腐豬肉撒了一地。
“還不是你出的損招,是你當初要把劉鎖柱招來,你說給我們娘倆找條活路。你活下來了,活好了,就卸磨殺驢……”
我看見劉鎖柱眼眶濕了,他低頭走了出去。楊秀紅哭得稀里嘩啦,一邊哭還一邊收拾。我幫楊秀紅收拾完殘局,才走出院門,剛拐過去,發現墻拐角處有一團黑乎乎的東西,還有煙頭忽明忽暗地閃。
“柱子哥,多冷啊,進屋吧,一會兒紅姐該找你了。”
劉鎖柱憨憨地笑:“不冷,心里著把火。”
我哧地笑出聲,說:“紅姐的話感動你了吧。”
劉鎖柱對著煙頭又燃起一支煙,抽了兩口,奄奄一息的煙頭宛若還陽的病人,又現出暗紅的螢火來。“小毛,我不圖啥,有個女人跟我好好過日子,累點苦點都能扛住。”
這晚,我終于理清楚了劉鎖柱在這個家里的身份。
炕上的癱子是楊秀紅法律上的丈夫,小文是他倆生的孩子。十年前,楊秀紅的丈夫販賣牛羊。每個月往返一趟呼倫貝爾,從內蒙古牧民手里買來牛羊,再雇卡車拉到省城去賣,賺取中間的差價,讓他們一家三口過得豐衣足食。那時候,楊秀紅的穿戴都是從省城的大百貨商場買來的。左鄰右舍艷羨不已,都說楊秀紅有福氣,嫁個能干的男人。楊秀紅揚著臉,說和他搞對象時爹媽都不同意,餓了三天才贏得了勝利。誰知,那次男人拉著一卡車羊外加五頭牛去省城,卡車剛走到大興安嶺,司機和押車的人合伙把他打個半死,推下車。幸虧一個路過的鄂倫春人救了他,否則他連命都沒了。在醫院里住了一年,花光了所有的積蓄,保住了命卻落得高位截癱。全家的生活一落千丈,后來連吃藥的錢都沒有了。小文也不念書了,說省下錢給他爸治病。男人躺在炕上唉聲嘆氣,有一天,他讓楊秀紅去海拉爾一趟,找一個叫劉鎖柱的朋友。
“這個人可靠,我要是死了,他能幫你料理我的后事。往后,你們娘倆也有依靠了。”
劉鎖柱來了,先是兩個男人談。后來又把楊秀紅叫進去,三個人插上門,在屋子談了一宿。劉鎖柱第二天早上趕回海拉爾,再來時,不但拉來了全部家當,還把他媽也帶來了。劉鎖柱是個光棍,家里就他和他媽兩個人。他媽一輩子不生養,還早早地守了寡,劉鎖柱是她撿垃圾時從垃圾堆里撿回來的。他媽就靠撿垃圾把他養大,左鄰右舍都知道劉鎖柱的身世,到了該結婚的歲數也沒有姑娘肯跟他。他媽四處托人,可姑娘們一聽說是劉鎖柱都搖頭,說連親爹親媽都不知道的男人誰敢跟?要不,誰好好的孩子舍得丟到垃圾堆里。劉鎖柱的身世阻礙了他的婚姻,可他卻不以為意。他說,自己沒死在垃圾堆里,就是老天爺憐惜他。劉鎖柱對他媽百般孝順,他十八歲就不讓他媽再出去撿垃圾,自己到處打零工,掙錢養活他媽。他就是在牧民的家里幫工時,認識的小文他爸。小文他爸每次去呼倫貝爾收羊時,都提前給他打電話。
楊秀紅是劉鎖柱第一個女人,他是處子身來到楊秀紅家的。兩人在旅游區賣了一陣子土特產,由于不放心留在家里照顧小文和癱子的老太太,他倆出兌了攤位和零散的貨回到博克圖。轉年就在房山頭接出幾間房子,開了有十二張床鋪的旅館。旅游季節,劉鎖柱負責接送客人。楊秀紅和他媽就負責做飯洗洗涮涮,不到三年就把給小文他爸治病借的錢還上了。還完了饑荒,劉鎖柱和楊秀紅商量,每月除去全家的生活費和小文他爸吃藥的錢,剩下的錢都給小文攢著。小文學習雖然在班上屬于中下游,但語文好,作文在全學校數一數二。劉鎖柱也把他當親生兒子養,每次出去都給他買東西。前年,小文想要雙耐克運動鞋,楊秀紅嫌貴說啥都不給買。冬天時,劉鎖柱借輛三輪車,蹬著三輪車到車站拉客。不但給小文買了一雙耐克鞋,還給他買一套運動服。
劉鎖柱說:“別看小文不吭聲,可他心里有數。”
我想留在博克圖過完年再走。一來劇本沒寫完,二來我要在博克圖過一個有年味的春節。我已經喜歡上了博克圖的寒冷和幽靜,寒冷令人神清氣爽。一聽說我留下過年,楊秀紅歡喜得哈哈地笑,她說,年夜飯一定多做幾個菜,再拍幾張照片留個念想。初三早上,我突然接到王立強的電話,他啞著嗓子對我說:“毛小毛,我對男人的眼淚又有了新的解讀。”
“我洗耳恭聽。”我的口氣明顯不耐煩。
“男人的眼淚是死亡。李斯民死時,淚珠像黃豆粒似的滾落下來……”
我的心被一只大手揪了一下,我咽了幾口唾沫打斷他的話:“王立強,你真歹毒。這么多年,我還真沒看出來。”
王立強哽咽地說:“毛小毛,李斯民真死了,死在辦公室,那天他值班。心梗。死時,手里攥著一只銅鑄的小蛇。陰陽先生費了好大的勁才掰開他的手指。我想,那條小蛇一定與女人有關吧,但絕對不是你,你屬羊。”我沒告訴王立強那條小蛇是我。大前年,我在拉薩買回一條銅鑄的小蛇。據說,是尼泊爾那邊過來的東西。我告訴李斯民,我就是一條美女蛇,一條只纏著你的美女毒蛇,你若是敢背叛我,我就吐出毒芯子毒死你。
“柱子哥,給我一支煙。”我顫抖地點著了煙。我想,我該回去了。走的那天,我把三千塊錢掖在軟緞棉被子下面。我說啥都不讓楊秀紅和劉鎖柱送,楊秀紅哭得眼泡紅腫,劉鎖柱他媽也一個勁地抹眼淚。她讓我把這里當成娘家,夏天旅游季節時再來,那時候菜園子里的豆角辣椒都下來了,想吃啥就摘啥。楊秀紅拉著我的手扭捏地說:“小毛妹子,姐對不起你。其實租房費是六百塊,我多說了二百。”
我攥著她的手說:“你是我姐,我們不分彼此。”
我拐過房山頭,小文突然從房后躥出來,他站在我面前說:“還來嗎?”
我點頭。
“那我攢錢買電腦,你教我寫作。”我發現,小文笑起來時嘴角往上翹,倒和劉鎖柱有點像。
從三輪車上下來時,天還沒完全黑透。我逡巡著車站的四周,想再仔細看一眼博克圖。突然發現在車站門口的垃圾箱旁,一個年輕女人正在翻撿垃圾,冷風掀開她污跡斑斑的棉襖。女人撿起一個飲料盒,仰起頭往嘴里倒,一條黑狗伺機撲上來搶奪。我滿臉淚水地看著眼前這個女人,用一瓶礦泉水換下她手里的飲料盒,還從背包里掏出劉鎖柱他媽煮的茶雞蛋,塞到她手里。女人呆滯地看著手里的茶雞蛋,宛若在看稀奇古怪的東西。難道,她好久沒吃茶雞蛋了嗎,還是她迷了心竅已然不認識茶雞蛋了。她又盯著我了一會兒,癔癥似的笑起來。“他不要我了,領著女人走了,還帶走了豆豆,豆豆是我這兒掉下的肉啊……”女人哇的一聲哭起來,還使勁地揪肚子,仿佛要從肚子里再揪個豆豆出來。
“天冷,系上棉襖扣——”任憑我怎么說,女人都不再搭理我,她一心一意地翻著垃圾。那條黑狗嗚咽地叫起來,我蹲下身也給它一個茶雞蛋。黑狗并沒吞下雞蛋,而是久久地望著我,我看見它眼里的淚光——我來時,只有這條流浪的黑狗迎接我,走時,又多了一個瘋女人。回到家,我才知道,李斯民的葬禮上,王立強比李斯民老婆的哭聲還大。我不知道李斯民在死亡的那個瞬間,是否感受到了幸福?只可惜,我們連交流的機會都沒有了。李斯民死了,我沒哭,但我卻開始抽煙了,而且很上癮。
我媽疑惑地念叨,怎么好模樣兒地就成煙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