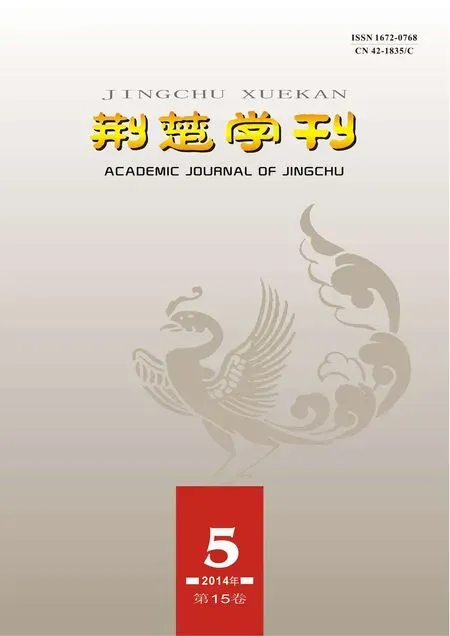新型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的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模式選擇與民族交融問題研究
劉 洋,姜昳芃
(大連海洋大學(xué) 法學(xué)院,遼寧 大連 116023)
新型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的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模式選擇與民族交融問題研究
劉 洋,姜昳芃
(大連海洋大學(xué) 法學(xué)院,遼寧 大連 116023)
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發(fā)展戰(zhàn)略已成為我國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的新引擎,如何在國家大的戰(zhàn)略背景下構(gòu)建適宜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城鎮(zhèn)化發(fā)展模式,兼顧少數(shù)民族固有的民族特質(zhì)傳承和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推進(jìn),成為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而伴隨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推進(jìn),少數(shù)民族群體在融入城市社會過程中也面臨著一系列問題與障礙;文章試圖從包容性發(fā)展、慢城理念、民族傳承等多維度路徑來實(shí)現(xiàn)新型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的民族交融與民族和諧關(guān)系的構(gòu)建。
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模式;民族交融
一、引言
城鎮(zhèn)化水平已經(jīng)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重要標(biāo)志,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管理水平與社會文明程度的核心標(biāo)準(zhǔn)。中國正處于城鎮(zhèn)化發(fā)展的關(guān)鍵階段,提高新型城鎮(zhèn)化水平,對于拉動內(nèi)需增長、推動國民經(jīng)濟(jì)升級轉(zhuǎn)型、提升城鄉(xiāng)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促進(jìn)國民經(jīng)濟(jì)良性循環(huán)和社會協(xié)調(diào)健康發(fā)展,都具有重大的前瞻性與現(xiàn)實(shí)意義。截至2013年底,中國城鎮(zhèn)化率達(dá)到53.73%[1],僅從數(shù)值比例上來看,中國已成功的步入到城市化發(fā)展的中級階段。然而,中國城鎮(zhèn)化比例迅速提升的背后卻是東、中、西部地區(qū)發(fā)展的非均衡性和居民幸福指數(shù)的泡沫化,顯然,城鎮(zhèn)化率的增長并不等于幸福感的提升。2013年上海市城鎮(zhèn)化率已達(dá)88.02%,除內(nèi)蒙古(58.71%)外另七個民族省區(qū)(廣西、西藏、寧夏、新疆、貴州、云南、青海)的城鎮(zhèn)化率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最低的西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率只有22.75%[2]。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由于受自然地理、歷史文化、社會經(jīng)濟(jì)等因素的影響,導(dǎo)致城鎮(zhèn)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薄弱、產(chǎn)業(yè)規(guī)劃缺乏持續(xù)性,民族地區(qū)整體城鎮(zhèn)化水平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qū),甚至遠(yuǎn)低于全國城鎮(zhèn)化的平均水平。
在當(dāng)今中國乃至世界,民族地區(qū)的發(fā)展?fàn)顩r一直為人們所關(guān)注。民族地區(qū)的社會經(jīng)濟(jì)發(fā)展?fàn)顩r關(guān)系到我國經(jīng)濟(jì)社會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也是我國全方位跨越式發(fā)展戰(zhàn)略的有機(jī)組成部分。城鎮(zhèn)化作為推動中國內(nèi)涵式發(fā)展的新引擎,是擴(kuò)大內(nèi)需的潛在動力,也是社會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的必經(jīng)路徑。因此,加快實(shí)施城鎮(zhèn)化發(fā)展戰(zhàn)略是少數(shù)民族和民族地區(qū)群眾真正實(shí)現(xiàn)全面小康社會的關(guān)鍵,也是實(shí)現(xiàn)民族地區(qū)又好又快發(fā)展的需要。十八大關(guān)于“新型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的確定,經(jīng)歷了十六大提出的“走中國特色的城鎮(zhèn)化道路”以及十七大對其的進(jìn)一步補(bǔ)充,由此可見黨中央和國務(wù)院對新型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的重視程度和實(shí)施力度。新型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的“新”集中體現(xiàn)在更加強(qiáng)調(diào)城鎮(zhèn)化的內(nèi)涵式建設(shè)與以人為本的可持續(xù)性上。如何在國家大的戰(zhàn)略背景下構(gòu)建適宜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城鎮(zhèn)化發(fā)展模式,以新型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作為契機(jī),將新型城鎮(zhèn)化發(fā)展作為民族地區(qū)情感交往、交流、交融的實(shí)現(xiàn)過程,是本文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二、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模式選擇的多維度詮釋
城鎮(zhèn)化模式的選擇是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理論和實(shí)踐模式的基礎(chǔ),是新型城鎮(zhèn)化內(nèi)涵式發(fā)展的重要起點(diǎn),城鎮(zhèn)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使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產(chǎn)方式日益趨同,如何挖掘和優(yōu)化民族地區(qū)獨(dú)特的資源稟賦和發(fā)展條件,通過比較優(yōu)勢走特色城鎮(zhèn)化發(fā)展之路成為第一要務(wù)。因此,民族地區(qū)以自身的資源稟賦為依托,或以特色資源模式,或以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模式,或以產(chǎn)業(yè)優(yōu)勢模式,或以歷史文化模式,或以多種資源配置復(fù)合模式,從多維視角下展開理論詮釋,對于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推進(jìn)具有重要的前瞻意義與指導(dǎo)意義。
(一)資源維下的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模式選擇
依據(jù)城鎮(zhèn)發(fā)展對資源的依賴程度,有學(xué)者把資源分為必需型資源和特色型資源。必需型資源是發(fā)展所必需的資源,包括土地資源、水資源、人力資源和資本資源[3],民族地區(qū)大多礦產(chǎn)資源豐富,應(yīng)結(jié)合當(dāng)?shù)刭Y源特色優(yōu)勢進(jìn)行產(chǎn)業(yè)開發(fā),通過共建特色鮮明的礦產(chǎn)資源產(chǎn)業(yè)集聚區(qū),實(shí)現(xiàn)“以產(chǎn)帶業(yè)、以業(yè)興城、產(chǎn)城融合”,以此來促進(jìn)民族地區(qū)的特色發(fā)展。
在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模式的選擇中,在資源維的視角下,合理開發(fā)豐富的礦產(chǎn)資源;依托各地區(qū)豐富的自然礦產(chǎn)資源,合理有序的建立符合國家產(chǎn)業(yè)政策的礦產(chǎn)品深加工冶煉產(chǎn)業(yè)集群;加大能源的開發(fā)力度;發(fā)展特色旅游業(yè);引進(jìn)高新技術(shù),加強(qiáng)生物技術(shù)的開發(fā)應(yīng)用等,為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發(fā)展奠定堅實(shí)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如西部資源與能源豐富的民族地區(qū)可根據(jù)自身的資源優(yōu)勢,創(chuàng)立自主資源品牌,帶動其他相關(guān)的產(chǎn)業(yè)聯(lián)動,如四川、重慶、貴州等礦產(chǎn)和化工資源豐富的地區(qū)宜選擇此類城鎮(zhèn)化模式。
(二)環(huán)境維下的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模式選擇
自然地理環(huán)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基礎(chǔ),是城鎮(zhèn)化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重要物質(zhì)條件,一定程度而言,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的發(fā)展無法擺脫自然環(huán)境的約束和影響。中國傳統(tǒng)的城鎮(zhèn)化路徑是忽略資源有限性和環(huán)境脆弱性的非集約性粗放式發(fā)展道路,在新型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指導(dǎo)下,為保護(hù)民族地區(qū)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應(yīng)從外延式的粗放發(fā)展轉(zhuǎn)向內(nèi)涵式的集約發(fā)展,走資源和環(huán)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包容性發(fā)展道路。
自然地理環(huán)境豐富的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模式可以依托當(dāng)?shù)靥赜械淖匀画h(huán)境資源和民族風(fēng)情,依托環(huán)境資源,大力發(fā)展具有民族風(fēng)情特色的旅游業(yè)和文化產(chǎn)業(yè),增強(qiáng)城鎮(zhèn)吸納農(nóng)牧業(yè)勞動力的能力,這既實(shí)現(xiàn)了對本地資源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hù),又實(shí)現(xiàn)了本地農(nóng)牧民就地城鎮(zhèn)化的目的。如云南地區(qū)有豐富的植物資源, 廣西地區(qū)有復(fù)雜豐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資源,這些地區(qū)宜選擇此類城鎮(zhèn)化模式。
(三)產(chǎn)業(yè)維下的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模式選擇
主導(dǎo)產(chǎn)業(yè)是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持續(xù)發(fā)展的生命力[4],只有城鎮(zhèn)產(chǎn)業(yè)的不斷集聚并形成一定的規(guī)模效應(yīng),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口向城鎮(zhèn)轉(zhuǎn)移與集聚,為當(dāng)?shù)氐陌l(fā)展提供充足的勞動力資源,以“產(chǎn)城融合”為動力推進(jìn)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的發(fā)展。所謂“產(chǎn)城融合”,是指產(chǎn)業(yè)與城鎮(zhèn)的融合發(fā)展,即以城鎮(zhèn)為基礎(chǔ),選擇合適的產(chǎn)業(yè);以產(chǎn)業(yè)為保障,驅(qū)動城市更新,形成產(chǎn)業(yè)、城市、人三者之間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模式[5]。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的發(fā)展必須要有合適的支柱產(chǎn)業(yè)作為支撐,“在工業(yè)化和城市化相伴而行的時代里,工業(yè)開發(fā)創(chuàng)造了財富,財富又把人集合起來。但是在今天,工業(yè)化和城市化并不一定是同義詞。”[6]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發(fā)展的定位一定要依據(jù)本地的資源稟賦與區(qū)位特征條件,發(fā)揮自身的比較優(yōu)勢,積極引導(dǎo)和培育并形成與發(fā)展特色主導(dǎo)產(chǎn)業(yè)。
民族地區(qū)可重點(diǎn)發(fā)展特色鮮明的支柱產(chǎn)業(yè),如以資源為導(dǎo)向的水電煤礦產(chǎn)的開發(fā)產(chǎn)業(yè)、以環(huán)境資源為導(dǎo)向的觀光旅游產(chǎn)業(yè)、以特色民俗產(chǎn)品為導(dǎo)向的中藥材采集加工產(chǎn)業(yè)、特色農(nóng)業(yè)的小農(nóng)場DIY體驗(yàn)產(chǎn)業(yè)等,逐步形成體現(xiàn)地域文化特色的“一鎮(zhèn)一業(yè)”的就地城鎮(zhèn)化模式。同時,“特色產(chǎn)業(yè)主導(dǎo)型”城鎮(zhèn)化模式的發(fā)展也離不開政府宏觀政策的扶持和鼓勵,如法律法規(guī)的出臺、政策規(guī)劃的修訂、資金技術(shù)的植入,都為民族地區(qū)的特色城鎮(zhèn)化提供了支撐條件。此外,產(chǎn)業(yè)維視角下的特色城鎮(zhèn)發(fā)展,還要發(fā)揮好主導(dǎo)產(chǎn)業(yè)的示范效應(yīng),適當(dāng)延伸和拓展產(chǎn)業(yè)鏈,聚集當(dāng)?shù)氐膭趧恿Y源,形成主導(dǎo)產(chǎn)業(yè)的規(guī)模效應(yīng),促進(jìn)當(dāng)?shù)亟?jīng)濟(jì)的內(nèi)生性增長。
(四)文化維下的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模式選擇
文化是一個民族特有的氣質(zhì)符號,是民族多樣化發(fā)展的靈魂和精髓所在,也是維系民族精神傳承的紐帶和橋梁。然而,在新型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傳統(tǒng)文化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致使具有民族特色及代表性的傳統(tǒng)文化出現(xiàn)了不同程度的自然流失與被迫廢棄,如民族語言、民族文字、傳統(tǒng)民居、民族服飾、民族飲食、民族工藝、民族戲劇、民族器樂、民族歌舞、民族禮儀、民族醫(yī)藥、民族習(xí)俗等逐漸遠(yuǎn)離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人民的日常生活。
欒川縣處于中國中央造山系秦嶺造山帶后陸逆沖褶皺帶復(fù)合部位,伏牛山腹地。這里礦產(chǎn)資源豐富,早在幾年前就已探明各種礦產(chǎn)達(dá)50余種,其中,鉬儲量達(dá)206萬t,居亞洲第一,世界第三,2006年被中國礦業(yè)學(xué)會加冕為“中國鉬都”。
文化維視角的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模式,可以通過努力開發(fā)、利用和提升多元化的民族文化資源,以民族地區(qū)特色文化為依托,推進(jìn)傳統(tǒng)文化特色的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進(jìn)程。從民族地區(qū)文化的保護(hù)到開發(fā)與利用,都要與民族地區(qū)的城鎮(zhèn)化進(jìn)程形成良性互動,推動環(huán)境友好型和資源可持續(xù)型的城鎮(zhèn)化模式構(gòu)建,這也是民族地區(qū)新型城鎮(zhèn)化頂層規(guī)劃的有機(jī)組成部分。我們可以將民族地區(qū)的語言文化、藝術(shù)文化、節(jié)慶文化、民族信仰文化等元素吸納到民族地區(qū)新型城鎮(zhèn)化文化建構(gòu)中,將民族地區(qū)傳統(tǒng)文化精華與現(xiàn)代化文化元素結(jié)合起來,推進(jìn)以文化維度為導(dǎo)向的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進(jìn)程。
(五)多維資源配置下的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模式選擇
結(jié)合民族地區(qū)的發(fā)展定位及本地區(qū)的資源稟賦情況,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模式可以根據(jù)文化、環(huán)境、產(chǎn)業(yè)、資源多維綜合選擇。針對民族地區(qū)的特點(diǎn),許多學(xué)者提出了頗具特色的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模式,如“小規(guī)模、多層次、多中心、適當(dāng)集中”的城鎮(zhèn)化模式[7]、邊貿(mào)帶動型模式、資源開放型模式、綠色城鎮(zhèn)化模式、候鳥型“飛地”性旅游推進(jìn)型城鎮(zhèn)化模式、“飛地”型城鎮(zhèn)化模式等[8]。根據(jù)已有研究,可以看出強(qiáng)調(diào)資源稟賦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相結(jié)合的城鎮(zhèn)化發(fā)展模式已基本達(dá)成共識,如何在這個大前提下探索多維化城鎮(zhèn)化動力結(jié)構(gòu)成為未來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努力的方向。
三、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包容性民族融合的過程
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促進(jìn)少數(shù)民族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與社會融合,然而這一融合的過程不可避免的會使人們的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趨同,也會使人們面臨因城鄉(xiāng)文化差異帶來的城市社會文化適應(yīng)問題,需要克服民族文化差異性所帶來的就業(yè)、社會交往、生活、心理和文化適應(yīng)等問題。這使得少數(shù)民族同胞在民族情感上抗拒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也成為導(dǎo)致城鎮(zhèn)化進(jìn)程在民族地區(qū)推進(jìn)較慢的原因之一。
然而,少數(shù)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瑰寶,在城鎮(zhèn)化過程中,要有意識地保護(hù)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以保護(hù)少數(shù)民族人民的情感和保持中華民族文化多樣性的格局。如何兼顧少數(shù)民族固有的民族特色傳承和推進(jìn)城鎮(zhèn)化進(jìn)程,成為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需要解決的問題。包容性民族融合理念對于這一根本問題的解決,具有理論的前瞻性和實(shí)踐的開拓性意義。來源于包容性增長的包容性發(fā)展理念,囊括了包容性增長所忽略的其他內(nèi)容[9]。所謂包容性民族融合理念的前提是發(fā)展,核心要義是保持民族特色、推進(jìn)民族發(fā)展,最終目標(biāo)是各民族的優(yōu)秀特質(zhì)為全民族所共享、促進(jìn)民族融合。具體而言,包容性民族融合理念的內(nèi)涵如下:
(一)包容性民族情感
民族情感是一種主觀體驗(yàn),它產(chǎn)生于民族成員對自己所處的實(shí)際地位和民族關(guān)系的道德倫理定位,是對本民族或他族產(chǎn)生的一種愛憎好惡判斷。過強(qiáng)的少數(shù)民族同胞的民族自豪感容易產(chǎn)生一種情感誤區(qū),拒絕接受他族正確和善意的批評,忌諱提及本民族的落后之處,從而不利于民族的成長和發(fā)展。在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不可避免的會將先進(jìn)的思想理念、技術(shù)和生產(chǎn)方式注入到民族地區(qū),勢必會沖擊到少數(shù)民族人民的情感。包容性民族情感是一種既尊重少數(shù)民族人民情感,又不破壞民族成員間友好交往而促進(jìn)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情感。
(二)包容性民族意識
(三)包容性民族傳統(tǒng)
民族傳統(tǒng)是在民族間的交流、交往與交融過程中實(shí)現(xiàn)的,是民族文化發(fā)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各民族都有保持或改變本民族風(fēng)俗習(xí)慣的自由和權(quán)利。因此,尊重各民族傳統(tǒng)成為新時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前提。包容性民族傳統(tǒng)是在本民族文化傳統(tǒng)、生活習(xí)慣得到充分肯定和尊重的前提下,與他民族共同發(fā)展、平等交流、互通有無,實(shí)現(xiàn)共同發(fā)展的途徑。
(四)包容性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共同認(rèn)可并遵守的核心價值觀、倫理道德亦或是宗教信仰、傳統(tǒng)觀念,民族文化能夠直接影響到一個民族的精神風(fēng)貌,它實(shí)際上是本民族與他民族相互交流、相互交融的結(jié)果,是民族精神的本質(zhì)與精髓所在。民族文化交流不僅應(yīng)注意民族文化具體形式的表層,也應(yīng)該注意作為深層文化的價值觀念、思維模式和心理特征,注意民族觀念、意識、感情的變化可能帶來的結(jié)果。在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少數(shù)民族要善于開放交往,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接納他族的現(xiàn)代文明,這也是傳承本族文化,延續(xù)民族發(fā)展的吐故納新的過程。
四、基于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模式選擇與民族融合的創(chuàng)新思考
城鎮(zhèn)化建設(shè)是我國經(jīng)濟(jì)水平發(fā)展和人民生活質(zhì)量提高的必經(jīng)之路,也是中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新引擎,亦是擴(kuò)大內(nèi)需的最大潛力所在,新型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的發(fā)展與推進(jìn)是不可逆的過程。加快實(shí)施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是少數(shù)民族和民族地區(qū)群眾真正實(shí)現(xiàn)全面小康的關(guān)鍵,我們很難從城鎮(zhèn)化建設(shè)的弱化上來實(shí)現(xiàn)對民族特質(zhì)的保護(hù),所需要做的是在認(rèn)識和了解現(xiàn)狀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創(chuàng)新性的思考,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處理之。
(一)依據(jù)區(qū)位條件,選擇恰當(dāng)?shù)某擎?zhèn)化模式
民族地區(qū)通常都具有其獨(dú)特的發(fā)展條件與資源稟賦,民族地區(qū)的城鎮(zhèn)規(guī)劃不能只從“率”上著眼,而要根據(jù)本地的比較優(yōu)勢找到自身的定位:或以文化定位、或以產(chǎn)業(yè)定位、或以環(huán)境定位、或以資源定位、或以幾種資源復(fù)合配置,總之要結(jié)合自身的區(qū)位稟賦選擇適宜的發(fā)展模式。
根據(jù)城市地理學(xué)家諾瑟姆(Ray.M.Northam,1979)對城市化過程的論斷:0~30%為城市化發(fā)展較慢的初期階段;30%~70%為中期加速階段;70%以后為成熟階段。如若從2013年中國城鎮(zhèn)化率達(dá)53.73%這一數(shù)值看,中國已步入城市化發(fā)展的中期加速階段。然而,中國快速城鎮(zhèn)化的背后卻是人口和地區(qū)發(fā)展的不均衡。目前不應(yīng)該一味的為追求均衡型城市化的發(fā)展而貪多求快,為了“城鎮(zhèn)化”而城鎮(zhèn)化,而應(yīng)該允許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城鎮(zhèn)化實(shí)行局部非均衡性發(fā)展戰(zhàn)略,走有民族地區(qū)特色的差異化城鎮(zhèn)化道路,先特色發(fā)展,后均衡發(fā)展。
(二)利用“慢城”效應(yīng),注入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的新動力
“慢城”一詞肇始于意大利語和英語的合成詞:cittaslow,它源于20世紀(jì)80年代意大利發(fā)起的“慢食”運(yùn)動,意思是慢節(jié)奏城市運(yùn)動。而“慢城”作為一種國際潮流,成為城鎮(zhèn)化的指導(dǎo)理念,更多展現(xiàn)出的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模式和全新的幸福理念:一個更加優(yōu)質(zhì)和愜意的生活氣息,在保護(hù)地方文化和民族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出可持續(xù)增長的內(nèi)驅(qū)力。
在“城市病”日益突出的城市化浪潮中,大城市正面臨內(nèi)涵式轉(zhuǎn)型發(fā)展進(jìn)程,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要對已有的發(fā)展模式進(jìn)行反思,即采取“慢城”理念起到預(yù)防演化“城鎮(zhèn)化病癥”的作用,尋找一種可持續(xù)化健康發(fā)展模式是基于“慢城”效應(yīng)的理性思考,同時也是為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發(fā)展注入的一劑新動力。
(三)傳承民族特質(zhì),建立個性民族城鎮(zhèn)
城鎮(zhèn)化不可避免的伴隨著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文明之間的沖突,民族地區(qū)的文化也會隨著生產(chǎn)方式與生活方式的變遷而發(fā)生變化,我們要摒棄在城鎮(zhèn)化推進(jìn)中“蓋高樓、建廣場”的“千城一面”的同一化建設(shè)誤區(qū)。
我國民族地區(qū)的城鎮(zhèn)化發(fā)展,必須要依據(jù)本地實(shí)際,在突出民族特質(zhì)上努力下功夫。民族地區(qū)雖然社會經(jīng)濟(jì)落后,但其獨(dú)特的歷史文化、民族宗教、民風(fēng)民俗、價值觀念、民族建筑都構(gòu)成了民族的獨(dú)特文化記憶和民族特質(zhì)。民族特質(zhì)就是競爭力,要充分利用這一比較優(yōu)勢,高度重視保護(hù)和發(fā)揚(yáng)民族地區(qū)原有的文化、宗教、地方和民族特質(zhì),將民族特質(zhì)與現(xiàn)代化內(nèi)涵有機(jī)結(jié)合,用本土特有的濃郁風(fēng)情和文化特色,來塑造城市的“外形”,澆鑄城市的物質(zhì)“軀殼”,充實(shí)城鎮(zhèn)的內(nèi)涵[10]。建設(shè)獨(dú)具風(fēng)情、體現(xiàn)民族特質(zhì)的個性民族城鎮(zhèn)成為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未來發(fā)展的新趨勢。
(四)給予民族尊重,促進(jìn)民族融合的包容性發(fā)展
民族尊重度是指他族對本族民族情感、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生活習(xí)慣、價值觀念等的認(rèn)同與接納程度,具體而言,就是在物質(zhì)、制度和精神三個層面,給予充分的民族尊重、保護(hù)民族情感。城鎮(zhèn)化對民族文化的保護(hù)和傳承是一把“雙刃劍”,城鎮(zhèn)化加劇了現(xiàn)代文明對民族文化的沖擊,而城鎮(zhèn)化促進(jìn)了民族文化的普同化。如何在城鎮(zhèn)化建設(shè)的潮流中給予各民族以足夠的尊重,對當(dāng)?shù)孛褡逦幕枰杂行ПWo(hù),促進(jìn)民族融合的包容性發(fā)展,使民族文化在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大放異彩是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五、結(jié)語
民族地區(qū)有著優(yōu)秀的民族文化和特質(zhì)的民族瑰寶,新型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給我們經(jīng)濟(jì)社會帶來巨大變革的同時,也對民族特質(zhì)產(chǎn)生了一定的沖擊和影響。新型城鎮(zhèn)化的推進(jìn)也從關(guān)注“率”向關(guān)注“人”發(fā)展,在這種包容性理念引導(dǎo)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發(fā)展轉(zhuǎn)變過程中,如何能既遵循民族特質(zhì)保護(hù)的發(fā)展規(guī)律,又通過一些必要的積極手段進(jìn)行干預(yù),將民族特質(zhì)在城鎮(zhèn)化浪潮中留下更多的印跡,使得民族地區(qū)共享城鎮(zhèn)化發(fā)展成果,已迫在眉睫。
[1] 國家統(tǒng)計局.2013中國統(tǒng)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2013.
[2] 蔣詩舟.中國省級行政區(qū)城鎮(zhèn)化率排名:上海88.02%排第一[EB/OL].中國經(jīng)濟(jì)網(wǎng)(2014-04-21)[2014-07-25].http://finance.ce.cn/rolling/201404/21/t20140421_2694137.shtml.
[3] 范文國,熊寧.我國小城鎮(zhèn)不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資源因素探討——以江蘇省為例[J].經(jīng)濟(jì)地理,2003,(1):42-46.
[4] 金逸民,喬忠.關(guān)于小城鎮(zhèn)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思考[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huán)境,2004,(1):62-66.
[5] 柳建文.新型城鎮(zhèn)化背景下少數(shù)民族城鎮(zhèn)化問題探索[J].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科版,2013,(11):16-22.
[6] [日]山田浩之.城市經(jīng)濟(jì)學(xué)[M].魏浩光,等,譯.大連:東北財經(jīng)大學(xué)出版社,1991.
[7] 王先鋒.“飛地”型城鎮(zhèn)研究:一個新的理論框架[J].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2003,(12):21-31.
[8] 劉曉鷹,楊建翠.欠發(fā)達(dá)地區(qū)旅游推進(jìn)型城鎮(zhèn)化對增長極理論的貢獻(xiàn)——民族地區(qū)候鳥型“飛地”性旅游推進(jìn)型城鎮(zhèn)化模式探索[J].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科版,2005,(4):114-117.
[9] Ravi Kanbur, Ganesh Rauniyar. Conceptualizing inclusive development: with applications to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2010,15(4):437-454.
[10] 麻三山.淺探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化中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保護(hù)[J].民族論壇,2005,(12):48-49.
[責(zé)任編輯:胡璇]
2014-09-01
國家社科基金項(xiàng)目(14BJY052)
劉洋(1985-),女,遼寧大連人,經(jīng)濟(jì)學(xué)博士,大連海洋大學(xué)法學(xué)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城市經(jīng)濟(jì)學(xué)、公共管理; 姜昳芃(1985-),女,遼寧大連人,經(jīng)濟(jì)學(xué)博士,大連海洋大學(xué)法學(xué)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jì)學(xué)。
F299.27;C956
A
1672-0758(2014)05-004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