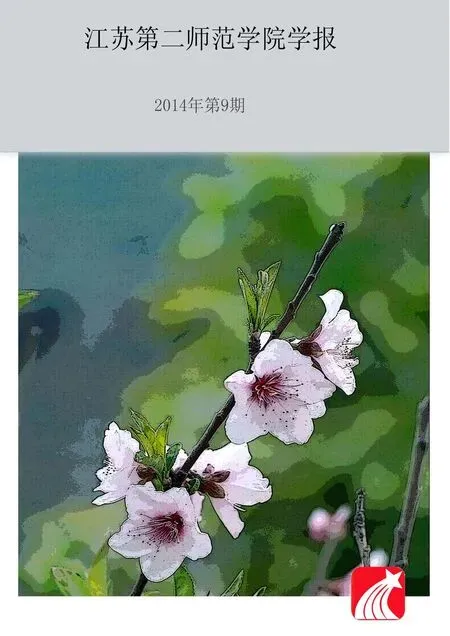一座自由孤獨的花園——論《他們眼望上蒼》中尋找“他者”的珍妮
郭雨微 焦曉婷
(河南大學外語學院,河南開封 475000)
前言
“他者”概念相對于自我,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他者與自我的辯證關系平行于客體對主體二元對立的關系。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他者具有不可知性、陌生性和他異性。列維納斯在其著作《存在與存在者》一書中談到他者,“世界上的他者只是一個穿上了衣服的客體”,或者叫“穿上了衣服的存在者”。[1](P.29)他者是流動的,無限的,即使他者換了衣服,換了形式,自我永遠不會真正認清他者;換了陌生的“面貌”的他者是陌生的,即使是熟悉的面貌的他者會有自我所不知的面貌;即使有著同樣面貌的他者也是有差異性的。女人(Woman)作為男人(Man)的一個相關項,宣告了女人的他者身份,女人是他者,男人的他者。與此觀點相反,列維納斯批判男性中心主義,主張女性的絕對性,而非男性的相關項并提倡女性書寫自己的差異性。
佐拉·尼爾·赫斯頓是曾經轟動20世紀的非裔美國女作家。其代表作《他們眼望上蒼》是黑人女性主義的代言人。小說情節并不復雜,講述黑白混血兒珍妮經歷三次婚姻尋找自己愛情的辛苦歷程。目前國內的研究集中于女權主義,自由的追求,反抗意識的覺醒,都將珍妮視為男性丈夫的他者,但是珍妮更多地是她經歷的主體,是個尋找他者的存在者。她正是列維納斯欣賞提倡的書寫自己性情的女性,更是超越他者尋找他者主體的女性。她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幸福,她的三次婚姻只不過是她對他者的三次否定,她在尋找他者的途中玩弄著他者的存在。珍妮無時無刻不在建立著愛情的花園,在臆想的愛情中尋找他者,當花園開始腐朽時,她會說“生活在別處”,尋找他者之路在別處。
一、春之篇:序幕
一切似萬物開始的春天,珍妮也似春天的少女,對愛情還很懵懂。珍妮懷有希望地打開她的花園,準備種植自己的愛情。她一直在等待著,等待著一個有歡唱的蜜蜂的世界,等待有個他者進入她的花園。
約翰尼·泰勒是珍妮的第一位他者,珍妮睜開眼就將眼前出現的吊兒郎當的約翰尼·泰勒視為她的蜜蜂,這既是荒謬的也是合理的。珍妮只是在臆想中的愛情尋找他者,若奶奶不阻止泰勒的在場,泰勒作為珍妮的他者的時間會更長。
列維納斯說過一句很精彩的話:“人類本質首先不是沖動,而是人質,他人的人質。”[2](P.252)如果說一開始在奶奶未去世前,珍妮的自由是受到他者奶奶的限制,那是因為珍妮成了奶奶的人質,之后奶奶為珍妮找了一位他者——洛根,于是珍妮成為了洛根的人質。
奶奶讓她與洛根結婚,而洛根的形象根本不屬于珍妮這座花園。洛根就是一潭死水,而珍妮是一汪活水。洛根的死水只能澆灌60英畝的土地,而不能給與珍妮的花園以營養。對于珍妮而言,洛根永遠不會招愛,他與珍妮也不會有愛情,因為洛根沒有給她想要的甜蜜的東西,像蜂蜜一樣甜蜜的東西。風琴和60英畝土地都不是她想要的,穩定的生活也不是她所看重的。不到一年的時間,洛根的愛慢慢褪去,他開始讓她流汗。他者眼中的他者珍妮是個不懂事的小不點,而真正的珍妮自我卻是天真浪漫的花朵。珍妮已經超出了洛根的認知范疇,洛根這面鏡子所反射出來的自我不符合珍妮的公式。當洛根準備往她的花園里拉頭騾子時,珍妮開始否定他者洛根的存在,為了不讓洛根進入珍妮的花園,珍妮選擇逃避,選擇離開。當珍妮告知洛根她要逃跑離開他時,他者洛根對主體珍妮卻進行著“不抵抗的抵抗”,他只是用言語教育她沒有別人能養活珍妮,因為洛根相信不會有其他的他者來供養珍妮的主體性存在,但洛根不知道下一位他者正在珍妮的花園靜候著。
二、夏之篇:繼續
在阿媽去世之后,珍妮有了一種解放感。她再次期待,期待愛情的籽粒落在柔軟的土地上,落在她的花園里。她是一個花朵,等待著蜜蜂的到來。
喬·斯塔克斯的出現是出于純粹的偶然性。一開始喬是沒有注意到珍妮的,是珍妮自己故意弄出聲音吸引了喬的目光,即喬是珍妮自己尋找到的他者。兩人相識是因為清水,而清水正是珍妮的花園所缺少的養分。巴士拉在著作《水與夢》中說“水吸收眾多的實體。水吸引眾多的要素。”[3](PP.104-110)同樣水也吸引著水。水本身就是女性物質,珍妮本身就是水。但是珍妮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水和水是不能聯姻結合的,水與水結合仍是水,水和水結合只會讓彼此看不清對方的主體性存在,她明明知道喬不是日出,花粉,和開滿鮮花的梨樹,但她仍以為喬會是她的蜜蜂,這種想法是荒謬的。兩個人20年的生活也像無味的水一樣沒有波瀾起伏。
列維納斯認為,愛情并不消融他者,而是維持他者;愛欲的本質不在于合一,而在于分離,在于他者的顯現與維持。列維納斯寫道;“愛的情愫在于一種不可克服的實存者的二元性,它是與那個總是滑開的東西的關系,這種關系不是使他性中性化,而是維持他性。”[4](P.78)當珍妮選擇喬時,喬成了珍妮的他者,結婚以后珍妮是喬的他者,而喬沒有維持珍妮的他性,而將珍妮消融在自我陶醉的“影子愛情”與自我設計的菲勒斯中心世界中。喬構筑了一個屬于自己的世界,他要讓所有他者圍繞著他運行,像行星繞著太陽一樣,他陷入了對自己的菲勒斯崇拜。珍妮像一只蝴蝶落入了喬所設計的蜘蛛網,陷入了名為空虛的深淵。
起初喬給她貴婦般的對待,讓她坐上高高的市長夫人的座椅,花粉與春光仿佛撒在她的花園里。之后喬不讓她參加門廊的聊天,不讓參加拖騾子,喬將珍妮花園里粗俗的雜草都鏟除;不讓她露出頭發,喬用厚重沉悶的烏云將花園的陽光遮擋。而珍妮是天性的使者,想笑就笑,想說就說。正如利奇和山姆討論的“謹慎”和“天性”一樣,喬是“謹慎”,對事業和自己的妻子珍妮都謹慎著,而珍妮確是“天性”的,是天性告訴她去說,去笑,去愛。她的花園需要的就是這些快樂的雜草和微笑的陽光。喬對事業的熱情和對她的冷漠,讓珍妮覺得孤獨。喬因為沒做好的一頓飯而重重打了珍妮一耳光,讓珍妮的主體性覺醒。她發現了自己自我的缺失,自己一直都是被喬當做一個自在的存在,一直被置于物質性的附屬地位。珍妮有自由選擇再一次逃跑,再一次離開,但是35歲的她不知逃向何處,因此她只能“像土地一樣默然地接受一切。無論是尿液還是香水,土地同樣無動于衷地把它們吸收掉”。[5](P.83)最終,珍妮玩弄了喬的存在,她將喬他者性的衣服剝開,當眾羞辱了喬的性能力減退并和旁觀者一起蔑視,嘲笑。喬的他者性陷入了面貌的裸露中,此時的他者喬已不是其過去所是,但珍妮也成為無關乎他者的自我主義者,珍妮已不關心病床上的喬,她對喬死前說的話是為了同一他者喬,也無不體現了她對自我的享受。隨著他者喬的死亡,珍妮立即復活。正如珍妮對弗奧比說的“我就是愛自由自在的生活”,她愛的是對自身的享受。于是她再一次敞開自己的花園,等待下一位他者的到來。
三、秋之篇:轉折
第三次遇見他者甜點心就是珍妮的秋天,不僅收獲了豆子,更收獲了自己的愛情。與喬的相遇相同的是,甜點心也是向珍妮借東西。與喬的相遇不同的是喬借的是水,而甜點借的是火。如果是喬是水,那甜點就是火,水與火具有“化學的婚姻特征”,“在邏輯上一者呼喚另一者,在性方面,一方渴求另一者”,“水就應該‘把自己獻給’火,火就應該‘娶’水”。[3](PP.104-110)即甜點心是珍妮的另一半,兩個人是應該合為一體的愛人。
甜點這個陌生男人,對于珍妮一點也不陌生。她和甜點很能談得來,從見到甜點開始,她的花園里有了月亮,浪漫的月光將花園的土地染成爛漫的顏色,滋潤了她一個人的太陽,花園里的太陽可以大笑。這位他者在珍妮眼中是位夕陽的兒子,他彈吉他,鋼琴,唱歌,給她的花園播撒種子與愛意;他能看透珍妮,“你的罐子里裝著世界,卻裝作不知道”他就是她花園里的蜜蜂,攜著芬芳,讓珍妮感到自己的存在;他帶來的一切對珍妮都是新鮮的,開心的:雜草,射擊,擲骰子,大沼澤,豆子,甘蔗……“在無聊的時候,他可以拿起幾乎任何一樣小東西,創造出夏天來。我們就靠他創造出的那幸福生活著,直到出現更多的幸福。”[5](P.151)因此由他者甜點心自指的珍妮體會到了自為的存在,她仿佛自由地鮮活起來,仿佛之前她是幅黑白肖像畫,現在忽然帶著色彩活動起來;她穿著甜點喜歡的藍色衣服,每天換一種發型,生命力全部釋放出來;花園里的大樹也瞬間成長壯大起來。
珍妮把喬的店賣掉,與甜點開始新的生活。當甜點出去釣魚未回,襯衣口袋里的200元錢又不見時,珍妮開始意識到他者的不可知性。但事實證明她對他者的認識是正確的。在沼澤里的摘豆生活是快樂的,即使甜點因為特納太太慫恿珍妮的話而象征性地打了珍妮,但珍妮卻仍相信這位他者對愛的真實性。與甜點心在沼澤里遭遇的洪水更加證明了甜點對珍妮的愛。在夜的風暴中,夜與水相容成一種恐怖,吞噬者萬物,珍妮與甜點心等待上帝的憐憫,他們眼望上蒼,將目光從水平方向轉向垂直的上帝,作為他者的上帝。上帝就是他性,是一種無限,是一種無所不在的“目光”。雖然看不到上帝的面孔,但珍妮一直轉向作為他者的上帝。“上帝卓越地存在著,它意味著一個高于任何高度的高度。”[2](P.252)面對風暴,珍妮毫無畏懼,因為上帝已經為她帶來了等待中的愛情,帶來了她最愛的他者,此刻的甜點心得他性已超越了上帝的他性。珍妮和甜點在水中與風暴抗爭,因為珍妮就是水,她是融于水,屬于水的,因此她是不會死在水中,而甜點心是火,水會使火熄滅,使他的生命窒息,甜點的死亡是必然的。赫斯頓對風暴意象的巧妙運用早已預示了甜點的死亡。其后甜點因為被瘋狗咬得恐水病,而被珍妮拿步槍射死。雖說珍妮是出于自衛,但是步槍是她提前準備的,甜點是為了救她而死,也是被她殺死的。正如甜點以前對珍妮說的“你掌握著天國的鑰匙”[5](P.118),仿佛他應經預示出自己的命運掌握在珍妮的手里,他要為珍妮而死。可以說是珍妮吞滅了最后一位他者。
四、冬之篇:尾聲
珍妮的名字從珍妮·梅克勞弗德到珍妮·梅克利斯克,到珍妮·斯塔克斯,到最后的珍妮·伍茲。她的名字經歷著變革,珍妮的他者之路也經歷著季節般的輪轉。從愛情啟蒙的茂綠春天,要往她的花園里拉騾子的洛根,到在愛情澎湃似火開花的夏天,把珍妮封閉在一個鳥籠里的喬,到再收獲愛情的橙紅的秋天,給珍妮帶來浪漫和蜂蜜的甜點心。經歷春,夏,秋般色彩變幻的婚姻后,珍妮不會問自己:愛情啊,你姓什么?她只知道自己存在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是為了種植一座自己的花園。
列維納斯在《時間與他者》哲學講座中提出自我與他者的相遇在本質上是神秘而不可理解的:“與他者的關系不是共群中的田園式的和諧關系,也不是一種將我們置于他者之位的同感;我們認為他者與我們相似,然而他者卻外在于我們;與他者的關系即是與大寫的神秘的關系。”[6](PP.75-76)由此可以說,珍妮與洛根不是共同勞作的和諧關系;珍妮與喬不是將她置于喬之位的同感;最后一位他者,甜點心與珍妮相似,又被珍妮殺死,甜點與珍妮是神秘的關系。但同時,珍妮是一個不完整的存在,她是一座孤獨自由的花園。現在珍妮是個身心寒冷的冬天,因為她的花園不會再開花,即使她有甜點心留下來的菜籽,她的太陽已不存在,意義總是消失在遠方。她知道生存在的窄狹局限,拋開它的塵世存在的偶然關系和至于藝術本身是否會消亡死掉,我們完全不用抱活在別處,她又將走上尋找他者之路,但他者是否會再現,經歷過真正生活回來的珍妮不知曉,無人知曉。
尋找他者之路的真相揭開了珍妮身上的西西弗斯性。珍妮一直舉著主體性這個大石頭,石頭上刻著“愛情”兩個大字,可是石頭不斷往下掉,主體性不斷下落,她一直不斷在重復著這個過程,直到最后。只要她不將自己的主體性拋開,這個過程會一直下去,直到她的花園枯萎,沒有春光。不過與西西弗的石頭不同,珍妮的石頭的重量是變化的,所耗的時間每次也是不同的。從其蹤跡中可以看到珍妮的存在,珍妮的花園經歷過不同的風景都見證了是她的存在。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1]列維納斯.存在與存在者[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列維納斯.上帝,死亡和時間[M].北京:三聯書店,1997.
[3]加斯東·巴什拉.《水與夢》:論物質的想象[M].長沙:岳麓書社,2005.
[4]Emmanuel Levinas.Les temps et l'pautre,Qua-drige1[M].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3.
[5]佐拉·尼爾·赫斯頓.他們眼望上蒼[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
[6]E.Levinas.Time and the Other[M].Pittsbukgh:Duquesene University-Press,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