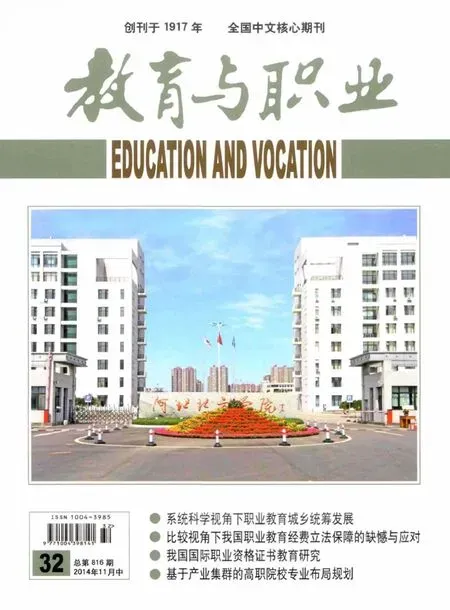比較視角下我國職業教育經費立法保障的缺憾與應對
何振海
一、我國職業教育經費立法保障的現實缺憾
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具有強烈的實用性、實踐性特征和技能操作導向,其教育過程需要更為豐富多樣的教學資源,因此較之于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對經費的需求更高。當前,我國正在大力推進職業教育的發展,但有效經費保障的缺乏,已成為阻礙我國職業教育發展戰略順利實施的關鍵因素,同時這一缺憾也是當前我國職業教育改革的重點內容之一。
客觀而言,造成我國職業教育經費得不到有力保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職業教育立法特別是經費保障立法體系尚未健全。在強調依法治國的當下,立法已經普遍成為規約、引導政府及社會主體行為的指南。立法環節的缺失必然導致政府與社會主體在相關領域行為活動的失范,職業教育也概莫能外。在我國的職業教育法律體系中,至今沒有專門的職業教育經費立法,國務院也沒有出臺專門的職業教育經費配套法規或實施條例。在已有的職業教育立法中,有關經費保障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也僅僅停留于宏觀或一般性的政策引導。如199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以下簡稱《職業教育法》)中,有關職業教育經費保障的條款只是宏觀性地提出“國家鼓勵通過多種渠道依法籌集發展職業教育的資金”,要求各級政府、有關部門制定相關領域職業學校的生均經費標準,同時做出國家“用于舉辦職業學校和職業培訓機構的財政性經費應當逐步增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挪用、克扣職業教育的經費”等原則性規定。國務院及相關部委的有關文件中,對職業教育經費或經費保障內容的規定也大都帶有類似特點。如2002年公布的《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國發[2002]16號)和2005年公布的《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國發[2005]35號),有關職業教育經費的規定只是原則上要求各級政府增加投入渠道和投入力度,缺乏更為剛性和明確的指標約束。這種現象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近年來我國職業教育在經費投入方面相對短缺的現象。例如,盡管我國職業教育經費投入由2005年的939.25億增長到2011年的2811.69億,但其占全部教育經費投入的比重卻始終徘徊在11%~13%,遠低于25%的世界平均標準,與優先發展職業教育的國家戰略形成了鮮明反差。
國家層面的職業教育基本法和上位法在職業教育經費保障方面相關規定所具有的宏觀性、原則性、模糊性特征,直接導致我國各地制定的《職業教育法》實施辦法(條例)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如北京市1997年制定的《職業教育法》實施辦法中,有關政府擔負的職業教育經費責任的內容僅限于“市和區、縣人民政府、有關部門用于職業教育的財政性經費應當逐步增長,并劃撥專款用于發揮骨干、示范作用的職業學校和職業培訓機構以及生產實習基地的建設”;1999年河北省制定的《職業教育法》實施辦法也只是要求“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應當保證用于職業教育的經費逐步增長”;2014年遼寧省修訂的《職業教育法》實施辦法中同樣僅做出“職業教育所需經費,按職業學校和職業培訓機構的性質,分別采取各級財政撥款、辦學主管部門(單位)自籌、按規定收取學費、學校創收、社會捐助等多種途徑解決”的規定。類似的模糊性法律表述在各地制定的《職業教育法》實施辦法中比比皆是。在現有職業教育法律體系中,有關職業教育經費最明確的法律表述僅僅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企業按比例提取職工工資用于職業培訓的規定,比例一般不低于1.5%;二是對各級政府按比例將征收的教育費附加中用于職業教育的規定,具體比例各地標準不一。換而言之,我國現有的職業教育法律體系并沒有對政府應負擔的職業教育經費具體責任做出強制性和明確性規定,也沒有要求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在制定職業教育生均經費標準時應結合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特點而有所傾斜。
上述職業教育經費立法保障的缺憾導致我國職業教育在發展中面臨著巨大的經費障礙。2014年教育部財務司有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不無憂慮地談到:“職業教育仍是各類教育中的‘短板’,與其培養規模和應有地位、作用不匹配。從投入總量上看,職業教育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與同階段普通教育相比仍明顯偏低。生均總經費和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經費中,中職與普通高中大體相當,高職僅為普通本科的一半。從來源結構上看,職業教育經費來源渠道仍較單一,財政性經費所占比例達到74%,多渠道籌資能力不強。從撥款方式來看,部分地區的職業教育經費投入還未建立制度保障體系。”①職業教育經費立法保障的現實缺憾與我國大力推動職業教育發展的國家戰略之間已經出現了巨大反差,構建具有我國特色的職業教育經費立法保障體系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強烈的緊迫性。
二、發達國家職業教育經費立法保障的主要特征
自近代以來,以立法形式保障職業教育的發展已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也是各國職業教育得以繁榮的基本經驗。在各國的職業教育立法體系中,為職業教育提供經費方面的切實保障,是最為核心和最為基本的內容。所謂經費保障,可通俗地理解為誰出錢,出多少,用到哪,給多久。縱觀近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職業教育立法的具體內容,其有關職業教育經費保障的相關規定基本是圍繞上述內容展開的。
(一)職業教育經費責任主體的確定性
有效立法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權責明確,而權責明確的前提在于責任主體的明確。具體到為職業教育發展提供經費保障方面,有效的立法首先要明確為職業教育提供或撥付經費的責任方。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在職業教育相關立法中,有關職業教育經費的法律條文無一例外地都對此做出了清晰界定,特別是明確了政府在為職業教育提供經費方面的首要責任。例如,1889年英國頒布的《技術教育法》明確將征收“一便士稅”以資助職業教育的權力授予“郡和郡自治市的議會”,1890年頒布的《地方稅收法》中授權地方政府從某些物品稅中按比例提取部分經費用于發展職業教育。由于責任主體明確,19世紀90年代英國職業教育發展所需的經費得到了切實保障,如利物浦市根據《地方稅收法》在1890~1898年征收的威士忌酒稅的提成就達80.7萬英鎊,其中90%用于發展該市的職業教育。相對充裕的經費為同期英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美國于1963年頒布的《職業教育法》規定聯邦在法案涉及年度按既定數額向各州撥付職業教育經費,同時要求各州政府提供等額配套經費。諸如此類的立法條款賦予了相關主體明確的經費保障職責,體現了責任主體的確定性和排他性,規避了因責任主體缺失或模糊造成的職業教育經費無人負責的現象,從而為職業教育獲得穩定、持續、充足的經費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職業教育經費數額及分擔比例的明確性
在責任主體明確的前提下,相關主體應該承擔多大比例或份額的經費責任,是職業教育立法需明確的另一關鍵環節。在發達國家的職業教育立法體系中,相關責任主體承擔的職業教育經費份額大都有非常明確的規定,這極大提高了法律實施的有效性。如美國于1917年頒布的《史密斯—休斯法》規定聯邦政府在1918財經年度為各州農科教師、督學和主任的工資撥款50萬元,為商業、家政業與工業三類教師工資共計撥款50萬元,以后逐年遞增。法案同時對地方政府所應履行的經費責任也做出了明確規定:“聯邦為農、工、商、家政等職業類教師、督學及主任的工資或培訓每花費1美元,州或地方學區還必須提供1美元的匹配資金。”此外,為了對各州職業教育的實施情況進行全方位的監督,法案還要求各州把“州內完成的工作和按本法案規定領取和支付撥款的情況,向聯邦職業教育管理署做年度報告”②。1960年,加拿大制定了《技術和職業訓練支持法》,要求聯邦政府在10年內撥款8億加元作為職業教育經費,同時要求各省級政府按照1︰3的比例分擔經費。1990年,為明確私人企業的職業培訓職責,澳大利亞頒布《培訓保障法》,規定年收入在22.6萬澳元以上的雇主須將工資預算的1.5%用于員工的職業培訓。
上述法案的共同特征在于,法案對相關主體在職業教育經費方面的具體責任都有明確界定。也正是由于責任明晰,這些法案在頒布之后大都得到順利執行,職業教育發展所需經費得到了有效保障。如美國在頒布《史密斯—休斯法》之后,1918財經年度聯邦為農科教師及商業、家政、工業等科教師的撥款分別為54.8萬美元和56.6萬美元,到1920財經年度分別上升到102.4萬美元和103.4萬美元,到1926財經年度即達到法案規定的300萬美元標準,分別為302.7萬美元和305萬美元。由于經費保障得力,獲得聯邦資助接受職業教師培訓的人數從1918年的6589人很快就上升到1921年的13358人,增長一倍有余。同時,在聯邦撥款的帶動下,地方政府的投資積極性也明顯提高,其中僅地方社區提供的職業教育經費即由1918年的120萬美元增至1921年的518萬美元。顯然,強制性的立法保障在確保相關主體責任履行的必然性和順利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職業教育經費保障的針對性和連續性
職業教育經費的立法保障,不僅要確保經費來源的可靠性,還要確保經費使用的針對性和連續性,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經費撥付對職業教育發展的促進作用。
職業教育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行業領域具體、分散,層次類型多樣,經費需求廣泛、多元。從發達國家職業教育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不可能在同一時期同時滿足所有類型和層次的職業教育所需的經費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各國通常采取的策略是,在充分考慮經濟社會發展需求與職業教育發展現實狀況的基礎上,通過立法,為經濟社會發展所需的職業教育領域、類型或層次提供充足的經費支持,并借助立法的強制性確保經費使用的有效性,在為職業教育提供切實保障的同時,實現經濟社會與職業教育發展的同步和共贏。以日本為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面對當時職業教育發展的停滯狀態,日本政府于1951年頒布了《產業教育振興法》,將中等及以上職業教育確定為國家資助的重點,法案實施后的1952年,日本為職業教育編列的經費預算就達到6.6億日元,有效改善了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環境,如職業高中的設備完備率從1952年的20%~40%提高到1957年的60%~80%,為戰后日本中等及以上職業教育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有效的經費保障。
從歷史上看,發達國家職業教育經費的立法保障還體現出了明顯的連續性特征,美國的職業教育立法在這一方面的特征尤為明顯。自1963年《職業教育法》頒布之后,美國通過持續性的立法活動,為職業教育的發展提供了長期穩定的經費保障,如1963年《職業教育法》規定,截止到1964年6月,聯邦須為各州職業教育撥款數額為6000萬美元,以后逐年增加,到1967財經年度達到2.25億美元,之后每年穩定在2.25億美元。1977年頒布的《生計教育激勵法》規定,自1977年起的5個財經年度內,提供總額為3.25億美元的生計教育撥款。這種堅實的經費保障無疑是美國職業教育長期保持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
三、我國職業教育經費立法保障的構建策略
在積極推進職業教育法律體系建設的背景下,借鑒發達國家職業教育經費立法保障的基本做法,為我國職業教育發展提供完備有效的立法保障,已經成為當前我國職業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重點內容。結合我國職業教育立法的現實需求,在為職業教育經費提供立法保障方面,我國應從如下幾方面著力推進:
(一)有效的職業教育經費立法保障,必須以完善職業教育立法體系為前提
目前,我國的職業教育立法主要有作為職業教育基本法的《職業教育法》(1996年頒布)、各地制定的《職業教育法》實施辦法、中央部門的規章文件(如《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國發[2005]35號)、《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見〉的通知》(中辦發[2006]15號)等)以及涉及職業教育的相關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就業促進法》《企業職工培訓條例》等)。從宏觀體系來看,《職業教育法》頒布已近二十年,卻未經任何修訂,嚴重削弱了其作為職業教育基本法所應發揮的效用,同時現有的職業教育立法中沒有國家層面的實施細則與配套法規,進一步導致《職業教育法》在實施過程中缺乏明確、具體的指導依據;從立法內容來看,眾多法律法規中有關職業教育經費保障的內容大都具有模糊性,看似為法律的實施提供了寬松的靈活空間和彈性范圍,實則回避了具體的經費責任歸屬;而且,由于大量職業教育相關法律、法規和文件系政出多頭,實行歸口管理,因此未能與《職業教育法》形成一個內在有機、完整的職業教育立法體系。
職業教育立法體系的不完善,一方面導致職業教育經費投入缺乏明確、可靠的法律依據,另一方面導致經費的投入責任、使用主體、管理機制凌亂分散,不利于職業教育經費投入、使用和管理的統籌規劃,降低了職業教育經費的使用效能。基于此,我國要構建完善的職業教育經費立法保障,必須將職業教育立法體系的完善作為前提,一是盡快完成《職業教育法》的修訂工作,使職業教育擁有一部可依賴的基本法;二是國務院應根據修訂后的《職業教育法》,結合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現實需要制定更為明確、詳細的實施細則和配套法規;三是各省級政府和中央部委應在國務院的統籌下制定省級實施頒發和部門條例,明確各自在職業教育中應承擔的具體職責。通過上述改革,逐步構建起完整的職業教育立法體系,實現職業教育責任的全覆蓋,使職業教育的各個層次、領域和環節都有法可依、有法能依,為職業教育的健康、科學和可持續發展提供更為扎實的立法支撐。
(二)有效的職業教育經費立法保障,必須體現經費責任的確定性
確定性是職業教育經費立法保障得以實現的基礎,也是發達國家職業教育經費立法保障的共同特征。這種確定性不僅體現在立法對職業教育經費責任主體(如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個人等)的明確界定上,更體現于對相關主體所承擔具體責任(如經費額度、比例等)的明確界定上。具體到我國而言,在健全職業教育立法體系的過程中,一方面必須堅持職業教育經費來源渠道的多元化方向,另一方面還必須首先明確各級政府所應承擔的經費責任。作為可行的改革路徑之一,我國在修訂《職業教育法》過程中,應綜合考慮國家有關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宏觀戰略,在立法條文中明確政府職業教育經費年度預算占教育總經費年度預算的最低比例。同時,各省在其《職業教育法》實施辦法中也應明確政府撥付的年度預算占總經費預算的比例,此比例依法不得低于《職業教育法》所確定的標準。此外,針對當前中央政府提供的年度性職業教育專項撥款,也應有專門立法對其加以規范和明確,包括確定專項撥款的總額、資助對象、使用范圍,以及地方政府配套經費的具體比例等。
除政府外,以企業為代表的社會機構也是職業教育經費投入的重要主體。在主要發達國家,相關立法對激發企業和雇主投資職業教育的熱情起到了重要的導向作用。以德國為例,在“雙元制”職業教育模式下,企業是職業教育經費最主要的來源,如2005年,德國企業在“雙元制”職業教育中的投入為276.8億歐元,而當年公共財政(包括聯邦和州)的投入為28.15億歐元,企業投入是政府投入的近十倍。德國企業為職業教育投入巨資的動力來源于立法的規約和激勵。德國《聯邦職業教育法》和《企業基本法》就明確規定,參與職業教育的企業一般可獲得其培訓費用的50%~80%的補助。與此相比,當前我國的相關立法還存在較大缺憾,盡管也有部分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做出了鼓勵企業投資職業教育的規定,并提出要在稅收、金融等方面對企業給予回報,但在實踐中,這些僅具有引導性的政策措施很難得以實現,各級政府對企業的優惠舉措大多停留在口頭或文件上,企業難以獲得實際收益,因此參與職業教育的熱情不高,投資力度不大。對此,我國在完善職業教育經費立法保障的進程中,應該將《職業教育法》有關“國家鼓勵通過多種渠道依法籌集發展職業教育的資金”的規定落到實處,通過專項立法、部門立法、地方立法的形式,加大對企業投資職業教育的扶持和鼓勵力度,特別是要明確企業投資職業教育的收益回報,如根據企業投入經費的數額按比例給予稅收優惠、政府按一定標準提供直接的經費補貼等。
(三)有效的職業教育經費立法保障,必須體現經費支持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構建是一項復雜而長期的系統工程,職業教育本身又是一個“高消費”的教育領域。基于這一特點,發達國家在通過立法為職業教育發展提供外部支持特別是經費保障方面,普遍體現出了較強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特征,確保了職業教育發展所需經費的穩步提升。如澳大利亞自1992年起開始頒布年度性職業教育與培訓撥款法案,立法機構每年都會根據職業教育發展的實際需要,對下一年度的撥款事宜進行修訂,稱作《某年職業教育與培訓撥款修訂法案》。法案的連續頒布有效保證了澳大利亞職業教育經費的穩定性增長。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職業教育立法體系本身存在嚴重的滯后性。具體到職業教育經費的立法保障方面,現有立法體系中既沒有專門的經費立法,更談不上對立法的持續修訂和完善。由于缺乏連續性的立法保障,我國對職業教育經費的撥付機制始終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和規約,職業教育經費在教育總經費中的低占比與國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戰略極不協調,政府與社會機構對職業教育的經費支持依靠的僅僅是作為投資主體的自覺性,而非源于立法的確定性和強制性。
在為職業教育發展提供連續和穩定的經費立法保障方面,我國的立法機構雖然不必完全效仿發達國家為職業教育經費制定年度性撥款法案的做法,但卻應借鑒其立法保障的連續性特征,最大限度地為我國職業教育發展提供穩定的經費保障。如針對職業教育快速發展的現實需求,全國人大應對《職業教育法》進行認真修訂和完善,特別是應結合國家經濟發展的宏觀形勢和現實需求,制定出相應的職業教育經費撥付標準;國務院根據《職業教育法》制定的相關實施條例或辦法,以及中央部門制定的相關法規文件也應體現出對職業教育經費支持的傾斜性,如確定職業教育經費在政府年度教育經費預算中的明確比例以及增長額度等;地方政府結合本地實際制定的《職業教育法》實施辦法也應按期修訂,核心內容是對職業教育經費的撥付總額、使用程序等進行適時性調整。借助上述立法,使職業教育發展所需經費得到長期保障和穩定增長。
[注釋]
①宗河.1.23萬億助推職教發展——教育部財務司有關負責人就職業教育財政投入答記者問[N].中國教育報,2014-07-01.
②夏之蓮.外國教育發展史料選粹:下[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