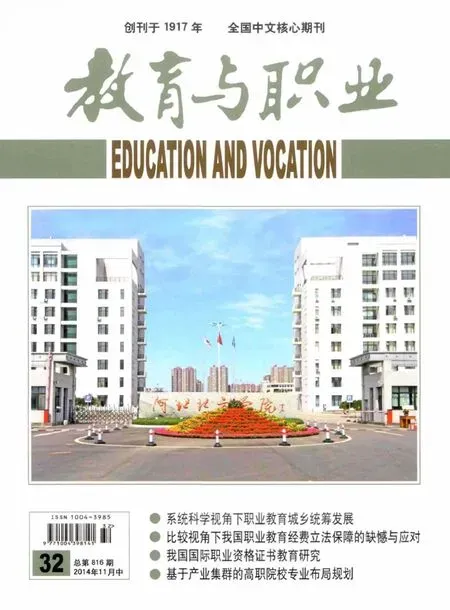高校少數(shù)民族預科語文教材的建設
池永文
教材是教學的基礎,高校民族預科班語文教材質(zhì)量的高低直接影響語文教學的質(zhì)量。高校民族預科語文教材建設歷來受到國家教育行政部門和學界的重視。教育部、國家民委曾先后組織編寫過四套教材,現(xiàn)行的語文教材是在2006年版的基礎上2013年重新修訂的,對于提高高校少數(shù)民族預科生的語文教學質(zhì)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實際語文教學過程中也存在諸多問題。本文將從預科語文的性質(zhì)、教材編寫范式、選文標準三個維度探討預科語文教材編寫的得失。
一、少數(shù)民族預科班語文課程的性質(zhì)
自20世紀以來,“大學語文”的性質(zhì)、學科定位等問題一直是學界爭論的話題。作為高校特殊的辦學層次——少數(shù)民族預科班,其語文課程的性質(zhì)是什么很少提及,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先要弄清何謂“語文”。“語文”一詞最先出自葉圣陶先生之手,1949年后在中小學課文里出現(xiàn)“語文”。葉圣陶先生解釋說:“什么叫語文?語文就是語言,就是平常說的話,嘴里說的話叫口頭語言,寫在紙面上的叫書面語言。語就是口頭語言,文就是書面語言,把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連在一起說,就叫語文。”很明顯,語文不等同語言,也不等于語言文學。
現(xiàn)行的普通高等學校少數(shù)民族預科語文教材,以“大學語文”命為書名,其編者的用義顯而易見,即與中學語文相區(qū)別。少數(shù)民族預科班是否屬于大學范疇,教育部《關于印發(fā)〈普通高等學校少數(shù)民族預科班高層次骨干人才碩士研究生基礎強化班管理辦法〉》第一條明確了普通高等學校少數(shù)民族預科班是普通高校特殊的辦學層次,暫不屬于大學范疇。民族預科班學生充其量是大學生預備生,沒有取得大學生學籍,這是其一。其二,教育部高校少數(shù)民族預科教材編寫委員會編寫的《大學語文·教學大綱》明確教學的目的是通過“補”“預”結合,進一步鞏固和擴展基礎知識,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理解能力、寫作能力、口語表達能力和研究能力。顯然,少數(shù)民族預科階段的語文教學是以“補”為重點的施教理念。“補”什么?在教育部2003年頒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課程標準》(新課標)中可以找到答案:與過去的課標相比,新課標重點突出夯實語文基礎知識,提高語文應用技能,培養(yǎng)高尚的審美情趣和一定的審美能力。高校少數(shù)民族班語文課程不同于大學中文系的語言學課程,不宜講授專門系統(tǒng)的語言學知識,也不能只講純文學作品,更不能成為文學史的壓縮版。就預科語文性質(zhì)和教學目標而言,高校少數(shù)民族預科語文教材只能叫“語文”或“預科語文”,不能命名為“大學語文”。否則,預科學生結業(yè)后分流到本科專業(yè)再學習“大學語文”不就是一種重復?
二、現(xiàn)行語文教材疑點
1.編寫范式的陳舊。魯迅先生在高度評價《古文觀止》時說:“選本所顯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教材作為教學內(nèi)容的重要載體,直接關系教學目標的實現(xiàn)。普通高等學校少數(shù)民族預科《大學語文》教材編寫的指導思想是“致力于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yǎng),提高民族學生正確理解和運用漢語言文字的能力,體現(xiàn)時代性、基礎性和教科書內(nèi)容的綜合性,重視積累、熏陶和培養(yǎng)語感,使學生掌握學習語文的基本方法、養(yǎng)成自學語文的良好習慣”。從本教材編排的指導思想上可以看出,教材缺乏特色,或者特色不鮮明。在高校少數(shù)民族預科教育階段,語文教學目標是突出語文的“工具性”、突出“人文精神”,還是“工具性”與“人文精神”并重?似乎都重要,但落實起來都虛空。因此,教材編排的體例是以文學史為結構主線,將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域的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文體串聯(lián)起來,形成直線平列式結構。再將所選文章加上解題、注釋、閱讀要求和簡析。這一體例有明顯的局限。它以文本的類型來編排,易把注意力投注到作品的形式上,突出語文的“工具性”,與大學中的寫作課接近,缺乏“人文精神”的培養(yǎng)。它雖然也注重能力培養(yǎng),但優(yōu)美文章的思想啟迪、道德熏陶、文學修養(yǎng)、審美陶冶和寫作借鑒等多方面的綜合效應未突出,也難以充分發(fā)揮出來。況且所選文章看不出編者獨到的“審美發(fā)現(xiàn)”,多是各種《大學語文》中常選的經(jīng)典之作。文章的注釋和簡析有現(xiàn)成的摘錄,突出了“編”而不是“寫”,“輯”而不是“述”的特征。預科語文教材一方面要按照本課程的內(nèi)在邏輯組織編選,另一方面要根據(jù)預科學生認識過程的客觀規(guī)律來組織選文,前者是教材選文的邏輯順序,后者是受教者的心理順序。心理順序是始,邏輯順序是終。二者互為一體,是實現(xiàn)教學目的的基礎。
2.教材編排結構不合理。高校少數(shù)民族預科學生都來自于內(nèi)地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邊遠的林區(qū)、牧區(qū)和邊疆自治區(qū)。他們的漢語基礎不盡相同,有的相差很大,特別是高考民考民的學生,漢語基礎更差。對中國的文言文很難理解,更難把握。在教材的編排結構中,首先就是中國古代文學部分,這一部分遴選了文言文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分4個單元選文41篇,占整個教材篇幅的42%,這種編排不適合學生的心理接受規(guī)律,是“無對象”、接受主體“不在”“沒有自我”的表現(xiàn)。一開始讓學生接受難學的古文,會使學生在心理產(chǎn)生畏懼感,一旦教師在教學方法上處理不當就更容易使學生產(chǎn)生厭學情緒。這種“主體性欠缺”必然會導致民族預科語文教學的低效甚至無效。因此,在文本的遴選上要先易后難,應有意傾向現(xiàn)代文,充分尊重少數(shù)民族預科學生的接受心理和學習習慣。
三、教材編寫的創(chuàng)新
1.教材編寫理念的創(chuàng)新。高校民族預科班是我國高等教育的特殊辦學層次,民族預科班的語文教學既不是“高四語文”,也不是高校中文系的文學史的“壓縮版”。在編寫教材的過程中,要緊緊抓住高校少數(shù)民族預科班語文課程的性質(zhì),深刻理解預科中“補”“預”的內(nèi)涵。“補”主要是夯實民族預科學生的漢語言基礎知識,提高基本技能,同時民族預科教育是本科教育前的適應性學習階段,這個階段的語文教學應加強學生的“人文精神”的培養(yǎng)。王建華教授認為預科階段的語文教學教育重點應放在對學生語文學習興趣培養(yǎng)和學習方法的傳授上。因此,在編寫預科語文教材時既要突出“補”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又要體現(xiàn)“預”的美育性。
2.教材編寫模式的創(chuàng)新。自從1992年全國使用統(tǒng)編的民族預科班語文教材的編排模式以來,多少受全國高校《大學語文》傳統(tǒng)編寫模式的影響,在編寫體例上往往是以文學史為結構線索體例;這種模式編寫的教材主要以時間為線編排文章,其優(yōu)勢在于條理清晰、系統(tǒng)性強,但弊端在于在教學過程中很容易將民族預科班語文課上成中文本科生的文學史專業(yè)課,讓民族預科學生聽起來一頭霧水,不知所云。如果以單元主題為結構體例,在教學過程中就能突出主題,提高學生的鑒賞能力和審美能力,但忽略了學生漢語言基礎知識的鞏固。筆者認為應以各個時期、各個地域的主要文學體裁中的經(jīng)典性文章為主線,編織民族預科語文教學知識網(wǎng)絡結構。文學作品與文學史是密不可分的,沒有作品的文學史是空洞的文學史,沒有文學史的作品是缺乏時代感的作品。要在語文教學過程中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讓學生在“補”中提高,在“預”中拓展。
3.教材選文的創(chuàng)新。所謂“經(jīng)典”主要體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文學性與思想性的統(tǒng)一。所謂文學性就是文學文本有別于其他文本的本質(zhì)規(guī)定性。在羅曼·雅各布森看來:“文學研究的對象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即那個使特定的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北師大教授童慶炳先生對此有過論述:“我們今天應如何理解文學性呢?隨著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掀起的‘美學熱’的滾滾浪潮,使大家在討論中逐漸形成了文學的特性是審美的共識。這就是說,審美是區(qū)別文學與非文學的根本特征。”如先秦諸子散文的思辨哲理和道德修養(yǎng),屈原憂國憂民的情懷,陶淵明“心遠地自偏”安貧樂道的理想堅守,這些文人作品中包含厚重的文學性、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藝術性,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先賢們的文章應是教材選擇的重要內(nèi)容。
二是現(xiàn)代性與時代性的統(tǒng)一。所謂“現(xiàn)代性”是指社會變革時期人從傳統(tǒng)社會轉變?yōu)楝F(xiàn)代社會過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知識理念與價值標準。在文學藝術上,體現(xiàn)為對真、善、美的追求。無論是屈原的詩歌還是孔孟的文章都折射著先賢們富有哲理的思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打著時代烙印,彰顯著現(xiàn)代精神,歷久彌新。魯迅敢于向幾千年封建禮教挑戰(zhàn)的現(xiàn)代精神,與他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勇于探索精神,永遠激勵著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像王蒙的《活動變?nèi)诵巍贰⑼醢矐浀摹堕L恨歌》,或表現(xiàn)轉型時期新知識分子的深沉痛苦,或抒寫動蕩年代青年女性的無奈命運,都表達了某種刻骨銘心的人生體驗和深切的人文關懷,都是現(xiàn)代性與時代性有機結合的經(jīng)典范本。
三是漢族作家與少數(shù)民族作家作品統(tǒng)一。2013年修訂版的《大學語文》雖然在每個單元補充了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發(fā)展史,但所選的文本很少涉及少數(shù)民族作家作品。本套教材的施教對象是來自于全國邊疆牧區(qū)、林區(qū)和貧困山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學生,他們希望了解少數(shù)民族的作家作品,特別是本民族的作家作品。事實上,各個時期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家像一顆顆耀眼的星星,閃爍在中華幾千年的文學歷史長河中,璀璨而奪目,成為中國文學不可或缺的部分。元代詩人耶律楚材,明代文學批評家李贄,清代詞人納蘭性德,小說家曹雪芹,現(xiàn)當代作家中的老舍、沈從文、瑪拉沁夫、阿來、張承志、霍達、葉梅等都是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優(yōu)秀代表。他們或用漢文書寫或用少數(shù)民族文字創(chuàng)作,其優(yōu)秀作品豐富了中國文學寶庫。如果在文選中多一些少數(shù)民族作家作品,會增加預科學生的民族自豪感,更能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從中感受中華多民族文化的無窮魅力。
此外,從地域角度看,中華燦爛的文學歷史,不僅包括中國大陸文學還涵蓋港澳臺文學。但在修訂的《大學語文》中沒有提及該地域的作家作品,不得不說是一大缺憾。現(xiàn)當代的作家中,金庸的武俠小說、瓊瑤的言情小說、李敖的散文、余光中的詩文都是傳世經(jīng)典。
教材的編寫是一項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需要編寫者對課程性質(zhì)的準確把握和對教學目標的全面理解,體現(xiàn)了編寫者的指導思想、編排范式、文學視野、審美情趣。作為全國高校少數(shù)民族預科現(xiàn)行唯一的通用教材,其地位和影響力是不言而喻的。我們相信,在今后的教學實踐過程中會有更多的同仁提出真知灼見,促進高校少數(shù)民族預科語文教材的建設。